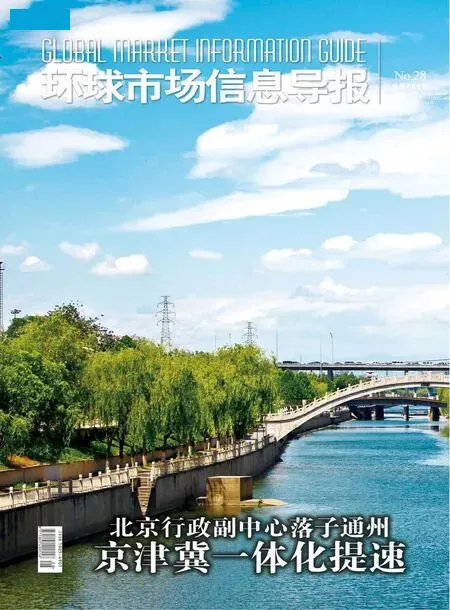那些年我们一起坐过的出租车
(文/小刀微微)
那些年我们一起坐过的出租车
(文/小刀微微)
Point
第一次去成都,就上演了“孤身一人冷雨夜吃火锅”的戏码。在双流那间明亮的火锅店里,连单份的芽菜猪肉包都有六只。

第一次去成都,就上演了“孤身一人冷雨夜吃火锅”的戏码。在双流那间明亮的火锅店里,连单份的芽菜猪肉包都有六只。可那天晚上,我不但越吃越长志气,还一个人去洗吹造型了一番,哼着小曲顶着一头飘逸潇洒的头发回到酒店。全天我统共只打了一辆车,司机路上几乎不怎么聊天。第一程从酒店载我到火锅店时,他把名片递给我,关照我用车时给他打电话就好。那个时代还没有打车软件,我过了很久以后才知道,成都是个很难打车的城市。
出租车司机是一群神奇的人。和他们交谈,有时好像探险,在真实与魔幻之间穿梭。曾经在路上和一位司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北京的798和宋庄。临了师傅说,很早以前他有一位做艺术掮客的老外客人,十分信任他,经常委托他运画。差不多也是那么早以前,我的朋友H君第一次离境前往某特区,看什么都新鲜。当地车辆均为右舵驾驶,而H刚考完驾照,从手排挡的教练车里解放,上了出租车就感叹:啊,这里的出租车都是自动挡啊。司机没说什么,只是深深地看了一眼H。那沉默的一瞥,让H君从那刻直到现在,都对那座城市没有好感。
比起能言善道的京城“的哥”,大上海的出租车厢显得安静和缺乏互动。有次一位女强人朋友想在车上补觉,结果遇到一位特例司机,一路喋喋不休,还会在等候红灯的电光火石间,回头和我那位昏昏欲睡的朋友做“眼神交流”。坐过几千次出租车后,我发展出一套登车程序:侧身落座后排右手座位,向司机问好,报目的地,系安全带。报地名的时候,哪怕司机并没有回头,我也微笑如常;司机不熟悉目的地,我打开手机导航找路线;安全带再脏,也照样扣好。如果有强迫症乘客的评选,我定能稳进前三。
全球打车最贵的城市里,我也严格执行此流程。稍有不同的是,在日本打车,乘客永远不用担心安全带是否会在白上衣上留下尘印。伦敦的司机大叔们则永远在读报纸:早上,中午,晚上。
当然凡事都有例外。有一次我顾不得打车流程,跳上车就开始痛诉自己的遭遇:晚上22点半加班、苦守酒店门口打不到车、狂风肆虐、手机没电、穿着窄裙和7厘米的高跟鞋,电脑包里还塞了不少死沉的资料,披头散发蹒跚北行……说得我当场泪水都快要掉下来了,司机一句话让人莞尔:“那我们俩太有缘分了!”
除了这个有缘人,最让人开怀的就属台北的一位司机师傅了。在那座绿意盎然、安静缓慢的城市,行车遵守交规,很少看到警察协调秩序,车与车之间懂谦让,不鸣笛。但那位台北司机却长叹一口气,嗲嗲地说:“这里开车太难了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