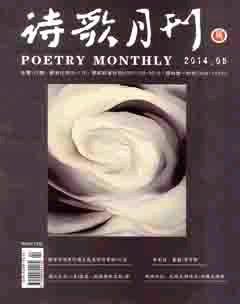苏家立的散文诗
苏家立
淹水的那天
水就这样从门缝下踱进来了,没和玄关的招财猫打声招呼。它们是饥渴的种族,吸干了每一片磁砖的颜色,留下透明的一层薄膜,仿佛罩在脚踝的面具,逼得脚趾甲里的污垢,不得不思考怎么漂白自己。
我拿出一张张乐谱铺在地上,省去替那些音符浇水的麻烦,而厨房的热水刚好烧开,野蛮的蒸气在眼镜上吐出一片森林。我戴着它,等发芽的音符爬到我要的高度。
从皮包里掉出几枚硬币,它们泡在水中,像是许愿池的切片,在大灯的显微下默默不语。我按下摇控器,而电视没有反应。水会退的,当我眼中的海,终于能溺毙一条纸做的金鱼。
门口的那只猫儿,它不断对我招手,而水逐渐通常是一整群离去的。
自杀者
被发现躺在浴缸时,他正试着进化成淡水鱼,嘴巴一开一合,红色的水不停冒出。几个小时前,他一个人在小钢珠店里,好不容易中了大奖,一颗颗油亮的珠子哗啦哗啦从机器嘴巴吐出,其中一颗掉进了公文包,另一颗掉到某位小姐的鞋跟下。
在公司,像一包随时可撕开的速溶咖啡,或许等着Z,或许是A,而今天送来了新的咖啡研磨机,但他是最后一个知道。穿着黑色套装的小姐故意踩住珠子,他嘴巴一开一合,体内的粉末还没有倒干净。
报警的是B,搬来对面已有一段日子,曾经和他去过酒店只是他不记得。
削皮
我知道他喜欢吃苹果,偶尔会切片泡在盐水里,但大多时候连皮一起吃,只留下孤伶伶的果核,像他背着妻子站在我家门前两三个小时。
用纤细的背看着他双眼递来的谎言,拿着钝掉的水果刀,我一个人在流理台削着心脏般大小的苹果,一圈又一圈,小心翼翼解下那条裹着青春的红色围巾,水声哗啦哗啦流着,我觉得自己的脖子空荡荡的,没有云肯从这样的悬崖坠落。
他以粗暴的方式脱掉了我的衣服,餐桌上削好的苹果一片也没动。今天的天气并不适合泡盐水,但牙龈有伤的他,只知道我腋下泌出的月光,有一点点危险的微酸。
苹果皮躺在砧板仰望厨房没关的灯,如果红算是一种正面。
书写
桌面有许多条河流,其中一条在灯光下显得有些年轻,我铺上一张薄纸,让手中的笔练习在岸上呼吸。
铅笔写出钢笔的痕迹,那不是我期待的泳姿。换了张纸,继续写字,直到铅笔把我写坏。灯光一闪一灭:[你才是最该被换的。]我恍然大悟,静静躺回床铺,拼命用黑夜擦着自己的尖锐。
隔天起床折棉被时,我连自己的黏液也弯曲了,阳光一照浮现了一些字,也许适合弹涂鱼产卵,孵化时我正在洗衣机旁,削着自己有霉味的脸。
剪指甲
他坐在镜子前,帮另一个人剪指甲。她的手指很细很长,像搁在图画纸的粉蜡笔,轻轻一折就断,剖面的颜色可能是亚麻色的。喀嚓喀嚓,指甲一片一片掉在光滑的磁砖,她不觉得痛,只觉得冷,而窗外慢慢收回了铺在客厅里的月光。
喀嚓喀嚓,满地散落着不再发亮的白屑,他不打算拿出口袋里黑色的指甲油。把地面的指甲扫一扫倒到窗外,天空又会亮了起来,她动了动十根指头,替镜外的人画上新的黑夜,指尖流出疲倦的街道和一扇扇被敲打的门。
指甲里的脏东西都到了镜子里头,他拿着指甲剪,开始替自己剪指甲。
牵线
牵着一条电线,我必须保持双手干燥。马路上的脚印大多是导电的,有的害怕月光,有的习惯风吹。我走到某面墙下,把手上的线插入角落的洞。我的瞳孔映出了墙后房子里的情景,一对夫妻开开心心吃着晚餐,他们没有孩子,养了一只看起来不灵光的柴犬。
突然降下大雨把柏油路烧成荒土,整座城市是一颗没充饱的电池,每个家庭有属于自己的线路,插在只有他们懂的插座,触电也不关别人的事。
我拔出电线,在原地等待放晴。
欺之以圆
那个呼拉圈从很久以前就躺在那里。有时,会有小朋友跳进又跳出,却没有人小心翼翼把它拿起,靠回油漆正在剥落的墙壁。
雨季来时,连脚印都会莫可奈何地消失。呼拉圈捧着一摊水渍,静静地望着习惯说谎的乌云,听它抛掷雨滴的声音。当积水溢出圆的拥抱时,弯曲的手臂缠不紧一条缎带。
无法等到满月纵身坠入。呼拉圈里,向来捆绑的是黎明后的黑夜,只有大人的腰身能轻轻转动。
然后留下公车站牌未干的油漆,终点不甚明确。
流浪
为了将流浪别上蔷薇,他把刺当成是自己的行李,一生都不曾放下。
直到从镜子发现自己是蓝玫瑰,他开始相信雨季能使他褪色,像当初把刺种在他怀里的女孩,即使园艺差强人意,还是把该插的枝,留在应岔出的地方。
那是怎么离开家乡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