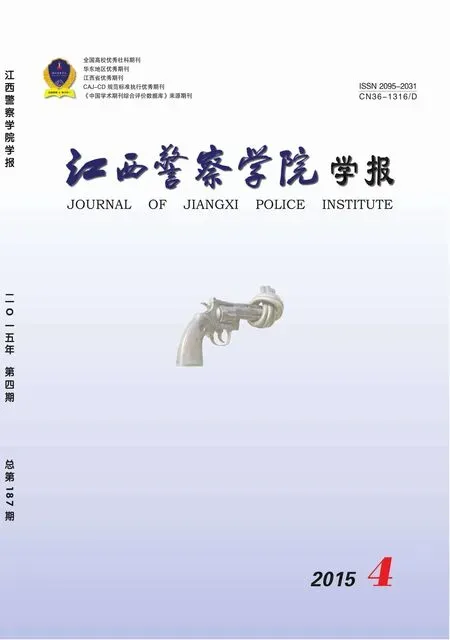“吊模斩客”式诈骗罪的分析
姜良浩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 400031)
对于生活中常见的“吊模斩客”行为,如果在行为过程中不存在暴力、胁迫等,司法实践中往往将其定性为诈骗罪。但是在承认结论正确的前提下,我们应当看到这些判决还需要更深层次的理论支撑。本文将从实践出发,对“吊模斩客”式诈骗罪认定中的两个关键问题进行分析和论证。
一、“吊模斩客”式诈骗罪的特征及司法现状
所谓“吊模斩客”,源自上海方言,是指以非法牟利为目的,在公共场所引诱、介绍、滋扰或者招揽被害人到特定的场所,伺机采取诈骗、敲诈勒索、强迫交易等非法手段迫使被害人以明显高于市场的价格进行消费的违法犯罪行为。
“吊模斩客”在生活中较为常见,普遍存在于酒吧、咖啡馆、KTV等消费场所,其犯罪团伙具有精细的内部分工。一般来说,以场所的负责人为中心,由“键盘手”通过网络聊天,以恋爱、交友、一夜情等虚构的借口骗取男性网友信任并约其见面,然后将信息传达给“传号手”,“传号手”整理信息并派遣“酒托女”与男性网友见面并将其引入特定场所进行消费,结账时亮出天价账单,使客人在女性朋友面前碍于情面不好推辞而付款,甚至直接采取暴力、威胁等方式强迫付款。由于“吊模斩客”成功率高,非法获利数额大,而且受害人往往碍于情面不会报警,因此给此类案件的发现和取证都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导致其成为生活中频发的一类违法犯罪行为。[1]
首先应当明确的是,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吊模斩客”行为并非单一罪名所能概括。从现实状况来看,被害人最后处分财产的具体状况不尽一致,被害人可能是在一系列的欺骗下主动处分财产,也可能是不愿付款从而遭到恐吓、威胁,甚至是直接暴力取财,这些情况分别可能构成诈骗罪、敲诈勒索罪和抢劫罪。笔者通过北大法宝的案例数据库,以“吊模斩客”为全文关键词,共搜集到21起相关刑事案例。其中以诈骗罪定罪的有7起,敲诈勒索罪定罪的9起,抢劫罪定罪的5起。
可见,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吊模斩客”的行为,如果在行为过程中以暴力、胁迫等方式强迫被害人进行付款,则构成敲诈勒索罪或者抢劫罪,而对于除此之外的其他“吊模斩客”,则一概以诈骗罪进行定罪。这几乎已成为司法实践中的通说。
二、司法实践存在的两个问题及其理论探讨
经笔者的查阅,在相关诈骗罪的认定中,法院在判决书中只是简单援引诈骗罪的罪状予以定罪,并没有进一步的解释和说明。例如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在一起判决中指出:“本院认为,被告人周某某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可见,判决书仅对其行为过程做了描述,却没有就关键问题进行论证。当然,也有司法实践人员针对此类案件进行过阐释。例如,“被告人以骗取被害人财物为目的……使被害人产生错误的认识和判断,自愿处分财产,应以诈骗罪定罪处罚。”[2]“行为人先安排女青年通过网络等方式搭识被害人……消费活动自始至终都充满了欺骗,被害人支付账单也是在受骗的前提下所为,因此,符合诈骗罪的要件。”[3]这些表述看似合理但是仍然没有涉及关键问题所在。
实际上,“吊模斩客”作为一类诈骗罪是有其特殊性的。其行为模式可以分为“吊模”和“斩客”两个环节,前者是指以虚构借口约男性网友见面,后者是指利用各种手段使其高额消费。从两个环节的不同状况来看,“吊模斩客”式诈骗又可分为两种类型,即单一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和双重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4]前者是指仅仅通过虚构借口将男性网友引入特定场所高消费,但所消费产品本身货真价实,或者虽然价格稍有提高但达不到欺诈的程度。后者是指不仅通过虚构借口将男性网友引入特定场所,而且所提供的消费品也存在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行为,例如将假酒伪装成真酒,将低档酒伪装成高档酒。根据笔者的案例收集与分析,在司法实践中,这两类情况都是以诈骗罪进行定罪的。
在双重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情形下,认定为诈骗罪是容易理解的。因为所消费的酒水存在假冒行为,致使男性网友陷入错误认识,并在其支配下付款造成财产损失,显然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但是对于单一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情形,笔者认为在错误认识和财产损失两方面存在认定上的难点。下面将分别对其进行论述。
(一)错误认识的实质化理解
在“吊模斩客”式诈骗罪中,有一种错误认识是必然存在而且贯穿始终的,那就是“酒托女”对男性网友所虚构的恋爱、交友、一夜情等见面理由,而在后续的消费环节,是否存在错误认识则并不确定。在前述单一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情形下,仅仅是“酒托女”引诱男性网友进行消费,所消费产品本身并无假冒情形,在消费环节本身就不存在错误认识。将其定性为诈骗罪,意味着司法实践中是将男性网友所陷入的“酒托女”将与之交友的错误认识定性为诈骗罪的错误认识,这种定性是否合理,还需要我们进行诈骗罪中错误认识的实质化理解。
诈骗罪中的错误认识,是指由于行为人的欺骗,使受骗者对客观事实的认知产生偏差,在这种错误认识的基础之上,将财产按照行为人所希望的方式进行处分。例如,认为自己所有的财产为他人所有,认为自己处分财物之后对方会按时予以返还,认为自己处分财物之后会获得相等甚至更大的回报等。基于这种心理,受骗者其实是“自愿”地处分财产。对于诈骗罪中的错误认识,笔者认为应当从两个方面进行理解。
1.应当从概念上理解错误认识的本质
我们不妨先从诈骗罪在财产犯罪中的类型划分来理解。在取得型财产犯罪中,可以分为夺取型与交付型,前者是指违反被害人的意志而取得财产,如抢劫罪、抢夺罪、盗窃罪,后者是指利用被害人的意思瑕疵而取得财产,如诈骗罪、敲诈勒索罪。[5]可见,诈骗罪是利用被害人意思瑕疵进而取得财产的两类犯罪之一。但这两类犯罪其意思瑕疵的存在点是不同的。交付应当包括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两个方面。[6]敲诈勒索罪的意思瑕疵在于意志因素,而认识因素是正确的;诈骗罪中的意思瑕疵在于认识因素,而意志因素是真实的。因此诈骗罪中所谓的“自愿”处分财产,其实就是意志因素真实但认识因素有误的状态,这也就是诈骗罪所特有的错误认识概念的本质。正是这一点使诈骗罪得以与其他侵犯财产犯罪区别开来。
2.应当从行为过程中理解错误认识的特点
从诈骗罪的基本构造来看,诈骗罪中的错误认识应当导致被害人处分财产这一直接结果,所以我们首先应当对处分行为进行研究。处分在实践中一般体现为交付,在民法上,“交付是指物的出让人以物权变动为目的,把自己占有的物或物权证书交给受让人占有的行为”。[7]民法上的交付需要交付意思毫无疑问,但刑法上的违法性与其他法律上的违法性存在区别,[8]诈骗罪中的处分是否需要处分意思,在理论界存在必要说、不要说和折中说。[9]笔者赞同必要说,如果被害人不是在处分意思支配下做出处分行为,那么行为人往往构成盗窃罪而不是诈骗罪。[10]
处分意思不仅必备,还应当是由错误认识所直接导致的。也就是说,受骗者是否是“基于错误认识”做出处分财产行为,其判断标准就在于,该错误认识是否直接导致了处分意思的产生,进而在其支配下作出处分行为。
在单一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情形下,男性网友所陷入的“酒托女”要与之交友的错误认识,是否导致了其处分财产的意思呢?笔者认为,在一般社会观念中,女性网友约会见面,就传达出一种默示的信号,即男性支付见面所需的必要费用是理所当然的。当然也有人认为,男性网友多是被不正当的见面动机冲昏了头脑,因而主动选择了付款,而犯罪心理学认为,侵害对象是影响犯罪人形成犯罪动机的情景因素,[11]因此,男性网友作为有责的侵害对象应当自己承担相应责任。
要驳斥这种观点,需要深入揣测男性网友的心理活动。一般来说,男性网友接受“酒托女”的见面请求,都是怀有一定的目的,即满足自己恋爱、交友甚至一夜情的目的,这其中不排除可能包含贪图美色等不正当动机。但是一方面,通过网络认识女性朋友最后发展至恋爱、结婚的现象在当代社会已经屡见不鲜,并无不妥;另一方面,即使我们认为一夜情等行为存在某些道德上的不正当性,这种不正当性也完全无法与犯罪行为相提并论。我们不能以道德上的压力否认“酒托女”的欺骗导致了男性网友陷入错误认识进而实施高额消费这种因果关系的存在。况且,在很多案例中,几乎所有的消费行为都是由“酒托女”主动完成的,包括选择酒吧、点昂贵酒水,如果男性网友没有陷入“酒托女”要与之交友的错误认识之中,是绝对不可能不表示反对的。这种情况下,实际上“酒托女”是通过使男性网友陷入自己要与交友的错误认识而达到将其财产据为己有的目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酒托女”所虚构的见面理由与男性网友高额消费之间的因果性和连贯性是合乎情理的。因此,即使在消费环节不存在欺诈的情形下,仍然可以把“酒托女”所虚构的见面理由使男性网友所陷入的错误认识作为诈骗罪的错误认识来看待,男性网友正是因为陷入了这样一种错误认识,所以做出了不阻止“酒托女”消费昂贵酒水的行为,从而处分了自己的财产。
(二)财产损失的实质化理解
在单一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情形下,男性网友所消费的酒水并不存在假冒情形,在经济价值上与其所支付的金钱是对等的,或者虽然认识到了假冒的存在,却基于在女性朋友面前的尊严而自愿付款,而公民对于自己的财产是有承诺和放弃权利的,如此看来,这种自愿性似乎也能够阻却财产损失的存在。没有财产损失也就没有法益受到侵害,也就不存在犯罪,因为犯罪的本质就是侵害法益。[12]而司法实践中把这些情形都认定为诈骗罪,说明这些情形下都是认定存在财产损失的,这无疑对传统的财产损失观念提出了挑战,需要我们进行诈骗罪中财产损失的实质化理解。
虽然我国通说认为构成诈骗罪应当具备财产损失这一要素,但是在刑法条文中并无直接体现,因此关于财产损失的理论研究也较为缺失。在理解财产损失的时候,我们可借鉴德国刑法理论进行比较。
德国刑法理论中,存在整体财产减少说和个别财产减少说的观点争锋。整体财产减少说认为,诈骗罪是对整体财产的侵犯。是否存在财产损失的判断标准在于受骗者的整体财产是否减少。具体判断方法为,将行为人取得的财产与提供的对价进行经济上的比较,如果前者高于后者,则认定受骗者存在财产损失,反之则不存在。
而个别财产减少说则认为,诈骗罪是对个别财产的侵犯。存在财产损失并不意味着受骗者的整体财产呈现出量上的减少,只要行为人的欺骗行为导致受骗者没有通过处分财产实现其预设的目的,就应当认定为存在财产损失。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可能向受骗者支付了与其所处分财产价值相当甚至更高的对价,因此受骗者的整体财产并没有实际减少,但是由于行为人所虚构的事实,导致这种交易对受骗者来说没有意义,所以这种看似公平的交易也应当认定为诈骗罪。因为诈骗罪侵犯的法益并不是财产主体或者对象本身,而是财产主体与对象之间的现实关系。当行为人的欺骗行为导致被骗者所期望的目的没有达到时,实际上就造成了所处分财产的无效,进而可以认定为财产损失。[8]例如,医生谎称就诊者患有急症,并趁机销售昂贵药品。如果药品本身货真价实,则就诊者并不存在财产上的减少。但是,医生的欺骗导致其购买的药品对自己没有价值,此时应当认定就诊者存在财产损失。医生给付的药品这种对价,并不影响财产损失的认定。
对于上述观点,笔者比较赞同个别财产减少说。即对于财产损失的判断,并不是受骗者处分的财物和获得的财物之间简单比较,而应当从受骗者的交易目的是否得到满足来进行判断。在“吊模斩客”式诈骗罪中,我们不难发现,在单一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情形下,男性网友在“酒托女”面前所点的酒水与其所支付的价款价值相当,并不存在整体财产上的减少。此时,所消费的真实酒水可以认为是行为人所支付的对价。所以,考察男性网友是否存在财产损失,应当从个别财产减少说的理论出发,其关键在于明确其预设目的是否实现,从而判断此次交易对其是否具有意义。
而男性网友的目的究竟是为了最终实现恋爱、交友、一夜情等目的,还是仅仅让此次约会显得体面一点?这似乎具有不确定性。可能有人认为,交友是一个概率事件,并非任何消费活动譬如请客吃饭都能换来交友的成功。但是我们应当看到,不管男性网友的期待程度如何,其目的都不可能会实现,因为“酒托女”的“虚情假意”抹杀了男性网友与之交往的任何可能性,所导致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男性网友所消费的酒水完全超出了其所预设的目的。男性网友虽然是自愿付款,但却是在一个完全错误的心理状态的支配下完成的,就如同本来身体健康的就诊者受到欺骗以为自己患病而购买药品一样。酒水、药品等交易的对象,只是行为人用来达到诈骗目的所支付的对价而已。
综上所述,男性网友所实施的处分财产行为,是由“酒托女”所虚构的见面理由所致,与其所预想的处分目的大相径庭。因此,基于个别财产减少说的理论,虽然所点的酒水与男性网友支付的价款价值相当,但也应当认定为男性网友存在财产损失。
三、“吊模斩客”式诈骗罪对诈骗罪认定的启示
本文对“吊模斩客”式诈骗罪的两点关键问题探讨,对于诈骗罪的认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在对于错误认识的理解上,应当紧紧抓住错误认识引发处分意思进而导致处分财产这一特点
其中处分意思是一个关键衔接因素。它既可以防止将非诈骗罪错误地认定为诈骗罪,又可为某些认定上有一定难度的诈骗罪提供理论支撑。
一方面,如果错误认识并没有导致处分意思,那么做出的相应行为就不应当认定为处分财产的行为。例如,行为人在超市购物时,将照相机的条形码撕掉并塞进方便面箱子里面,售货员只收取了一箱方便面的价格,将方便面和照相机一起“处分”给了行为人。在这个过程中,售货员完全没有意识到照相机的存在,因此更没有将照相机交给行为人的处分意思,不符合由错误认识引发处分意思进而导致处分行为的行为构造,所以不能认定为诈骗罪。实际上,这属于完全违背被害人意思而取得财物,应认定为盗窃罪。[5]处分意思的存在,正对应了诈骗罪是利用被害人意思瑕疵取得财物这一特征,而不是完全违背被害人意思取得财物。
另一方面,对于某些错误认识和处分财产看似没有必然联系的行为,如本文所探讨的“吊模斩客”,如果在错误认识和处分意思的产生之间存在较为合理的因果关系,也可以认定为错误认识导致了处分财产行为,进而认定为诈骗罪。这一点前文已经详细解释,在此就不再赘述。
(二)在对财产损失的理解上,应当采用个别财产减少说而不是整体财产减少说
不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中,个别财产减少说都更为合理。行为人所支付的对价可以在量刑时有所考虑,但是不应当对罪名的定性产生影响。该理论不仅适用于诈骗罪,对盗窃罪、侵占罪等其他取得型的财产犯罪同样适用。例如行为人进入被害人的办公室盗窃了一部价值2000元的手机,同时将2000元现金放在桌子上,我们认为仍然成立盗窃罪,留下的2000元现金不能阻却盗窃罪的成立。因为对于手机来说,其作为财物的占有权已被侵犯,被害人已失去对其使用、收益等一切权利,即使行为人支付了相应的2000元甚至更多的现金,也完全无法弥补该手机作为一种特定财物的任何效用。总之,只要行为人使被害人失去了对个别财产的相应利益,就应当认定为具有财产损失。
综上所述,我国对诈骗罪的罪状规定较为简单,理论上也并没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很多判决都需要进一步的理论探讨作为支撑。笔者希望通过对“吊模斩客”式诈骗罪的两点关键问题研究,明确诈骗罪简单罪状之下所隐藏的实质构成要件,对实践中非诈骗罪的行为予以排除,同时对认定较为困难的诈骗罪予以理论上的支撑,从而能够对诈骗罪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1] 阮江占.“酒托”犯罪呈低龄化规模化趋势[N].法制日报,2012-10-12(8).
[2] 雷海峰.“吊模斩客”行为应如何定性 [J].中国检察官,2012,(10):46.
[3] 凌鸿.“吊模斩客”的罪名认定[J].人民司法(案例),2011,(6):16.
[4] 俞小海.“财产犯罪中被害人承诺效力的扩大化与财产损失的实质化”[J].政治与法律,2014,(7):44.
[5] 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162-889.
[6] 黄伯青,管勤莺,周孟君.“被害人自愿交付”是区别诈骗罪与盗窃罪的关键[N].人民法院报,2010-07-15(7).
[7] 张俊浩.民法学原理(上册)(第三版)[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417.
[8] 张明楷.论诈骗罪中的财产损失[J].中国法学,2005,(5):120-131.
[9] 刘明祥.财产罪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230.
[10]刘洋.对诈骗罪错误认识与交付意思的再思考[J].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院学报,2012,(5):66.
[11]罗大华,李德,赵桂芬.犯罪心理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47.
[12]张明楷.法益初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3.
——兼论“二维码偷换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