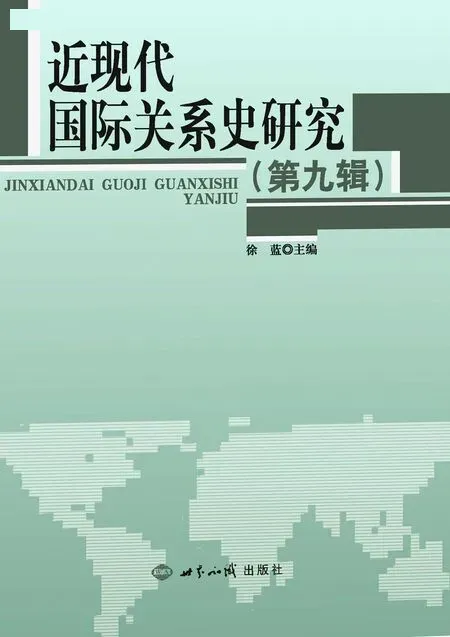欧洲流亡科学家、科学国际主义与英美核武器研发合作的肇始
史宏飞
20世纪30年代,纳粹的反犹、反智政策,破坏了业已形成的、跨大西洋科学共同体内自由、公开的氛围,也迫使欧洲大批优秀科学家流亡英、美。英、美科学家对欧洲同行的救援活动成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国际主义活动的典范之一。流亡科学家颠沛流离的经历和英、美同行的救援行动,激起了跨大西洋科学家共同体对于纳粹行为的愤慨。在发现铀元素的核裂变现象有可能应用于武器后,流亡科学家担心纳粹会利用核武器来奴役世界其他地区人民,这将与科学促进人类福祉的初衷相悖。他们利用跨大西洋共同体的科学家之间的联系,通过劝说英、美政府领导人关注核裂变研究,最终促成英、美政府的核研发合作。本文使用科学家回忆录、口述史、书信言论集以及英、美官方档案,试图从科学国际主义*按照克拉克·米勒(Clark A. Miller)的研究,科学国际主义(Scientific Internationalism,或者Science Internationalism)是指相信科学领域的国际合作会在很多方面促进更广泛意义上的国际和平与繁荣的理念。科学国际主义产生于18—19世纪的跨国科学活动之中。这种跨国科学活动包括两类:一类是出现于18—19世纪欧洲大陆的化学、医学等国际会议和跨国科学探索活动(天文观测、地理探索等),这些活动促进了科学家的跨国流动、专业知识的传播和生长以及人类对未知领域的探索和理解;一类是19世纪出现的为控制和预防霍乱、黄热病、黑死病、疟疾等流行病而形成的国际合作协议和国际卫生法规,这些国际合作依托于专业的医生和公共卫生专家团体进行疾病检疫、瘟疫控制等。及至20世纪,参与国际科学合作活动的主体逐渐多元,如科学家、学术团体、针对国际问题的(跨国)非政府组织以及国家政府等,科学国际主义的含义也逐渐丰富。大体说来,学术界主要从三个层面使用“科学国际主义”这一术语,或者说,科学国际主义包含三个方面的含义:第一,是指科学家共同体内部的一些原则和科学活动得以开展的规范,强调科学知识应该存在于自由流动、公开发表的环境中,不受现实国家疆界的限制,其生产和传承有自己的规律,即通过科学家的跨国交流与合作来促进人类社会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和理解。各种跨国的专业学会和科学家在科学研究方面的跨国交流活动集中体现了这种科学国际主义原则。这层含义与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提出的“科学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Science)”意义相近。第二,是对与跨国科学合作活动相关的思想与活动的概括。这种跨国科学活动包括三类:第一类是由超国家行为体发起,协调各个国家就某科学相关问题展开合作。如联合国气候大会协调各国进行有关碳排放的数据交流、技术共享等活动,这一类组织还有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第二类是由国家政府发起,向他国提供科技援助或与他国进行科技交流与合作,这类活动在20世纪后半期尤为突出;第三类是由科学家个人(团体)或(跨国)非政府组织发起,就某一科学问题召开会议,发表宣言,提出主张,以引起公众或各国政府的关注,以及推动政府层面的国际合作。不管是超国家行为体主导、政府主导,还是个人或者非政府组织主导,在具体的活动途径上,都依托科学家利用其专业知识进行跨国合作。第三,是指关于科学研究目标的信念,即认为科学研究的最终目标是为促进的角度对这一段历史进行考察,希冀能深化有关英美核武器研发合作历史的研究,并促进对科学与20世纪国际关系演进的理解。
一
受益于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一战之后,物理学等自然学科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深,大西洋两岸的科学研究交流日益频繁,与核物理相关的研究已经形成跨大西洋科学家共同体。当德国犹太科学家汉斯·贝特(Hans Bethe)①由于涉及的科学家较多,不便在注释里一一说明其相关生平,请参阅文后附件。在慕尼黑大学师从阿诺德·索姆菲尔德(Arnold Sommerfeld)研究物理学时,美国的伊西多·拉比(Isidor I. Rabi)、爱德华·柯登(Edward U. Condon)等青年科学家也来参与索姆菲尔德主讲的理论物理学专题课。1931—1932年,贝特在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下,先后访问了“原子物理学之父”厄内斯特·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领衔的剑桥卡文迪许实验室(Cavendish Laboratory)、意大利罗马大学恩里克·费米(Enrico Fermi)的实验室。*Interview of Hans Bethe by Charles Weiner on November 17, 1967, Niels Bohr Library & Archives, 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 College Park, Maryland, USA, http://www.aip.org/history/ohilist/4504_2.html. [2015-04-06].由于卢瑟福在原子物理学研究中的权威地位,剑桥卡文迪许实验室成为很多研究者眼中的圣地。包括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亨利·史密斯(Henry Dewolf Smyth)、马克·奥利芬特(Mark Oliphant)等在内的很多人都到卡文迪许实验室访问或工作过, “实验室中大概有一半人员是从国外来的,其中也有不少美国人”。*Interview of Sir John Cockcroft by Charles Weiner on March 28, 1967, Niels Bohr Library & Archives, 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 College Park, Maryland, USA, http://www.aip.org/history/ohilist/4557.html.[2015-04-06].从1924年到1930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及其支持的国际教育部(Rockefeller-backe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Board)共资助了135名欧洲科学家到国外做博士后研究,其中大部分资助给了德国、俄国和英国的科学家。有近三分之一接受资助的科学家选择在美国的科研院所从事研究,占据洛克菲勒基金会博士后研究资助的最大比例。*Charles Weiner, “A New Site for the Seminar:The Refugees and American Physics in the Thirties,” in Donald Fleming and Bernard Bailyn,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Europe and America, 1930-1960,Cambridge,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190-234,see p.196.科学家的访学,知名实验室的吸引以及非政府组织的资金支持,都极大促进了跨大西洋科学家共同体内部的知识交流和互动。科学家之间可以及时了解同行的最新进展,同时也通过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与同行分享,并启发新的研究,这些活动使科学国际主义理念进一步得到深化。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于1932年受邀访问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当时媒体报道认为,美国的科学将因为“移民科学家的到来”而繁荣,“科学移民”促进了“科学国际主义”。*“Science Internationalism Aided by ‘Scientific Immigrants’,” The Science News-Letter 22, no. 604 (1932),p.287.正如历史学家玛格丽特·高英(Margaret Gowing)所说:“(1939年以前的世界)依然是和平年代……知识的产生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程度:来自不同国家的科学家群体可能进行相似的实验,或者几乎同时实现理论跨越,所有的发现都自由发表,不会被刻意隐藏……国际主义在科学研究中依旧占据主导地位”。*Margaret Gowing and United Kingdom Atomic Energy Authority, Britain and Atomic Energy, 1939-1945,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64,p.33.
整个人类的福祉,而不是服务于狭隘的国家政策和国家利益。这一理念从科学国际主义活动出现时即已经确定,基本一直延续下来,存在于各种后续的科学国际主义活动中。克拉克·米勒关于科学国际主义含义的研究,参见:Clark A. Miller,“‘An Effective Instrument of Peace’: Scientific Cooperation as an Instrument of U.S. Foreign Policy, 1938-1950,”Osiris21, No. 1 (2006),pp.133-160;迈克尔·波兰尼有关“科学共和国”的研究,参见:Michael Polanyi, “The Republic of Science: It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Theory,”Minerva:AReviewofScience,Learning&Policy38, no. 1 (2000),pp.1-21;关于科学国际主义的部分相关研究可见:Sverker Sörli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Aspects of Cross-Boundary Science: Scientific Travel in the 18th Century,” in Elisabeth Crawford, Terry Shinn, and Sverker Sörlin(eds.),DenationalizingScience:TheContextofInternationalScientificPractice, Boston,MA: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3,pp.43-72; Robert A. Moore, “Medical Internationalism,”TheScientificMonthly61, No. 3 (1945),pp.173-180; G. Olague de Ros, “The Union Medica Hispano-Americana (1900)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Scientific Internationalism,”Dynamis26 (2006),pp.151-168; Joseph Manzione, “‘Amusing and Amazing and Practical and Military’: The Legacy of Scientific Internationalism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45-1963,”DiplomaticHistory24, No. 1 (2000),pp.21-55; John Krige, “Atoms for Peace, Scientific Internationalism, and Scientific Intelligence,”Osiris21, No. 1 (2006),pp.161-181;Cornelia Knab, “Plague Times: Scientific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Manchurian Plague of 1910/1911,”Itinerario35, No. Special Issue 03 (2011),pp.87-105; Zuoyue Wang, “U.S.-China Scientific Exchange: A Case Study of State-Sponsored Scientific Internationalism During the Cold War and Beyond,”HistoricalStudiesinthePhysicalandBiologicalSciences30, no. 1 (1999),pp.249-277,etc.
然而,纳粹上台后的一系列反犹、反智行为,打破了20世纪30年代的自由氛围,威胁到已经存在、并且不断深化的科学国际主义。
1933年,纳粹正式清除科教系统里有犹太血统的知识分子和异见者。由此,具有犹太血统的和一些不愿接受纳粹极权统治的科学家们开始了大规模的“洲际转移”。*李工真:《纳粹德国流亡科学家的洲际转移》,《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第143—164页。从德国开始,随着纳粹对其他国家的侵略,流亡科学家群体的规模不断扩大,最终导致欧洲大陆一大批优秀科学家流亡英、美,这其中就包括后来在英美原子弹研发和合作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奥托·弗里希(Otto Frisch)、鲁道夫·派尔斯(Rudolf Peierls)、利奥·西拉德(Leo Szilard)、尤金·魏格纳(Eugene Wigner)、爱德华·泰勒( Edward Teller)、詹姆斯·弗兰克(James Franck)和汉斯·贝特等人。
纳粹上台之初,利奥·西拉德就感到“反犹和反智主义情绪弥漫在大众演讲和报刊社论中”。在犹太人大规模流亡之前,他就逃往维也纳。*William Lanouette and Bela A. Silard, Genius in the Shadows: A Biography of Leo Szilard: The Man Behind the Bomb,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pp.114-116.之后,西拉德联系时任伦敦经济学院院长的威廉·贝弗里奇爵士(Sir William Beveridge,即后来的贝弗里奇勋爵)等人,成立了学术援助委员会(Academic Assistance Council),委员会的宗旨即是捍卫学术自由的价值和原则。*学术援助委员会(Academic Assistance Council),于1936年更名为保护科学和学术协会(the 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Science and Learning),并与1999年更名为危境学者委员会(the Council for At-Risk Academics, CARA)。Shula Marks, “Introduction,” in Shula Marks et al., In Defence of Learning: The Plight, Persecution, and Placement of Academic Refugees, 1933-1980s,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p.4.作为这个委员会工作的主要协调者,西拉德等人通过筹款来资助英国的科研院所提供临时岗位给流亡科学家。*William Lanouette, “A Narrow Margin of Hope: Leo Szilard in the Founding Days of CARA,” in Shula Marks et al., In Defence of Learning: The Plight, Persecution, and Placement of Academic Refugees, 1933-1980s,pp.45-57; Spencer R.Weart and Gertrud Weiss Szilard, Leo Szilard: His Version of the Facts, Selected Recollections and Correspondence, Cambridge,MA: MIT Press, 1978,pp.32-52.从1933年到1939年二战爆发,学术援助委员会共成功救援1500多名欧洲科学家。*除了学术援助委员会之外,参与救援工作的欧美机构还有洛克菲勒基金会(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国际救助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Rescue Committee)、社会研究新学院(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也称为 University in Exile)、美国教友会(American Friends Service Committee)、学者与医师紧急委员会(Emergency Committee for Scholars and Physician)、美国犹太人联合疏散委员会(American Jewish Joint Distribution Committee, JDC)以及国际联盟下属的知识分子合作部(Intellectual Cooperation Section)和国际学生服务部(International Student Service)等。在救援欧洲流亡知识分子活动中,这些组织之间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合作,见:Tibor Frank, “Organized Rescue Operations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1933-1945,”in Marks et al., In Defence of Learning: The Plight, Persecution, and Placement of Academic Refugees, 1933-1980s,pp.143-160; Charles John Wetzel, The American Rescue of Refugee Scholars and Scientists from Europe, 1933-1945,Ph.D.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1964.得益于跨大西洋科学家共同体的存在,在流亡前已经为英美同行所知的重要科学家成功流亡英美。如贝弗里奇勋爵所言,这些科学家“知道所有国家中他们同行的工作及其价值”。*Lord Beveridge, A Defense of Free Learning,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p.9.当时,哥本哈根的理论物理研究所(现已更名为尼尔斯·玻尔研究所)在尼尔斯·玻尔的主持下,也收留了大量欧洲流亡科学家。玻尔争取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等组织的援助经费,将这些流亡科学家送往英国、美国的科研机构,支持他们继续从事研究工作。*Victor Weisskopf, “Overview,” in Herman Feshbach, Tetsuo Matsui, and Alexandra Oleson, Niels Bohr: Physics and the World,New York: Routledge, 2014,p.7.这样一场跨大西洋科学家共同体内部的自救与互救活动,成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国际主义行动的典范之一。也正是因为颠沛流离的逃亡经历,使流亡科学家对纳粹的反犹、反智政策形成更大的愤慨,这为之后科学家以科学为工具战胜纳粹,避免人类遭受奴役埋下了伏笔。
二
跨大西洋科学共同体的学术交流,科学家之间的相互启发,共同推进了与原子弹研发相关的理论研究。恩里克·费米发现超铀元素存在的事实,启发奥地利物理学家利兹·梅特娜(Lise Meitner)和德国科学家奥托·哈恩(Otto Hahn)继续拓展费米的研究,并通过实验证实了使用中子轰击铀原子产生放射同位素的现象。而梅特娜又启发其侄子奥托·弗里希,通过实验验证了裂变以及裂变实验会产生大量能量的假设。*Margaret Gowing and United Kingdom Atomic Energy Authority, Britain and Atomic Energy, 1939-1945,pp.23-25.随后,弗里希将实验结果告知将要访美的尼尔斯·玻尔。1939年1月26日,玻尔在华盛顿第五届理论物理学会议演讲时提到关于裂变的新发现,激发了美国物理学界对这一发现的关注。他的演讲还没结束,就有很多科学家急匆匆赶往自己的实验室去重现弗里希的实验。*A. Pais, “Niels Bohr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hysics,” in Feshbach, Matsui, and Oleson, Niels Bohr: Physics and the World.p.20; Margaret Gowing and United Kingdom Atomic Energy Authority, Britain and Atomic Energy, 1939-1945,p.26; [英]奥托·弗里希:《残缺的记忆》,张昭里、余学工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04页。据统计,1939年这一年,发表在全世界物理学研究期刊上有关裂变反应的文章有将近一百篇。*Martin J. Sherwin, A World Destroyed: Hiroshima and Its Legacies, 3rd ed.,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p.17; Richard G. Hewlett and Oscar E. Anderson, The New World, 1939-1946: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 Volume I, University Park,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2,p.13.考虑到当时欧洲主要国家已经或者将要处于战乱之中,能够在短时间内出现这么多的研究成果,足以说明这项研究发现已经吸引了非常多的科学家。到1939年末,有关超铀元素、原子裂变的现象,都已经通过实验,得到基本验证。理论上已经可以认为,原子裂变存在被用作武器的可能性。*科学家已经设想裂变链式反应在理论上是存在的,但这只有通过较大规模的实验才能验证,需要花费大量资金。
这种可能性,引起了流亡科学家的警觉,他们担心如果纳粹掌握了这个研究,就可能将其极权统治扩张到世界其他地方。在一些科学家看来,原子裂变引发链式反应形成大规模爆炸,这种即便只有“极小可能”的事情,也会威胁人类生命。因为,10%的可能性都会让人“受到极大的刺激”, “希特勒的胜利会取决于它”。*Richard Rhodes, The Making of the Atomic Bomb,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8,pp.280-281.很多流亡科学家都非常恐惧纳粹首先造出原子弹,因为“欧洲的生活体验”使这些科学家“对纳粹有深刻的了解”。*Richard Rhodes, The Making of the Atomic Bomb, p.381.“假如他(希特勒)真的垄断了原子弹,那么,尽管他的经济力量还很弱,这个德国的独裁者也有可能奴役全世界”。*[德]罗伯特·容克:《比一千个太阳还亮:原子科学家的故事》,北京:原子能出版社,1991年,第49页。正是基于自身的流亡和失去国籍的经历,流亡科学家对纳粹的奴役和极权统治有比一般人更深刻的体会。在他们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本质上是一场自由与奴役之间的战争。跨大西洋科学共同体的存在所依赖的自由、开放已经遭到纳粹统治方式的威胁,如果纳粹掌握原子武器知识,利用原子弹奴役整个世界,那么世界范围内的自由、开放将不复存在。正如爱因斯坦在二战后呼吁对原子弹进行国际控制时所说,“我们帮助创造这种新的武器,是为了防止人类的敌人先于我们造出(原子弹)。考虑到纳粹的心智,如果纳粹(早于我们造出原子弹),那将意味着不可想象的毁灭和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奴役。我们将这个武器交于英美人民手中,使他们成为全人类的受托人,以及和平与自由的战士”。*“The War is Won, But the Peace is Not, December 10th, 1945,” in David E. Rowe and Robert J. Schulmann, Einstein on Politics: His Private Thoughts and Public Stands on Nationalism, Zionism, War, Peace, and the Bomb,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pp.381-382.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核科学家处于这场战争的最前线。其一,针对科学研究原则而言,他们要捍卫科学知识生产所需要的环境,确保跨大西洋科学共同体所需要的自由、开放;其二,针对纳粹可能使用原子弹奴役人类社会而言,他们要设法阻止其成为现实,避免让科学成为纳粹奴役统治的工具。这两个相互联动的目标,体现出科学国际主义的理念:科学知识的产生和积累需要维持跨大西洋科学共同体自由、开放的交流环境,促进人类社会对未知领域的认识和理解;科学知识并非某个政权或者国家进行奴役统治的工具,而是最终促进人类社会整体福祉的工具。
正是为了维护科学国际主义理念的目标,流亡科学家们利用他们的科学家网络,在大西洋两岸的美国和英国开始劝说同行谨慎关注核裂变研究,并游说政府关注和积极资助科学家关于裂变反应的研究。
首先,科学家采取措施避免那些服务于纳粹的科学家获知其他同行的最新研究进展。西拉德给当时还在法国的弗里德里克·约里奥-居里(Frederic Joliot-Curie)发信,主张有关铀裂变链式反应可能性的讨论最好“私下里与(目前住在)英国、法国和美国的科学家进行”,“就这一问题,目前先不要公开发表相关研究”。*“Document 29, Leo Szilard to F. Joliot, February 2nd, 1939,”in Weart and Weiss Szilard, Leo Szilard: His Version of the Facts, Selected Recollections and Correspondence.pp.69-70.
其次,科学家努力打通美国大学与联邦政府之间的沟通渠道,并争取到资金和设备支持,验证原子裂变链式反应的可行性。在当时的美国,大学科学家与政府之间基本不存在畅通的沟通渠道。*Laura Fermi, Illustrious Immigrants: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from Europe, 1930-41,Chicago,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p.183.1939年,美国海军部和海军实验室(Naval Research Laboratory)虽然注意到在哥伦比亚大学进行的裂变实验,但并未给予资助。*Hewlett and Anderson, The New World, 1939-1946: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 Volume I,pp.15-16.西拉德在美国物理协会(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见到海军研究实验室的技术顾问罗斯·古恩(Ross Gunn),表示希望海军部能够资助裂变实验,古恩对此反应冷淡。*“Document 52, Ross Gunn to Leo Szilard, July 10th, 1939,” in Weart and Weiss Szilard, Leo Szilard: His Version of the Facts, Selected Recollections and Correspondence,pp.89-90; “Document 1, Ross Gunn to Leo Szilard, July 10th, 1939,” in George T. McJimsey,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Franklin D. Roosevelt Presidency, vol.43:The Atomic Bomb, Development and Diplomacy,Bethesda, MD: LexisNexis, 2009,p.1.这一时期,英、美政府并不资助对核裂变的研究,大部分英、美本国科学家和官方也并不看好该研究的前景。*Sherwin, A World Destroyed: Hiroshima and Its Legacies,pp.18-19.而西拉德又是一位失去国籍的流亡者,难以取得政府官员的信任。*Leo Szilard, “Reminiscences,” in Fleming and Bailyn,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Europe and America, 1930-1960,p.111.西拉德转而向一些个人寻求资助。他在纽约的居所里见了很多银行家和商人,不厌其烦地向他们描绘链式裂变实验的前景,都未能成功获取资助。*Lanouette and Silard, Genius in the Shadows: A Biography of Leo Szilard: The Man Behind the Bomb,p.197.
此时,哥伦比亚大学提供给西拉德临时使用实验室的三个月期限已经结束,他通过计算得出石墨—铀系统的实验将很有可能成功。这让西拉德及其好友尤金·魏格纳非常担心纳粹可能控制比属刚果巨大的铀矿藏。两人找到爱因斯坦,计划利用爱因斯坦的国际声望,通知比利时政府,但三人此时都身处美国,又觉得通知比利时政府时最好先告知一下美国政府。*Lanouette and Silard, Genius in the Shadows: A Biography of Leo Szilard: The Man Behind the Bomb,pp.198-199; Leo Szilard, “Reminiscences,” in Fleming and Bailyn,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Europe and America, 1930-1960,pp.111-113.爱因斯坦此时也是第一次了解到这些研究的潜在影响。他们最终决定,以爱因斯坦的名义,直接致信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以便尽快引起美国政府的重视。这封信认为:“在不久的将来,铀元素可能成为产生能源的新来源”,“通过在大量的铀中进行原子链式反应,可以产生巨大的能量和与镭类似的新元素,现在的(研究)几乎可以确定这将在近期实现”。关于这种新现象的应用前景,这封信明确认为“这将导致一种新型的具有极大能量炸弹的制造”。信中建议,总统委托一人充当政府与在美国进行原子裂变研究的科学家们之间的联系人。联系人的职责包括:第一,通知政府有关研究的最新进展,为政府行动提供建议;第二,通过联系人与一些愿意资助的个人,或者与拥有足够设备的实验室合作,使当前受到大学实验室预算限制的试验工作加速进行。最后,信中提及在纳粹德国的一些科学家也在进行和美国一样的工作。*“Document 54, Leo Szilard to Albert Einstein, August 2nd,1939,” in Weart and Weiss Szilard, Leo Szilard: His Version of the Facts, Selected Recollections and Correspondence,pp.92-93.
这封信最终由亚历山大·萨克斯(Alexander Sachs)当面递交给富兰克林·罗斯福,并成功引起了罗斯福总统的注意。萨克斯是经济学家和银行家,与罗斯福私交甚好。1939年10月11日,在见到罗斯福时,萨克斯重述了西拉德、魏格纳、泰勒等人的研究工作及其前景,并建议他采纳爱因斯坦等人的建议。*“Document 6, Alexander Sachs to President, October 11th,1939,” in McJimsey,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Franklin D. Roosevelt Presidency, Vol.43:The Atomic Bomb, Development and Diplomacy, pp.20-21.罗斯福之后指派国家标准局(National Bureau of Standards)主任莱曼·布里格斯(Lyman J. Briggs)负责组建铀顾问委员会(Advisory Committee on Uranium,也称U委员会或者布里格斯委员会),就科学家提出的有关铀元素研究的应用问题进行全面调查。*“Document 10, Franklin D. Roosevelt to Albert Einstein, October 19th, 1939,” in McJimsey,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Franklin D. Roosevelt Presidency, Vol.43:The Atomic Bomb, Development and Diplomacy,p.26.10月21日,铀顾问委员会与西拉德、魏格纳、泰勒等流亡科学家进行第一次会议。西拉德在会议中阐述了氧化铀与石墨结合的系统中,链式反应的可能性。石墨作为实验催化剂,会俘获原子裂变反应所释放的中子,如果俘获率很低,那么链式反应就能形成(没有被俘获的中子会去轰击其他原子,形成链式反应)。如果能够获取俘获率的临界值(Intermediate Value),就可进行大规模实验。*Hewlett and Anderson, The New World, 1939-1946: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 Volume I,p.20.铀顾问委员会之后向罗斯福报告时认为,目前的铀裂变反应实验即便只是理论上存在“为潜艇提供动力”,或者“产生比任何已知炸弹更强大的摧毁力”的可能性,也“值得获取政府的直接财政支持”,并且建议扩大委员会代表数量,以便支持和协调不同大学之间的工作。*“Document 11, Lyman J. Briggs et al. to Franklin D Roosevelt: ‘Possible Use of Uranium for Submarine Power and High Destructive Bombs’, November 1st, 1939,” in McJimsey,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Franklin D. Roosevelt Presidency, Vol.43:The Atomic Bomb, Development and Diplomacy,pp.27-28.政府与科学家之间的沟通渠道正式建立。政府可以通过这个渠道获取有关铀裂变研究的进展,而科学家的资助需求也可以通过这个渠道反映给政府。
然而,这样的安排并没有产生令人满意的结果。随着欧洲同行研究成果的出现,局面变得更为令人焦虑。自11月铀顾问委员会的报告提交给总统的几个月后,科学家们一直未收到研究资助。西拉德后来回忆说“直到(1940年)2月1日,依然没有任何来自华盛顿的消息——至少没有给我消息。我本以为只要我们展示了(实验)……人们就不难感兴趣,但我想错了……我们还没有拿到购买石墨的钱”。*Weart and Weiss Szilard, Leo Szilard: His Version of the Facts, Selected Recollections and Correspondence,p.115; Lanouette and Silard, Genius in the Shadows: A Biography of Leo Szilard: The Man Behind the Bomb,p.214.与此同时,西拉德又得知法国约里奥-居里有关铀—水系统模型实验结果已经非常接近于链式反应。*Weart and Weiss Szilard, Leo Szilard: His Version of the Facts, Selected Recollections and Correspondence,p.115.如果纳粹得知约里奥-居里实验的消息,后果将不堪设想。
焦虑之中的西拉德又一次找到爱因斯坦,商议催促政府尽快采取措施。西拉德写了一篇关于铀—石墨系统中裂变链式反应的文章,投给《物理学评论》(PhysicalReview),“除非政府要求文章不要发表”或者“政府有意向采取更进一步的措施”,这篇文章就会发表出来。西拉德负责向刊物编辑说明投稿用意,爱因斯坦告诉萨克斯,请其将科学家研究的新进展和西拉德投稿的事情通知罗斯福,以此“要挟”罗斯福政府迅速采取措施。*“Document 71, Leo Szilard to John T. Tate, February 14th, 1940,” in Weart and Weiss Szilard, Leo Szilard: His Version of the Facts, Selected Recollections and Correspondence,p.118;“Document 75, Albert Einstein to Alexander Sachs, March 7th, 1940,” in Weart and Weiss Szilard, Leo Szilard: His Version of the Facts, Selected Recollections and Correspondence,pp.120-121.这次行动产生了一些实质结果:其一,联邦政府拨款6000美元给西拉德和费米所在的哥伦比亚大学继续铀—石墨系统实验;*Lanouette and Silard, Genius in the Shadows: A Biography of Leo Szilard: The Man Behind the Bomb,p.216.其二,罗斯福指示安排了政府代表和科学家之间的会谈。*“Document 18, Franklin D. Roosevelt to Alexander Sachs, April 5th, 1940,” in McJimsey,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Franklin D. Roosevelt Presidency, Vol.43:The Atomic Bomb, Development and Diplomacy,p.41.1940年4月27日,科学家代表与政府代表进行了座谈。之后,萨克斯向罗斯福再次提交了有关铀—石墨系统反应实验的新进展和建议。受益于6000美元联邦政府拨款,在哥大进行的实验有了令人非常满意的结果。科学家呼吁政府投入更大规模的资助,“铀事务已经具有不可拖延的紧急性”,需要有组织地开展规模活动,政府与大学之间沟通机构的工作应该更为高效、灵活,而纳粹对铀裂变的研究“似乎已经超过美国”。*“Document 31, Alexander Sachs to Franklin D. Roosevelt, May 11th, 1940;” “Document 32, Alexander Sachs to Lyman J. Briggs, May 13th, 1940;” “Document 34, Alexander Sachs to Edwin M. Watson, May 15th,1940;” “Document 35,Alexander Sachs to Edwin M. Watson, May 23rd,1940,” in McJimsey,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Franklin D. Roosevelt Presidency, Vol.43:The Atomic Bomb, Development and Diplomacy,pp.76-79,81-83.1940年6月,科学家的诉求终于在政府机构重组中实现。罗斯福指示成立了国防研究委员会(National Defense Research Committee,NDRC),由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担任主任,并将莱曼·布里格斯负责的铀顾问委员会重组为国防研究委员会附属的委员会之一。*“Document 41, Franklin D. Roosevelt to Vannevar Bush, June 15th, 1940;” “Document 42, Franklin D. Roosevelt to Lyman J. Briggs, June 15th, 1940,” in McJimsey,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Franklin D. Roosevelt Presidency, Vol.43:The Atomic Bomb, Development and Diplomacy,pp.96-99.至此,铀裂变研究正式成为政府支持的研究项目之一,至少可以与其他项目一起争取美国政府的资助了。
回顾这个过程,可以发现西拉德、爱因斯坦等欧洲流亡科学家,在游说美国政府关注并资助铀裂变研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即便这一时期联邦政府还没有将铀裂变研究看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紧急项目,其间也出现过政府官员对流亡科学家的不信任,但在半推半就之间,美国的铀裂变研究终于缓慢步入正轨。
与美国政府在这件事上的态度类似,已介入欧洲战事的英国政府也迟迟未能认识到铀裂变研究的军事应用前景,而是将大量的政府资源倾注给雷达等他们认为战事亟需的研究。最终,同样是从欧洲大陆流亡到英国的科学家们,促使英国政府改变了对铀裂变研究的态度。与美国不同的是,英国政府的态度转变很快,这也使英国的铀裂变研究,在一段时期之内超过了美国。
欧洲战事爆发之时,奥托·弗里希受马克·奥利芬特*马克·奥利芬特博士毕业于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师从核物理之父厄内斯特·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他是一个很典型的因为战争,接受政府要求转变研究方向的例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他从事的就是核物理的研究,欧洲战事爆发之后,他投身于英国的雷达研究。和美国一样,这些研究当时属于保密项目,不能由外国科学家参与,所以弗里希和派尔斯等流亡科学家得以继续进行他们的核物理研究。[英]奥托·弗里希:《残缺的记忆》,第110—111页。邀请,正在伯明翰访问。弗里希和鲁道夫·派尔斯计算出大概1千克的金属铀-235即可满足制造“超级炸弹”的链式反应要求。他们担心德国科学家也取得同样的研究进展。*[英]奥托·弗里希:《残缺的记忆》,第113页。二人写了一份备忘录,通过奥利芬特递交给英国政府。这份备忘录解答了有关铀裂变应用的几个关键问题:满足炸弹要求的最小重量;炸弹如何被引爆;如何分离铀-235;铀裂变引发爆炸产生的辐射危害,等。*The Frisch-Peierls Memorandum, 1940,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 ‘Super-Bomb’; Based on a Nuclear Chain Reaction in Uranium,” in Philip L. Cantelon, Richard G. Hewlett, and Robert Chadwell Williams, The American Atom: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Nuclear Policies from the Discovery of Fission to the Present, 2nd ed.,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1,pp.11-15.
备忘录引起了英国防空空战科学调查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the Scientific Survey on Air Defense and Air Warfare)的高度关注。一方面,委员会指派乔治· 汤姆森(George Paget Thomson)与奥利芬特等科学家就这个问题进行全面讨论,另一方面,委员会指示英国驻美国大使馆科技专员了解美国针对铀裂变研究的进展,得到的回复是美国科学家对原子裂变研究的应用并不看好。然而,英国政府并没有因美国的态度而降低对原子裂变研究的关注。*Margaret Gowing and United Kingdom Atomic Energy Authority, Britain and Atomic Energy, 1939-1945,pp.43-44.防空空战科学调查委员会设立下属委员会,组织英国境内的科研机构对铀裂变问题进行协作研究,这个委员会就是后来的玛德委员会(M.A.U.D. Committee),由汤姆森担任主席。*George Thomson, “Anglo-U S. Cooperation on Atomic Energy,” American Scientist 41, No. 1 (1953),pp.75-80.
初始阶段,英国也出现了对流亡科学家不信任的情况。由于弗里希和派尔斯是流亡科学家,玛德委员会刚设立之时,并没有通知他二人。但是,弗里希和派尔斯显然是很重要的科学家,因此,英国政府将玛德委员会转变为以政策建议为主的政策委员会,在其下又设立技术附属委员会(Technical Sub-Committee),这样就将政策研究和技术研究分开进行。弗里希和派尔斯的研究工作通过技术附属委员会处理,*Margaret Gowing and United Kingdom Atomic Energy Authority, Britain and Atomic Energy, 1939-1945,pp.46-47.从而让这些流亡科学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到了1941年夏,英国通过这种方式或者允许剑桥、牛津等大学聘用外籍科学家的方式,将大量的欧洲流亡科学家吸收进玛德委员会负责协调的铀裂变研究中。*这其中就包括在20世纪50年代参与发起帕格沃什科学与世界事务会议(Pugwash Conference on Science and World Affairs)的波兰科学家约瑟夫·罗特布拉特(Joseph Rotblat)。
由于英国政府支付所有参与铀裂变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工资以及实验经费,玛德委员会高效地协调各个大学、研究机构之间的工作,并且巧妙将流亡科学家吸收进铀裂变研究中,英国对原子裂变研究的进展非常之快。到了1941年春,弗里希和派尔斯备忘录中提出的几个有关原子弹制造的关键问题基本已经通过实验解决,“似乎铀-235炸弹将成为可以运输的武器,可以作为盟国的军备”。*Margaret Gowing and United Kingdom Atomic Energy Authority, Britain and Atomic Energy, 1939-1945,pp.52-70.英国的这些研究已经远超同期美国。1940年秋,亨利·蒂泽德(Henry Tizard)率领英国科学家代表团到美国访问,希望与美国同行进行交流时,却发现美国正在进行的大部分研究和实验要落后英国好几个月。*Septimus H. Paul, Nuclear Rivals: Anglo-American Atomic Relations, 1941-1952,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0,p.19.
美国的一些科学家也深知这一点。美国国防研究委员会成员卡尔·康普顿(Karl T. Compton)在抱怨铀顾问委员会效率低下时说:“即便我们拥有在数量上比英国多、质量上世界顶尖的核物理学家,英国同行(的研究进展)却已经远远超过我们”。*“Karl T. Compton to Vannevar Bush, March 17th, 1941,” Bush-Conant File Rel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tomic Bomb, 1940-1945, Records of the Offi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G 227, microfilm publication M1392,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Washington D.C., n.d. (ca. 1990). Digitalized by Center for Research Libraries. http://www.crl.edu.[Hereafter cited as Bush-Conant File Rel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tomic Bomb]. Scan Date: 3-05-2008. Identifier: m-b-000337-n2-f3.造成美国落后的原因除了铀顾问委员会本身效率低下之外,更重要的是美国政府对于铀裂变研究的态度还未彻底转变。虽然1940年6月份以后,铀裂变研究可以与其他研究项目竞争政府资助,但在资助铀裂变研究上,美国政府态度依旧暧昧。首先,与英国政府对所有参与铀研究的科学家和工作人员支付薪水、资助设备不同,美国政府此时还没有支付这些进行铀研究的科学家额外的薪水,科学家们只能依靠所在大学的薪水和实验设备进行研究。其次,政府的铀研究资助也不能满足研究需要。科学家们曾通过铀顾问委员会向国防研究委员会申请14万美元的经费,主要研究链式反应的临界值及其控制。两个多月以后,国防研究委员会只批准了4万美元经费。*“Lyman J. Briggs to Vannevar Bush, July 1st, 1940,” Bush-Conant File Rel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tomic Bomb, Scan Date: 3-05-2008,Identifier: m-b-000337-n2-f2; Hewlett and Anderson, The New World, 1939-1946: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 Volume I,p.27.这些资金根本就不够研究临界值反应。
总之,虽然英国和美国在接受流亡科学家有关铀裂变军事应用的劝说上面态度有快慢之分,但至少使两国政府都注意到铀裂变研究,开始有意识地资助或者部分资助铀裂变相关的研究。因此,流亡科学家的游说活动改变了铀裂变研究的地位,使其从一个政府并不看好的研究项目,变成了可以吸引政府高度关注、或者与其他项目一起争取经费的研究项目。
三
直到英国玛德委员会基于弗里希-派尔斯备忘录形成的《玛德报告》,正式传送到美国之后,罗斯福政府对待铀裂变研究的态度才正式彻底转变。
1941年7月,玛德委员会的成员们完成《玛德报告》并提交给英国战时内阁科学顾问委员会(War Cabinet’s Scientific Advisory Committee)。报告对铀-235制成核武器的实现方法、花费以及预期影响做了讨论,最终认为:“铀弹是可制成的,并会对战争结果产生决定影响;这项工作应以最高优先权继续,以便在最短时间内产出炸弹;与美国的合作应该继续和扩展”。*“Report by MAUD Committee on the Use of Uranium for a Bomb,1941,” in Cantelon, Hewlett, and Williams, The American Atom: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Nuclear Policies from the Discovery of Fission to the Present,pp.16-20.值得一提的是,报告中提到的“现阶段的与美国合作”主要还处于零星的对研究信息的分享和交流阶段,英美双方偶有一些科学家到对方的研究机构考察和讨论。战时内阁科学顾问委员会组成了一个国防服务小组(Defense Service Panel)对《玛德报告》进行数次讨论,认为“发展铀弹应该被当成第一等重要事务,应该采取所有可能的措施”。*Margaret Gowing and United Kingdom Atomic Energy Authority, Britain and Atomic Energy, 1939-1945,p.101.
就在英国国防服务小组讨论时,《玛德报告》已经通过科学家跨国关系网络传到美国,并引起了在美科学家的高度关注。先是美国国防研究委员会的物理学家托马斯·劳里森(Thomson Lauritsen)访英期间,参加了玛德委员会的会议,其时《玛德报告》的草稿已经出台。这个草稿不久就出现在华盛顿科学家的眼前;*Letter Lauritsen to Bush, July 11th, 1941, in footnote of James Conant, “A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an Atomic Bomb”, p.20, in Bush-Conant File Rel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tomic Bomb, Scan Date: 3-05-2008,Identifier: m-b-000337-n2-f3.其后,8—9月间,马克·奥利芬特又访问伯克利加州大学,奥利芬特与厄内斯特·劳伦斯(Ernest Lawrence)交流了玛德委员会正在开展的工作。劳伦斯将英国同行的行动告诉了时任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国家学术委员会(National Academy Committee)主席阿瑟·康普顿(Arthur Compton),并主张催促美国政府也应加速对这种炸弹的研究。*布什于1941年1月要求国家科学院组建了国家学术委员会,专门对铀研究进行评估,以确保在为罗斯福政府提供决策时更有说服力。Hewlett and Anderson, The New World, 1939-1946: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 Volume I,pp.33,38-39;Margaret Gowing and United Kingdom Atomic Energy Authority, Britain and Atomic Energy, 1939-1945,p.85.当10月初,《玛德报告》最终稿传到布什和詹姆斯·柯南特(James Conant)手中时,他们对英国同行的研究大为吃惊。*“G. P. Thomson to James Conant, October 3rd, 1941,” in Bush-Conant File Rel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tomic Bomb, Scan Date: 3-05-2008,Identifier: m-b-000337-n2-f4.在这封信后附有一份完整的《玛德报告》,完成时间标为1941年7月15日。布什随即派出哈罗德·尤里(Harold Urey)等著名物理学家到英国深入考察、了解情况,同时要求国家学术委员会对在美国进行的裂变研究进行独立评估。*“Vannevar Bush to Arthur Compton, October 9th, 1941,” in Bush-Conant File Rel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tomic Bomb, Scan Date: 3-05-2008,Identifier: m-b-000337-n2-f5; Hewlett and Anderson, The New World, 1939-1946: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 Volume I,p.45.
事实上,罗斯福政府的态度发生重要的转变之时,国家学术委员会的评估报告以及尤里等人到英国的考察报告都还没有出来。*国家学术委员会的报告完成于11月6日,报送罗斯福总统的时间在11月27日,尤里等人的访英报告完成于12月初。国家科学院召集了全美顶尖的物理学家和工程学家对美国正在进行的裂变研究进行了数次讨论,最终得出了与《玛德报告》类似,但不如其乐观的结论。“Report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by the Academy Committee on Uranium, November 6th,1941,” in Bush-Conant File Rel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tomic Bomb, Scan Date: 3-05-2008,Identifier: m-b-000337-n2-f5; “Vannevar Bush to the President, November 27th, 1941,” in Bush-Conant File Rel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tomic Bomb, Scan Date: 3-05-2008,Identifier: m-b-000337-n2-f5; “Preliminary Report to Dr. V. Bush from Professor Harold C. Urey relative to his Trip to England in Regard to the Uranium Problem, December 1st, 1941,” in Bush-Conant File Rel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tomic Bomb, Scan Date: 3-05-2008,Identifier: m-b-000337-n2-f5.所以,这种转变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美国科学家进一步系统论证的结果,而是大西洋对岸英国科学家的研究惊醒了罗斯福政府,使其对待铀裂变研究的态度彻底发生了转变。
布什10月9日和总统罗斯福、副总统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在白宫进行了一次讨论。会上,布什以《玛德报告》的内容向总统和副总统汇报了英国同行的研究。*这次会议没有留下会议记录,会议之后布什发给柯南特一份绝密备忘录。“Memorandum for Dr. Conant, October 9th, 1941,” in Bush-Conant File Rel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tomic Bomb, Scan Date: 3-05-2008, Identifier: m-b-000337-n2-f5.显然,英国的进展给罗斯福的刺激非常大,会议最终决定解散效率低下的铀顾问委员会,建立新的、负责原子武器研制的委员会,即后来官方机构中的Section-1 委员会。*由于国防研究委员会在资助与战争相关的科学研究上权限太低,无法有效协调相关研究中的军—民关系。1941年,联邦政府又设立了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Offi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OSRD),其主任可直接向总统汇报工作,并将国防研究委员会置于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之下。布什升任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主任,柯南特接替布什任国防研究委员会主席。美国原子弹项目在进入大规模试制研发,命名为“曼哈顿工程”之前,这个项目被命名为S-1部,直接隶属于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Background, in Bush-Conant File Rel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tomic Bomb, Scan Date: 2-01-2008, Identifier: m-b-000337-n1.这个委员会的成员由布什、柯南特、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Henry L. Stimson)、总参谋长乔治·马歇尔(George C. Marshall)以及亨利·华莱士(总统的个人代表)组成,其级别明显要比铀顾问委员会高出很多。会后,罗斯福让布什起草给英国首相丘吉尔的书信,谋求与英国在原子裂变研究的官方合作, “似乎我们应该迅速就贵国玛德委员会和敝国布什领导下的机构进行的研究进行合作,以便于进一步协调、扩展和共同推进”。*“Document 49, Franklin Roosevelt to Winston Churchill, October 11th, 1941,” in McJimsey,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Franklin D. Roosevelt Presidency, Vol.43:The Atomic Bomb, Development and Diplomacy,p.178.
鉴于英国此时研究的先进位置,丘吉尔政府似乎对罗斯福的提议并不太热衷。*直到收到罗斯福信件两个月之后,丘吉尔才回复罗斯福说,他已经安排英国相关科学家和美国科学家在英国的代表见面,讨论英美合作事宜。Margaret Gowing and United Kingdom Atomic Energy Authority, Britain and Atomic Energy, 1939-1945,p.123;Andrew J. Pierre, Nuclear Politics: The British Experience with an Independent Strategic Force, 1939-1970,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pp.26-27.但在双方科学家的促进下,英美之间还是进行了一系列有关原子裂变研究的合作。英美从事原子裂变的科学家之间的交流顺畅,合作程度不断加深。在美国的科学家也对英美之间的这种合作和交流非常重视,并希冀于不断推进。布什1942年4月致信英国原子武器研究项目参与者约翰·安德森爵士(Sir John Anderson)表示,他对英、美双方之间的合作“总体满意”,并建议确保英美之间进行“完全交流”。*“Vannevar Bush to Sir John Anderson, April 20th, 1942,” in Bush-Conant File Rel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tomic Bomb, Scan Date: 2-05-2008, Identifier: m-b-000337-n3-f2.正是通过与英国科学的交流和合作,美国有关原子裂变研究发展迅速,这成为二战时期英、美等国进行的原子弹研发合作的肇始。
其后在英美之间,针对是否合作、如何合作有过多次沟通和博弈,但最终在原子弹研发上面展开了深度合作。来自大西洋两岸的科学家共同在美国“曼哈顿工程”中,为了避免人类最终被纳粹奴役而夜以继日地工作,进行跨国科学研究合作,共同对抗极权对人类的威胁。
结 语
基于科学国际主义理念的影响,跨越大西洋的科学家们在促进英、美原子弹研发合作的肇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
首先,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受益于稳定的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的充足资助,跨越大西洋的美欧已经形成了良好的科学研究氛围。科学研究所需要和秉持的自由发表、公开讨论作为一种常态存在于跨大西洋科学家共同体中,科学家通过专业期刊、学术会议、国际访学等,践行着科学共同体内的科学国际主义理念,而这也是科学研究最基本的要求和原则,即:科学知识的产生、传播有其自身规律,不受现实国家疆界和政府统治的限制。而纳粹上台后的一系列反犹、反智行为干扰和威胁到了科学研究需要的自由、公开氛围,这激起了科学家对纳粹统治的恐惧和愤慨。得益于跨大西洋科学共同体,一大批优秀科学家通过自救或者互救流亡英、美,成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重要的国际主义活动之一,也为之后的铀裂变研究跨国合作提供了前提。
其次,跨大西洋科学家共同体内科学家们的相互启发,最终发觉了铀裂变应用的军事前景,而颠沛流离的经历使流亡科学家对铀裂变的应用更为敏感,他们担忧纳粹会使用原子武器奴役全世界人民,从而在大西洋两岸开始警示英、美政府。这正是科学国际主义的最高理念所在,科学是促进全人类福祉的工具,而不是某个国家或者政权制造奴役的工具。科学依靠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进行生产和传播,目的是为了关怀和促进人类整体福祉。至于国家或者政权的行为,流亡科学家只是依据它们利用科学知识的目的而选择支持或者反对。
再次,从英、美官方对铀裂变研究的态度转变和两国核武器研发合作的肇始来看,也得益于流亡科学家在大西洋两边的交流和游说活动。英国政府通过弗里希-派尔斯备忘录注意到铀裂变研究的重要应用前景。西拉德等流亡科学家在美国几次三番地游说活动,改变了铀裂变研究的地位。其后,通过跨国科学家网络传到美国的《玛德报告》,彻底改变了美国政府对待铀裂变研究的态度,而《玛德报告》内容又是以弗里希-派尔斯备忘录为基础的。最终,《玛德报告》的内容让罗斯福在美国国家学术委员会独立的评估报告还未出具之前,就意识到美国已经处于落后地位,并积极寻求与英国政府的合作。这是科学国际主义在国家政策层面上的体现,科学成为对外政策的工具,国家之间就某一科学问题,通过对外合作以加速达到目标。
综上,就本文的研究而言,这些促进英、美政府关注、资助并就核武器研发进行合作的流亡科学家,并非是因为他们本身效忠于英、美国家,而是他们从事科学所需的环境受到威胁,加之受自身流亡经历的诱发,敏感地意识到纳粹极权统治的奴役性质和核武器对人类文明的毁灭性,才游说英、美政府关注并投入核武器的研发,并最终促成了英美核武器研发合作的肇始。科学国际主义理念成为流亡科学家们行动的根源,也成为原子弹制造过程中和战后,一批科学家寻求核武器的国际控制、核禁试、核消减等具体主张的理念根源,即:科学并非是某个国家制造奴役或者发动军备竞赛、谋求世界霸权的工具,而是促进整体人类福祉的工具。
附:
本文所涉科学家生平简介
(按姓氏字母排序,依据维基百科英文版、相关传记、回忆录完成)
Bethe, Hans(贝特,汉斯,1906—2006)
贝特出生于德国,由于其母亲是犹太人,所以1933年纳粹上台之后,他就失去了在德国图宾根大学的教职,在阿诺德·索姆菲尔德的帮助下,暂时容身于英国,后来接受美国康奈尔大学物理系的教职邀请,一直待在美国。二战时期,贝特是“曼哈顿工程”技术部主任。1967年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Bohr,Niels(玻尔,尼尔斯,1885—1922)
玻尔出生于丹麦,他在原子结构和量子理论上有突出贡献。1922年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1933年纳粹上台时,玻尔利用自己创建的哥本哈根大学理论物理研究所,为流亡科学家提供临时工作,并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联系,为这些流亡科学家提供资助或者寻找合适的工作,经由玻尔援救的科学家有:奥托·弗里希、詹姆斯·弗兰克、利兹·梅特娜、爱德华·泰勒等人。由于玻尔的母亲是犹太人,纳粹1943年开始搜捕玻尔。在丹麦反抗军的帮助下,玻尔逃亡至瑞典,最终又由英国空军将其接到英国,参与英国的原子弹研发项目。
Compton,Arthur H.(康普顿,阿瑟,1892—1962)
美国核物理学家,192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1941年,国防研究委员会主席万尼瓦尔·布什任命阿瑟·康普顿为国家科学院国家学术委员会主席,对铀裂变研究进行总体调查,在美国“曼哈顿工程”正式施行之前,国家学术委员会共提交给国防研究委员会三次报告,为整个工程的施行做了周密论证。后来,阿瑟·康普顿在“曼哈顿工程”中担任建于芝加哥大学的冶金实验室主任。二战结束之后,他任职于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
Compton,Karl T.(康普顿,卡尔·T., 1887—1954)
美国物理学家,1930—1948年任麻省理工学院校长。1941年,担任万尼瓦尔·布什领衔的国防研究委员会成员,之后又带领美国雷达研究代表团访问英国。1945年,他被选入临时委员会(Interim Committee),参与研讨并向总统杜鲁门建议有关原子弹使用事宜。战后,他担任军事训练总统委员会主席和海军研究顾问委员会成员。
Condon,Edward U.(康登,爱德华·U.,1902—1974)
美国核物理学家,二战期间美国雷达研究和“曼哈顿工程”的参与者。1945—1951年担任国家标准局主任。
Conant,James B.(柯南特,詹姆斯·B.,1893—1978)
美国化学家,1933—1953担任美国哈佛大学校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与美国化学武器研制工作。1940年成为国防研究委员会成员,1941年接替万尼瓦尔·布什成为主席。1945年5月,进入临时委员会(Interim Committee),研究并向总统杜鲁门建议是否向日本使用原子弹,7月,他与奥本海默等人一起见证了世界上第一次原子弹爆炸实验。战后,成为美国原子能委员会总体顾问委员会成员。1955年担任美国驻西德大使。
Einstein,Albert(爱因斯坦,阿尔伯特,1879—1955)
出生于德国的理论物理学,1921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家。1933年纳粹上台时,他正在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问,之后宣布放弃德国国籍,不再返回德国。20世纪30年代曾参与对流亡科学家的救援工作。二战结束之后,爱因斯坦呼吁原子弹的国际控制。1955年,他与哲学家罗素一起发布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成为帕格沃什科学与世界事务会议的开端。
Fermi,Enrico(费米,恩里克,1901—1954)
出生于意大利的物理学家,1938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由于其妻子是犹太人,1938年移民美国,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从事核物理相关的研究。战后,费米成为美国原子能委员会总体顾问委员会的成员,1949年时极力反对美国进行氢弹的研发。
Franck,James(弗兰克,詹姆斯,1882—1964)
出生于德国的物理学家,1925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纳粹上台之后,清除大学系统具有犹太人血统的工作人员,弗兰克对此不满,遂以辞去哥廷根大学教职抗议。之后协助英国的弗雷德里克·林德曼(Frederick Lindemann,即在英国原子弹研发过程中对丘吉尔产生重要影响的 Cherwell子爵)帮助流亡的犹太科学家在英国或者美国找工作。1933年底,在尼尔斯·玻尔的帮助下,他离开德国,在丹麦停留一年之后,前往美国,先后就职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在“曼哈顿工程”中,弗兰克担任芝加哥冶金实验室化学部主任。二战后期,弗兰克担任原子弹政治与社会影响委员会主席,主持撰写了有关原子弹使用的《弗兰克报告》(Franck Report)。
Frisch,Otto(弗里希,奥托,1904—1979)
出生于奥地利的犹太科学家。1933年纳粹上台之后,他移居英国伦敦。1940年与鲁道夫·派尔斯共同完成弗里希-派尔斯备忘录,引起英国政府对原子裂变研究及其应用的关注。之后,他作为英国原子弹项目代表团成员,赴美国参与“曼哈顿工程”。
Hahn,Otto(哈恩,奥托,1879—1968)
德国化学家,因为发现原子裂变于1944年获诺贝尔化学奖。作为纳粹迫害犹太人政策的反对者,1938年,他帮助利兹·梅特娜逃往荷兰。二战以后,他参与了反对将核能用于武器的社会运动。
Joliot-Curie,Frederic(约里奥-居里,弗雷德里克,1900—1958)
法国物理学家,1935年获诺贝尔化学奖,居里夫人的丈夫。法国被纳粹攻陷之前,他设计的铀—重水反应模型展示了铀裂变反应可以产生能量的现象,法国沦陷之后,他与同事将研究文献和实验原料转移到了英国。
Lawrence, Ernest(劳伦斯,厄内斯特,1901—1958)
美国核物理学家,1939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曼哈顿工程”中,他主要负责铀同位素的分离,参与创建伯克利劳伦斯国家实验室(Lawrence Berkeley National Laboratory)和利维摩尔劳伦斯国家实验室(Lawrence Livermore National Laboratory)。
Meitner,Lise(梅特娜,利兹,1878—1968)
出生于奥地利犹太人家庭的核物理学家。1938年他逃亡荷兰,之后建立与尼尔斯·玻尔等人的工作联系,并就核裂变研究与玻尔、奥托·哈恩、奥托·弗里希等有过多次书信往来。1942年,他拒绝去参与美国“曼哈顿工程”,美国用原子弹轰炸广岛之后,她对原子能被用于武器表示遗憾。
Oliphant,Mark(奥利芬特,马克,1901—2000)
澳大利亚物理学家。他在英国卡文迪许实验室获得学位,发现氢的同位素,在第一次核聚变试验中发挥重要作用。1937年之后他成为伯明翰大学物理学教授,二战爆发之后加入雷达研究。是他将弗里希-派尔斯备忘录递交给英国政府,并在之后成为玛德委员会成员。
Peierls,Rudolf(派尔斯,鲁道夫,1907—1995)
出生于德国犹太家庭的物理学家。纳粹上台时,他正在剑桥大学做研究,之后接受援助,留在英国。1937年他成为伯明翰大学数理物理学教授。1940年与奥托·弗里希合作完成的弗里希-派尔斯备忘录引起英国政府的重视。1943年他参与英美原子弹研发合作,加入“曼哈顿工程”。
Rabi,Isidor I.(拉比,伊西多·I.,1898—1988)
出生于波兰的犹太人,幼年时移居美国,1944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二战时期他参与麻省理工学院放射实验室的雷达研究,后来参与美国“曼哈顿工程”。战后,担任美国原子能委员会总体顾问委员会成员,1952—1956年担任总体顾问委员会主席。他还曾担任战争动员办公室科学顾问委员会成员,和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科学顾问。
Rotblat,Joseph(罗特布拉特,约瑟夫,1908—2005)
波兰犹太人,物理学家。纳粹上台之后的反犹以及对外战争,造成罗特布拉特妻子遇害。当觉察到核裂变的应用前景时,他认为能够阻止纳粹获得核武器的途径就是让英国先掌握核武器,对纳粹形成威慑,但他并不赞成使用真正使用核武器。因而1944年得知美国军方领导层决意要在战争中使用核武器时,他退出了“曼哈顿工程”。之后,他转向放射医学研究和核降尘研究,核降尘研究最终成为1963年《美英苏部分核禁试条约》达成的因素之一。他是1955年罗素—爱因斯坦宣言的签署人,并成为帕格沃什科学和世界事务会议早期负责人之一,1995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Rutherford,Ernest(卢瑟福,厄内斯特,1871—1937)
出生于新西兰的物理学家,被称为“核物理之父”,1908年获诺贝尔化学奖。
Smyth,Henry D.(史密斯,亨利·D.,1898—1986)
美国物理学家。二战时期为“曼哈顿工程”顾问,美国官方第一本有关“曼哈顿工程”历史的书由他完成并于20世纪40年代末出版,也被称为《史密斯报告》(Smyth Report)。战后曾任美国原子能委员会成员和美国驻国际原子能机构(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大使。在任美国原子能委员会期间,他曾反对美国快速发展氢弹,主张核武器的国际控制。
Sommerfeld,Arnold(索姆菲尔德,阿诺德,1868—1951)
德国物理学家,量子物理学界泰斗级人物,很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与各国原子弹研发的科学家都是他的学生,例如:汉斯·贝特、鲁道夫·派尔斯等。20世纪20年代他在德国慕尼黑大学开设的研讨班吸引了大量后来的核物理学家前去听课,包括美国的罗伯特·奥本海默。
Szilard,Leo(西拉德,利奥,1898—1964)
生于匈牙利的犹太人物理学家。1933年纳粹上台之时他流亡英国,又于1938年移居美国。在英国期间,他帮助援救欧洲流亡科学家和知识分子。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初,他是游说美国罗斯福政府关注铀裂变研究的主要发起者。1942年,加入芝加哥大学冶金实验室。广岛原子弹事件之前,他屡次游说政府不要使用原子弹,并组织科学家请愿。
Teller,Edward(泰勒,爱德华,1908—2003)
理论物理学家,生于匈牙利,犹太人,被称为“氢弹之父”。1933年,在国际营救委员会(International Rescue Committee)的帮助下,他流亡英国,后又辗转至丹麦,与尼尔斯·玻尔一起工作。1935年接受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教职邀请,赴美就职。“曼哈顿工程”中,泰勒加入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理论物理部,研究核聚变问题。由于当时“曼哈顿工程”的主要研究精力集中在核裂变问题,泰勒郁郁不得志。1949年之后,泰勒力推氢弹研究。
Thomson,George P.(汤姆森,乔治·P.,1892—1975)
英国物理学家,1943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1930年开始担任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教授,直到1952年。1940—1941年他担任英国玛德委员会主席,协调英国各个科研机构的铀裂变研究,最后形成的《玛德报告》影响了英国政府关于核武器研发的态度。
Urey, Harold(尤里,哈罗德,1893—1981)
美国物理化学家,1934年获诺贝尔化学奖。尤里专长于同位素分离技术,1941年被科学研究与发展局吸收进监督铀裂变研究项目进展的S-1执行委员会,其后又与英国科学家交流有关同位素分离技术的研究。战后,他成为促成原子能国际控制的重要人物。
Wigner,Eugene(魏格纳,尤金,1902—1995)
理论物理学家,生于匈牙利,犹太人,1963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1930年,魏格纳即已接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邀请移居美国,而1934年返回欧洲暑期旅行时,目睹耳闻纳粹反犹暴行,在朋友的劝说下,尽快返回美国。这次经历对他刺激极大。1939年和西拉德一起与爱因斯坦商议致信罗斯福政府注意铀裂变研究。“曼哈顿工程”中,他负责领导核反应器的设计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