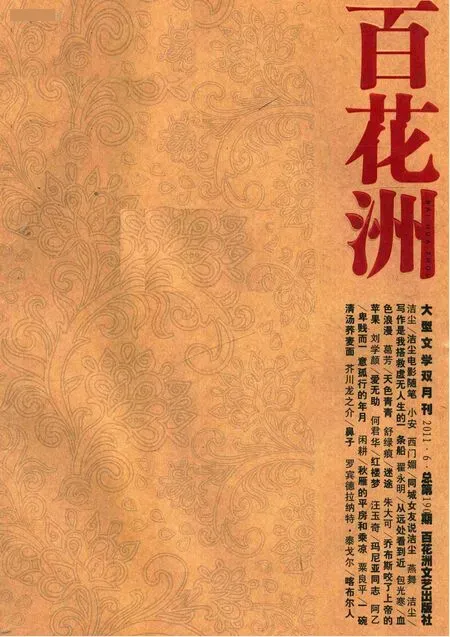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我不知道其他动物对世界是不是有自己的看法,但已经发达了脑力的人确凿是具备这种能力的,何况我们国人一向有议论时政和风尚的嗜好。还是契诃夫那句话说得好,“大狗叫,小狗也叫”,我想那叫就是对世界发表看法吧,虽然它的叫与不叫也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但既然上帝赋予了它叫的权利,那它便不能违背上帝的意旨。这似乎能在很大程度上解释我为什么要从事写作的问题,也成为我继续写下去的真正动力。
记得美国作家约瑟夫·海勒有一部作品叫《出了毛病》,我并不真正喜欢这部作品,而是为《出了毛病》这个书名所震撼,我觉得可以用它来概括我们古今中外所有经历和未曾经历的历史和现实。我一向认为,写作者和他所面对的世界是一种敌对的关系(如果“敌对”这个词有些严重的话,我可以换成诸如“对立”这样相对温和的词),他天生带着啄木鸟的目光打量出现在它面前的树木和森林,即使再被赞誉为“盛世”的时代在写作者的笔下也是伤痕累累的,鲁迅那句“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虽然是不为人所喜的老话,却是写作者必须秉承的至圣法则。这部《饕餮综合征》就是遵循这种写作原则的产物,代表了我这段时间内的写作方向。
应该说,《饕餮综合征》是一部关于信仰的作品,或者更完整一些说,这是一部有关信仰和背叛的作品,主人公(曾经的革命者、警察、妓女的女儿和失业工人)先后背叛了曾经的信仰,而走到了自我人生的背面。这当然也是一种选择的结果,而且是一种更加顺应时代的选择,并不是主人公们凭着一己的意志就能决定了的,纵观中国整个20世纪波澜壮阔的社会变迁,身在其中的人们如果不发生人生道路的转折几乎是不可能的。我无意指责人们坚守或背叛信仰的选择之举,只是意在告诉人们,失去或背叛信仰并不是一件十分简单的事,而是伴随着炼狱般的挣扎和拷问的,我不过是把这种挣扎和拷问的过程用文字呈现出来罢了。
进入中年以后,我在鄙视了19世纪的文学状况很长一段时间之后,突然喜欢上了左拉(当然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为没有真正错过上上个世纪的文学大师而感到庆幸。相对于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这位一直被误认为是“自然主义”流派代表人物的作家对社会历史和人性世态的解剖和批判,其力度和广度丝毫不比他们逊色。是的,批判,我愿意再次重复一遍这个词,作为一个合格的写作者,对他所面对的写作对象即社会和世界,保持这样一个认知的视角无论如何都是必须的。
不要误会,我在这里说到左拉等前辈作家,并不意味着我这部《饕餮综合征》(更有它后面的几部作品)就是批判现实主义之作,不是的,它和我们所说的“现实主义”写作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我早就固执地认为,写作者在批判他所面对的写作对象的时候,绝不能顺从那个现实世界所提供给他的逻辑,不仅不顺从,反而要抗争,要推翻,要打碎,要重建,要再造,没错,写作者的任务唯有创造,创造一个只顺从他的美学逻辑的艺术世界。在这里,卑微的写作者就是无所不能的上帝,“要有光,就有了光”。
有必要再使用一部作品的名字,就是米歇尔·布托尔的《变》,我以为用这个宝贵的“变”字来说明今天的写作者所应该具有的写作姿态是非常恰切的。自从天才的卡夫卡、乔伊斯们开创了崭新的现代文学写作样式之后,抵达21世纪的文学再也不可能与过去具有相同的形貌,所谓“现实主义回归”的说辞不过是一厢情愿的梦呓而已,约翰·巴斯关于“传统文学形式与技巧已到尽头,应对文学形式进行实验和创新”的忠告,对于中国这样在现代文学创作上的“后发”国家里的写作者而言,是没有任何理由不牢记在心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