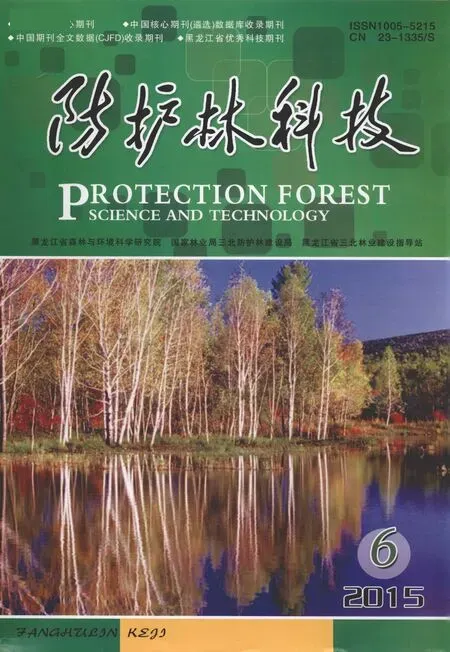试议生态文明的历史传承与发展
庞春祥,佟朝晖
(1.哈尔滨商业大学 法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76;2.黑龙江省林业厅,黑龙江 哈尔滨 150090)
人类对文明的认识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文明形态的定型化和自我扬弃体现着人类的发展追求和意识觉醒,是一个漫长而联动的实践过程。文明形态的历史传承与超越,不仅是一个由自发到自觉的实践历程和认识历程,更是一个由人治走向全面法治的不断进步和超越的进程。
1 人类对文明的认识
人类对于文明的认识不是短时间内就形成的,而是经过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文明不是天然的,不是从来就有的。马克思认为文明是相对于野蛮而言的,文明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进一步指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文明是一种社会品质”[1],它标志着人类社会进步状态和社会开化的程度。文明对应着野蛮,理解文明必须先探讨野蛮。字面上理解,野蛮中的“野”乃蛮荒之所在,即无人类蛮荒之所在。以人类为基点,蛮荒应为“人”之外的动植物生命世界和无生命之自然界。人类起源于“蛮荒”之所在。“蛮”字字面解释为粗野,凶恶,不通情理,实为暴力与落后的代名词。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此华夏民谚之意可以解释人类文明的短暂历程。它与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文明史的发展历程不谋而合,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视为人类文明的进化历程。特别是在前3个社会形态,可以说是野蛮占据上风,期间充满着动植物世界的“弱肉强食,强者为王”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野蛮的生存竞争。在人类历史中,也较普遍地存在着“人可非人”、“人可为财产”而随便交易的不平等的野蛮状态。众生依托自然界在生命规律和自然规律的支配下演绎发展。其中人类大脑的自我主体意识和平等意识觉醒的最快,这推动了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而推动了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不断进步,由野蛮的暴力不断地走向契约的秩序。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运用了唯物主义历史学方法,以“生存技术”为标准,把人类社会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3个阶段,提出了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理论。当代学者将人类文明的发展阶段分为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商业文明和生态文明[2]。原始文明,即采集——狩猎文明。此阶段,人类完全借自然“恩赐”得以生存和发展。人类几乎没有改造或控制自然的能力,人类敬畏自然[3]。在农业文明阶段,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些许变化。因新劳动工具的出现,人类不再完全依赖自然之“恩赐”生存,而是通过农耕或畜牧,使自身的物质生活需要基本得到满足,生存条件亦得改善。人类开始具有些许改造或控制自然的能力。人类对自然不再似从前那般敬畏,人与自然的关系出现裂痕。概括地讲,前2种人类文明的发展,虽然也对动植物界和自然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并未超越大自然的自我净化能力,空气、水源、土壤的自我净化能力消解了人类的负面影响,人类的生存发展条件在不断地得到改善,但却是缓慢的。步入工业化的近代,特别是工商业文明的联动发展,使人类适应、改造甚至“征服”自然的能力空前提高,人类行为尤其是经济行为的负外部性改变了自然界和动植物世界原有的自然循环秩序,超越了依其自身规律自我净化和调适的能力,表现为多种动植物的灭绝或濒危,环境污染之荒漠化、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地污染及能源危机等种种不可持续现象的频繁涌现,已经成为地球村主宰的人类之生存之痛。人类如果不进行主动的自我调适和改变,这种工商业文明的进步性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它的反面。因为在生物与环境的关系即生态中,人类是能动的创造者和强大的改变者。生物与环境关系是否和谐自调,并不取决于人类以外的其他生物。人类以外无论是何种动物和植物都是大自然的被动适应者,受自然规律的调解与控制,遵循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法则。只有智能的人类,在经历了农耕文明走向工商业文明的进程中,取得了机械、电子、信息、生物、医疗等各个领域的革命性成果,使人类具有了改造自然,甚至毁灭自然的超强能力,在个体自觉和群体盲目的市场竞争规律作用下,工商业文明的进步意义渐趋停滞,并不断地走向其反面,于是生态文明呼之欲出,很快成为当今人类有识之士和世界各国的普遍共识。
2 生态文明的提出
“生态”一词通常是指生物的生存状态,指生物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简言之,生态就是指一切生物在自然界的位置和生存状态,以及它们之间和它们与环境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1866年德国动物学家赫克尔认为,一切生物都是环境整体的一部分。他摆脱了从生物个体出发的传统的孤立思考方式,提出“生态”就是生物与环境的关系,并在其《有机体普通形态学》一书中正式提出了“生态”一词[4]。
“欧阳志远提出,继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之后的第三次产业革命是在人与自然的矛盾激化的背景下由生态学理论指导的工业技术体系的革命。在这种变革中,社会的物质生产体系也将相应地由工业体系演变为生态化的生物产业体系。中心产业是生态化的生物产业。……这是继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之后,物质生产体系的又一次质变,其影响和意义将远远超过前两者[4]。”
陈泉生指出,各学科领域强调生态化,这说明人类深刻地意识到不保护好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恶化不加以制止,人类的所有努力将失去意义。与自然和谐相处,协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不再是生态学本学科的分内事,而是包括法学在内的所有学科必须重视的问题[5]。
苏联科学院科尔巴索夫教授在《生态学:政策与法》一书中首次提出了“生态法”概念,此后,“生态法”一词全面取代了环境法、环境保护法、自然保护法、自然环境保护法等名词,成为俄罗斯法学领域里的一个专门术语,独联体和东欧的一些国家随后也开始大量使用这一词汇。此外,美国学术界也有人使用生态法和生态法学概念,并出版有专门的生态法学期刊,从期刊内容上看,主要涉及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环境保护以及生态保护等领域[6]。
郑少华在其《可持续发展与第三次法律革命》一文中提出了“第三次法律革命、社会变迁与可持续发展之法制整合”的观点,认为“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引,我们应构筑一种法律新理念——自然本位;人是自然的一分子,人并不是宇宙的中心,人与自然界应和谐共处”[7]。马克思、恩格斯建立了以“劳动”为基础的人类进化理论。人通过劳动使人与自然发生一种共在关系,但是,人在与自然的互动过程中,人的欲望满足的“快感”会在征服自然的“陶醉”中无限扩张,如果人以“征服者”的姿态对待自然,那么,人的劳动在创造自身的同时,也会毁灭自身。这一聪明的预见已被工商业文明下的人类困境之现实所印证,于是人类竖起了生态文明的大旗,开启了工商业文明的扬弃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实践征程。
3 生态文明的发展方向
可以说,生态文明源于对工商业文明的反思,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对整个人类文明进程的反思。如果说农业文明是“黄色文明”,工业文明是“黑色文明”,那么生态文明则作为“绿色文明”代表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更高层次和未来方向。
生态文明要求人类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生态文明相对于工商业文明,最显著的特征是强调人类对自然界的尊重,要求人类的经济和社会活动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与自然、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相互依存、共处共融;人类在利用自然时必须遵循自然规律,不得随心所欲,要对自身的发展需求进行适当地限制。
法治是文明的一部分,因而法治文化也是生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法治规范人类行为,进而推动全社会生态忧患意识、生态责任意识和生态道德意识的形成,是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应有之义,也是美丽中国实现的有效途径和深远目标[8]。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666
[2]宋全超.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问题路径研究[D].石家庄:河北经贸大学,2014
[3]杨通进.现代文明的生态转向[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
[4]蒋冬梅.经济立法的生态化理念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021
[5]陈泉生.科学发展观与法律发展:法学方法论的生态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52
[6]曹明德.生态法的理论基础[J].法学研究,2002(5):98-107
[7]郑少华.可持续发展与第三次法律革命[J].法学,1997(11):18-20
[8]王树义,周迪.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法治[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2):114-124,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