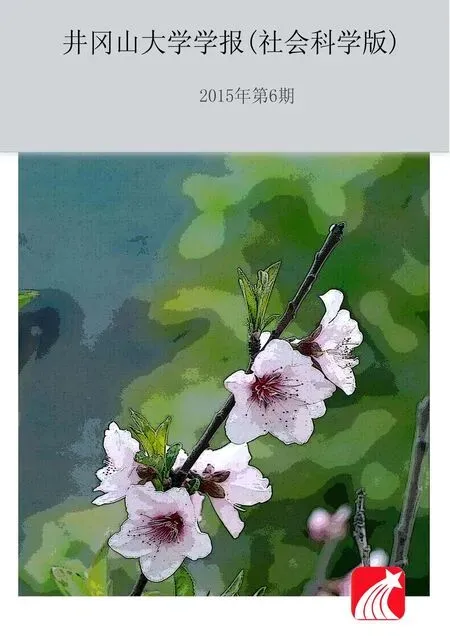关怀伦理视域下的社会正义可以接受吗?
——对迈克尔·斯洛特关怀正义观的批判
方德志
(温州大学法政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
关怀伦理视域下的社会正义可以接受吗?
——对迈克尔·斯洛特关怀正义观的批判
方德志
(温州大学法政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
迈克尔·斯洛特从关怀德性伦理学推衍出一种社会 “正义”观 (即一种偏斜于 “关怀”动机的法治程序型),认为国家的立法人员和司法人员只要从关怀的动机进行立法和执法活动,该社会就会是正义的。但该理论方案难以付诸现实。原因在于,偏斜的 “关怀”动机会使立法、司法人员在立法和执法过程中优先考虑亲近利益,由此导致国家内部成员之间的不公平对待;在国际上,立法、司法人员会优先考虑本国利益,导致国家之间的不公平对待,使国际问题难达一致。只有从不偏斜的 “仁慈”动机出发进行立法和司法活动,才能保证国家内部和国际之间的公平和正义。斯洛特的关怀——正义观,是为了调和当代西方女性关怀伦理学关于 “关怀”与 “正义”二元对立问题的争论,但其理论方案力度不够。
迈克尔·斯洛特;关怀的正义;道德情感主义
一、基于关怀动机的社会正义观
斯洛特的关怀正义观派生于他所构建的移情——关怀(德性)伦理学。基于移情的关怀德性伦理学旨在从人的那种关切他人生命福祉(wellbeing)的道德情感动因(即关怀/care)来统一地评价行为者及其行为是否合道德性。当且仅当一个人的行为动机(motive)是源自关怀这种道德动因(motivation),该行为者的行为才是合道德的,该行为者也才是道德上的好人。
沿着这一思路,斯洛特对一个国家范围内的社会行为也进行了道德评价,认为要从社会行为表象背后的人们的关怀动机来评价一个社会是否正义,由此形成一种关怀视域下的社会正义观。“从关怀也能一般地开发出正义和社会道德之理想。……假如各个个人能够亲密地(intimately)和人道地(humanely)关怀他人,那么这些人同样也能关怀自己国家(的善)和其他国家(的善)。”[1](P93)这里,斯洛特把对社会的道德评价与对个人的道德评价做了一种类比。社会就像是一个大写的“人”,其行为就是类似于由法律、制度、社会习俗等这些外在建制构成,要评价一个社会是否符合道德,是否正义,就要看制定和执行该社会之法律、制度、习俗的人们是否从关怀动机出发。当且仅当这些人从关怀的动机出发来制定社会法律、制度、习俗,该社会才是正义的。否则,即使该社会有效地运行着,也不代表它是一个正义的社会。“假如一个社会被看作是由生活在某种制度下的人们群体组成,那么,一种基于行为者的方法将自然地会坚持:一个社会之道德上的善性、它的正义,将依赖于构成该社会之人们群体的整体动机是怎么样地好。……因此,我们最终得出的是这样的观点:把社会的正义德性看作是个人德性(virtue)的一种功能”。[1](P101)
从立法角度看,在一个国家,如果精英领袖、特权阶层或利益集团为了局部的利益 (例如为了维护既得权力或利益)而制定各种维护社会稳定的法律和制度(例如禁止工人罢工、言论自由等),这样的社会就是不正义的,即使这些法律和制度的确推动了社会的有效运行。又如,在国家间,假如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缺乏实质性地关怀他国人民的生命福祉,这样的国家依然是不正义的,即使该国法律和制度能够增进本国人民的生命福祉。“很明显,法律、制度和宪法是由那种对他国福祉之关切不足(的动机)而驱使的,也会被批判为不正义的。……即使(根据目前的概念)该社会的内在运作是完全正义的。”[1](P102)
从执法角度看,当且仅当司法、行政等执法人员保证司法和行政程序是从关怀动机出发的,其执法结果就是正义的,即使制造了冤案错案也仍然是正义的。“基于行为者的观点也暗示了:假如依据的是正义的程序,即便在法庭上证据被 (无辜地)误导了,判刑和惩罚某个未犯罪的人仍可以是正义的。这个结论就其自身来说没有什么特别不合理的。”[1](P106)在社会财富分配方面,斯洛特先是认为平均分配要好于不平均分配,后来则坚持“损有余而补不足”,这可以防止发生递减边际效应。
人的“移情”能力是促使人们践行关怀动机的人性基础。为此,斯洛特认为实现一种关怀视阈下的社会正义需要培育人的移情能力,假如人们都能对他人的生命福祉予以移情地关怀,彼此之间形成对关怀的信任,关怀的正义就可以变成现实。“假如移情和关切他人对我们来说是自然地发生,并且能够通过适当的教育和社会生活形式来培育,那么这里所描述的正义也许代表了一种在实践上可以达到的社会道德概念、一种相对的现实的社会道德理想。 ”[1](P110)
二、作为关怀的正义观错在哪里
斯洛特构建关怀正义观,主要是以道德情感主义的理论立场来矫正传统的道德理性主义立场,力图完全以道德情感主义的学理来讨论个人道德和社会道德(正义)问题。在他看来,“一个特定社会下的正义不能仅仅从一个特定时间内的那些制度(或法律)所是的方式中‘读取(read off)’出来。……而是要依靠这个社会的 ‘(伦理)灵魂’”。[1](P109)根据斯洛特的理论,现实生活中之所以要处处讲规则,恰恰是因为我们缺乏关切他人生命福祉的那种道德情感动机,由此导致人们(对道德本源——德性的遗忘)误认为遵守规则就是道德本身,所以,他认为从情感动机的角度来诠释社会正义是一个“更为深刻地通人性的东西”。
斯洛特的立论动机固然是好的,但是,派生于关怀动机的社会正义观存在一个重要的 “生理缺陷”,即由一种偏斜的品质结构形式会派生出一种偏斜的社会行为效果。因为关怀德性,作为一种情感动因,在结构形式上具有“重近轻远”的内在特征 (由此导致人的道德行为表现出对亲近之人的关怀程度要强于对疏远之人的关怀程度),那么由各个个人扮演的立法者,在立法时也必然首先从重考虑到“亲近之人”的生命福祉,然后从轻考虑“疏远之人”的生命福祉,由此制定的法律、制度必然不具有关切人们生命福祉的普遍有效性。例如,在制定涉外法律时,立法者自然会考虑本国利益重于他国利益,由此导致国家间(例如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一些问题(环境污染、宗教冲突等)难以达成共识。
理想/理论与现实之间是有差距的。我们不能因为关怀的正义观在现实(私人)生活领域还行之有效就足以说明它本身就是正义的。只要我们内心中有一种声音在呼唤:我们应该象关心自己的亲近之人那样去关心陌生人,那就说明一种基于偏斜的关怀动机建置的社会正义观是行不通的。换言之,一种基于关怀动机的正义观会让人们内在地感受到:偏斜地关心自己的亲近之人是不完美的,是有缺陷的,是不应该的,我们应该平等地关心他人。这是一个心照不宣的心理事实。可见,斯洛特由移情——关怀德性动机推出一种关怀的社会正义在理论上行不通。
实际上,只有源自“仁慈”动机的社会正义观才是普遍有效的,它从理论上可以保证立法者和司法者以利益“中立者”的身份从事立法、司法活动。的确,从理论上看,现实社会中每一个立法者、司法者都被预设为一个基于 “仁慈”动机从事立法、司法活动的人。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相信这个社会是公平的、正义的,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常说道德和法律是内在统一的(即法律讲“一视同仁”。当然,现实中不排除立法者、司法者的偏私动机。但是,基于“仁慈”的正义理念或理想依然存在)。就此而言,一种严格意义上的道德情感主义理论,应该从一种经验的道德情感(关怀)过渡到一种先验的抑或说一种纯粹的道德情感(仁慈)来为其社会正义观奠基。其实,按照斯洛特构建基于行为者理论时的初衷,他的情感主义道德观是以康德的道德观为理论对手的 (即相比康德把人的理性品质作为人们行为的道德动机,斯洛特是把人的关怀品质作为人们行为的道德动机)。如果继续这个初衷,斯洛特应该在一种非偏斜的“仁慈”①斯洛特也考虑了一种普遍的道德情感——仁慈(benevolence),但是最终否定了由普遍的情感派生出的社会正义。他认为人的情感本性就是偏斜的,不能普遍化,甚至基督教上帝的“圣爱”也是一种偏斜化的表达:上帝就如爱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每一个人。道德动机上推衍其社会正义观,才能在理论上与康德道德观(及其正义观)真正形成一种理论“对峙”的效果。关于从一种与康德的理性主义道德观之理论“对峙”效果来探析人的道德情感能力以及情感主义道德观,笔者在其他文章已有论述,这里不再赘述(参阅拙文:《情感与存在》,载于《道德与文明》2015年第2期)。这里想要说明的是,在严格的道德情感主义理论立场上,不可能出现基于“关怀”的正义和基于“仁慈”的正义之两种正义现象,关怀伦理视阈下的社会正义观只是一种理论假象 (在一定意义上它可以导致社会极不正义)。或者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是基于“仁慈”正义的一种经验表现形式。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从认识论上看,仁慈只相当于一种纯粹形式意义上的(道德)实践情感。那么,它如何变成一种具体的道德情感呢?这其实就是一个关于纯粹认知意义上的“仁慈”情感动机的时空性转化问题。仁慈之情感动机的时空性转化形式具体表现为两种动机形式:一种是类似于基督教“圣爱”的动机形式,因为上帝能够超时空地“此时此地”爱每一个人,但由于它是超时空的,因而也就不在时空性转化范围之内;另一种就是斯洛特讲的“关怀”动机形式,因为人不能超时空地爱每一个人,总是受制于现时空而只能爱有限的人②就此而言,时空性概念就相当于是作为人的纯粹道德情感的后天之相对性的经验直观形式。。其实,对于这种受时空性限制而只能爱有限的人的关怀动机,也要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出于象基督徒那样的动机——不是根据血缘亲近关系——去爱此时空的与其照面的每一个人;另一种就是出于关怀伦理学以及传统儒家所讲的那种动机——根据血缘亲近关系——有差别地爱有限的人③斯洛特以及女性关怀伦理学所讲的“关怀”道德情感类似于传统儒家血缘语境下的“仁爱”道德情感。。两者关怀动机情况,前一种情况比后一种情况更显正义。故,从理论上看,基于“关怀”动机的社会正义观,只是基于“仁慈”动机的社会正义观的经验表现形式,不足以作为社会正义之理想。
其实,对斯洛特的“关怀”正义观的批判方法也适用于对传统儒家“仁爱”道德情感理论及其隐含的社会正义观的批判和矫正:“仁爱”之“爱”并非源自血缘亲情,而是源自“人是情感的存在者”,血缘之仁爱只是纯粹之仁爱的时空性转化形式,即其经验性表现形式而已。如果说纯粹之仁爱的目的是追求一种“自我”与“他者”相关联性的“幸福”存在,那么儒家道德之社会正义观的通俗化表述应为:一个人的行为,只有以促这种关联性“幸福”为动机,才是道德的、正义的行为,即便它是从“亲亲”开始。反之,如果从“亲亲”开始,阻碍或限制了这种关联性幸福的形成,那就不是正义的行为。所以,在源自儒家“仁爱”伦理的正义观中,那种反映人际间之普遍关联性的“平等幸福”原则要优先于人际间之特殊关联性的“亲近差异”原则。这就意味着即便人们是处于一种特殊关联性的“亲近原则”之中,其行为也必须以增加他人幸福或至少以不损害他人幸福为目的,该行为动机才是道德的、正义的,否则为了“亲近之人”的幸福最大化而损害“疏远之人”的幸福,其行为动机就是不道德的、不正义的。孔子讲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即蕴涵了一种平等式的幸福主义的正义观④传统儒家蕴含的“平等——幸福主义”正义观与近代西方提倡的“自由-幸福主义”正义观有学理上的差异,前者建置于人的伦理属性及其情感动机,后者建置于人的生物属性及其理性(功利)动机。。
三、斯洛特之关怀正义观的当代特殊语境
斯洛特之所以提出一种关怀伦理视域下的社会正义观,主要是受当代女性关怀伦理思想的影响。从当代女性关怀伦理学来看,“正义”和“关怀”分别代表男女两性不同的道德思维原则。“正义”是男性道德思维的结果,它适用于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自由主义及其权利观的理论框架;“关怀”是女性道德思维的结果,它适用于以“他者”为中心的关系主义及其责任观的理论框架。在女性关怀伦理思想发展过程中,吉利根(Carol·Gilligan)认为“正义”与“关怀”的对立标志着男女两性在道德原则上的对立。之后,诺丁斯(Nel Noddings)、赫尔德(Virginia Held)、霍夫曼(Martin Hoffmann)等人在各自著作中将这两个道德原则加以继承和发挥,由此形成了当代关怀伦理视阈下“关怀”与“正义”问题之讨论。例如赫尔德说道:“一种‘正义视角’强调普遍的道德原则和如何应用原则到特殊的事例、并且尊重关于它们的合理论证;一种‘关怀视角’更注意人们的需要,即人们之间的实际关系怎样能维持和修补,并且尊重当作出道德判断时对所在境况的讲述和敏感性。”[2](P41)
当代关怀伦理学家对“正义”问题的讨论又是源自对罗尔斯“无知之幕”设计的“正义”理论的批判。在他们看来,以罗尔斯为代表的传统规范伦理学虽然擅长于理论的精密设计,但却无利于提高现实人们的道德水平,因为“为什么人们,尤其是高技能生产者,会在现实生活中遵守‘差异原则’,而此时他们却又不受控于‘无知的面纱’,且清楚自己生命中所处的位置?”[3](P262)的确,现实当中一个明知自己身份、家庭等各方面条件都很优越的人是很难选择那种偏袒于 “最不利者”的正义原则,除非他们有普遍的仁慈之心(这正是德性伦理兴起的背景)。反观女性,长期以来通过自身的行动(例如抚育孩子、照顾老人等活动)来践行关怀原则,却现实地改进了人们的道德水平。所以,他们强调切实的道德实践行为优先于精致的道德理论本身,自我对构成“我——你”关系的责任和义务优先于个体的自由权利,人际间依存性的 “关怀”价值优先于人际间分离的“正义”价值,等等。这些都是关怀伦理学给当代人类带来的道德新图景。正是基于此特殊背景,斯洛特在将“女性”主义视角转化为“情感”主义视角之后,力图将“关怀”和“正义”内在地统一起来,诠构了一种关怀伦理视阈下的社会正义观。
正义问题是西方政治伦理思想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大体来说,西方社会对正义的逻辑思考可分为“自然的正义”和“伦理的正义”两类。自然的正义强调人的生物性,提倡人们对个人的天赋才能予以普遍“尊重”,为此它寄希望于通过人的理性设计(契约)来推动个体对自然权利(空间)的最大化占有;伦理的正义强调人的社会性,提倡人们对个人的生命价值予以普遍“尊重”,它通过诉诸人的情感之给予性功能,推动个体对他人、整体之存在的关怀和认同,对社会弱势者的关照。现实的社会正义往往是这两种正义逻辑的交织运行,但有时会发生偏颇。近现代西方社会由于片面推崇人的生物性意义上的正义观,忽视人的社会性意义上的正义观,导致人的社会性生存出现危机。自边沁、密尔将基于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背景下的个人幸福观推广为一般的社会正义观(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基于人的生物性意义的正义观就以个人的自由权利观表现出来。当然,随着个人自由权利的极端膨胀,这种基于生物性的社会正义并没有带来个人的幸福,因为它以抽象地理性契约掩盖了人之关联性的生存事实。人毕竟也是情感动物,没有人际之间的情感给予性和接纳性,个人的幸福无法感受,伦理的正义也无法给予。这也揭示出了内置于现代西方社会的两大价值危机:个人之幸福与社会之正义。当代西方关怀伦理学所思考的正是何为个人的幸福和社会的正义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罗尔斯的“正义论”也是要调和这种价值危机。他根据人的先天自由平等和后天差异之两大原则,从社会“最不利者”受益最大化的角度来评价一个社会制度的正义问题,充分体现了一种普遍关切的人道主义精神。“无知之幕”中的人虽然是一种纯粹理性利己的人,但在现实中,他们又是有缺陷的人,由于无法控制的偶然致因而可能成为“最不利者”。这个“最不利者”,作为一种“中立者”身份,其生命福祉应该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关切的对象。“最不利者”生命福祉的增加,意味着“最利者”(作为关切者)生命福祉的相对减少。在此意义上来说,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制定者,罗尔斯的动机恰好就是斯洛特所期望的那种社会“立法者”的动机,该“立法者”的动机既关切了自己的生命福祉,又关切他人的生命福祉,因而更具有一种社会普遍有效性 (而斯洛特只是从道德情感的利他性特征来讨论社会正义问题,行为者本人并没有被放在一个“中立者”的位置,那么行为者本人可能因为这种“正义”制度而牺牲了自己的利益,这就是不全面的关切。这又退回到他之前反对道德评价——在 “自我”与 “他者”之间——的不对称性问题上去了)。应该说,在理论上,罗尔斯的“正义论”比关怀伦理视域下的正义论更有说服力,它兼顾了自然的正义和伦理的正义,也兼顾了康德的抽象主义方法(纯粹理性)和密尔的功利主义(趋利避害)价值取向,不失为基于仁慈动机的正义观之现实妥协形式之一。但是,关键是“无知之幕”中都是没有丝毫情感的人,所以,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作为近现代西方政治伦理思想的集大成——只推崇了人的道德算计能力,却丝毫没有开发人的社会情感价值,这正是以斯洛特为代表的当代西方关怀论者在心理上最不能接受的地方,故关怀伦理学领域产生了所谓的“关怀”与“正义”如何统一的问题。
[1]Michael A Slote:Morals from Motives[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2]弗吉尼亚·赫尔德.关怀伦理学[M].苑莉均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3]马丁·L·霍夫曼.移情与道德发展:关怀和公正的内涵[M].杨韶刚 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
Is Social Justice in the Vision of Care Ethics Acceptable?——A Critique to the Justice in Slote's Care Ethics
FANG De-zhi
(School of Politics-Law,Wenzhou University,Wenzhou 325035,China)
Based on his care virtue ethics,Michael Stoles deduces a perspective of social"justice",one "care"-inclined motive legal procedural type,and argues that a society will be just as long as its state legislators and judiciaries duly carry out their duties under the motive of care.That theory is hardly applicable in practice,because under the motive of"care" the said personnel tend to carry out their duties with preference to the close and intimate interests,hence leading to unfair treatment between members within a nation.In addition,nation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may be also unfairly treated as the legislators and judiciaries will consider their own national interests first,hence impeding consensus on international issues.Only legislation and judiciary under the non-inclined motive of benevolence can guarantee fairness and justice within and between nations.Slote's care-based justice,a conciliation for the 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care and justice in contemporary feminist care-ethics,is not theoretically persuasive.
Michael Slote;care-based justice;moral emotionalism
B82-0
A
10.3969/j.issn.1674-8107.2015.06.008
1674-8107(2015)06-0044-05
(责任编辑:韩 曦)
2015-09-25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西方情感主义伦理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5BZX095);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项目“情感主义视域下的道德知识学研究”(项目编号:13YJC720011)。
方德志(1979-),男,安徽舒城人,讲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哲学——伦理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