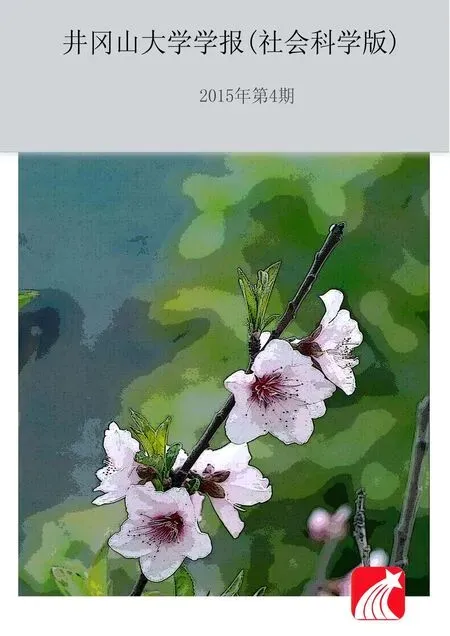任弼时早期党团关系思想探析
刘魁(赣南师范学院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江西 赣州 341000;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流动站,上海 200433)
任弼时早期党团关系思想探析
刘魁
(赣南师范学院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江西 赣州 341000;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流动站,上海 200433)
党团历史早期,两者发展处于相互交替上升状态。党团组织关系,一般上层较好,下层则龃龉不断。出于革命形势需要,党团关系也一再调整。在各种避免党团关系危机失控的措施中,任弼时等主张党团分化与党团民主,一度在解决党团纠纷问题方面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任弼时;中国共产党;青年团;关系
任弼时作为中共第一代主要领导人之一,深入学习与研究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并结合中国的具体革命实际,不断总结中共自身建设的经验,为加强党的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中在党团关系方面,任弼时有着独到的见解和精辟的阐述。①相关论述有:李玉琦:《任弼时建团思想浅议》,《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1994年第3期。李玉琦指出,任弼时对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成立以来党团关系的科学概括是,党的领导是共青团健康发展的决定因素,团应主动接受党的领导;任淑艳:《团建初期任弼时对“党团关系”的理论定位和实践探索》,《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任淑艳认为,对“党团关系”的定位,任弼时反对把青年团建成游离于党外的第二党,推崇指导与尊重相结合的党团关系。这些理论至今仍具有指导意义。
一、问题的由来
192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共青团即已诞生,从名称(青年社会革命党)上看,共青团已有政党取向,虽然此时的共青团还不是一个全国性的组织。此后数年,对青年团的性质以及党团关系一直存在模糊认识。1925年1月26日至3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决定将团的名称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弼时当选为中央局委员,负责常务,任组织部主任。[1](P32-33)
由于党团在目标与任务方面的一致性,换言之,党团都要群众化,务求在组织上接近与引导群众,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主张革命而不妥协”。[2](P1-2)加之党在创建时期,党的组织还不普遍,甚至许多地方尚无党的组织,青年团以青年占主体,团员富于政治理想,人数又远多于党员人数②据1925年1月统计,当时全国有共产党员995人,团员人数2400多人,团员人数大约是党员人数的2.4倍。参见张予《五卅运动,以至形成团协助党开展工作,或代替党去指导工人运动,学生运动更是如此,完全由团指导。[2](P19-21)五卅运动期间表现得更加充分,青年团做了许多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工作。
显然,青年团在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等政治活动中具有很强的独立性,一旦下级党部在工作中表现“畏缩退后”情形时,很容易导致各地党团关系紧张。在工作方面,党对团缺少指导与帮助,以至团员看不起党,将党看成“机会主义组织”,轻视党的力量与作用,在领导群众斗争时单干。双方很少互派代表出席会议,即便有,多半是团的代表出席党的会议,党只派技术人员出席团的会议,或干脆不派。团没有机会广泛讨论党内问题,或担负党内工作,党也不重视团的意见与提议。[2](P32-37)
党团关系紧张,甚至弄成党团之间的斗争,必定会引起极严重的结果。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当时党内有三种不同的主张:一种观念认为青年工作困难,团在中国没有存在的必要,主张取消团的组织,便可以加强党的力量;第二种观念认为,以团代党,将团的名称改为青年共产党,入团年限提高到25岁或28岁,主张团应领导一切,成为整个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第三种观念是,一切工农运动由党负责,青年团只须注重学生运动和文化工作,“替党做技术工作”。[2](P32-37)
二、任弼时的主张及其理由
针对以上三种观念,中共中央高度重视,认为党团双方假若不能负责纠正,这种倾向极其危险。五卅运动以前,学生运动完全由团负责,五卅运动以后,中共看出学生运动具有极大的政治作用,并且这种作用随着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而继续扩大。因此,中共中央决定,对于学生运动工作,党团双方负责指导。[2](P19-21)“八七”会议即规定,党团关系须极为严格的变更,各级党部与团应切实实现互派代表的原则,团部代表须参与讨论党的政策问题,且有表决权。[3](P230-233)
1927年12月,青年团中央局召开扩大会议。6日,由时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青年团中央总书记任弼时起草,中共中央常委会讨论后,中共中央和青年团中央联合发出通告——《纠正取消主义和先锋主义倾向》。大会对上述三种观念提出严肃批评,认为是青年运动中的危机。取消团的组织,党在青年工农中的影响也会 “消灭”;以团代党,青年团“可以走到形成第二党的危险”;把团看成专做文化运动的组织,容易导致青年工农走向改良主义的道路,消灭了青年团的政治作用。 [2](P32-37)
任弼时等人指出,团的定位是帮助党获得青年工农群众参加革命斗争的政治组织,因而,青年团应加强团的政治任务,团应注意青年工农中的下层工作,积极领导青年工农参加政治斗争,在斗争中建立自己的组织,广泛讨论党内政治问题,使团真正布尔什维克化。中共中央进一步强调,共产主义青年团不是党的附庸机关,团的组织应当保团的发展与工作的进行。同时,党要帮助青年团在工农青年群众中的发展与斗争,党团指导机关在工作中要防止青年团成为第二党的危险。[2](P32-37)
在各自的扩大会议上,党与团的中央并未仅仅停留在分析党团关系不好的现象,指出团反对党的倾向的危险性,而是提出了具体的纠正措施。诸如,党团互派代表参加各级会议,彻底实行党内民主主义;各级党部经常听团的工作报告,随时加以指导与帮助;党内一切政策的决定,应注意团的意见与提议,以便党能了解团的情形,团能明了党的政策,消除主张上的冲突;党员应努力参加团的工作,增加党在团内的成份与影响;在实际工作中,党应多给团以物质上的帮助,团应经常介绍优秀的团员入党(不满23岁者不必脱团),持续不断地输送新的积极分子到党内工作;在领导工农群众斗争中,党的组织弱小时,团须注意强健党的组织,提高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团部机关认为当地党部机关的政策和行动不当时,可向上级党部机关陈诉意见,要求上级党部机关审查;反之,团的组织薄弱时,尤其在乡村,党须指派得力人员担负团的工作,建立团的组织,时常派人到团内报告党的情形与政策,加强团内的政治教育工作。[2](P32-37)
对党而言,若党组织不能扩大,则工农运动等政治工作将不能充分发展。同理,站在团的立场来看,党不断地吸纳团内优秀分子,团组织极可能因此而松懈,乃至涣散。所以,许多团不愿意将团的能干分子介绍入党,或输送到党内工作。[2](P19-21)
毋庸置疑,在“斗争紧张情状”之下的党组织如要扩大而强固有力,上述党团关系亟待调整。任弼时等人认为,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党团必须从严分化,年过23岁的团员必须完全脱离团,20岁以上的团员全部介绍加入党,即使不满20岁而很能干的团员,也必须入党。由此可见,党团分化的结果是团员年龄降低,团组织更加青年化,有团组织而无党组织的地方,可以创建党的组织,团内兼党员的份子不断增加,党亦更容易在团内施行教育工作,党组织由此更加扩大而强固。[2](P19-21)
三、党团关系再调整
团的初期(1920年至1925年),青年团即有成为第二党的倾向。党与团的中央要求各级党团之后,团的政治作用被削弱,学生运动等方面的政治工作不再由团包办,而是在党的指导下开展,党加强了对团的领导。团在学生群体中扩大组织的同时,党亦能很好地掌控,因为党可以调动团内负责同志的工作。[2](P19-21)
然而,国共分家后,国民党进行清党反共,在白色恐怖之下,各省党组织迭遭破坏,党的干部牺牲无数,党员自首、告密与叛变也时有发生,有时上级党部亦不能幸免。于是,党的基础日益削弱,党组织逐渐脱离群众,与社会隔绝。从中央到支部,层层机关的工作效能大受影响,不少党部机关从上到下“多形成空架子”。一些党的机关几经破坏,各地党部有时唯一的办法便是请求中央派人前往恢复。可是,这一办法实行的结果,不但不能建立“新的关系”,而且“旧的基础也日益缩小”。工作不仅难于推进,新建的机关又极易被人发现,屡遭破坏,反而助长了党员依赖机关与忽视下层群众工作的观念。[4](P19-20)
正因为党组织在各地不健全,扩大会议中有关党团分化问题的决议,在各地具体执行过程中往往偏离原先预定的设想。按照决议,各级会议,党团互派代表出席,互相报告工作情形,互相介绍成员,互帮对方健全组织。但是,无论组织上,还是工作上,许多地方的党团关系“毫不密切”,党团相互闹纠纷,会议没有派代表参加[5](P376-381),甚至互相对立,相互取消的情形,也“时有所闻”。[6](P536)
为处理党团关系问题,一些地方规定,党团组织有合并情形的应立即分开,23岁以内的团员划归团,23岁以上的团员划归党。[5](P376-381)毋庸置疑,这样的划分方法的确简单而省事,但对于地方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并无多大助益。1927年12月,中共中央在给福建省临委的复示中便指出,23岁以下青年皆属团员,这样的规定过于 “死板”,应该调整为:凡18岁以上的团员 (积极分子)亦可以介绍入党,成为党兼团员,必要时,仍可留团内工作。[7](P312-313)
可见,扩大会议前,党团组织是混在一起,工作关系没有划分清楚,组织关系极不明确。团代替了党的工作,党亦没能监督和指导团。扩大会议中,党与团的中央强调,党调团内人员,以不妨碍团的工作为原则,并须征求团的同意,如双方争执时, 应由上级党团机关解决。[2](P32-37)扩大会议后,党团关系虽有所纠正[8](P228-231),但仍有不少地方,少数人员包办一切,党任意调动团内负责人。[9](P550-551)
细究原因,党团关系之所以如此纠结,主要症结在于,党团的对象大都是青年成份,党与团的工作又无大的差别。[10](P587-588)党与团的关系,在上层较好,在下层则不协调,容易发生“内耗”[11](P21-212),但又不是政治方面的争执,而是争钱、争群众。党主张团应自谋出路找经费,团则向各政权机关提款,甚至主张党团经费要平分。此外,党团在年龄上亦有争端,一些地方,赤卫队大都为年龄偏大者,少先队尽是壮丁组成,党主张取消少先队,团则坚决反对。此类争执,不胜枚举。
为化解党团之间的争端,中共中央对党团关系重新作了一些调整。例如,团在红军中只有小组,不经党的决定,团员不能由团任意调动;少先队年龄为18岁以下;团的经费为党的经费的一部分,党向团提供必要的办公费;团员转党员,以工作需要为原则,不再拘泥于年龄。经过这一规定,党团紧张关系有所缓和。[12](P209-212)
在军队中,党团如各有独立组织,不利于秘密工作与统一指挥。故而,中共中央规定,在军队中,党团组织必须统一,如党与团的支部同时存在时,团的支部取消,所有党员均为双重身份——兼为团员,党团合组共同的支部,受士兵运动委员会管理,党随时引导团参加士兵运动,各级士兵运动委员会受党的指挥;在红军或工农革命军中,团员与党员应有所划分[13](P146-147),团虽可单独成立小组或支部,但受军队内党部指挥,注重于军队中的政治教育以及文化娱乐工作。[10](P587-588)1930年6月至9月,在李立三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宣传部长期间,组织实施了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军事冒险计划,革命事业遭到重大损失。
1930年9月24日至28日,中共在上海召开六届三中全会,大会着重批判和纠正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14](P35)中共领导人认为,团是非党的组织,从支部直到中央,团参加党的组织的目的,是注重团的政治责任,而不是与党合并。因此,将党团组织合并是错误的,必须立即恢复党团各自的独立系统。党须督促团加紧青年工作,并尽可能地不调动团的工作人员。[15](P52-53)会后,党的组织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
党组织一旦恢复与发展,任弼时等中共领导人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再度调整党团关系。责成各级党部加强党对团的领导,将团转变成无产阶级青年群众组织,团成为党的助手。党通过吸收大批团员入党(团员不必脱离团)的方式,达到党经过团,团发动广大青年群众进行战争动员的目的。[16](P6-11)
党领导团,党的地位上升,党团纠纷是没有了,但又出现了老问题,地方党部“取消主义”观念严重。地方党部很少检查团的工作,专门讨论团的工作更少,互派代表制度没有完全实行。党团支部经常只开联席会议,不开团的支部会议。[17](P294-296)许多地方甚至有党无团,即使有,团不仅缺乏干部,兼党的团员少,一些地方,团员的数量更比党的还少。[18](P625-627)
无论紧急动员,还是艰苦战争,青年工农群众在苏区和红军中的作用非常明显。党团对立或党取消团,无疑都会对革命事业造成严重影响。1932 年3月,任弼时在汀州召开的闽粤赣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指出,党忽视团的工作是极端错误的,各级党团在组织上必须建立亲密的关系,开会应互派代表参加。党应把团的建设工作看成自己重要任务的一部分,对青年团要加紧政治上的领导和工作上的帮助,特别要帮助团发展组织和进行青年工农群众的工作。[19](P366-367)将团员中政治觉悟高和工作能力强而成份又好的团员大批介绍入党,做兼党团员,增强党的力量。纠正只有23岁以上才能入党和团不将最好的团员介绍入党的现象。[20](P14-17)从支部起,兼党团员担任团的各级委员会的书记,党经过兼党团员加强对团的领导。[21](P71)必要时,党调一部分干部做团的青年运动工作。[22](P648-649)1933年 3月,任弼时在湘赣两省组织会议上再次强调,党应加强对团的领导,团应群众化与青年化。团向党输送干部,党调动团的干部须得到团的同意。[16](P6-11)
不可否认,中共领导人的言论对党团关系的定位固然重要,然而,党能否领导与指导团,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党员干部的素质。以江西石城为例,石城新的领导方式未能完全建立,党员干部的政治水平与工作经验欠缺,许多区委书记不懂职工运动、工会组织、劳动法、工人斗争纲领等,“工作无计划,群众斗争未曾发动”,不知如何领导团。有几个区的团区委比区委书记的工作能力更强,区委书记不敢去领导。[23](P674-698)福建省也不例外,各级党部对团的领导非常薄弱,“甚至连入团号召有的党部还不知道”。中共中央也一再指出,党须转变这种现象,党要帮助团加强对赤少队与儿童团的领导,加强对团员的教育工作,尤其是新团员。团应输送大批进步的团员入党。[24](P525-527)
四、结语
自党诞生之日起,党团发展就一直处于不平衡状态,党团关系也几度调整。外部环境不好时,为规避风险,党员脱党、叛党现象不断,团组织发展超过党组织。外部环境转好时,党的政权稳固,党的地位突显,出于各种利益诉求,工农群众入党踊跃,党组织发展又超过团组织。一旦党组织发展受限时,党为了自身发展,需要不断地补充新鲜“血液”,往往触动团的利益。从党的创建时期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向团索取的多,而反补的少,由此,党团关系很容易龃龉;反之,党组织蓬勃发展时,党往往将团纳入从属的范围,降低团的地位,党团的地位与作用又显现不对等状态。为避免危机失控,中共中央也一再对党团关系加以纠正。诚然,任弼时等党的领导人主张党团分化与党团民主时,党团关系最好,二者比较融洽。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任弼时年谱(1904-1950)[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2]任弼时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3]“八七”中央紧急会议文件(1927年8月7日)[A].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3.
[4]周恩来.在白色恐怖下如何健全党的组织工作(1929年3月25日)[A].周恩来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5]中共德安县委关于第一次扩大会议情况给中共江西省委的报告(1929年7月27日)[A].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地武装起义·江西地区[Z].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
[6]江西省委通告——过去党组织缺点及今后组织工作的主要路线(1929年6月17日)[A].江西省档案馆,等.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Z].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7]中共中央关于福建省临委负责人联席会议决议问题给福建省临委的复示(1927年12月30日)[A].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地武装起义·综合册[Z].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1.
[8]王鸿泉关于江西组织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28年2月18日)[A].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地武装起义·江西地区[Z].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
[9]中共闽西特委给省委的报告(1929年12月12日)[A].江西省档案馆,等.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Z].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10]中共中央关于兵运策略问题的通告(1928年7月10日)[A].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地武装起义·综合册[Z].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1.
[11]吴振鹏关于江西中共组织的发展与现状向中共中央的报告(1928年1月7日)[A].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地武装起义·江西地区[Z].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7.
[12]张怀万巡视赣西南报告(1930年4月5日)[A].江西省档案馆,等.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Z].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13]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1929年9月28日)[A].江西省档案馆,等.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Z].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14]中共中央组织部,等 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8-1937.7)[A].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1921-1997)第二卷(上)(Z).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
[15]周恩来.关于武汉工作问题(1930年9月4日)[A].周恩来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6]任弼时.目前党组织上的中心工作[J].斗争,1933,(5).
[17]中共闽粤赣特委常委第一次扩大会的决议(1931年2月27日)[A].江西省档案馆,等.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Z].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18]赣西南会议记录(1930年10月13日)[A].江西省档案馆,等.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Z].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2.
[19]目前政治形势与闽粤赣苏区党的任务(1932年3月5日)[A].江西省档案馆,等.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Z].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20]苏区中央局关于巩固党的组织与领导的决议(1933年1月10日)[A].中共福建省龙岩地委党史研究室.反对所谓“罗明路线”问题[M].厦门:鹭江出版社,1993.
[21]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中共湘赣省第二次代表大会(1932年11月14日)[A].江西省档案馆.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Z].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
[22]苏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案之二: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1931年11月)[A].江西省档案馆,等.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Z].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23]党的组织状况——全省代表大会参考材料之四(1933年9月22日)[A].江西省档案馆,等.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Z].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24]中共福建省委工作报告大纲(1933年10月26日)[A].江西省档案馆,等.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Z].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On Jiangxi's Exploitation of Red Tourist Resources:A perspectiv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Strategy
ZHU Xiao-li
(Nanchang University,Nanchang 330031,China)
Jiangxi enjoys abundant red tourist resources and it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exploiting the resources.However,it also faces some problems like repetitive development and weak derivative products.Hence intellectual property strategy is important and inevitable for Jiangxi's better exploration of red tourist resources in according to the province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demands.It is imperative to apply the strategy in six respects.First is enhancing the red tour practitioners'intellectual property consciousness;second is improving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system of red resource exploitation; third is reasonable judgment of right subjects of the property;fourth is building a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net for the red resources;fifth is facilit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quality tour products;sixth is fighting against infring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ies.
intellectual property strategy;Jiangxi's red tourist resources exploitation
D26
A
10.3969/j.issn.1674-8107.2015.04.001
1674-8107(2015)04-0005-05
(责任编辑:韩 曦)
2015-05-04
江西省艺术科学规划项目“传承与谋变:苏区革命文化研究”(项目编号:YG2014006)。
刘 魁(1978-),男,安徽旌德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