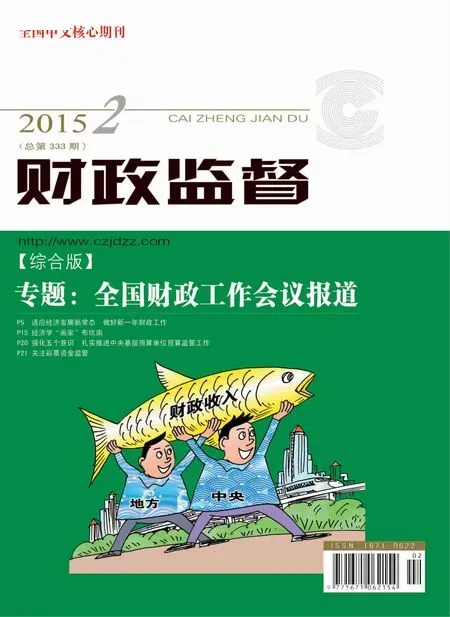经济学“画家”布坎南
●本刊编辑部
经济学“画家”布坎南
●本刊编辑部


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公共选择理论奠基人、宪政经济学之父詹姆斯·M.布坎南
当地时间2013年1月9日,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公共选择理论奠基人、宪政经济学之父詹姆斯·M.布坎南(JamesM.Buchanan)在美国布莱克斯堡去世,享年93岁。这位经济学家最突出的贡献是,他在公共选择理论上的创建让人们意识到,政治也可以用经济的方法来分析。
也许最能准确表达布坎南贡献的莫过于瑞典皇家科学院给予其的颁奖词——“布坎南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将经济学中个人间相互交换的概念移植到了政治决策的领域中。于是,政治过程便成为一种旨在达到互利的合作手段。但政治秩序的形成要求人们接受一套规则、一种宪法。这反过来又强调了规则形成的极端重要性和宪法改革的可能性。”而布坎南自身也曾说过“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把40年来人们用以检查市场经济的缺陷和不足的方法,完全不变地用来研究国家和公共经济的一切部门”。
出生于美国南方、务过农、当过兵,著述颇丰、风格平实,布坎南被看作继哈耶克之后又一代思想巨擘,在经济学界乃至整个学界都有广泛影响。这位自称“田纳西农民”的经济学大师对自己的定位好比一位“画家”。他在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后的一次演讲中说,“假如一位画家只有红色的颜料,那么他的画将只有红色的色调。这位画家并不是有意选择画红色的画,然后再去购买红色的颜料。他只是利用手中既有的材料,来做他能够做以及必须做的事,同时在整个作画过程中,也能充分享受创作之乐。借着这位画家的创作,其他人能从中得到一些新的启发,从而也给画家带来一些收入——这种善意的结果,让这位画家以为他的自传式的文章取名为《胜过耕田》(英文:BetterThanPlowing)。”
“诺奖之名并未将我推上智慧巅峰”



1919年10月3日,布坎南出生于美国田纳西州的农民家庭,家境清贫但地位可谓显赫。他的祖父曾任田纳西州州长,父亲在家族留下的大片土地上务农,且积极参与当地政事,颇受欢迎;母亲则饱腹诗书、勤学不倦,直至布坎南就读大学前一直为其辅导功课。
自小布坎南便就读于“布坎南学校”——在这所以其祖父命名的学校完成了十年的基础教育,大学(田纳西师范学院)期间,布坎南学习兴趣集中在数学、英语、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且其成绩名列前茅,给这个来自乡村的少年以极大的信心。布坎南毕业后获得经济学奖学金,到田纳西州大学进修,于1941年获得硕士学位。太平洋战争期间,布坎南应征入伍,大部分时间在巡弋珍珠港与关岛的尼米兹上将号上服役,荣获青铜星章,用他自己的话说“度过了四年有声有色的军旅生涯”。退伍后于1946年进入芝加哥大学研究所就读,1948年在经济系获得博士学位。
此后的布坎南致力于开拓公共选择研究领域。1955年,布坎南远赴意大利研究,受到欧洲财政学派影响,1956年至1959年在弗吉尼亚大学等校任经济学教授,并领导以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哲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托马斯·杰斐逊中心;1962年与戈登·塔洛克合著出版公共选择理论的奠基之作 《同意的计算》,并与塔洛克共同创建公共选择学会,出版了《公共选择》这本权威杂志。1968年至1969年布坎南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任教,1969至1982年在弗吉尼亚理工学院任教期间,与塔洛克一起创建和领导了公共选择研究中心,该中心于1982年转移至乔治·梅森大学,此后这里成为公共选择理论传播的大本营。1986年布坎南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就在布坎南诺贝尔奖领奖致辞的结尾,他说道“‘诺贝尔奖得主’之名并未将我推上智慧的巅峰”,他在会上决定尽量避免那些因他的“诺贝尔奖光环”而来的活动邀请,他反对以诺贝尔奖为导向的科学精英主义,提出他和其他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观点并不应该比其他人的观点受到更多的尊重。

1986年,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布坎南(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奖理由是,布坎南“发展了经济和政治决策的契约论与宪法基础”。
一方面,这是布坎南的谦逊之辞,另一方面,这确是这位经济学大师一直以来所秉持的治学态度——反对特权,敢于不同,创造性地形成关于真实世界的设想,并以最适合研究者天赋的方法,展示这些设想之间的关系。在这种治学态度之上,他又深受两位学者思想的影响——一位是他在芝加哥大学读博时的导师奈特,这位全心追求真理、不惮质疑任何权威的质朴学者让布坎南在六周内学会从经济学角度看世界并自此成为市场秩序坚定的支持者;另一位则是他在离开芝加哥大学前夕偶然发现其作品的瑞典经济学家维克塞尔,其“除非人人都赞成、否则就有人受损”等与布坎南不谋而合的观点使之成为他的第二精神导师,在其领诺奖之时更是通篇以维克塞尔的语录为主线。
布坎南坚持经济学基本原理,认为经济研究最重要的任务不应该是研究如何实现资源最优配置,而应该是研究人与人之间的“交易过程”,他坚守亚当·斯密经济学传统,坚持经济学研究乃至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对象是人之“交易行为”、“交易过程”,而在这一基础之上,以“经济人假设、个人主义方法论、作为交易过程的政治”为三大假设前提,布坎南构筑起公共选择理论大厦,指出只有把政治理解为人们在政治过程中的交易行为,才能真正发现政治的奥秘,且在这一领域,布坎南至少做出了“政府失灵理论、政府财政本质及打开政治投票的黑箱”三个方面振聋发聩的贡献。而这一作为经济学家的贡献,被认为是将经济分析方法对政治领域的一场学术殖民运动。因此,布坎南也被视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代表性人物。而其对规则的最初选择即对宪政原则的关注,更是让其成为政治哲学领域的伟大思想家、“宪政经济学之父”。
现任公共选择研究中心主任唐纳德·布德罗认为布坎南对所有议题都思考深入,“他从来不肤浅,他也从来不把聪明等同于智慧和真理。他关心宏大的议题——发掘真相的合理方式、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政治的本质等,思考得很哲学且深刻”,在布坎南逝世后布德罗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说道,“在历史上,很少有经济学家既精通狭隘、形式化的分析,同时又能提供一些对社会和社会科学深远且具哲学性的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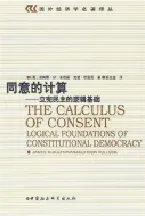

中国学者眼中的布坎南意义
自公共选择理论传入中国后,布坎南本人及其理论和实践影响了一大批中国学者。
“税收伦理学”研究者姚轩鸽评价布坎南一生“至诚向善、聚精根本”、有着“执着于人类社会治理根本问题的大智慧与大情怀”;
而在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苏振华看来,在不太严格的意义上,布坎南的离开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芝加哥学派的所有自由主义大师至此全部凋零,“相比今天泛滥的工具经济学家,超越学科边界、构建宏大理论体系、深具时代问题关怀的如布坎南这一代思想家,像离群的孤雁,逆着风飞。他们走了以后,这样的思想家恐怕就不大可能再现了”,苏振华曾撰文感慨道。
大师已逝,其人其事、其思想精神则永存。
曾经受教于布坎南、在“布坎南小屋”(乔治·梅森大学公共选择研究中心办公室)与这位长者共同早读过两小时的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席主任薛兆丰研究员在其纪念布坎南的文章中为我们这样近距离地描写了这位经济学家更为真实的一面:
“布坎南勤奋过人,清晨开始工作,以别人没空喘息的速度回信,自己的全集20卷之巨;他平常文质彬彬,但也会兵戎相见;他忠实地给予学术朋友以大力的支持,曾经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经济学研究生项目找来第一桶金,但他也由于缺乏耐心,而与弗吉尼亚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弗吉尼亚理工大学都不欢而散;他对计量经济学相当质疑和排斥,但对博弈论则热情拥抱;他桃李满天下,但只有极少数学生能成为他真正的入室弟子;他没有来过中国,但他盛赞华人学者杨小凯,为其英年早逝深表惋惜”……
薛兆丰在文末总结道:“恪守经济学教训,解构了政府黑盒和官员动机,捍卫个人自由,并通过宪政经济学研究不懈地追求平等,是布坎南教授留给后人的珍贵精神遗产。”

尽管布坎南在生前并不愿意过多谈论中国,认为其理论植根于西方文化传统和价值理念,并不一定适用于古老的东方土壤,但其在1998年回答中国经济学家汪丁丁的访问中有关中国改革的寥寥数语却发人深省:“关于(中国)市场导向的改革,至关重要的是把这些改革置于对法律与制度框架的必要性的理解之上,在这一框架内,人们能够履行各自在市场中的职能。关于财产和契约的法律,关于以老实的态度进行交易的传统,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没有了这些东西,市场导向的改革就毫无意义可言。”
无论在经济领域还是政治领域,只有有效的“法律和制度”才能确保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对“程序正义”的重视、对规则高于一切的认知,被视作布坎南的思想精华。
同样深受布坎南思想影响、并曾经统校过布坎南经典《宪政经济学》中译本的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冯兴元认为布坎南的理论“把政治和经济打通了,两张皮变成了一张皮”,“其思想确为一些寻找中国治理药方的有识之士提供了宝贵的逻辑和思路”;“虽然国情不一样,但不影响他的理论在中国做一些修正后的解释”。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前中国人民银行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认为布坎南作为公共选择理论鼻祖,使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更加密切,“其理论告诉我们:经济改革绝不仅仅只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密切相关”;姚轩鸽则更为直接地指出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对当下中国而言,其最重要的启示在于“要真正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福祉总量,关键在于如何有效约束公权力,首要是要有效约束政府的征税权力。”


与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左)、黄有光(右)
这位经济学大师级的“画家”已然在其“画布”上留下了恢弘的创作,“我们最好的怀念方式就是认真阅读、理解并积极应用这些宝贵的理论和分析方法,希望能够对中国的制度变革和社会进步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夏业良如是说。■
(执笔:阮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