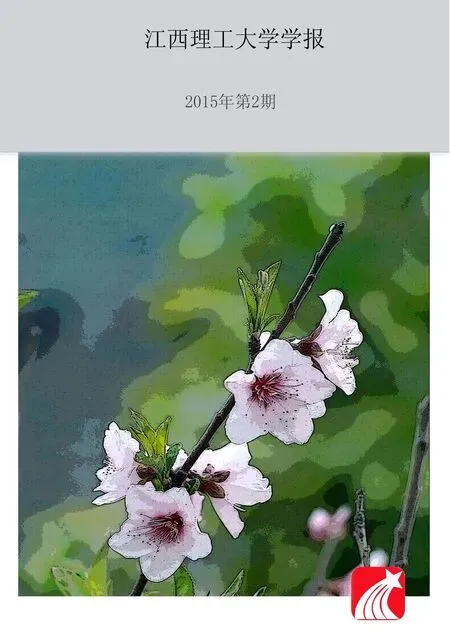关于生态智慧与生态文化的若干思考
(江西理工大学文法学院,江西 赣州 341000)
(江西理工大学文法学院,江西 赣州 341000)
人、文化与自然,具有天然的矛盾对立性。但对立不等于对抗,在对立中可以求得和谐,这就需要生态智慧。传统社会的生态智慧,是自发的、被动的、甚至是盲目的顺应自然节律的结果。工业文明是征服自然、反自然生态环境的文明,其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是对生态智慧的反动。现代意义的生态文化是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价值内核的人类生活方式,是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基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体系,是自觉形态的生态智慧,是对工业文明人类中心主义文化模式的“颠覆”。在当代中国语境中,要积极落实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的发展战略,大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化,以培育社会大众的生态文明理念,为开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提供价值支撑和智力支持。
生态文明;生态智慧;生态文化;生活方式;美丽中国
一、生态智慧的内涵及其历史形态
“智慧”一词,《新华字典》的解释是:“对事物能迅速地、灵活地、正确地理解和解决的能力”。而《辞海》对“智慧”的定义有二:“①对事物能认识、辨析、判断处理和发明创造的能力。②犹言才智、智谋。”
值得说明的是,知识不能等同于智慧,智慧需要有知识的武装,但有知识不一定有智慧。知识需要转化为人的思维与行动的方法、智谋、能力等,才生成智慧。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必须面对的最基本的关系。人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创造文化,同时也使自己超越动物性,成为社会的人、文化的人,并继续用文化的方式去适应与改造自然,创建起人文世界。也就是说,文化作为人类的一种生存方式,本质上体现的是社会中的人类对自然的一种适应与改造,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所以在人类文化中,不乏生态智慧。
按照上面对智慧的定义,本人对生态智慧的理解和界定是:广义来说,生态智慧是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中形成的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人类文化。狭义来说,生态智慧就是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理解和判断,以及创造性地处理人与自然的矛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荣的智谋和能力。
人必须利用和改造自然才能创建自己的文化,文化正是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创造性活动中形成的。从这个意义上,文化与自然,具有天然的对立性,文化本身就是从这种对立性中产生出来的。文化与自然有着天然对立性的含义,一方面是自然界不能完全满足人的需要,即天然的自然物质形态不能成为人的生存生活资源,自然与人是对立的。因此就有另一方面,人必须去改造自然,即改变天然的自然物质形态使其成为适合人的形态以满足人的需要,即以文化的方式让自然适合自己——人与自然也在对立着。因此,从人类的原始阶段开始,人、人的文化就与自然相对立:一是自然界并不能提供人类所需要的所有生存条件,即自然是人的对立面;二是人的行为、人的文化生存方式破坏了自然界的原有面貌,具有反环境性,即人是自然的对立面。
原始文明是人类文明的萌芽阶段,人完全依附于自然,其本身就是一种“自然存在物”。这个时期,人与自然是浑然一体的,人类利用自然界现成的东西,采集和狩猎是主要的生产方式。我们可以想象,仅掌握低下水平的原始工具——木棍、石器、骨针、最先进的武器也就是弓箭罢了——的人类,在强大的自然面前,在各种各样自然灾害(酷暑寒冬、狂风暴雨、大雪冰雹、洪水猛兽、火山地震、森林大火、疾病瘟疫等等)构成的恶劣的环境中,其处境是怎样的凶险!其生活是多么艰难!人类在恶劣的环境中艰难地生活,在异常强大的自然界面前,人们表现出对它的恐惧、崇拜心理,因为对人类来说,自然永远是一个巨大的神秘的存在,由此自然的力量被异化为统治人类的神祗和精灵。这样的状况,就谈不上人与自然的和谐。当然,也就谈不上人类有什么生态智慧。
但毕竟人类拥有文化,文化成为人类既适应自然又对抗自然的力量。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人类从恐惧自然、崇拜自然,慢慢到学会适应自然。人类要从自然环境中获得生存能力,适应自然,就要向自然学习,增加对自然的认识,增加适应和改造自然的本领,这就形成了人类最初的生态智慧。这个阶段说的是农业文明的出现。农业文明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文明转型,产生了以耕种与驯养技术为主的生产方式,初步改变了人对自然的完全依附地位,标志着人对大自然的有限的开发和利用。农业文明主要利用的是自然环境中的水土资源,农业文明时代的产品是在自然状态下也会出现的生物体、自然物,人依然必须适应自然、顺应自然,这就表现出了人类的生态智慧。
这样的状况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占有了很长的时段。但由于人类有了文化,而文化具有积淀性、传承性与创造性,文化的力量终究会变得强大起来,人类就慢慢增加着超越自然的力量,并不断超越自己,改变对自然的完全顺从、适应的关系,实行对自然的掠夺与征服。特别是近代工业革命以来,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对自然的改造能力和支配能力也在不断增强,人类对于自然的欲望也不断膨胀,自然的面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自然已经不再是原来的自然了,而成为了人类的资源库、加工厂、垃圾场。这个阶段,就是工业文明时期。
工业文明与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原始文明、农业文明时代都不同。18世纪60年代,英国纺纱机和蒸汽机的运用,标志着工业文明时代的到来、人类文明第二次重大转型。工业时代同古代农业的重要区别在于:一是采用机器生产。二是在生产中广泛应用科学技术,由此社会生产力获得大发展,并以空前的规模作用于自然界,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三是工业生产引起的是自然界在自然状态下不可能出现的变化,很多产品是在自然状态中不可能出现的人工制品。四是大量使用石化资源。
工业文明的出现使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人类利用科学技术这一巨大力量,对自然界展开无情的开发、掠夺与挥霍,自然界成了人类征服的对象,人类成为主宰和统治地球、主导生物圈变化的最重要力量。同时,人化自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建立了人工生态系统。人工生态系统,无论是现代农业生态系统还是城市生态系统,都是十分脆弱的,一旦一个技术系统出现问题,整个系统就会瘫痪。
工业文明还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工业废气的超量排放导致空气污染和臭氧层的破坏,导致温室效应;工业废水、生活污水的排放使得江河湖泊水质大面积污染,并出现淡水危机;森林被大面积砍伐,造成生物多样性减少、水土流失严重;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土地、草场的过度利用,导致其生产力下降,荒漠化、石漠化现象严重,等等。而且,生态环境问题不再是局部性的,而是全球性的了,是整个地球生物圈的危机。工业文明是征服自然的文明,是反自然生态环境的文明,也是生态智慧缺失、甚至可以说是对生态智慧反动的文明。
工业文明带来的全球性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存。 “人类力量所创造的文明背叛了人类自己,也正被这种文明送进坟墓。”[1]
面对全球生态危机的严峻挑战,促使人们对生态危机的根源进行反思。反思是全面的,包括对生产和生活方式、社会制度、科学技术、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模式的反思等等,其中最深刻的反思是对文明与文化的反思。这种反思促使人们意识到:工业文明奉行的是以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模式,这种文化价值观是导致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必须摒弃。人类必须重建人与自然之关系,形成不同于人类中心主义的新的文化价值观。对工业文化价值观的批判和反思、生态意识觉醒的最重要的成就,是现代生态文化的形成及其推动的人类文明的生态化转型——生态文明的形成和发展。
二、现代生态文化——生态智慧的先进形态
生态文化是人类生态智慧的现代呈现与先进形态。
关于生态文化的界定,我国著名学者余谋昌认为,生态文化是一种不同于工业文化的新文化,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从狭义理解,生态文化是以生态价值观为指导的社会意识形态、人类精神和社会制度。如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生态经济学,生态法学,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等等;从广义理解,生态文化是人类新的生存方式,即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存方式。”[2]卢风即认为:“生态文明就是广义的生态文化。”“狭义的生态文化是以生态价值观为核心的宗教、哲学、科学与艺术。在广义的文化中,狭义的文化主要体现于理念和艺术,当然它也直接渗透在语言、风俗和制度中,甚至还体现在技术和器物之中。”[3]
对于生态文化的界定,必须在对文化的理解基础上形成。笔者所理解的文化,从广义来说,文化是有着内在机理和价值内核的人文世界群体的生活方式。从狭义来说,文化是在满足人的需要的创造活动中形成的观念形态的价值体系。基于这样的文化界定,笔者也给生态文化下一个简要的定义:从广义来说,生态文化是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为价值内核的人类生活方式。从狭义来说,生态文化是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基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体系。
由此,展开现代生态文化的若干生态智慧的特征:
第一,现代生态文化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价值内核。
文化作为人的存在方式,是人类在改造世界、处理自身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过程中所形成的生活方式。佛得说:“在自然环境和人类行为之间,总有一个综合了具体的目标和价值、集知识与信仰于一体的‘中间项’:换句话说,就是一种文化模式。”[4]
但纵观人类文化演变的历程,人与自然的关系都是建立在对立基础上的:原始文化表现的是人对自然的盲从;农业文化体现出人对自然的顺从,工业文化即是人对自然的掠夺与征服。上述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大都是扭曲和错位的[5]。
如前所说,文化,在本质上有与自然相对立的方面,具有天然的反环境性,改变自然生态系统的原始天然性与完整性。但问题不在于文化与自然生态系统的这种对立——矛盾对立是事物 (系统)内部及事物(系统)之间的本质属性,是客观存在和客观规律,问题在于如何解决矛盾。对立不等于对抗,也不必然导致对抗,在对立中可以求得统一,求得“和合”,求得“天人和谐”。现实中人与自然的对抗,是由于人对自然的态度和作用方式造成的,本质上是人类价值观的扭曲和错位。人类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价值观,以确立一种新的正确的文化价值观,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新的文化价值观的形成除对生态危机的深刻反思外,还具有其深层科学基础和根据:即现代自然科学革命。
20世纪以来,现代科学技术出现了一系列划时代的新发现和新革命。如相对论革命、量子力学革命、混沌学革命、生命科学革命、系统科学革命(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耗散结构论、协同学、突变论、超循环论,以及非线性科学和复杂性科学)等。上述自然科学的发现开启了人类观察自然的新视角,并以崭新的方法重新构画了自然界及其演变的面貌:系统演化、复杂性、非平衡、非线性、非稳定、不可逆和不规则才是自然界的真实图景。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在许多领域也表现为模糊性、不可预测性、统计(大数)规律等。
生态科学从这场科学革命中获得了理论支持。1869年,德国的海克尔提出了生态学概念,用它来称谓研究生物体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科学,即生态学。海克尔之后,一门崭新的学科——生态科学诞生了。现代生态科学吸收与综合了物理学、化学、生物科学、系统科学等领域的最新成果,发展出一门研究关系人类及整个生物圈持续存在和演化的综合性、横断性、开放性的崭新学科。根据系统科学、环境科学和现代生态学的理论,整个地球生物圈是一个大的生态系统。生态系统是指由生物群落及其地理环境相互作用所构成的一个功能系统。它是生物群落与其环境之间由于物质循环和能量循环而形成的统一整体,是在一定时间和空间里,生物和非生物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统一体,是一种复杂的、动态的系统。人类出现后,形成人类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通过能量流动、物质循环和信息联系,人与其他生物、生物与非生物之间存在着一种生态关系,并形成一种既相互竞争又相互适应、补偿的协同进化机制,没有脱离环境而能够独立存在的生物及其种群。人类作为一个有生命的种群,也是地球生物圈这一生态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并非人类中心主义所认为的那样,处于生态系统的中心。生态系统里,各个生命系统之间以及生命系统与环境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系统中存在的复杂的反馈机制,使之处于一定的稳定状态,即生态系统的平衡。人类的生存发展依赖自然生态系统,因此生态平衡是与人类的生存、发展、命运息息相关的。认识生态平衡的重要性,了解生态平衡的规律,是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思想前提。这就要求人类对环境的开发利用必须持谨慎态度,必须尊重生态规律。生态科学所揭示的这些生态规律,使人类意识到,西方工业文化所坚持的人类中心主义是导致生态危机的主要根源,一种新的思想,将人类置于自然生态系统中、人与自然必须和谐相处的生态整体主义思想,开始得到了普遍的认同。生态学也由自然生态学扩展到社会生态学,扩展到人类的文化、精神层面上来——生态文化价值观由此形成。
我们说人与自然和谐是生态文化的价值内核,是因为这一价值理念已成为一种统揽自然、社会、政治、经济、伦理及其社会生活其他各个领域的核心观念,一种革新了的、当然也有待进一步完善的文化观的最基本的原则。
第二,现代生态文化是自觉重建的与生态文明形态相适应的一种文化模式。
笔者将狭义的生态文化界定为“是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基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体系”,是要说明生态文化建设的提出是时代要求。建设生态文化,是人类文明转向生态文明时代的必然。
工业文明出现其自身难以克服的诸多危机后,有识之士认识到要从社会文明形式的高度来反思工业文明。保罗·伯翰南1971年发表《超越文明》,其中指出,人类站在了后文明的门槛上,这种文明不同于以往的任何文明。1984年,前苏联学者开始正式使用生态文明一词,意指一种生态文化和生态学修养的提升。1995年,美国学者罗伊·莫里森在其出版的《生态民主》一书中正式将生态文明作为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文明形式。在我国,最早使用生态文明的概念的是生态学家、农业经济学家叶谦吉,他在1987年从生态学和生态哲学的视角来界定生态文明。之后,生态文明成为研究界广泛研究的重要话题。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作为党的文件首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这是对我国多年来生态文明的理论研究成果和实践成果的总结。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专辟一章对生态文明加以阐述和部署(即第八部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将生态文明建设摆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高度。报告提出“生态文明新时代”的概念,并首次把“美丽中国”作为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
何谓生态文明?这种更高级的文明形态的特征是什么?对此,国内外学者说法各异。国外学者更多的是从科学技术发展引起社会结构转型特征来说明,如后工业社会、第三次浪潮、信息社会、知识经济时代等等。在我国,叶谦吉最早从生态学的视角来界定生态文明:“所谓生态文明就是人类既获利于自然,又还利于自然,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又保护自然,人与自然之间保持着和谐统一的关系。”[6]邱耕田先生也有类似的定义[7]。俞可平曾从文明形态的角度对生态文明进行界定[8]。潘岳即将生态文化定义为一种文化伦理形态[9]。陈寿朋也侧重以观念形态来定义生态文明,认为“生态文明是人类在发展物质文明过程中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成果,它表现为人与自然和谐程度的进步和人们生态文明观念的增强”[10]。
总的说来,生态文明是一种新的文明,即较之工业文明更先进、更高级的文明,是对工业文明的发展和超越。其对工业文明的超越性表现为克服工业文明的弊端与缺陷,保证自然环境和资源的永续与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因此生态文明是指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自觉地遵守生态规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积极争取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荣所取得的积极成果的总和,是人类在处理与自然关系时达到的进步状态,是当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
文明形态的转型必然要伴随文化模式的转型。甚至可以说,只有文化模式转型的先行,才会有文明形态的转型。其中,文化模式中的价值内核的嬗变,是文明形态发生重大转变的先声。因此,从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必然要有生态文化的构建为先导。生态文化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灵魂”,而人与自然和谐这一生态文化价值内核即是生态文明“灵魂的灵魂”。生态文化就是适应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而生成的文化模式,是现代意义的生态智慧,是生态智慧的先进形态。其中,生态哲学是生态文化的世界观、价值观等的观念呈现,是生态智慧的精华;生态伦理学是生态文化在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规范方面的理性要求;生态经济学,生态法学,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等等也都是生态文化在社会生活各领域的体现;生态文化的日常生活表现是制度、规范、经验、习俗、礼仪等等。
三、应对传统生态智慧与现代生态文化做出区分
学界在使用生态文化这个概念的时候,有些学者习惯将传统社会人类那些有利于环境保护与生态维护的观念和行为,都纳入到生态文化的范畴,并认为生态文化与人类文化与生俱来。
需要指出的是: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种说法是不太恰当的,在概念定位和使用上是不够严谨的。
首先,每个文明时代都有与其相应的文化模式,即文化是一个整体的范畴。“文化模式”这一概念是由美国人类学者本尼迪克特提出的。她认为文化本质上是趋于整合的,即是一个由各部分有机结合而形成的整体,不同的整体各具特色,因此形成各不相同的具有内在统一精神和价值取向的文化模式。生态文化作为与生态文明时代的文化体系和文化模式,也是一个整体。传统社会的人们有利于环境和生态维护的观念和行为,是零星的、松散的、不成体系的,而且并未形成一种生态文化模式,与现代生态文化模式不可同日而语,只能称其为生态智慧,或者说只是生态文化的一些要素。
其次,也是最根本的区别:传统社会的生态智慧,是自发的、被动的、甚至是盲目的顺应自然的结果,是缺乏自我意识和自觉意识的集体意识或集体“无意识”,只知道“这样做”,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如果说他们做出了符合自然规律的实践活动,也是完全凭着自然节律的支配而自发、盲目形成的活动,是一种日常的情感性的意识和行为,特别是缺乏主动性和创造性,具有浓郁的自然主义色彩,并主要以宗教、经验、习惯、风俗等表现出来。即使会上升到哲学层面,也是带有直观、直觉、感悟、猜测的性质。尽管甚至有的凭直觉感悟能直抵宇宙奥秘的某些真谛令现代人感到震惊,那也只是对自然与人文关系某些现象的直觉或感悟,只是获得了某种程度的“抽象的规定”,而没有达到和形成“理性的具体”。而现代生态文化是一种文化的自觉形态,是建立在现代生态科学研究成果基础上、理性地认识了生态系统及其规律、自觉摆正人在自然中的位置和作用,主动追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目标的结果,是理性的、主动的、自觉的和创造性的价值观念体系和生活行为方式。所以说,现代生态文化与传统社会的生态智慧或“生态文化”是有明显区别的。
当然,现代生态文化建设必须吸收传统生态智慧作为自己的养料即精神资源,并对其加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但更根本的是:生态文化将是对工业文明人类中心主义文化模式的 “颠覆”——颠覆几个世纪来一直支配人类为了自身需要而企图征服自然、疯狂地掠夺自然、为所欲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这场“颠覆”意味着一种文明范式的转换,即从工业文明时代向生态文明时代的重大转型。
结论是:我们要着力构建的是生态文化模式——现代意义的生态智慧、生态价值体系、生态生存与生活方式。这一话题放在当代中国语境中,就是要积极落实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的发展战略,就是要大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化,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并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化的建设、传播、教育和熏陶,培育社会大众的生态意识,造就具备生态文明理念、特别是生态价值观念和生态伦理规范的生态人格、生态公民,从而使广大人民群众在积极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自觉地承担起保护自然环境、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平衡、美丽和持续发展的使命与责任。我们相信,通过大力建设和发展生态文化,将为推进生态文明进程、开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和智力支持。这,也就是我国生态文化建设的价值目标和宏伟蓝图。
[1]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51.
[2]余谋昌.生态文化:21世纪人类新文化[J].新视野,2003(4):64.
[3]卢风.论生态文化与生态价值观[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93-94.
[4][英]米·凯尔顿.环境决定论与文化理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51.
[5]余达忠.生态文化的形成、价值观及其体系架构[J].三明学院学报2010(1):21.
[6]成亚威.真正的文明时代才刚刚起步——叶谦吉教授呼吁开展“生态文明建设”[N].中国环境报,1987-6-23.
[7]邱耕田.三个文明的协调推进: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基础[J].福建论坛,1997(3):24.
[8]俞可平.科学发展观与生态文明[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4):4.
[9]潘岳.中国国情国力[J].中国国情国力,2006(10):1.
[10]陈寿朋.浅析生态文明的基本内涵[N].人民日报,2008-1-8.
关于生态智慧与生态文化的若干思考
赖章盛, 吴丹
2095-3046(2015)02-0082-05
10.13265/j.cnki.jxlgdxxb.2015.02.018
G07
A
2014-12-1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13BKS039)
赖章盛(1955- ),男,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生态文明与生态文化等,E-mail:lzs5583@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