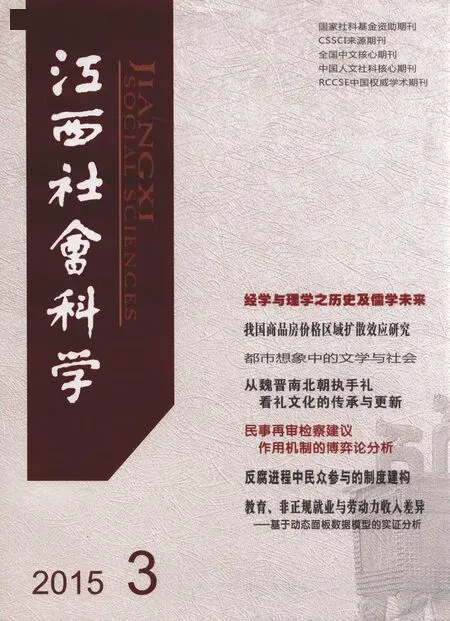古代礼学“乐”观念新诠
刘 舫 陈居渊
古代礼学“乐”观念新诠
刘 舫 陈居渊
中华文明又称“礼乐”文明,一般研究者在探讨礼乐关系时,往往认为“乐”就是古代进行祭祖典礼活动时使用的音乐。实际上通过对“乐”的字义分析和传统乐义的辨析,可以发现,音乐不仅是指“乐”的器物,还包含了更深层次的来源于人性的好恶的情感,即“乐合同”。“礼乐”并不是“礼”和“乐”的简单结合,而是互根互济的整体,“乐”在古代礼学中并不从属于“礼”,而是研究礼时所不能忽略的理论基础。
礼乐;礼学;乐论
刘 舫,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
陈居渊,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师范大学中国礼制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上海 200433)
“中华文明”又称为“礼乐文明”。礼乐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得以维系和发展所依赖的一个完整的制度系统,它由古代最高统治者制定,即“制礼作乐”。“礼”是指社会的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历代研究对此有非常详备的阐述。而对“乐”的指向,目前大多数研究将其框定为古代人们进行典礼时所用的音乐,并且认为 “作乐”的实质是通过音乐的和谐之声来调和古代等级森严的人伦关系,从而与礼形成互补,以达到社会平衡的效果。然而早在两千年前,孔子在《论语·阳货》中就提出了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的质疑。因此怎样理解“礼乐”之“乐”?何谓“乐同”?又如何认识“礼乐”关系?对此,本文尝试作一些新的探讨,以求教于大方。
一、“乐”义辨析
“乐”,一般是指古代祭祖典礼中的钟鼓之音。《说文解字》释“乐”为:“五声八音总名,象鼓鼙。木,罛也。”《尔雅·释训》云:“罜罜,乐也。”《周颂·执竞》:“钟鼓罝罝、磬罞将将。”郑玄解释为:“祭祖考之庙,奏乐而八音克谐。”[1](P589)“乐”的初始含义为架在木上的鼓之象形,这种解释直到清代并无异议。近人罗振玉以甲骨卜辞为据,提出新说,认为“乐”即“从丝付木上,琴瑟之象也。……许君谓‘象鼓鼙。木,罛’者,误也”[2](P40)。其实,“乐”作为儒家经典,与《诗》、《书》、《礼》、《易》、《春秋》并列为“六经”之一。《乐经》虽已亡佚,但关于“乐”的记载却散见于《诗经》、《尚书》、三《礼》、《史记》以及先秦诸子等著作中,其中又以《礼记·乐记》最为集中。从这些文献记载来看,“乐”的内涵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用音符谱曲的 “比音之乐”,即音乐,如《礼记·乐记》云:“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二是“行礼之乐”,即典礼活动时所配的音乐,如《仪礼·乡饮酒礼》云:“乃合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苹》。”三是“人情之乐”,如《荀子·乐论》云:“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由此,一般学者都认为,“乐”就是指古代举行典礼时使用的音乐。由于古代的“乐”是一个比较完整的音律体系,不同场合的音乐,其类型和曲目也有种种不同的区别与功能,同时也往往表达出多种多样的思想感情。周谷城曾经指出:“所谓乐者出于人心,布之于管弦云云,即音乐的意思……把快乐用乐器表现出来,即成音乐。快乐、音乐、乐器三种意义,都是乐字所具有的。”[3](P435)这样,就把“乐”理解成有形的音乐和器乐了。
然而,将“乐”理解为纯粹的“音乐”或者“器乐”,这在古代并不是定见,如孔子当时就提出了“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的质疑,《礼记·乐记》中对“乐”作了这样的解释:“乐者,非谓黄钟、大吕、弦、歌、干、扬也,乐之末节也。”“干戚之舞非备乐也。”“故人不耐无乐,乐不耐无形。形而不为道,不耐无乱。先王耻其乱,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这说明将“乐”仅仅理解为用来满足人的感官,或者说是起着修饰和陪衬人的情感的作用,显然不是“乐”的根本所在,而是“乐”的“末”,即所谓“乐之末节”、“乐之形”。在孔子看来,真正的“乐”,应该是体现“世治”与“政和”的《雅》、《颂》之“乐”,即所谓“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由此可以看出,乐舞其实是一套表意系统,通过音乐和歌舞的恰当来传递信息。《礼记·乐记》说:“是故古之君子不必亲相与言也,以礼、乐相示而已。”考《仪礼》中记载的诸侯卿大夫之礼,如觐、聘、射、燕、馈食等礼仪中,用“乐”都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并且根据礼仪的不同和参加者身份贵贱,有一套严格的用乐规制。如:“凡射,王奏《驺虞》,诸侯奏《狸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蘩》。”[4](P1892)这种等级分明的“乐”,并不完全是为了点缀古人行“射礼”的仪式,而是与仪节相配合,生动地传达着行射礼者的用意。如《仪礼·士丧礼》中所载的“主人要节而踊”、“踊无算”、“哭成踊”、“拾踊”等(详见《仪礼·既夕礼》),这些也都可视为古代“乐”的另一种形式。“乐”不仅是单纯地使用乐器弹奏出音律,还包含了曲、歌、舞,如《左传·隐公五年》记载:
九月,考仲子之官,将《万》焉。公问羽数于众仲。对曰:“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故自八以下。”公从之。于是初献六羽,始用六佾也。
《万》是古代宫廷舞蹈的名称,舞者手持羽毛和乐器起舞。舞者人数的多少象征了主人身份的贵贱,人数越多说明身份越高,舞蹈的场面和效果自然更加恢宏,然而孔子却认为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士可忍,孰不可忍”,正说明“乐”不仅包括音符、乐器、舞美,更主要是彰显其中所蕴含的人文义涵。由此看来,“乐”并不是为取悦感官而作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仍需要眼、耳、身的体验,但只是经由感官进入,其真正的指向是“心”,目的是感人心。《国语·周语下》说:“夫乐不过以听耳,而美不过以观目。若听乐而震,观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枢机也,故必听和而视正。”这里的乐虽仍指音乐,却强调了心的作用。五官是心的枢机,虽然心控制五官,但五官所接收的内容却影响塑造心。欢乐的感觉是官能的感觉,是直接的感觉。《礼记·乐记》说:“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孔颖达疏云:“乐出于心,听之则欢悦,是情之不可变也。”这里的“情”并不是“听之欢悦”的感情,而是引发听之欢悦的音乐蕴含了符合人性的节律,因而心产生了乐的情感,只有这样的情感才是 “不可变”的。所以孙希旦补充解释道:“人情万变不穷……天下人情皆管摄于是而不能外。”[5](P1010)“万变不穷”的人情和“管摄于是”的情感,两者有着很大的区别,前者是应物的直接表现,而后者则源于德性的实现。所以《礼记·乐记》又说“君子明乐,乃其德也”,郭店楚简《五行》简二九:“和则乐,乐则有德。”可以说这里所谓的“德”,其实就是“君子乐得其道”的另一种说法而已。
至于如何来体现这个“乐”,《论语》中有两处记载。一是《述而》篇:“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二是《雍也》篇:“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这里所说的就是人们津津乐道的 “孔颜乐处”。《庄子·天道》说:“夫明白于天地之道者,此谓之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这是庄子的乐处,他的乐更不牵扯任何声色,已与天地泯化。儒家和道家的“乐”,表明古人已经意识到摆脱感官的嗜欲,去寻找一种不依赖外界的属于人类的自足的情感。《礼记·孔子闲居》记载孔子的话说:“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此之谓三无…… ‘夙夜其命宥密’,无声之乐也。”孔子在此处引用《周颂·昊天有成命》解释“无声之乐”,认为是“言成王夙夜积德,以承藉乎天命者甚宏深而静谧”[6](P1276)。成王体会到了传承天命的真谛,那就是延续先王们的德行,“无声”之乐,即不是通过有形的表达方式,如语言、音乐等,而是通过心灵传递的共同的志趣,这样的情感不会随着时间而改变,因而人类的德性得以延续,这也许就是“乐”的本义所在。
二、“乐合同”释义
“无声之乐”固然只有圣人才能体验,但是“乐”不是个人内在境界的追求,而是人之为人,总是在寻找这种适宜情感的要求。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天赋的能力,不役于物而能役物,以及摆脱物诱后所引发的情感。由于这种情感,往往是建立在“乐”的基础上的,并且为人们所普遍接受与认同,故可称“乐合同”。
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孟子·告子》)
耳之欲五声,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此三者,贵贱愚贤不肖之若一,虽神农、黄帝与桀、纣同。圣人之所以异者,得其情也。(《吕氏春秋·情欲》)
古人很早就区分了五官、五官的对象、五官因对象而引起的感情这三者,不仅如此,他们还发现了心不像五官直接开放于外物,但却会像五官对外物有反应一样产生情感。在这个意义上,心和五官没有区别,所以古人推断,既然在声色美这些方面,无论贵贱愚贤都能取得一致的好恶,那么心应该也可以。所以说“人心之有二取,名好、恶”[6]。也正是如此,那么“我心”也就同然了,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合情合理”。
从理论上说,“我心之所同然”是人人都应具备的。然而,情感上的“贵贱愚贤不肖之若一”和事实上的 “圣人先得”,表明一般人生来并不清楚自己的禀赋。《管子·禁藏》说:“凡人之情得所欲则乐,逢所恶则忧,此贵贱之所同有也,近之不能勿欲,远之不能勿忘,人情皆然,而好恶不同,各行所欲,各以所欲行之,而安危异焉。”“君子志道”和“小人志欲”,两者所获得的“乐”的内容不同,但情感是一样的,而要让小人见欲则恶,见道而乐,却要经过教化。也就是说,“乐”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在教育中设计和引导的。《周礼·春官·大司乐》云:“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礼记·文王世子》云:“凡学,世子及学士,必时。春夏学干戈,秋冬学羽龠,皆于东序。小乐正学干,大胥赞之。龠师学戈,龠师丞赞之。胥鼓南。”乐官一个很重要的职责是教育贵族青年,内容是传授典礼中的乐舞,前文中说过,古代的乐舞不是单纯的歌舞表演,而是象征理义的身体行为,也可以说是为“心”而设计的体操,操习乐舞其实就是在实践礼义。可见,人们认为通过一定的手段和方法,众人之心是可以趋向于一个“音调”的,而这个过程就是“同”,即同好恶,其结果就是“乐同”,也就是同见礼而好,见欲则恶。《乐记》云:“乐者为同……同则相亲。”郑玄注曰:“同,谓协好恶也。”[1](P1529)《说文》:“协,众之同和也。”《玉篇》:“协,合也。”“乐”就是所有人一致的好恶判断,无论是君王还是平民,对于同一事物的美丑好坏的判断是一样的。虽然平民也许一辈子都没有机会享用到贵族专享的美味,但一旦他有幸尝到这些食物时,肯定能确认它的美味程度大大超过自己平时所食。“生,好物也;死,恶物也。好物,乐也;恶物,哀也。哀乐不失,乃能协于天地之性,是以长久。”(《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同好恶是“协于天地之性”,对君子小人遵守社会规范的要求可以是不同的,但理义的标准不能是多重的,反过来说,正是因为人们对于理义的体认是一致的,才有了君子小人的区分。子夏云:“故申之以孝慈,道之以忠敬,陈之以德义,示之以好恶,鼓其情性而民自乐其道,而不知其所以也,可谓其神矣。”(《子夏易传·系辞》“鼓之舞之以尽神”注,四库全书本)“乐”所表达的,正是协贵贱之好恶于一致,在对这个“一致”的认同上,所有人的好恶判断被要求为“同”。
《乐记》记载魏文侯问乐于子夏,子夏答曰:“夫古者天地顺而四时当,民有德而五谷昌,疾罠不作而无妖祥,此之谓大当。然后圣人作,为父子君臣,以为纪纲。纪纲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后正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此之谓德音。”李安宅指出:“乐本是有组织的音,本无善恶是非之可言,因为有感而发,本是自然而无伪的。但儒家的习惯,无论什么东西,无论怎样自然,都非与以善恶是非之评价不可,如性有善恶之类,所以乐也不能逃出例外,因此,就将音分为德音与溺音,溺音谓之音,德音谓之乐。”[7](P29)“德音”并非指歌颂道德的音乐,而是圣人把父子君臣的纲纪作为理义的条目颁布给社会。所谓“宫商角徵羽,五声之名也。君臣民事物,五声之实也。实治则声从而治,实乱则声从而乱”[8]。这里的“声”就是音乐,统治者的“雅乐”歌颂的是人人向往的太平盛世,而真实地反映社会风气的则是民间传诵的歌谣,如《诗经》中为人熟知的“郑声淫”就不被称为“乐”。也正因此,光有美好的道德愿望是无法实现于社会的,这种道德追求只有通过成为曲调,成为典故,把一个个教条化为生动的故事,成为人们津津乐道、口耳传唱的有形之乐,才能深入人心。“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皆形见于乐”,乐的丰富主题表现的即是人们对于理义的理解和反响,即所谓“乐与民情无间然矣”。乌程姚氏亦谓:“律小大之称,比终始之序,以象事行。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皆形见于乐,故曰:乐观其深矣。”[9]此时也就达到了真正的“乐和同”了。
三、乐—礼:同与异的实质
分析了“乐”和“乐同”的含义后,就可以重新审视礼乐关系,前人的研究基于“乐”是举行典礼时的音乐,认为“乐”的作用体现了君王与民同乐的精神,民众因为获得了音乐的享受,从而更加崇敬君主,尊敬诸侯等。不可否认,在礼仪上演奏的音乐旋律,如《清庙》烘托祭祀的庄重肃穆,《四牡》、《皇皇者华》表达君臣之懿,在“观礼乐”这点上,礼和乐的相互配合也可以解释得通。所以当“礼乐”并称时,一般认为指的就是行礼和用乐,如,杨向奎认为:“‘乐’属于与‘礼’结合在一起的‘仪’。”[9](P352)陈戍国认为:“礼与乐的关系,礼当然是占主导地位,而乐的作用不可轻视……礼乐各有各的作用,但乐必须服从礼。”[10](P51)这种“礼主乐从”的看法正是基于把“乐”理解为“用乐”,由于“乐”相对“礼”而言的单一内容,进一步解读结果即是“销乐归礼”,也就是“礼典用乐即是行礼”[10](P352)。因此乐往往被认为从属于礼,原因是礼有 “仪”和“义”,而乐似乎只有“乐曲”可与“礼仪”相当,那么乐的精神仍要从礼那里借来,于是“作乐”就成了“奏乐”。不仅如此,由于“礼”已经包含了教化和实践的意思,如昏礼寓意男女有别、射礼寓意长幼有序、丧服寓意贵贱亲疏等,人们通过礼仪的实行逐渐加深对礼义的体会,从而使礼义观念深入人心,社会形成按照礼的规定和精神处断行事的共识,从而达成各得其所,各行其道的社会秩序。这样看起来,“礼”的思想和手段都非常完备,对于社会已经足够,所以才会有“乐”从 “礼”,即乐是辅助完成礼的手段之类的观点。然而,既然“制礼”已经如此周备,那还需要“作乐”何为?如果“乐”只是缘饰,那么没有“乐”的“礼”仅仅是缺少了乐舞之声吗?
从《诗经》来看,乐器、乐舞为多见,而《周易·豫·象传》云:“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也是指具体的乐事。根据罗倬汉的考证,“礼乐”连称始于祭礼,但具有超出具体事物的含义,则始于《论语》:“礼为合理,为人生规检之义,已彰于《诗》《书》,而乐之事,若如《三百篇》之言,则去抽象理法之义仍甚远,故在《诗》中仅有礼器、乐器、礼事、乐事之散出,俱不能成为二者相须为用,以资人生之大法。其举乐以配礼,使乐亦如礼之超于个别事为而的人生范型之义者,据今存典籍,端自《论语》始。”[11](P46-52)证之《论语·学而》:
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礼对人人相同之求做了一个“分”,贵贱、男女、长幼的规定要求每个人“各安其分”,不去觊觎别人的所得。所谓“礼者,序也”,礼的实质是差别。然而,既然君王之欲与平民之欲相同,那么为什么君王得到的物享与平民的相去甚远,却又能够要求每个人都俯首帖耳、安之若素呢?这仅是对生来的身份贵贱进行规定就可以解决的吗?把“相同”变成“差别”仅依靠礼制的规定就可以成就的吗?
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简二二载:“笑,礼之浅泽也。乐,礼之深泽也。”笑是礼浅层的表现,而乐是礼深层的表现。“笑”和“乐”区分开来,说明“乐”不是指快乐的意思,而是比快乐更深层次的情感。简文“礼”作“罣”,又《集韵》“樂,羨,娱也,或从心”[12](P724),两者从字形上看都从心,“乐”是悦心之乐,是在为礼时产生的愉悦的情感,让具有“相同”之欲的人成为不同身份的人,其中的紧要之处正是“同好恶”的“乐”的情感。《管子·牧民》说:“先王之治天下……取天下之同好共恶而制荣辱焉。”天下好“节”以为荣,恶“不节”以为辱,于是“好恶形于心,百姓化于下”,逐渐形成社会的价值取向,在处于相同的境况时,无论身份贵贱,人们的好恶判断是一致的,正因为有了这个一致的好恶感,人们才会谨于“守分”,不敢有“非分”之举,所谓“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共同的好恶情感导向的是人伦的清明,贵贱男女长幼的秩序得到保障,“上所化谓之风,下所习谓之俗,迁此之彼为移,更有为无曰易”[9]。在舆论和自省的双重作用下,人们知道隐藏或克服私欲,融入社会倡导的中道里。可见,“乐”所体现的是一种凝聚了众情之好恶的人伦体系,而这种体系中的人伦秩序正是礼所需要的。所以《乐记》云:“知乐则几于礼矣。”礼所倡导的“安分守己”之可能,正是源于个体分得了众人之所“乐”,即人伦之德,从而“乐”于遵循,并以之为“乐”。由此可见,“乐”使礼的“差等”的实质通过“合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果没有“乐”,无论礼意还是礼仪都不是由(众)人之(公共)“心”而发的,只是僵死的规定性而已,人们或许表面上遵循着礼,但内心并没有产生与之呼应的情感,也就不可能在遇到新的情况时自发产生相同的情感,从而也不会形成“共义”的秩序,而是出现各人各义的局面,那么礼秩也就无从着落。
“礼乐”并不是“礼”和“乐”的简单结合,而是互根互济的整体,清儒汪绂说:“礼乐二者,不惟相须,而实相合。……分之则为二体,其本则只一原;犹阴阳之循环无端焉。”[13]“礼乐”并称时,乐指与礼的“差序”互相资用的“和同”。礼乐是经天纬地的法则,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每个组成部分都按照各自的“分”有序地运行,礼的用处便是把这个“分”建立起来,也就是规定边界,通过劝导人们节制自己的欲望以及行为来不断强化这个无形的区分。与此同时,乐的用处便是把执“分”的各部分稳定下来,使人们各行其道,各安其命,但同享共乐,即《中庸》所说的:“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一方面天地之间万物各具其理,体现了礼的“异”,另一方面万物又遵循天道,流行不息。可见,万物以礼异,以乐合,形成一个万变不离其宗的整体。因此,“乐”在古代礼学中并不从属于 “礼”,而是研究礼时所不能忽略的理论基础。
[1](清)阮元.十三经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2]罗振玉.增订殷墟书契考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6.
[3]周谷城.礼乐新解[A].周谷城学术精华录[C].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4](清)孙诒让.周礼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7.
[5](清)孙希旦.礼记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9.
[6](唐)释玄应.一切经音义·俱舍论(卷十七) [M].清海山仙馆丛书本.
[7]李安宅.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8](元)陈罤.礼记集说[M].民国嘉业堂本.
[9]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10]陈戍国.先秦礼制研究[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
[11]罗倬汉.论礼乐之起源[J].学原,1947,1(7).
[12](宋)丁度.集韵[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3](清)汪绂.乐经或问[M].续修四库全书本.
【责任编辑:王立霞】
K203
A
1004-518X(2015)03-0126-06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礼制变迁及其现代价值研究”(12&ZD134)
——论庄子之“物无贵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