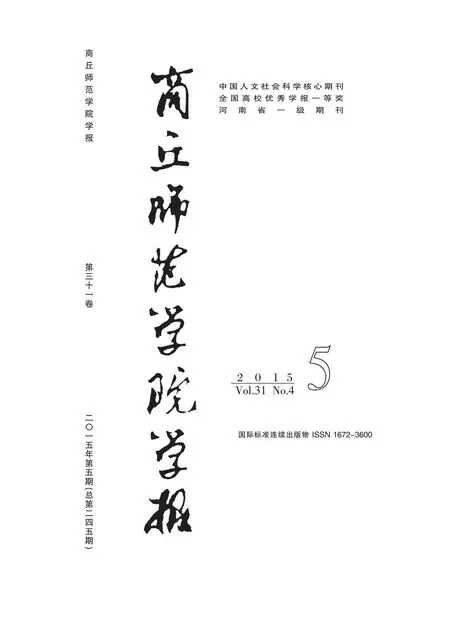语言符号的任意性、理据性与翻译的复杂性研究
轩 治 峰
(商丘师范学院 外语学院,河南 商丘 476000)
语言符号的任意性、理据性与翻译的复杂性研究
轩 治 峰
(商丘师范学院 外语学院,河南 商丘 476000)
自从索绪尔提出语言符号任意性的论断之后,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理据性就成了人们争论的焦点,而且还有一些误读。其实索绪尔的语言符号任意性理论不是造成翻译的主要障碍,造成主要障碍的是人类认知思维的任意性。对人类认知思维任意性作深入、透彻研究,再从繁杂的任意性中找到相互转换的规律,则是翻译研究所要重视的。
语言符号任意性;理据性;翻译的复杂性
自从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出版之后,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理据性就成为语言学家们争论的重点。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的任意性是第一原则。他在书中说:“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们所说的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相联结所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更简单地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1]101-102对此观点,支持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在国外,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形式主义语言学派将索绪尔的“任意性”发挥到极致, 其认为语言是独立于其他认知智能之外的一种任意的自主的形式系统,语言的能指与所指之间毫无关系可言。美国描写语言学派后期的代表人物霍凯特(Charles F.Hockett)也把任意性列为语言的基本属性[2]4。 我国语言学界的大多数学者如陈望道、岑麒祥、高名凯和桂灿昆等人也基本上接受了这一派的观点。直到现在,王德春(2001)和郭鸿(2001)等人仍对索绪尔的观点坚信不疑。然而,反对的声音也此起彼伏。例如法国知名语言学家邦尼斯特(E.Benveniste)就反对任意性,他说:“符号根本没有日内瓦学者所设想的那种任意性。确切些说,符号对外部世界来说是任意的,但在语言中它却不可避免要受到约束,因为对讲话人来说,概念和语音形式在他的智力活动中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共同执行其功能,而语言形式,如果不与概念相对应,便不可能为理智所接受”[3] 305。在认知语言学兴起之后,国外一些学者如雅可布逊、霍珀、汤普森等对索绪尔的论点提出了质疑,并从语言结构的相似性着手,论述了语言符号的理据性。我国学者许国璋先生以及后来的沈家煊、严辰松、王寅等人也从语言符号的相似性入手探讨了这一问题。然而,折中派的学者也大有人在,如周庆光(2004)、王艾录(2003)、李二占和张文鹏(2005)、韩昆和安福勇、李金学和范进科(2006)、李鑫华(2005)、钟帆(2008)等都认为,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理据性是对立统一的。然而,对于语言符号在何种情况下是任意的,在何种情况下是具有理据性的,任意性和理据性都表现在哪些方面,学者很少论及,特别是对人类认知世界的任意性和各种语言间各种相互的交错论述者更是甚少,因此,笔者拟从这些方面论说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理据性,并对人类认知世界的任意性在语言中的反映和翻译的复杂性予以探讨。
一、对索绪尔语言任意性的解读
要谈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就要弄清楚什么是任意性。在此,索绪尔所用的词是arbitrariness,是由形容词arbitrary派生出来的。根据《柯林斯英汉双解大词典》,arbitrary 的含义为:“ If you describe an action, rule, or decision as arbitrary, you think that it is not based on any principle, plan, or system.It often seems unfair because of this.”意为“若将某个行为、规则或决定描述为arbitrary, 你则认为这一行为、规则或决定并非基于任何准则、计划或体系”。也就是随心所欲,不受约束。索绪尔在谈到任意性时说:“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联系是任意的。既然我所说的符号指能指与所指联系起来产生的全部结果,我可以简单地说:语言符号是任意性的。”他举例说:“‘sister’一词的意义与法语词的能指‘s-o-r’之间并没有内在联系;这个意义在不同的语言中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并且在不同的语言中也都有一个方式表达这个意义;‘ox’一词在国界的一侧用‘b-o-f’表达,而在国界的另一侧则用‘o-k-s’来表达。”[1]103这是说,名和事物之间没有联系,对一个事物,人们可以随意地给其命名。此观点有没有其合理性呢?
可以从三方面去理解这一问题。其一,从绝对的方面来讲,能指和所指或名和物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这就如一个人,生下来之后父母要为其命名,所命的名字与这个人没有必然的联系。如一个人的名字叫“大山”,但这个人跟世间所存在的“大山”没有一点联系。之所以称呼某人(他/她)能有所反应,是人为的,不是固有的。能指和所指或名和物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客观事物是固有的,而各语言中为它们命的名不是固有的,而是人为的,是将名字强加在客观事物上的。这正如《金刚经》中释迦牟尼所说:“佛告须菩提:‘是经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以是名字,汝当奉持。所以者何?须菩提,佛说般若波罗蜜,即非般若波罗蜜,是名般若波罗蜜。’”[4]78-79“须菩提,诸微尘,如来说非微尘,是名微尘。如来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4]152“须菩提,若菩萨作是言:‘我当庄严佛土’,是不名菩萨。何以故?如来说庄严佛土者,即非庄严,是名庄严。”[4]106-107释迦牟尼之所以反复用这种句式,就是告诫人们,不要执著于名,不能完全表达客观事物或概念,能指和所指或物和名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其二,从不同语言间来讲,在人类部族之间没有交往,处于封闭状态时,各部族为其所处环境及所遇事物命名相互不受影响,你这样命名,我这样命名,这也是任意的,没有规则可循。如汉语中的“火车”,英语是“train”,日语是“汽車”,德语是“Zug”,希腊语则是“tre’no”,从这方面考察,索绪尔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其三,语言符号是人类在认知世界的基础上给世界万事万物赋予的名称,反映着人们认识世界的痕迹。然而,不同语族的人在相互不交往的情况下对世界的认知也是任意性的。特别是语系间无亲缘关系的不同语言间,这种任意性更为凸显。这种任意性主要体现在范畴化、认知视角、隐喻化和换喻化等方面。世界万事万物虽然为人类共有,但对其范畴化或分类并没有共同的标准,都是各自按照自己的标准任意划分,任意命名。如对动物的分类,在汉语中,“鹅”和“大雁”是两类动物,而英语却将其归为一类动物“goose”,鹅在英语里是goose,大雁在英语里是wild goose,差别只在于野生或家养。再如对卵生动物的Egg的分类,这一单词在英语中是我们最熟悉的单词了,但就其所指,汉语中与其真正匹配的对等语是什么呢?真正按生物科学上讲,只有“卵”与其相对应,“卵”是指母体中经过受精就能够产生生命的细胞。英语中的egg可指所有这类细胞。然而,在汉语中,鸡鸭等鸟类所产的卵分类为“蛋”(如鸡蛋、鸭蛋、鹅蛋、鹌鹑蛋、鸟蛋等),昆虫和鱼产的卵叫“子儿”(如鱼子儿、虫子儿、蚕子儿等),而虱子所产的卵又叫“虮子”。范畴化任意性更为明显地表现在人们对空间概念的范畴化中。不同语言对空间范畴的划分都是根据自己族群的认知划分的,各族群之间没有规则可循。如对空间“上”和“下”概念的范畴化分,汉语把高于一个平面的概念都称之为“上”,把低于一个平面的概念都称之为“下”。而英语对这两种概念的划分则相当复杂。这里不多赘述。而对于动作行为和抽象概念的范畴化的任意性则最为明显。无论考察哪两种毫无亲缘关系的语言,都会发现这种范畴化上的任意性,如汉语的“说”,汉语范畴化或分类是按照文体的差别而分类的,如“说”、“谈”、“讲”、“言”、“道”、“曰”、“云”等,而英语中却按使用搭配的方法分类,如“say”、“speak”、“talk”、“tell”。汉语中以上同义词只是在适用场合上有差别,基本概念都是相同的。但英语中以上同义词表达的是不同的概念,在搭配和使用方法上都不相同。再如英语的“carry”,其基本意思为“to support the weight of sb/sth and take them or it from place to place; to take sb/sth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这一概括性极强的词语在汉语中找不到表达相同概念的词语。只有在具体使用中才能有“拿、提、搬、抗、抱、背、携、夹、驮”等具体语境中的对等语。这种现象的出现也是不同语族人对世界认知的任意性的表现,也是语言符号任意性在另一方面的具体表现。
然而,从另一重角度讲,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又是无法站住脚的,这就是语言符号的理据性。
二、语言符号理据性解读
虽然索绪尔的语言符号任意性有它合理的一面,但一旦涉及一种语言系统,语言符号任意性的合理性就要大打折扣,理据性就会上升。这是因为,任何一种语言都是一个体系,一种语言的语言符号之间必然要受到各种规范的约束。理据性在英语中称做motivation,是与任意性相对,其意思是指一切类型的语言符号发生、发展的自组织动因,也指语言系统外因素对语言的制约。理据性也常被定义为“非任意性”,如Hiraga[5]就将理据性定义为“the term ‘motivation’…signifies the non-arbitr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m and meaning.”(理据性这一术语指语言形式和意义之间非任意性的关系)。 Lakoff[6]448则将其定义为“可解释性”,其原话是:“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 and B is motivated just in case there is an independently existing link, L, such that A-L-B ‘fit together’.L makes sens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 and B.”(只有当A和B之间独立存在某种联系L时,A-L-B “相互匹配”, L解释A和B之间的关系, 那么, A与B之间就是有理据的) 。而Croft[7]102则又强调了经验结构的作用,他说:“the structure of language reflects in some way the structure of experience, … The structure of language is therefore motivated or explained by the structure of experience to the extent that the two match.”(语言结构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经验结构……因此,二者相匹配时,经验结构为语言结构提供理据,即经验结构解释语言结构。)由以上三个定义和Haiman等人的定义,李福印[8]43将理据性归纳为“理据性指的是语言形式和意义之间的一种非任意的、可论证的、意义激发形式且形式反映意义的关系。
理据性首先是一种特定语言系统的语言特性。根据郭中(2007)、李二占(2010)、何静(2007)、李二占和张文鹏(2005)、何熊(2006)、孙红丽(2005)、林艳(2006)、周庆光(2004)等人的研究,语言符号的理据性表现形式为:1.语言系统内部的制约性;2.一种特定语言的语言符号在发音和语义之间的理据性;3.语言系统内部语言符号、语言书写符号及其构词的理据性;4.语言系统内部句法的理据性;5语义发生的理据性;6.语言相似性等。这些理据性,在任何一种语言内部都会具体体现出来。比如一个人,出生之后父母要为其取名,这时存在着可选择的任意性,但同时又必须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首先要考虑的是,孩子的名字里必须包含他/她家族的姓氏,这无论是中国或是外国基本上都大致相同。其次要有排他性,父母给孩子取的名字必须不能和其家族或近邻的名字相同,要具有专指性。再者就是父母的理念或对孩子的期望,要吉利、大气。若加上取名的宗教迷信,汉语中要按照五行相生相克,英语中要遵照基督教、天主教的习俗,取名时就有更多讲究。这里就包含着在取名时所受到的外部制约和姓名符号产生的动因。所以任意性就大大降低,理据性就凸显了出来。在一种语言中,这一语族的先人在给世间万事万物命名时也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律。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物名的排他性,即这种事物的语言符号必须区别于另一事物的语言符号,否则就会造成语言上的混乱。比如,无论在哪种语言中,在为水果命名时,不同的水果名字肯定不同,没有一种语言把表示“苹果”的符号再用来表示“橘子”的。汉语中的“苹果”为什么发音为“pínɡ guǒ”,其动因只有古人知道,橘子为什么发音为“jú zi”,其中也必有动因,只是我们不了解罢了。但在给水果命名时,先人绝对要遵守排他性原则。
对于语言发音上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除了从拟声这方面探讨其理据性之外,很少再能找到证据,这是因为除了拟声词外,其他此类的发音的形成是无从考证的,因为在古代人们没有记录声音的工具。但人们可以从训诂学、音韵学中找到一定的理据。
而文字则是有可考的证据,文字符号的形成的理据性在中西方语言中都可以找到。对于汉语而言,许多学者都从汉字的起源论证了汉语文字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理据性,从最早的《尔雅》到东汉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从清代王念孙的《广雅疏证》、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郝懿行的《尔雅义疏》再到现代王显春(2002)的《汉字的起源》、郑慧生(1996)的《中国文字的发展》、王宁的《训诂学》,无不展现了汉字语言符号的理据性。对于英语语言符号的理据性考察,我们不妨读一下邓万勇(2006)的《英语字母研究》和马秉义(2005)的《英语词汇系统简论》,其中英语语言符号的理据性也会一目了然。
其次,不同语言系统间语言符号之间也存在理据性。其原因有二。其一是因为,凡是人们形成一个社会共同体,进行相互交流时,都要有一种规则制约,如在联合国,虽然联合国有多种工作语言,但在对每项重大国际事务进行商讨、辩论或作出重大决议时,各种措辞又必须具有一定的理据性,而且翻译成各种工作语言时,措辞与所指事件或所指概念必须一致,否则就会造成混乱,无法达成共识。其二是不同语言的相互渗透或影响。在当今世界上,各个国家都进行相互交流,语言间相互影响在所难免。愈是相邻的地区,不同语言的相互影响力就愈大,词汇的渗透、语法的渗透都会发生。如英语和法语、德语,汉语和日语、韩语,甚至梵语,之间语汇的相互借用,表达方式的相互影响,随处可见,这也是语言符号理据性的具体体现。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为什么叫现在美国总统为“奥巴马”?其理据就是Obama在英语里的发音就是如此,这是模仿其声音。再问美国人为什么这么叫他,那是因为他出生在这个家族,父辈、祖辈就是这个姓氏,再往下追问,还能找出理据。America 一词在汉语中被译成“美国”或“美洲”,这一词语也是一样,都是语言间语音相似性的理据性在起作用。
三、语言符号任意性、理据性与翻译的复杂性
语言符号的任意性特征造成了不同语言间的差别,这种差别不仅仅是语言符号的声音或书写符号的不同,更是由于人类认知的任意性所造成的不同语言的语言符号和语义之间的纵横交错。在英汉两种语言中,很难找到语义完全对应的词语的主要原因,就是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人类认知的任意性。汉语在语音和文字上的最小表义单位都是单音节的字,而英语的都是词素或单词,音节不像汉语都为单音节,而是单音节多音节都有。汉语给事物命名大都按照汉人特有的认知方式命名,如“汽车”就是汽车,表示由燃料为汽油的引擎所驱动的在公路上行走的车,命名的依据是这种工具带有轮子,并靠轮子转动而行走,属于汉语的“车”之类,又因其燃料是易挥发的“汽油”,故命名为“汽车”。而英语里就没有“车”这一概念分类,没有这样的命名。虽然vehicle一词含有车辆的含义,但它是指所有的交通工具,包括轮船和飞行器,其概念范畴远比“车”的概念范畴大,而且其认知思维和命名的视角跟汉语都不相同,我们若将“汽车”翻译成“gas vehicle”,就会贻笑大方,令英语国家的人不知其所云。唯一的方法就是人家怎么命名我们就怎么翻译。在美国,称其为automobile,英国英语里就没有这样的范畴,必要时就用“car”这一下义词代替。汉语的汽车一般按外观和功能可分为货车、大客车、小客车、出租车、救护车、越野车、赛车、轿车等。我们在翻译时无法按汉语的思维逐字翻译,只能随英语国家的人们说trucks、bus、passenger car、taxicab、ambulance、SUV、racing car、car或sedan等。这些词的组成都非按概念组合的方式构成,而是单独命名。Car一词的命名和所指也非汉语学习者所了解的那样只指“小轿车”或“小汽车”,同时也指有轨电车、吊篮、电梯的升降室和火车的车厢等。汉语的小轿车只指那种有双排座的且有固定车顶的轿车,即sedan,绝对不能有别的所指。在翻译car这一词时,就造成了确定词义和选词的麻烦。
由于人类认知思维的任意性和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不同语言的词语的所指在概念上相互重叠、相互延伸,造成一种语言的一个词语,在另一种语言中分散到许多词语之中,而各个词语又有自己的意义王国,再度向外扩展,形成不同语言词语概念王国疆域的纵横交错。若再加上隐喻和转喻思维,这种纵横交错的词语概念王国能织成两张不同地域划分的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让翻译者稍有不慎,就会陷入误译的沼泽。如汉语的“上”和“下”翻译成英语时,其复杂程度远非一般人所能想象到的。 “上”字远非英语的“on”、“over”、“above”、“up”等所能表示;有时它延伸到“in”、“with”、 “off”、“against”等词语上,有时则要隐身,变得无影无踪。“下”的翻译也同样。另外,一种语言中有对某一概念的命名,有的则没有,而是用描述法表示;有的词语涵盖的只是另一种语言词语的一部分,有的是几个词语的综合。翻译时的概念整合、重组又给翻译造成了困难。
总的来说,索绪尔的语言符号任意性理论不是造成翻译的主要障碍,造成主要障碍的是人类认知思维的任意性。对人类认知思维任意性作深入、透彻研究,再从繁杂的任意性中找到相互转换的规律,则是翻译研究所要重视的。
[1]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2版)[M].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2.
[2]霍凯特(Charles F.Hockett.)现代语言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3]石安石.语义研究[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8.
[4]金刚经 [M].吕祖,济佛,注解.海口:海南人民出版社,1994.
[5]Hiraga, Masako K..Diagrams abd metapgors: Iconic aspects in language[J].Journal of Pragmatics,1994(22).
[6]Lakoff, George.Woma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World [M].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
[7]Croft, Willian.Typology and Universals [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8]李福印.认知语言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郭德民】
Arbitrariness of Linguistic Signs, Motivation and the Research of the Complexity of Translation
XUAN Zhife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gqiou Normal University, Shangqiu, Henan Province, 476000)
Ever since Saussure out forth the theory of arbitrariness of linguistic signs, the argument between the arbitrariness and motivation of linguistic signs has become one of the focuses in linguistic studies.Besides, there are some misunderstandings about the theory.After the interpretation the arbitrariness and motivations of linguistic signs,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lativity of arbitrariness and motivations of linguistic signs and the complexity of translation.
arbitrariness of linguistic signs; motivations; complexity of translation
2014-12-05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英汉词语语义疆域认知对比与翻译机制研究”(编号:2011BYY006)。
轩治峰(1957—),男,河南睢县人,教授,主要从事认知语言学、语言哲学与翻译研究。
H059
A
1672-3600(2015)05-013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