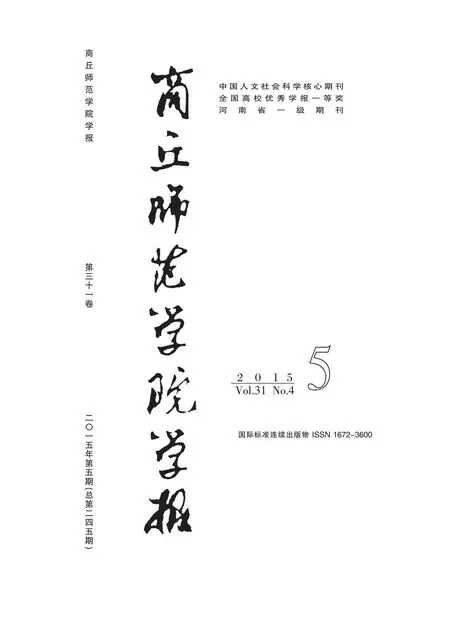再论《周官》之成书
石 超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 北京 100872)
再论《周官》之成书
石 超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 北京 100872)
《周官》又名《周礼》,在古代被奉为五经之一,长期扮演大一统帝国官方意识形态之承担者的角色。然而,此书作于何时、成于何人之手等问题,却始终悬而未决,众说纷纭。为了使《周官》研究更加深入,有必要在回顾、检讨前人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新近出土文献及其相关研究成果作为参考。此举或可使《周官》成书时代、学派归属等问题得到解决。
《周官》;《周礼》;二重证据法;荀子学派;焚书坑儒
近两个世纪以来,学界关于《周官》成书时代的问题,曾有过多次热烈讨论。各种假说均被提出,简单归纳,无外乎如下几类:周公首作,作于西周,作于春秋,作于战国,作于周秦之际,作于汉初,刘歆伪造等。大致来看,《周官》成书时代之上下限必定不超出西周初年与西汉末年。此范围之确定,乃得益于孙诒让、康有为、钱穆、徐复观、顾颉刚、杨向奎、刘起釪等诸先生的反复讨论与论证。在此基础上,金春峰、彭林的研究,进一步将这个范围缩小为不早于周秦之际、不晚于文景之治。鉴于此,笔者以为,金、彭两位前辈的结论似可沟通,此范围可进一步缩小为秦朝建立后到“焚书坑儒”的施行之间。需要指出的是,该假设不仅能够适应《周官》成书时代研究结论的总趋势,更可以得到大量新近出土文献,尤其是秦汉竹简之佐证。可以说,《周官》成书时代之问题,在秦汉简大量出土的刺激下,定将再次成为中国学术界的前沿课题之一。
一、对《周官》研究的批判性回顾
继金春峰、彭林之后,张国安于2003年发表了《周礼成书年代研究方法论及其推论》(以下简称张文)一文。该文大致回顾了自康有为以来学界对《周官》一书讨论的大致情况,并引用彭林先生的说法对以往所有研究方法作出了归类:“(1) 从文献到文献的方法;(2) 运用金文材料的研究方法,即所谓二重证据法;(3) 研究《周礼》思想的时代特征进而推断成书年代的方法……思想史的方法。”[1]这三种方法亦可进一步概括为:《周官》与传世文献比对之方法,《周官》与出土文献比对之方法,《周官》与主流思想史比对之方法。张文分别对这三种研究方法作出了批判性回顾。
首先,“文献比对的提问或从文献到文献的论证,都是将某个局部材料,通过思辨性解释,作肯定与否定性的联结,将其纳入到某个先在的文献资料的整合体系中去。思辨性解释有赖于这个先在的整合体系,而这个整合体系的确立、完善则又需要这个局部材料的支持——也许这就是所谓的‘解释学处境’”[1]。质言之,张文认为,《周官》作为史料,与其他传世文献具有平等的地位。故而,在使用某种史料定位《周官》成书年代及作者之前,首先要确定所使用的史料自身的年代及性质。困难的是,在很多情况下,所选用的史料往往又要借助《周官》来说明自身。因此,这种方法难免有“循环论证”的缺陷。
其次,“运用金文材料的研究方法,仍是一种文献比对,仍有解释学处境。当然,金文材料作为文献材料与传世文本文献相较有其特殊性,后者由于传播学效应,其原始信息有可能被遮蔽、扭曲、变异甚或亡失,而金文材料则避免了这一过程,因而具有极强的原始性和可信性,自然是文献比对的首选材料。但由于金文材料获得的偶然性,再加之零碎、片段、文辞简约等局限性,在实际的研究中引入传世文本文献加以比对,在所难免”[1]。按照作者的意思,即便“金文”具有传世文献所不具有的原始、可信性,也并不能以此为坐标来衡量《周官》。也正是因为金文的原始性,我们要想准确理解它,还是不得不借助于传世文献。所以,引入“金文”不但没有使问题得到解决,反而在《周官》与其他传世文献之间强行插入了“第三者”,使得我们距离问题的解决反而更远了一步。
最后,针对“思想史的比对”方法,作者说:“思想作为思想史的局部,包括比对中的其他局部,其得以解释、发现,受制于思想史的整体,而真正的思想史的整体构成,却又有待于这些尚未确定的局部思想确定。稍作辨析,便可发现,其比对思辨赖以可能的基础就建立在‘凡任何思想都具有该思想的时代特征’的思想史整合体系的思维假定上。依此断定,主流思想之外的任何思想都是不可能发生的,若发生了也只能排斥于思想史之外。”[1]可见,所谓“某某书的主体思想所反映的时代特征”一类的论证思路与方法,在作者看来是最不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原因即在于对一部作品的主体思想之归纳可以一人一意,是一种较之文本比对更抽象、更玄虚的比对方法。
张文在分析了前人所用方法的种种困难和缺陷之后,认为这是“比对思辨的‘解释学处境’”之“根本性”所致。并且进一步指出,“若回到我们所能直接面对的现象,那只能是作为历史遗迹的《周礼》的文本形式,当下直觉到的便是某个官制以及由文本标题暗示出来的与早已成为过去的周代制度的某种关联。就文本而言,最易于也较为恰当的提问便是该文本的命名形式——命名者与编纂者是一还是二?”[1]在此新的提问方式下,张文又逐一捡起前面被批判的三种方法,依次论证了以下一些小结论:1.《周礼》一名后起,此书本名《周官》;2.《周官》之名是本书作者(们)所定,即命名者与编纂者为一;3.《周官》的官制设计是对西周制度的追忆、体认;4.《周官》之缺少《冬官》一篇是因为作者(们)遭变故而未及完成(最大的可能即秦火);5.从《周官》全书对冢宰的重视来看,其书作者很可能是宰官(管理奴隶的小官)或膳夫(宫廷厨师)的后裔。
暂且不论张文在方法论上的得失,仅就其结论中作者身份一点而言,便会使我们大跌眼镜。一部影响中国古代两千余年、长期占据帝国意识形态宝座的皇皇大典,其作者身份竟被定位为宰官或膳夫后裔,于情于理大概都不能具有多强的说服力。虽然孔子早在春秋之季,便首开“有教无类”的先河,但在战国末年那样的情况下,仅靠宰官或膳夫后裔来编一套《周官》这样的经国大典,其结论的幻想性、不严肃性是极其明显的。众所周知,《周官》一书之编纂形式、意图与《吕氏春秋》十分接近,后者乃秦国国相吕不韦召集各国、各派学者,历时数载方才编成。那么,像《周官》这部无论在形式、内容、思想成就上,都与《吕氏春秋》不相上下的作品,仅靠宰官与膳夫的后裔之力,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编成的。即便没有国相那样的权势、地位,也不可能没有专业学者以及见识超群的领袖人物的共同努力。
当然,张国安的结论虽然有待商榷,但其对《周官》研究领域的方法论问题的反思颇有价值。前文所引作者对三种类型研究方法的批判性论述,也代表了笔者的意见。同时,笔者亦必须指出其对《周官》研究方法论之反思方法的某些不足。
第一,对《周官》研究领域已有成果未能全面掌握。张文所列已有研究成果没有超出彭林在其《周礼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中所介绍的范围。但在彭林大作问世不到两年之久,金春峰便出版了《周官之成书及其反映的文化与时代新考》一书。此书的结论与彭林相左,认为《周官》成书于秦统一六国的过程之中,由进入秦国的六国学者兼采诸家学派思想,以法家、儒家为主线编就而成。该结论在很大程度上乃依靠大量引入睡虎地秦简等新出土文献资料而得出。
第二,未能领会“二重证据法”之真谛。诚然,出土资料及金文的解释需要依靠传世文献的佐证,在二者极其匮乏的情况下,确实会出现张国安所谓“循环论证”的困境。但自我国考古事业蓬勃发展以来,大批具有宝贵史料价值的一手文献不断涌现,使依靠传世文献解读出土文献的局面有了很大、甚至彻底的改观。日本学者工藤元男所著《睡虎地秦简所见秦代国家与社会》一书就是使用出土文献所载内容解释其自身而得出可靠结论的代表之作。如果能将这种可靠结论进一步运用于《周官》研究,恰可弥补《周官》与传世文献比对、《周官》与金文资料比对时所产生的不足,亦可以纠正在资料不足的情况下运用“思想史比对”方法得出的结论之偏差。
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工藤元男的工作进行简单的介绍。
二、将睡虎地秦简研究所得最新成果引入《周官》研究
工藤元男的《睡虎地秦简所见秦代国家与社会》一书的全部章节均为曾经独立发表的论文。所论均为利用竹简秦律探讨统一过程中秦史的基本问题,对我们了解战国中后期到秦王朝建立这一段时间内的制度、思想动态,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下面选取书中第二、三章重点评述。
第一,《秦的都官和封建制度》。作者在这一章中介绍了秦国封建制的两种特点。一种表现为其所继承的西周分封制度下所产生的宗室贵族的旧邑;另一种是商鞅变法创设的军功褒奖制下的封邑。在统一六国、加强集权的过程中,秦国不仅要强固关中地区,平衡粮食财政,还要解决国内的封建遗制,而秦简中首次出现的设于旧封邑之地的“都官”一职正是针对这种政治需要而出现的。作者指出,秦简所见都官是先秦文献中没有记载的官制机构。因此,以往研究都以汉代文献所见都官、中都官及颜师古注为线索作出解释。从某种意义来说,这是不得已的事。正因为都官是传世文献中没有记载而由于睡虎地秦简的出土才被人知道的机构,所以我们才应该在秦简中对其作出系统的解释,并将其放在战国秦汉史的整体背景中考虑其意义。笔者认为,这是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方法论意识。对于出土文献中所包含的内容,在传世文献中缺载的情况下,首先应该依据该出土文献自身内容作出比对、阐释,其次才是参考传世文献中类似的内容进行对比研究。后者不仅可使出土文献得到进一步澄清和阐发,而且还可以解决传世文献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就工藤元男在此章中所得结论而言,其所讨论的秦朝封建制度的两种特点,恰与《周官》中所载封建制度相似,或可成为《周官》成书时代与秦统一六国之历史时代相近的重要佐证[2]50-72。
第二,《秦的领土扩大与国际秩序的形成》。作者指出,秦国在推进国内中央集权化的同时,不断地对周边地区发动战争、扩大领土。在这个过程中,秦国一定接收了许多其他六国的民众和其他民族。作者将论域集中在秦简中“真”、“夏”两种法律身份之定义,并以汉代属国的形成过程为线索,对秦的臣邦概念作了分析。通过对比这一前一后两种极其类似的历史运动,说明了那些被纳入秦统治的人转变为“新秦人”的历史过程。此过程与《春秋公羊传》成公十五年条所见思想有相通之处:“《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3]462-463据此,统治的第一阶段从本国开始,第二阶段对华夏各国不分彼此。何休《公羊解诂》在他的三科九旨说中还加上了第三阶段:“夷狄进至于爵”。到了这一阶段,华夏、夷狄之别就消失了。因此,工藤元男认为不能否定《公羊传》曾受到过秦国法制的影响[2]73-104。
工藤元男认为公羊学夷夏之辨受到秦身份制度影响这一结论,我们以为不妥。首先,秦人向来以“西人”、“虎狼”自居,其身份制度中的“夏子”是否证明他们在战国末年开始以“华夏”自居,还需要更多的旁证。因此,对“夏子”概念中之“夏”字的来源还有很多需要证明、澄清的工作要做。在此之前将“夏子”与“华夏”建立关联是冒险的。同时,在秦简中与“夏子”对立的“真”亦是一个十分新鲜的概念,在传世文献中找不到可以辅助说明“真”为何指代被秦征服之地人民的资料。故而,秦简中“真”、“夏子”还有可以讨论的余地。其次,公羊学为齐地儒学,是儒学中颇为特别的一支,其特殊性表现在其理论的恢宏与外向。而齐国恰是六国中最后一个被秦征服的国家,这样的历史事实表明,在秦国身份制度运用到齐国人民身上之前,公羊学的基本理论架构(“以夏变夷”乃其中重要部分)早已形成。所以说,公羊学深受秦国推行的身份制度影响的结论就不能完全被接受。
与此结论相反,我们说秦国的身份制度很可能受到公羊学夷夏之辨的影响,似乎更加合理。众所周知,秦人建国历史远比其他六国尤其是齐国为短。在地缘上,秦人与西戎杂处,在身份认同上秦人以“虎狼”自居。因此,与中原诸国相比,秦人在文化上属于后进,秦人自身也对自己的文化层次存有某种自卑的心理。在合纵连横的战国中晚期,秦国的对外政策始终奉行“远交近攻”的原则,其攻击对象主要为三晋及楚,其“远交”之对象则主要是齐。可见,在文化上,战国后期的秦国主要以齐国为楷模。这从秦朝建立后的七十博士制度与齐稷下学宫建制十分相似可以得到证明。鉴于此,我们认为,公羊学夷夏之辨的理论与秦国身份制度的一致性,非但不能说明公羊学受秦制的影响,反而更进一步证明了秦国在文化上对齐国的尊重、模仿和贯彻。
与本文论题密切相关的是,秦人的身份制度虽然不能用来说明公羊学的理论来源,但却恰可解决《周官》中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官制设置的理论来源问题。请看《周官·大司马》:“方千里曰国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4]1104这种对全国领土整齐划一的规划,显然是脱离实际的。但是,在其幻想性质的描绘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几分社会现实的影子。在秦统一六国的过程中,越到后来,这种以“国畿”为中心向外辐射的统治模式就越明显。在秦国所推行的身份制度以及郡县、分封制度中,处处可见与《周官·大司马》所涉及的理想国图景相类似的情形[5]34-38。
以上是对工藤元男两篇文章内容的大致介绍与批判性检讨,可以看到这两篇文章都是利用新出土文献对古代社会制度、法律、风俗以及这些社会存在对当时人们思想动向的影响之研究,堪称利用地下文献研究制度史、思想史的范例。当然,从相反的角度审视这一研究,其优点亦是其不尽完美之“蔽”。两篇文章均侧重于对睡虎地竹简本身的研究,而未及将其结论运用到解决传世文献诸多问题的领域,忽略了出土文献对学术史、思想史的澄清、修正之作用。因此,我们认为,工藤元男虽然在研究秦简本身问题上的创获颇丰,但在使用这些结论解决传世文献诸多问题的工作上则存在不足。若能将其对秦简研究的结论全面引入《周官》研究,应该能得出更有价值的结论。
三、关于《周官》之成书的新假设
通过前文的分析,似可初步对《周官》之成书提出一种新假设。此假设,或可澄清其书与周秦之际思想史的关系。限于篇幅,本文暂不对此假设展开详细论证,仅从宏观层面予以说明。
关于《周官》成书的时代,笔者有如下假设:第一,《周官》一书的成书上限当不早于《吕氏春秋》成书之年。因为从著书规模、结构以及意图来看,《周官》与《吕氏春秋》都有相似性。但从自身体系的圆满程度来分析的话(如果《冬官》不缺),则《周官》优于《吕氏春秋》。因此,《周官》当是在借鉴《吕氏春秋》得失的基础上开始编撰的。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战国时代天下一统的局面之出现,是在齐国迅速衰落之后才日渐明显的。吕不韦相秦后,秦国所展开的一系列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使得这种统一趋势日渐明朗。而《周官》这样一部致力于为即将出现的统一帝国设计统治制度的著作,只能出现于统一态势十分明朗之后。这也是《周官》成书上限定在《吕氏春秋》以后的另一个原因。第二,《周官》一书的成书下限当定在秦统一全国后,李斯上书实施“焚书坑儒”之前。这一假设与张文不谋而合。其理由亦与张说相同,即《周官》在形式上缺少《冬官》一篇,不是由于原来有而后来丢失,而是因为《冬官》一篇根本没有完成。其所以未完成,正是因为秦朝“挟书令”禁止“诗书”流传。而就《周官》内容中的大量儒家思想来看,恰属于“挟书令”所禁止之范围。
关于学派属性,笔者将《周官》一书归于荀子学派。第一,荀子作为先秦儒家的殿军及百家争鸣的最后总结者,其在当时学术界的地位当是无人可敌。而其弟子、后学之人数,亦当颇众。虽然荀子弟子见于文献记载的不多,但均有重大的代表性,似可将其划分为四派,且四派均有其代表人物及作品:1.脱儒入法的左派:韩非、李斯;2.传经为业的右派:浮丘伯;3.以礼统法的正统派:《周官》编纂者;4.穷究天道的自然科学派:张苍。在这四派的划分中,与《周官》关系最密切的当然是正统派。笔者提出这样的假设,是以彭林与金春峰的著作为基础的。他们都用大量篇幅指出荀子儒学的最大特征即礼刑并称、儒法兼综,但二人同时又强调其根本上还是以儒统法。而这一特征又时刻贯彻在《周官》每一篇官制的设计之中,可以说是《周官》写作的指导思想。笔者在此只是明确提出《周官》为荀子弟子所作而已。第二,荀子后学四派中的右派,当与《周官》一书的流传存在极密切的渊源。众所周知,浮丘伯为荀子亲传弟子。汉朝建立之初,汉高祖刘邦的小弟楚元王刘交,又是浮丘伯的亲传弟子。而西汉中后期为皇家秘府校理藏书的刘向、刘歆父子,则是楚元王的直系后代。从此学术传承之谱系来看,刘向、刘歆父子的家学,即是荀学。注意到《周官》在汉代经学中地位的上升,与刘歆的大力支持脱不开干系的事实,均可证明《周官》与荀子学派的深刻渊源。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周官》一书的成书上限晚于《吕氏春秋》之面世,其下限则为“焚书坑儒”与“挟书令”之颁布。其作者,当为荀子后学中秉持“以礼统法”之理念的“正统派”。其所以能被保存与流传,当归功于荀子后学中以浮丘伯为代表的“传经之儒”。
[1]张国安.《周礼》成书年代研究方法论及其推论[J].浙江社会科学,2003(3).
[2][日]工藤元男.睡虎地秦简所见秦代国家与社会[M].[日]广濑薰雄,曹峰,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3]公羊寿.春秋公羊传注疏[M].何休,解诂.徐彦,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4]郑玄.周礼注疏[M].贾公彦,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5]金春峰.周官之成书及其反映的文化与时代新考[M].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3.
【责任编辑:李安胜】
2015-01-03
石超(1985—),男,内蒙古包头人,博士生,主要从事先秦哲学研究。
B21
A
1672-3600(2015)05-004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