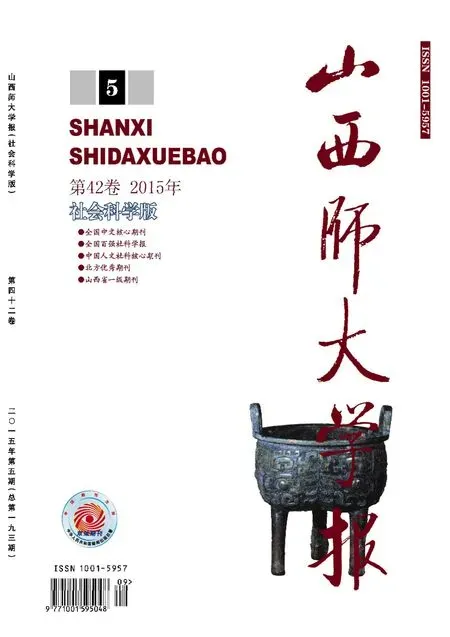夸父逐日的主题复原与神话逻辑
卫 朝 晖
(天津师范大学 初等教育学院,天津 300387)
在中国所有的神话故事中,“夸父逐日”应是极为特殊的一个,以至于引发众多研究者的浓厚兴趣。伴随着对故事主题言人人殊的多样化理解,该问题成为备受学界关注的焦点。这里不再对“追求光明”说、“驱赶太阳”说、“昼夜循环”说、“立杆测影”说、“巫师祈雨”说、 “英雄盗火”说、“部族斗争”说、“道之寓言”说等等作一一罗列与梳理,也不仅仅满足于再增列一家新观点,而试图从既丰富多样又未免纷乱的阐释处境中探求这个故事的独特性、故事之间的关联性以及神话的逻辑与阐释的方法——在这则神话魅力四射的背后,究竟是什么不断地误导着人们的复原性阐释以最终演变为发挥性阐释?
一
被命名为“夸父逐日”神话的文献出处主要有《山海经》的两段文字和《列子》的一段文字,我们有必要先就此作个辨析,其原文如下:
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山海经5海外北经》)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载天。有人珥两黄蛇,把两黄蛇,名曰夸父。后土生信,信生夸父。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将饮河而不足也,将走大泽,未至,死于此。应龙已杀蚩尤,又杀夸父,乃去南方处之,故南方多雨。(《山海经5大荒北经》)
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于隅谷之际。渴欲得饮,赴饮河、渭。河、渭不足,将走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邓林。邓林弥广数千里焉。(《列子5汤问》)
三处意思不尽相同,孰先孰后、孰优孰劣?其一,故事情节开端不同,第二、三处“夸父不量力”属故事外添加评论,明显有后期加工的痕迹。其二,故事结尾不同,第三处在邓林前后都作了文学化的修饰润色,一般也是后来传承者加工的痕迹。其三,尤其是第三处将第二处的“景”写作“影”,出现了理解上的明显错误。原因是“景”是日光的意思,夸父可以追日光,朝着太阳光芒跑,而太阳哪里有影子呢?要追事物的影子,只能背对太阳跑,像《庄子》全书最后一句所讲的“形与影竞走”那样。其实夸父逐日与影子无关,而《列子》记载显然有纰漏。
经过比较可知,目前大多采用的第一处表述(《山海经5海外北经》一段)显得最为原始而质朴,实际上也是夸父逐日故事的“标准版”;第二处略次之,除了增加评论性的文字外,追日故事本身叙述得较为简要,而且着眼于夸父之死的地点即成都载天,不过又给出夸父的身世(后土、信)与情节(应龙、蚩尤)关联两个重要信息;第三处围绕夸父逐日故事而巧取前两处的“并集”,尤其赋予铺陈描写,雕琢辞句,在追求完善、华美的同时反却丢失了原意、原味,因而材料价值最为不足,写作年代也最晚。
就前两处来看,第一处叙述得更详细,加上有较强的独立性,更容易使读者从言词、口吻之间寻求到事件的中心所在。古语一向十分精炼,然而细心揣摩可以发现,故事叙述并非平铺直叙,而是存在着盘桓、滞留现象,文中的“饮”与“河渭”集结了整个故事的分量。事件的有效起因是渴与涸,事件的直接后果是河渭几近干涸,这个因果一定是故事自身所关注的焦点和重心。第二处《大荒经》的叙述表面上看文字较长,然而对夸父逐日这则神话来讲又显得较短,尤其是两个“将”字突显事件的运动性,加快了叙述节奏,而其叙述重心已偏向夸父之死的必然和殁身之所即成都载天这个地点。很显然,第二处对夸父逐日的表述远不如第一处那么从容而自足,其神话的神性与神格也同时大大降低,但将应龙杀蚩尤与夸父的神话故事联系在一起,应引起研究者足够的重视。
二
神话解读必须回到经典文本与核心叙述中。可以肯定,夸父逐日事件的重心在于渴与涸的因果关系,也就是因渴致涸构成了这则故事最基本的叙事框架。摆在远古人面前的问题是,怎样的干渴才能导致河渭的干涸?从神话产生的机缘上讲,这个问题与怎样的喷吐才能导致河渭洪涝同质无异。可以说绝大多数的神话都是远古人民对种种现实疑惑所作的充满神性而令人满意的回答,例如借盘古回答天地自然的由来,借女娲回答人类自身的由来,而第二处《大荒经》回答了南方气候的因由,用“故南方多雨”五字作结。神话源自神话产生的现实的契机,此刻向人类的想象发出邀请,于是远古人民借助自己在“自然的人化”即“使人的感觉成为人的”[1]87进程中渐已具备的卓越的想象力,来弥补这一困惑所带来的巨大空缺,完成想象力支配下的得意之作。
然而,作为得意之作的神话故事并非只是任意的、偶然的。远古人民此时不仅必须寻找一个巨人的形象,而且尽可能优先找到一个公众形象。所以在保存神话最原始、最完整的《山海经》中,尽管仍有其他的巨人、巨人国,但频频出现的巨人是夸父,因超渴豪饮导致河渭干涸的也非夸父莫属,更遑论出身显赫的夸父原已进入神话世界与神人系统中,自然成了这则故事的角色承担者。无论如何,因饮致涸作为叙事框架和事件核心,夸父的出现意味着故事的发端得以确定。因此毫不奇怪的是,河渭干涸的故事仅仅从夸父奔逐开始,而夸父奔逐之前在这则故事之外,既可以是本然无故事,也可以是对这则故事本无价值的故事。如此看来,对首句“夸父与日逐走”的叙事缘起所作的任何疑惑及其添枝加叶,在我们力求复原神话主旨的意义上都不过是画蛇添足。
立足于河渭断流的重大现实事件敷衍而成的夸父逐日故事,并不能因被敷衍、被演说而转移读者的视线。对这则神话的读解必须时时把握一条主线,即以素朴的方式表达渴饮致干的因果逻辑关联,其他的因素都是这条主线的延伸与绾结。回到文本、回到事实、回到远古人民的心理与思维的真实境遇中,人们面对的是一场巨大的灾异所带来的生存危机和极度困惑,人们迫切需要一种必然是超人间力量的解释和回答。因而原始神话总是非常现实地面对宏大的已然事件,然后运用同样宏大的方式拓展出宏大的视野,结构出宏大的虚幻事件。神话,如果不是意外缺失的话,就完美地存在于神话表述中,既有其质又有其文。神话的主干是质实的,不可变化的;而神话的羽翼则栩栩然,灵动不居,迁思妙想。我们既不能因华美的羽翼而遗弃躯干,也不能执泥于一桩历史事件而丧失灵性。
鉴于此,本文认为,夸父逐日的神话故事以渴饮致干为叙述重心,而夸父随日奔跑,愈近愈热,愈热愈渴,原本一位巨大的神人在竭其力、灼其身的情形下,似乎无论有怎样滂沛的水源都不足以解其渴、还其生。现实中河渭见底,然北部的大泽如故,天下之水不可能尽干,在本故事中夸父之死是逻辑必然。尤其是神话故事中的夸父已是战亡者的形象,原本就与水火之争有关,再加上河渭一带有夸父活动的印迹,向北的一座大山又是传说中夸父的亡身之地,所以不管本故事中想象的、叠合的成分有多少,最重要的即是人们眼中的神话必须具备尽可能多的、甚至本来大致如此的叙事合理性。随着历史故事与神话演绎的不断丰富,一则新神话故事的产生不仅有了更多可以采取的母题与元素,同时也生长在已有故事群的特定空间里,只有通过高妙的叙事思维与艺术才能最终给世人的求知以满意的回答。
解释性神话的创作承担着特定的任务,夸父与日逐走只是故事的因缘,叙述的走向完全是朝着渴饮与干涸行进的,除了重点解释滔滔河渭竟会缺水的现状外,还解释了北部大泽为何安然无恙,神人夸父为何死在成都载天,最后解释了大旱之年为何出现其叶沃若、其华灼灼的万亩桃林。无疑,夸父此番奔跑带来或导致一系列现实中令人费解的灾异结局,将一系列已然的因素都贯穿了起来,实际上最终完美地回答了人们的诸多疑惑。
三
《山海经》为司马迁所“不敢言”[2]123卷,但这只是针对书中描述的“怪物”而言。从《山海经》的布局结构、章句文气来看,这部列入《二十二子》的旷世经典是以相当谨严的笔法写作而成的。晋代文学家、训诂学家郭璞强调须以平常心来阅读,例如其中有关周穆王西征见西王母的故事,“若《竹书》不潜出于千载以作征于今日者,则《山海》之言其几乎废矣。”[3]原序20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给予《山海经》足够重视,借书中的详细描述对黄河古道的流向进行了深入探究。整体来看,《山海经》尽管涉及面甚广,但首先是一部极重要的地理学著作;各种丰富资料或亲见,或耳闻,皆有所遵循,徐徐道来,并无故弄玄虚、哗众取宠之意。
不仅《山海经》的地理真实、历史真实被人们所忽视,而且神话故事的地理真实、历史真实也被人们所忽视。就创作而言,解释性神话的叙事逻辑一部分来自历史事件的自身逻辑,一部分来自定向性想象的逻辑必然。其主要特征是先知果而未知因,表现为从果到因的思维与想象活动。就对解释性神话的读解而言,读者必须正确处理因果二要素的基本关系,充分认识这类神话中的“果”具有极强的事件真实性与现实性,神话的想象基于这个事实而展开特定的联想与夸饰。夸父逐日故事中的神格体现并不在于夸父缘自怎样伟大的抱负和魄力才去与日逐走——从这一点看“夸父不量力”的前评论仍是有意味和意义的;而真正在于饮尽河渭之水仍不足解其渴,巨人之腹竟能盛下养育祖祖辈辈的长河之水,尽管历经千山万水,备受骄阳炙烤。
明晓解释性神话的创作逻辑,就会以缘起的方式看待“因”,以审美的方式看待那超人间力量的神奇想象,以实存的方式看待“果”。在夸父逐日的故事中,最重要的事实之果就是河渭断流,其次是桃林盛开。无独有偶,《山海经·大荒南经》记载:“有宋山者,有赤蛇,名曰育蛇。有木生山上,名曰枫木。枫木,蚩尤所弃其桎梏,是谓枫木。”郭璞注:“蚩尤为黄帝所得,械而殺之,已摘弃其械,化而为树也。”这与夸父“弃其杖,化为邓林”及《山海经·中山经》“夸父之山,其木多柟,多竹箭,其兽多牛、羬羊,其鸟多鷩,其阳多玉,其阴多铁,其北有林焉,名曰桃林,是广圆三百里,其中多马”的记述同出一辙。《山海经》作者首先关注的是眼前这片桃林与枫林,由此现状而追溯其形成的来历;这种转化既符合生活中插柳成荫的事实经验,又显然成为神话创作可以复现和效法的“母题”(motif)。[4]1—5神话创作并非想当然,而是受多种因素制约,包含种种缘由,只有发现内在逻辑,才能做到以神话的方式去解读神话。
一个完满的神话必然像历史那样,尽可能与其他事件形成相互关联的整体,以增强叙述的真实感。《山海经》中两次写夸父逐日,并与《大荒北经》黄帝擒蚩尤的神话联为一体,然而却出现了夸父之死两说的情形。究其实质,夸父逐日由河渭溯及太阳,水火相交相抗,结果是水不胜火,一方面河渭断流,另一方面夸父因炙热干渴而死,火盛水少显而易见。黄帝蚩尤大战的实质恰也是水火之争,黄帝一方先水战,蚩尤复以大水攻,最后黄帝终以干旱火热制胜。其中应龙虽以水战告退,但又兼具致旱神力,《大荒东经》云:“应龙处南极,杀蚩尤与夸父,不得复上,故下数旱。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这表明在水火不容的斗争中,自然界确实出现了火盛水干的巨大灾害;神话创作则将真实的历史故事与真实的自然变故以天人应合、相类比附的方式交织在一起。所以说,神话故事不仅包含着自然与历史,也蕴涵着对立统一的哲学元素,又在文学、审美的意义上,揭示了人类在前行中饱尝水深火热之磨难,惟有自强不屈,积极应对,掌握自然,适应环境,才能生生不息,成就英雄事业,展现英雄本色。
[1]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2]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3] 山海经[M].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4] 吕微.神话何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