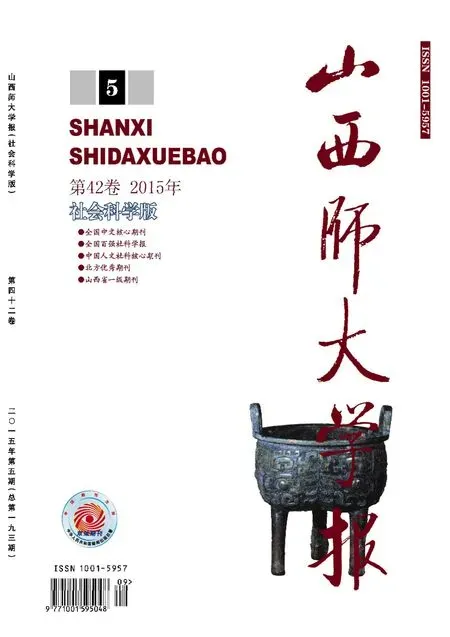血社火民俗的“行为表达”与“事件性”特征
----以山西省洪洞县 “小河拆楼”为个案
张 西 昌
(西安美术学院 美术史论系, 西安 710065)
社火是以视觉感知为主体的综合性表演艺术。在其发展过程中,与傩仪、祭礼、杂戏、戏曲等诸多艺术都有形式及内涵上的关联。与戏曲相较,社火民俗不依赖于固定人为的表演空间,而是在原生多变的自然空间中通过近距离的观赏与互动,使表演者与观众之间形成共同性场域。这也是社火民俗得以形成和传播的重要质素。
侧重于演出过程中演员与观众、舞台表演与表演现场关系及行为表演研究的西方表演学理论,在我国戏曲研究上有所推进,但在社火民俗领域内还未及展开。社火民俗游演空间的多元性导致了表演形式的多变性,这也是表演学理论学术切入的趣味之所在。本文将通过对某类个案的剖析,来研究社火民俗表演和传播的心理路径,由此揭示其衍生和存在的社会功能。
一、“小河拆楼”民俗的形式与游演的物质要素
血社火*血社火是对带有血腥暴力装扮色彩的民俗游演活动的官方统称,此概念据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宝鸡。地方称谓分别有“快活”、“八扎”、“把斩”、“血故事”等。该民俗目前仅见于陕西关中地区和山西晋南地区,山西省洪洞县小河村的此项民俗以其故事梗概命名,被称为“拆楼”或“小河拆楼”。的表演方式分为静态、动态和动静结合三类。静态即采用哑社火的游演方式,演员保持固定姿势,也不言语,主要靠扮相进行视觉传播。动态表演中,演员肢体处于运动状态,比较自由。动静结合则是在部分环节中,演员可通过简单动作进行表演。根据笔者在陕西和山西两地的调研,“小河拆楼”是血社火民俗中仅见的动态个案。
“小河拆楼”的民俗内容源自对杨家将故事的加工附会,表现的是奸臣王强带领爪牙欲拆杨家“天波府”,反遭杨门女将痛击而狼狈逃窜的故事情节。在化妆环节上,小河拆楼与其他血社火基本类似,即借助特制的道具和血浆等物,通过血腥的化妆手段,形成暴力恐怖的视觉效果。在音歌的伴奏下,演员以碎步跑跳,并连带嚎叫的方式进行表演。动态的游演方式是“小河拆楼”区别于其他血社火的最大不同之处。
“小河拆楼”的演员队伍有一定顺序,最前端为横幅,上书“小河拆楼”字样,接下来是彩旗队,然后是音歌队,中间部分为王府家丁十余人,也就是经过特技化妆的王府家丁,这些人员也有排序原则,小道具在前,大道具在后,细节上并无定规。接下来是王强,王府家丁与杨府女眷中间留有适当距离,再下来是杨家旗,旗后为杨家家眷,杨洪领头,然后是杨八姐、杨九妹以及众多的杨家女眷。这些人员所组成的表演队伍大致在15米左右。队伍的安排充分注意了由身体语言所形成的节奏感。整个队伍中,核心表演者是以血腥化妆而引人眼目的王家家丁,并以身体动作和喊叫声来形成队伍中最富吸引力的动感环节。
“小河拆楼”民俗游演的物质要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视觉要素
血社火有着血腥恐怖的视觉外衣。与其他社火形式相较,血社火并不侧重角色扮相的视觉美,而是借用幻术的某些手法,反其道而行之,以视觉幻化的途径造成视觉的凶酷、残忍之感,从而达到对观众心理的刺激作用。
笔者曾对血社火做过分析,认为其(血社火)可能与杀虏庆功、血祭仪礼、佛教思想、道教方术等因素相关,但更多应该是幻术的分支性发展,在展示形式上借鉴了传统社火的做法,并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善恶报应的伦理观念,以弘扬正义,抑制邪恶为主旨。[1]58古代幻术中避实就虚、以假似真的做法,在技术上和血社火有着近似的姻缘。
视觉暴力对人类心理的作用具有双面性:一方面,在深层次的生理诉求中,可以引起人们对常规生活拘囿产生突破和释放的某种快感,这种快感与人类早期生活的遗传记忆具有紧密的联系,这也是为什么人类一直不能控制自己对于暴力内容产生好奇的原因;另一方面,还可以引起人类的生理不安,并与生活的常态和祈愿发生冲突,从而更加强化人类对于自身平安和健康的主观诉求。在既定的文化环境和空间中,这种视觉暴力一方面被部分人群所认同,更对民俗文化心理产生了深层次的传播效应。
(二)身体要素
物质性的身体(形体)也是重复一定姿态和动作的结果,正是这些行为本身才产生了使身体(形体)成为一个独特的、有性别的、有种族的、标明文化的身体(形体)。身份,它作为形体的和社会的现实,经常通过“行为表演”显示出来。[2]35身体是表演艺术的直接和主要参与要素。这是由于技艺的具身性特征造成的。但凡社火表演活动,在组织过程中,对演员挑选大致有三个原则:一是从造型角度考虑,演员的身形、脸型和气质要与所承担的角色有所契合;二是从年龄性别和体重角度考虑,尤其是(高)芯子社火和背(挈)社火,因为演员需要悬空中或背负,就需要对体重有所规定;三是从诉求角度进行考量,社火游演具有一定的巫术色彩,由此负载了一定的心理祈愿和调节功能,需要借此达到驱灾避害和得福纳降的乡民,则可以根据诉求来调配。这些挑选规则是针对身体而设定的,也是身体能够介入表演活动的前提条件。
在社火表演中,大多对身体的技能性要求不高,主要是考验演员体能的耐力,当然有些项目也是例外,如“小河拆楼”演出中的“音歌”表演,演员除演奏外,还需有一定的步法和身体语言,这种半舞蹈性的表演与扭秧歌类似,对演员的基本功提出双向性考量。柔韧性好、动作规范、身姿优美的表演者会给观赏者带来审美的愉悦感。相对而言,特型(指血腥扮相)演员的技巧性要求不高,只要身体健康(最好有健硕的外形)即可参加表演。表演时,演员要脱去上衣,裸露身体,并通过化妆在身体不同部位带饰特制道具。角色不同,道具和表演姿势也不同。该表演中,王强和杨门女将不需要特型装扮,着戏服,做追赶状。血社火演员则在音歌的伴奏中,以小碎步奔跑。这种身体语言是艺人们经过长期摸索而最终确定的。表演需有规定性的艺术化手段,它区别于现实,现实中的奔跑方式,虽然真实,但不利于表演,也不雅致,不易于建立观者对表演艺术的心理认同。同时,这也是隔离表演内容和现实存在的一种手段,以表明故事的真实性,从而达到教化宣传和舆论塑造的目的。
(三)时空要素
文化空间的形成在时空上具有特定性,也就是说必须在一定的物质基础和特定的时间内,才会形成文化氛围。文化的传播也离不开特定的时空环境,因此,人类传播行为的秩序是受时间和空间因素制约的。传统生活中,自给自足的各种艺术形式点缀和丰富着乡民的生活空间,在受制约的同时,也充盈着人类主动性的拓展。这些时空,呈立体、隐潜和交叠状存在。
社火民俗的表演空间因其表演方式而有所不同,地台社火的空间相对固定,其他以游走方式表演的社火类型,空间则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社火表演的空间大多由村道、家户、田径、庙宇、集镇、广场等不同形态组成,在表演中,不同景观的形态、色彩都会成为社火表演的视觉环境和陪衬,从而共同构筑社火表演的场域效果。
小河村是个具有数百年历史的古老村落,背塬面水,地势缓陡,自清代以来的各类建筑与自然环境共同构建了小河村的物质空间。因为血社火都有不进家户的禁忌,因而,“小河拆楼”的民俗表演也与该村的公共空间及宗教场所密切关联。村落是乡民在历史生活中逐渐累积起来的物质与精神元素的结合体,也是民俗活动赖以存在、生长和传播的土壤。在村落这一熟人社会中,仅仅具有经济方面的自足是不够的,同时必须具有精神生活方面的某种自给自足。村落作为一个精神交流、信息共享的文化空间,可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村民的精神需求得到满足。[3]195因此,村落民俗仪式的意义不仅在于其外显性的文化象征,更在于其内向性的人际精神调整。
据笔者理解,在诸多民俗中,文化空间的时间性可有两种指向:一是指民俗活动整体存在的时间;二是指民俗活动完成所需要的时间。虽然两者在现实中是交叠的,但可以分成两个维度予以考量。社火表演大多集中在正月,与春节的气氛互为依靠,但同时,社火表演的气氛中也有春节整体的民众心理作为支撑。在这段时间里,农业活动基本停止,乡民们最关注的是自我娱乐以及敬神祈愿的精神意义。虽然在目前的工业化语境中,这种民俗心理有所淡化,但它依然是调剂民众心理的内在因素。社火表演在中国民间有相对固定的时间周期,大致集中在正月初五至十五之间,具体的表演日期则要视客观情况而定。组织时间的半固定性特征,也是社火表演令人期待的原因之一,尤其是血社火表演,时间的机动性更强。陕西和山西区域的血社火表演,大都有两年或三年表演一次的传统,因为规模相对较小,因此机动性更强,这种时间的长周期性和不确定性,更加强化了血社火表演的神秘色彩。
另外,有些血社火的表演时间亦很短,原因是该民俗活动大多集中在气温较低的正月,特型演员需要裸露身体,尽管演员在化妆前喝了酒,但出于健康考虑,还是要限定演出时间,通常以半小时左右为宜。在很短的时间里,观众要领略“小河拆楼”的视觉形式,也是颇感仓促的。“小河拆楼”属于沿线路进行游演的民俗种类,观众基本上也要随之处于动态之中,这与戏曲及地台社火的表演大不相同,正是基于此因,“小河拆楼”的演出氛围才更加惊心动魄,这是一种极为特殊的表演方式,在演出过程中,演员所面对的观众群体处于不断的变换之中,这不同于一般演出形式之中的互动关系。
(四)声响要素
声响不仅给听者一个空间感觉(在这方面应该想到:我们的平衡感官是在耳朵里),同时直迫入人的身体,而且经常能引起心理和情绪的反应。[2]175这里的声响不单指音乐,而是演出空间里各种声音的综合。为了加强气氛,社火表演通常都有音乐伴奏,且以铿锵的锣鼓为主。“小河拆楼”的伴奏乐曲是音歌,由小腰鼓、小锣和镲综合伴奏的轻音乐,是“小河拆楼”民俗美学基调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社火中,锣鼓伴奏只是作为渲染气氛,并不与演员直接发生关系。而音歌伴奏除了声响渲染之外,还与演员的步伐相契合,不仅音歌演奏者要有近似于舞蹈的步伐,演员们也要踩着鼓点,以碎步方式行进。音歌伴奏可以契合特型演员的表演而伴奏,也可以作为独立的表演内容来出现。
除了音歌伴奏,“小河拆楼”在演出中还有其他声响。有一种哨音,称为胡哨,由专人在演出队伍近旁,伴随着队伍行进,发出响亮刺耳的响声。这样,一方面引起观众的注意,二来也辅助开路,同时还能以强分贝的音律刺激观众,使受众心理与血腥恐怖的视觉感知相配合,借以达到民俗演出的效果。在社火演出中,观众与演员的距离很近,甚至有的项目,演员与群众还能相互窜动,引起彼此的骚动,调动群众情绪,增强演出效果。因此,观众的情绪互动在社火演出中极为重要,它是一种反应,也是一种反作用。观众的喧哗、嬉闹、惊叹、掌声等要素,都是社火表演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随机性的偶发声响,有时甚至超越既定声响要素的作用。这一点,社火与戏剧大不相同。游演类、动态类的社火项目更是如此。
二、“小河拆楼”民俗的“事件性”意义
从表演艺术的角度来说。所谓“事件性”是指由于观众的直接参与,使得“表演”行为向“事件”性转换,这种变化也使表演所阐释的“艺术”与“生活”之间的界限趋于淡化。*余匡复认为:“当代戏剧把原来不要观众参与的‘舞台表演’变化为要观众参与的‘事件’,这意味着观众在表演现场变换了原来的客体角色,从而把‘表演’生动地转化为正在发生的‘事件’。让(使)观众参与(介入)‘表演’(‘事件’)其目的是把‘艺术’(比如戏剧表演)和生活本身一致起来,连接起来,排除旧美学把‘艺术’和‘生活’严加分隔的倾向。当观众成为表演(事件)的参与者之时,也是‘艺术’和‘生活’不再有明显界限之日。”其实,古老的社火民俗很早便具有“事件性”特征,这种由乡民自发组织和参与的民俗活动,是在自己生活内部生发出来的精神活动样式,其组织权、表演权、传播权和消费权,都在自己所属的空间里展开,而不是带有共性表演的职业人自外部切入。在乡民眼里,社火角色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有些社火角色不仅只具有艺术特色,同时还具有宗教特征,乡民们认为有些角色在装扮好身子之后,演员已经不是他本人了,甚至不能随便开口讲话,依此来看,演员和角色是分离的。而在非宗教性的角色中,乡民又常常忽略演员的角色性,认为他就是同村的熟人,这种模糊跳跃的认知方式,使得社火民俗游离于“艺术”与“生活”之间,相对于经典化的表演艺术而言,界限极其模糊。在“小河拆楼”的表演中,这种特征极其明显。有时候,或者在有些观众那里,表演者是从属于角色的,有时则会被部分人视为普通的村民,从而加以嬉闹。这种看似不严肃的表演活动其实正表明了社火民俗的“事件性”意义。也即是说,正是由于这种“事件性”特质,才拉近了乡民对民俗活动的归属性的认知距离。
在笔者看来,社火民俗的“事件性”特征所折射出来的价值是“自娱自乐”,这是社火民俗在农业社会之所以稳定传承的精神内核。需要注意的是,自娱自乐不仅仅是指娱乐本身,就乡民权利而言,这种“自我组织、自我参与、自我消费”的自由度,正是娱乐得以发生的基础。从这个角度而言,社火民俗所呈现的“事件性”,才会将观众放置到艺术和日常生活的规范和法则之间,因而,它比任何由外人所组织的演出形式都具有参与感和鲜活性。
[1] 张西昌.血社火的视觉暴力及伦理性探析[A].李超德.东吴文化遗产:第四辑[C].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13.
[2] (德)艾利卡·费舍尔·李希特.行为表演美学——关于演出的理论[M].余匡复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3] 张士闪.乡民艺术的文化解读:鲁中四村考察[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