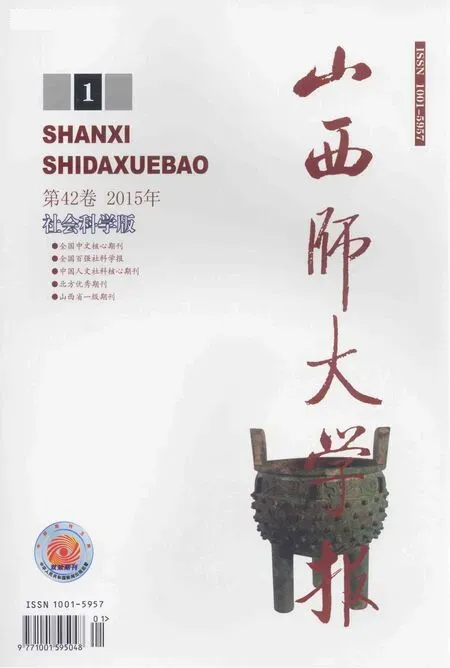析《虚证》的双重叙事
王 静
刘恒的《虚证》讲述一个已过而立之年的单身男子与人和善却又性格软弱,常常陷于自责的泥潭,童年喜欢的舞蹈、青年钟爱的绘画以及临死前热衷的诗歌,都没有能够如愿取得成就;有着独身的信念,又沦于出于道义与同情的不清不楚的爱情,面部手术的失败更加重了这个一贯被人认为漂亮男子的自卑,最终在一个“五一节”的午夜沉水自尽。故事由死者生前在专修班的一个同学讲述,他与死者是相识不足一年的朋友,两人并无相见恨晚之感,谈不上深交。他无法理解这个常把“死”挂在嘴边,善良而又自卑的朋友竟真的选择了自杀,便多方搜集材料,力图弄清朋友自杀的真相。
《虚证》所采用的是一种同故事叙述,即“叙述者与人物存在于同一个层面的叙述”。叙述者“我”与主人公在生活中有交集,对主人公有所了解,叙述者既在故事之中又在事件之外。这样的身份赋予叙述者以很大的自由,对于不同事件、场合保有绝对的发言权,可以全知、不知、详知或知之不多,在文本中体现为多叙或少叙。叙述者的多叙或少叙的自由并不意味着隐含作者的淡化或退出,相反,恰是隐含作者深度介入的方式,体现着隐含作者的价值观。
在《虚证》中我们总是能看到一些熟悉的影子,冷漠的旁观者几乎随处可见,叙述者“我”对旁观者持有强烈的批判态度,那么隐含作者又意在何处呢?
一、“我”对旁观者的批判
小说由逻辑学教员的点名写起,专修班的成员都是工作多年为了一纸文凭而重返校园的“苦命人”,可谓社会阅历丰富,然而正是这样一群人在面对这场涉及已逝者的点名时却哄笑不止。郭普云待人和善又乐于助人,但当他离开后,同学们丝毫没有念及同窗之谊,他的自杀只不过增加了他们的笑料和谈资。旁观者毫无对逝者的尊重,反倒多了些许的冷漠与欢愉。“我”起初也在发笑的人之列,听到“自然除名”后便不由得心里一惊止住了笑声,进而意识到“最可怕的是那种没有人带头而又众口一声的‘轰轰’的窃笑”。“我”跳出了哄笑的人群,成了众人皆醉中的独醒者,由此可见,“我”是不愿与这些旁观者为伍的,不愿做他们的帮凶。“我”的与众不同的表现正是叙述者所埋下的伏笔,“我”与大众的脱离使“我”站在了一个可以审视生者与死者的至高点,在这样的精心安排下,由于正义与良心的驱使或是探秘的心理使读者不自觉的产生了向叙述者的情感偏移。
“我”从众人中跳出去观看他们,此时的读者是站在比叙述者更高的位置,同时关注着“我”与其他人。读者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了这个探秘者“我”身上,企图跟着叙述者的脚步找到一个出口,看看我们的主人公到底经历了怎样的惨痛遭遇,但这个叙述者是值得我们深信的亲密伙伴吗?似乎并非如此。读者不自觉的情感转向,只是走向了叙述者所小心翼翼设下的圈套,看似平静的叙述过程,实则存在隐含作者与叙述者声音的重合与分裂。
叙述者对那些闲言碎语的嚼舌根者充满着鄙夷与厌恶,对那位正直不惑之年又“嘴刁嘴碎嘴毒”的老大姐,更是深恶痛绝。在旁观者看来郭普云完全是自寻烦恼,一个“脸俊人好家贵,有官儿当,有学上,能写诗,会画画”的人,整日唉声叹气觉得自己老是不顺,他的郁闷与失落在常人眼中是没有来由的。身边的人,无论亲疏远近都无法理解郭普云的烦闷,不知其为何心忧。在他们眼中,郭普云无疑是在“为赋新词强说愁”。“我”虽然也不理解郭普云的忧愁,但把他当哥们,憎恨那些造谣生事者,甚至诅咒那个嚼舌根的老大姐。这样毫无遮掩的愤懑与情感表达,进一步使叙述者赢得了读者的好感。因为读者显然不愿意把自己当成庸众中的一员,即使不比侦探聪明,没有过人的才华,也不乏善良与正直的美德。
郭普云自杀前写了六封诀别信,在给厂党委办公室的信中提到不要去找他,他已去往一个很干净的地方。苦心搜救的人们把目标锁定在竭力寻找很干净的地方上,从山脚到山顶反反复复全面撒网,甚至去了北戴河,结果却无功而返,人们开始对这世界上究竟有没有一块干净的地方产生怀疑。这是叙述者对旁观者的讽刺,没有结果的繁忙行动终于使他们开始怀疑自身的认知。每个人都在为生活奔走,无暇去顾及去思索生存的环境。他们只是苦于找不到一片干净的地方,徒劳无功的忙碌使他们烦恼,但并没有更深刻的思考,这是对人生于浊世而不自知的隐喻。
郭普云的尸体被一位农民捞上岸时已经肿胀不堪,被鱼类啄食过的五官完全破损,这位生前一向因漂亮面孔而被人羡慕的美男子,现在已是令人不忍直视。这一细节描写,不仅在指出自杀者生前死后的强烈反差,更是对旁观者无声而有力的一击。奇丑奇臭的腐尸将旁观者的同情心驱赶得灰飞烟灭,同时又被无数的好奇心笼罩着,“郭普云正处在人生最悲惨的境地,但他周围的同类们似乎更关心事件的戏剧性”。百无聊赖的看客全然用冷漠与厌恶在打量摆在他们面前的尸首,人们面对悲剧偶有的短暂震惊与惊恐过后都在庆幸自己不是受难者了,于是便怀了一种侥幸与窃喜。围观者们报着一种观赏的态度,在已逝者面前展开无尽想象,彼此窃窃私语互相交流着看法,这一场景的热闹喧哗与追悼会的冷清形成了强烈反讽。追悼会设在废弃的仓库,没有一位亲人出席,只有空荡荡的哀乐,这位生前的孤独者在尘世的最后一段旅程也只有孤独为他送葬。不相干人的强烈好奇心与亲朋的冷漠缺席形成对比,对死者而言,所有的生者都是毫无例外的旁观者。
隐含作者通过叙述者之口将这些旁观者的众生丑态暴露无遗,在这一层面上,二者的价值观相同。意即“叙述者对事实的讲述和评判符合隐含作者的视角和准则”,形成了相对可靠的叙述。《虚证》的深刻之处恰在于隐含作者与叙述者的价值观并不完全相同,两者之间存在分裂。
二、隐含作者对叙述者的远观
故事通过“我”的讲述来叙写,探讨郭普云自杀的原因,以期作出解释。这是一场关于生死的拷问,叙述者在追本溯源的同时也在寻找一条自我救赎之路。最终当“我”模仿郭普云的死亡体验失败时,方感到理解他的无力,也失去了对死、死者再玄想的兴趣。历经这一番长久的探索,尾章中与夜半垂钓者畅谈后,“我”如释重负,重拾了对生活的巨大热情。看似叙述者已历经凤凰涅槃而浴火重生,实则不然,一步步走向实证的同时,也接近了最真实的“我”,叙事者沦为了一向为他所鄙夷与不屑的旁观者中的一员,被隐含作者推向了批判的对立面。
小说从逻辑学教员的点名写起,在与夜半垂钓者谈话后结束。为何以逻辑学课作为叙述的起点?“我”想要追寻的是一种符合逻辑的解释与说明,历经漫长探索,却无法获得一个合逻辑的结果,夜半垂钓者将“我”重又拉回了现实。与“我”在逻辑学教员点名时众人哄笑唯有自己自觉停止的状况相比,重回现实的结局无疑是由一种外力所致而主体又心甘情愿的沉沦。“我”本是一个探寻者,与身边那些只关心自身生活琐事的人是不同的,在对生命、活着与死亡进行思考。向真相逼近的种种努力终落世俗的尘网,妄图改变世人对郭普云的庸俗看法,做一个精神的独立坚守者,却沦入庸常。恰如“我”最初为“狂人”,在呐喊中奔走呼号着探寻真相,希望拨开世人被庸俗尘封的眼睛,却终于成了世俗芸芸中的一员,回归到“我”所在的现实,像“赴某县候补”的狂人一样,“我”也要重新像身边的人一样在“太阳底下忙碌起来”。
文本叙事中所出现的细节过剩、视角越界以及信件披露,在增强文本可读性的同时也在对叙述者的可信性进行解构。郭普云死后,“我”因曾经自己对待他的态度而深感自责,包括对他的爱情观、世界观、诗歌创作热情等等的不理解而进行嘲讽。叙述者的自责、内疚以及对传播流言蜚语诋毁者的痛恨之情散布于文本的边边角角,不时跳出来冲击读者的眼球,很容易博得同情与理解,但随着叙述的深入,叙述者的不可信也暴露无遗。
第一章主要写郭普云生前最后一天在家中的活动,以对话的形式突出了杀鸡与吃晚饭两个场景的描写。在前者中,叙述者写到细心的郭普云弄破了鸡苦胆后“呻吟了一声”。晚餐场景中,这样的细节描写更多,郭普云清理鱼刺时“脸红扑扑的”,在向妹夫解释红烧鱼的做法时“父亲看了他一眼”,他一共喝了八杯酒“可是谁也没在意”……叙述者犹如置身于郭普云家中的隐形旁观者,所有人的一举一动乃至内心所想都被“我”一览无余。这种过剩的细节描写与视角越界,在逼真再现场景的同时,也暗指出叙述者的不可信。
隐含作者与叙述者的再次较为明显的分离体现在第五章,这一章主要写郭普云与赵昆的爱情。“我”出于对朋友的关心,屡次为郭普云介绍相亲对象,却无一例外的遭到了他的无情拒绝,总是表现出一副对女性对爱情毫不在乎的姿态。在得知他已朝着爱情出发时,“我”是为他感到欣慰的,但在关于郭普云性无能的闲言碎语中,叙述者的心态是很微妙的。一方面,非常厌恶那些中伤郭普云的人;另一方面,思前想后又觉得这谣言并非完全不可信。叙述者对主人公的态度是复杂的,由维护到同情再转向了怀疑,心理距离很显然在慢慢地拉大。在一步步地探究真相的过程中,叙述者的真实自我也逐渐浮出水面,即和冷漠的旁观者一样,在知晓别人隐私的同时获得快感。收到吴炎的一封回信后,再次去信问了很多涉及隐私的问题,也因再没有得到任何回复而感到失落。这一解密的行程终于暗暗成为了叙述者自我剖析的旅程,“我”痛苦的原因在于总也找不到造成郭普云死亡的种种根源,“比起他凄凉的死亡,我更关心的似乎是整个推导的逻辑过程以及它被人接受的程度。”
三、隐含作者的声音
揭开重重面纱,步步逼近死亡真相的实证过程,最终却以“虚证”名之。研究者多认为死者已矣,没有办法去实证,故名之以“虚证”。这一说法在经另一作家兼刘恒朋友的刘庆邦之口后,更是被广为接受,刘庆邦认为故事的原型是他们都认识的一个富有才华的年轻人,大家都为他的自杀深感惋惜,曾言“斯人已去,实证是不可能的。刘恒只能展开想象的翅膀,用虚证的办法自圆其说”。依笔者之见这种说法并不妥帖,作家创作不是为了立案破案,又何谈实证虚证死无对证之说?所以更应把“虚证”这一题名与文本放在一起加以解说,二者形成了一种反讽的效果。况且这样巧妙的结构和布局与其说是在“自圆其说”,倒不如认为是在进行一种思考,一种关于生与死的探寻。叙述者以失败告终的探寻是一场“虚证”,他只是充当了这次解密行动的领路人,这不仅仅是隐含作者对叙述者的否定,更是隐含作者声音的显现,是对于生死存在的哲学思考。
结构上的精心安排在正文的八章中都有所体现,每一章的事件既相互关联又彼此独立,每章都从郭普云生前的事件写起,每章结尾处又都跳出故事缅怀死者,循环往复,层层深入。事件的分散与连缀有序安排之外,值得注意的是文中所出现的议论,从这些议论能够窥见隐含作者的立场。《虚证》中的议论多是一种含蓄的议论,即“在描写的字里行间里潜在地透露出来的隐含作者的看法”。
叙述者竭力将一切不为常人所知的事实挖掘出来,供读者观看、思考,最后才体悟到:知道一些内幕后,以为明白了,细想却只能是更加糊涂。第八章摘录了死者自杀前所写的六封信,在结构和内容上与第一章形成呼应。郭普云在写给吴炎的信中提到他在看川端康成的《雪国》时,想到了三岛由纪夫,这一细节是对第一章内容的延展,他所看重的是三岛由纪夫的自杀,“死得那么辉煌,仍旧摆脱不了对生的绝望的悲哀”。川端康成认为未留遗书的自杀是一种恒久地活的延续,而急欲摆脱活着的郭普云是不屑以川端康成为前驱者的,反其道而行之,断然写了六封诀别信,由此可见,郭普云所要挣脱的亦是“生的绝望的悲哀”。郭普云的文学追求,与已被改变了的时代环境相冲突、抵牾,一味的坚守、固执己见,最终也只能是败下阵来。郭普云以自杀作为一种妥协,但同时又是一种反抗,是对个体自由意志追寻未果而做出的生命献祭。
在叙述者的引导下,读者所看到的是一个善良、真诚、友善、恬静柔和、优柔寡断、敏感而又习惯自责的郭普云,便理所当然的认为他的性格造成了他的悲剧,如此便突显了造成郭普云悲剧的个人因素,淡化了时代环境的影响,也就是说在叙述者的展现下遮蔽了形成郭普云性格的其它重要因素。在郭普云的生命悲剧中,另一重难以忽视的因素是女人。小时候在少年宫学舞蹈时,由于女同学和舞蹈老师的亲睐招致男同学的厌恶,自此便小心谨慎地处理与同学的关系,努力得到同性的好感。18岁的郭普云在军艺排演场结识24岁的漂亮女军人,懵懂初恋无疾而终。父亲再婚,他的生活又闯入两位女性,从郭普云的讲述中可以看出与他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聪明和任性,与继母关系冷淡,叙述者在郭普云与妹妹之间营造了一种暧昧气氛。最后给郭普云带来致命打击的应是与赵昆恋爱的破产,生理缺陷被公之于众。
如果从隐含作者与叙述者分裂的角度分析,叙述者所遮蔽的恰是隐含作者所看重的。在郭普云的一生中,童年遭际固然对性格的养成起了很大作用,但善于自省而聪明的他,在后来的日子里总能赢得老师和同学的喜爱,转折发生于中学毕业收到录取通知书而无法再继续上学的那一刻。只需将叙述者所有意隐藏的时间稍加整理,就会发现,当16岁的郭普云遇上了1966年之后命运便从此走上了另一条轨迹,正常学业难以继续,生母的奇异缺席(逝世还是离异不得而知),继母与无血缘关系妹妹的闯入,和漂亮女军人的懵懂初恋,几乎发生于同一时期,这一时代环境对郭普云最终人生悲剧的产生有着难以忽视的影响。
[1](美)詹姆斯·费伦.作为修辞的叙事:技巧、读者、伦理、意识形态[M].陈永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当代小说名家珍藏版·刘恒卷[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
[3]刘庆邦,刘恒.追求完美,永无止境[N].光明日报,2010.
[4](美)布斯.小说修辞学[M].华明,胡晓苏,周宪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