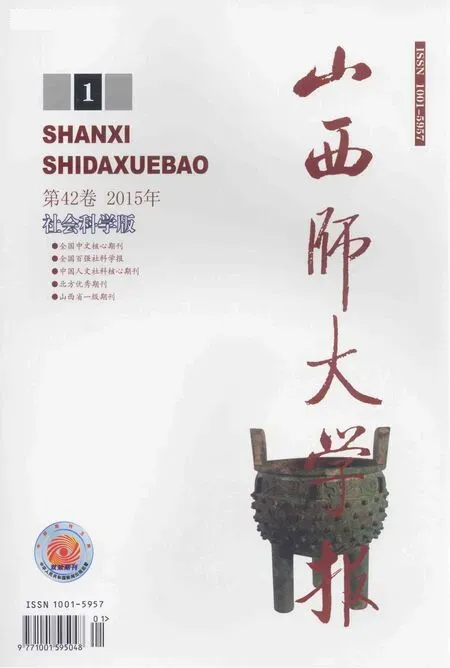集体行动中的修辞策略:隐藏的文本与弱者的武器——以大同“跪留市长”事件为例
段鹏飞
集体行动的产生需要具备一些必要条件,只有当大众对行动所倡导的价值目标产生认同感时,集体行动才得以转化为现实。一场集体行动所持有的话语体系和组织策略往往很难兼顾到每个参与者及群体的情感和利益诉求,为了有效动员群众,行动组织者会有意进行调整,形成一种大众认同的解读范式。在大同“跪留市长”这场集体行动的动员策略中,隐藏的文本与弱者的武器两种形式有力地建构起集体认同感,成为了扩大行动规模、表达行动诉求的最终话语框架体系。
一、最初的发起:从无人响应到万人签名
因煤而兴,因煤而困。大同顶着中国“煤都”的光环,在城市化发展浪潮中,一再遭遇产业结构失衡、环境日益恶化等的顽疾。从2008年到2013年,耿彦波对大同市进行了翻天覆地的改造,古城恢复、城市建设的规模之大,争议之多,令这座北魏古都在1500多年后再次成为国人众所瞩目的焦点。“再造古城”的是非功过虽然不是本文的评述对象,但是却如蝴蝶效应一般,为这场集体行动的话语和行动特征——本文的研究对象——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1.导火索:预期突变的调任。就在造城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时,2013年2月7日耿彦波“意外地”被山西省委调任太原。之所以称之为“意外”,是因为仅在4天前耿彦波刚刚被山西省委组织部公示为大同市委书记考察对象,大同民众都认为他还能用五年的时间收拾残局。“在民主推荐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耿彦波同志被公示为市委书记的人选,这已经是铁板钉钉。还不到七天的公示期,突然间就变卦了。”(访谈对象L)
2.群体利益的分化与共识。彼得·布劳把不平等看做是社会分化的一种形式,当资源占有量发生变化时,不平等的等级序列也会随之变化。在大同“再造古城”过程中,拆迁获利机会上的不平等,将利益相关者分化成两个不同群体。正如一位退休老干部G所言,“大同市这五年城市建设,出现了两派,一派挺耿,一派反耿。”
(1)拆迁受益者。伴随造城计划而来的是大拆大建,尤其棚户区和城中村的改造。《大同市2012政府工作报告》显示,拆迁波及到居民16万户,到耿彦波离任时完成了13万户。受益于拆迁工程的并非只有拆迁户。“建材商胡立民告诉新京报记者,2008年之前,他的生意冷清,几乎维持不下去了。耿彦波在大同大兴土木后,他抓住商机,三年赚到了一百多万”。
(2)利益受损者。大规模拆迁同时也带来了安置的巨大难题。“先拆迁,后安置”的政策让数万户居民居无定所,只能到处寻租。“拆迁户都是3年多才安置,一个月之内搬走的就有3000元补偿,租房补贴600元;一个月内不搬的断水断电拆厕所。”(访谈对象Z)与此同时,工程承包商也因市长的调任对工程余款能否到手开始挂肠悬胆。
五年间大同的城市面貌焕然一新,“恢复古城确实改变了大同面貌,高楼大厦、树木绿化、城墙庙宇……”(访谈对象Z);“以前鼓楼街道坑坑洼洼,碰到下雨泥溅的到处都是。改造后,马路变得整洁多了,现在出来散散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觉得很高兴。”(访谈对象L)Z和L分别是“反耿”和“挺耿”的代表人物,但他们在耿市长为城市环境作出的贡献一致认可,而且对其突然被调任都持不解态度。至此,不同群体的情感和利益都捆绑在了一起。“不管好与坏,你让他干完,铺这么大一个摊子,烂摊子谁来收拾?”(访谈对象Z)
3.从网上呼吁到集会签名。从2月7日调任伊始,许多市民开始在网络上频频互动交流。情绪持续发酵,若干在民间声望较高的人士约定初三在和阳门广场集会。
初三早晨,二三百人齐聚和阳门广场。集会组织比较松散,广场上的人们都在有条不紊地签名、写标语、编顺口溜。“人们来了干什么来了,光是聊天?我突然想起来像南门广场街上挂的红灯笼,有气氛挺热闹,所以弄一些红布子写点东西。这就形成了签名挽留。”(访谈对象L)
签名挽留不到一个小时,广场上聚集的人群越来越多,上百米的红条幅写得密密麻麻。积极分子们开始发表演讲,他们周围聚集着很多群众。随着大家的情绪越来越高涨,他们开始带领人群呼喊“耿彦波请回来”、“大同人民需要你”,提议大家举着条幅上街。
二、上街游行与跪留市长——民意爆发的顶点
签名集会的队伍就这样上街了。游行队伍人数最多时达到三四千人,由于多数是周边路人临时参与进来的,所以队伍流动性比较大。“大多数是看热闹的。赶上庙会,街上人多。一开始只是二三百人,后来游行那么长的队伍还是看热闹的多,人们都是受鼓动加入进来的。”(访谈对象Z)
但是,游行队伍结构的主体开始固定。这部分群体包括L在内的拆迁受益者、尚未得到妥善安置的市民和工程款未结清的施工队在内的利益受损者,再加上临时动员的浮动群众。各个群体在统一的集体行动背后实际上都有着不同的行为动机逻辑,但是当各群体面对“非零和型公共物品”——大同市民的群体利益时,集体认同感便会增强,人们团结起来去争取实现行动目标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所谓“非零和型公共物品”,就是当享用这些公共物品的人的数量增加时,群体中每个个体从中能获取的好处并不会减少。和平、民主、法制就是这样的公共物品)当然,如前所述,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虽然在某些宏观层面有些许共识,但是他们的分化程度还是很高的,甚至可以用很尖锐来形容。据此可以推断,他们的结合仅仅是一种利益或策略上的结合,能将三者凝聚在一起的集体认同感并非固有存在,而是在集体行动的话语修辞体系和符号性行为中不断被建构起来的。
1.认同感的建构——隐藏的文本。“隐藏的文本”是耶鲁大学教授詹姆斯·斯科特在《支配与反抗的艺术——隐藏的文本》一书中提出的。他通过这一概念来阐述底层群体的意识形态特征,并以此解释和理解底层群体的难以捉摸的政治行为,与公开的文本相对,它是发生在后台的话语,避开了掌权者的直接监视,这种在统治者背后说出的言说、姿态是千百万普通人生存智慧的重要部分。从集会开始的无人响应到城墙下的万人签名,从广场上茫然不适的民众到马路上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集体认同感环绕着隐藏的文本不断被建构。
(1)口号、标语。积极分子在动员市民参与时特别强调“家乡情结”的重要性。游行队伍上街后,“耿彦波,好市长”、“留住耿彦波,建设新大同”、“要让大同变香港,只有留住耿市长”、“苦干实干玩命干,路好城好环境好,耿市长,大同人民想念你”、“大同人民需要你,大同人民期盼你,大同人民热爱你”等等的口号被无休止地呐喊着。帕累托认为,说服听众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无休止地重复同一件事情。重复尽管没有半点逻辑—经验的价值,但比最好的逻辑—经验论证更加有效。重复尤其能影响感情,改变剩遗物,而逻辑—经验的论证只能影响理性。这些重复的口号简洁又充满煽动性,街上的路人也被游行队伍的热情所感染,因为此刻他们觉得大家成为了一个荣辱与共、共同担当的集体。就像当时正在街上陪家人逛庙会的Q所说的,“当听到‘大同人,站进来’的时候,我立马就热血沸腾起来,那种城市的归属感特别强烈。我也不图啥,只是想跟着大部队绕一圈”。
当队伍走到市政府门口后,几位积极分子手持扩音器继续朝人群喊着口号,“坚持到底,就是胜利”、“咱们要不懈努力,竭尽全力,同心协力,把我们的心声向省委、工会,向北京请愿”,一边维持队伍的高涨情绪一边延长集体行动的持续性。此时,人群已陷入了一种非理性的狂欢,大家积极地响应着积极分子的呼吁。
(2)演讲。演讲作为一种在公共场合进行宣传鼓动的语言活动,可以调动集体心智中的非理性因子。一段声情并茂的演讲,会让现场的听众短时间内信服、接受、认同其所倡导的价值观念。L是其中一个演讲能力超群的积极分子。他有很强的记忆力和丰富的材料储备,对耿彦波的事迹如数家珍,还特意去模仿耿的口音。他通常使用一些与众不同的词语,如古诗、名句、传奇故事或者押韵的顺口溜,针对听众感兴趣的议题针砭时弊,不管走到哪里都是人群中的焦点。
类似L经常演讲的积极分子还有好几位,他们的风格也都不尽相同。有的人喜欢讲述自身的故事,以真实感带动大家的情绪;有的人喜欢收集如照片、书籍等民间资料,制作出精致的作品给大家解说;还有的人肢体语言丰富,经常绘声绘色地说上一段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
(3)持国旗,唱国歌。国旗、国歌是一个国家的象征符号,承载着每个子民对他们祖国的认同感。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已将这种情感内化到人们心中,使得所有国人看到国旗的颜色或听到国歌的旋律,都不由心潮澎湃。尤其是在人群密集、情绪高涨的场合,这种行为不仅能引发在场者的社会唤起效应,完成一些非理性的任务,也能使他们的个体身份模糊化,顺从于群体规范。“唱唱国歌完全也是下意识的,在那么庞大的队伍里,唱大家都会唱的国歌,这不大家都聚在一块了”(访谈对象G)
2.情感或利益的诉求与表征——弱者的武器。詹姆斯·斯科特通过对马来西亚的农民反抗进行研究,发现并不是所有的反抗形式都充满了暴力与抗争。公开的、有组织的社会行动对于多数下层阶级来说是过于奢侈,因为那即使不是自取灭亡,也是过于危险的。有鉴于此,他提出了反抗的日常形式来理解弱势群体的抗争武器,通常包括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偷盗、暗中破坏等。“跪留市长”这场集体行动本身的目标指向是地方性的政治主体,相对于政府而言,运动主体的结构构成属于弱势群体,在表达情感或利益的诉求时会谨慎地采用一些策略,即弱者的武器,以避免极端的直接对抗。
(1)下跪。在笔者的视频资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游行队伍行进到市政府门口时,约有数百余人跪倒在地上,在几个积极分子的带领下,一遍又一遍高喊“耿彦波,回来”、“耿市长,大同人民需要你”等简洁有力的口号,手中拿着耿彦波的照片和各式各样的条幅、标语,甚至有人还提着几样年货。“他一下子走了,人们感觉像是大同的灵魂一下子走了,大同人失去了方向。有一部分人说是给耿拜个年吧,完了就拜年,人们在跟前的也跪下了。”(访谈对象L)表面上看似拜年的下跪,实则传达出了众多行动者们的一种普通情绪——希望政府有人出来表个态。正如彼时有人喊道,“看看我们有多少人,市政府倒是给个说法”。
中国社会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仍然处于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的过渡阶段,伦理道德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仍占有重要地位。其中下跪是中国的一种传统礼仪,民间有“一跪天,二跪地,三跪父母”的习俗,老百姓给官员下跪是表示对皇权的臣服。虽然跪拜礼已被国家以政令的形式予以废除,但是文化传统仍然以尊卑有序的礼俗约束着人们的行为。所以,当集体行动的参与者在象征权力的政府门前表达自己的诉求时,会不自觉地通过下跪这么一种符号性极强的行为,是一种弱者武器的典型形式。
(2)搭便车行为。“搭便车”是奥尔森在其著作《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提出的核心定义,他将每个行动者都假设为“理性人”,在追求公共物品时,其中一些人可能会想别人都在为达到目标做出贡献,而自己可以坐享其成。游行过程中,有一部分人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当时有承包商、地产商,他们一看耿走了以后自己的工程也不好说了。看见事儿弄得这么大,他们后来也就加入了。有的出车搬运物资,有的给买水,有的花钱条幅印传单,还有的打旗、打着横幅走到市政府的。”(访谈对象Z)开发商们都把集体行动视为一个表征自身利益诉求的绝佳场域。
此外视频资料中还清楚显示,游行队伍里有一些“另类”群体显得格外引人注目。队伍的最前方有一个患有智力障碍的年轻人,举着耿彦波的大幅照片,跟着人群中呼喊的口号他的嘴里也在嘟哝着。笔者特意再三向若干访谈对象询问,但得回来的反馈都不尽相同。有的说是他的父母也在队伍当中,带着他凑热闹的;有的则推测说是开发商花钱雇来的……真真假假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样弱势群体的出现本身就是弱者最好的武器。
(3)裸体抗争。弱者的武器作为一个行动资源库,行动参与者不仅从中拿取他们熟悉的方式来行事,而且会依据弱者自身的智慧创造更加行之有效的形式。L在游行当天,突发灵感地运用了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裸体抗争,顺利化解了他遇到的困境。“初八那天,天没亮我就起身准备去和阳门。没走出小区门口,就让几个便衣拦住了,说是要搜我身,并且要带我去所里讯问。僵持了一会儿,我看脱不了身,就想了一个办法。等八点的时候,小区的人慢慢多起来了,我就开始脱衣服。围观的人越来越多,那几个便衣一看我不好惹,就灰溜溜地走了。”(访谈对象J)
通过以上对大同“跪留市长”这场集体行动进行历时性描述,本文简要勾勒出导致其爆发的社会背景及因拆迁获利机会不均而生成的利益群体的结构图谱。集体行动的参与者,大致可以划分为拆迁受益者、尚未得到妥善安置的市民和工程款未结清的施工队在内的利益受损者、临时动员的普通百姓。古城尚未完的建设工程,一半壮美一半荒芜的城市景观,满目苍夷的拆迁残迹,妥善安置的空头承诺,尚未拿到地却提前支付的土地出让金,悬而未决的工程欠款……不同群体各自怀有自身的担忧。当市长突然被调离这一导火索迅速点燃大同民众情绪时,行为动机原本迥异的各个群体把情感及利益诉求纷纷聚焦于对这一政策的埋怨与不解。
在游行过程中,集体认同感和情感利益诉求的表现形式不断被行动修辞策略建构。行动发起者为了获得更多的盟友或动员更多的参加者,有意对话语策略进行一定的修订,以能联合那些原本与他们的情感或利益出发点均有一定差异的组织或个人来支持或加入这一行动。行动组织者没有采用直接表达诉求的话语体系,而是使用包括口号、演讲、唱国歌、下跪、搭便车等属于“隐藏的文本”和“弱者的武器”的行动策略,不断摁下一个个的修辞按钮以吸引大多数人的参与,表达民众的情感和利益诉求。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隐藏的文本和弱者的武器其实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区分,它们的拟合程度很高。正如斯科特所强调的那样,隐藏的文本至关重要而又未足够强调的方面是,它并非仅包括语言行为,而是包括整个的实践过程。对许多农民来说,诸如偷猎、盗窃、秘密地逃税和故意怠工都是隐藏的文本的组成部分。同样,“跪留市长”这场集体行动的诸多修辞策略,如签名、口号、演讲、下跪等话语和符号性行为充分展现了民间智慧,不同程度地避开了政治决策的逻辑,小心翼翼地遮掩起本质内核,为他们的诉求套上了一层隐形的文本。既是增强集体认同感的建构工具,也是弱者表达自身诉求的同时避免公开对抗风险的必然之举。
[1]“耿彦波粉丝团”事件再调查:耿走后125项工程停工[J].新京报,2014-11-13.
[2] James C.Scott,Weapons of the Weak: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1985
[3]赵鼎新.集体行动、搭便车理论与形式社会学方法[J].社会学研究,2006,(1).
[4]郭于华.再读斯科特:关于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J].中国图书评论,2007,(8).
[5](法)雷蒙·阿隆(RaymondAron)著,葛智强,胡秉诚,王沪宁译.社会学主要思潮[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6](美)詹姆斯·C.斯科特(JamesC.Scott)著,郑广怀,张敏,何江穗译.弱者的武器[M].译林出版社,2007.
[7]王金红,黄振辉.中国弱势群体的悲情抗争及其理论解释——以农民集体下跪事件为重点的实证分析[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