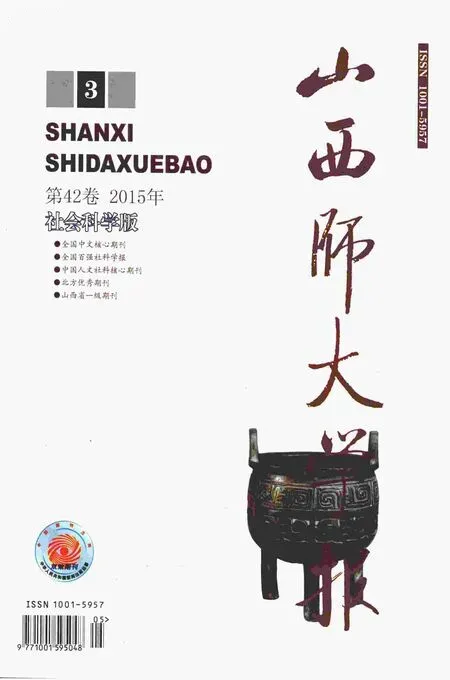汉魏六朝俗赋与乐府的关联谫论
马 言, 冷江山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
自刘歆将“诗赋”当作一个整体而载录《七略》,后世班固、挚虞、刘勰、刘熙载并纪昀等人皆认为诗赋一体,亘古不变。这些论断虽然都指的是“雅赋”与“雅诗”,但是“雅赋”与“俗赋”并为赋体,“雅诗”与“俗诗”皆为诗体,都有一定共性,故俗赋与乐府亦当存有关联。而这种关联就是交互影响,表现在题材、手法和传播方式等方面。需要说明的是,关于“俗赋”的概念,近现代学者游国恩、马积高、郑振铎、傅芸子、程毅中并伏俊琏先生等均有论述。其中程毅中先生所论最具开创性[1],伏俊琏先生承之而论[2],而我们就是在此基础上展开讨论的。
一、题材类同
俗赋与乐府皆产于民间,亦共同反映着底层民众的生活。汉王褒《僮约》便讲述了一个幽默风趣、诙谐逗人的民间故事:王子渊到寡妇杨慧家作客,让奴仆便了去酤酒,便了不但不去,反而拉着她前往死去的男主人坟前“说理”,王子渊怒而下券买便了,并言其日后四季需要从事的劳动云云。听完券文,便了词穷而叩头哆嗦,落涕一尺,逗人发笑。关于此文,马积高、霍松林、万光治和郑振铎等皆认为其为俗赋。是赋以四言为主,语言通俗,描述动人。裘锡圭先生亦在《〈神乌赋〉初探》中指出:“四言的大赋是比较接近民间文学的较早出现的一种赋。”晋石崇仿之而作《奴券》,无论是内容,还是语言风格,都与之类似。
与此相类,乐府《孤儿行》则讲述了一个在兄嫂百般虐待下,孤儿不得不四季艰苦劳动、为人牛马的悲惨故事:
孤儿生,孤子遇生,命独当苦……南到九江,东到齐与鲁。腊月来归,不敢自言苦。头多虮虱,面目多尘土。大兄言办饭,大嫂言视马。上高堂,行取殿下堂。孤儿泪下如雨。使我朝行汲,暮得水来归……三月蚕桑,六月收瓜……乱曰:里中一何譊譊,愿欲寄尺书,将与地下父母,兄嫂难与久居。[3]567
宋郭茂倩《乐府诗集》谓“孤儿为兄嫂所苦,难与久居也”。诗旨与《僮约》《奴券》类似,皆言底层百姓的艰辛生活。又《妇病行》一诗,讲述了妇人连年累病,临危托孤,死后丈夫沿街乞讨而孤儿哭天抢地的故事,展现了底层百姓悲惨的生活境遇。出人意料的是,汉墓出土的《神乌赋》末尾雌乌劝雄乌善待孤儿语“疾行去矣,更索贤妇。勿听后母,愁苦孤子”与《妇病行》妇人临终托孤语“属累君两三孤子,莫我儿饥且寒”神似。《神乌赋》为西汉后期之作,而《妇病行》则远早于此,可见《妇病行》对《神乌赋》的影响。
除了这种表现底层民众的贫苦生活外,还有对贫困本身的描绘。如汉扬雄《逐贫赋》通过主体人与客体“贫”的戏谑对话,直接表现贫困。晋束晳《贫家赋》则通过对屋舍、财物、衣被、追债、乞讨、食草等描绘,尽述贫困。而曹丕《上留田行》一诗不仅类于《孤儿行》表现孤儿悲苦主题,“贫子食糟与糠”一语更是将孤儿贫苦之状直接展现出来,令人同情。
禽鸟题材也是俗赋和乐府共同关注的焦点。汉墓出土的《神乌赋》即讲述了一个“禽鸟相斗和生死诀别的寓言故事”[4]。裘锡圭先生认为此赋“作者是一个层次较低的知识分子,而且是在民间口头文学的强烈影响下创作此赋的”[5],扬之水、谭家健、伏俊琏和踪凡等也都认为其为俗赋。需要说明的是,是赋虽言禽鸟之事,然揭示了底层百姓生活艰辛,有冤难伸的困苦。乐府古辞《乌生》,萧涤非先生认为是西汉民间乐府。[6]其与《神乌赋》内容相似,讲述了幼乌被游荡儿用弹弓打死而母乌却束手无策,只能归于天命的故事:
乌生八九子……我秦氏家有游遨荡子……我一丸即发中乌身,乌死魂魄飞扬上天……我人民生,各各有寿命,死生何须复道前后。[3]408
其实,这种现象并非凭空虚构,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现实。司马彪《续汉书》谓“桓帝时,童谣曰:‘城上乌,尾毕逋,一年生九雏;公为吏,儿为徒,一徒死,百乘车。’”郭茂倩《乐府诗集·杂歌谣辞》亦收录此谣。另外,禽鸟离别似乎为当时流行的文学母题,乐府古辞《艳歌何尝行》亦揭示了禽鸟的生死离别:
飞来双白鹄,乃从西北来……妻卒被病,行不能相随……念与君离别,气结不能言……若生当相见,亡者会黄泉。今日乐相乐,延年万岁期。[3]576—577
双鹄并飞,雌鹄却病而不能随,夫妻生死离别。要知道,汉代相当时期内,战乱频繁,男子服役出征甚至战死都可能促使妻离子别,孤儿益生。加之豪强横行,使处在社会底层的百姓生活步履维艰,有病难治,有冤难伸。这便是俗赋与乐府共同关注的社会现实。
考虑水岩化学反应的复杂性,很难确定反应条件,因此,煤样中碳酸盐矿物质化学反应动力学控制方程可写成[15-17]:
夸张式调侃人物也是俗赋和乐府的一个共同点。汉朝常与胡人交战,加之中原中心思想的影响,汉人对胡人多有鄙视和丑化,尤其是胡人的矮小身材,成为汉人百说不厌的笑料。又汉代“百戏”流行,矮小的俳优广布,且多丑陋不堪,故多以此类比。东汉蔡邕《短人赋》即是一篇嘲笑胡人矮小、丑陋的俗赋。赋云:
侏儒短人,僬侥之后……雄荆鸡兮鹜鷿鹈,鹘鸠雏兮鹑鷃鴜。冠戴胜兮啄木儿,观短人兮形若斯。巴巅马兮柙下驹,蛰地蝗兮芦即且。茧中蛹兮蚕蠕蝢,视短人兮形若斯。木门阃兮梁上柱,弊凿头兮断柯斧。鞞鞑鼓兮补履朴,脱椎枘兮祷薤杵。视短人兮形如许。[7]
其所嘲虽为胡人,然将胡人比喻成侏儒,故亦可视作对侏儒的描绘。东汉繁钦《三胡赋》残句“莎车之胡,黄目深精,员耳狭颐。康居之胡,焦头折颈,高辅陷无,眼无黑眸,颊无馀肉。罽宾之胡,面象炙蝟,顶如持囊,隈目赤眥,洞頞卬鼻”[8]1764。又谓“额似鼬皮,色象萎橘”[8]4287。与此相对,郭茂倩《乐府诗集》所辑《俳歌辞》则直言侏儒形象,且形貌动作并举:
俳不言不语,呼俳噏所。俳适一起,狼率不止。生拔牛角,摩断肤耳。马无悬蹄,牛无上齿。骆驼无角,奋迅两耳。[3]520
侏儒虽为观众提供欢乐,但因其处于社会底层,多为文人士大夫所不屑,终为“玩物”,故与胡人并举而为俗赋和乐府所关注。
与调侃人物丑陋不同的是,俗赋和乐府亦歌颂美女。西汉司马相如《美人赋》盛夸邻家女子与上宫女子的美貌。乐府《陌上桑》中罗敷的美貌令人忘乎所以,且后世拟作皆承之而盛赞罗敷之美。《孔雀东南飞》则盛夸刘兰芝的美丽。汉李延年《北方有佳人》则以倾城倾国夸饰其妹。曹植《美女篇》及后世傅玄、魏收和萧子显等人拟作亦尽情描绘美女。另外,还有对女子出身和遭遇的关注。如东汉蔡邕《青衣赋》以青衣(奴婢)为主要描写对象,尽写青衣之美及男女之情,颇有游戏味道。汉乐府《伤歌行》则以女主人公感情为线,表现婚姻不能自主的悲痛。《青衣赋》以积极的笔调述情,风格幽默。《伤歌行》虽格调悲伤,但亦表现了女主人公的不幸遭遇及月下思人的痛苦。就此而言,尽管俗赋与乐府共同反映了丰富多样的题材内容,但这些内容通过什么方式表现出来,则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
二、手法交互作用
俗赋与乐府不但有共同的书写题材,而且这些题材的表现方式亦有相似之处,二体交互作用。赋体的长篇铺排和“乱”的存在影响乐府而为其所接受,乐府音律讲求的特点促使俗赋被采入诗而更以“乐府”之名,这是二者交互作用的必要条件。
西晋陆机《文赋》谓“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9],明确了诗赋二体各自的特性和本质。明胡应麟《诗薮》谓“文章自有体裁,凡为某体,务须寻其本色,庶几当行”。[10]否则即为“别调”或“失体”。俗赋作为赋体以铺排叙事为要,乐府作为诗体以抒情感叹为长。王褒的《僮约》作为故事俗赋,对奴仆便了四季的劳动极尽铺排之能事,然因其以幽默诙谐的态度讲述故事,故感情色彩较淡。而《孤儿行》作为乐府,虽也长于叙事,但感情投入更多。全篇字字含泪,句句深情:“泪下如雨”、“泪下渫渫,清涕累累”云云,将情感抒发推向极致。《妇病行》诸如“不知泪下”、“泣坐不能起”、“对交啼泣,泪不可止,我欲不伤悲不能已”等字眼蕴泪含情,将病妇、丈夫的伤痛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催人泪下。
我们知道,同一题材的抒情,赋比诗更加酣畅,这是由于赋语韵散间杂,虚字夹用,句式散缓。诗体因体制短小,抒情顿挫,且对仗的讲求使其无法铺开,故情感内敛。那么《孤儿行》、《妇病行》为何抒情直爽,而《僮约》述情隐约?探寻其因,二诗杂言、虚字及俗语的夹用,致使结构散缓,略无停顿,抒情顺畅,非常惬意。虚字如“者”、“且”、“呼”、“耳”、“复”、“与”;俗语如“兄嫂”、“大嫂”、“大兄”、“两三”、“不能”、“收瓜”、“一言”、“我儿”、“有过”、“慎莫”、“抱时”、“褥复”、“到市”、“不能”、“买饵”、“不能已”。虚字连带的句式散缓不羁,俗语的参与使其顺畅通俗。而《僮约》作为赋体却抒情不浓,只因大量的时空铺排,近似口语式的语言,幽默风趣的讲诵风格,是为讲述故事而非抒发情志。其体为故事俗赋,而非述情俗赋。这种现象的存在不能否定赋体较诗体长于抒情的本然规律。乐府诗抒情的酣畅亦不能否定诗体抒情的节制,只因乐府的抒情一顺是因其具有赋体特征。因此,赋体体物铺事,直抒情志;诗体点逗物事,含蓄抒情,这是明辨诗赋二体的重要识见。
《孔雀东南飞》是一篇学界公认的乐府诗,然观其体制,颇具赋体特征。关于此点,明谢榛《四溟诗话》谓:“‘孔雀东南飞’,一句兴起,馀皆赋也。其古朴无文,使不用妆奁服饰等物,但直叙到底,殊非乐府本色。”[11]谢氏之言甚谛。诗云“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此显为赋体时间铺排,一叙到底,酣畅无碍,无比惬意;又云“妾有绣腰襦,葳蕤自生光。红罗复斗帐,四角垂复囊。箱帘六七十,绿碧青丝绳”,句中“腰襦”、“红罗”、“斗帐”、“箱帘”、“复囊”、“青丝绳”等铺写,近似赋体铺写名物,分次罗列;复云“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着明月当。指如削葱根,口如含丹朱”,此句“足”、“头”、“腰”、“耳”、“指”、“口”等全方位、立体式描绘似赋体空间铺排,上下左右分而言之。正如清刘熙载《赋概》所言:“赋兼叙列二法。列者,一左一右,横义也;叙者,一先一后,竖义也。”
此外,“乱”的存在也是俗赋与乐府交互作用的条件。“乱”本为音乐特性。《乐记》谓:“乐者,心之动也……再始以着往,复乱以饰归。”《论语》朱熹注亦谓“乱,乐之卒章也 ”,又《国语》韦昭注谓“摄其大要为乱辞”。《楚辞》中也有“乱”,如《离骚》、《招魂》、《哀郢》、《涉江》、《抽思》、《怀沙》等,又王逸《楚辞章句》云:“乱,理也。所以发理辞首,撮其要也。”需要明辨的是,“乱”作为歌辞的结尾,与前面的主歌部分比较,有篇幅小、句式短的特点[12],而作为楚辞的“乱”,一般长于其前的各个歌节。[13]但是,汉代惟大曲才有“乱”。宋郭茂倩《乐府诗集》谓:“大曲又有艳,有趋、有乱。辞者其歌诗也,声者若羊吾夷伊那何之类也,艳在曲之前,趋与乱在曲之后,亦犹吴声西曲前有和,后有送也。”[3]377又据《乐府诗集》所引《宋书·乐志》载大曲十五曲,《孤儿行》、《妇病行》和《孔雀东南飞》皆非大曲,然其皆有“乱”。《孤儿行》、《妇病行》明显有“乱曰”的字眼,且《妇病行》主歌部分仅9句54字,而“乱”竟有16句78字之多,“乱”显然多于主歌,而这正是楚辞(赋体)“乱”的特点。我们知道,赋体一般有“序”、“正文”、“乱”三部分。《乐府诗集》所录《孔雀东南飞》有序和正文。虽然没有“乱曰”字眼,但是“两家求合葬”至“戒之慎无忘”明显具有“乱”的总结性质,所以可视作“乱”,这也是受赋体影响。伏俊琏先生就认为《孔雀东南飞》受《汉书·东方朔传》所引《上书求仕》影响,而《上书求仕》则受俗赋影响,故而《孔雀东南飞》受俗赋间接影响。叶桂桐则直接判断它是“文人赋”[14]。
其实《孔雀东南飞》本为俗赋,后以文人俗赋的体制被采入乐府,按照乐府声律要求予以加工改造,并更以“乐府”之名。《汉书·礼乐志》云:“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章之调,作十九章之歌。”[15]1045关于采诗,徐中玉先生认为:“民风当然不只反映在诗里,这‘诗’字,不但不只指《诗经》和《诗经》未收入和后出的,其实包括了一切民间的创作,口头的和书面的,有韵的和无韵的,各种体裁和样式的。”[16]故颇具赋体特征的《孔雀东南飞》很可能是以文人俗赋的体制被采入乐府。何涛与张桂萍认为在乐府里,作为诵读的“楚辞”就是“赋”,而当它被配上乐调歌唱时,就成了乐府歌“辞”[17]。《孔雀东南飞》虽然被采入乐而冠以“乐府”之名,但仍保留了俗赋的基本特征。杨荫浏先生就认为,《孔雀东南飞》“从内容、艺术形式和演唱的效果看来,这类歌曲可能已不是一般的歌曲, 而是一种说唱音乐”[13],是说甚谛。这种两属的特征,正是俗赋和乐府手法交互作用所产生的结果。俗赋与乐府内容和艺术形式上的相似还只停留在文本层面,而它们都是“表演式”文学,所以深入探讨其表演亦即传播情况,是厘清二者关联的根本所在。
三、传播方式相似
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指出:“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民间的小儿女,村夫农妇,痴儿怨女,歌童舞妓,弹唱的,说书的,都是文学上的新形式与新风格的创造者。这是文学史的通例,古今中外都逃不出这条通例。”[18]俗赋和乐府皆是“表演式”文学,且都先流行于民间,然后在官方传播。所以其传播情况有许多相似之处,主要有:表演者多是俳优、乐伎、歌者和讴者等,传播地点集中在陶楼乐坊、富家堂院或户外游娱之地,受众多为普通百姓、富家财主或皇室贵族,且皆以娱悦受众为目的。
(一)俗赋和乐府在民间的传播情况。无论是俗赋还是乐府,其本身所具有的娱乐性促使其在民间广泛传播,为大众所接受,而这就缘于二者所具有的相同特征:表演者有时一人,有时多人;表演都需要乐器伴奏;表演地点多在陶楼乐坊或富家堂院;传播者与创作者时分时合。如俗赋的表演有时是一人诵唱或一人扮演不同角色说唱;有时是两人扮演不同角色对话。这类俗赋表演往往极尽赋体铺张夸饰之能事,运用通俗易懂的俚语和俗语,讲述或捧腹大笑或催人泪下的故事,这从上文所列俗赋的内容可知。而关于表演的具体情况,因其过于俚俗而为史家所鄙弃,我们无法从传世文献得知,但从出土的说唱俑形象可得一二:表演者大都躯体粗短,上身裸露,下衣宽松垂落,一手执槌,一手抱鼓,头、臂戴装饰品,歪头耸肩,眯眼歪嘴,开怀大笑,腹部丰腴,整体形象滑稽诙谐,颇具夸张性和娱人性。满城1号墓、南昌贤士湖14号、甘肃灵台傅家沟、江苏仪征烟袋山等西汉墓及河南密县后士郭2号东汉墓*引自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397页。中所出土的说唱俑,均表现出夸张的动作和滑稽的表情。同时,细看不难发现几乎每一个出土的说唱俑都抱着鼓,说明鼓为他们的主要演奏乐器。至于表演地点,有的在陶楼的门廊下,有的在陶楼的楼上,面向街上观众表演,而有的则在主人家庭院内。至于传播者与创作者的分合情况,目前尚无传世文献记载,但因其是民间村夫农妇、小儿、艺人及无名文人等杂相创作和传播,所以我们推知,创作者和传播者可能为一,亦可能不一。
与俗赋不同,乐府则进入了史家视野,其在民间的传播,文献多有记载。《宋书·乐志》谓:“凡乐章古词,今之存者,并汉世街陌谣讴,《江南可采莲》、《乌生》、《十五》、《白头吟》之属是也。”因乐府相和歌辞与俗赋最为接近,故所论以相和曲为主,兼有其他。《宋书·乐志》谓:“相和,汉旧曲也,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可见乐府是有乐器伴奏演唱的。至于乐器,《乐府诗集》引《古今乐录》谓:“凡相和,其器有笙、笛、节歌、琴、瑟、琵琶、筝七种。”[3]377乐府《古歌》谓“弹瑟为清商”,宋鲍照《堂上歌行》谓“筝笛更弹吹”云云。这在出土文献中亦可见。1954年河南洛阳防洪渠二段第七十四号墓和1971年四川省遂宁县东汉墓出土的陶楼上都有弹琴俑。
乐府表演者亦与创作者或合或分。《乐府诗集》引《风俗通》谓百里奚的妻子自己造词,自己弹奏。此虽为秦例,其他朝代亦如此,尤其是朋友相聚或外出游玩时,往往会有现作现唱(详见下文)。此外,廖群先生例引《公无渡河》的传播情况,说明歌者对原有歌辞进行配乐而演唱。狂夫的妻子本是原唱,后来子高的妻子丽玉不仅配乐弹唱,而且又将曲子传授给邻女丽容。还有《乐府诗集》中《饮马长城窟行》, 虽然题为“古辞”, 但是引《乐府解题》云“或云蔡邕之辞”。因此,这首乐府概先由蔡邕创作,再由专业歌者演唱。据此是否可以这样推测:汉代歌者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大家创作的诗歌,或原封不动或改造加工而歌唱。
至于传播地点则多是主家厅堂、乐坊或游冶之地。《长歌行》谓:“来到主人门,奉药一玉箱”;《陇西行》谓“好妇出迎客……送客亦不远”;晋傅玄现作《前有一樽酒行》谓“同享千年寿,朋来会此堂”;宋鲍照现作《堂上歌行》谓“四坐且莫喧,听我堂上歌”;陈张正见现作《前有一樽酒行》谓“前有一樽酒,主人行寿”等等,其中“主人”、“好妇”、“送客”、“此堂”、“堂上”等字眼显然表明表演是在主家厅堂之上。又1969年山东嘉祥南武山古墓出土的画像石和江苏邳县白山故子两座东汉墓发现的画像石,亦表明表演地点在厅堂。而曹植《斗鸡篇》谓“游目极妙伎,清听厌宫商。主人寂无为,众宾进乐方”,说明演奏既在主家,又在乐坊。且四川郫县汉墓出土的石刻画像《宴饮乐舞》亦说明演唱在庭院。外出游冶之地则如《西门行》谓“出西门,步念之,今日不作乐,当待何时”。又1976年滕州市城郊马王村出土的建鼓楼阁垂钓图画像石和2011年滕州市城郊乡东寺院村古墓中出土的画像石亦表明演奏地点在户外游冶之地。
另外,还有一则材料值得注意。1971年四川省遂宁县东汉墓出土了一座反映地主生活的陶楼。楼有上下两层,上层是抚琴俑和歌唱俑表演,下层右侧有一个裸露上身击鼓说笑的说唱俑,张嘴吐舌,一手握锤,似乎达到了表演的高潮。从这个出土的陶楼,我们大概可以获得以下信息:这是反映地主生活的画面;演唱地在陶楼;歌者用琴伴奏;抚琴者与歌者不是一人;俳优击鼓表演俗赋,滑稽诙谐;乐府与俗赋表演在同一楼内。这不仅说明了乐府表演者为两人,以琴为演奏工具,而且还说明了俗赋和乐府在民间的传播都需要乐器,并且表演地点和受众都一样。
(二)俗赋和乐府的官方传播情况。俗赋在官方的传播,一方面通过赋家或俳优表演,另一方面则通过王公贵族的喜好而推崇。汉代俗赋在宫廷的传播有的是由赋家或俳优独自完成,有的则是由赋家创作,俳优表演,但以后者居多。其中赋家诸如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和曹植等。冯沅君先生曾援引前辈学者称“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有似优人的脚本”[19]。东方朔和枚皋则直接被皇帝以俳优蓄养。东方朔所著《大言赋》和宋玉同题赋相似,都属于民间娱乐文艺。而枚皋“谈笑类俳倡,为赋颂,好嫚戏”,作娱赋可读者120篇,不可读者数十篇。其实,他们创作俗赋乃职责所在。这些赋家因献赋而为皇帝所召,多拜为郎官,供职于乐府,而乐府作乐就是为皇室贵族提供娱乐。因此,乐府不但如上文徐中玉先生所言“采集俗赋入乐”,而且还创造了大量的俗赋,以供朝廷饮宴和帝王出游之需要。而汉武帝、汉宣帝和汉灵帝以及后世王侯对俗赋的喜好则促进了俗赋的传播,以致王侯贵族纷纷观赏。如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了两个说唱俑;曹植初见邯郸淳便如俳优般表演。
至于乐府,其被乐府机构采入宫内,演唱者亦是倡优,歌辞或为乐府机构专业人员或为其他朝臣制作,且亦如俗赋多在朝廷宴会或皇帝出游时演唱,并以歌颂形式欢悦君王。如《董逃行》谓“奉上陛下一玉柈,服此药可得神仙……陛下长生老寿,四面肃肃稽首,天神拥护左右,陛下长与天相保守”;《王子乔》谓“圣主享万年,悲吟皇帝延寿命”;曹丕《临高台》谓“愿令皇帝陛下三千岁”;《王公上寿酒歌》谓“皇帝永无疆”;梁吴均《城上乌》谓“陛下三万岁”;梁周舍《上云乐》谓“但愿明陛下,寿千万岁”;《钜鹿公主歌辞》谓“皇帝陛下万几主”云云。亦如俗赋一般,帝王的喜好促进了乐府的传播,很多王侯贵族自家就蓄养歌女。如赵飞燕是阳阿公主家的歌女。又《汉书·贡禹传》谓“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数十人”,并且当时出现了“至与人主争女乐”的奇异现象。
王运熙先生指出,善于滑稽辞令的赋家与演唱乐府的黄门倡优地位类同,且大多赋家供职于乐府机构,不但创作俗赋,而且还将俗赋改造成乐府。赋家兼乐人的双重身份促使俗赋与乐府在题材选择,表现方式以及传播方面有了相同或相似的条件。综上而言,俗赋和乐府在表演者、表演时间、表演地点、表演方式、表演目的和受众等方面,或相似,或相同,这也就促进了二者相互借鉴,相互影响。
总之,俗赋与乐府交互影响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二者传播方式的类同,而赋体长篇铺排和存有“乱”的特征与乐府音律讲求的特点是二者交越互用的必要条件,共同反映民间底层社会生活则是交互的基础。然而需要强调的是,在诗体拥有绝对话语权的历史背景下,赋体与诗体的交互虽然可以促进赋体一时的繁荣,但从长远来看,其往往会因被改造而变体。尤其是唐代对声韵的严格讲求对其负面影响最大,使其僵化乃至僵死。因此,宋代至今,俗赋被分流在词、说话、曲、小说、评书、评话和相声等文艺中,而不再独立存在。
[1] 程毅中.敦煌俗赋的渊源及其与变文的关系[J].文学遗产,1989,(1).
[2] 伏俊琏.俗赋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8.
[3] 郭茂倩.乐府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7.
[4] 谭家健.《神乌赋》源流漫论[J].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8,(10).
[5] 裘锡圭.神乌赋初探[J].文物,1997(1).
[6] 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7] 徐坚.初学记[M]. 北京:中华书局, 1982.
[8] 李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60.
[9] 严可均.全晋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
[10] 胡应麟.诗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11] 谢榛.四溟诗话[A].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2] 崔炼农.“乱”之源流考辨——《乐府诗集》音乐术语丛考之一[J]. 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6,(3).
[13] 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
[14] 叶桂桐.论孔雀东南飞为文人赋[J].中国韵文学刊,2000,(2).
[15]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6] 陈勤建.文艺民俗学导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
[17] 何涛,张桂萍.“辞”“赋”与乐府[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3).
[18] 胡适.白话文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19] 冯沅君.冯沅君古典文学论文集[C].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