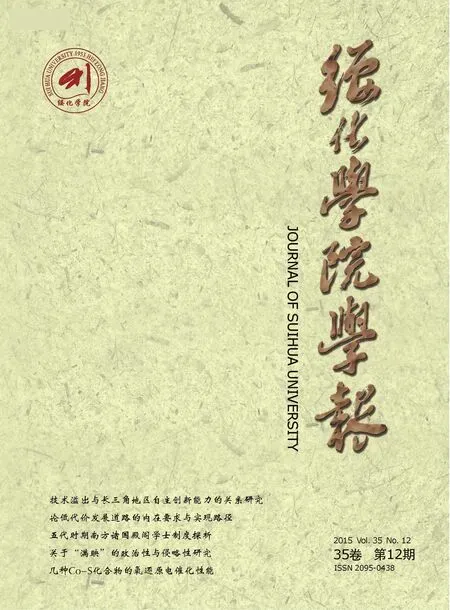从两次复仇看张良的传奇人生
严振南
(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 广西南宁 530000)
从两次复仇看张良的传奇人生
严振南
(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 广西南宁 530000)
在张良一生共经历了两次复仇,博浪沙刺秦和扶刘灭项。复仇贯穿着张良的一生,无论是助刘降秦,还是扶刘灭项,都是张良复仇的手段。而张良“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的人生归宿,是复仇完成,人生理想幻灭,在现实中无路可走后的一种精神补偿。张良的传奇一生,与其复仇的使命息息相关。
张良;复仇;从仙
张良,字子房,秦末汉初时期重要谋臣,被刘邦封为留候,其祖父开地、父平,曾五世相韩,秦灭韩后,张良倾尽家财寻求刺客,为韩报仇,从此走上了复仇之路。博浪沙刺秦,是张良传奇一生的开始,随后一系列的传奇经历更是为后人津津乐道,如:下邳偶得黄石老人兵法、协助刘邦计取峣关、智斗鸿门宴、阻封六国、鸿沟回杀项羽、兵围垓下、谏封雍齿、举荐商山四皓等。而辟谷谢世,托身仙道更为张良的一生增添了神秘色彩。
有关张良的生平记载,主要集中在太史公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中,《史记》中,张良的生平事迹除了在《留候列传》中外,还出现在《项羽本纪》《高祖本纪》《韩信卢绾列传》等篇目中,《汉书》则集中呈现在《张陈王周传》《高帝纪》《陈胜项籍传》中。
一、第一次复仇:博浪沙刺秦
秦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博浪沙刺秦掀起了张良传奇一生的序幕。《史记·留侯世家》记载:
良尝学礼淮阳,东见沧海君。得力士,为铁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东游,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误中副车。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贼甚急,为张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1](P2034)
博浪沙刺秦,掀起了张良第一次复仇序幕,报强秦灭韩之仇成为张良的责任和使命。关于张良刺杀秦始皇的原因。《史记.留侯世家》记载:
留侯张良者,其先韩人也。大父开地,相韩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岁,秦灭韩。良年少,未宦事韩。韩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韩
故。[1](P2033)
张良家族五世相韩,灭国之仇不共戴天,因此,向强秦复仇成为张良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张良的强烈复仇愿望和先秦时期儒家思想中复仇观念的强化密切相关。
(一)儒家“忠孝”思想的内在驱动。复仇观念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儒家经典中对复仇有明确记载,孔子和子夏关于复仇的一段对话。
《礼记.檀弓上》记载中:
子夏问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曰:请问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与共国;衔君命而使,虽遇之不斗。曰:请问居从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为魁,主人能,则执兵而陪其后”。[2](P321)
《孟子·尽心下》记载:
吾今而后知杀人亲之重,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然则非自杀之也,一间也。[3](P196)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儒学思想在对待复仇问题上态度十分鲜明,其中对待父母之仇态度更加强烈,为报父母之仇必须杀死仇人。作为儒家经典的《公羊传》又将君臣之义与父母之仇联系起来,将臣子讨伐弑君者与报父母之仇等同。在先秦时期,人们将父子的关系与君臣关系等同。所以子应对父尽孝,臣应对君尽忠,如果君、父被人伤害,臣或子不为之报仇,则将被千夫斥责其不忠、不孝。基于这样的“孝道”意识和复仇观,张良为韩复仇,是对其家族,乃至整个韩国的忠孝,向秦复仇便成了张良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故瞿军在《下郊子房山吊古》:“曾传博浪独棰秦,半为君恩半为亲。不惜万金扶旧国,将凭一敛慰先人。”清人毛际可评价到:“夫子房发愤于五世之仇,枕戈待旦,而藉手于力士一击,亦安能预知扶苏之必不得嗣位,胡亥之必至于亡,而徐以俟始皇之自毙哉?然子房之原本忠孝,又非荆柯之借交报仇所敢望已。”[4](P180-181)这突出说明了张良思想中深受需家“忠”“孝”文化观念的影响。
(二)游侠风气对第一次复仇行为的影响。《史记·游侠列传》记载: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启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1](P3181)
从司马迁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侠客的品质,他们有“言必信,行必果”的强烈的责任感,有“不爱其躯,赴士之启困”的献身精神。这种游侠的社会风气,对张良第一次复仇的行为的选择上有重要影响。公元前230年,韩被强秦所灭,面对灭国之难,张良弟死不葬,拿出全部家财寻求刺客刺杀秦王,替韩报仇。终于,公元前218年,在秦始皇第三次巡游到阳武博浪沙时,张良带领沧海力士向秦始皇击出一棰。从韩灭亡到博浪沙棰秦,身负国仇家恨的张良,为了这一击,等待12年。然而沧海力士的铁锥误中秦始皇车队副车,这次刺杀行动失败,张良亡匿下邳,开始近十年的亡命生涯。张良亡身下邳,经历的传奇性事件——偶遇黄石老人。《史记·留侯世家》记载:
良尝间从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堕其履圯下,顾谓良曰:“孺子,下取履!”良鄂然,欲殴之。为其老,强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业为取履,因长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惊,随目之。[1](P2034-2035)
圯上纳履,让张良获得了黄石老人的《太公兵法》,拥有了为帝王师能力。
(三)一心系故国,十年磨一剑。《史记.留侯世家》记载的圯上老人的传奇故事,正是张良第一次复仇中断后,隐匿下邳近十年的缩影。十年后,为韩报仇的时机再次到来。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农民起义爆发,二年正月景驹自立为楚王,张良也“聚少年百余人”前去投靠景驹。然而阴差阳错,张良却成了刘邦身边的谋臣。张良投靠刘邦,并非要辅佐刘邦夺取天下,而是要完成十年前的未完成的为韩报仇计划。只因张良向他人讲述自己苦心钻研的兵法谋略不被重用,唯独刘邦愿意用他的计策,并拜张良为厩将。《史记.留侯世家》记载:
良数以《太公兵法》说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陈季雅认为:“造汉非子房之素愿,其心但欲亡秦耳。[1](P2036)
1.积极复国,说服项梁立韩后裔为王。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十二月,雍齿叛沛公,以丰降魏,沛公还击不能下。四月,沛公入薛见项梁,项梁益沛公卒五千,五大夫将十人,沛公还击丰,拔之。六月,项梁召集各路将领汇集薛地,张良跟随沛公到薛地得见项梁,因陈王已死,项梁决定立楚怀王孙心为楚王,此时,项梁在义军中威望极高,且各路将领齐聚薛地,算是一次真正意义的义军会盟。张良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请求项梁立韩诸公子横阳君成为王,项梁答应了张良的请求,立以为韩王,拜良为韩申徒。项梁的认可无疑让积极复国的张良看到了希望,张良积极为韩国的重建而奔波,与韩王将千余人西略韩地,得数城。然而,攻得下却不能坚守,“秦辄复取之,往来为游兵颍川”[1](P2036),张良只能追随韩王成在韩故地游击。
2.继续复仇之路,再得韩后裔——韩王信。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楚怀王“令沛公西略地入关”,刘邦一路上收集陈胜、项梁的散兵,经砀转军北上至城阳,与杠里的秦军对垒,刘邦击败秦两支军队。沛公引兵继续西进,在昌邑与彭越相遇,两军合并一起攻打秦军,然而,战势不利,还至栗(河南夏邑)时,和刚武侯军队相遇,吞并其四千余人。随后,与魏将皇欣、魏申徒武蒲的军合并作战,共同攻打昌邑,未攻下,因此,只得取道,西过高阳。二月,沛公用郦食其计策袭陈留,得秦积粟,拜郦商为将一同攻打开封,开封未下,遂北攻白马的秦军,取胜后又进攻曲遇,杨熊最终兵败走荥阳,为秦二世所斩。
沛公带兵攻阳武,下轘辕、缑氏,绝河津,击赵贲军尸乡之北,随后,攻打雒阳,进攻受阻,“战雒阳军,军不利,还至阳城。”[1](P359)。此时,沛公与在颖川一带游击的张良和韩王成相遇,在张良的帮助下,沛公夺取轘辕,轘辕关地势险要,为历代兵家必争和控守要地,《元和郡县志》载:“轘辕山,山路险阻,十二曲道,将近复回,故曰:轘辕”。同时,张良还帮助沛公降下韩故地十余城,“沛公之从雒阳南出轘辕,良引兵从沛公,下韩十余城”[1](P2037)。张良在降下韩故地时,又得了韩后裔——韩王信,“沛公引兵击阳城,使张良以韩司徒降下韩故地,得信,以为韩将,将其兵从沛公入武关。”[1](P2631)。攻下韩故地后,沛公令韩王成留守阳翟,至此,韩王成终于有了立锥之地,结束了奔波游走的命运。而张良和韩王信随沛公继续征战,攻下宛,西入武关。
3.计取峣关,张良终报灭国之仇。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八月,沛公攻破武关,随后,欲带兵两万强攻峣关,张良谏曰:“秦兵尚强,未可轻。臣闻其将屠者子,贾竖易动以利益为张旗帜诸山上,为疑兵,令郦食其持重宝啖秦将”[1](P2037)(于是沛公“乃用张良计,使郦生、陆贾往说秦将,啖以利”[1](P361)(,结果,秦将果然叛变,并想联合沛公一起西袭咸阳;沛公欲接受秦将联合,张良再次进谏曰:“此独其将欲叛,恐其士卒不从,不如因其怠懈击之。”[5](P22),沛公听从张良的建议,“沛公引兵绕峣关,逾蒉山,击秦军,大破之蓝田南。遂至蓝田,又战其北,秦兵大败。”[5](P22)。
汉元年(公元前206年)十月,秦王子婴降。从公元前230年,“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到公元前218年,博浪沙第一次棰秦,失败后,亡身下邳十年,再到公元前206年子婴降沛公,张良用了近24年的时间,终于报了秦的灭国之仇,完成了第一次的显性复仇。清代顾炎武《亭林诗集》卷五《子房》对张良赞颂到:
天道有盈虚,智者乘时作。
取果半青黄,不如待自落。
始皇方侈时,土宇日开拓。
海上标东门,长城绕北郭。
欲传无穷世,更乞长生药。
子房天下才,是时无所托。
东见仓海君,用计亦疏略。
狙击竟何为,烦被十日索。
譬之虎负隅,矜气徒手博。
归来遇赤精,奋戈起榛薄。
峣关一战破,蓝田再麾却。
啧啧帜道旁,共看秦王缚。
二、第二次复仇
(一)一心辅佐韩王成,辞别汉王赴故国。反秦大业完成后,论功行赏成为秦灭亡后的第一件大事。汉元年正月(公元前206年),项羽佯尊怀王为义帝,而自立为西楚霸王,成为实际上的权力掌控者,分封各路诸侯。项羽背弃楚怀王“先入定关中者王之”的约定,“更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而韩王成因袭韩故地,都阳翟。”至此,张良“为韩报仇”的心愿得以完成,他不仅借助刘邦的势力灭掉了秦国,还帮助韩后裔成重新获得了韩故土。
四月,天下已定,诸侯各归其封地,汉王亦启程前往汉中,张良却未跟随汉王入汉中。张良最大政治理想是复家复国,辞汉归韩,辅佐韩王成治理韩国,是此时张良唯一的愿望,所以,在褒中张良与汉王辞别,启程归韩,并建议汉王烧掉栈道,亦示项羽无东归意向。
自薛地受封至褒中辞别,张良以韩申徒身份助汉王破峣关,夺蓝田,智斗鸿门宴,请封汉中。张良虽不时地出现在汉王身边,在身份上却从属于韩王成的韩国,刘邦和张良的关系,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盟友关系。这种盟友关系存系的根本原因,是存在一个共同的敌人——秦。随着秦王朝的灭亡,这种盟友关系也随之解除。
(二)项羽杀韩王成于彭城,张良再燃复仇火焰。汉之元年(公元前206年)四月,诸侯兵罢戏下,各就其国,然而韩王成却未能到封地。韩王成被项羽带到了彭城,随后降为侯,接着又被项羽杀死。项羽在彭城杀死了韩王成,让张良相韩的梦想彻底破灭。对于项羽杀韩王成的原因,《史记》和《汉书》中均有明确记载。
1.张良为汉王出谋划策,项羽怀恨在心。《史记.留候世家》中记载:“韩王成以良从汉王故,项王不遣成之国,从与俱东...又杀之彭城。”[1](P2039)张良以韩申徒(等同于韩国丞相)身份助汉王先入咸阳,并躲过鸿门宴一劫,使项羽在与刘邦的争斗中处于劣势。项羽把对张良的怨恨强加到了韩王成的头上。他一心辅佐的君主,还是因自己而被杀,这无疑给了一心相韩的张良重重一击。
2.韩王成无军功而受封,难以服众。《史记·项羽本纪》中明确记载:“韩王成无军功,项王不使之国,与俱至彭城, 废以为侯,已又杀之。”[1](P320)自薛地张良向项梁请封韩王以来,韩王成并未做成一件可以服众的事情。首先,项梁使张良求得韩王成,立以为王,开始与韩故地的秦斗争。然而攻下来的城池,很快便被秦军夺了回去。直到沛公打到韩故地时候,良引兵从沛公,才拿下了十几座城池,韩王成方得以留守阳翟。其次,项梁战死定陶时,韩王成却因为害怕而跑去投奔怀王,“项梁败死定陶,成奔怀王”[1](P2631),这完全违背了项梁“立韩诸公子横阳君成为韩王,欲以抚定韩故地”[1](P2631)的初衷。韩王成在整个反秦战争中表现平庸,碌碌无为,封王难以服众。
(三)助刘反项,复仇之路又起。汉元年七月(公元前207年),项羽诛杀了韩王成,张良辞别汉王东归相韩的政治理想彻底覆灭。故主被杀,苦心经营的一切化为了泡影,张良复仇的火焰又重新被燃起。然而,当时西楚霸王项羽的实力非常强大,向项羽寻仇,绝非张良能凭借一人之力可以完成。若想复仇,必须寻找一位强大的帮手,而汉王便是最佳人选,因为他们又有了共同的敌人——项羽。魏了翁说:“沛公既王汉中,送至褒谷辞归相韩,劝王烧绝栈道示项羽无东意。当是时亦未尝劝汉王以取天下,俾之匿形藏影为还定三秦之计则有之矣。逮夫项羽杀韩王成,良既已无可事之主,然后间行归汉,求所以帝刘灭项者,始终为韩报仇,而假手于汉耳。于声利之间泊若无情而其思虑之所发,从容定计,亦倐忽变化而不可测。”
1.遗书项羽,骗其击齐。汉元年八月(公元前207年),汉王还定三秦。项羽听说汉王已经兼并关中,并且意欲继续东行军,而北面齐赵又皆叛变,因此大怒。面对这样的局势,张良遗书两封,项羽干扰其判断,劝项羽向被击齐,为汉王东进减轻阻力。
张良留给项羽的封信,实质上是颗烟雾弹。在第一封信中,张良对项羽说:“汉王失职,欲得关中,如约即止,不敢复东。”[5](P2028),汉王“如约”的原因是项羽“背约”,项羽在分封诸侯时,违背义帝“先入定关中者王之”的约定。项羽“负约”在前,汉王“失职”在后,第一封信起到了提醒项羽的作用,让项羽对“负约”的行为心生愧疚,从而麻痹项羽对局势的判断,放松对汉王的警惕。接着张良的第二封信,又给被麻痹的项羽指明出路,“以齐反书遗羽,曰:“齐与赵欲并灭楚”,张良将祸水北引,项羽果然进入了张良预设的圈套中,“羽以故无西意,而北击齐”[5](P32)。
刘邦很快还定三秦,并进一步谋划东归。“汉王还定三秦,乃许信为韩王,先拜信为韩太尉,将兵略韩地”[1](P2632)“项羽闻汉王皆已并关中,且东,齐、赵叛之,大怒”[1](P321),然而,项羽此时深陷和齐的交战中,无暇分身,张良的两封信为汉王东进赢得了时间。项羽大怒的原因主要不是因为汉王还定三秦,而是因为汉王既然还定了三秦,却仍然继续向东进军,这和张良说汉王会“如约即止,不敢复东”恰恰相反,项羽方才意识到自己上当了。汉元年八月(公元前206年),当听说汉王遣韩信东归略韩地时,项羽马上采取对策,“乃令故项籍游吴时吴令郑昌为韩王,以距汉”[1](P2631)。汉二年十月(公元前205年),韩信攻下韩国十几座城池,韩王郑昌降。十一月,汉王立韩太尉信为韩王。
2.下邑献计,战略合围。留给项羽两封信后,张良自韩间行归汉,被刘邦封为成信侯,真正地成为了刘邦的人。项羽诛杀了韩王成,摧毁了张良复兴故国的政治理想,向项羽寻“杀主灭国”之仇,成为张良重归刘邦的重要目的,因此,归来后的张良跟随汉王“从东击楚”[1](P2039)。
汉二年春(公元前205年),“汉王部五诸侯兵,凡五十六万人,东伐楚”[1](P321)(《史记.项羽本纪》),并趁着项羽与齐军交战的时间,和项羽打了一个时间差,成功拿下项羽的都城彭城。项羽听到彭城被攻占的消息,马上率三万精兵返回彭城,“项王乃西从萧,晨击汉军而东,至彭城,日中,大破汉军。”[1](P322),项羽将兵三万破汉兵五十六万,汉王一路狼狈逃窜至下邑。
面对滑铁卢式的溃败,汉王下马踞鞍而问曰:吾欲捐关以东等弃之,谁可与共功者?”良进曰:“九江王黥布,楚枭将,与项王有郄;彭越与齐王田荣反梁地:此两人可急使。而汉王之将独韩信可属大事,当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则楚可破也。”[1](P2039),在当时复杂的战争局势下,张良纵观全局,向汉王推荐了黥布、彭越和韩信三员大将。张良的计策,让在楚汉之争中处在劣势的汉王由弱变强,对项羽形成了战略合围。
韩兆琦在《史记讲座》一书中对三股军事力量在楚汉战争中的作用进行了详细分析:黥布军事力量位于楚国南部,他原是项羽手下一员猛将,被项羽分封在九江,如果能利用项羽和黥布的矛盾拉拢黥布,既能削弱了项羽的实力,同时又能将黥布发展为自己的盟军,在南面牵制项羽;彭越的军事力量位于河南和山东交界处,位于楚国的北部,并且首先举起反项羽的大旗,联合彭越,在楚国北部形成牵制项羽的军事力量;韩信被刘邦留在后方,军事才能卓越,重新重用韩信对刘邦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张良的这一套思想指导了刘邦由弱变强,为消灭项羽铺平的道路。刘邦采纳了张良的建议,“乃遣随何说九江王布,而使人连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韩信能不能特将北击之,因举燕、代、齐、赵”,事实证明张良下邑推荐的三个关键性人物是正确的,“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5](P2028)。张良下邑献计策向项羽复仇的第二步,从战略上合围项羽。
3.垓下之围,四面楚歌。张良下邑献出的计策,在整个楚汉战争中,对汉王起了战略指导作用,直接奠定了刘邦在与项羽斗争中的胜利地位。虽然,从整个楚汉战争来看,刘邦很多数处于劣势地位,一路被项羽追杀。如汉二年(公元前205年)四月,汉王彭城败北,十几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只带着数十骑逃出项羽的包围,然而,太公、吕后又被项羽抓为人质;随后,汉王退守荥阳,结果粮草匮乏,被项羽围困,刘邦带着数十骑逃出包围。然而,在张良的帮助下,汉王总能转危为安,听从张良的计策,给项羽致命一击。刘邦和项羽的激烈争斗,是张良向项羽复仇的最好的机会,张良向汉王所献之计,统统将矛头指向项羽。
首先,为了避免汉王力量被分散,张良“借箸消印,阻封六国”,同时,为了避免汉王内部分化,张良又劝汉王立信为齐王,并征信的军队击楚,这两项举措,从内部上保证了向项羽复仇的可能性;其次,在楚汉相持未决,刘邦被项羽射伤卧病时,张良强请汉王起行劳军,以安士卒,从而稳固了军心,稳定了复仇之路;鸿沟之约,刘邦和项羽欲划鸿沟而治,项王遵守约定,引兵而东,汉王也遵守约定,准备西归。刘邦和项羽的妥协,让张良复仇之路出现危机,此时,如果汉王西归,张良苦心经营的复仇之路将付之一炬。于是,张良和陈平劝汉王不要西归,一鼓作气灭掉楚国“汉有天下太半,而诸侯皆附之。楚兵罢食尽,此天亡楚之时也,不如因其机而遂取之。今释弗击,此所谓‘养虎自遗患’也。”[1](P331),汉王听之,张良的复仇之路得以继续。
汉五年十月(公元前202年),“汉王乃追项王至阳夏南”[1](P331),结果因为韩信和彭越的违约,楚国的军队打败了前来追剿的汉军。韩信和彭越不从约,张良的复仇之路就会受阻。因此,张良为汉王指明了出路:“君王能与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接着又告诉汉王详细的划分方法:“君王能自陈以东傅海,尽与韩信;睢阳以北至穀城,以与彭越:使各自为战,则楚易败也。”[1](P331-332),汉王听从了张良建议,韩信和彭越热情高涨,皆率军前来。
汉元年十二月(公元前202年),围羽被围垓下,陷入四面楚歌境地,最终西楚霸王自刎乌江。随着项羽自刎乌江,张良的第二次复仇宣告结束。
三、功成不居,隐退避世,从赤松子游
张良以帝王师的身份,凭借《太公兵法》的谋略最终成功地向秦报了灭国之仇、向楚报了灭主之仇。二次复仇的成功,在策略上,张良更多地依靠了“黄老哲学”的思想。面对复仇,信奉“黄老哲学”的张良始终坚持着“忍”的思想,等待时机,黄老哲学“忍”的核心是虚静,阴柔,敛迹于无形。关于“黄老哲学”的特点,韩兆琦在《史记讲座》一书中写到:其主要特点是“讲究清静无为”“通过无为达到无不为”。它讲究“以柔克刚”,讲究“后发制人”,讲究“吃小亏占大便宜”等等。在楚汉战争中,虽然多时候,刘邦都处在下风,然而正是张良的谋略,让刘邦由弱变强,将项羽推向绝路,这正是“黄老哲学”在军事上的表现——柔弱处见锋芒。在张良的两次复仇中,最具转折性的事件分别是向秦复仇时的计取峣关和向楚复仇时的背鸿沟之约,这两次军事谋略充分显示了张良的“阴柔”,杨时(宋代)曾经这样评价过张良的两次行动:“老子之学最忍,他闲时似个虚无单弱的人,到紧要处发出来,使人支吾不住,如张子房也。子房如峣关之战与秦将连和了,忽乘其懈击之;鸿沟之约与项羽讲解了,忽回军杀之,这便是柔弱之发处,可畏!可畏!”
无论从一开始向秦报灭国之仇,还是后来向项羽报灭主之仇,复仇已经成为张良政治理想幻灭后,还继续存在的重要原因,复仇是支撑张良在现实世界斗争的重要精神支柱。因此,随着复仇之路的结束,张良对现实生活的欲望也随之消逝。这种欲望消逝的表现,便是不慕名利,从赤松子游。汉六年(公元前201年),刘邦封功臣称赞张良:“运筹策帷幄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功也。”[5](P2031),而张良推辞到:“始臣起下邳,与上会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计,幸而时中,臣愿封留足矣,不敢当三万户。”[5](P2031)。
面对刘邦的赏赐,张良表现的很寡淡,最终也只是自请了个留候。因为功名利禄本就不是张良追求的,张良的人生目标是复仇,帮助刘邦仅仅是复仇的一种手段。秦的灭亡和项羽的死,标志着张良对韩故国使命的完成,是对张良最大的封赏。因此,张良在《史记.留侯世家》中的自述:“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仇强秦,天下振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乃学辟谷,道引轻身。”[1](P2048)李赞(明代)评价到:“夫秦、项灭而英雄之恨已销,可以辟谷谢世矣。”
从张良的两次复仇,我们可以看出,张良在政治理想上受儒家“忠君”思想影响,在军事战略中受“黄老哲学”思想影响,在人生态度上又深受道家思想影响。两次复仇贯穿着张良的一生,无论是助刘降秦,还是扶刘灭项,都是张良复仇的手段,最终强秦被灭,项羽自刎。而张良“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的人生归宿,是大仇得报,人生理想幻灭,在现实中无路可走后的一种精神补充。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3.
[2]王国轩,王秀梅.孔子家语[M].北京:中华书局,2012.
[3]黄文娟,许海杰.孟子[M].北京:西苑出版社,2011.
[4]胡朴安鉴,吴拯寰译.清文观止[M].长沙:岳麓书社, 1991.
[5]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4.
[责任编辑 刘金荣]
The Analysis of Zhang Liang's Legendary Life Through the Two Revenges
Yan Zhennan
(School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Nanning,Guangxi530000)
Zhang Liang has experienced two important revenges,Assassination of First Emperor of Qin in Bo Lang Sha and Help Liu Bang win over Xiang Yu.Revengeswere throughout Zhang Liang’s life.Whether it is to help Liu Bang to capture The Qin empire,or to help Liu Bang destroy Xiang Yu,there are themeans of Liu Bang’s revenge.And Zhang may abandon the world and follow Chi Song Zi to the world of God,and is the end result of completed revenge and life ideal disillusionment,in reality world.Zhang Liang has no way to go,as a kind of spiritual compensation.Throughout Zhang Liang’s legendary life,hismiss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revenge.
Zhang Liang;revenge;legend
K207
A
2095-0438(2015)12-0075-05
2015-08-09
严振南(1988-),男,山东临沂人,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唐宋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