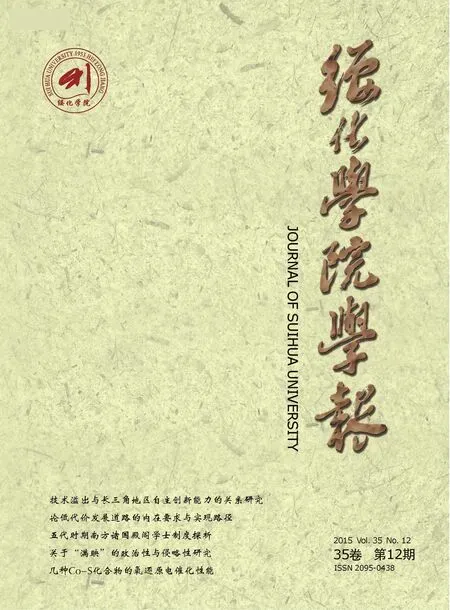异类的悲剧:孙悟空形象的心理和文化分析
贾国庆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辽宁大连 116081)
异类的悲剧:孙悟空形象的心理和文化分析
贾国庆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辽宁大连 116081)
《西游记》在幽默的揶揄、活泼的童趣和奇幻的情节的表象背后,是长歌当哭,演绎的是孙悟空个人挑战社会、精英无奈于庸才、个性毁灭于共性的异类悲剧,孙悟空形象是一个高度异化的悲剧形象。从异化悲剧的诞生,经历异化悲剧的过程,最终达到诛心之悲剧结果,整部《西游记》可以说是孙悟空异化的悲剧史。文章将以文化内涵、社会背景、民族心理等文化角度为切入点,分析孙悟空的异类形象,以及作为异端,其与群体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孙悟空作为异类的悲剧结局及其原因。
孙悟空;异类;悲剧;心理分析;文化分析
作为从石头中蹦出的石猴,从“花果山福地,水帘洞洞天”到后来的为王数百载,闯龙宫,探地府,再到最后的大闹天宫,无一不显示着孙悟空追求超越、自由,不甘平庸的品质。然而,一路西行,悟空身上的反抗精神逐渐被磨灭、改造,最终沦为自觉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斗战胜佛”。这是齐天大圣作为异类,逐渐夭折的悲剧。
一、孙悟空形象:从异类到同化
(一)天性阶段。孙悟空的出生,非常特殊,可以说是天上地下,古往今来,绝无仅有。这也注定了他生来就是“异类”,注定了在那个注重出身的时代,他必定是悲剧结局。由于悟空从小无父无母,也不是生活在凡间帝王严密的管辖之下,因此,他的天性得以充分发挥,在其生命的早期,按他自己的说法,这是一个“无性”的阶段。
石猴早期的心性,与它的出生大有联系。书中第一回写道:“那座山正当顶上,有一块仙石。其石有三丈六尺五寸高,有二丈四尺围圆。三丈六尺五寸高,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二丈四尺围圆,按政历二十四气,上有九窍八孔,按九宫四卦。四面更无树木遮阴,左右倒有灵芝相衬。盖自开辟以来,每受天真地秀,日月精华,感之既久,遂有灵通之意,内育仙胎。一日迸裂,产一石卵,似圆球样大。因见风,化作一个石猴……”[1](P2)这个石猴便是孙悟空,从此处我们也可以看出作者想要体现的对儒释道三家的态度,正如陆钦所说:“作者是表现出一种表面上以宣扬佛家思想为主,实际上三家哲理智慧同等称赏、三家并重、各彰其美的思想观念。”[2](P104)
称王之后,孙悟空便在“花果山福地,水帘洞洞天”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这是石猴天性、本性最真实的体现。石猴说自己“一生”无性显然是在说大话,他没有意识到自己以后将会拥有漫长却逐渐迷失本性,最终沦为悲剧的“一生”。“从总体上讲,石猴应该还算得上是一位贤明的君主,不过是‘朝游花果山,暮宿水帘洞’,与众猴‘合契同情’而已”。[3](P14)这般同志,在当时那个封建等级制度森严的时代不可不谓之为“异类”啊!
(二)生性、任性阶段。寻访神仙的过程并不顺利,前八九年并没有找到真仙。他终得拜菩提老祖从师,学得一身几乎天下无敌的功夫。在悟空被赶下山的时候,祖师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你这去,定生不良”,祖师的这句话,也就预示着孙悟空天性及无性阶段的结束。
通读《西游记》,从悟空跟着菩提老祖学艺期间所发生的种种事端中,我们不难看出,他作为异类,已经在众人中脱颖而出,显得如此的与众不同。最具代表性的应该是在学艺之初,孙悟空这不学,那不学,惹得师傅佯怒,师兄弟埋怨,从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看出,“悟空和其他的弟子大不相同。他们之间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悟空做事有着明确的目标”。[3](P19)他放弃舒适的王位,在海外漂泊数十年,目的就是要学一个长生不老之术,不再受阎王的约束和管辖。对与这个目的不一致的本领都不想学,恰恰反衬出他坚定不移的决心。孙悟空与身边的人有着本质的区别,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品质,注定了他作为异类而最终得到的悲剧结局。
孙悟空回到花果山,看到水帘洞,一种恍如隔世的温馨感觉浮上心头,伴随着的还有一种无以名状的满足感和陶醉感,但眼前看到的事实却是自己的猴群被混世魔王欺侮,甚至连水帘洞也差点被霸占。他找到妖怪,三下两下把他打死了。此次事件,应该可以说是悟空学成归来的第一次小试牛刀,它对悟空的心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他后来做出一连串“越矩”的事奠定了基础,也为他遭受打压、排挤,以致出现悲剧结局埋下了导火线。
混世魔王侵占花果山这件事,其长期的影响是,激起了悟空的斗心,加上悟空自负一番本事,斗心逐渐膨胀,他的心性也在不知不觉中改变。这也就加快悟空被视为“异类”的进度,以及沦为悲剧的速度。在这种斗心的促使下,出现的便是著名的“龙宫取宝”、棒打幽冥界;几次受天庭招安,又反出天庭。至此,孙悟空彻底被天界当做“异类”,为整个天庭乃至西天佛祖所不容。所以,最终,同为统治阶级的如来佛祖出手了,大手一挥,将五指化作金木水火土的“五行山”,轻轻把孙悟空压住了,这一压,就是五百年啊!到此,孙大圣生性、任性阶段亦宣告结束。
(三)收性阶段。五行山下,被压五百余年的孙悟空终于盼来了天庭的一位高级官员——观音菩萨。于是在悟空和观音之间进行了一次重要的对话,他对观音菩萨说:“我已知悔了,但愿大慈悲指条门路,情愿修行。”这次对话为孙悟空开启了新的人生方向,改变了他此后的人生命运,也喻示着悟空将要成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最终成为悲剧性的异类。从此,“他的行为模式与‘妖’的距离越来越远,与体制内神仙的做法越来越相似”。[4]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阶段,是悟空沦为悲剧异类的一个重要时期。
这次的谈话,菩萨和悟空可以说是双赢。一方找到了保护取经人的满意人士,另一方则成功脱去了五行山的束缚。接下来,悟空便开始了艰辛而又矛盾重重的西行取经之路。在拿到真经之前,师徒四人经过了八十一难;同时取经途中各方矛盾也是显现而出。首先,是孙悟空与唐僧的矛盾。悟空是五百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怎么甘心屈于一介凡夫俗子之下呢?于是,就经常出现不服从管理的情况。其次,是悟空和以菩萨为首的天庭的矛盾。在取经途中,他们不断遭受那些由于天庭的纵容而下界为祸的妖精的侵袭,悟空怎能不怨恨?最后,是悟空和自己的矛盾。一开始,悟空就是以一个异类形象的个体出现的,只是,在那样的环境中,异类注定是被排斥的,所以悟空为了生存,不得不改变自己。所以悟空在这种矛盾的心态中,便有了“二心”的争斗。
而且,在这个阶段,悟空最大的变化应该算是,了解了人情世故,并逐渐变得老于世故。颇能反映悟空变化的是,对于黑水河作恶的鼍龙的处理。他与敖顺的短短几句话,有打有拉,恩威并施,意思照顾得非常全面,处理也极为妥当,简直就是政治老手的处理方法。这一系列的变化,无不向我们透露出一个信息,那就是,悟空不再是异类了,他已经融入了那个群体之中,他作为异类的历史已经远去,而正在书写的是他逐渐沦为悲剧英雄的史诗。
(四)“从心所欲不逾矩”阶段。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师徒四人到达了西天,悟空也被封为“斗战胜佛”,这标志着他更高层次的无性阶段,我们亦可称之为“从心所欲不逾矩”阶段,同时,也标志着悟空心性变化过程的最终结束,及他悲剧结局的彻底定型。
对于“从心所欲不逾矩”,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怎么对怎么干,怎么干怎么对,心里想什么就做什么,都不违反规矩;虽然有规矩,并不妨碍思想和行为的自由,即身体有约束,心灵无约束”。[5]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后,行为不再需要意识去引导,而是顺其自然。成佛后的悟空,应该就是这种境界,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结合自己的欲望和理性思考之后再行下手。
要达到这一境界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必须对矩有深刻的认识。到达西天的孙悟空,对三界的的矩是了然于心了,完全能够在三教九流中混得如鱼得水,也逐渐成为天界的一支建设性力量。至此,孙悟空曾经具有的反抗精神完全消失了,这或许是三界都乐于见到的结局,但是,从悟空个人的角度出发,这是个悲剧,是一个作为异类的悲剧。
二、孙悟空的异类悲剧意蕴
(一)脱离于群体之外的异类。这一异类形象,主要体现在孙悟空自我意识的觉醒,接着对权威的挑战,高扬个性,追求自由平等,打破思想的桎梏,蔑视一切“礼”与等级。“其中最突出的是理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这种自我意识的觉醒首先体现在对生命极限和精神自由的追求上”。[6]《西游记》的第一回中,孙悟空漂洋过海访神仙至西牛贺州,于斜月三星洞的菩提祖师习得“与天同寿的真功果,不死长生的大法门”。此后在第二回中,孙悟空大闹阴司,强销生死簿,将自己和猴子猴孙的名字尽数划去。这些看似叛逆、狂放不羁的行为,实际上蕴含着孙悟空对生命本身的关注,企图通过延续生命的长度来实现个体生命的价值。然而,这一切的一切都使悟空成为众人眼中的怪物,他那种似天生的叛逆与反抗性格,使他仍和整个群体格格不入,成了特立独行的异类。
(二)遭受群体压抑的异类。或许是悟空反抗的方式不对,太过张扬,又或许是他的行为真地在撼动着整个统治阶级的根基,总之,种种行为给他带来的后果只有两个——招安和围剿。
第一次招安发生在悟空学成归来,悟空上天以后,出任弼马温。其实,我们都能看出来,虽说天庭是让悟空做了官,可是,实际上是以貌取人,并没有把他当回事儿。因为悟空的不懂事,在出任弼马温期间驳了玉帝及整个天庭的面子,玉帝大怒,派出托塔李天王和三太子哪吒率天兵天将擒拿悟空。只是,此时的悟空神功盖世,将众天神打得落花流水,玉帝的如意算盘落空了。
既然硬的不行,那还是来软的吧!天庭进行第二次招安。采取的措施是“不与他事管,不与他俸禄,且养在天壤之间,收他的邪心,使不生狂妄”。只是悟空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在得知没有被邀请出席蟠桃会后,恼羞成怒,大闹天宫。最终,老大终于看不过去,出手了,大手一挥,将大圣压在其下,一压就是五百年。这一举动也将之前暗地里的压制与打击变为了赤裸裸的压抑与排斥,也许,在三界看来,这本就是作为异类注定了的归宿。
(三)夭折的异类。之所以谓之“夭折”,是因为悟空是以一个反抗者的形象出现的,但是,因为多重原因,他的反抗与叛逆都遭到打击、镇压直至扼杀,最后失败了,以至于不得不委屈就全,皈依佛门,并且在西行的途中,逐渐被消磨了本性,成为芸芸众生中的一份子。
1.与神权系统斗争的失败。在被压五行山之前,孙悟空斗争的对象是天庭的神权系统,以及在此系统下的一些不合理的现象。主要的斗争行为包括龙宫索宝、冥界除名、弃官出走、自立为圣和大闹天宫。其中,大闹天宫是孙悟空挑战神权的巅峰。
2.皈依佛门,保唐僧西行。被压在五行山下,悟空过了五百年凄惨的生活,也在这漫长的日子里,不断反省自己的行为,至于他都反思了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后来观音菩萨来到之后要将悟空解救利用,悟空感激之下许之情愿,愿意取经修行。其实,对于孙悟空“情愿修行”背后的想法,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不过法力无边,观音也不怕他反出天去,至此,孙悟空与菩萨达成了协议,皈依我佛,开始了他的保唐僧西行之途,也迈出了沦为悲剧的第一步。
(四)悲剧的异类。悟空作为天地自然之子,出生伊始就沉浸于自由的生活中,他学道于菩提祖师,后来,还是被如来的无边佛法降服。他作为有别于整个社会的异类,终归是失败了,这个失败本身就体现出悲剧性。
1.个人挑战社会的悲剧。在《西游记》整个故事中,除了菩提祖师和花果山的猴子们,几乎每一个有名有号的角色都曾与孙悟空有过节,由于不懈追求自由、平等、友爱、真诚等等,“在不知不觉中,孙悟空被置身于整个社会的对立面,担负了只身挑战全社会的悲剧使命”。[7]这种个人挑战社会的对比关系,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最后的结局。
2.精英无奈于庸才的悲剧。孙悟空的本领是从来都不被怀疑的,就连玉帝都承认他是“天地精华所生”。然而,在整个故事中,孙悟空充满了精英无奈于庸才的悲哀。
3.个性毁灭于共性的悲剧。在《西游记》结尾,以孙悟空接受佛祖尊封“斗战胜佛”的结局,结束了战斗历程。至此,孙悟空早已不是曾经的那个喜欢自由、挑战权威的“心猿”。他接受了给他造成千辛万苦的佛祖的封赏,成为了班列释册的佛尊,如此这般,紧箍咒是没有了,异类的个性也消失全无了。“具有反抗与叛逆特征的个性精神,不仅没有能够对腐朽、陈旧的共性造成冲击和改进,反而被共性同化了”,[7]这实在是孙悟空作为异类的悲剧性的最高潮!
三、个人悲剧与时代悲剧——孙悟空形象的文化分析
(一)个人的悲剧。毋庸置疑,孙悟空地是一个英雄,同样,无可置疑,孙悟空是一个悲剧英雄,确切地说,他应该算是一个平民的悲剧英雄。说他是平民的英雄,是因为,我们可以将他的智勇理解为人民智勇的缩影。他的出身并不高贵,也决定了他的思想的平民化。那么,他的一切行为必定带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他反抗的出发点仅仅是个人,而不是从整个阶级的角度出发。比如,他竖起“齐天大圣”的旗号而被天庭讨伐的时候,说道“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由此可以看出,孙悟空的说法还是存在着根本的局限性。其次,他反抗的手段和方式存在缺陷。他的斗争完全是个人的,并没有与同样受着压迫的人联合起来,如此一来,不管怎样努力,他的力量还是很薄弱。然而,他的命运又带有浓重的悲剧色彩,因为不管他怎样反抗,最终的命运终究是逃不脱注定的归宿——归于神,听命于神。从个人的角度来讲,悟空反抗失败,沦为悲剧的原因,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悟空作为个体,面对的是整个社会,或者说是三界,力量对比悬殊过大。下至妖魔,上至西天佛祖,都卯足了劲儿要将他除之而后快,这就决定了他的追求是孤独的。其次,悟空的两次被招安为他后来被孤立埋下了祸端。两次招安虽然使他摸了天庭的部分虚实,但由于被招安,他与玉帝之间就有了事实上的君臣名分,那么他的造反就是名不正言不顺的了,必然得不到众神仙的理解、同情与支持,从战略上陷于孤立。最后,悟空的反叛是盲目的,他打出的是“强者为尊”的旗号,但是他对天庭真正的实力并没有深刻的认识。在车迟国三清观中,悟空竟然不知道“三清”是什么人,还将他们错认为“菩萨”,连八戒都鄙视他。
(二)时代的悲剧。孙悟空的反叛斗争过程体现着他对自由、平等的不懈追求,这是他的正常追求。但是,他的追求与皇权、礼法的维护者发生冲突。“孙悟空毫无退路地把自己放在了同一种根深蒂固的制度相对立的地位,而这种制度的核心是任何一位最高统治者都不容许触动其毫毛的森严的等级制度。一切封建统治的规章制度秩序都是为维护等级制的永远稳固而设置的”。[8]他们需要的是“顺民”,而不是“顽逆”,所以,当孙悟空用个人力量来挑战整个权威时,一切社会统治力量便共同作战于他,孙悟空失败的悲剧也就注定了。
可以说,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无可避免地留有作者所处时代的思想文化烙印。“这种希望凭借个人的能力去自由地实现自我价值的强烈愿望,正是明代个性思潮涌动、人生价值观念转向的生动反映。”[9](P122)但是,在那个推崇儒学,以程朱理学为社会标本和文化信条的时代,强调的是“存天理”、“灭人欲”。所以,以悟空为缩影的明代士人追求自我的行为,毫无疑问地被看做是异端,自然被无情地打击和抹杀。
无可否认,吴承恩在创作《西游记》时,必然受当时盛行的王学左派和李贽的“童心”说的张扬个性思想的影响。这种观点包含有反对封建等级制度的平民思想,它崇尚人性,反对封建禁欲主义的说教;强调身为家国天下的根本,以“安身立本”作为封建伦理道德的出发点。因此,在孙悟空身上,我们可以轻易发现受这种思想影响所留下的痕迹。而这最终导致的也就是悟空这一悲剧形象的产生,这是时代的造就。
讨论到此我们会形成以下判断:就作者吴承恩的思想而言,儒、释、道三教思想兼具,早、中年以儒为主,晚年偏向于佛、道。在作品中,作者对三教有吸收有摒弃,对道教贬斥较多,然而,作者的思想终究是存在着局限,无法超越所处的社会历史的语境范围。在整个故事中,孙悟空可以叛逆、狂傲,但最终只是在维护社会基本秩序的前提下的反抗。所以,在作品中,我们看到了美猴王向孙行者的转变,看到了如来的约束,同时也感受到了紧箍咒的制约。归根到底,还是个性自由与社会规范相矛盾的反应。这也是作者思想的矛盾,他所接受的正统思想为儒家思想,说到底还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与此相对应,《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无论前期是如何的张扬放纵,都必须回归到规范之中,所以作品中的孙悟空毫无选择,不得不接受了各种制约,走上了一条“正路”,这是统治阶级需要的,这便是作为时代所产生的悲剧。
[1]吴承恩.西游记[M].长沙:岳麓出版社,1987.
[2]陆钦.名家解读《西游记》[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
[3]周方银.解码《西游记》[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4]赵心宪,聂树平.孙悟空形象的悲剧性本质问题[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2(6).
[5]李建栋,王丽珍.从“天马行空”到“从心所欲不逾矩”——孙悟空名号的文化意蕴[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7(3).
[6]周先慎.孙悟空形象的时代精神和文化意蕴[J].东南大学学报,2006(5).
[7]郭明友.论孙悟空形象悲剧意蕴的广度与深度[J].名作欣赏,2010(17).
[8]董国炎,刘明坤.孙悟空新解读[J].明清小说研究,2008 (1).
[9]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四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 王占峰]
I207.4
A
2095-0438(2015)12-0031-04
2015-07-02
贾国庆(1988-),男,山东菏泽人,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电影《邱少云》观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