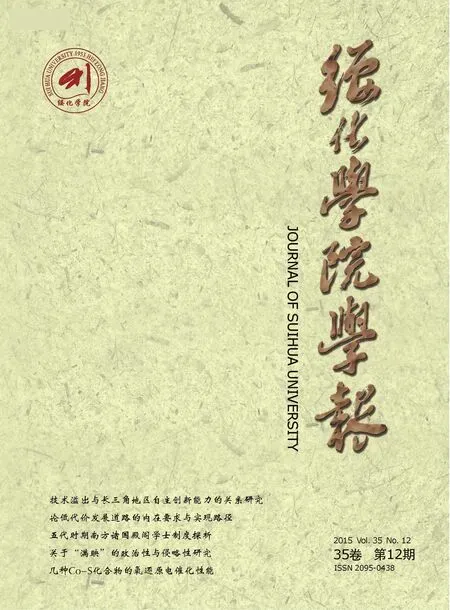辛格的《冤家,一个爱情故事》谫谈
彭威
(兰州财经大学外语学院 甘肃兰州 730020)
辛格的《冤家,一个爱情故事》谫谈
彭威
(兰州财经大学外语学院 甘肃兰州 730020)
美国犹太作家辛格的长篇小说《冤家,一个爱情故事》采用现实主义手法,深刻揭露了纳粹大屠杀对犹太幸存者造成的肉体与精神创伤、伦理危机以及身份认同困惑。小说既表达了作者对犹太人遭受深重苦难的同情和对纳粹分子所犯滔天罪行的严厉谴责,也折射出作者自身惨痛的人生经历。
辛格;《冤家,一个爱情故事》;纳粹大屠杀
艾·巴·辛格(Isaac Bashevis Singer,1904-1991)是美国著名犹太作家,于197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小说受到世界各地读者的广泛喜爱。作为一名犹太裔作家,辛格的小说充满了浓厚的犹太性,“表现了犹太民族的历史命运和现实际遇,从而在美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1](P394)《冤家,一个爱情故事》详细描述了纳粹大屠杀后流散到美国的犹太幸存者生活状况的长篇小说,也是二战后较早对犹太幸存者给予深切关注的小说,具有深远的文学和历史意义。本文结合小说所反映的特殊历史语境以及辛格本人的人生经历,从肉体与精神创伤、伦理危机以及身份认同困惑三个层面阐释作者对大屠杀犹太幸存者这一特殊群体的思考,试图为我们深刻理解小说的独特内涵提供新的视角。
一、肉体与精神创伤
犹太人自从两千多年前被赶出“流着奶与蜜”的应许之地后就流散于世界各地,成为无根的漂泊者,屡屡遭到歧视、驱逐、杀戮乃至几近种族灭绝。二战期间德国纳粹分子对犹太人种族灭绝式的大屠杀是犹太人遭受的最为严重、惨痛的苦难。“600万活生生的人类仅仅因为他们是犹太人而被灭绝。欧洲犹太人几乎停止存在,全世界三分之一的犹太人被杀害。”[2](P37)辛格的长篇小说《冤家,一个爱情故事》正是基于这一历史背景,围绕着从欧洲逃亡到美国的犹太幸存者的生存状况而展开。小说以赫尔曼为主人公,讲述了他作为一个大屠杀幸存者在美国的爱情、婚姻、宗教等方面生活故事。小说中的犹太幸存者大多是带着满身的伤痛逃亡到美国的,这些伤痛伴随终生且时时折磨着他们,让他们痛苦万分。大屠杀期间,赫尔曼为了逃避纳粹的搜捕躲藏在一个只能容身的草料棚中达三年之久,他家的佣人雅德维珈每天“给他端来食物和水,把他的粪便端走”[3](P238)。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藏了三年之久的赫尔曼出来后患上了严重风湿病和坐骨神经痛。“吃东西以后,他就胃痛。吹到一点风他的鼻子就塞住了。他常常喉咙痛,嗓音变得越来越嘶哑。耳朵里有什么东西使他感到痛——化脓了,还是长了东西?”[3](P273)赫尔曼的身体已经垮掉了,带着浑身的病痛,他只能苟延残喘地活着。玛莎也是伤痕累累地逃到美国,她曾经在纳粹集中营呆过,侥幸逃过大屠杀,但身上没几处完好的皮肉。睡觉前,“她总是喜欢打开手电,让赫尔曼看那些死人在她胳膊、胸脯和大腿上留下的伤痕。”[3](P278)玛莎的母亲厄普身体则更加糟糕,“他患有心脏病、肝病、肾脏病和肺病。每隔几个月,她就要昏过去一次,每次医生都说她没救了,可每次她又逐渐复原了。”[3](P276)而赫尔曼原来的妻子塔玛拉身体上也留下了一大片伤疤。辛格并没有通过人物之口详细描述纳粹分子如何折磨犹太人,然而他们永久的肉体创伤中足以看出纳粹超乎人类想象的残忍,这是纳粹所犯下滔天罪行的明证。
纳粹留给犹太幸存者的肉体创伤和病痛或许可以通过医药来救治和缓解,而唯独精神上的大屠杀创伤后遗症是任何高明的心理治疗师也难以抚慰的。辛格对犹太幸存者肉体伤痛的勾勒只有寥寥几笔,然而对他们所遭受精神创伤的刻画在小说中则俯拾即是,细致入微。小说中的每一个幸存者几乎都有精神问题,如果从医学的角度来进行诊断,他们都可视为精神病患者,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赫尔曼就是一个典型的饱受精神折磨的病人。草料棚里三年的非人生活使他的精神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来到美国后他经常出现幻觉,认为自己仍然生活在被纳粹统治的波兰。他总是感觉纳粹分子在跟踪他,担心自己的住处被他们发现,时时幻想着纳粹分子藏在地铁站、门背后、大街拐角处、商场里等,似乎无处不在。赫尔曼每晚都在做与纳粹分子厮杀的噩梦,经常算计着哪些地方适合藏身,要多少食物才能维持生存。这种精神折磨让他整天头脑昏昏沉沉,恍恍惚惚,仿佛生活在幻境之中。兰伯特拉比是赫尔曼的雇主,赫尔曼的工作实际上就是为他代写各种文章。这个外表豪爽的犹太拉比看似已经摆脱了纳粹噩梦,但实际上他同样遭受着精神上的折磨。当兰伯特看到赫尔曼整天因为担心纳粹分子找上门而变得神经兮兮时,便建议他去看看精神医生,然而他自己却也坦承:“就是我,有一段时间也找过精神分析医生。”[3](P257)而兰伯特还透露他的妻子也整天精神恍惚,有时开着煤气就外出买东西,有时突然变得歇斯底里开始骂人等等。
小说中人物的精神创伤不仅表现为一种大屠杀后恐惧症所有引起的精神疾病,还表现为一种幸存下来的愧疚感和自责感。小说中的犹太幸存者从未表现出一种逃离死亡的庆幸感,相反他们内心觉得当家人和同胞在大屠杀中惨死而自己却幸存下来是一种无法饶恕的罪过。赫尔曼一想到两个孩子被纳粹杀死而自己却在美国活了下来就开始自责,他甚至打算这辈子再也不生孩子。玛莎的母亲希拉普认为亲人死去而自己活着是一种莫大的耻辱。在玛莎看来,“她犯下的最大的罪行就是:在这么许多无辜的男女惨遭杀害的时候,她居然一直活着。”[3](P276)死去的人已经结束了肉体和精神的折磨,而留给这些幸存者的是无尽的自责和愧疚感,让他们觉得自己的生命是由死去的家人和同胞换来的。也许只有“生不如死”这个词才能恰当地描述他们的真切感受。
可见,这些犹太幸存者是幸运的,然而又是极其可怜的。说他们幸运,因为相对于那些被驱赶进焚尸炉的犹太人,他们侥幸捡了一条命,但纳粹留给他们的肉体和精神创伤又时时刻刻在折磨着他们,勾起那段噩梦般的日子,让他们随时想起自己梦魇般的经历和被屠杀的亲人。他们在美国这个繁荣的国家过着一种行尸走肉般的生活。辛格通过刻画犹太幸存者的伤痛表达了对犹太人遭受人类历史上罕见磨难的血泪控诉。
二、伦理危机
伦理道德问题是犹太文化的核心之一,也是辛格小说的重要主题。犹太文化以犹太教文化为基础,而犹太教本质上又是一种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宗教。犹太教教义中充满了各种道德训诫,摩西十诫是最为重要的道德戒律。大屠杀颠覆了犹太人心中各种道德戒律,小说中的犹太幸存者除了要忍受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外,还往往陷入前所未有的伦理危机中而无法自拔。
从犹太教伦理的角度来看,信仰上帝应该是每一个犹太人首先要遵守的伦理准则。上帝与摩西在西奈山订立契约,如果犹太人信仰全知全能的上帝,上帝则会拯救犹太人于水火之中。千百年来,犹太人抱着这一信念虔诚地信仰上帝,遵守与上帝的契约。然而,幸存者在经历了大屠杀的灾难后却出现了严重的信仰危机。他们开始怀疑上帝,诘问上帝,甚至谩骂和诋毁上帝。在亲人和同胞惨遭屠杀,自己受尽磨难后,原本虔诚的赫尔曼开始怀疑这个仁慈的上帝为何当时袖手旁观。他经常在内心诘问:上帝到底是否存在?犹太人受难时他躲到哪里去了?犹太人为何要相信一个并不存在的上帝?赫尔曼原来的妻子塔玛拉则直言不讳地说:“在孩子们遇难以后,我不会相信上帝了。”[3](P359)确实,一个能在无辜的孩子们被杀死、活埋、焚化时而袖手旁观的上帝如何让人相信呢?玛莎对上帝的态度则更加直接,她明确表示自己“憎恨上帝”,甚至还讥讽上帝:“屠杀犹太人是合乎天理人情的。犹太人一定要被屠杀——这是上帝的希望。”[3](P269)塔玛拉的叔叔里布——一个原本无比虔诚的人也无法相信这样的上帝,他感慨“怎么可能要求那些经历过毁灭的人去信仰上帝和他的仁慈呢?”[3](P462)由此可见,大屠杀已经彻底动摇了上帝在犹太人心中的地位,让犹太人渐渐失去精神支柱和道德理念,不仅对犹太人身体和精神造成戕害,更是对犹太宗教伦理准则的一种残害。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整体上采用第三人称全知全能的叙述方式,然而在谈及上帝在犹太人惨遭屠杀而为何袖手旁观这问题时,作者本人则直接插入叙述,将自己对上帝的看法毫不掩饰地表达出来:“各种宗教都是谎言。哲学从一开始就彻底破产。有关进步的种种不兑现的诺言不过是吐在世世代代殉道者脸上的唾沫……犹太人永远要在奥斯维辛被烧死。”[3](P262)“在慕尼黑的小酒馆里,那些曾玩弄过儿童的颅骨的凶手们从高大的酒杯里喝啤酒,在教堂里唱赞美诗。真理?不在这片丛林中,不再坐在火热的熔岩的地球上。上帝?谁的上帝?犹太人的?还是法老的?”[3](P466)这种以作者口吻直接对上帝发出诘问的例子还有很多,从中可以看出辛格是有意通过转换叙事者口吻的手法来直接表达对上帝怀疑和不满的情绪。由此可见,小说中虚拟人物对上帝的信仰危机实际上也是积郁在辛格本人的内心,在这点上作者与小说人物心理有共通之处。
辛格本人对上帝的诘问与其人生经历有很大关联。辛格于1935年辗转来到美国,目的就是为了躲避日后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辛格的嗅觉是敏锐的,在一份访谈录中辛格谈到:“1935年希特勒已经执掌了权政……我预见到了那场大屠杀。”[4](P330)然而,不幸的是,他的母亲和弟弟却在这场屠杀中因缺少食物供给,被活活饿死。辛格本人也正是为了逃命才漂洋过海到美国避难。上帝眼睁睁看着他的亲人遭难而袖手旁观,这是辛格心中永远的伤痛,也是辛格在几乎所有小说中都对上帝提出质疑的重要原因。总之,大屠杀让无数原本虔诚的犹太人开始怀疑上帝,动摇了本坚定的宗教信仰伦理根基,在信仰层面对犹太人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大屠杀不仅直接导致了犹太人的宗教信仰伦理危机,还间接地造成了犹太人在很多其他层面过着一种违反伦理规范的生活。大屠杀对犹太幸存者婚恋伦理观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各种不伦之恋、未婚生育、重婚、多个情人等现象普遍地发生在他们身上。赫尔曼在波兰时原本有着幸福美满的婚姻,然而,逃难到美国后为了报答玛德维珈救命之恩,他违背犹太教婚姻伦理,先是与非犹太裔的雅德维珈举行了世俗的婚礼结婚,却又背地里与玛莎——一个有夫之妇偷情,后来意外发现原来波兰的妻子塔玛拉还活着,又跟塔玛拉纠缠不清。在日常生活中,很多犹太人或迫于无奈或主动放弃心中的道德戒律。为了维持生存,赫尔曼成了一个捉刀者,给兰伯特代笔写各种布道稿、文章、书籍,这是一种赤裸裸的欺骗行为。兰伯特拉比本人一面在犹太人面前布道,宣扬上帝的福祉,一面却又通过坑蒙拐骗来聚敛钱财。玛莎为了保住性命和得到一点物质上的好处,也曾经跟不同的男人保持性关系。很多犹太人已经开始不遵守习俗蓄留胡子和鬓角,不过犹太人的节日,不遵守安息日,与异族通婚,等等。这些都不符合犹太伦理规范,而这样的犹太人在小说中比比皆是,可见这种现象的普遍和严重。
正如辛格在序言中写到的,伦理的缺失一方面是缘于小说人物的个性和命运,但其背后的原因基本上都可以归咎于大屠杀。如果没有这场屠杀,这些犹太人会像往常一样在各自的生活中扮演应有的角色,而非被驱赶到一个陌生的国家,发生如此多不幸的事情。犹太人建立起来的道德秩序都因为大屠杀的到来而受到严重的冲击。在这一过程中这些犹太人并非乐意这样做,而是身不由己,他们内心极度痛苦。伦理秩序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一角度来看,大屠杀对犹太伦理规范造成额冲击实际上也是对犹太文化造成的一种严重的文化创伤。
三、身份认同困惑
身份认同的基本涵义指:“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这个词总爱追问:我(现代人)是谁?从何而来、到何处去?”[5](P37)犹太人在几千年的流散历程中尽管也常常对“我是谁?”“我属于哪里?”等身份问题产生困惑,但绝大多数犹太人都拥有一种共同的民族认同感,即我是犹太人。这是因为二战前的犹太人主要分布在欧洲大陆,他们往往形成自己的犹太社区——“格托”(ghetto)。“格托”中的犹太人较为完好地保存着犹太文化,如信仰、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形成了一种相对封闭的文化圈,因而生活其中的犹太人也形成了比较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然而,大屠杀彻底改变了这一格局,逃难到美国的犹太幸存者面临着严重的民族认同危机。赫尔曼经常问自己“我是谁?”他身边的很多犹太人也开始对自己是否是真正的犹太人而感到困惑和迷茫。这些人已经开始抛弃犹太人的传统,过着一种现代美国的生活,然而他们又不被美国人所认可,处于一种边缘地带。他们偏离了犹太文化和习俗,但是又不敢彻底与之决裂,他们开始怀疑自己犹太人的身份,却又无法承认自己属于任何其他民族。这种游离在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的尴尬给让他们内心备受煎熬,痛苦万分。
从原因上看,民族身份认同危机和困惑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初入美国的犹太人没有形成能产生文化凝聚力和民族认同感的犹太社区。小说中的赫尔曼租住在一栋整天夹杂着各种口音的大楼中,几乎不认识周围的邻居,也从不打交道。玛莎与母亲租住在一个狭小的房子里相依为命,塔玛拉与叔叔住在一起。这些犹太人都散落在美国的各个角落。散居的方式以及犹太人之间缺乏交流和沟通难以形成一种文化凝聚力和归属管以及认同感。此外,犹太人民族身份认同危机与美国文化的同化力量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于犹太人来说,美国文化有着一种难以抗拒的诱惑力。美国人倡导个性、民主、自由,在生活方式上崇尚简单、舒适的原则。受到现代美国文化的影响,犹太人开始逐渐抛弃犹太风俗习惯,对犹太节日、族内通婚习俗、饮食原则等也采取非严格的方式,在美国这个多元文化的国家一步步被同化。然而,同化又不是彻底的,他们毕竟还在很多方面保留着犹太文化根基,但又无法得到美国主流社会的认可,同时也经常招致一些仍然坚守犹太传统的同胞的鄙视,因此这些犹太人对自己的身份感到非常困惑。
小说中犹太人的身份认同困惑还体现在国家身份认同层面上。逃到美国的犹太人不仅面临着民族身份丧失的危机和痛苦,还面临着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对他们认同的问题。小说中的幸存者大多通过逃难等方式来到美国的,根本不被视作美国人看待。他们大多面临着语言、就业、医疗等多方面的困难,通常只能从事一些收入低的累活、脏活或者干脆找不到任何工作。赫尔曼尽管拥有大学文凭且学识渊博,但根本无法找到能发挥其才华的工作,因而他只能给兰伯特拉比做枪手。玛莎在一个餐厅当出纳,赚取微博的工资以解决自己和母亲的日常开支。塔玛拉没有工作,只能四处游荡,靠他叔叔开的那间小书店勉强维持生活。他们都没有取得美国国籍,只是以难民的身份寄居在这个国家,因为并不被视为美国人。然而,他们又失去了自己的祖国,或者遭到祖国的抛弃,或者在自己的祖国被屠杀。他们既不是波兰人、法国人、俄国人,也不是美国人,他们成了没有国籍的漂泊者。这种国家身份认同的危机折磨着这些身处异乡的犹太人。他既不是原来的国家身份,也不被新世界的美国所认可,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也无法真正融入到美国社会,因而痛苦万分。这种身份认同危机和困惑固然有人物个人的原因,然而如果没有大屠杀,这种情况也不会出现。
事实上,辛格本人对于这种身份认同的困惑深有感触。根据辛格的传记,他历经千辛万苦来到美国后,在这个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的地方感觉被悬置起来。他经济窘迫,认识的人极少,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离开犹太文化土壤,又不被美国所接受和认可,甚至在长达四五年的时间里写不出任何东西,因而沮丧万分,痛苦至极。可以看出,发生在小说人物身上的身份认同困惑和痛苦也是早年辛格本人内心的真实写照。
结语
从标题上看,小说《冤家,一个爱情故事》是有关爱情的,但实际上隐藏在小说错综复杂的爱情故事背后的是辛格对纳粹分子大屠杀罪行的控诉和痛斥。小说中犹太幸存者所遭遇的种种创伤、不幸、磨难、痛苦本质上都是纳粹大屠杀所造成的。事实上,铭记和反思犹太大屠杀不仅对于犹太人具有重要意义,对其他民族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因为“纳粹大屠杀,是人类共有的历史财产,人类有责任和义务反思,并开展相应的大屠杀教育。”[6](P92)
[1]傅景川.二十世纪美国小说史[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6.
[2]黄陵渝.犹太教[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3]辛格著.杨怡译.冤家,一个爱情故事[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4]艾·巴·辛格.亚伯拉编.艾·辛格的魔盒——艾·辛格短篇小说精编[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5]陶家俊.身份认同导论[J].外国文学,2004(2).
[6]相征.关于以色列纳粹大屠杀教育的研究[A].潘光等.纳粹大屠杀的政治和文化影响[C].北京:时事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 王占峰]
I106
A
2095-0438(2015)12-0060-04
2015-06-15
彭威(1982-),男,湖北赤壁人,兰州财经大学外语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比较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