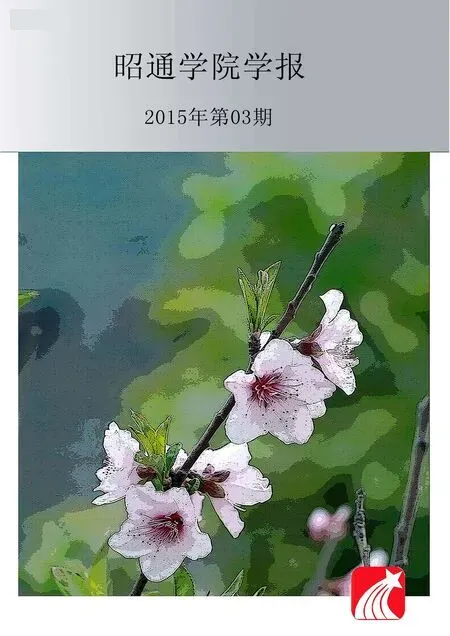徘徊于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之间——论毛姆《面纱》中的中国形象
周琳琳
(三亚学院 人文与传播学院, 海南 三亚 572022)
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1874-1965)是20世纪英国颇具声誉的作家。他一生爱好旅行,作品富有异国情调。毛姆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1919年10月,他曾游历中国四个月,并在回国后创作了几部以中国为背景的作品,描绘了他的中国印象和对中国文化的感悟,长篇小说《面纱》即是其中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形象学研究在国内的兴起,《面纱》中的中国形象也备受关注,引起了不少研究者的兴趣。毛姆在书中塑造的“中国形象”徘徊于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之间,一方面是丑陋的、低劣的;另一方面,又是神秘的、美好的,充满了理想化色彩。
一、意识形态表述下的中国
这里的“意识形态”,并不具有政治、论战意义,而只具有描述意义,“它只是一种被理想化了的诠释,通过它,群体再现了自我存在,并由此强化了自我身份”[1]。采用形象学的文本内部研究方法来分析,小说在词汇、等级关系和故事情节方面都流露出浓厚的意识形态。
(一)词汇
词汇是构成他者形象的最基本单位。“在某一特定时期,某种特定文化中,或多或少储存了一批传 播 ‘他 者’形 象 的 词 汇。”[2](P.128)。 在 《面 纱》中,描绘中国地理环境和中国人的词汇构成了一个个词汇场,以共同生成的概念的、情感的词库构建了一个中国的形象。
小说中涉及到中国的空间主要是香港和湄潭府。凯蒂最初听瓦尔特提起香港时,觉得那儿的生活令人向往。然而婚后来到香港后,却很快就不喜欢它了。除了社交活动的稀少外,还因为香港的脏和热。“肮脏”和“炎热”是描述香港时最常出现的两个词汇。小说中多次提到过香港很热,中午街上一个人都没有,人们懒得出门。凯蒂在闲谈中也曾表示,准备像往年一样避开香港的酷暑。在婚外情败露后,凯蒂必须跟随瓦尔特赶赴湄潭府,那里显然更加肮脏不堪,“垃圾堆积如山”,“从垃圾堆里散发出难闻的恶臭”。此外,湄潭府是瘟疫的发生地,那儿的人们跟苍蝇似地一个个死去。因此,“死亡”、“尸体”、“棺材”等词汇频频出现,凸显了这个中国小镇的荒蛮和恐怖。
除此以外,小说中有不少中国人的形象,如中国厨子、中国轿夫、中国孤儿等,但这些中国人的形象基本上都是沉默而令人生厌的。
凯蒂很讨厌和唐生经常幽会的那家古玩店的那个老头子,他总是“堆了一脸讨好的笑”。
修道院里的女孩们“全长着中国人的褐色眼睛和黑色头发”,“面黄肌瘦”,“身同侏儒”,“鼻子都是扁扁的”,在凯蒂看来几乎没有正常人的模样,令人生厌。中国婴儿也毫无可爱之态,“她们全身通红,手脚不停地乱舞。一张张中国人样子的小脸儿古怪有趣,皱巴巴地扭出了苦相。凯蒂觉得她们不像人类,而是某种罕见的不知名的动物。”[3](P.113)
传递着中国理想的满洲公主,在凯蒂眼里更像是一个人偶。她脸颊上“抹着厚厚的红粉”,“眉毛明显拔过”,“嘴唇涂得血红”,“眼睛微微斜睨”。这些关于外貌的词汇,是西方常见的描述中国女人的套话。
显然,这些描述中国形象的词汇,传递的是一种浸透意识形态的、绝对的相异性。
(二)等级关系
对小说中描述中国的词汇进行分析后可见,在作者——注释者和他者——中国之间存在着等级制度。“这种等级制度从总体上看表现在我——叙述者——本土文化与他者-人物-被描述文化 的 两 组 关 系 的 对 立 上。”[4](P.79)具 体 来 看,可以从时空和人物体系等方面进行研究。
首先,在时空范畴上,香港狭窄炎热,凯蒂的医生曾建议她为了避免香消玉殒,最好避开那儿的酷暑;而湄潭府瘟疫肆虐,俨然是一个笼罩着死亡阴影的蛮荒之地。香港、湄潭府,它们都是与英国不一样的地理空间,是与现代的西方世界相对立的落后之地。
其次,在人物体系上,中国人与西方人在容貌、手势、言谈、服饰、性情等方面均有明显的区分和对立。由描述中国形象的词汇可见,中国人作为黄种人,在形态上的相异性得到了强调。这种对黄种人形态上相异性成分的描述中,隐喻着的是白种人——黄种人、文明——野蛮的对立关系,从中透露出西方人以自我为中心的傲慢与偏见。
(三)故事情节
小说中,毛姆通过程序化和模式化的叙事序列建构了中国形象。其中,中国的满洲公主爱上了英国人这一情节尤为突出。
凯蒂从圣约瑟姐妹口中得知,韦丁顿大革命时在汉口救了一家满族贵族的命。于是,那位满洲公主便疯狂地爱上了他,并为了追随他而离家出走。他走到哪儿,她就跟到哪儿。
以凯蒂的视角来看,韦丁顿身材瘦小、秃顶,长着一张猴子似的脸,十分逗趣,活像一个老男孩儿。他既不英俊,也不郑重内敛,然而,一位贵为皇亲国戚的满洲公主却义无反顾地爱上了他。这个故事的象征意义就是中国人受到优秀的西方文明的诱惑,西方人的优越感呼之欲出。
和沉默的中国人形象相反,毛姆还在小说中以敬仰的态度塑造了一位法国女修道院长。她出自法国一个名门望族之家,是个出色的女人。那些被父母遗弃的孤儿,却被院长慈母般加以关照。小说中多次提到,孤儿们很依恋院长,而院长一见到孤儿肃穆的脸上便露出了亮色,微笑着爱抚她们。她和蔼地站在她们中间,俨然就是慈祥的化身。包括院长在内的修女们,放弃了一切——她们的家、祖国、爱、自由,还有高雅的情趣、享受和舒适。她们来到这个霍乱横行的中国小镇,甘愿忍受贫穷,做出牺牲,听从吩咐,从事繁重的活计,整日进行祈祷。她们犹如圣母玛利亚转世,不远千里来拯救这些中国孤儿。
如此,在这些修女们无私的爱和无畏的牺牲精神的映衬下,“弃婴”现象更加凸显了中国人的冷酷、野蛮和落后,表达了种族主义歧视。
二、乌托邦想象中的中国
毛姆非常喜好中国文化。小说中的中国建筑、满洲公主以及对“道”的阐述,集中体现了毛姆对中国的乌托邦想象。
(一)中国建筑
小说中凯蒂在即将到达牧师住宅之前,看到了山坡上耸立着一座拱门。它与众不同,在逐渐西沉的太阳前面形成了一道美丽的剪影,带给她一种不祥的预感,它似乎有某种特殊的意义,但具体是什么她却说不上来。接下来的一夜凯蒂就梦到自己来到了一座拱门跟前,拱门美妙的轮廓似乎突然有了灵性,它的身形狂舞不羁,变幻不定,好像印度教里的千手观音。惊醒之后,她从窗户望出去,看到城堡上方呈现出一道彩墙。它是如此神奇、虚幻、缥缈,使凯蒂不禁悄然泪下,突然有了从未体验过的神思飞扬的感受。她觉得她的身体此时只是一具空壳,而她的灵魂在涤荡之后纯净无暇,她相信这就是美。在瓦尔特死后,凯蒂又一次凭窗远眺,这座美丽、奇妙、神秘的庙宇再次让她感到心神安宁。
中国建筑给凯蒂带来了灵魂涤荡和心神安宁,它也寄托着毛姆对中国古老文明的陶醉。
(二)满洲公主
小说中,韦丁顿和满族公主的异国恋情深深地迷住了凯蒂。满洲公主好似某种事物的象征,召唤凯蒂前去相见。
“……此刻她的心里朦朦胧胧浮起了一种遥远的、神秘的感觉。是的,她方才意识到这里是东方,古老、玄异、深邃的东方。从这位体态优雅的女子身上,凯蒂隐约看到了东方的理想和信仰。与之相比,西方人的所谓信念就显得粗陋野蛮了……这张色彩艳丽的面具后面,隐藏的是对世间万物的真知灼见,她五指修长的柔嫩的手,握的是这个未知世界的钥匙。”[3](P.159)
这位满洲公主,是毛姆特意塑造的一个极具象征性的形象,以寄寓自己对中国文化的思索。
(三)道
毛姆对庄子的哲学思想尤为喜欢,这也体现在小说中对“道”的阐释中。
在见了满洲公主之后,凯蒂曾对韦丁顿说她在寻找某种东西,但是到底找的是什么她也不能确定。韦丁顿说她找的是“道”。沃尔特逝后,凯蒂问及韦丁顿什么是“道”,毛姆借韦丁顿这个热爱并熟知中国文化的英国人之口表达自己对“道”的理解和认可。
17世纪,英国的罗伯特勃顿在《忧郁的解剖》中曾提出这样一种观点。在他看来世上所有政治、宗教、社会以及个人内心的种种矛盾都可以概括成一种病,即“忧郁”。他为诊治这些无处不在的流行病,开了不少“药方”,其中就包括东方文明。而在《面纱》中,在正遭受着情感危机、灵魂找不到归属的凯蒂眼里,中国的文化强烈地吸引着她,也成了她的“药方”,并最终促使她走向了新生。
三、作为他者的中国
据葛桂录先生的《跨文化语境中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所述,英国文化中的中国形象长期以来在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之间相互颠覆。18世纪中期之前,中国形象在英国文化中基本上是一种理想化的美好形象。很多学者和作家通过对中国乌托邦式的描述,表达他们对自身社会和体制的不满。但18世纪后半期至19世纪以后,随着英国成为世界强国和中国的因循守旧、国力衰微,中国形象也由美好的乌托邦堕落成丑陋的野蛮国。这时的英国需要一个愚昧荒蛮的异域形象来反衬本国的先进制度和文明,通过贬抑中国形象来维护自身的文化和现存体制。由此可见,“这些批评中国或赞美中国都是出于他们自己的文化理想,均是为了改良他们自己的政治和社会。”[5]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英国文化中的中国形象徘徊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之间。一些英国人仍肆意丑化和妖魔化中国。与此同时,以罗素为代表的一些英国知识人士却把目光转向中国传统文化,希冀用其来拯救濒危的西方现代社会。这充分说明了“异国形象从来都不是自在的、客观的产物,而是自我对他者的想象性制作,即按自我的需求对他者所做的创造性虚构,是形象塑造者自我欲望的投射。”[6]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绝非是真实的中国,它展现的是英国人的文化心理,反映的也是英国的需要。
作为一名英国作家,毛姆对中国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毛姆热爱中国传统文化。他亲历中国,是想寻觅中国昔日的荣光和古典的灿烂。另一方面,他又难免带有英国社会对中国形象的集体想象物的成分。而现实中国的破败和落后,又加剧了这种倾向,使他对中国的看法不可避免地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面纱》里的中国形象,美好与丑恶并存,这真实地体现了毛姆对中国复杂矛盾的文化心理特征。其实,无论是贬抑的意识形态表述,还是美好的乌托邦建构,都不是真实的中国,而是“他者”的想象。它既是英国关于中国的社会总体想象物在毛姆身上的投射,也是毛姆作为一个独特个体对“他者”的理解和想象。
[1]褚蓓娟,徐绛雪.“他者”在注视中变异——论比较文学中的“形象”[J].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9):282—286.
[2]陈惇,孙景尧,谢天振.比较文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3]W.S.毛姆.面纱[M].阮景林,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
[4]赵小琪.比较文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5]葛桂录.“中国不是中国”:英国文学里的中国形象[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5):64—70.
[6]姜智芹.当东方与西方相遇——比较文学专题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2008: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