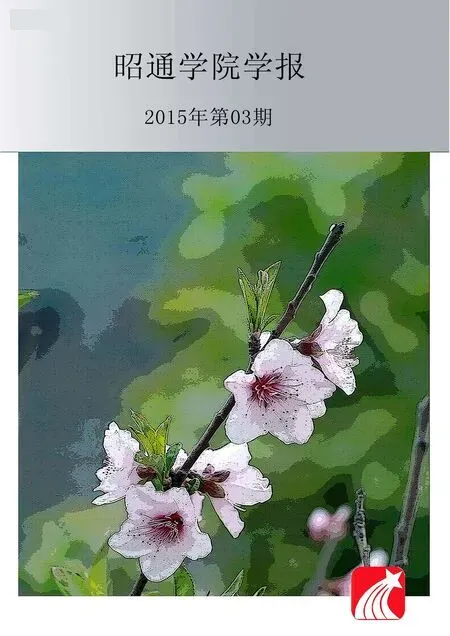1949—1966年文学影视剧中的阶层性研究
董 鹏, 赵雪琪
(1.卡莱(梅州)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计划部, 广东 梅州 514759; 2. 南开大学 文学院, 天津 300192)
●文学研究
1949—1966年文学影视剧中的阶层性研究
董 鹏1, 赵雪琪2
(1.卡莱(梅州)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计划部, 广东 梅州 514759; 2. 南开大学 文学院, 天津 300192)
自1949年至1966年,中国影视剧的创作和评价主要以政治话语为主导,其人物形象再现也被高度“刻板成见”化。农民,因其与红色政权性质的一致性,具有先天的政治正确性,成为一个被大写和极力讴歌的主体。而地主与知识分子,则以其政治的反动性与革命立场的模糊性,在影像文本中被置于与“革命性”对立的一极。这种影视剧中的人物再现,深刻定格并影响了这一时期中国的文化生态,也影响了中国80年代乃至延续到新世纪的文化版图。
影视剧; 政治话语; 审美维度; 阶层镜像
政治倾向与阶级立场,是中国文艺界在1949年至1966年间评价文艺作品最主要的两大标准。同样,这种“垄断性”的审美价值维度,也使绝大多数的文艺工作者都将关注点转向政治上更为“安全”和“保险”的题材和领域。仅以影视剧为例,“十七年”间的中国当代影视创作主要呈现出三种叙事模式:第一类是以再现中国共产党辉煌战争历史为主题的“革命英雄主义叙事片”,代表性作品有《平原游击队》(1955年)、《铁道游击队》(1956年)、《上甘岭》(1956年)、《狼牙山五壮士》(1958年)、《英雄虎胆》(1958年)、《红色娘子军》(1961年)等;第二类是“新旧社会两重天”的“控诉和报恩”式叙事,代表性作品有《一口菜饼子》(1958年)、《白毛女》(1950年)、《祝福》(1956年)等;第三类则是响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美学号召,以讴歌社会主义建设新成就以及在此过程中涌现出来的无数“先进典型”人物为叙事主题,代表性作品有《李双双》(1962年)、《我们村里的年轻人》(1959年)、《红旗谱》(1960年)、《暴风骤雨》(1961年)等。在这三类影视剧中,以工农子弟兵为主的“贫苦劳动者”是浓墨重彩进行渲染的主角。“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时期的中国电影,大体上就是一部形象化了的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劳动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奋战的历史。”[1](P.366)而工农子弟兵以外的其他阶层,如地主、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以往的社会精英阶层,则完全沦为叙事配角,他们在文本中经常性地以一种“高贵者的愚蠢”,映衬着“卑贱者的聪慧”。本文主要结合具体的影视剧文本,详细分析影像叙事中的阶层镜像,进而探讨这种阶层镜像背后所折射出的政治文化内涵。
一、农民:游移在“政治化符号”与农民天性之间
十七年文学影视剧中的农村与农民再现像是一个空壳,除了负载着太多的政治和革命内涵以外,农民的气质和思维几乎荡然无存。在诸多的创作者中,能生动再现较为原生态的农村及农民形象的,似乎只有不多的作家,如乡土气息浓厚、同农民有着某种“亲缘性”的作家赵树理等。赵树理的很多文学作品以及由此改编而成的影视剧,虽然也时有僵硬的政治介入,但其在作品中反映出来的农村状况、农民的世故人情等,还是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农民的性格特质和农村的原生态面貌。与赵树理相比,其他大多数创作者由于知识分子气质与农民气质之间天然的隔膜与疏离,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过于迎合,使他们对农民题材剧浓墨重彩的书写更像是一种知识分子借此宣示立场和态度的文本策略,其文本中对农村和农民形象(尤其是文本主角)的再现,带有浓重的概念化、教条化和简单化特点。在这种“英雄十先进”、“口号十标语”、千篇一律的人物模式之下,艺术人物形象本身的审美性几乎荡然无存。
(一)“新旧社会两重天”话语主导下的“苦难者”形象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政权主导地位也由此最终确立。新中国建立伊始,对新政权合法性的确认以及认同感的培养成为建国后文艺界的头等大事。配合意识形态的刚性要求,文艺界开始掀起“忆苦思甜”、“新旧社会两重天”等文本叙事热潮。在这股叙事热潮中,涌现出来不少以批判旧社会、歌颂新政权为主题的影视剧。如1950年由王滨、水华执导拍摄的《白毛女》;1950年由导演石辉执导的电影《我这一辈子》;1956年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改编自鲁迅小说的电影《祝福》;1958年由北京电视台首播的新中国第一部电视剧《一口菜饼子》;1964年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动漫片《半夜鸡叫》等。综观这些影视剧,贫苦农民往往以“苦难集中承受者”的角色出现,而文本也基本属于“苦难”的铺排叙事。《白毛女》中的喜儿,从小与父亲杨白劳相依为命。生命中的亮色便是过年时父亲杨白劳给买的二尺红头绳,以及困苦生涯中相携相持的恋人王大春。但生命中的这点希望和亮光由于发生在万恶的旧社会,注定要遭遇破灭:先是父亲杨白劳被恶霸地主黄世仁疯狂逼债,因不堪其辱最终选择在日历除夕之夜自尽身亡。紧接着,喜儿被抢入黄宅,受尽凌辱和折磨,原先的恋人王大春及其母王大婶一家也被驱逐,原本美好的爱情最后归于破灭。怀孕的喜儿历尽艰险,终得逃脱黄世仁虎口,可在逃脱途中又遭遇婴儿早夭之厄。喜儿走投无路、万念俱灰,只好深山穴居,一头青丝变白发,被村民误认为白毛仙姑,由人转向“非人”般的生活。历尽颠沛流离,喜儿最终依靠早先投奔红军、后随八路军返乡的旧时恋人王大春,得以摆脱“困苦”的恶性循环,实现了从“非人”向人的转变。电影《祝福》中的祥林嫂,年纪轻轻遭遇丧夫之痛,被婆家卖给贫苦农民贺老六为妻,因贺老六的真诚、老实,祥林嫂的生活也由此获得了暂时的安定,并于一年后生了儿子阿毛。后来,贺老六不幸感染伤寒,又遭遇卫老二逼债毒打,在病痛交加中死去,儿子阿毛也被野狼吃掉。走投无路的祥林嫂被迫去鲁四老爷家帮佣,却又因其坎坷的经历被视为“不吉祥”的罪人。重重打击之下,祥林嫂变得木讷、精神恍惚,并最终走上乞讨之路。在一个风雪交加的“祝福”之夜,祥林嫂永远地倒在了雪地上。
综观这一时期以农民为主体的“苦难者”形象,一方面体现了农民辛苦劳作、希望改变命运的不懈努力;另一方面,则是旧时代背景下底层始终挣不脱的“苦命”轮回。个体命运的决定力量不再取决于个体自身,而是由黑暗的旧社会与万恶的剥削制度所决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帝国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体系剥夺了贫苦人所有的生存希望。在重重压迫之下,农民群体虽然于艰难困厄中也有微弱的反抗,但这种依靠农民自身而进行的反抗换来的却常常是更大的厄运。正是在这种宿命般的噩运轮回中,革命话语的正当性与合法性被凸现出来。而中国共产党也正是在帮助贫苦群体摆脱不公正的制度层面,获得了中国底层群体绝大多数的支持与拥护。
(二)新农民:革命和建没话语主导下的“先行者”形象
为了适应新中国成立后不同阶段的任务重点,作为革命和建设的主体力量——农民,由于其天然的群体优势,被寄托了过多的政治厚望。同其他阶层相比较,中国农民数量庞大,他们不仅具有最强烈的革命要求,而且“最听共产党的领导”[2](P.20)。这些特点使农民很容易成为革命与建设实践过程中的“先行军”。受限于当时的文化体制和文学环境,塑造并反映这种“先行者”角色,通过精神感召的力量,以“先进”带动“后进”,促成更多的阶层和群体融人到革命和建没的大潮中来,成为文艺作品积极响应政治号召的不二选择。总体来说,基于不同的时代主题,中国农民先后作为“革命先行者”和“建设先行者”的形象,出现在诸多文艺作品中。前者的代表性作品多集中于前文所提到的革命英雄主义的叙事片中,如《红色娘子军》中的吴清华等,《闪闪的红星》中的少年英雄潘冬子等;后者则主要集中在“社会主义建设”主导话语下的影视剧中,代表性的作品及人物形象有《暴风骤雨》中的赵玉林,《李双双》中的李双双,《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中的高占武、孔淑珍、曹茂林,《创业史》中的梁生宝等。
这些颇具政治教化意味的典型人物,虽然人物形象各异,但又体现出高度的共性:他们多为农民群体中的佼佼者,政治觉悟高、集体主义意识强、忠诚党的事业;他们多背负家仇国恨(父辈被国民党或日本人杀害,所以向往、热爱新中国);在他们向先行者的蜕变过程中,多有一个引路人的角色,这个引路人的角色多由革命和建设队伍中的党员代表充当(如《闪闪的红星》中的红军父亲潘行义和红军干部吴修竹,《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中的退伍军人高占武,《暴风骤雨》中的赵玉林等)。这些引领者的设立,一方面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者角色的不断强调和确认,另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也暗示了农民知识层面的不足。而他们最终蜕变为英雄、典型人物的过程,也是农民天性从其身上不断剥离的过程。通过这种过程最后成就的农民典型,已经“不是农民气质或农民意识的体现”,而是“‘无产阶级化了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人的形象”[3]。在文本中,这种农民典型代表了当时农村最先进的力量,而这种先进评判的一个主要标准,是建立在对党中央政策的即时呼应与积极贯彻上。如此,政治策略转化为文本策略,农民典型形象直接成为政治图解。与这种人物形象政治符号化相伴随的是神圣化、理想化,即“为了将一个人变成典型,新闻报道往往不惜一切将他从人群中抽离,他的言行本是常人应有的也可能有的,却一定要让那些言行变成他一个人的独特价值所在,于是,‘宣传’把他变成‘模范’的过程,就是把他从人际、人伦、人群中的普通人变成一个奉献者、施予者甚至拯救者的过程,也就是自觉不自觉地推开、轻慢甚至贬抑其他普通人的过程”[4]。这种刻画,无疑与因袭千年负重、无论在物质上还是在思想上都从未真正占据主体的、传统的中国农民形象有巨大的割裂。这样的“农民肖像”已经不复是鲁迅笔下的麻木、愚昧、冷漠的形象,而成为一个为其他社会群体所仰视的、新时代的“弄潮儿”,在创作中也存在着过于“以理念取代形象、故意拔高而牺牲农民气质的偏颇”[5]。
(三)中间人物:更为自然和真实的农民群像
从1949年到1966年,除去上述两类颇具政治内涵的人物形象,还涌现了大量不那么“伟大、光荣、正确”,但却更真实、更符合农民习性和气质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形象在影视剧文本中大多以“配角”、“中间人物”、甚至“反面人物”的面貌出现。由于这些人物形象不需要负载太多的政治教化功能,反倒体现出了一种更为丰富和多元化的人物美学特质。如根据赵树理的《三里湾》改编的电影《花好月圆》(1958年)中,村长范登高热衷于跑买卖,搞个人发家致富,精明能干但集体观念不强,还有斤斤计较、算计过头的“糊涂涂”、“能不够”、泼辣任性的小俊,敦厚善良的玉梅,唯父母之命是从的有翼等。电影《李双双》里的孙喜旺:憨厚朴实,有点大男子主义,和稀泥,胆小怕事,讲人情。《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中心灵手巧、被村里人戏称为“七十三行”、憨厚老实的曹茂林,耿直率性、好打抱不平的王二狗和刘小亮,美丽善良、心灵手巧的木匠之女小翠等。《暴风骤雨》中的老孙头性格开朗,说话诙谐有趣,喜欢卖弄点小聪明,爱吹牛,渴望翻身解放但又胆小怕事,拥有农民的正义和善良,但又经常性地表现出狡黠的一面。这些农民形象,在影视剧中或作为“绿叶”的角色来烘托典型人物的英雄气质,或由于私念严重而成为与典型人物尖锐对立的反面形象被加以批判。这些人物在文本中的非主流地位,为创作者营造了一种相对独立的创作空间。同那些典型人物相比较,他们的形象较少拘泥于政治理念,更多地体现了创作者的自由意志。这些配角或中间人物,无论在生活作派、语言心理方面,还是穿着打扮上,都散发出浓厚的乡土趣味与生活气息。由于这些人物的存在,这个时期的农民形象并没有完全趋向于单一化、片面化,农民群像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保持与延展。
二、地主:财富的“不能承受之重”
与对工农大众等贫苦群体的讴歌相对立,对地主、大资产阶级等财富集中持有者的大力批判成为这时期的创作主流,因为他们是底层群体痛苦与不幸的主要根源。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他们主要基于思想和文化解放的层面,对维护封建礼教与传统的乡绅阶层展开激烈批判。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诸多文艺作品中的乡绅阶层形象,主要是恪守儒家文化伦理与观念的旧文化代表者,呈现出守旧、顽固、严厉、迷信等特点,而对其财富积累层面的指涉在文本中并不多见。比较典型的有鲁迅笔下的鲁四老爷、赵太爷、七大人,巴金笔下的高老太爷等。20世纪30年代左翼思潮发展之后,地主、资本家的阶级身份开始凸显。以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为标志,对这个阶级的批判开始成为无产阶级文艺所着力倡导的内容。不同于五四时期,这个时期对乡绅阶层的批判不再着力于文化话语的立场,而更多地着力于革命和阶级斗争式的话语批判。在这一类话语体系中,地主阶层财富积累的正义性和正当性,与贫苦农民之间不平等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连带其阶层存在的合理性都被强烈质疑乃至批判。
仅以地主为例,自1949年至1966年,各类影视剧文本累计塑造了将近几十个形态各异的地主形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白毛女》中的黄世仁,《半夜鸡叫》中的周扒皮,《红色娘子军》中的南霸天,《暴风骤雨》中的韩老六等。纵观这些文本中的地主形象,他们不仅是农民物质赤贫的罪魁祸首,而且还成为农民精神痛苦的主要制造者。具体来说,地主经济上的“原罪”主要基于其财富的集中和垄断,而这种财富的集中和垄断则来自于其贪得无厌的心理,以及对贫农高强度的经济剥削:如不顾贫苦佃农死活的高比例收租行为,对农民劳力的无情榨取和剥削。《半夜鸡叫》中的周扒皮,为了让长工早起多劳动,半夜学鸡叫;《暴风骤雨》中的贫苦农民赵玉林,辛苦为地主韩老六劳动一年,不仅分文未得,还因为大年夜讨要工钱而被韩老六抓去做了劳工。作品中地主的道德和政治罪恶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社会底层尊严的蔑视与不屑,如改编自鲁迅小说的电影《祝福》,文本中除了对鲁四老爷封建守旧特点的刻画外,还加入了鲁四老爷对穷人不屑与蔑视的描写。二是地主的为富不仁与道德伪善,如《白毛女》中对地主黄世仁家大门牌匾“德贯千顷”的强烈讽刺等。三是地主无法无天、罪大恶极的刽子手行为,如对恶人黄世仁、韩老六、南霸天的形象刻画,无一不紧密扣合着欺男霸女、不可一世、横行乡里、鱼肉百姓、无恶不作等恶霸地主的革命文本要求:“应该深刻地来描写那些反面的、敌对的人物中的形象,引起人们对于他们的仇恨和警惕。”[5]在这样一种阶级斗争、革命话语的政治化叙事下,地主身份开始成为财富阶层的不能承受之重:“富人的富是丑恶和罪恶的象征,富人等于坏人,而作为对立面的穷人的穷自然是善和美的化身,穷人等于好人。在几乎所有的土改宣传品中,富都是一种罪恶,富人统统为富不仁,行善也是伪善,意味着对穷人更大的欺骗和伤害。而反过来,所有的好事都是穷人干,穷则意味着不仅道德高尚,乐于助人,还意味着富有爱国精神,勇敢坚强。”[6]相对应的,传统乡绅、地主对于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意义全部被抹杀。在这“十七年”间政治的高压之下,他们不仅经历了阶层的整体性毁灭,而且严格遵循革命政治要求的文本话语也在另一个层面上将这个阶层抛入近乎万劫不复的文化深渊:地主在影视剧文本中成为一个极具贬义化与耻辱性的身份称谓,它几乎成为罪恶与残酷的代名词,这种刻板成见化的形象定格影响深远,直到进入21世纪的现在,我们依然可以在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方方面面,鲜明地感受到地主叙事话语和叙事模式的影响。现代周扒皮、现代版黄世仁、斗地主等流行话语,从一个层面印证了政治化的文艺给个体、阶层所造成的文化之殇。
三、知识分子:一个革命政治话语中的“暧昧群体”
在昂扬的革命叙事话语中,知识分子成为一个充满模糊意指和暧昧立场的特殊群体。在主要依据财富和政治立场来划分阶级身份的新中国,知识分子成为一个最难界定的群体。一方面,知识分子身份地位独特,他们不占有生产资料,主要依靠脑力劳动来维持自我生存;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在政治立场层面多具有超脱性与暧昧性的特征,如自由主义以及超越于政治纷争之外的学术独立曾经是旧中国很多知识分子的追求目标。另外,很多知识分子如梁漱溟、沈从文等都曾对革命和战争持保留态度。这几方面的特征使知识分子在以毛泽东为首的革命阶级版图中,一直是一个既被团结又经常被斗争和改造的群体。毛泽东曾经将知识分子划归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并不是一个阶级或阶层,但是从他们的家庭出身看,从他们的生活条件看,从他们的政治立场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7](P.641)毛泽东进而指出,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小资产阶级存在着同革命格格不入的气质,比如,他们容易动摇,“无论在哪个革命中间,他们总是动摇的,不坚定的”[7](P.400)。知识分子经常会表现出顽固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倾向,“许多革命知识分子身上的个人主义毒素,说它是头脑中的私有制,是再恰当不过的”[8]。知识分子同革命主体——工农大众存在着情感隔膜,如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明确指出,知识分子很多时候过于清高,不主动深入到革命大众群体中去,他们不爱工农大众的感情,不爱工农大众的姿态,不爱工农大众萌芽状态的文艺,有时甚至公开鄙薄工农大众的文艺。[7](P.807)这几点综合起来,注定了知识分子在革命政治话语中的边缘化状态。
1949年8月至11月,上海《文汇报》展开了关于文艺作品“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大讨论,这场讨论最终以“可以派”的代表冼群在1952年的“自我反省”而告结束。紧接着这场讨论,从1951年开始,一系列以乡绅、知识分子、资本家为主要表现对象的文艺作品相继受到批判,包括《武训传》(1952年)、《我们夫妇之间》(1951年)、《太太问题》(1950年)、《青春之歌》(1959年)等。仅以《我们夫妇之间》、《青春之歌》为例,在这两个文本中,我们看到了颇具小资情调的知识分子,在昂扬的革命话语热潮中所经历的一系列内在与外在的情感、行为的困惑与冲突。《我们夫妇之间》讲述来自大上海的知识分子干部李克,与贫农出身的童养媳、劳动模范张英在革命环境里恋爱、结婚。解放后,这对夫妻被调往上海,在城市的现代化语境下,夫妻二人迥异的文化背景、阶层出身导致了两人在感情和生活层面出现了严重分歧。相比较于贫农出身、革命正义感十足的妻子张英,作为知识分子代表李克的人格被映衬得相当渺小:他不仅贪慕虚荣和享受,而且过分关注自我,具有比较严重的个人主义倾向,如反对妻子收养孤儿,反对妻子向灾区捐款等。影片最后以革命妻子张英对李克成功的精神感召和李克的自省作为结束。作为十七年文学中为数不多的以知识分子为主角的城市题材剧,《我们夫妇之间》以一对普通夫妻日常生活层面的微观冲突,隐喻了革命工农兵审美与知识分子气质之间的割裂与对立。而在这种尖锐的对立面前,知识分子除了痛苦而漫长的自我改造、自我反省、积极向工农兵靠拢之外,别无选择。《青春之歌》塑造了以林道静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像,其中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功利派知识分子余永泽;有落井下石、乘人之危、将林道静嫁给当地权贵的校长余敬唐;还有认敌为友、中途变节的知识分子戴瑜。而林道静最终则正是在根正苗红的共产党员战士卢嘉川、江华、郑瑾的启蒙与帮助之下,从一个软弱、幼稚、略有个人主义倾向的小资产阶级最终成长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纵观这两部作品,可以看出,知识分子不复为以往文化思想启蒙者的形象,而变成了需要不断被工农无产阶级革命者和建设者启蒙和教育的对象,也正是在革命者的引领与革命实践过程中,知识分子的灵魂得以重生。从1949年到1966年,这种“谦卑的”、“俯就式”的话语模式,一方面为知识分子赢得了一个极其有限的叙述空间;另一方面也导致了知识分子与其作品之间的日趋割裂。主要表现为:知识分子思维与革命思维的割裂,叙述者与被叙述者之间的割裂,作品审美与作品思想内容之间的割裂等。这种割裂最终在“文革”期问达到顶峰。
四、结语
在1949年至1966年间,大写的工农兵革命者、小写的地主与知识分子,构成了镜像文本中最为主要的冲突要素。这种文本中的冲突同时伴随着美与丑、白与黑、正义与邪恶、革命与反革命等价值判断与价值定性。影像创作一方面紧密贴近政治流行话语的逻辑;另一方面,文本中的影像建构也在不断延伸着流行政治话语的影响力。在这种文艺与政治相互影响、相互建构的文化语境下,中国社会的阶层版图被彻底改写,伴随着荧幕上频频出现的、被“大写化”了的群体肖像,底层工农兵一跃而成为最具文化影响力和文化典范意义的群体。他们的审美趣味开始占据高地:“有许多在旧时代被认为是美的事物,此时却被看做是丑的了;反过来,当初被当做是丑的东西,现在却被认为是美的。雍容华贵,浓妆艳抹,不事劳动,出入于歌厅舞榭,浅斟低吟与绿酒红灯之下的达官贵人、公子小姐,过去曾是人们仰慕的对象,但新中国建立初期却遭到大众的鄙夷;粗手大脚、汗流满面的劳动者,梳着小辫子、身着列宁装的女工,过去被看做是低贱的、脏的、丑的,如今却被公认是美的。不仅生活中如此,对电影形象的美丑评价也是如此。”[1](P.4-5)底层话语、底层审美的激进凸现,一方面使长期被遮蔽的社会底层得以“浮出历史地表”,底层的话语权与文化影响力大为提升;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底层话语的提升并非建立在其经济、文化等诸多优势资源基础之上,而更多地依靠政治的刚性干预与促动,而这种外力干预下的文化繁荣不过是一时的文化幻象,一旦外力消失或者社会语境改变,底层文化可能就会面临加速度般的坠落。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鲜明地印证了这一点。从80年代的文化精英话语,到90年代的资本精英话语,再到2000年以后的“大众狂欢”话语,工人、农民为主的底层,构成了一个典型的、与现代化相对立的“他者”形象,贫困开始成为他们的“不能承受之重”。镜像话语中,他们或被漠视、或被悲悯、或被消费、或被调侃;而与他们直线坠落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日益被大写化的文化精英、政治精英和资本精英。这种全新的阶层图谱,影响了中国80年代乃至延续到新世纪的文化版图。
[1]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稿1949—1959[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
[2]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程光炜,论50—70年代文学小的农民形象[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4):185—202.
[4]魏天真. 我们愿意中的毒[J]. 读书.2008,(6):59—64.
[5]茅盾. 新的现实和新的任务[J].文艺报.1953,(11):15—29.
[6]张金国. 华北地区土地改革之诉苦研究[D]. 兰州:兰州大学,2009.
[7]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程光炜. 关于五十至七十年代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J]. 文学评论,2001,(6):65—72.
Study on hierarchical 1949—1966 years literature TV series
DONG Peng1, ZHAO Xue-qi2
(1.Carlisle (Meizhou) Rubber Manufacturing Co., Ltd, Meizhou 514759, China; 2. School of Literature,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g 300192, China)
from 1949 to 1966, the creation and evaluation China TV drama mainly political discourse dominated, the reproduction of characters are highly “stereotype”. Farmers, because of its similarity with the red political nature, with political correctness congenital, become a capital and strongly eulogize the subject. But the landlords and intellectuals, with fuzzy reactionary nature of their political and revolutionary stand, were placed with a “revolutionary” opposite pole in the image text. This kind of TV characters deep freeze and reproduction, the effect of culture ecology in China during this period, also influenced the Chinese 80’s and continued into the new century cultural territory.
film and television play; political discourse; aesthetic dimension; class image
2014-11-01
董鹏(1980— ),男,陕西安康人,研究员,硕士,主要从事现代文学研究。
I207.35
A
2095-7408(2015)03-005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