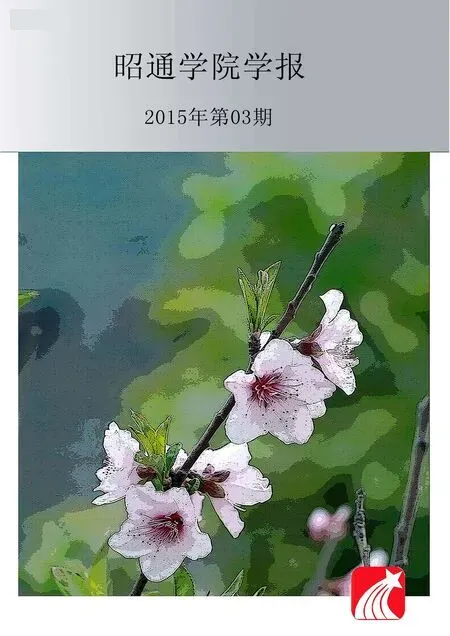宋濂文论思想与明洪武朝政治文化语境之关系研究
闵靖阳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北京 海淀 100875)
●文学研究
宋濂文论思想与明洪武朝政治文化语境之关系研究
闵靖阳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北京 海淀 100875)
宋濂的思想以理学为体,注重经世致用,可以代表明初帝王推行的国家意识形态,对明代文学理论发展具有导向作用。宋濂的文学理论主要由文学本体论、文学创作论和文学批评论三部分组成。宋濂认为文之本源是道,文之本质在于明道,明道之途径在于宗经,文之功能在于实用。其创作论首重养气,要求师古但从心出,以五美言诗。雅正中和是宋濂的文学批评标准。文章通过——宋濂身份的变化与其文学理论的关系,洪武朝的政治思想环境与宋濂思想的关系,洪武朝的文章风貌与宋濂文学理论思想的关系——三个维度论述宋濂的文学理论思想与明洪武朝政治文化语境之关系。
宋濂; 文学理论; 政治文化语境
宋濂的思想以理学为体,注重事功,基本上可以代表明初帝王推行的国家意识形态,对明代文学理论发展具有导向作用。宋濂元朝时期不仕,创作了大量诗文,充满社会批判意识,是当时“山林文学”之典范。投靠朱元璋后为明朝重臣,诗文风貌发生了一定变化,多颂圣应制之作,成为明朝前期“台阁文学”的源头。然而宋濂的文学思想并无显著差异,只是侧重点不同,前期更注重对文学本体的探讨,后期更强调文章的经世致用功能。
一、宋濂的文学理论思想
宋濂的文学理论思想源于哲学、学术思想,融合了部分创作经验,涵盖了诗论和文论,以文论为主体,主要由文学本体论、文学创作论和文学批评论三部分组成。
(一)本体论
1、文之本源是道,文之本质在于明道,明道之途径在于宗经
宋濂的文学本体论源于其哲学思想。宋濂的哲学思想以理学为体。宋濂从学于许谦、柳贯,许谦、柳贯是黄榦的三传弟子,而黄榦一派在朱熹弟子中最重道统。因此宋濂的理学和文论思想同样首重道统。从理学道统的根本思想出发,宋濂的文论观念自然认为文之本源是道,文之本质在于明道。宋濂的文道论在《文原》、《文说》和《徐教授文集序》中论述得最为充分。
“文以载道”基本为宋代理学家的共识。周敦颐首先提出“文以载道”,朱熹发展为“道文一贯”,道为文之本源,文是道的显现,文之本质在于明道。宋濂的“道”的主体是孔子之“道”,辅以孟子和理学家发展阐扬的“道”。“道德之儒,孔子是也,千万世之所宗也。我所愿则学孔子也。其道则仁义礼智信也,其伦则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也。其事易知且易行也,能行之则身可修也,家可齐也,国可治也,天下可平也。我所愿则学孔子也。”[1](P.71)宋濂的“文”是能够显现儒家圣人之“道”的,“文”的本质在于“明儒家圣人之道”。“明道之谓文,立教之谓文,可以辅俗化民之谓文。斯文也,果谁之文也?圣贤之文也。非圣贤之文也,圣贤之道充乎中,著乎外,形乎言,不求其成文而文生焉者也。不求其成文而文生焉者,文之至也。”[1](P.1568)文的意义就是道之显现方式,文的最高境界就是文中充溢着道,文即是道,道即是文。圣人自能“道积于厥躬,文不期工而自工”[1](P.1352),而普通人明道之途径则在于宗经。
宋濂的思想逻辑有这样一个链条,即道——圣——经。道是终极本体,圣人能够掌握道,圣人通过写经来呈现道。“是故天地未判,道在天地;天地即分,道在圣贤;圣贤之殁,道在六经。凡存心养性之理,穷神知化之方,天人应感之机,治乎存亡之候,莫不毕书之。皇极赖之以建,彝伦赖之以叙,人心赖之以正。”五经即是“至文”,即是道之显现。“后之立言者,必期无背于经,始可以言文。”[1](P.1351)五经是道的呈现,是文之典范,人只有用文载道,只有不违背道、不违背五经的思想,才可以作文。
宋濂传承了儒家1 500年间的明道宗经思想。《荀子·乐论》曰:“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道归是矣。”荀子认为道通过圣人的言说而显现,圣人体悟道,将其言说而为经。这是儒家明道征圣宗经思想的源头。扬雄的《法言》即明确提出明道征圣宗经思想。而《文心雕龙》则将原道征圣宗经思想运用于文章之学。与前人相比,宋濂明道宗经的文章本体论并无创见。因文章的典范是五经,当世人文章的最高境界是通过效法五经的文章风貌传达五经的思想,文章的最高境界不是自然而出,戛戛独创,而是复古。宋濂由明道宗经的文章本体论派生出的文章复古论开创了贯穿明朝始终的复古思想的先河。
2、文之功能在于实用
宋濂的哲学思想除了程朱的理学,还存在婺学的维度。婺学以吕祖谦学说影响最大。婺学不同于程朱理学与陆九渊心学之处在于,程、朱、陆都侧重心性道德的修养,而婺学追求事功,重视经世致用之学,在事功中培养心性道德。宋濂是浙江金华人,受金华传统的婺学的影响很大。因此,对事功的追求一直存在于宋濂的思想根处。宋濂投靠朱元璋,后来成为最接近帝王意识形态的士大夫的代表,婺学追求事功思想是其原动力。基于经世致用思想,宋濂的文论亦强调于世有用。
宋濂认为文学的本原是道,本质在于明道,文章之功能即在于实用。“明道之谓文,立教之谓文,可以辅俗化民之谓文。”文的功能在于通过显现道,宣讲道德心性,而教化众生,建立儒家理想的政治、人伦秩序,匡正时事之弊。“凡所以正民极,经国制,树彝伦,建大义,财成天地之化者,何莫非一文之所为也?”[1](P.55)宋濂认为诗文同源,其诗论亦强调诗“发乎情,止乎礼义”[1](P.2024),赞扬汪广洋的诗歌“受丞弼之寄,竭弥伦之道,赞化育之任,吟咏所及,无非可以美教化而移风俗”[1](P.482)。宋濂的文章功能论是儒家传统文章教化观与婺学事功观的结合,入明之后,身为文坛领袖,更将二者合而为一。
(二)创作论
土石坝的稳定性计算主要考虑水位以上坡体的渗流压力,而水位以下部分,将坡面以上水体视为一种有重度无强度的特殊材料,本次坝坡稳定计算采用Bishop简化条分法[7]。
由于文的本质是明道,如何创作充盈道的文章,自然是宋濂思考的重要问题。
1、首在养气
儒家的养气观念源于孟子。孟子的“气”是配义与道的崇高的人格自然产生的道德仁义之气,是精神人格的高境界。孟子善养浩然之气,同时将养气同知言关联,广为后世儒者推崇和效法。《礼记·乐记》云:“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伪也。”韩愈便有“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之论。韩愈将道德之“气”与文章创作结合,气充沛则文章自然顺达。宋濂的养气论延续了这一儒家传统。《文原》曰:“为文必在养气,气与天地同,苟能充之,则可以配序三灵,管摄万汇。……人能养气,则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当与天地而同功也。……大抵为文者,欲其辞达而道明耳,吾道既明,何问其余哉?虽然,道未易明也,必能知言养气,始为得之。”[1](P.1404)“天地之间,至大至刚,而吾籍之以生者,非气也耶?必能养之而后道明,道明而后气充,气充而后文雄,文雄而后追配乎圣经。”[1](P.1838)可见宋濂的作文养气观直接源于孟子、《礼记·乐记》、韩愈等对于言、乐、文与气之关系的思考。宋濂认为人能养气才可能明道,明道后气更充盈,气充盈后文章才能雄肆而顺达,这样才真正是宗经,将五经之道实践。养气是明道和宗经的中介,是作文的前提。
2、师古而从心出
宋濂的老师之一黄文献说:“作文之法,以群经为本根,迁、固二史为波澜。”[1](P.1028)宋濂年轻时深信此说并躬行之,晚年依然以五经为本根,只是补充了“六籍之外,当以孟子为宗,韩子次之,欧阳子又次之。”[1](P.1046)作文师法五经是宋濂一生的根本主张。在诗论中宋濂提出作诗师法的具体方法。“其上焉者,师其意,辞固不似而气象无不同;其下焉者,师其辞,辞则似矣,求其精神之所寓,固未尝近也。……诗乃吟咏性情之具,而所谓风雅颂者,皆出于吾之一心,特因感触而成。”[1](P.209)宋濂吸纳了《礼记·乐记》的“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诗大序》的“吟咏性情”、“发乎情”,韩愈的“师其意而不师其辞”,对于黄庭坚的“夺胎换骨”好像也有所吸取。宋濂对本体意义的“心”的重视源于陆九渊思想。师法五经及孟、韩、欧等文之意,从心所出是宋濂作文基本方法。
3、五美言诗
宋濂以诗文创作名世,积累了宝贵的创作经验,其文学理论同时亦是创作经验的总结。他提出作好诗的五种条件:“诗,缘情而托物者也。其亦易易乎?然非易也。非天赋超逸之才,不能有以称;其器才称矣,非加稽古之功、审诸家之音节体制,不能有以究其施;功加矣,非良师友示之以轨度,约之以范围,不能有以择其精;师友良矣,非雕肝琢膂,宵咏朝吟,不能有以验其所至之浅深;吟咏侈矣,非得夫江山之助,则尘土之思胶扰蔽固,不能有以发挥其性灵。五美云备,然后可以言诗矣。”[1](P.608)才情、学识、师友、苦思、外物五个维度是创作诗歌的前提条件,这五个维度是递进上升关系,满足的条件越高诗歌境界越高。宋濂五美言诗的诗歌创作论吸收刘勰、陆游、严羽等前贤之论,根据自身的创作经验,总结而成,确是师古而从心所出。
宋濂的文论创作很大一部分是对别人的诗文集写的序言和评论,因此,宋濂的文学批评观在宋濂文论中地位突出。宋濂的文章批评论同样源于其文学本体论和文学创作论。明道宗经是其批评论的基础和核心,着重肯定他人诗文的现实价值,勉励作者不断提升精神境界和道德修养,建议作者师法五经但诗文创作从心而出。在具体的批评标准上,宋濂主要依据雅正中和为标准进行文章批评。《<杏庭摘稿>序》评论洪潜夫的诗“和而不怨,平而不激,严而不刻,雅而不凡”,[1](P.73)《<田氏哀慕诗集>引》称赞田奂笃的诗“丰缛而纡徐,粹雅而冲和”,[1](P.498)《<叶夷仲文集>序》肯定叶夷仲的诗“温醇而有典则,飘逸而有思致”,[1](P.1029)《书刘生铙歌后》评论黄文献的文章“和平渊洁,不大声色,而从容于法度”,[1](P.1555)《题李易安所书<琵琶行>后》批判《琵琶行》发乎情却不能止于礼义。[1](P.1623)可见,宋濂的文学批评重视雅正,要求中和,很明显地传承了《中庸》之道和《诗大序》等儒家经典的诗文观。
二、宋濂的文学理论思想与洪武朝政治文化语境之关系
(一)宋濂身份的变化与其文学理论的关系
研究宋濂的文学理论思想与洪武朝政治文化语境之关系的前提是对宋濂身份、特别是政治身份变迁的认知。宋濂50岁以前一直在家乡从学讲学,不仕,其身份是学者和文人,主要从事学术研究和创作诗文作品。故此时宋濂的文论较多理学色彩,重视道、圣、经、性、文等儒家传统范畴的探讨,重视精神境界的修养,较少现实针对性,其明道宗经的文章本体论主要形成于此时。1360年宋濂投靠朱元璋后成为朱元璋的文学侍从,一度为太子师甚至帝师,身份由学者和文人转变为政治家,身份的转变必然造成思想意识的变化。宋濂前期的思想明道宗经与事功并重,但以明道宗经为思想主体,经世致用之学蕴含其中。后期作为政治家,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自然是维护本阶级与自身的利益,除继续高扬明道宗经外,对经世致用之学的思考与探索成为其思想的显著特色。朱元璋赞之为“开国文臣之首”,既是对其作为醇儒的赞赏,更是对其学对国家政治、文化建构具有重大实用价值的肯定。宋濂在朱元璋的要求下主编了《元史》,编写了《大明日历》、《大明律》等国家重要典籍和法律,参与国家重大礼乐制度、典章制度的制定,《明史·宋濂传》云:“在朝,郊社宗庙山川百神之典,朝会宴享律历衣冠之制,四裔贡赋赏劳之仪,旁及元勋巨卿碑记刻石之辞,咸以委濂,屡推为开国文臣之首。……一代礼乐制作,濂所裁定者居多。”这时宋濂的文论更加突出文的政治文化建构功能。“凡所以正民极,经国制,树彝伦,建大义,财成天地之化者,何莫非一文之所为也?”同时由于理学被朱元璋推崇为国家意识形态,宋濂作为醇正的理学家,又为文坛领袖,自然肩负起推广理学,推广国家意识形态的任务。由其理学思想派生的文论思想自然也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成分。罗宗强说:“宋濂的文学观是洪武朝文学思想的主导,是适应开国气象的文学思想最为完整的表述。”[6](P.67)这是由洪武朝初期的政治文化环境和宋濂的政治身份共同决定的。
(二)洪武朝的政治思想环境与宋濂思想的关系
朱元璋的统治思想是儒法并用,外儒内法。对于朱元璋的儒家观,宋濂的影响甚大。宋濂利用自己太子师的身份,常对朱元璋父子进行儒家意识形态的灌输。朱元璋初期好黄老之术,宋濂屡以五经荐之。朱元璋曾问宋濂儒家的帝王之学首要的书,宋濂首举《大学衍义》。夏燮《明通鉴》记载,朱元璋命人在新落成的宫殿壁上书写《大学衍义》,并说:“《大学》平治天下之本,”[2](P.1410)“朕观《大学衍义》一书,有益于治道者多矣。”[2](P.2489)朱元璋采纳了宋濂等儒者的建议,建立国子监、太学等官办学校,开设科举考试,学校教育“当以孔子之道为教”,“一以孔子所定经书诲诸生”,教学内容主要为四书五经。宋濂在读书人中也影响极大,《明史·宋濂传》载:“士大夫造门乞文者,后先相踵。外国贡使亦知其名,数问宋先生起居无恙否。高丽、安南、日本至出兼金购文集。四方学者悉称为‘太史公’,不以姓氏。”而宋濂作为“开国文臣之首”,其儒学思想与朱元璋以儒为体的治国策略互相强化,对洪武朝国家意识形态建构的功劳是首屈一指的。宋濂本来就坚持经世致用的文章观念,在这样的政治思想环境中,其以儒为本,以理学为正宗,以明道为文章的最高追求,以六经为文章的最高范式的文章观念更加强化。
(三)洪武朝的文章风貌与宋濂文学理论思想的关系
洪武朝的文章风貌是直接在朱元璋文章观的影响下形成的。朱元璋作为开国帝王,对文章的要求是有助于巩固统治,由于文化素质不高,不能理解夸饰性的文章之美,同时这样的文章对巩固统治没有直接帮助,自然为其所恶。“唐虞三代,典谟训诰之辞,质实不华,诚可为千万世法。……朕尝厌其雕琢,殊异古体,且使事实为浮文所蔽。其自今凡告谕臣下之词,务从简古,以革弊习。尔中书宜播告中外臣民,凡表笺奏疏,毋用四六对偶,悉从典雅。”[2](P.1512-1513)朱元璋的文章观尊崇典籍,注重实用,要求直陈其事,反对修饰。朱元璋的圣谕改变了洪武朝初期官员的文风,并推而广之,集合宋濂等人在科举考试中初步制定了八股文的文章做法,进行了从上至下将全体读书人囊括殆尽的文风改革。尽管宋濂不赞成八股文,但限于政治地位和政治身份,依然在文风改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当然宋濂以理学为体的文章观念不同于朱元璋彻底实用主义的文章观,但尊典籍重实用是二者的共同之处。因朱元璋对儒家经典的重视一定程度上是宋濂长期儒家意识形态渗透的结果,朱元璋也颇为欣赏宋濂以经世致用为鹄的、以雅正中和为审美标准的文章观,故朱元璋的文章观念受宋濂的影响也颇深。这个意义上,宋濂对洪武朝的文章风貌产生了重大影响。
[1]罗月霞. 宋濂全集[M]. 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2]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明太祖实录. 中华书局,1962.
[3]梅新林, 王嘉良. 江南文化研究·第5辑宋濂研究专辑[M]. 北京:学苑出版社,2011.
[4]魏青. 元末明初浙东三作家研究[M]. 山东:齐鲁书社,2010.
[5]王春南. 宋濂方孝孺评传[M]. 江苏: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6]罗宗强. 明代文学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3.
The Research on ‘Song Lian’s Literary theory’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t and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 of the Ming
Dynasty during the Reign of Zhu Yuanzhang’
MIN Jing-ya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Song Lian’s theory was based on Neo-Confucianism, focus on statecraft, not only represented the national ideology which the empire of early Ming Dynasty pursued, but also directed the development of Ming Dynasties’ literary theory. Song Lian’s literary theory mainly consisted of literature ontology, literary creation, literary criticism. Song Lian proposed Dao was the origin of literature. The appearance of Dao was the essence of literature, and respecting classics was the way. The literature’s function was practical. He required the writers improve moral realm and personality, and study ancient writers and works, but must according to their own ideas to create. There are five necessary conditions to write excellent poetry. Beauty, Justice, middlebrow were the criterion of Song Lian’s literary criticism. This research discuss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ng Lian’s Literary theory and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 of the Ming Dynasty during the reign of Zhu Yuanzhang’ through three dimensio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ng Lian’s status change and he’s literary theor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ng Dynasty during Zhu Yuanzhang political thought and Song Lian’s theor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ng Dynasty’s during Zhu Yuanzhang article style and Song Lian’s theory. The paper used the poetics of culture method, literature analysis method.
Song Lian; Literary theory;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
2014-11-26
闵靖阳(1982— ),男,辽宁沈阳人,讲师,在读博士,主要从事意境论与毛泽东时代美术史论研究。
I206.2
A
2095-7408(2015)03-004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