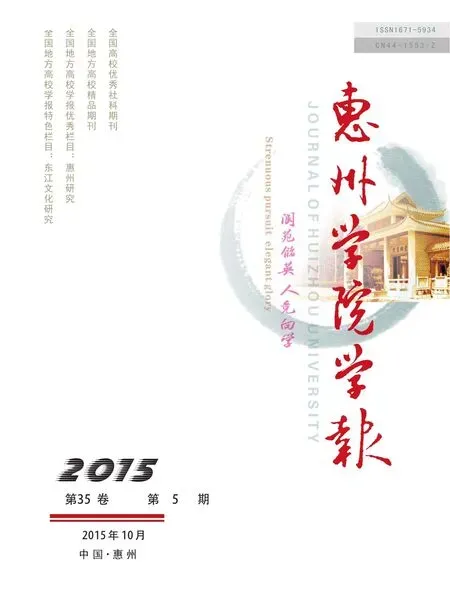失效的拯救 回归的身体——试论穆时英笔下的都市小说
张 俊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穆时英,这位“新感觉派圣手”,把都市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对现代都市文学的贡献是毫无疑问的。以至于苏雪林称赞道:以前住在上海一样的大都市,而能作其生活之描写者,仅有茅盾一人,他的《子夜》写上海的一切,算带有现代都市味。及穆时英等出来,都市文学才正式成立。[1]355的确,穆时英用“新感觉”的手法,呈现了百货大楼、饭店、咖啡馆、跑马场、舞厅、公园、电影院等可供消遣娱乐的现代公共空间和时装、西餐、咖啡、鸡尾酒、霓虹灯、广告牌、旅馆等充塞着新鲜刺激的现代物质文明。也因此,这些空间和物质的享受主体——都市现代男女,便构成了都市最鲜活的“风景”,尤其是都市尤物,作为“城市物质魅力的载体,也更加速了城市中不可避免的商业化进程”[2]216。当都市被具有如此吞噬性力量的现代物质“暴力”裹挟着,人们所疑惑的是,穆时英笔下的都市小说只能被理解为“物的文学”吗?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地拥抱“现代”,具有自觉意识的都市主体甘愿沦为物的媒介和符号吗?如果拒绝,他们又是以怎样的姿态和方式?生活在“东方巴黎”的上海,“一个与传统中国其他地区截然不同的充满现代魅力的世界”[2]192,他们真的能够与传统中国及其生活方式诀别吗?而解决这些问题,其实也是在尝试回答和辨析穆时英先生一向被非难和质疑的地方,即他的作品“与生活,与活生生的社会隔绝”[3]614,并且也是在将他的都市小说创作与同为新感觉派的作家刘呐鸥的进行有效的区分,从而彰显穆时英笔下的都市小说的独特性。下面笔者将详细述之。
一、失效的拯救
穆时英的都市小说重技法的实验,以散文诗的抒情笔调勾勒都市里的声光灯影,用蒙太奇的电影切割法剪辑都市生活的碎片化场景,“彻底摒弃了小说的故事或情节线索的因素”[4]161。尽管小说中的故事或情节被如此淡化,可是在散乱的片段化场景中依然集中传递着关于拯救的信息代码。《白金的女体塑像》中三十八岁的谢医师给他的第七位病人治疗——一位身体孱弱,没有血色的女性。其实这只是最基本的关乎健康与身体的拯救。事实上,在穆时英的笔下,还有一些超越身体,辐射到知识、感情、价值、信仰等诸多抽象层面的拯救。而这诸多层面,可以从医生/病人这一基本的拯救模式升华成导师/学生的拯救格局。《玲子》中玲子的文学基础不太扎实,“我”受托于约翰生博士,成为玲子的导师,拯救她稍显薄弱的学业知识。在《骆驼·尼采主义者与女人》这篇中,主人公认为骆驼坚忍、顽强,拥有不抱怨、不疲倦的韧劲,而人生本就布满荆棘,肩负重担,因此他认定人生当与骆驼形成呼应,哪怕是抽哪种烟。所以当他目睹一位小姐吸着朱唇牌的烟时,便自觉地扮演了人生导师的角色,以命令的训斥式的口吻对她的生活方式进行拯救和“启蒙”:“不懂吗?我告诉你,我们要做人,我们就抽骆驼牌,因为沙色的骆驼的苦汁能使灵魂强健,使脏腑残忍,使器官麻木。[5]195”在《CRAVEN“A”》中“我”对于那个被众多人鄙夷为“那么cheap的”[5]241舞女余慧娴充满同情和关怀,便自觉充当她生命里的精神导师,承诺内心是真正爱她,期许能给予她生活和心灵的宽慰。在这项关于拯救的宏伟工程中,拯救者无一例外地都由男性主体来胜任;被拯救的对象,无论是身体上的疾病,知识上的不足还是生活方式的选择,心灵的创伤,都毫无疑问地投射给女性,不管这个女性主体的身份是贵妇、学生还是城市漫游者、舞女等。
那么,这些拯救的效果如何呢?除了《白金的女体塑像》中谢医师用太阳灯烘照女病人的身体,令其稍有起色外,其余的以“导师”命名的超越身体之外的抽象拯救不得不接受失效的严肃事实。笔者细数那些失效的拯救:与其说“我”在给玲子尽心辅导,毋宁说“我是她思想上和行动上的主宰,我是以她的保护人的态度和威严去统治了她”[5]177,“我”忽视了玲子作为一名少女在成长期的隐秘的下层感情,给她带来的不是身心健康,而是情感伤痛。(《玲子》)尼采主义者反复地强调和指引健康的人生方式,即骆驼式的隐忍,可却被女人“不懂”、“没法子懂”、“不明白”的答复毅然拒之门外。(《骆驼·尼采主义者与女人》)尽管“我”想爱护这个CRAVEN“A”,但最终的结局是,CRAVEN“A”依然绝望地默默离世。(《CRAVEN“A”》)这些失效无不在昭示着拯救的被动与苍白。饶有兴味的是,当导师们的拯救被宣告破产时,与之相伴的是女性身体进行拯救的胜利。在女性身体的帮助下,医生和导师获得了清醒和自救。《白金的女体塑像》中谢医师在遇到第七位女病人时,用太阳灯给这位女客烘治,看到她裸露的身体后,他的反应与平常有很大的不同:慌张、颤抖、充满了蒸腾的原始的欲望、难以把握自己。于是回家后决定认真组建一个完整的家庭,从此过上安定的生活,而事实上,他确实这么做了。《玲子》中玲子在和“我”这个导师即将分别之际,主动捉住“我”的手,把脸凑上来,胳膊拖着“我”的脖子,用她的身体暗示“我”对男女感情的忽略,令我幡然醒悟。“我”便用吻她来拯救自己长久以来积累的愧疚之情。《骆驼·尼采主义者与女人》中尼采主义者在现代小姐身体的诱惑下,摧毁了自己之前的理想信仰,不再坚持隐忍耐苦的生活方式,学会了放松和享受。那么,为何这些都市女性的身体能够强烈地拨动男性的心弦,能够有如此巨大的力量实施良好的拯救呢?首先得厘清这些都市女性身体的具体内涵。
二、现代经验的郁结
这些都市女性的身体,其实是一个复合的整体概念。它涵盖女性本身的肢体形象,其次还有肢体所披覆的服饰,最后还有这两者熔炉后所呈现的综合精神面貌。伴随着这些女性出场的首先是她们的身体形象。对于这些都市女性的描摹,几乎都是如此,即肢体形象为拥有高挑的身材,丰满的胸脯,纤细的腰肢和手腕。具体到面部则都有经过化妆的修饰:嘉宝型的眉,细长的睫毛,枣红的腮,鲜红的嘴唇。而她们的服饰呢,并非珠光宝气,也并非宽松自在型的。旗袍装是整体造型,多为暗绿色或墨绿色。有时也有衬衫、披肩、网袜——墨绿的衬衫,白绸的衬衫,红色的披肩,缠绕的网袜。耳朵上总是装饰着黑宝石或宝塔形的长耳坠子。这些女性的身材特征总是曲线线条、性感妖娆,一副撩人的姿态。其实这样的肢体形象往往潜藏着性的暗语,即这些女性是图画、是风景,自觉或不自觉供奉给男性主体观摩,并以此来挑动男性与生俱来的,拥有强烈原始欲望的“弱点”。再看她们的服饰和妆容,以精致的化妆品点缀修饰面庞,以流行的服饰来衬托曲线的形体。这些信号无不通知人们:“现代”来了。“这一时期上海的时装紧跟欧洲(主要是巴黎)时尚,例如一旦巴黎的时尚服饰出现展示,不到三个月就会在上海流行开来”[6]48。也就是说,这些都市女性生活在当时中国最大的贸易港口和通商口岸,又是半殖民地的租借地区,她们最先嗅到日新月异的商品味道。她们不断推陈出新,跟着时尚的步伐走,这些便集中体现在时尚的服饰上。曼妙的身材搭配时尚的服饰,按理说,这些女性的精神状态应该是活力四射、光彩照人。可是她们眼睛里呈现出来的恰恰相反,她们疲倦、无力、憔悴。白金塑像型的妇人“荔枝似的眼珠子诡秘地放射着淡淡的光辉,冷静地,没有感觉似的”[5]4。墨绿衫的小姐“羽样的长睫毛下柔弱得载不住自己的歌声里边的轻愁似的”[5]182。CRAVEN“A”“眼光淡到望不见人似的,不经意地,看着前面”[7]238。有意思的是,都市男性们并没有因她们婀娜的姿态,与世界同步的服饰而沉迷,他们陶醉于心的正是女性身体这种独特的颓废。“可是我爱着她呢,因为她有一颗老了的心,一个年青的身子。[7]245”“我爱憔悴的脸色,给许多人吻过的嘴唇,黑色的眼珠子,疲倦的神情······”[7]283。
为什么穆时英小说中的都市女性身体能够浸染到男性的心灵深处呢?笔者认为问题的关键正在于这些女性身体所透露出来的精神真实。因为就肢体和服饰而言,刘呐鸥笔下的女性不乏这些,可是她们的精神面貌却大相径庭。颓废美在刘呐鸥小说中的都市女性那里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容易受惊的眼睛在男子面前忽闪忽闪,跳舞时男孩式的短发随风飘动,肌肉充满弹力,看起来一副运动型的近代女性。这些女性的状态俨然性感与可爱、温柔与野蛮交织并置,自由、开放、洒脱的情怀喷薄而出。不仅身体的精神状态如此,她们更把这种自由、开放、洒脱的形象踏实地贯彻到与男性交往的具体实践中。于是,人们看到刘呐鸥小说中的都市女性能够自如地游离在男性之中,又总能令男性无力把握自己和他人。《游戏》中的女性在舞池一面与男主人公步青跳舞甚欢,一面告诉他即将与另一个男子交往,然后一段时间后又去找步青,最后她不在乎地安慰步青要愉快相爱,愉快分手。《风景》中的一位夫人在火车上对男子燃青主动搭讪,在旅馆主动递吻。《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中女子与男子H和T同时约会,然后同时当面告诉他们要与另一个人约吃饭。这些女性通常都是主动出击,并且与男性保持交往很短暂,追求速度、新鲜、直白、方便。这样的交往方式也决定他们之间并没有纯粹的爱情,可是即便如此,她们却总能令男性在心里不断地做自我宽慰来应允她们随时而来的要求。也因此她们在异性心中已被固化为近代都市的所产。“都市的所产”使得有研究者认为“这些‘摩登女郎’的身体被放在‘物品’的位置上······一方面,它是这些物象符号的集合体;另一方面,它使这些集合起来的符号高度形象化,因此能够更方便地进入都市叙事,这又是首先通过获得一个女性身体而达成的。[8]27-28”笔者认为尽管“摩登女郎”们擦Cyclamen香水,拎Opera包,坐“飞扑”,穿欧式服装,高跟鞋······这些生活组成部分无不与物质化密切联系,但都市的产儿内在的性格和精神却没法等同于物质。她们虽然展示了物质化的一面,但更传递了女性在面对现代商品经济快速涌来时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的选择。而其实“摩登女郎”所背负的时尚“似乎可以作为一种有用的方式来表示工业化资本主义文化生活永不停息的变化的欲望,以及时尚本身所表达的求新求变的特征。[9]88”正因为如此,在现代工业文明铺天盖地地卷来时,她们没有驻足反思,而是选择与其同步。不仅在物质享受上与其同步,更在精神认同层面与其同步,一切务必求新求变。所以刘呐鸥笔下的女性身体,更直观地说,是作为一种现代“现象”存在的,只有神经末梢的刺激,很少有冷却后的审视。
而穆时英笔下的女性身体却不仅仅作为一种“现象”存在,它更是一种现代经验的郁结。黑牡丹坦白道:“脱离了爵士乐,狐步舞,混合酒,秋季的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车,埃及烟······我便成了没有灵魂的人。那么深深地浸在奢侈里,抓紧着生活,就在这奢侈里,在生活里我是疲倦了。[7]304”这段话很好地说明了这些都市女性们身体的颓废。一方面,她们也和刘呐鸥小说中的“摩登女郎”一样,享受着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所带来的刺激,便捷。另一方面,却又有很深的焦虑,即深谙这种新鲜、自由带给她们的是毫无确定的方向,欲望的过度膨胀,热情里的浮躁,生活的无规律,真诚的坍塌,道德节操的失守滑落,信仰的缺失,一切皆过度、泛滥。她们其实有很强的自省意识,也在有意无意地审度这种新兴的生活方式的价值与合理性到底有多少。在这种生活的内核中,末梢的刺激与沉重的心理负担并存,极度的欢乐与莫大的空虚混合,因此多重杂糅后是到处可见的矛盾,并且失望、寂寞、孤独、疲惫感压过了兴奋、刺激、快感、。而这些都市男性在目睹了如此复杂的女性身体后,心灵深处不得不受到浸染与拯救。他们认同的正是身体所散发的颓废感,一种处在现代生活中的多种经验的并置。因为这种复杂的现代生活也是他们的真实生存处境,这些女性仿佛一面镜子,抑或是男性们的另一半真实的自我,当他们不期巧遇时,已没有了性别之分,此时他们是一个完整的象征符号,他们共同谱写着现代生活的经验曲目。所以在这种精神真实中,这些都市女性的身体便有意无意地拯救着都市男性,让他们找到了生活在现代模式中的真切体认,内心获得安慰,生命找到认同。“她没问我的姓名,我也没问她的。可是我却觉得,压在脊梁上的生活的重量减了许多,因为我发觉了一个和我同样地叫生活给压扁了的人”[7]305。
三、回归的身体
上述已经讲到,刘呐鸥小说中的女性身体很少涉及冷却后的审视,但并非没有。只是“摩登女郎”自身鲜少反思,而在“摩登女郎”代表的资产阶级与辛苦的产业工人之间起连接作用的管家却扮演了审视者的角色。唯一对“摩登女郎”的主动诱惑予以拒绝的男性是《流》这部小说里的镜秋,他对于这种近代的都市产物是可以淡定抗拒的,他心仪的是纺织业老板家的家庭教师小瑛,他爱她“并不是她有了美丽的容姿,或是有了什么动人的声色。她可以说是一个近代的男性化了的女子。[10]20”显然,镜秋需要的其实是现代独立的女子,可以做他革命事业的同盟军的男性化了的女子。这样的女性正可以和他一起举行工人暴动,而暴动恰恰是镜秋缓解现代生活焦虑的途径。在他认为,这些摩登女郎享受着琳琅满目的高端商品,肆意的挥霍钱财,实际是在压榨工人的汗水,让广大劳苦大众苦不堪言,因此必须要领导工人暴动来改变这种结局。在刘呐鸥的小说中,都市女郎在尽情地控制男性,忘我地消遣娱乐时,总有另一个截然不同的环境形成对照。如“远远地只听见着修路工人的铿锵的锤声”[10]4,“他这时才知道他忘了这市里有这么许多的轮船和工厂”[10]37。所以刘呐鸥小说里审视现代生活经验后采取的是一种带有左翼情怀的解决之道。相比于刘呐鸥,穆时英选择了另外的方式。
穆时英的小说中这些在快速生活的轨道里跌落的现代身体该如何安放呢?遗憾的是,CRAVEN“A”选择了离开世界,以墨绿衫的小姐为代表的大多数依然继续浮沉。只有极少数的选择自救,他们如谢医生、黑牡丹。而他们自救的方式都是回归。谢医师做了三十八年的单身男子,下班后在没有任何道德羞耻感、没有任何感情、冷静无力的白金塑像似的女病人身上获得了启发,于是选择回归家庭。同样地,黑牡丹在机械的高速旋转的生活轮子中自觉意识到有机体的自己总有一天会跌倒的,于是在遇到圣五这个隐士风的绅士后,选择回归生活的驿站。回归后的身体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谢医师原本“有一张清癯的,节欲者的脸;一对沉思的,稍含带点抑郁的眼珠子,一百四十二磅重的身子。[5]3”回归后,“他有一张丰满的脸,一对愉快的眼珠子,一百四十九磅重的身子。[5]12”黑牡丹说:“这三天,我已经加了半磅咧”,“便明朗地笑起来”[7]312。他们不仅在体重上增加,得到舒展,精神上也是愉悦轻松。因为他们的回归其实是选择了中国传统的有规律的生活方式,放逐了嘈杂的自由,不用给无机的节奏催着往前跑,而且家庭让安静的心灵有了坚实的依托。谢医生并不是简单地结婚。他要的是织绒线的女人和孩子。妻子可以给他放洗澡水,可以和妻子商量菜单。这些无不是传统中国家庭的生活模式。回归的不仅仅是身体,更是一种精神。信仰得到了重新确认,意义被重新定义,价值被重新创造。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生活方式并非陶渊明式的归园田居,它的生活基础仍然是现代的多元物质。谢医师回归家庭后,依然穿西装、打领带、喝咖啡、抹古龙香水、驾汽车。或许这方面的集中代表是《黑牡丹》里的圣五,一个有中国传统隐士风的“贤士”。圣五也大学毕业,但是他并没有选择在现代生活里放肆的挥霍生命。而是用一份不算小的遗产在郊外买了一套充满果香的别墅,每天早上都去散步,过着休闲安静的过活。他的离群索居并不是与外界完全隔绝,他“每天喝一杯咖啡,抽两支烟,黄昏时,自个儿听着无线电播音”[7]306,他的生活里也包容着现代的物质文明。他的回归是一种建立在现代物质文明基础之上的精神回归,而这种回归也确实给他带来了健康幸福的生活。而这也恰巧说明了那些以“导师”命名的超越身体之外的抽象拯救为什么会失效。其实导师们一直是在用抽象的价值理念去拯救学生。导师认为人生就该像骆驼一样承受生命的苦重;认为真诚的爱就能够去感化一个人,给她带来快乐。尽管这些拯救的出发点都是那么合理,但他们忽视的正是已经到来的现代物质文明这个实在的基础。他们忽略了现代人多变的味觉感知,忽略了陪伴中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场景。离开了这个基础,“一切概念,一切信仰”自然会稍显空洞,对她们而言,“一切标准,规律,价值全模糊了起来”[3]616。在都市现代文明的活动场域中,不管拯救者有无实力去启动这种拯救,她们都有意无意地不满足和抗拒这种抽象的拯救。所以无论是郁结的现代经验还是物质相随的回归,穆时英的都市小说都没有脱离社会,脱离生活,而且他不止停留在现代社会和生活的表面,他还挖掘表面之下的冰山,关心人的生存方式——如何健康合理地栖居在不断发展的现代世界中。因此他的小说并没有把人沦为物的附属品或符号,仍落脚于人的文学,并将中国传统的家庭生活方式、修身养性的情操与西方吞噬性的现代物质文明有机融合。
[1]苏雪林.苏雪林文集:第3卷[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355.
[2]李欧梵.李欧梵自选集[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3]穆时英.穆时英小说全编[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
[4]夏元文.论穆时英小说结构模式的创新[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0(1):161.
[5]穆时英.穆时英小说·白金的女体塑像[M].北京:九州图书出版社,1995.
[6]顾跃.先锋·颓废——常玉与中国美术现代性研究的另类视角[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48.
[7]穆时英.南北极公墓[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8]张屏瑾.摩登·革命——都市经验与先锋美学[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1.
[9]乔安妮·恩特维斯特尔.时髦的身体——时尚、衣着和现代社会理论[M].郜元宝,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0]刘呐鸥.刘呐鸥、章衣萍卷[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5.
——都市女性自爱力系列
——对其附逆之事的再思考
——从《文学界》追悼特辑到夭折的文艺团体“中日文艺家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