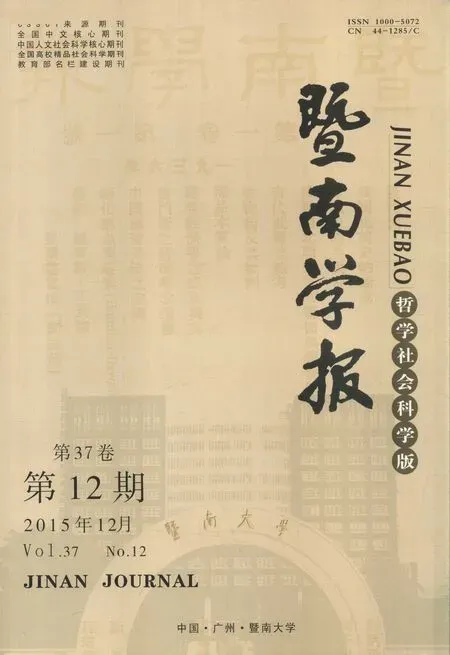“花踪文学奖”与马华文学新生代的崛起
王列耀,彭贵昌
(暨南大学 中文系,广东 广州 510632)
1990 年3 月,《星洲日报》宣布举办“星洲日报文学奖”,同年6 月详列征文细则,并更名为“花踪文学奖”。从1991 年开始,“花踪文学奖”每两年举办一次,从未间断,至今已历十三届。回顾二十几年来的“花踪”之径,我们发现“花踪”与马华文学新生代作家的崛起是密不可分的。黎紫书、龚万辉、曾翎龙、梁靖芬等一大批新生代作家通过“花踪文学奖”走上文坛,成为当下文坛的中流砥柱;而早在台湾等地成名的陈大为、钟怡雯、黄锦树等人也通过“花踪文学奖”的认可,“回归”马华文坛。
一、“花踪机制”对新生代的期许
《星洲日报》举办“花踪文学奖”,可谓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集宣传、刊载、出版于一体,这是其他举办华文文学奖的华人社团等组织所不具备的。1991 年,“花踪文学奖”创办之初,《星洲日报》的读者人数是57.2 万人,其读者人数逐年攀升,1992 年增加到68 万人,从此稳坐马来西亚第一大华文报的位置,2003 年之后读者人数更是越过了100 万大关。有着这样庞大读者群的《星洲日报》举办的“花踪文学奖”,影响不可小觑。
《星洲日报》及其创办的“花踪文学奖”对中华文化的传承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有学者在研究《星洲日报》与华人关系的时候指出,在文化传播方面,《星洲日报》作出了以下贡献:①传播中华文化;②提升读者的华文水平;③培养读者学习风气;④推动文艺发展。笔者认为,“花踪文学奖”凭借其强大的宣传机制和隆重的颁奖典礼,在这几方面都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颁奖典礼声势浩大、隆重绚丽,主办方、评委、得奖者和文学爱好者齐聚一堂,加上主办方邀请的歌舞团、艺术家的表演,热闹非凡。在马来西亚这个华人文化处于边缘地位的国度,颁奖典礼上满溢着“中国性”的表演,成为了强化华人身份和强调华人文化的仪式,不断唤起人们的民族情感与记忆。主办方还借着在“花踪文学奖”颁奖典礼时著名作家、学者齐聚一堂的机会,举办“花踪国际文艺营”。世界各地的著名作家、学者在参与“花踪文学奖”决审的同时,也都在文艺营中担任文学专题的主讲人。此外,在前后两届“花踪文学奖”的间隔期间,主办方还以“花踪系列讲座”形式,为两年一次的文学奖“保温”,邀请华文文学界享有盛誉的作家主讲,每次讲座也都反响热烈。以第一届“花踪文学奖”为例,“花踪系列讲座”的主讲包括黄春明、王蒙、痖弦、於梨华、郑明娳、张贤亮、张洁等著名作家、学者。这些活动对文化传承有着推动作用,特别是对作为文化传承主体的年轻人来说,更是影响深广:充满着文化气息的隆重颁奖典礼激发起年轻人对中华文化的热情和对获奖的期待,文艺营和系列讲座则对心怀写作理想的年轻人有着极大的激励和指导作用。
从主办方《星洲日报》对“花踪文学奖”的定位来看,他们对年青的一代写作者是充满着期许的。一方面,《星洲日报》希望将“花踪文学奖”打造成在整个华文世界都具有影响力的奖项,因此主办方力邀海内外的著名华文作家、学者参与评审、举办讲座,并设立世界华文文学奖,将此殊荣授予华文文学界的文学“巨人”,以彰显他们对华文文学的巨大贡献。另一方面,“花踪文学奖”中占据主导部分的甄选奖部分,则是力图为马华文坛培养接班人。《星洲日报》社长张晓卿曾经不止一次地在《花踪文汇》的序言中表达自己对传承华族文化的寄望,这种寄望很大程度上落在了对年青人的期待上。从“花踪文学奖”的宗旨来看,也可以发现这一特点。“花踪文学奖”在创立之初定下的宗旨是:鼓励创作、发扬文学和传承薪火。“鼓励”的对象和“传承”的主体必然都是年青一代,从第二届开始的宗旨“开拓国际视野,提升文学品质,反映时代精神”中的“开拓”和“提升”等词,显然也更针对年青的一代,其主体不是指向风格已经成型或者已经扬名的老作家。“花踪文学奖”培养文坛新秀一方面出于报刊负责人身上所体现的文化人的责任感,另一方面出于现实考虑——主办方培养文坛新秀的渴望也是极为迫切的:《星洲日报》副刊所要面对的问题之一是“本地高水平文学作者群有萎缩危险”,“花踪文学奖”所起到的拔擢新人的作用,则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途径。可以说,《星洲日报》举办“花踪文学奖”的一大目标就是挖掘文坛的新生力量。
以“传承薪火”为目标的“花踪文学奖”,期待着年轻作家接过文学的接力棒。从首届文学奖开始,新生代作家就崭露头角,从第二届开始,斩获奖项的新生代作家人数大大增多,这一群体开始成为“花踪文学奖”最重要的得奖群体。新生代作家生长在马来西亚,从祖辈身上继承了中国文化,努力于中文写作。但是,能让他们一展拳脚的机会不多。华文报刊是马来西亚最重要的文学园地之一,无论是出自于经济上的考量或是文学上的认同,“花踪文学奖”都能激励写作者,特别是年轻作家。散文作家梅淑贞认为:“星洲日报创办文学奖是件好事。甭管是有人抱着为‘利’而来也好,或是为‘名’来也罢,还是为‘名’为‘利’都好,肯定是他们都要拿出真本领来,这也是激发起文学创作的泉源之一。”“花踪文学奖”这块土地,激励着许多马华新秀萌芽生长,渐渐成为日后的参天大树。他们的书写,展现了新生代华人的生存环境和内心世界,也形成了对马来西亚境内马来族文化“霸权”的抵抗。二十多年的时间也证明,文学与传媒结合的“花踪机制”,为马华文坛挖掘、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新生代作家,推动着马华文学的发展。
《星洲日报》通过自身的传播和资本优势,将“花踪文学奖”打造成“文学奥斯卡”,让更多的人将目光投向了文学这块被冷落已久的土地,给予了文学场巨大的象征资本。新生代作家,就在这个“奥斯卡”中崛起。
二、步入“花踪”舞台的新生代
《星洲日报》对新人的拔擢是不遗余力的。从1988 年《星洲日报》复刊起,在“文艺春秋”版面发表作品的作者中,新生代作家的比例日渐扩大。为了向文坛推荐新人,“文艺春秋”版块还在90年代推出过“新人出击”“新秀特区”等专辑。在“花踪文学奖”中,对新秀的重视也十分明显——从第三届开始开辟了“新秀奖”鼓励年轻人。新秀奖分为小说、散文、新诗三个组别,开放给20 岁或以下的年轻人参加,将文学奖的象征资本授予这些对写作抱有憧憬的青少年。然而,即使是在“花踪文学奖”的其他奖项中,新生代也占据了主导位置。
从甄选奖方面来看,从第二届开始一批新生代作家的名字就被人们熟知,小说方面有李天葆、黎紫书、刘国寄、陈志鸿、翁弦尉、梁靖芬等,散文方面有钟怡雯、林幸谦、许裕全、黄灵燕、龚万辉、曾翎龙等,新诗奖有陈大为、庄若、林健文、游以飘、吕育陶、周若鹏等,其中黎紫书、许裕全、龚万辉、曾翎龙等作家还经常跨组别获奖。从推荐奖来看,我们更容易看出主办方《星洲日报》的评奖倾向。“花踪文学奖”的推荐奖(包括小说、散文、新诗)的得主必须是在《星洲日报》文艺副刊“文艺春秋”和“星云”发表至少2 篇小说或3 篇散文或3 篇新诗的作者,参赛者在其他报刊上发表的作品则被排除。进入决审的作者,首先必须在《星洲日报》副刊发表作品,并经过报社编辑人员的推选,此举既在于吸引马华作家扎根于《星洲日报》副刊,也以权力话语姿态冷落了其他竞争对手。因此,在推荐奖中,权力运作的痕迹比各项甄选奖更为明显,导向性也更加突出。通过对历届获奖名单的统计,我们发现导向性更强的推荐奖同样更倾向于新生代作家群体。从第一届开始,新生代作家就成了推荐奖的主要候选人,此后,新生代作家所占比例越来越大,直至囊括各大奖项,到第四届起,推荐奖已经被新生代作家们尽收囊中。我们可以从九届的推荐奖获奖名单(第十届起取消了推荐奖这一奖项类别)中一窥新生代在推荐奖中的获奖情况。
推荐奖获奖名单:

第一届 第二届 第三届 第四届 第五届小说 小黑 潘雨桐 潘雨桐 黎紫书 陈志鸿、黎紫书散文 褟素菜 寒黎 林幸谦 钟怡雯 陈大为新诗 方昂 小曼 方昂 陈大为 陈强华第六届 第七届 第八届 第九届小说 黎紫书 黎紫书 黄锦树 陈政欣散文 钟怡雯、邡眉 林幸谦 杜忠全 许裕全新诗 林健文 陈强华 林幸谦 沙河
从这个得奖名单中不难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在《星洲日报》主导的文学奖中,新生代已经成为主力,这也是马华文坛代际更迭的表现。学者刘小新指出,“这一新世代作家群的崛起是90 年代以降马华文坛的最大事件,标志着马华文学已进入世代更替和文学范式转移的新时期……”在“花踪文学奖”之中,新生代作家被奖项“认可”之后,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在之后的文学奖评奖中不同程度地参与到评审过程中。李天葆、黎紫书、夏绍华、吕育陶、刘育龙、林艾霖、梁靖芬、庄若、许裕全等人都参加过复审或新秀奖决审的评审。从参赛者到评奖者的转变,意味着他们在马华文学的场域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这不啻是新生代权力的加固。
这个代际的崛起与对主流文学场的占据,更明显地表现在马华文学大奖的颁奖上。“花踪文学奖”从第十届开始,增设了“马华文学大奖”,授奖于过去两年对马华文学有突出贡献的一位或者两位马华作家。得奖者除获得高额的奖金(马币1 万元,是所有征文种类中奖金最高的奖项)外,《星洲日报》还将为其出版一本作品。马华文学大奖主评焦桐说,这个奖有两层用意,一是肯定本土文学的创作,及定位本土文学的坐标。至今为止马华文学大奖的获得者有:木焱、梁靖芬、黎紫书、沙禽、黄锦树。具有着标杆意义的大奖的得主清一色是新生代作家,宣告着新生代已经掌握了文坛的“话语权”。正是《星洲日报》举办的“花踪文学奖”,从甄选奖、推荐奖,再到复审或新秀奖评审,最后到马华文学大奖,一步步将马华新生代作家推上马华文坛的历史舞台,并将他们的作品“经典化”,使他们成为文坛的主导。
“花踪文学奖”对新生代的重视不言而喻,新生代对“花踪文学奖”也深感认同。多次获得“花踪文学奖”,在台湾等地也屡获大奖的黎紫书,在获得第四届散文奖首奖之后,表示得到“花踪文学奖”是她的“一点点的骄傲”。获得第六届世界华文小说奖时,她说“但每每记得自己曾得过奖,居然还很欢喜”。第九届获得马华小说佳作奖、马华散文佳作奖的曾翎龙,在得奖感言中也坦言自己曾进过六次“花踪文学奖”决审都空手而归,依然坚持着写作希望折桂。
赴台留学并留居台湾的马华作家,同样认为“花踪文学奖”是马华文坛最成功的文学奖,期望获得“花踪文学奖”以彰显自己的马华身份。在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已获得多项重要文学奖的钟怡雯,获第三届“花踪文学奖”散文首奖时表示,每年陈大为都“逼”着她参赛。陈大为更是直接表达了自己的想法:“我不是在追逐‘花踪’的名利,也不是在寻求这项肯定,而是一种身份的认同。虽然我的创作生命从台湾开始,所师法/所吸收的全是中国(大陆)及台湾的养分,虽然我得过3 次台湾的两大诗奖,并且第一本诗集也在台北出版,虽然我的诗作题材一向都非关大马,但我毕竟是大马人,马华文坛的一分子,所以我必须替自己寻找这个身份的认同。在马华的诸多文学奖当中,我只认同‘花踪’,所以我一直虎视眈眈,但一再失手。如今,总算弥补了心中这个缺憾。”曾获“时报文学奖”等奖项的林幸谦,在获得第三届“花踪文学奖”散文推荐奖时,也表达了“花踪文学奖”对他的特殊意义:“能够得到此奖,让我感到我并没有远离家乡,仍旧生活在这里。这里有我最珍贵的记忆。”黄锦树也曾透露自己曾经多次投稿参加“花踪文学奖”的评审。
在华文处于边缘地位的马来西亚,用华文写作是孤独的。“花踪文学奖”隆重如奥斯卡的颁奖礼,已经不单单只是对参赛者本人及作品的肯定,更是以隆重的文化盛宴,激励着那些已经站上颁奖台或者想要站上颁奖台的新生代作家们。诚然,马华新生代的发展离不开自身的努力,但也不可否认,“花踪文学奖”为新生代作家提供了起飞的平台,使新生代作家以后生可畏的姿态迅速成长。“花踪文学奖”凭借其苦心经营树立起的权威,成为了新生代作家心中的标杆。
伴随着新生力量而起的,是丰富多元的文化景观。在《花踪文汇1》的序言中,张晓卿直言:“希望通过主动的反思和批评,能为这个已经绚烂多姿的社会,创造更丰富和更有气质的文化内容。”这种“丰富性”,正是历届的“花踪文学奖”所力图实现的。
在90 年代,马华文坛在报刊上展开了几次激烈的论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经典缺席”以及“马华现实主义的实践困境”,这些论战归根结底是不同代际之间美学原则的角逐。可以说,“花踪文学奖”的评审也是论争的缩影,文学奖的评审过程同样是不同的美学原则之间的角力。此外,马华文坛的论争在一定程度上为新生代的创作奠定了理论基础,而“花踪文学奖”的得奖作品,则是在创作层面呈现了美学原则角逐的成果,这些作品受到来自华文文学主流地区的认可,从而实践对“马华现实主义困境”的跨越。
为了评奖的公正,“花踪文学奖”的终审评委大多数来自美国或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地区,包括张错、李欧梵、李锐、刘心武、王安忆、陈思和、潘耀明、黄子平、杨牧、焦桐等诸多名家。虽然从第三届开始,小说、诗歌、散文奖的决审评委会中各加入一位马华本土作家,但是人数占多数的外籍评委还是拥有着评奖的主导权。相对而言,这些本身就是著名作家或学者的外籍评委更倾向于多元、前卫的美学风格,而不仅仅是维护马华文坛传统中曾为主流的马华现实主义文学。新生代作家们在创作中往往大胆地打破常规语言,以陌生化的效果将文字呈现在读者面前,这通常都受到评委们的肯定。黎紫书的《把她写进小说里》(第三届小说首奖)是非常典型的一例,文章大量的词句都被评委指为过于拼凑、刻意,如“5 月的能量”、“捆住我的文学绳索”、“保持着无语问苍天的姿态”此类。语言的不规则运用让评委们展开了讨论,有评委认为这种语言是一种破碎的语言。但这篇文章最后得了首奖,证明这种语言已经开始被接受。黎氏日后的创作大抵都是用这样的语言风格进行,也频频得到肯定与嘉许。钟怡雯也是一位致力于语言运用的新生代作家。她的《可能的地图》(第三届散文首奖)一文中充满着诗化的语言,如“或已悬空的地理”、“穿越时空的银河”等,也有日落的阳光像是条大白舌头舔走希望一类的新奇意象。钟怡雯的散文虽屡次被评委指出缺乏足够深刻的文化内蕴,但是她对文字的经营却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在第五届的马华小说终审时,各位评委也就黎紫书的《流年》一文也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出自马华本土的终审评委梁放质疑这篇小说作为马华小说的本地色彩不强,希尼尔则觉得作者的文字功底很好,能以极好的意象与古诗词入文,大加赞赏,在最后的表决中《流年》得到最高分,获得该届马华小说首奖。纵观“花踪”的得奖作品,现代性、前卫性、多元性在新生代作家的作品表现得十分明显,新生代的这种审美趋向也被评委认可和鼓励。获得第五届散文奖首奖的翁弦尉的《弃物祭文》一文运用了意识流的手法,极具实验性和现代性,以开放式的结构赋予了语言、文字新的活力,整篇文章结构和语言都显得非常独特。评委在讨论这篇作品与其他作品的比较时,提到这是“传统散文和新式的散文的拔河。”(永乐多斯语)新生代所追求的融合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多元美学风格,与传统的写实风格拉开了距离,在一次次的被认可中成为了时代的文学主潮。
在对新生代创作美学的承认这一方面,“花踪文学奖”功不可没,这种承认,也使得台湾等地的一些马华作家“回归”本土。当陈大为在1995 年编选《马华当代诗选(1990—1994)》的时候,他被质疑是以台湾视角来评判马华诗歌。然而当以陈大为等为代表的新生代诗人在“花踪”屡屡获奖,特别是获得具有承认和表彰意味的“推荐奖”之后,新生代的美学就被“花踪”赋予了象征资本,宣
三、新生代美学风格的确立
告着被马华文坛承认,实现从其他华文地区到大马本土的回归。借此,《星洲日报》也构建起马华文坛的多元化文学生态,使马华文学与其他地域的华文文学可以形成沟通与对话。
在得到主流文坛的承认之后,新生代作家在“花踪文学奖”中努力践行着多元美学的尝试。当然,这样的美学追求跟他们自身的经历不无关系。20 世纪90 年代,社会瞬息万变,身处大马或者游走于海外的马华作家都无法摆脱全球化的浪潮和信息科技发展的影响。在这个大环境下,新生代作家无论是从自身经历、传媒还是网络,获取到的信息量都是巨大的,他们与世界的联系也更加紧密。“花踪文学奖”这个舞台,为马华作家提供了与世界华文文学接触甚至竞争的机会,也为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与创作提供了良好的展现平台。此外,不少“花踪文学奖”得奖的新生代作家,曾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地接受较高层次的教育:陈大为,台湾师范大学文学硕士、博士;钟怡雯,台湾师范大学文学硕士、博士;翁婉君,台湾大学国文所硕士;黄锦树,淡江大学国文所硕士、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博士;林幸谦,台湾政治大学文学硕士、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翁弦尉,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黄灵燕,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梁靖芬,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高学历并不等同于杰出的写作能力,然而这种求学经历,给作家带来了宽广的视野。马华新生代的创作并不都是现代主义风格的,然而,在90 年代多种因素的合力之下,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美学已经成为新生代的重要追求。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这种追求被“花踪文学奖”授予了象征资本,获得了马华文坛的承认,这使得他们有勇气在这样的美学实践中继续前行、探索。下面我们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获奖作品的考察来一窥新生代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美学追求。
邡眉的《素人自画》(第四届散文佳作)是新生代的写作宣言。文中以绘画艺术为论题,以臼齿象征艺术的教条,主张艺术不应为规则所限。借此作者也表现出对文学的看法:“文字惯性聚集,笼统写法,已唤不起令人惊艳的感受,失去弹性的魅力。文字的写法如果能够像绘画那样充满生命力的移形换样,该有多精彩!”
詹明信的“文化分期说”把资本主义分成了三个阶段,“二战”之后的西方则处于第三阶段——晚期资本主义阶段,随之而起的是作为其文化表征的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一大特征是解构,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则是许多文学流派所进行的语言实验和话语游戏。生活在全球化语境下的马华新生代作家,自然也深受影响,他们在写作题材丰富的同时,手法也越来越多元。在这一点上,元小说可以作为代表。元小说(即“后设小说”)的手法在“花踪文学奖”的得奖作品中多有表现。对元小说的定义众说纷纭,各种说法的共同特征都离不开它对小说虚构性的暴露。其中,戴维·洛奇的观点是被广为接受的:“元小说是关于小说的小说:这类小说以及短篇故事关注到自身的虚构本质与创作过程。”
黎紫书的《把她写进小说里》(第三届马华小说首奖)在“花踪”拉开了元小说的序幕。在《把她写进小说里》中,“我”既是书中的人物,又在尝试写着别人的故事,因此主人公江九嫂既在“我”所在的现实中,又在“我”虚构的书中之书里。江九嫂的一生在“我”的不断回忆和探寻中被拼合出来,在许多的描述中,回忆和“我”的虚构被作者有意模糊起来,让读者分不清楚虚构与真实。“我”不停地追述和想象关于江九嫂的一切,最终,整个《把她写进小说里》的文本顺着“我”对她故事的追寻和想象而完成了本身的叙述。黎紫书在这篇作品里打破了固有的现实主义手法,让作者的主体性得到更好的体现,同时很好地表现了对创作的一些思考,为马华小说拓展了更大的叙事空间。
从黎紫书开始,元小说手法便较为频繁地被运用在创作中。如在第六届的“花踪文学奖”马华小说部分,就出现了两篇具有元小说色彩的作品,分别是梁靖芬的《水颤》和陈绍安的《禁忌》。《水颤》中,“我”不断地在文本中强调对郑和下西洋故事的叙述的不可靠,甚至设计让祖上郑和遇上了哥伦布。“我”虚构了郑和与哥伦布见面的场景,因为“我”忍不住要给祖上安排贴心伙伴。文章中的多处描写都指向了我祖上郑和的这段故事的叙事的不可靠性,以元小说的手法消解了正统的历史。《禁忌》这篇文章的全题是《禁忌——虚构补选文体与真实小说观念之差》,在标题中已经点名文中有“虚构”的色彩。在这篇文章写到的有数据、日期等材料支撑的政治选举中,作者不停地强调其中的虚构色彩,并把它写得非常荒谬;在虚构的异族恋爱故事中,又写得非常真实。在文章中作者多次强调“小说是真实的,生活很虚幻。”作者用元小说的方法,有意弄混真实与虚构,抒发马来西亚社会异族恋爱悲剧的隐痛,同时也讽刺了政治的肮脏和荒谬。
寓言书写也是新生代写作的特色之一。新生代作家不再局限于现实主义的写作方式,常常以寓言书写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寓言都是一种叙事文体,作者通过构造人物情节,有时还包括场景的描写,构成完整的‘字面’意义,即第一层意义,同时借此喻表现另一层相关的意义。”詹明信在分析第三世界文学时认为,这些文学文本都是以政治寓言和民族寓言的形式出现的。这个理论虽然一定程度上建立在白人中心主义的文化语境中,然而他关于寓言书写的论述还是值得我们参考借鉴的。在寓言书写上,黎紫书的小说《国北边陲》(第六届世界华文小说奖首奖)是最典型的代表,这篇作品具有后现代主义的魔幻色彩,以家族命运来指涉马来西亚华族的命运。作品中的“你”通过父亲遗物中的笔记和信件一步步追寻和还原着家族的历史,并跟随着祖辈的脚步去寻找传说中的龙舌苋。龙舌苋的根部是可以让家族血脉得以沿承下来的解药,整个家族祖祖辈辈找寻龙舌苋,若不得则命陨中年。这是一则关于民族文化的寓言:没有文化的根基则无法延续家族,甚至民族的命脉。可是最后“你”发现要找寻的龙舌苋却是无根的,龙舌苋其实也不是家族血脉可以延续的唯一解药,隐喻着族群主义和族群迷信都是一种困境,只有以一种更加开放的姿态容纳其他的文化,并以此重塑自身的旺盛生命力,方是根治之药。“你”的个体与家族命运,就是马来西亚华族命运的一种指涉。
翁弦尉的《弃物祭文》(第五届散文首奖)同样是一篇以寓言来书写国族的作品。岛上的时间将“我”的种种感觉都燃烧殆尽,化成种种工业制品,“我”的生活变得机械化。作品中还用蚂蚁来象征这座岛屿城市里每天疲惫于工作和琐事的人们,坐公车时蚂蚁垂下的触角就是人们在上班路上无精打采的隐喻。人们唯恐丢掉的“票根”又像是生活里种种规则以及机械化的程序,象征着人们被现代化的文明所困,已经完全失去了自主性,沦为了文明的奴隶,只能像一只只蚂蚁,毫无目的地在这个机械化的城市里劳碌奔波。在新诗体裁上,游以飘的《在我万能的想象王国》(第二届小说佳作)是在童话外壳包裹下的政治寓言。国王“为大人与小孩设计一套同样的发型和公民课本”,他拳头状的皇冠在城市上空罩下阴影,覆盖着所有的宣传渠道,“藉以防止皇宫的尊严/被阳光晒伤”,是对大马教育体制和传播体制的极大讽刺。后文还以王国中的种种景况隐喻嘲讽政府的愚民政策、种族歧视、政治表演、思想管制等等。在结尾,一句“得承认这地图始终是马来西亚”道破天机——寓言中所有嘲讽与指责都指向了马来西亚。
元小说手法和寓言写作在“花踪文学奖”的出现,表明马华新生代作家进一步拓展创作空间的实践,得到了理解与支持;促使他们不断紧跟世界文坛的脚步,自觉地对小说、散文、诗歌的形式本身进行有意识的思考和实践。
马华新生代作家们在语言的运用上也更加自觉。他们的前辈李永平在语言上煞费苦心,而新生代在语言上的追求又不同于李永平等人对语言纯粹的中国性的追求,而是一种更多元化的语言运用。前文所提过的《流年》《可能的地图》《弃物祭文》等文章的语言都反映出这样的特色。网络语言入诗等现象,也表现出马华新生代作家语言运用的多样化。吕育陶的作品就是一例。《造谣者的自辩书》(第五届新诗佳作)运用了大量的网络语言和网络表情,营造出陌生化效果,充满时代感和新鲜感;《和ch 的电邮,网站,电子贺卡以及无尽网络游戏》(第六届新诗佳作)也以网络的形式隐喻现实的荒谬。诗歌从形式变革入手,进而在内容和精神层面上,为马华诗歌开辟了一条更为多元化的道路。
文学奖的风格是报刊副刊风格的延续,文学奖的风格也是当时副刊和文坛主流风格的缩影。“花踪”中常见的地志散文就是报纸副刊中常见的散文类别,小说中的后现代技法以及诗歌的寓言书写也都是新生代的典型美学风格,在新生代作家的其他作品中大量出现。在很大的程度上,“花踪文学奖”凭借对新生代作家美学风格的引导,构建了马华文坛的生态。然而,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文学奖机制对文坛生态建构方面的一些弊病,题材方面的“扎堆”就是其中明显的一项。比如小说奖中,个人化的“小叙事”和同性恋等边缘题材的书写,在“花踪文学奖”中曾多次出现,我们在新生代作家的其他创作中,也可以找到非常多同类别的作品。在“花踪文学奖”中,涉及同性恋书写的有翁弦尉的《上邪》、梁伟彬的《梦境与重整》、林俊欣的《树》等,而在文学奖之外,翁弦尉的《游走与沉溺》《喧哗与沉潜》《自祭文》《沉睡的吉普赛少男》,黎紫书的《裸跑男人》,陈志鸿的《腿》等作品,也都涉及此类题材。同样,热衷于个人的“小叙事”,摒弃国族“大历史”以及灰暗的语言基调,都是新生代小说家作品中常见的风格。可见,“花踪文学奖”的获奖作品是新生代作家创作的一个缩影,同时,也具有着一定的导向性。在文学奖对美学风格的强调之中,作者们书写的题材呈现越来越小的趋势,具有社会现实意义的作品也逐渐减少。虽然这样非常具有私人化色彩的边缘书写和“小叙事”让文学园地更加丰富多彩,可是一味淡化社会意识的作品大量出现还是会影响到文学功能的发挥。一味“文以载道”让文学肩负起现实的责任会给予文学过重的负担,文学作品之中社会意识的极度匮乏,也是另外一种极端;这是值得警惕的。
尽管“花踪文学奖”在多年的发展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其对马华文学的贡献却不言而喻。依托具有强大经济资本和象征资本的《星洲日报》及其副刊平台的“花踪文学奖”是一个微缩版的马华文坛,我们可以从中见证过去二十余年来马华文坛的代际更迭和创作潮流的变迁。“花踪文学奖”显著地加速着代际更替,勾勒出中生代与新生代之间的“交接”轨迹,见证并影响着新生代逐渐稳健壮大,成为马华文坛中流砥柱。可以说,“花踪文学奖”发展的历程就是许多新生代作家成长的历程。当然,新生代的成长得益于“花踪文学奖”这个大舞台的同时,也得益于其自身的努力,因此文学奖与马华作家之间呈现双向互动的关系:“花踪文学奖”为马华文坛提供一个“标杆”,树立一个榜样;同时,文学的进步也需要马华作家们自身引以关注,领会其深意,突破瓶颈。只有在内外兼修之下,马华文学才有走出去的契机。或许在不久的将来,真正实现“马华文学的抬头——由文学的边陲,至‘东南亚华文的重镇再至中国华文文学在海外的重要分支’,乃至于‘世界华文文学重要的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