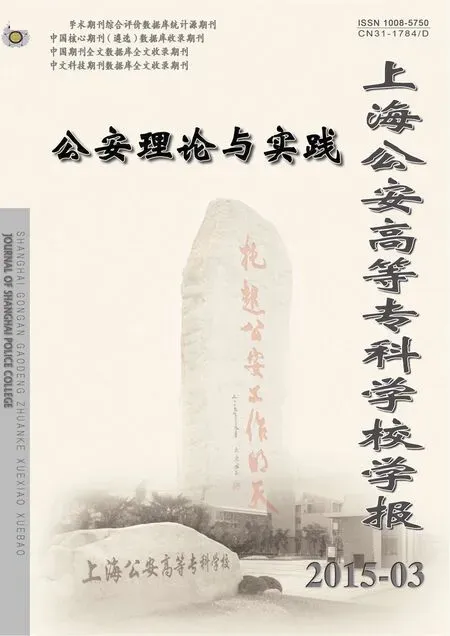三论金融诈骗犯罪主观方面
三论金融诈骗犯罪主观方面
李宏杰,鲍新则
(华东政法大学, 上海 200042)
摘 要:非法占有目的是金融诈骗罪中必不可少的主观内容,其不仅是立法技术的体现,也是司法实践中合理区别此罪与彼罪的标志。金融诈骗罪中的明知包括犯罪行为和犯罪结果,且只能是直接故意,即直接追求某种犯罪结果的完整心理态度,间接故意中的放任有结果归责之嫌。认定金融诈骗罪中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主观要素需与行为人具体实施的诈骗行为相融合形成证据链和因果关系的法律逻辑。
关键词:金融诈骗犯罪;非法占有目的;明知 ;犯罪目的
责任编辑:陈 汇
一、问题之提出
围绕着我国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五节“金融诈骗罪”中八种具体金融诈骗犯罪而引发的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争论,无外乎肯定说、否定说和有保留的肯定说。否定说主张除《刑法》第192条的集资诈骗罪和第193条的贷款诈骗罪在法条的罪状中明确规定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其余六种具体金融诈骗罪即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有价证券诈骗罪和保险诈骗罪均未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作为构成要件。肯定说认为集资诈骗罪和贷款诈骗罪规定“以非法占有目的”是为了区别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骗取贷款罪,其余六种具体金融诈骗罪没有上述文字是立法功利主义的使然。诚如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林纪东先生所言,“法律是以其极少的条文,网罗极复杂的社会生活,为便于适用和遵守起见,条文固应力求其少,文字应力求其短,以免卷帙浩繁,人们有无所适从之叹”。[1]
金融诈骗罪作为从诈骗罪中分离出来的一种形式,必然兼具金融犯罪和财产犯罪的双重属性,其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一方面侵犯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另一方面侵犯公私财产所有权。[ 2 ]故诈骗罪和金融诈骗罪之间存在法条竞合关系。陈兴良老师一语中的地指出:“包容型法条竞合的两个法条之间的特征之一就是表现为一法条所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在整体上包涵了另一法条所规定的构成要件,在任何情况下,能够为其中外延小的法条所评价的犯罪行为,从逻辑上必然能够为另一外延大的法条所评价。”[ 3 ]有保留的肯定说主张,金融诈骗罪一般要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但如《刑法》第195条规定“骗取信用证的”行为构成信用证诈骗罪就属于“占用型”金融诈骗罪。我国金融诈骗罪中的“诈骗”包括骗取财物型诈骗和虚假陈述型欺诈两种情形。骗取财物型诈骗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而虚假陈述型欺诈则不必具有非法占有目的。[4]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第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否是金融诈骗罪的必要构成要件要素;第二,如果“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金融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要素,其与刑法理论中的主观要素(罪过形式)如何匹配,是故意犯罪的认知内容抑或是意欲的范畴;第三,近几年来的司法解释均是从客观要素(行为骗取财物的事后行为)来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这是否有客观归罪的嫌疑。基于此,笔者试图另辟蹊径分析金融诈骗罪中的主观要素和客观要素,并对传统刑法理论中提出的主客观相一致原则提出自己的见解。本文所要论证的中心观点是,司法实践中客观要素的引入是为克服主观要素所存在的缺陷而进行的一次司法解释适用的努力,要成功地将司法解释中所列举的客观要素加以“激活”,就需要将主观要素与客观要素进行适当的融合。
二、金融诈骗犯罪“非法占有目的”之存在论
在讨论金融诈骗罪之前,必须将目光投向“诈骗罪之树”的主干,即刑法分则第五章中具体罪名之诈骗罪。诈骗罪作为重要的财产犯罪,虽然理论上对其侵害的法益存在“所有权说”与“占有说”之对立,[ 5 ]但是,将“非法占有目的”作为诈骗罪乃至所有取得财物型财产犯罪的共同构成要件却鲜有异议。即便在立法上并非所有国家的刑法典均将其明文规定在刑法条文中,①如我国刑法典将诈骗罪的罪状表述为“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并未规定非法占有目的。与此类似的是《日本刑法典》,条文表述为“人を欺いて财物を交付させた者は”,亦未见“非法占有目的”之踪影。理论上却均坚持“非法占有目的必要说”为通说;实践中,“日本的判例一贯坚持‘非法占有目的必要说’的立场,只不过在不同时期对非法占有目的的内容要求不同”。[6]
(一)条文关系:金融诈骗罪包容于诈骗罪
单从罪名上看,不难得出一个粗糙的结论——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罪之间存在法条竞合关系,诈骗罪是一般罪名,金融诈骗罪是特殊罪名。由此条文关系出发,金融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中理应包括“非法占有目的”。这一结论虽是显而易见的,却并非毋庸置疑。首先,“诈骗罪”是个罪名,而“金融诈骗罪”则是类罪名,包括了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等在内的八个具体罪名,这便要求更为细致地分析,不能大而化之地概括,每一构成要件都是为具体个罪而量身定做的。其次,我国将金融诈骗罪规定在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而非第五章“侵犯财产罪”,于是有学者据此指出,金融诈骗罪的保护法益是金融管理秩序,而不是财产所有权,进而否定了两者的法条竞合关系,提出对此种法益的侵害无需“非法占有目的”亦为可能。[ 7 ]最后,就条文表述而言,整个第三章第五节仅对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规定了非法占有目的,其他金融诈骗罪均无主观要素的明文规定,部分学者因此主张,从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的角度出发,同时考虑到司法实践中打击金融诈骗活动的需要,不将“非法占有目的”作为其主观目的。[8]
笔者认为,首先,提出“金融诈骗罪”是一个类罪名,无法认定其与诈骗罪之间直接存在法条竞合关系的观点固然合理,但这并不妨碍在承认诈骗罪与每一个具体金融诈骗个罪之间存在法条竞合关系之后,进一步认为诈骗罪与整个第三章第五节的罪名存在法条竞合关系。据此,类罪名与个罪名之间的差异事实上并没有排除法条竞合关系的成立。
其次,“金融诈骗罪侵犯的是金融管理秩序而非财产所有权”则存在明显的谬误。诚然,我国刑法分则进行章节划分时主要考虑的因素是犯罪行为所侵犯的法益(或曰犯罪客体),但这一原则在第三章第五节“金融诈骗罪”中存在例外。“我国现行《刑法》顺应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的要求,将包括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票据诈骗罪等在内的八种金融诈骗犯罪从财产罪的一般诈骗罪中分离出来独立设罪,并单独设立‘金融诈骗罪’一节将这八种诈骗罪归入其中。由于金融诈骗罪所包括的八种具体犯罪行为的手段都具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即诈骗的共同特征,因此第五节‘金融诈骗罪’不是按犯罪客体划分的,而是按犯罪手段划分的。”[ 9 ]可以说,刘宪权教授的论述十分清楚地阐明了“金融诈骗罪”并非在对法益的侵犯上区别于普通诈骗罪,而是发生在特殊领域即金融领域的特殊诈骗罪的集合。①刘宪权教授同时针对刑法分则此处的分类进行了十分深刻的批判,认为其既无必要性,也无合理性。具体内容参见刘宪权:《金融犯罪刑法学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9-13页。这并没有否定金融诈骗罪对金融管理秩序的侵犯,事实上在刑法分则诸多罪名中,侵犯双重法益(或者说双重客体)的不在少数。在一般诈骗罪单纯侵犯财产权益的基础上,金融诈骗罪又侵犯了金融管理秩序,这进一步证明了金融诈骗罪与诈骗罪之间存在特殊与一般的法条竞合关系。
最后,因缺乏明文规定而否定“非法占有目的”的观点过于片面。刑法以犯罪构成作为判断犯罪成立与否的标准,而在微观层面,犯罪构成又由具体的犯罪构成要件要素组成。以刑法是否明文规定为标准,可以将构成要件要素分为成文的构成要件要素与不成文的构成要件要素,前者的存在形式毋庸置疑,在适用过程中也不易产生歧义,后者则是指“刑法条文表面上没有明文规定,但根据刑法条文之间的相互关系、刑法条文对相关要素的描述所确定的,成立犯罪所必须具备的要素”。[10]在金融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既存在作为成文的构成要件要素的情况,也存在作为不成文构成要件要素之情形。针对前者,我们可以直接“看见”它;至于后者,我们通过其与诈骗罪间的法条竞合关系,或者根据条文本身的描述②如信用卡诈骗罪中,虽然仅在第四种行为方式即“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中规定了“非法占有目的”,但是这间接提示了其他三种行为方式也必须具备这一目的,否则便失去体系上的协调性。“确认”其存在。
(二)立法技术:隐藏“非法占有目的”的理由
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五节之所以“隐藏”部分犯罪的“非法占有目的”是出于立法技术方面的考量而有意为之,一言以蔽之,第一是为了简洁,第二是为了提示,第三是为了强调。
首先,“简洁”使法典趋于精炼,使条文便于理解,并且给解释学留下了广阔空间,特别是客观目的解释,法律具有滞后性,需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做出相应的调整和修正。然而,“简洁”也是一柄双刃剑,从前文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最终确认金融诈骗罪中普遍存在“非法占有目的”这一“不成文的构成要件要素”,在此过程中也产生了不少疑问与争论,如果立法者“不嫌繁复”地在每一个金融诈骗个罪中予以明示“非法占有目的”,相信理论界与实务界便不会产生如此诸多的烦恼和困扰。因此,简洁本身并不足以支撑这样一种立法模式,必然存在其他理由加以佐证。
其次,隐藏的反面在于“彰显”,我国刑法在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中明确规定了“非法占有目的”,是为了发挥一种提示作用,提示的理由在于这三种犯罪本身的特殊性。第一,针对集资诈骗罪,刑法分则中除去本罪名外,尚且存在三种构成犯罪的非法集资行为,即《刑法》第160条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以及第179条擅自发行股票、公司债券罪,而本罪名与其他三个罪名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有此要求即为集资诈骗罪,没有此要求,再根据行为方式的差异,分别构成上述三种犯罪。[11]第二,针对贷款诈骗罪,刑法分则中除去本罪名外,还设有第175条高利转贷罪和第175条之二的骗取贷款罪,三者均为金融领域中涉及贷款的犯罪,具有很高的亲缘性与相似性。有学者指出,贷款诈骗罪与骗取贷款罪是交叉型的法条竞合关系,同时骗取贷款罪与高利转贷罪之间也存在一种法条竞合关系。[12]其主要区别也在于主观目的方面,“非法占有目的”在此的功能是显而易见的。第三,针对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作用在于明确界定“恶意透支”与“善意透支”之间的界限,同时也为了减少此类犯罪的打击力度,仅对其中超过规定限额或者期限,并且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3个月仍不归还的行为规定为犯罪,经发卡银行一次催收后显然是不再存在善意透支的可能性,3个月的宽限期也体现了刑事立法的谦抑性。
最后,所谓“强调”是指,通过法条表述中的区别对待从而产生直观判断,对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主观方面进行强调,毕竟这三种犯罪的发生率在整个金融犯罪中的比例是较高的,由于刑事立法的模糊性而导致市场经济活动束缚手脚,那在自由和秩序的博弈中过度迁就秩序则有些厚此薄彼了。中小企业融资难在目前的大环境下是不争的事实,如果再悬置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刻提醒那些企业主稍有不慎、前功尽弃,长此以往对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不利的。
三、金融诈骗犯罪“明知”之体系论
明知的内容是按照一般的社会生活常识来确认的,而不能按照法律或者其他专业的知识来衡量,这也正是所谓“外行的平行评价”。[13]风险社会理论提出,工业社会有其自身系统制造的危险而身不由己地突变为风险社会。[14]在认定故意时,通过放弃或放宽意欲要素的要求而将关注重心放在认识因素之上,便成为理论为迎合风险社会之现实需要而被迫做出的应变之举。[15]在行为式的构成要件中,其实质内容是法益侵害危险而不是法益侵害结果,因而只要明知行为具有法益侵害危险而实施的,就应该认为具有故意。只有在结果式构成要件中,其实质内容是法益侵害结果,因而只有对这一结果具有意欲才能构成故意。[16]我们一般认为,刑法总则中的“明知”①《刑法》第14条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是对危害结果的明知,而刑法分则中具体罪名的“明知”是对该罪犯罪对象的明知。
然而随着风险刑法理论的呼之欲出,不少学者将故意这种罪过形式如犯罪分类一般分为行为故意和结果故意,而通说行为犯与结果犯的区别在于:第一,某一犯罪的构成要件中是否要求必须具有法定结果;第二,某一犯罪的既遂标准中是否以侵害结果的出现而成立犯罪既遂状态。其实我们不难发现,既遂与未遂界限的划分依赖于构成要件中是否对法定结果予以明文规定,而除直接故意外,间接故意和过失犯罪均要求行为产生危害结果。由是之故,行为故意对应直接故意,结果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行为故意存在未遂形态,结果故意不存在未遂形态。刑法之所以对有的犯罪作出对象“明知”要求而对有的犯罪则不予明确,主要是基于各种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差异。[17]
纵观金融诈骗罪八个罪名,立法者是从犯罪对象上予以规定的(集资诈骗主要是从行为方式上予以规制的),诚然集资诈骗这一行为一旦成功实施无疑对社会产生风险,社会是人的集合,信誉和信用是人与人之间赖以延续的纽带,我们是否有必要将集资诈骗罪归为行为犯中的行为故意?在结果式的构成要件模式中,构成故意具有对结果的认识及意欲,这是一种结果故意。在行为故意的情况下,认识要素对于故意具有决定性作用,而意欲则被认识所包裹,而隐藏在其身后。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行为故意只要表明认识因素即可,而不要另外认定意志因素。[18]换言之,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多余的,因为集资诈骗的行为故意不需要意志因素中的目的。这一说法明显不妥,如此便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从司法上架空了。风险刑法理论很大程度上是为应对和解释危险犯、持有犯等犯罪类型而应运而生的概念,集资诈骗行为肯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风险较大的非法行为,并且该罪的构成要件中还有数额较大的要求。
笔者认为金融诈骗罪中的“明知”从刑法总则而言,是对行为和结果的知悉,八种金融诈骗罪的行为均是行为人对诈骗行为的明知,即使用隐瞒真相、虚构事实的方法或手段,结果均是被诈骗对象遭受财产损失(银行在多数金融诈骗罪中充当行为人和被害人之间的载体,从表面看是银行被骗,但最终这一损失都由特定的主体来承担,唯独贷款是银行遭受财产损失),且达到数额较大的程度,这一数额较大的客观事实也是判断行为既遂与未遂的重要标准。从刑法分则而言,只有票据诈骗罪中第一款下设第一、二项规定了明知是伪造、编造、作废的汇票、本票、支票而使用的,但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保险诈骗罪中第一款下设第一、二、四、五项均使用了“故意”一词。除集资诈骗外,刑法条文对其余的七种金融诈骗罪均列举了行为方式,其中贷款诈骗、金融凭证诈骗、信用证诈骗、信用卡诈骗和有价证券诈骗在行为方式中都采用“使用……的”模式,这是一种动宾搭配的立法模式,五种犯罪对象都是使用一词的宾语,如采用“使用明知是……的”这一立法用语显然违反语法结构,使用是动词而明知也是动词,两个动词重叠放置语义不通顺。而票据诈骗罪的立法却采用了“明知是……而使用的”的立法模式,在并列结构上同时强调明知和使用这两个行为,此外,票据诈骗罪的规定位于上述五种诈骗罪之前,显然立法者是要强调对于伪造的金融工具必须以明知为前提。[19]
四、“非法占有目的”与犯罪目的之关系论
事实上,“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不仅在金融诈骗犯罪范畴内是一个难题,在财产犯罪领域内同样是一个十分值得研究而又特别难以破解的问题。究其本质原因,乃在于客观与主观之间那难以逾越的鸿沟,或许可以形象地将其表述为“知人知面不知心”。“非法占有目的”是行为人对于通过非法手段实现占有他人财产结果的一种心理期待,是行为人内隐于心的、深层次的思想活动,所以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和模糊性。这导致了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行为人心理事实的准确了解、把握和确定存在一定的难度。并且,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虽然要求在认定行为人构成金融诈骗犯罪时,必须确定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但是由于没有统一的、系统的对于金融诈骗犯罪“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模式,所以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怎样证明“非法占有目的”,以及在刑事诉讼中需要证明到什么程度的难题。
从心理机制上分析,动机→目的→行为→结果,这是一个前后推进的、行为导致结果发生的过程。刑法理论称为断绝的结果犯,日本大塚仁教授则称为直接的目的犯。这种目的通过行为人的构成要件行为本身或者作为其附随现象,自然被实现。德国刑法理论称为缩短的二行为犯,日本大稼仁教授则称为间接的目的犯。为实现这种目的,需要行为人或者第三者实施与其构成要件性行为不同的行为。[20]无论是直接目的犯还是间接目的犯,这里的目的都是独立于犯罪故意的一种主观心理要素。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目的犯之目的称为超过的主观要素。[21]至此,我们不难发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诈骗罪的题中应有之义,立法者将金融诈骗罪从诈骗罪中独立出来形成法条竞合关系,故“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理所应当也是金融诈骗罪的必要构成要件之一。
八种金融诈骗罪中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质疑最大的莫过于信用证诈骗罪中行为方式之一的“骗取信用证”的行为。骗取信用证的行为实际上包含两种情形:一是通过欺骗手段使银行开具信用证(骗开信用证);二是通过欺骗手段骗取他人已经持有的信用证(骗得信用证)。[22]其实,我们可以将之与《刑法》第177条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相比较,该罪中的金融票证包括票据、金融凭证、信用证和信用卡,并且根据传统的牵连犯理论,伪造、变造金融票证后又使用的,是手段行为和目的行为的类型化行为,择一重罪处罚。张明楷教授认为骗开信用证的行为人,是无形伪造的间接正犯,成立伪造金融票证罪(间接正犯)的既遂犯。[23]根据张明楷教授的观点,“骗取信用证”的行为已经被归责于伪造金融票证罪,那我们也可以进一步推断,骗得信用证的行为完全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相当于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主动处分信用证予行为人。笔者认为这是立法的一大失误,我们通过刑法修正案将骗领信用卡的行为规制为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并且在信用卡诈骗罪的行为方式中增加了“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的”,显而易见的是骗开信用证的社会危害性大于骗领信用卡,但在立法上却对后者提前予以规制创设一个新的罪名,而前者却在处罚更为严重的罪名中作为一种行为方式。
诚如上述,德日刑法理论认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和故意之内的犯罪目的是有区别的,前者是故意之外的主观要素,其与客观构成要件中的行为也并非一一对应,而需要构成要件之外的客观行为来证明这种主观要素,所以又称为超过的主观要素。故意之内的犯罪目的与犯罪结果具有密切联系,它是主观预期的犯罪结果,这种目的的客观化就转化为一定的犯罪结果。目的犯之目的与本罪的犯罪结果并无必然联系,它是与故意并存的另外一种主观心理要素。[24]陈兴良教授进一步认为这两种目的存在两种情形:一是不可罚的事后行为;二是因牵连关系而构成牵连犯。但我们一般将伪造货币之后的使用行为视作不可罚的事后行为,却将伪造金融票证后使用的行为定性为牵连犯,其实两者果真有类型上的差异吗?我们把习以为常的个案结论作为刑法学理论,却缺乏对边缘问题的类型化思考和研究,当类似情形被司法实践证实理论的牵强附会时,便套用另一种与之无缝对接的理论抑或将其称为先前理论之例外,需要引起特别的重视。如此,我们沉浸在汗牛充栋的理论中无法自拔,但终究为我们创造的理论所累。
财产犯罪中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往往直接表现为行为人径直取得财物,物都是可以通过估价机构用数字来量化的,钱款又是一般等价物,是最为直观和清晰明了的,而金融诈骗罪中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首先取得的是获得钱款的凭证,相当于买期房中的钥匙,房子尚且还在建造中。根据一般人的观点,钥匙和锁是一一对应的,获取凭证只是暂时的,最终的目的是换取与凭证等价或等值的钱款,正如莘莘学子求学的最终目标是考取名牌大学,因此首先要考取重点高中,但重点高中显然不是终点。但司法实践中的案件却又是具体的,我们首先必须依赖每个案件的客观事实来丈量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其次适用法律来评价行为人的行为,确实也不存在只是单纯地制作“钥匙”的人,夜以继日地重复着同样的动作将这种制作“钥匙”的行为作为目的对待。我们可以将以上过程表述为:伪造金融票证(制作“钥匙”)→兑换金融票证(拿“钥匙”开门)→取得财物(进入房间)→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取得这一空间的所有权)。
五、结论与出路:主观要素与客观要素的融合
传统刑法理论认为目的犯只存在于直接故意中,间接故意是不存在目的犯和犯罪未完成形态的。从心理事实来说,当行为人所放任的结果与行为人所追求的目的不具有同一性时,即二者分别为不同的内容时,二者完全可能并不矛盾地存在于行为人的主观心理中。[25]一言以蔽之,就是对构成要件内的结果持放任态度,而实现了构成要件外的目的。以金融诈骗罪为例,实现了非法占有目的,对被害人遭受的财产损失或者说行为人取得财物持放任的态度。因为间接故意犯罪都是结果犯,存在对结果的意欲,这种意欲就表现为放任。这里的放任,是指对可能发生的结果持一种纵容的态度。相对于希望结果发生的直接故意,间接故意对结果是容忍其发生。[26]其实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在认识层面往往是明知危害结果可能发生,两者在意欲方面存在本质区别,前者是希望,后者是放任,而明知危害结果必然发生这种情形在司法实践中很难证明行为人绝对的认知程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金融诈骗罪的司法解释是从行为人使用资金的行为方式来反推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如行为人为了将生意做大而向银行骗贷,其生意成功后就将所贷钱款悉数归还,我们是不可能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但如果行为人生意失败,我们却完全可以“明知没有归还能力而大量骗取资金的”将其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或许有人质疑为何不定骗取贷款罪。我们将行为人做生意改为为了大规模走私,走私成功后依然如数归还贷款,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使用骗取的资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恐怕还是能够认定其具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如果走私失败更是有恃无恐。
综上,使用骗取的资金进行合法活动的,及此其实已经构成骗取贷款罪,如果合法活动失败、人财两空的话,构成贷款诈骗罪似乎也是情理之中;使用骗取的资金进行非法活动的,直接以贷款诈骗罪定罪处罚。在上述几种情况下,骗取贷款进行合法活动,但合法活动失败而构成贷款诈骗罪的情况就是典型的以危害结果苛责,行为人在主观上很难说是直接故意,但间接故意有理有据,明知可能经营失败而无法归还贷款,依然固执己见骗取贷款,最终血本无归。
主观要素和客观要素的融合只有在消极的事实层面才有可能性。所谓消极的事实层面是指最大限度地避免错判和误判,即轻罪重判或无罪轻判。对“占有目的”具体含义的解释,完全可以从证据链和客观情形的因果关系中来甄别和印证行为人的主观内容,金融诈骗罪中的故意认知是显而易见的,但直接故意的意志层面需要在事实和证据中来发现线索佐证和强化行为人的意识。最高人民法院行为列举式的司法解释是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前提,侦查和检察机关需要在此基础上形成证据链和符合客观事实的因果关系的法律逻辑,还原行为人的主观内容,非法占有目的可以反映出行为人通过实施特定金融诈骗犯罪行为直接追求某种犯罪结果的完整心理态度,将“非法占有目的”的标准与“隐瞒、欺诈”的表现形式进行适度的“嫁接”,这或许是此种融合的有益尝试。
参考文献:
[1]林纪东.法学通论[M].中国台湾远东图书出版公司,1953:89.转引自张明楷.保险诈骗罪的基本问题探究[ J ].法学,2001,(1).
[2]刘宪权,吴允锋.论金融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 J ].法学,2001,(7).
[3]刘宪权.金融犯罪刑法学新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439.
[4]卢勤忠.金融诈骗罪中的主观内容分析[ J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1,(3).
[5]于志刚,郭旭强.财产罪法益中所有权说与占有说之对抗与选择[ J ].法学,2010,(8).
[6]张明楷.论财产罪的非法占有目的[ J ].法商研究,2005,(5).
[7]罗欣.关于金融诈骗罪的两个问题[ J ].法律研究,2000,(9).屈学武.金融犯罪主观特征解析[ J ].法学杂志,2004,(1).
[8]顾晓宁.简析票据诈骗罪的主观要件[ J ].中国刑事法杂志,1998,(1).屈学武.金融犯罪主观特征解析[ J ].法学杂志,2004,(1).
[9]刘宪权.金融犯罪刑法学新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9.
[10]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M].法律出版社,2011:125.
[11]侯婉颖.集资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司法偏执[ J ].法学,2012,(3).
[12]刘宪权.金融犯罪刑法学新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220.
[13][德]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M].许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356.
[14][德]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M].吴英姿,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102.
[15]劳东燕.犯罪故意理论的反思与重建[ J ].政法论坛,2009,(1).
[16]陈兴良.刑法中的故意及其构造[ J ].法治研究,2010,(6).
[17]卢勤忠.金融诈骗罪中的主观内容分析[ J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1,(3).
[18]陈兴良.教义刑法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434.
[19]卢勤忠.金融诈骗罪中的主观内容分析[ J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1,(3).
[20][日]大塚仁.刑法概论(总论)[M].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24.
[21]陈兴良.目的犯的法理探究[ J ].法学研究,2004,(3).
[22]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M].法律出版社,2011:711.
[23]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M].法律出版社,2011:711.
[24]陈兴良.目的犯法理探究[ J ].法学研究,2004,(3).
[25]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M].法律出版社,2011:276.
[26]陈兴良.刑法中的故意及其构造[ J ].法治研究,2010,(6).
Comment on Subjective Aspects of Financial Fraud
Li Hongjie, Bao Xinze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0042, China)
Abstract:The purpose of illegal possession as subjective contents is essential to the determination of financial fraud, which is not only the embodiment of legislative technology, but also a sign that reasonably differentiates one crime from another in judicial practice. Deliberateness of fi nancial fraud involves criminal behaviors and results, which constitutes direct intention, namely the whole process of direct pursuit of certain criminal results. Meanwhile indirect intention consists in letting it happen. The determination of financial fraud covers such factors as subjective elements, behaviors of illegal possession, chain of evidences of offenders’ specifi c implementation and legal logic of cause and effect.
Key Words:Financial Fraud; Purpose of Illegal Possession; Knowingly; Purpose of Crime
作者简介:李宏杰(1991—),男,白族,云南人,华东政法大学2013级刑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刑法学;鲍新则(1990—),男,回族,上海人,华东政法大学2013级刑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刑法学。
收稿日期:2015-02-05
DOI:10.13643/j.cnki.issn1008-5750.2015.03.009
文章编号:1008-5750(2015)03-0066-(09)
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D9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