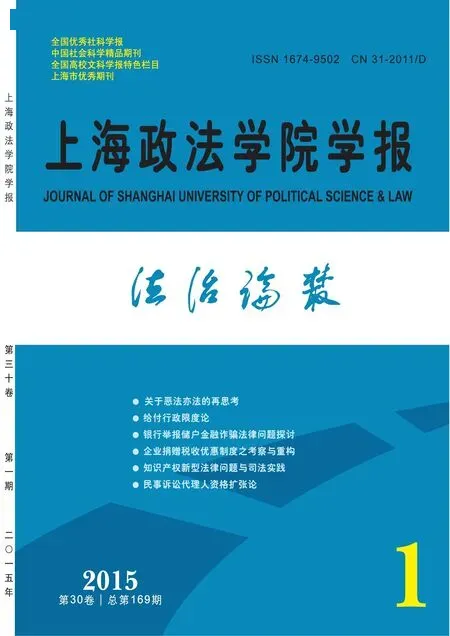关于恶法亦法的再思考
牟治伟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长沙 410007)
关于恶法亦法的再思考
牟治伟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长沙 410007)
恶法亦法还是恶法非法,自古及今,这都是一个永恒存在的问题。通过对安提戈涅和苏格拉底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形象的描述,探讨了恶法非法和恶法亦法的理由。恶法非法的理由是存在着一个衡量法律善恶的更高的标准,不符合这个更高标准的法就不是法律。恶法亦法的理由是将法律作为衡量自身公正与否的惟一标准,法律的存在与法律的好坏是两个不同的评价标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之间存在着不可跨越的鸿沟,不能以法律之外的价值标准来否定法律的实际存在。恶的法律也是法律,不仅意味着一种秩序要求,而且可以在承认现存法律的基础上保持一种对法律的批判态度,从而促进法律的进步。由于人类理性的有限性,恶的法律的存在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恶法亦法与恶法非法之争所揭示的是背后法价值中安全与正义之间的紧张冲突。本文认为,应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尊重法的安定性。法律只要是经过正当法律程序制定的,就应该得到遵守和服从,即使这种法律在内容上有可能是坏的。
神法;国家法;恶法;理性;正义;安定性
一、两种法律秩序——安提戈涅的故事
安提戈涅是古希腊悲剧家索福克勒斯笔下的一个女主人公,国王克瑞翁禁止人们为安提戈理的哥哥举行葬礼,因为他生前违反了国家的法律。然而,安提戈理并没有理会克瑞翁国王颁布的法律,勇敢地埋葬了她的哥哥。安提戈理的行为使克瑞翁国王大为恼怒,并要求她说明理由,安提戈理说道,她所违反的只是克瑞翁的法律,而不是不成文的法律。
“希腊人曾把葬礼看成是神法的命令,违反者将会遭到神的惩罚性报复”。①[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安提戈理才毅然无视克瑞翁的法律。在这里,安提戈涅以更高一级的法律来对抗克瑞翁国王的法律,并宣称因为国王的法律与神法相冲突,因而无效。
从安提戈涅的言行中可以看出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法律秩序,一种是以国家法为代表的法律秩序,另一种是以一种更高级别的法为代表的法律秩序。当这两种不同的法律秩序发生冲突时,人们就面临着是服从国家法还是更高级的法的一种价值选择。国家法作为国内的一套法律秩序,理应得到人们的遵守与服从,否则,若由个人肆意违反,妄加践踏,人人都可以对其效力提出质疑,进而拒绝服从,那么法的权威与尊严势必荡然无存,法的稳定性亦必随之动摇,由法律所维持的安全与秩序必定不复存在。国家的法律可能具有保守、滞后、不一致、相互矛盾的地方,然而,它毕竟可以让你在它的庇护下过着可预期的稳定生活。没有这样的一种稳定的法律秩序,人们就会感到无所适从,整日生活在充满着各种意外、不确定性和危险的环境之中。
也许在安提戈涅看来,她只是凭着神刻画在她心中的法律与血浓于水的亲情而去埋葬她亲爱的兄长,自己的行为具有不容置疑的正当性,这种正当性即使国家的法律也不能加以否认和拒绝。当安提戈涅不得不在遵守国家的法律与内心的道德情感之间作出选择时,她不假思索地选择了依据自己心中的道德感情来行事。可是,正是这样的一种选择将国家的法律视若无物,使国家的法律秩序面临崩溃的危险。
试想,倘若每个人都以国家的法律不符合自己内心的道德情感为由而拒绝遵守,那么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存在着一种稳定的法律秩序。因为作为单个的人,其内心的道德或者正义感必然是主观的、不确定的、模糊不清的甚至相互矛盾的,而法律则是具体的、普遍的、一致的、公开的因而是可预期的,以不可名状的更高的法律来取代现行的、具体的、公开的法律,最后的结果就是人们的行为失据。安提戈涅在私人感情的驱使下,置整个国家法律秩序于不顾,妄借神法来否定国家的法律。然而,神法是什么?这并不是黑纸白字,一清二楚的,试图以人之有限理性来窥视神法之精微奥妙,真可谓是不自量力。既然神法无迹可寻,势必因人而异,每个人皆可各执一词,声称自己理解的法就是神法。倘若如此,那么克瑞翁国王也可以声称其国家法就是神之理性与意志的真正体现。可见,安提戈涅妄图借神法以对抗人法,虽言之凿凿,然其理则漏洞百出。对此,安提戈理也许会借后来的西塞罗之口辩解到:
“真正的法律乃是一种与自然相符合的正当理性,它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并且是不变而永恒的。通过命令的形式,这一法律号召人们履行自己的义务;通过它的禁令,它使人们不去做不正当的事情。它的命令和禁令一直影响着善良的人们,尽管对坏人无甚作用。力图变更这一法律的做法是一种恶,试图废止其中一部分的做法也是不能容忍的,而要想完全废除它的做法则是不可能的……。罗马的法律和雅典的法律并不会不同,今天的法律和明天的法律也不会不同,这是因为有的只是一种永恒不变的法律,任何时候任何民族都必须遵守它;再者人类也有一个共同的主人和统治者,这就是上帝,因为它是这一法律的制定者、颁布者和执行法官。”①[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18页。
克瑞翁国王的法律是如此地违背人的理性和良知,因此不应该得到遵守与服从。安提戈涅不会看着哥哥的尸体被鸟兽啄食而无动于衷。虽然神的法律不像人法那样清楚可见,但是人应该爱自己的亲人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实了,人凭着自己的良心可以很容易地感觉得到,这是比白纸黑字的国家法更清楚不过的了。法律是用来维护社会秩序的,但是这套秩序应该是与人的理性相契合的,倘若法律已沦为一套逆情背理的僵死教条,倘若法律违背了人类最基本的生活伦情,那么这样的法律就不具有法律的本性,就不应该得到遵守与服从。
在这两种法律秩序的冲突中,究竟应该选择服从哪一种法律?坏的法律是否构成人们不服从法律的理由?对此,也许我们应该认真对待200多年前潘恩对待坏的法律时所发表的意见:
“假使有一项坏的法律,那么,反对实施这项法律是一回事,但是去揭露它的过错,推论它的不当以及阐明为什么应该加以废除或为什么必须用另一项法律来代替,便完全是另一回事。
对于一项坏的法律,我一贯主张(也是我身体力行的)遵守,同时使用一切论据证明其错误,力求把它废除,这样做要比强行违犯这条法律来得好;因为违反坏的法律此网一开,也许会削弱法律的力量并导致对那些好的法律肆意违犯。”①[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18页。
潘恩认为,只有遵守坏的法律,才有可能避免人们去违反好的法律。只有在法律存在的情况下,才谈得上对法律的批判与改进。如果每个人都可以依据自己的主观感情来随意地否定现存的法律,这只会导致法律秩序本身的崩溃并损害到自己及其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因为当一个国家不存在法律秩序时,人类将不得不遵守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这无论如何是法律秩序的否定者所不愿意看到的。因此,我们应该最大限度地遵守国家的法律,即使它可能对你来说是不公正的。苏格拉底正是以生命来捍卫法律权威和尊严的最好范例,苏格拉底通过行为向后世表明了:即使是坏的法律也应该得到遵守与服从。
二、恶法亦法——从苏格拉底的审判说起
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因被控告腐蚀青年人的心灵,相信他自己发明的神灵,而不相信国家认可的诸神被判处死刑。临刑前,老朋友克里托去监狱探望他,并劝说他越狱逃走。克里托对苏格拉底说,雅典的法律是不公正的,没有必要服从这样的法律。苏格拉底拒绝了好朋友的劝告,认为拒绝服从国家的法律是一种罪恶,因为这会摧毁法律和整个国家。苏格拉底说道:“如果公开宣布的判决没有效力,如果人人都可以违反城邦的法律,这个城邦还会继续存在吗?”①[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一卷·申辩篇》,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4页。苏格拉底认为,他从出生起就受到城邦法律的保护和教育,并享受了法律带给他的所有好处,法律就是他的父母和卫士。不仅如此,法律还是公民和城邦之间签订的一种契约,不服从法律就是违背了自己和城邦之间签订的契约。这种背信的行为本身是一种罪恶,因为它摧毁了国家的法律。苏格拉底认为,如果法律不公正,作为公民完全可以自由地离开这个城邦,到别的法制下生活,但他终身也没有离开过雅典城邦。既然他选择了在雅典城邦下生活,就应该遵守这个城邦的法律,不能因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就拒不服从城邦的法律。②同注①,第46页。
苏格拉底不惜牺牲生命也要遵守城邦的法律的行为,为后世树立了一个不可磨灭的守法公民的形象,他向后人昭示了“守法即正义”、“宁愿忍受不正义也绝不做不正义的事”的精神,阐释了公民为什么要遵守法律的理由。法律尽管存在不公正的地方,然而,它毕竟为我们提供了安定的生活环境,保护了我们的成长,使我们的生命、财产不会遭受到任意的侵犯。苏格拉底的这种精神和态度成为后来的法律实证主义者津津乐道的话题。法律实证主义的鼻祖霍布斯认为,法律是公民与主权者之间所立的契约。在自然状态,由于不存在一个共同权力使大家慑服,人与人之间就处于一种相互为战的战争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不存在正义与非正义之分。“是和非以及公正与不公正的观念在这儿都不能存在。没有共同权力的地方就没有法律,而没有法律的地方就无所谓不公正。”③[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96页。为了抵御外来侵略和制止相互之间的侵害,人们订立契约,将自己在自然状态中的所有权利都交给一个主权者行使。主权者的权力则是不受任何限制的。主权者的职责在于寻求和平和保障人们的安全。法律就是人们彼此之间订立的契约,正义包含在“所订契约必须履行”这一自然法中。由于主权者是所有订约之人的人格的承当者,所有订约之人都是主权者行为的授权者,所以主权者的一切行为都是符合订约之人利益的。
“主权者所做的任何事情对任何臣民都不可能构成侵害,而臣民中任何人也没有理由控告他不义,因为一个人根据另一个人的授权做出任何事情时,在这一桩事情上不可能对授权者构成侵害。既然像这样按约建立国家之后,每一个人都是主权者一切行为的授权人。因此,抱怨主权者进行侵害的人就是抱怨自己所授权的事情,于是便不能控告别人而只能控告自己。甚至还不能控告自己进行了侵害,因为一个人要对自己进行侵害是不可能的。”①[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36页。
在霍布斯看来,唯有主权者能充当立法者,而正义就是符合法律的规定,因此法律不可能是不公正的,因为法律就是关于正义与非正义问题的法规,法律就是衡量正义与非正义的惟一标准。②同注①,第206页。霍布斯认为,人类的事情绝不可能没有一点毛病,人们的生存状况也不可能没有弊端,但是因为这些毛病和弊端而拒绝服从国家的法律,那么所造成的危害将为祸尤烈。霍布斯说道:“任何国家之中最大的弊端却不是由于臣民不服从和破坏建立国家的信约而来的。”③同注①,第161页。既然法律就是衡量正义的惟一标准,那么就没有恶法非法之说,所有的法律都是正义的,法律就是衡量善恶的惟一标准,法律就是公众的良知意识。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不是将法律作为衡量自己行为善恶的标准,而是以个人的良知意识作为判断善恶的标准,国家就必然要陷入混乱。因为个人的良知意识不仅可能是错误的,而且是分歧复杂和模糊不清的。④同注①,第252页。
以奥斯丁为代表的法律实证主义者在继承霍布斯思想的基础上,将法律的存在和法律的好坏区分开来,认为“法的存在是一个问题。法的优劣,则是另外一个问题。法是否存在,是一种需要研究的问题。法是否符合一个假定的标准,则是另外一种需要研究的问题。一个法,只要是实际存在的,就是一个法,即使我们恰恰并不喜欢它,或者,即使它有悖于我们的价值标准。”⑤[英]约翰·奥斯丁:《法理学的范围》,刘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08页。奥斯丁明确将法律的存在与对法律的价值判断区分开来,认为法理学的对象是实际存在的由人制定的法律,而对法律的评价,则是属于伦理学或政治学方面的范畴。在奥斯丁之前的功利主义思想的创始人边沁就曾明确说道:
“可以把对法律问题发表意见的人分为两类:解释者和评述者。解释者的任务是向我们说明他所认识的法律是什么;评论者的任务则是向我们评述法律应当是怎样的。因此前者的任务主要是叙述或探讨事实;而后者的任务则是探讨理由。解释者在他的范围内涉及的思维活动只是了解、记忆和判断;而评论者则由于他所评论的事情有时牵涉到那么喜欢与不喜欢的感情问题,所以要和感情打交道。”⑥[英]边沁:《政府片论》,沈叔平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96页。
边沁在此将对法律的解释与对法律的评论严格区分开来,认为前者涉及的是“法律是什么”的问题,因此法律解释者应该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后者涉及的则是“法律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因此法律的评论者则应该是一个世界公民。边沁将法律是什么和法律应该是什么区分开来,认为在一个法治的政府之下,善良公民的座右铭就是“严格地服从,自由地批判”。⑦同注⑥,第98页。
将对法律的事实性陈述与价值判断区别开来,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法律。法律是否存在,这是一个事实判断的问题;而法律的好坏则属于价值判断的层面。我们不能因为说这是一个坏的法律,就否定它的存在,说它不是法律。
在恶法是不是法律的问题上,后来的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家哈特把这一问题归因于人们采用了不同的法律概念的缘故。哈特认为,自然法学派所采用的是狭义的法律概念,只有良法才是法律。“如果我们采用了广义的概念,就会使我们在理论探讨中将下列所有规则都归在一起,并视为法律”,在他看来,采用狭义的法律概念不但一无所获,而且还会“导致我们把即使展现出法律的所有其他复杂特征的规则,都一概加以排斥。将这种规则的研究留给其他学科的建议,除了混乱以外,肯定不会有别的结果。”①[英]哈特:《法律的概念》,张文显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5页。
自然法学派坚持恶法非法,坚持法与道德不可分离,认为法律必须符合最低限度的道德诉求,法律实证主义者坚持将法与道德分离开来,认为只有将法与道德分离开来才能使法律不受各种意识形态的影响,也才能真正地保持道德批判的武器。坚持“恶法亦法”并不是意味着一定要遵守它们,正如哈特所说的,“这是法律,但它们是如此邪恶以至于不应该遵守和服从。”②同注①,第203页。混淆法律与道德,断言法只有符合某些道德原则才是法,必将导致盲目服从或错误反对法律秩序。因为一方面,只有符合正义、道德的法律才是法的另一种表达,就是:法是符合正义、道德原则的。这就会使人们相信除了“恶法”外,所有的法律都是正义的,都是完美无缺的,无需作任何改革,这样的话,法律的发展必定会停滞不前,人们也会盲目地支持现有的法律秩序。另一方面,关于法律正义与否的问题,也是一个仁者见仁的问题,由于并不存在一种令所有人都乐意遵循的正义的、道德的原则,每个人的道德观念也是千姿百态的,法律究竟应该符合哪些人的道德,这些都不能通过理性来解决。倘若法律体现了一些人的正义观念和道德原则,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些不符合他们所认可的正义观念和道德原则,那么这就会出现无政府状态的危险。再者,正如自然法学派所声称的,实在法只是人们的理性所发现的正义原则的体现,立法者并非是在创制法律,而是凭借人的理性发现已经存在的符合人之本性的自然法。如果正义能客观地为人的理性所认识,那就根本不需要实在法,既然一方面肯定正义是存在的,另一方面又说它不能明确地加以规定,那么这种讲法本身就是矛盾的。
三、“恶法亦法”的理由
(一)价值与事实的二元对立要求坚持恶法亦法
根据著名的“休谟定理”,从纯粹事实性陈述出发,不可能推论出任何规范性命题,规范与事实之间存在着严格的对立。道德上的善恶并不是理性思考的结果,而应属于价值判断的范畴。③[英]休谟:《人性论下》,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08~509页。规范属于“应然”范畴,而事实性陈述则属于“实然”领域,规范性命题最终只能通过其它规范性命题而获得“理由”。例如,如果说某人杀了人应该处死,那么这是因为人们预设了一个杀人应该处死的规范性陈述,而这一规范性陈述又是基于人的生命应该得到保护这一更高价值的规范性陈述中获得理由的。简言之,事实陈述是“客观”的,而规范与价值的来源则是主观的;主客观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以致不能在逻辑上从一种类型的陈述自动过渡到另一种类型的陈述。
作为一种事实判断,存在着真伪之分;作为一种价值判断,则没有对错之别。“真伪之判断根本有别于善恶之判断。后者正是价值判断之通常表述方式。‘真’仅表明符合事实,而非符合预设之价值。真伪判断判明某事实存在与否,此判断不受判断者好恶影响,并可由经验检验,在此意义上其具有客观性而受理性之控制。……价值判断不应与对多数人实际上选择个人自由这一事实之陈述混为一谈,后者乃是事实陈述,自有真伪可言。若多数人认为个人自由优于社会保障之陈述为伪,则相反陈述即为真,后者便在逻辑上排除了前者;但其不能排除个人自由尽管不为多数人所重,但仍为最高价值,因而‘优于’社会保障这一价值判断。价值判断不与事实判断相矛盾。唯其如此,此判断才是特定意义上之价值判断,就此而言,事实与价值总是两个不同领域。”④[奥] 凯尔森:《纯粹法学》,张书友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396页。爱因斯坦也认为,科学只能断定是什么,而不能断定应该是什么,“有关是什么的知识并不直接打开通向应该是什么之门。”⑤[美]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晚年文集》,方在庆、韩文博、何维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页。由此可见,实证主义法学者主张“法律的存在是一回事,它的好坏又是另外一回事”,这是将对法律的事实判断与对法律的价值判断区分开来的科学方法;而自然法学派则主张只有良法才是法律,这是一个价值判断,主张法律应符合某种主观的价值标准,而所谓的价值标准则属于“应然”的范畴。根据“休谟定理”,自然法学派混淆了规范与事实之间的严格对立,将法律的事实陈述与价值判断混为一谈,企图以某种主观的价值判断来决定法律的存在与否,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倘若坚持说“恶法非法”,则会得出“恶人非人”的荒谬结论。
(二)法律的稳定与发展要求坚持恶法亦法
当我们在谈到一项法律是好是坏时,主要是指该项法律的内容是否符合人们心中的道德感情和正义观念。也就是说,坏的法律至少也具有某种程度的形式合理性,如符合法律的普遍性、一般性、公开性、一致性、平等性等形式特征。在人们的价值观念上被视为是坏的法律,违背人们的朴素正义理念的法律,至少可以维持一种稳定的秩序,使人们在行为的时候具有一定的可预期性。法治在某种程度上依靠的正是规则所具有的可预期性。正如哈耶克所说的:“撇开所有技术细节不论,法治的意思就是指政府在一切行动中都受到事前规定并宣布的规则的约束——这种规则使得一个人有可能十分肯定地预见到当局在某一情况中会怎样使用它的强制权力,和根据对此的了解计划自己的个人事务。”①[英]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冯兴元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3页。人们可以根据事先公布的规则的指引来安排自己的行为而不必担心自己的行为会遭到无端的否定。倘若直接否定坏的法律,法律自身的稳定性势必受损,人们的行为也会失去凭借。法律所带来的秩序还可以防止专制者根据自己的意志任意行事,不仅法律朝令夕改,而且使人们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否会受到惩罚。因为意志的反复无常根本没有任何形式的可预期性,人们不管做什么,都有可能受到专制者意志的惩罚。②刘星:《西方法律思想导论》,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43页。坏的法律虽然会给人们的行为带来不便,甚至会导致一些不公正的结果,但是,相对于直接否定法律的效力从而使法律变得不确定性而言,坏的法律的好处依旧大于随意否定法律后的无法无秩序状态。
(三)人类理性的有限性要求坚持恶法亦法
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必然会存在着坏的法律。承认坏的法律也是法律,可以使我们将法律与道德、好的法律与坏的法律明确地区分开来。这样,人们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到现存法律所具有的缺陷,并努力去改善现在的法律,使其朝着正义的法律迈进。如果认为坏的法律不是法律,那么就意味着现实中存在的法律都是符合公平和正义理念的法律了,那么法律就丧失了任何改进的机会了。将符合道德性质的法律作为法律存在的必要条件,势必会使法律蒙上一层道德的神圣光环,从而阻碍法律的进步和发展。③同注②,第205页。相反,坏的法律也是法律,将法律的存在和法律的好坏作为两个不同层次的客体来进行评说。“坏的”法律也是实际存在的法律,但是因为它是“坏的”法律,所以我们可以对它进行批判、指责、改进,从而使“坏的”法律可以通过我们的努力变成好的法律。“恶法亦法”所体现出的不完善的法律秩序正是法律得以变得更加公正更加文明更加理性的前提。由于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和可错性,使得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制定出一整套完美无缺的法典,因此法律总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毛病,甚至于还存在着重大的缺陷,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事实,如果认为坏的法律不是法律,这不仅超出了人类理性的限度,而且还有可能导致人类理性的滥用,使人类误以为可以凭借其自身的理性去任意地设计出的一整套完美的理想蓝图,从而将人类带入其自身设计的锁链之中。“理性仅仅是一种戒规,亦即对成功行动之可能性的限度所达致的一种洞见,因此它往往只是告诉我们何者不能做。这种戒规之所以是必要的,完全是因为我们的智识无力把握实在的全部复杂性所致。”④[英]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37页。正因为我们的理性有所限度,正因为我们的知识无力把握实在的全部复杂性,恶法亦法才有其存在的空间。或者可以换句话说,恶法亦法必然存在,因为人类理性永远无法穷尽事物的本质。
四、“恶法亦法”——正义与法的安定性之间的冲突与协调
在“恶法亦法”与“恶法非法”的争论中,更深层次的冲突在于各自所追求的法律价值不同。“恶法非法”的主张者要求法律必须符合最低限度的道德和正义原则,违背人类基本良知和道德情感的法律不具有法的本性,因此不能称作法律。正如拉德布鲁赫所说的:“可能有些法律,其不公正性、公共危害性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它们的效力,它们的法的本性,必须被否定。”①[德]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法律智慧警句集》,舒国滢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59页。法律实证主义者则认为,法律就是法律,法律自身的安定性及其法律所象征的秩序的安定性具有最高的价值。在法律实证主义者的眼中,正义并不是衡量法律公正与否的客观标准,相反,正义只能是法律下的正义,即合法性。正是因为法律的出现才有了正义,而非先有了一个正义的理念后才根据这个理念制定了正义的法律。
法律实证主义者将正义与法的安全性都纳入法律的怀抱,认为正义只能是法律下的正义,离开了法律根本无正义可谈。因此法的安定性就成为法律首要实现的价值,不可能存在正义与法的安定性之间的冲突,因为正义就是合法条性,而法律又是安定与秩序的象征,由此可以推断出法的安定性也是正义的一部分。而自然法学派则以某种抽象的正义观来评价法律,认为不符合这种正义观的法律的效力必须被否认。这样,在正义与法的安全性之间就不可避免地会存在着一种紧张的冲突。
在正义与法的安定性的问题上,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的态度值得我们深思。在二战以前,拉德布鲁赫认为,正义只是法律的第二大任务,法律的第一任务是法的安定性,也就是秩序和安宁。拉德布鲁赫引用歌德的话说道:“比起忍受无规则,我更愿意经受不正义”,“在你身上发生了不公正的事,也比全世界都没有法律要好。”②[德]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法哲学》,王朴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85页。在亲历了二战期间纳粹的暴行后,拉德布鲁赫改变了他对法的价值的排序,将正义放在了第一位,而将法的安定性放到了第二位。拉德布鲁赫认为纳粹的法律由于有意否认了构成正义核心的平等原则,因此根本不具有法的本性。
在面对正义与法的安定性之间的冲突时,拉德布鲁赫在原则上还是主张尊重法的安定性,认为实证的、由法令和国家权力保障的法律有优先地位,即使在内容上是不正义或不合目的性的。只有当实证法与正义之间的矛盾达到了一个如此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以至必须通过否定作为“不正当的法”来寻求正义时,拉德布鲁赫才承认否定法的效力。即使如此,在满足正义要求的同时,为尽可能少地伤害到法的安定性,拉德布鲁赫认为并非每个法官都应该被许可自行草拟法律,这项任务应该交由一个更高级的法院或者立法机关来掌有。③同注②,第232~234页。
恶法亦法最大限度地维护了法自身的安定性和国家秩序的安定性。“恶法”只要是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制定的,就应该得到普遍的遵守和服从,对它的否定与废弃也只有通过同样的方式来进行。这里所谓的正当的法律程序,是指:一般法律的制订必须经过51%的议会多数才能通过,然而,为避免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压迫,必须存在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多数通过的法律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符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形式法治原则;二是51%的多数的形成符合“对于所有可以设想的意见、流派和运动来说无条件地达到多数的机会均等的原则”。④[德]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概念》(合法性与正当性),李秋零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4页。若承认人们有权随意否定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无异于是在说每个人都是直接的立法者,都只服从自己认为是正确的法律。这样,国家的法律秩序就会变得极度不稳定,人们随时都可能生活在一种“无法”的状态之中。
诚然,法律可能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坏的地方、甚至于违背了人们公共的正义感情,对这样的法律,人们可以公开地、自由地、和平地批判它、指责它甚至于采取非暴力的方式反抗它。①非暴力反抗是一种公开的、非暴力的、既是按照良心的又是政治的对抗法律的行为,其目的通常是为了使政府的法律或政策发生一种改变。[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64~365页。通过这种方式促使立法机构去认识到法律的缺陷并最终改变或者废除该法律,这不仅表达了对法律的忠诚,而且也维护了法的安定性。“我们必须寻求正义,同时注重法的安定性,因为它本身就是正义的一部分。”②[德]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法哲学》,王朴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36页。法律必须符合正义、理性、自由,这不是守法者和执法者借以评价法律善恶的理由,而是说立法者在立法时,必须以正义、理性和自由作为法律的价值追求。立法者应该是仁慈的、温和的、宽大的、人道的,法律则应当是铁面无私的,每一具体案件中的执法者也应当是铁面无私的。③[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60页。恶的法律也是法律,因为法律是一种事实存在,我们不能因为它是“恶的”而说它是不存在的。恶的法律只要具有法的普遍性和一般性,就应该得到遵守和服从。因为,诚如施密特所说:“时至今日,法律——作为一项具有实质合理性、公正和理性的规定——的所有其他特征都已经相对化并且变得很成问题了;对理性法的自然法信念以及法律中的理性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荡然无存了。如果说国民法治国尚未彻底沦为变化不定的议会多数的专制主义的话,它所依靠的不过是事实上还存在的对法律普遍性的那一点点残余的尊重而已。这并不是对实质意义上的法律的充分的、详尽的界定,但它确实是一般的、逻辑的、不可避免的最低要求。法律也许很糟糕,很不公正,但是,由于法律具有普遍性和抽象性,这种危险就减少到了最低限度。法律的保护作用、甚至法律的存在理由本身都在于这种普遍性。”④[德]卡尔·施密特:《宪法学说》,刘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68页。
(责任编辑:马 斌)
DF02
A
1674-9502(2015)01-001-08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4-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