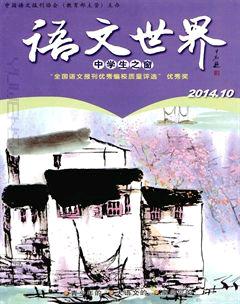一种长寿几百岁的婚姻制度
单之蔷
许多生物活着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长寿,而是为了繁殖。繁殖完,它们的生命似乎就没有了意义,因此很快就会死去。
在内蒙古正蓝旗境内一个无名湖泊边的草地里,数不清的蓝色的豆娘伏在草叶上,仔细看,会看到它们一对一对地正在交配,雌雄二者围成一个心形的造型,很美。受到扰动,它们飞舞起来,好像一阵迷雾。其实我们不应该干扰它们,因为这是它们一生最辉煌的时刻,过不了几十个小时,当它们把卵产在水里后,它们就会死去。豆娘的稚虫会在水中呆上一两年,才顺着水草爬出水面,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它们褪去外壳,羽化成为美丽的豆娘,迎来交配繁殖的那一刻。
蜉蝣,朝生暮死。朝生,性成熟;暮死,繁殖后。
蝉的幼虫在地下一住多年,长的可达13年以至17年之久。这一切的等待与准备,仅为一个短暂的繁殖期。夏季出土后,雄蝉爬到树上不懈地鸣叫,目的是吸引雌性来交配,当秋风起时,它的生命就结束了。
在加拿大落基山中的一条河中,我看到成群的鲑鱼逆流而上,穿越险滩去产卵。产卵后,河中漂满了死去的雌鱼。
活着是为了繁殖。极端的例子还有螳螂,当雄螳螂爬到雌螳螂背上开始交配时,雌螳螂开始吃丈夫的身体——当然是先吃头,如果是先吃下面,那螳螂这个物种就不存在了。
为什么会是这样?按照时髦的社会生物学的解释:生物的个体只是运载基因的一个机器,是基因为了达到复制自己的目的而临时组建的一个工具。基因生存的全部或者说唯一的目的,就是不断复制自己。豆娘、蜉蝣、蝉、鱼、螳螂作为个体死去了,但是它们的基因却传播下去了,基因的目标达到了。它们从其寄存的一个生物个体转移到了另一个个体后,就抛弃了前面的寄主。基因是不朽的,而寄存基因的生命是随时可以抛弃的外套。
人能摆脱这样的命运吗?我认为人已经依靠自己创建的文化摆脱了受基因摆布的宿命。人活着可以不为了繁殖,不为了传播基因,人能够追求许多高尚的目标。人已经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譬如长寿就是人对抗自私的基因所取得的一个成果,或者说是文化战胜自然选择规律的一个例证。
一份欧洲人各个历史时期的平均寿命表说明了这一点:青铜时代,18岁;古罗马时代,29岁;文艺复兴时期,35岁;18世纪,36岁;19世纪,40岁;1920年,55岁;1935年,60岁;1952年,68岁。
这份表的开始和结尾很有意义。青铜时代,18岁,平均寿命刚刚超过性成熟期;1952年,68岁,这已经超过了女性更年期的年龄。
从基因的角度看,生物生存的全部目的,就是不断地复制自己,繁殖就是一切生物的目的,但人摆脱了“基因复印机”的命运。如今,上海人、北京人的预期寿命已经超过了80岁,很多人虽早已不能生育,却仍幸福地活着。
为什么要把繁殖与长寿扯在一起,因为在生物界,这两个问题的确是紧密相联的,前面的例子说明了这一点。豆娘、蜉蝣、蝉、螳螂,它们无法改变命运,只能听从基因的摆布。但是人类是个例外,人类可以通过文化对抗基因的计划。
比如,人不想生完就死,在环境、饮食、运动、卫生、医疗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努力,收效很大;其实还有收效更大的办法来提高人类的寿命:只要人类改变一下婚姻制度,确切说是生育制度,要想活到一百岁、二百岁、三百岁甚至一千岁理论上完全能够做到。
具体的做法是:不断地推迟结婚的年龄,实际上是推迟生育的年龄。如果只允许30岁以后才能结婚生育,那么30岁以前就死去的人,就没有了传播后代的机会,如果将死亡的原因视为多基因的组合,那么这种组合就传播不下去,就消失了;如果这个国家进一步提高育龄,要求40岁以后才能生儿育女,那么这个国家的平均寿命很快会进一步提高到40岁以上。如果考虑到男女之间的差异,规定男70岁、女40岁才能结婚生育,那么人的平均寿命可以进一步提高到50、60岁以上。
除了婚姻生育制度外,再辅以像驯化动植物和繁育良种那样的技术,届时,男人至80、100岁尚能工作,女人至60、80岁仍可生育,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这样的制度理论上可以把人类的寿命无限提高,甚至千岁也有可能。
这套说法不是我的发明,是英国生物学家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这本书中说到的。他是从一个叫梅达沃(Peter Medawar)的生物学家那里引来的。我只不过加以发挥,说得更清晰明确罢了。
既然有这样的方法,可以大大地提高人类的寿命,为什么人类不这样做呢?并非不能为,而是不想为。因为长寿是否值得追求就是一个问题,而且究竟多长算长寿。长生不老值得追求吗?如果人不死,人生还有意义吗?
在一个竞争的环境中,追求长寿的国家不具有优势。战争中,爱惜生命的长寿者不可能抵挡得住视死如归的勇士。在有限的资源下,如果有哪一个国家刻意去追求长寿,那么它离灭亡也就不远了。
对个体而言,大多人愿意长寿;但对一个族群,或者一个社会而言,长寿未必是好事。假如从秦始皇到康熙大帝都活着,中国会怎样?
写完这篇文章,我站到了窗前,看到落日的余晖洒满了街道,一对夫妇可能刚从菜市场出来,他们的满头银发告诉我:他们可能有70多岁了。男的一手拎着一袋菜,一手扶着女的,他们踽踽走来,我忽然有了一丝感动,因为这是只有人类社会才可能出现的情景。
我去过许多荒野,在野生动物很多的可可西里,我看到了跑起来震天动地的野牦牛群,看到了为争夺配偶,把利剑一样的长角插入对方身体的藏羚羊,我看到的都是健硕有力的年轻的野生动物,我从没有看到过衰老的、走路颤颤巍巍、牙已落尽的野生动物,衰老在动物界就意味着死亡,这是荒野的定律。
人的存在是否就是为了打乱基因的计划、抵抗自然选择的宿命呢?
(选摘自《中国国家地理》2008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