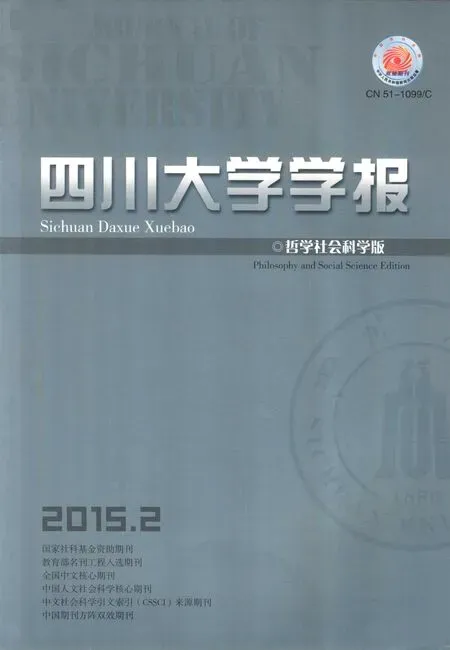马基雅维利的转向——论敌友划分的限度
李世祥
“敌友划分是政治的标准”,卡尔·施米特1932年把这句话作为《政治的概念》第二章的标题。在施米特看来,政治的第一要义在于弄清楚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1947年,纽伦堡国际法庭将施米特无罪释放,他回到老家闭门专心著述,将自己的住所称为San Casciano,而真实的San Casciano位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省,是马基雅维利的故乡。施米特自比马基雅维利,恐怕不仅仅是因为二人晚年命运相似,更有可能缘于精神的契合。
1512年,美第奇家族在西班牙雇佣军的帮助下推翻佛罗伦萨共和国,解除了马基雅维利的职务,随后又将其下狱。马基雅维利出狱后回到家乡,在清贫的生活中写下了《君主论》、《论李维》、《佛罗伦萨史》和《战争的技艺》。《战争的技艺》①马基雅维利:《战争的技艺》,崔树义译,冯克利校,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第192页。马基雅维利的《战争的技艺》有三个中译本,另外两个是:《兵法》,袁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用兵之道》,时殷弘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除特别说明外,本文的《战争的技艺》引文均出自崔树义译本。是马基雅维利唯一生前出版的作品,但研究者关注却相对较少。《战争的技艺》在军事思想史上有着重要地位,费利克斯·吉尔伯特将马基雅维利视为现代战争艺术的开创者。②费利克斯·吉尔伯特:《战争艺术的复兴》,彼得·帕特雷主编:《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代》,时殷弘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第2-22页。关于《战争的技艺》与其他三部作品的关系,学界有两种不同观点。曼斯菲尔德认为,鉴于《战争的技艺》在生前出版,马基雅维利在这部书中的笔触要比另外几本书委婉得多,没有说什么“人们忘记父亲的死要比忘记遗产的丧失来得更快些”一类惊世骇俗的话(《君主论》17章)。③Harvey C.Mansfield,Machiavelli's Virtue,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6,p.191.但尼尔·伍德持相反的意见,他认为《战争的技艺》有关军队组织和领导艺术的论述凸显了马基雅维利在政治领域的关注重点。其理由是,在16世纪的意大利,人们谈论政治、宗教话题时直言不讳很危险,而谈论军事问题则可以通畅明快,少些顾忌,因此研究《战争的技艺》有助于澄清“其政治著作中的一些含混模糊、前后矛盾和有意避而不谈的地方”。④尼尔·伍德:《兵法》英文本引言,见《兵法》袁坚中译本附录,第285页。尼尔·伍德甚至说,研究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哲学,最好从《战争的技艺》开始,这样就更容易理解《君主论》和《论李维》的治国治民之术。
战争与政治的一体性
从《战争的技艺》反观《君主论》、《论李维》和《佛罗伦萨史》,我们会发现马基雅维利的军事思想已经完全渗透到其政治哲学的枝枝脉脉中。《君主论》谈到如何利用自己或他人的武力建立新君主国,军队有哪些类型,何种军队最可靠,君主在军事方面应该担负什么样的责任。《论李维》分析罗马人如何征战,古今军事体制的差异,雇佣军的危险,兵将之间的关系,甚至从技术层面研究炮兵的利弊、要塞的用处和将帅熟悉地形的重要性。《佛罗伦萨史》更是可以称为一部战争史。马基雅维利认为治军与治国有很大的相似之处。谈到选取兵源要用质朴粗俗的本国人时,他说:“任何优秀的雕刻家都永远不会相信,自己用形状糟糕的大理石雕刻出华美的雕像,但他非常相信用未加任何雕琢的大理石就可以。”(卷七235)马基雅维利在《论李维》(卷一11章)中几乎原封不动地重复了这句话:
而今,打算创建共和国的人将会发现,较之那些已经习惯于城市生活、文明已经烂熟的人,在没有文明的山民中间,他更易于取得成功;雕塑家要想制作一尊漂亮的雕像,与其采用另一个雕塑家打造出的蹩脚半成品,远不如采用全无雕饰的石材来得容易。①马基雅维利:《论李维》,冯克利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9页。
用同一句话来比喻治军治国,说明在马基雅维利心目中,治军和治国是一码事儿,二者都像雕塑一样是创造性的技艺,都要塑造不成熟的人群。无论是成为伟大的开国者,还是成为伟大的军事统帅,创新精神都必不可少。
军人生活与平民生活密切相关,只有在军队的保护下,国家建立起来的法律和制度才能得到保持,军队最能体现出公民对于国家的忠诚,军事纪律是培养爱国主义的有效方式。“一个人只有依靠自己的军队才能站稳脚跟,只有通过国民军的方式才能组建自己的军队,无论在任何地方,都不能以别的方式组建军队,也不能以别的方式组建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卷一页189)。波考克在《马基雅维利时刻》中主张,马基雅维利将古代政治生活和大西洋共和传统联系了起来。在马基雅维利那里,士兵与公民是双向的,只有公民才是好士兵,只有士兵才是好公民:
军人品德使政治品德成为必需,因为两者可以在同一目标中表现出来。共和国是共同福祉,一切行动皆以增进这一福祉为目标的公民,可以说将生命贡献给了共和国,而爱国军人为国捐躯,两者通过为普遍目标牺牲个别利益而使人性臻于完美,在这方面他们是一样的。一个人可以通过军事纪律学会做一个公民,展现其公民品德。②J.G.A.Procock,The Machiavellian Momen:tFlorentine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 Atlantic Republican Tradi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5,pp.vii-viii,199.转引自崔树义译《战争的技艺》,第8页。
昆廷·斯金纳也认为马基雅维利信守军人服务于政治共同体的人文主义理念,通过军队把这种理念渗透到政治共同体中。《战争的技艺》证明马基雅维利“对公民士兵理想始终如一的信奉,远不仅仅是对……人文主义常识的重复”。③Quentin Skinner,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Vol.1,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pp.173-175.转引自崔树义译《战争的技艺》,第9页。这种军事生活与平民生活的一体化首先体现在君主身上,“君主除了战争、军事制度和训练外,不应该有其他目标、其他思想,也不应该把其他事情作为自己的专业,因为这是统帅应有的惟一专业”(《君主论》,14章)。政治共同体必须以强力来维护,没有强大忠诚的军队,政治共同体无法抵御内忧外患,只有政治统帅与军事统帅真正做到合而为一,政治共同体才有可能取得最大限度的安全。波考克和斯金纳都深信,马基雅维利对古代美德颇为敬重并主张公民士兵是公民服务于政治共同体的保障。他们忽略掉的是,公民毕竟不同士兵,把公民混同于士兵可能会对政治共同体产生什么样的负面影响。
军事准则在政治中的适用
马基雅维利总结出二十七条军事准则,第一条是:“于敌有利者则于己有害,对己有利者则于敌有害。”(卷七页154)而韦格蒂乌斯对此的表述是:
于己有利的,于敌应有害;于敌有助的,于己必有害。因之,我们不应当做或者不去做符合敌人意愿的事,而只应当做或者去做我们认为于自己有利的事。如果你去效尤敌人为自己的利益而做的事,那你就是反对你自己了。反之亦然:如果敌人想效法你那样去行动,结果一样,因为你希盼为自己所做的事恰巧正是反对他们的。①韦格蒂乌斯:《兵法简述》,袁坚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第184页。
马基雅维利只是把韦格蒂乌斯的话颠倒了次序,几乎没做什么更改。政治的首要问题是划分敌友,弄清楚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一点在战争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如果搞不清敌友,战争必然是一场无意义无结果的混战。
划分敌友观念在西方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从荷马史诗、柏拉图对话到古希腊悲剧,很多古典著述对敌友划分都有着深刻的思考。古代政治共同体的进化是从家庭、家族、部落到城邦,敌友划分的源头可追溯至你我的区分。布伦戴尔把友情分为三个类别:第一类就是与父母兄弟的感情,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亲情;第二类是城邦公民组成的朋友圈子,相互之间享有共同利益;第三类最接近现代的朋友观念,因相互尊重爱慕而成为私人朋友。②布伦戴尔:《扶友损敌:索福克勒斯与古希腊伦理》,包利民、吴新民、李春树、焦华红译,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56-58页。对朋友的情感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感激,而这种感激最初源于对父母生育抚养的感激,进而延伸至对兄弟之情的感激。丈夫和妻子的爱恋泛化为友情,从两性到父母子女,再到兄弟,再至他人。家庭的不同推衍至族群的差别,正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库朗热从宗教的角度对敌友划分给出了另一种诠释:
与祭祀死者有密切关系的圣火,亦是每个家庭所私有的。这家火代表着他们的祖先;是每家的神佑所在,与邻居的家火无干,因为它只保佑着邻居。每家的家火只保护每家的家人。这种宗教于是限于各家的院墙以内。祭祀并不向外人公开。举行祭祀时,只允许本家人参加。家火永远不会被放在户外,不会被带出家门,唯恐外人看个真切。希腊人总是将家火置于院内,以避外人的玷污和窥探。罗马人也将之置于屋内。所有的这些神灵、圣火、户神、亡灵,人们都称作家神。祭祀都在私下秘密地举行,所以西塞罗说他们是进行秘密祭祀。若举行时为外人窥探,即使只是那么一个眼神,也会令他们有一种不祥之感。③库朗热:《古代城邦——古希腊罗马祭祀、权利和政制研究》,谭立铸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6页。
家庭、胞族、部落和城邦各有自己的神明,遵奉自己的家神,这是你我区分的源头,也是敌友演化的基础。古代战争征服敌人后往往要求失败者信奉自己的祖先神,荷马笔下的战争既是人的战争也是诸神之争。
为了取得胜利,对于战场上的敌人可以无所不用其极,正所谓兵不厌诈。马基雅维利在《论李维》(卷三第40章)中直率地说“在战争中运用欺诈是件光荣的事”。要做到兵不厌诈其前提就是密谋,马基雅维利总结的兵法原则有4条涉及密谋:“在实施前一直让敌人一无所知的谋略是最好的谋略;当你意识到敌人已预见到你的谋略时就改变谋略;在你必须做的事情上多征询别人意见,把你以后想做的事情只告诉少数人;不要让敌人知道你打算如何排兵布阵。法布里奇奥说,要想扰乱敌人军心,必须要做些让敌人惊恐的事情,比如让一些人假装援军蒙蔽敌人,苏尔皮提乌斯曾把稻草人绑在骡子上,使之看上去像一队骑兵,从而战胜了法国人。”(卷四页52-54)“除了欺诈,将帅为了赢得战争还要残酷无情。为打败塞西亚士兵,马其顿的腓力把最信赖的骑兵部署在部队后面,对逃兵格杀勿论”(卷四页70)。“实施律法必须苛刻严厉,司法者必须铁面无私。罗马人对脱离哨位者、放弃指定战斗岗位者、藏匿东西出营者、谎报战功者、违反帅令作战者和因贪生怕死而丢弃武器者,统统处以死刑。若是一个步兵大队整个军团犯下一种类似错误,为了不全部处死,他们就把这些人的名字放在袋子里抓阄,抽出十分之一的人处死”(卷六页112-114)。
在马基雅维利的其他著作中,战争上的欺诈和残酷在政治领域也体现得淋漓尽致。马基雅维利认为,君主应兼俱狮子和狐狸的素质,把欺骗用得炉火纯青,同时懂得如何掩饰这种兽性,做伟大的伪装者和假好人(《君主论》第18章)。“论残酷与仁慈,被人爱戴是否比被人畏惧来得好些”,马基雅维利认为君主最好是既受人爱戴又令人畏惧,如果两者不能兼备,令人畏惧则比受人爱戴安全得多,因为人类“忘恩负义,容易变心,是伪装者、冒牌货,逃避危难,追逐利益。……爱戴是靠恩义这条纽带维系;然而由于人性是恶劣的,在任何时候,只要对自己有利,人们便把这条纽带一刀两断。可是畏惧,则由于害怕受到绝不会放弃的惩罚而保持着”(《君主论》第17章)。切萨雷·博尔贾的残酷为罗马尼亚带来了统一和秩序,恢复了和平与忠诚,汉尼拔的残酷令士兵感到敬畏,取得了卓越的军功。马基雅维利还举了一个集欺诈与残酷于一身的例子,西西里人阿加托克雷。这个人是陶工的儿子,为人邪恶,后参军一路晋升为叙拉古的地方执政官。他伪称商讨国事召集叙拉古元老院和富人开会,然后把他们全部处死,取得了这个城市的统治权。马基雅维利评论说,阿加托克雷勇于决断,出卖朋友,不讲信用,毫无恻隐之心,没有宗教信仰。“如果考虑到阿加托克雷出入危殆之境的能力和忍受困难、克服困难的大勇,我们就觉得没有理由认为他比任何一个最卓越的统帅逊色”(《君主论》第8章)。
《君主论》是教授帝王治术的秘籍,关起门来谈欺诈和残酷情有可缘,而崇尚共和的《论李维》同样如此,让人不由得感叹马基雅维利智性的“勇敢”。他直白地提出,卑贱者要想成为权贵,仅仅依靠武力很难成功,但使用欺诈却绰绰有余。以欺诈和残酷开国的还有罗马人,其最大骗术是拉拢拉丁人入盟,以盟友的名义把这些拉丁人变成奴仆。“在罗马人最初的壮大过程中不乏欺诈;对于想从微不足道的开端登上巅峰的人,这也是必须运用的伎俩;正如罗马人之所为,它越是隐蔽,就越不应当受到责备”(《论李维》卷二第13章)。马基雅维利在《论李维》中用一章的篇幅分析阴谋,长达15页。“论阴谋”的目的是告诉君主或国家如何防范阴谋,因为能对君主开战的人不多,而搞阴谋者却到处都是。针对君主的阴谋缘于多种原因,主要是民众的憎恨或者财产名誉受到侵害。能够对君主搞阴谋的人要么是大人物,要么是熟悉君主的人,这些人的动机是统治的欲望,想取君主而代之。马基雅维利把阴谋分为三个阶段:预谋、实施和实施之后,而阴谋失败的原因是事情败露、勇气不够、谋划不精细。策划阴谋者如果想取得成功一定要保密,同时确保不留下证据和口实,不要像普劳蒂亚努斯那样给护民官萨图尼努斯写下一道刺杀皇帝塞弗儒斯的手令。与针对君主的阴谋相比,针对共和国的阴谋风险要小些。反对国家的阴谋一般发生在腐败的共和国中,如喀提林阴谋。拥有武装的人针对共和国搞阴谋更容易成功,就像凯撒那样。马基雅维利提出实施阴谋的手段既有刀剑又有毒药,而下毒的办法更危险,更不确定。
君主之大敌,莫过于阴谋。反对他们的阴谋一旦出现,他们不是死于非命,就是蒙受耻辱。假如阴谋得逞,他们丧命;假如阴谋败露,他们干掉阴谋家;然而人们总是认为,那不过是君主在罗织罪名,他是以被他处死者的鲜血和财产为代价,来满足自己的贪婪和残暴。(《论李维》3.6.21)
“论阴谋”一章可以说是在做双重教导,一方面告诉君主和共和国如何防范阴谋,另一方面也是在提醒阴谋者取得成功需要注意的事项。马基雅维利赤祼祼地告诫人们,运用残暴无耻的手段可以获得用正常手段无法获得的东西。马基雅维利把军事准则应用于政治领域的后果就是,其政治著作毫无顾忌地鼓动统治者要敢于残忍和狡诈,完全违背了古代经典作家对于统治者的谆谆教诲,与色诺芬对比,其面目将变得更为清晰。
马基雅维利的转向
纽维尔认为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和《论李维》中对色诺芬的分析篇幅比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的论述加起来还要多,而且在色诺芬出现的地方往往应该是更具影响力的作家。①纽维尔:《马基雅维利和色诺芬论君主的统治:一个双重的碰撞》,张奇峰译,韩潮主编:《谁是马基雅维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54页。马基雅维利在《论李维》中有五次谈到色诺芬,其中四次谈色诺芬笔下的居鲁士 (2.13.1,3.20.1,3.22.4,3.39.1),一次谈色诺芬笔下的希耶罗 (2.2.1)。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三次谈到居鲁士 (6.3,14.6,26.1),两次谈到希耶罗 (6.7,13.6)。通过引述居鲁士的事例,马基雅维利试图说明君主要善于欺诈,同时要能够装得仁慈慷慨实则残忍无情。在“卑贱者能飞黄腾达,更多地依靠欺诈而非武力”一章,马基雅维利做出下述评论:
色诺芬在其居鲁士行传中表明了行骗的必要。他所描述的居鲁士,在对亚美尼亚国王的远征中充满了欺诈;他笔下的居鲁士,夺取王国靠的不是武力,而是行骗。他从这种行为中得出的惟一结论是,想成就大事业的君主,必须学会行骗。此外他还描述了居鲁士如何以种种手法,欺骗他的舅舅、米底人的国王基亚克萨里斯;他表明,不靠欺诈,居鲁士不可能取得那些丰功伟业。(《论李维》2.13.1)
但是,读过《居鲁士的教育》后,我们会感觉这并不是色诺芬的原意,而是马基雅维利戴着自己的眼镜在断章取义。无论是征伐亚美尼亚还是处理与基亚克萨里斯的关系,居鲁士都不像马基雅维利说的那样奸诈,至少色诺芬没有把居鲁士描述得如此奸诈。马基雅维利后面(《论李维》3.20.1)也承认,色诺芬不辞辛苦地阐明居鲁士的仁爱慈祥,从没有表现出傲慢残暴,由此赢得了胜利和荣耀。但马基雅维利笔锋一转,说汉尼拔同样功名赫赫,却使用了截然相反的方式,即残忍无情,其真实用意在于强调后一种品质。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同样谈及居鲁士的仁慈宽厚,还强调罗马统帅西庇阿刻意效仿居鲁士。关于获得自己武装的先知或君主,马基雅维利列举了摩西、居鲁士、罗慕路斯和忒修斯,而其中只有居鲁士一人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可见居鲁士在马基雅维利心中的份量。马基雅维利认为居鲁士的事例能够证明君主必须善于欺诈这一结论,当无法用居鲁士来证明政治家必须残酷时,马基雅维利便转而用汉尼拔来说明。
除了居鲁士,马基雅维利还引用了色诺芬谈到的历史人物希耶罗。色诺芬这本书的名字是《希耶罗或论僭政》,马基雅维利在《论李维》中把希耶罗作为专制者的代名词,是自由的对立者,祖国的敌人。这个名字 (尽管不是同一个人)在《君主论》中却摇身一变成为依靠能力成为“君主”的典范,他建立武装抓住机会成为叙拉古的新王。希耶罗二世发现自己的雇佣军没有用处但又无法解散时就把他们斩尽杀绝。马基雅维利举这个事例不过是在重申残酷是统治者必备的素质。通过把仁慈的居鲁士变成欺诈的居鲁士,把僭主希耶罗变成有能力的残酷的君主,《君主论》只字不提僭主一词,马基雅维利完全混淆了居鲁士与希耶罗、君主与僭主的差别。
马基雅维利为什么如此重视色诺芬?纽维尔给出的答案是,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相比,色诺芬更为广泛深入地探讨了君主对于政治共同体繁荣稳定的重要作用。色诺芬在《远征记》中也分析过军事领导人和政治领导人需要采取相同的手段,这可能给了马基雅维利些许提示。不过,色诺芬认为对敌人采取欺骗、计谋和暴力是正当的,但从未提出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对待同胞或战友。恰恰相反,色诺芬写道:
如果一个希望在城邦获得荣誉,不仅是为了使自己不做不法行为的牺牲品,同时也是为了在正义的事上对朋友有所帮助,并且使自己在执政期间能够为祖国做一些有益的事情,他自己既然具有这样的心情,为什么不可以和与自己有同样心情的人结交为亲密的朋友呢?难道他和那些高尚而善良的人们的合作之后反而会使自己对国家不能有所贡献吗?①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吴永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69页。
在色诺芬看来,友情既是政治共同体的基础,也是人类弥足珍贵的一种情感,政治家需要竭尽全力把友谊留在政治共同体内。色诺芬借苏格拉底之口分析了朋友与敌人形成的情感心理因素,“人们天生倾向于友爱:彼此需要,彼此同情,为共同的利益而通力合作。意识到这种情况后,人们会心怀互相感激;但人们也有一种敌对的倾向。因为那些以同样对象为美好可喜的人们,会因此而竞争起来,由于意见分歧就成了仇敌。分争和恼怒导致战争,贪得无厌导向敌视,嫉妒导向仇恨”(《回忆苏格拉底》2.6.21)。色诺芬本人与苏格拉底的关系就是政治共同体内友情的一个例证。古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在《地理学》中曾提到,希腊人公元前424年与底比斯人在德林姆 (Delinm)交战时,色诺芬从马上摔下来,幸亏苏格拉底救助才逃过一劫。色诺芬后来写回忆录纪念苏格拉底并为之辩护。耐人寻味的是,马基雅维利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到色诺芬笔下的居鲁士,①参见 《君主论》14 章;《论李维》,2.2.1、2.13.1、3.20、3.22.5、3.39.1-2。对苏格拉底却只字不提。
结 语
尼尔·伍德说:“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谈到夺权,但总是将这视为一种非法的政治活动。他也没有细谈夺权所需要的方法和步骤。古人与马基雅维利在这个问题上态度如此不同,其原因在于经典的观念是必须从根本上区分敌友,区别对待。这就引出了学术上的分工:古代政治理论家几乎只关注友人之间、同胞之间如何相处,而敌我之间的事则属于军事理论的研究范围。”②尼尔·伍德:《兵法》英文本引言,见《兵法》袁坚中译本附录,第270-271页。古典思想家把敌友视为政治生活天然的一部分,他们认为人在公共生活中必须要有朋友,即便是自视为幸福的人也需要朋友,为了朋友甘愿做出牺牲,朋友的敌人便是自己的敌人。亚里士多德关注敌人与朋友在伦理学上的意义,一方面谈到勇敢是应该具备的品质,最典型表现是在战场上对敌作战勇敢(《尼各马可伦理学》1115a29-34),另一方面说即使幸福的人也需要朋友,因为人是政治的存在者,必定要过共同的生活。幸福的人拥有那些本身即善的事物,与朋友和公道的人共享这些事物显然比与陌生人和碰巧遇到的人共享更好(《尼各马可伦理学》1169a 16-22)。“朋友是非常令人向往的,这不仅是因为社交的快乐,还因为他们带来帮助和支持。他们作为不幸时的避难所,是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并且,它们是实现政治抱负必不可少的基础”。③布伦戴尔:《扶友损敌:索福克勒斯与古希腊伦理》,第40、69页。与朋友的重要性相比,敌人在古代伦理观念中的份量要轻一些,扶友要比损敌更具强制性。因为,向敌人报仇是人们很自然产生的欲望,违反这一原则至多声誉上受损,而人们出于自私的动机很有可能不遵守扶友的原则,要遏制这一倾向就需要有强大的社会舆论批判以形成规范性力量。即便是在战场上,人们仍然无法避免某种困境:私人性质的朋友在战场上成为敌人。格劳科斯和狄俄墨得斯为世交的朋友,却要在战场厮杀,他们两个为了逃脱这个困境就选择与其他人作战,因为还有其他许多人可杀(《伊利亚特》6.227-229)。正如布伦戴尔所说:“虽然‘扶友损敌’原则在战争环境下最为有效,但是并不能把这一规范在战争中的模式简单地套用到其他更广范围的关系领域中。”
不幸的是,马基雅维利似乎并不在乎这一提醒,把敌友划分在战争中的应用原则毫无保留地在政坛中加以实施。马基雅维利没有考虑或不愿考虑的是,敌友划分原则在战争中和在政治中有着实质的不同,战场上极少出现使忠诚和敌意与其他美德的标准相协调的问题,利益冲突的可能性更小。战争中的敌友划分更为简单,更加血腥残酷,在使用诡计方面没有道德上的顾虑。那么,马基雅维利基于什么考虑要突破敌友划分的这一限度?为什么要把君主与普通人的伦理道德切割开来?在《战争的技艺》卷二,法布里奇奥谈到丧失美德的原因时说,基督教使今天的人们不再像古代一样奋力保卫自己。在古代,战败者不是被处死就是被卖为奴隶,境遇无比悲惨,而人们现在已经没有了这种恐惧。马基雅维利在《论李维》前言中直接以自己的口吻说,“我认为,造成此种状况的,主要不是当今的宗教使世界羸弱不堪,或贪婪的惰怠给众多基督地区或城市带来的罪孽,而是缺少真正的历史见识”。④马基雅维利:《论李维》,第44页。然而,把《论李维》读完,人们会发现马基雅维利在这里说的是反话,他认为使世界衰弱的恰恰是基督教。对观伊拉斯谟的《论基督君主的教育》,我们明显感觉到马基雅维利的心中充满了对“和平的”基督教的敌意。马基雅维利的过人之处在于敏锐意识到敌友划分在政治中的重要意义。问题的关键是,马基雅维利走得太远,模糊了敌人与朋友、政治共同体的内与外、战争与和平的界限,从根本上改变了古人对于政治的理解。政治共同体的根本目的从此不再是善,其基础不再是友谊,军队也不再是友爱共同体,和平变成了战争的间歇,敌友划分泛化为政治的普遍标准。后世政治共同体内的斗争因之变得更加残酷焦灼,以至于霍布斯干脆宣称“一切人是一切人的敌人”(《利维坦》卷一第13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