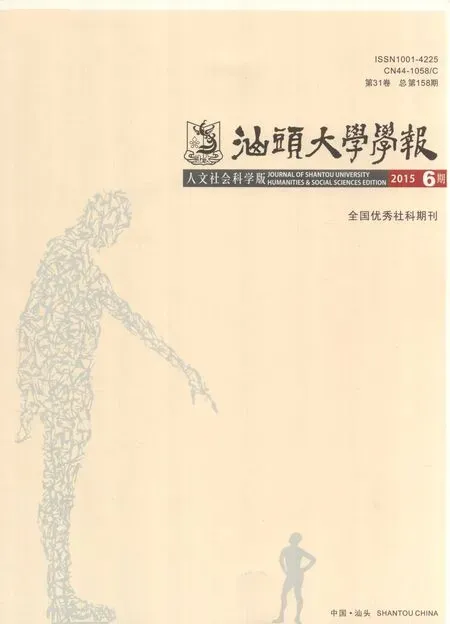“love”的日译“恋爱”小考
徐青
(浙江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浙江杭州310018)
“love”的日译“恋爱”小考
徐青
(浙江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浙江杭州310018)
明治前期,来自西方的新思想、新词汇开始大量涌入日本社会,外来语的爆棚也造成日本人对“外来语”的“误用”和“滥用”现象显著。英语“love”与日语译词“恋爱”之间,东西方在表述异性相爱的词语中自有文化内涵的差异性。
“love”;日语;恋爱;翻译;文化
日本东京大学著名翻译理论家柳父章(1928-)指出,“在翻译工作中,看起来最为简单的问题其实是最困难的。如果,以常识观念来判断的话,首先我们会认为在翻译中构文最为困难……其实,在翻译中最成问题的莫过于对西欧引进的语言进行翻译时,产生的外来语滥用现象。”[1]
明治前期,来自西方的新思想、新词汇通过翻译开始大量涌入日本社会,日本人对“外来语”的“误用”和“滥用”现象显著。本文试以英语“love”为例,围绕日语译文中的“恋爱”以及大正时期日本著名的文艺批评家厨川白村在著作《近代恋爱观》中所主张的恋爱观在“五四”时期中国文艺界的传播与发展作一概述。
一、英语“Love”与日语“恋爱”
英语“love”一词被翻译成“恋爱”始于何时?在此,有必要对“Love(恋爱)”的历史进行回顾。在19世纪中国出版的汗牛充栋的汉英辞典中,《英华字典》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字典。可以说《英华字典》代表了19世纪西方人士编纂汉外辞典的最高成就,但由于基督教中华传道会传道士,德国人罗存德(WilhelmLobscheid,1822-1893)与教会的纷争,使《英华字典》在中国的发行受阻,在国内几乎很难找到罗存德的字典及其著作。《英华字典》出版后,购买者中日本人占了绝大多数,这对日本近代英日辞典的编纂、译词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远远超过汉语。
从幕末到明治初期,也就是1868年之前,日本人主要使用的字典就是罗存德的《英华字典》(1847-1848),该字典很早就出现了“恋爱”一词,但是,这里的“恋爱”是针对动词“Love”的翻译,不是针对名词“Love”的翻译。此外,罗存德对“to love”的翻译词从“爱,好”开始,也译成“爱惜”和“恋爱”。在名词love的译词一览中,有“爱情,宠,仁”等,但就是没有出现“恋爱”一词。
日本的辞典《和兰字典(汇)》(1855-1858)里对“Liefde”的译文是“宠爱”、“爱敬”、“仁”等。在《仏语明要》(1864)中,把“amour”译成“恋·爱·财宝”。在日语字典中出现“恋爱”一词,最早是佛学垫的《仏和辞林》(1887),把“amour”译为“恋爱。钟爱。好爱。爱。”[2]95
日本的女性教育家、评论家,《基督教新闻》主笔严本善治(1863-1942)把“Love”翻译为“发自深邃灵魂的爱”。对此,柳父则认为自己无法理解,并指出“Love”绝对不是指“灵魂”。当然不能绝对地否认对“爱”的理解,有人是会把“灵魂”和“肉体”区别进行思考的。但是,传统日本人的“恋”和“爱”、“心”和“肉体”是不做区别思考的,这与把“恋”和“爱”合在一起思考正好相反。因此,柳父认为对“Love”的解释,如果出现强调“灵魂”的“恋爱观”的存在也无可非议。[2]94
柳父在《翻译语成立事情》中指出,在岩本之前,日本对“恋爱”翻译的用例其实很少,最早的用例应该是1870-1871年,日本的武士、启蒙教育家中村正直(1832-1891)翻译的《西国立志编》。原文为“to have fallen deeply in love with a young lady of the village”,被译为“已经深深地爱上村中的少女”。日语原文中的“恋爱”一词,是变动动词的语干,因此中村是把《英华字典》中的“恋爱”作动词来使用。[2]96
当“Love(恋爱)”开始在日本社会上出现的时候,柳父认为与通俗的“恋”等“充满不洁之感的日本通俗文字”不同,指出“Love”与日本通俗的词语“恋”具有不同的含义。因此,需要造出一个能够对应“Love”的新词。这就是现在我们经常在电影、电视以及各种公共场所频繁使用的“恋爱”。我们不难发现,“恋爱”与“充满不洁之感的日本通俗文字”和“恋”是不同的,“恋爱”更为文雅,而且具有高尚的价值。他们的不同在于“恋爱”带有“清洁正直”和“发自于灵魂深处”即更高更深层次的感情——“爱”。
二、“恋爱”的首译者北村透谷与基督教
在西欧“Love”等同于“恋爱”,但是,到明治前期日本还没有出现“恋爱”这个单词,或者可以说基本上不存在。“日本的男子对女子充满的爱恋只是肌肤之亲,没有深深地发自灵魂深处的爱”[2]91。总之,岩本所谓的“恋爱”一词内涵高尚,但是,相对应的词语在日语中却没有。因此,“恋爱”是当时的新造语。在这之前没有“恋爱”这个单词存在,相应的意义当然也不可能存在。
日本真正开始使用“爱”、“恋”和“love”这些词语是在明治维新后,是文明开化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产物。日本著名的诗人、评论家北村透谷(1868-1894)在有关恋爱和精神价值的评论文章《厌世诗家与女性》中指出:“恋爱是人的妙药,先有恋爱后才有人,如果把恋爱抽离的话,人生毫无色彩可言。”[3]428社会活动家、评论家、小说家木下尚江(1869-1937)评论北村的这句话“宛如被炮轰般,这样认真地谈论恋爱的话语在我国还是第一次出现。”[3]432北村于明治二十二年(1889)结婚,《厌世诗家与女性》就是北村自身恋爱和结婚经历的写照,他的恋爱和结婚的情形虽然与岩本基本相同,但是,北村在赞美恋爱的同时也提到了婚姻生活所带来的束缚。北村与岩本两人对于婚姻的态度正好相反,虽然他们都是基督教信徒,但并非都赞美恋爱,岩本因为是基督教徒,所以对恋爱的反应非常的谨慎。
我们现在使用的“爱”就是基督教的概念。在日语中因为没有相当于英语的“love”一词,因此对“恋”和“爱”的释义不尽相同。英语“I love you”和法语“Jet’aime”无论如何都无法用日语进行翻译。因为深埋在英语和法语中的语言感情,在日语中从来就没有过,没有“我爱你”、“我对你有了恋慕之情”的表述。正好也反映了至此为止在日本人的思想里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感情。“恋爱”的流行,首先是“恋爱”这个词语的流行,在这个词语的支撑下,“恋爱行为”才开始在有勇气的年轻人中间传开。在这些年轻人中占较大比例的是知识分子群体或是出生于书香门第的年轻人,特别是基督教徒(新教)及其周边的人士。知识分子较多的原因是能够理解西方语言并使用外来语。受基督教的影响,岩本等人在解释“恋爱”时特别强调其在精神方面的意义。“恋爱”作为新造词也涉及到语言问题,从严本到透谷的言行中,我们不难发现日本在对“恋爱”思想的继承的同时,非常重视“恋爱”的时代性和历史性。同时,从译词的角度我们也能发现,“恋爱”必须是灵肉一致、合二为一。
三、近代日本——爱的虚伪
但是,日本著名的评论家、小说家伊藤整(1905-1969)在著名的论文《有关近代日本的“爱”的虚伪》[4]中分析在基督教中以神为前提的“爱”的概念时指出,日本人对于“爱”的理解与基督徒理解的“爱”不尽相同,该文也同时考察了日本与西欧文化的不同点。
伊藤指出:男女之间的执着,使用宗教词语“爱”来进行定义,有与宗教同质的倾向,是欧洲文化中最为显著的特点。在没有信仰、没有祈祷和忏悔的前提下,当我们要诉说理想的男女之间的交往时,使用西欧的“爱”这个词语,或用“爱”来表达夫妇之间的关系会使我们感到踌躇、困惑。其实这层感情在日语中可以称之谓“迷恋”、“恋爱”或者“爱慕”,但却绝不是“爱”。在日本人的思想里没有像基督徒那样努力地,把原本很个人的“性”或者是对他者的“爱”进行纯洁化的习惯。
对于日本人来说,男女之间的“肉体之亲”就是“恋”,不存在把它同化为“爱”,并进行祈祷的念头。对于日本人来说夫妇之间的爱情是指相互之间是否拥有宽恕之情和正直的执着。在日本知识分子中,把男女之间的结合用外来语“Love”的日译词“爱”来进行思考并成为习惯后,有多少日本女性会因此而绝望。因为像江户时期的男女关系都是以“迷恋”和“爱慕”等词语来表达,如果不使用令人感到敬畏的“爱”这个词语的话,即使被对方背叛,对于女性来说所受到的打击或许会不那么严重。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现代人在使用“爱”这个词语时,实质上是对“性”的强制性束缚。不是因为“爱”,而是因为互相间的“迷恋”、“爱慕”、“执著”、“强制”和“束缚”,最后终于“厌倦”,以致“逃离”。
大正时期是日本社会男女殉情和名人婚外恋丑闻的高发期。日本女性开始对“自我”觉醒,已经不再满足于由自己的父母所决定的婚事,开始探索精神上和经济上的独立。可以说“自由恋爱”是生活方式上的一种跳板,在这一时期接二连三地发生像芳川镰子(正二位勲一等伯爵枢密院副议长芳川显正第四个女儿,曾称子爵夫人)与司机的殉情自杀;女演员松井须磨子追求岛村抱月不成自杀殉情;出自镰仓时代的公家、与大正天皇是堂兄妹的女歌人柳原白莲给丈夫(九州的炭鉱王,伊藤传右卫门)的公开绝缘信;东北大学教授石原纯与アララギ派歌人原阿佐绪的恋爱,以及作家有岛武郎与杂志《妇人公论》记者波多野秋子在轻井泽的殉情自杀事件等在当时的日本社会闹得沸沸扬扬。可想而知,“恋爱行为”在当时日本社会开始流行的同时,也引起了社会上大部分人士的反感。
四、厨川白村的“恋爱”
1922年日本大正时期著名的文艺批评家厨川白村(1880-1923)的《近代的恋爱观》[5]一经出版,立刻受到社会和文坛的重视,点燃了大正恋爱论热潮的导火索,为此白村曾一度与作家有岛武郎(1878-1923)二分天下。该书从1922年初版发行至1924年再版,已达106版[6]。可见其在日本受欢迎的程度。由于《近代的恋爱观》是大正民主主义高涨时期出版的一部专论“婚姻观”的著作,共有三部分构成,即《近代的恋爱观》、《再论恋爱》和《三论恋爱》,因此有人称其为白村的“恋爱论”三部曲。
白村借用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的精神医学家榊保三郎博士(1870-1929)的《性欲研究与精神分析学》[7],用科学的学说来解释性欲与道德宗教的关系。大泽谦二为其作序,指出:“现在诸君如读本书,恐怕会大为震惊。人在婴儿期既有性欲,当君读到这天使般清纯可爱的婴儿喜欢手淫时,也许会惊讶地合不拢嘴。儿童稍有发育,便会发展至近亲爱,这还是纯然的性欲。而且,对我们这样注重孝悌的人来说,它已成为最为重要的道德根源。当然,它也成为基督教所说的爱的根柢,读到这儿,诸君又会作何感想呢?基督教徒说除了神,不存在爱。但我们毋宁说除了深深根植于性欲之外,爱不存在。”[5]146-147
像弗洛伊德等精神分析派们也举出了许多例证进行了说明。指出:人呱呱落地时就已经具有性欲,吮吸母亲的乳房时就已经开始启动自己的性欲。虽然,白村认为人类道德生活之根本的爱来自于性欲,并对两性间的恋爱基于性欲这一事实深信不疑。但是,同时他又指出,在武士道的旧道德里,欠缺对两性之间恋爱的理解。仅仅只从生殖的角度来思考两性关系,或者把两性关系当做性欲游戏。比起动物来说在人类生活里,两性间的恋爱与动物不同,两性关系不是简单的性欲作用,它会随着人类的进化而得到升华,成为至高的道德、信念和艺术。[5]8-9
白村认为世间只有极少数人才会从灵与肉两方面完全地拒绝与异性的接触。由这样的“性欲”所产生的爱之力,具有更为令人惊叹的升华作用。可以成为对真理和知识的爱欲,或变成对艺术的挚爱。如果进入虔诚的宗教生活,就会变成希求神灵欣求净土的信仰。无论是科学、艺术、还是宗教,都和热恋中的男女所陷入的陶醉境地相差无几。[5]26
五、近代日本的恋爱在中国的传播
白村的文艺理论在“五四”时期就被翻译到中国,但似乎并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五四”落潮后,白村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达到高潮,几乎所有的作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白村的影响。如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田汉、茅盾、臧克家、胡风、徐懋庸等。[8]其中鲁迅受白村的影响最为显著,起到的传播作用也最为广泛。他曾翻译厨川《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和《走向十字街头》中的《西班牙剧坛的将星》、《东西的自然诗观》等文章,并且将《苦闷的象征》作为他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讲课时的文艺理论讲稿。此外,剧作家田汉留学日本时曾慕名拜访过白村[9]。白村的《近代的恋爱观》于1923年7月由任白涛改题为《恋爱论》翻译出版(两种版本)。1928年8月夏丐尊完成了白村的恋爱部分的翻译,《近代的恋爱观》出版。共计有三种单行本在中国刊行,可推测其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传播之广泛、意义之深刻。[10]
期间创造社群体也正好立足于日本大正时期开放的都市社会,以民主思想为主导的大正思想背景和开放自由的都市人文环境使创造社这群来自封建保守、从小受过严格传统儒教文化教育的青年相对轻易地逃过了精神文化上的障碍。当中国国内的年轻人还在为新思想与保守落后的社会环境矛盾和冲突痛苦焦虑时,他们却可以在日本相对开放民主、追求人道精神的“大正民主”和“大正浪漫”中自由地呼吸。如创造社的成员郭沫若不顾家庭的反对,大胆追求日本姑娘安娜并和她同居、生儿育女;田汉留学中途回国,瞒着家人带着表妹私奔日本,后又与其同居;郁达夫和张资平陷入更深的性的苦闷之中,而终至“沉沦”。可见创造社成员对传统儒教文化的挑战、寻求真我,并以日本社会的这股“恋爱”风潮为依,开始从理论上思考理想的爱情和婚姻模式,并在实际生活中进行追求。
以上研究结果发现:首先,在明治时期“恋爱”作为西洋文化元素,通过北村的文章《厌世诗家与女性》使日本人开始认识到现实生活中恋爱和结婚的矛盾性;其次,在追求民主、人道精神的“大正民主”和“大正浪漫”时期,白村的畅销书《近代的恋爱观》中所提倡的“灵肉一致”的“恋爱至上主义”在日本社会引发了空前的反响;最后,白村的恋爱观在创造社等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群体中得到传播发展。
虽然日译词语“恋爱”从出现至今,经历了近一个半世纪的岁月,但是,“恋爱”作为人类生命永恒的主题,白村所主张的通过自由恋爱,解放个人甚至于社会、解放人类甚至于国家的恋爱论绝非一次过时的思潮,即便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也不过时。对“恋爱”的意义、解释以及与“经济”的关系仍有待于更深层次的展开和研究。
[1]柳父章.何谓翻译[M].东京:法政大学出版局,2011:1-9.
[2]柳父章.翻译语成立事情[M].东京:岩波新书,2010.
[3]北村透谷.现代文学大系1坪内逍遥·二叶亭四迷[M]//北村透谷集.东京:筑摩书房,1967.
[4]伊藤整.有关近代日本“爱”的虚伪[M]//近代日本人发想的诸形式.东京:岩波书店1981.
[5]厨川白村.近代的恋爱观[M].东京:改造社,1922.
[6]李强.厨川白村与《近代的恋爱观》[J].日本语言文化研究,2005:278.
[7]榊保三郎.性欲研究与精神分析学序[M].东京:实业之日本社,1919:1.
[8]黄德志.厨川白村在现代中国的译介与传播[J].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8(9):81.
[9]田汉.田汉文集[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
[10]工藤贵正.民国时期有关比昂松和施尼茨勒的翻译作品[J].日本亚洲言语文化研究,2001(3):1.
(责任编辑:李金龙)
I313.075
A
1001-4225(2015)06-0065-04
2015-06-14
徐青(1971-),女,上海人,文学博士,浙江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浙江理工大学2014年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基于中日教师合作教学的日语专业翻译课程改革与实践”(jgel201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