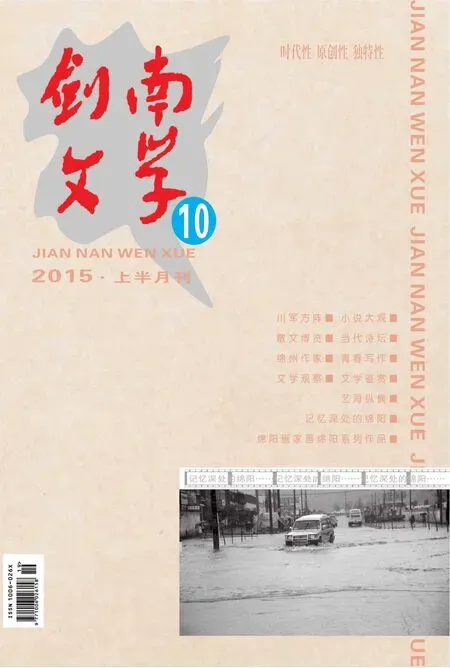中国·绵阳第一届“李白诗歌奖”提名奖得主沈苇特辑
“李白诗歌奖”提名奖沈苇授奖辞
沈苇是一个对生存世界有着极其敏锐的现代性体验的诗人。在中亚这块土地上,多样的地理风貌和多民族生活方式培育了沈苇独特的体验方式,他的诗既偏爱有力度的诗境、阔大的想象,表达着诸如生命的起源与再生、死亡与永恒、人与世界关系的哲思,又表现出充满分裂感的、渴慕的、隐疼的声音;他的诗既拥有质疑与追问的沉思气质,同时又具有深刻的同情力,如同宗教的慰籍,竭力抚平人性的创伤并蕴涵着生命与和解的信念。沈苇诗中所表现的个人体验的深度与范围,对社会更加普遍、因而也更为广阔范围内的事态的回应能力,使他能够把地方性经验转化为与时代的基本问题相关的诗学主题。他的“诗歌地理学”由此变得宽广、深邃而无限。《沈苇诗选》不仅让我们看到视觉美学中的西域,孤寂与柔情,明澈而神秘,更能让人感受到生活在那里的人所拥有的一种噬心的爱与悲伤。
沈苇获奖感言
今天,从李白诗中的西域赶来绵阳领取这个以“诗仙”命名的诗歌奖,倍感荣幸,将它视为蜀地对边疆的一种祝福,是恰如其分的。我要向李白故里的这种气度,向评委会的关爱和肯定,由衷地说一声:谢谢!
关于李白是不是一位“胡人”,这应该属于历史学家们讨论的话题。但从李白作品来看,这是一位明显西域化、中亚化和胡人化了的诗人,用另一种说法,当是一种自我与身份的转换。这位站在中国古典诗歌金字塔塔尖的歌者,同时是拥有神奇分身术的诗人:狂士、饮者、游侠、幕僚、谪仙人、道教徒、高蹈派、纵横家等等,一位多样化、综合性的诗歌圣手。这也使他的作品成为那个令人神往的诗歌时代兼具继承性和独创性的奇伟诗篇。新诗百年之际,大家都在重提继承与创新,我理解的继承就是古典精神的当代转化,用诗歌这一“重构的时间”,接上“传统”这口底气,就像李白当年所做的那样,将从诗经到乐府的传统变革出新。我相信,古典从未远离我们。

沈苇(1965-)浙江湖州人。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1988 年进疆,当过教师、记者,现为新疆作协专业作家,《西部》杂志总编。
代表作品
诗集《在瞬间逗留》、《高处的深渊》等
李白已化为我们的现实之一,是我们永在的诗歌亲人,他的许多诗篇具有当下指喻,几乎包含了对今天的诉求和祈祷。二十多年前,我从太湖畔的丝绸之府出发,坐四天三夜的绿皮火车,沿丝绸之路西行,被遥远的西域收留、接纳,从一个远游者变成一个远居者,个人命运已和这片亚洲腹地紧紧连在一起。回头一看,这是一个从有三点水的“湖人”变成没有三点水的“胡人”的过程。我用漫长的“西游记”,完成朝向李白诗中天山、昆仑、楼兰等的“致敬之旅”。边地自古多忧患,人们通常喜欢引用李白《关山月》的开篇“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却忽略了它沉痛的预言式的结尾:“戍客望边邑,思归多苦颜。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但今天在绵阳,我至少对自己、也对他人有了一点信心:肉身挣扎在沙漠瀚海,心,可以升起为一枚太白诗中的“天山明月”。
代 表 作
流 年
又一个春天轻轻降落枝头
绿色轰然作响,有些放肆、有些冒昧
风俗、景色、人群七高八低
零零落落,像艰难的诞生
被莫名的冲动和兴奋困扰
极目远眺,日子的队伍望不到尽头
就像等待圣餐的人们,焦灼又充满耐心
万物呈现了:商店、机关、工厂、寺院
身披晨光,各就各位
看哪,嫩绿的日子正赶往贫寒的家乡
赶往坍塌的老屋、不在的童年
一座废园在灵魂深处歌唱
一座废园总结好时光
我在一个黑皮本上醒来
在祖居的星球上睁开眼睛
像迷茫的公鸡,叫了两声
抖落梦的羽毛和语言的碎片
在世界边缘醒来,徜徉
抱着暗淡的决心
从零回到零,从创伤回到创伤
从源头回到源头,从沉默回到沉默
小小的颤栗的生命,大地最后的守望者
白昼大面积向下俯冲
我想起横卧地下的同类
他们有福了,如此果断地拒绝了世界
先于我向着沉默的深处大步迈进
但是,什么声音在喧嚣中说话
在人群中指出道路和卓越者
什么声音发现了我,并且议论我
一瞬间,使我恍惚经历了
从海洋到沙漠的一亿年
目睹海枯石烂、沧桑巨变、生死轮回
真的,世界比想象的还要突然
在这里趴下,在这里挣扎
在这里同流合污又超凡脱俗
时间的脚步踩过脊背
停下来,狠狠跺几脚
世界在继续,用最后的油料
开足马力前进
总有新一代降生
总有一个摇篮供我们啼哭
总有一个座位让我们坐下叹息
总有清茶、灯光、音乐、游戏
总有交媾、颤抖、撕咬、抚摸
总有肉体的腐烂和灵魂的煎熬
总有妓院在男人身上
老虎在女人心中
……
世界象一副扑克牌,其迷人的组合
像各省区的婚姻
世界的心脏,恰恰是一台疯狂运转的
机器,有时停下来,喳喳叫两声
白昼和夜晚轮番俯冲
春天之外,天空打扫干净了
百花盛开,簇拥,呐喊
仿佛打劫城池的部队在逼近
风啊风,低低地吹
惊醒睁眼睡着的人
他们跪下,麦色躯体微微弯曲
双手伸向大地,要捉住几只月亮
却翻出陈年的红薯和土豆
更为遥远的地平线,宁静而舒展
哀伤的旗帜渐渐鼓起勇气
当它终于迎风招展
整个天空都在歌唱
我打开门窗,万物涌进房间
那时日月、花木、鸟兽
是遐想中的天使、遥远时代的光荣
神的鞭子抽打我,如春光抚慰羔羊
我轻轻推开孤独和绝望
它们已在光芒中溶化
流年在剥削万事万物,我的愤怒我的宽容
与我一起攀登、上升
在一个看不见的地方,一个仁慈的所在
我小小的爱要与伟大的爱汇合
在秋天的喀纳斯
几只水鸟,撩开秋天困倦的眼帘
碧绿的湖水,不住向外扩展
环绕在湖边的山,顺势又长高了几分
喀纳斯的秋天被游人灌醉
马背上的风景,趔趄着
就要骑不稳了——
沿岸正在沐浴的白桦,从流淌的风中
伸出双手,把即将跌倒的风景
稳稳扶住
就这样被她抱走吧!哪怕陶醉片刻
有那么多游人,一年又一年不断前来
想要寻找的,不就是这种感觉么?
历经千年风霜,喀纳斯湖始终不老不衰
依偎在青山的怀抱,和青山寸步不离
用平静的厮守
——相约生死
在秋天的喀纳斯
我坚信那些背着相机的人
并不是真的在捕捉风景
正午的忧伤
你要独自去山上享用一个宁静的正午
畅饮阳光的甜橙汁,也吞服它的毒箭矢
如果你是一块岩石,需要继续锤炼
如果你是一块坚冰,将融化成水、溪流
如果你是一块油脂,正好为一盏灯点燃
你将忆起一些美,一些温暖
衰老身体上的胎记,姑娘唇边的美人痣
但除了左手与右手的相握
你抓不到另一只手,一起痛哭,消失
看上去你已历尽沧桑,这多少带点傲慢和自负
远处,雪峰闪耀的牙只咬住天空的一角
脚下,大地起伏,向着无垠铺展
阳光流泻,缺乏节制。一切都是垂直的
光线像林木,植入山谷、旷野、村庄、畜群
在周而复始的生育、繁衍之后
它们将继续受孕。一切都是垂直的
正午取消了谜团似的纠缠的曲线
事物与事物的婚姻只以直线相连
因此万物看上去单纯、简洁而深邃
在山顶,谦卑将你放入一个深渊
在山顶,如在一个阿拉伯式的穹顶
在经历了一千零一夜之后,上帝离你并不遥远
但稍等片刻,随着太阳西移
一切都将倾斜:光线,山坡,植物,人的身影
从明朗事物中释放出的阴影,奔跑着
像一场不可治愈的疾病,传染了整个大地
你活得不够漫长,所以还在孤零零地燃烧
但风景熄灭,天空渐渐暗淡
灰烬的余温会保佑你的后代
天鹅唱着挽歌,低低的飞翔擦伤了湖面
混血的城
让我写写这座混血的城
整整八年,它培养我的忍耐、我的边疆气质
整整八年,夏天用火,冬天用冰
以两种方式重塑我的心灵
它被叫做“美丽的牧场”
青草疯长成楼群
一顶顶毡房突然膨胀为城市
街上驶过杂色汽车
如同牧羊鞭下的一群
身披尘土,来自各自时间的黑暗……
它远离大海,远离浪涛拍岸
另一种浪涛拍打我——
热的血、浓的血、清洁的血、泥泞的血
在大十字和小十字相遇,融会成
同一种赤诚的血
现在,我缓步进入人群
我要记住一双双流动的眼睛——
那蓝色火焰的摇曳和凝视
无论是汉人、维吾尔人、哈萨克人、蒙古人
是时间中的兄弟姐妹
被同一种夜色覆盖眼帘
又被同一种晨光唤醒
从小西门到二道桥,从一种繁华
到另一种繁华,我的听力拒绝喧嚣
但我记住鼓声,咚咚咚发自城市的胸膛
是真正有力的心跳。还有——
孜然飘香,送来烤肉的尖叫
一串肉在火上尖叫就是一只羔羊
在火上尖叫,是一百只羔羊在火上尖叫
——多少羔羊葬身人的口腹之坟
“啊,愿你们安息。”我低声默祷
沿丝绸之路走来了
东方的贵客,西方的嘉宾
你们要在汗腾格里停一停
看鸽群如何围着一轮清真的新月盘旋
嘴里发出咕噜咕噜的赞美
仿佛它们早已熟读了《古兰经》
夏天,请从郊外摘来玫瑰
献给首府最美的女人
但美丽的女人太多,令人眼花缭乱
晕头转向,以致于浪费了玫瑰
冬天,我决定抓住你的魂魄不放
让时间的脚步慢下来,驻足稿纸
我要用火热的诗句拦截一场大雪
而每日的餐桌上,要有一份
传统的食谱:土豆、白菜和萝卜
构成感恩的朴素理由
让我再来写一写那些通宵达旦的聚会
烈酒唤醒头脑里的精灵
也惊动骨子里的恶魔
一次,当天才的程娃放肆地亵渎圣灵
我在他身上浇下半瓶伊力特
以便盛开一朵液体火焰
圣灵岂能亵渎!瞧,虔诚的基督徒大可
如何克制着内心的愤怒
这座城市已染上一点孤寂
一点享乐的虚无和忧伤的快感
我说:“出发吧。”它起身驶向未来
一路推开阳光、风沙和罕见的雨水
在无始无终的时间沙漠里
像海市蜃楼,出现,然后消失
将一具真实投进我的诗篇,充实我的表达
整整八年,我,一个异乡人,爱着
这混血的城,为我注入新血液的城
我的双脚长出了一点根,而目光
时常高过鹰的翅膀
高过博格达峰耀眼的雪冠……
- 剑南文学的其它文章
- 王昌龄边塞诗的拉康式解读
- 你为什么不幸福了(外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