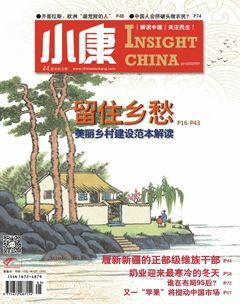诗里诗外余秀华
轩篙
等待未完,除了爱情,还有诗歌被人认可,还有走出这封闭的村庄,还有回报父母。余秀华说,聊以自慰的是,目前已经有湖南出版社和长江文艺出版社跟她联系,希望可以为她出版诗集。
近日,随着一首名为《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的诗在网络“病毒般蔓延”后,余秀华火了。这个患有脑瘫的湖北农妇,被学者沈睿誉为“中国的艾米丽·迪金森(美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她的第一本诗集《摇摇晃晃的人间》也将于最近出版。
“一个无法劳作的脑瘫患者,却有着常人莫及的语言天才。不管不顾的爱,刻骨铭心的痛,让她的文字像饱壮的谷粒一样,充满重量和力量。”2014年《诗刊》9月号重点推荐了余秀华的诗,编辑刘年如是推荐。写了16年诗的余秀华,终于被大众所识。
38岁的余秀华,来自湖北钟祥市石牌镇横店村。因为出生时倒产,脑缺氧而造成脑瘫,余秀华无法干农活,也无法考大学,高二下学期便辍学回家。从此之后,诗歌成了她忠实的伙伴。
诗歌、残疾以及私密的旅行
“你可以想象,一个农村的中年妇女心怀锦帛地坐在电脑前面,一指敲打出文字,让它们按照我的心意组合,完成一个下午私密的旅行,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美好到我心忧伤”——未完成小说《泥人》
2014年12月4日,横店村。
1个小时后,汽车导航终于败给了这个水塘密布的村庄,问了3次路,笔者才沿着曲折的田间小路,来到余秀华家门口。
5间平房两道门,这是一座普通的农村院落,略显破旧但并不衰败,院里厅堂,打扫得干干净净。因为残疾,余秀华走路摇摇晃晃,说话也模糊不清,但是当她拿起扫帚扫地时,却和常人无异。
很多年来,余秀华在家中所能做的,就是扫地、做简单的饭菜。干活时,扫帚充当了她的拐杖,一如诗歌在她生命中的角色。
在给《诗刊》配发的自述中,余秀华写道,诗歌“不过是一个人摇摇晃晃地在摇摇晃晃的人间走动的时候,它充当了一根拐杖。”
这根拐杖,让她在艰难的人生道路上自觉安稳。“当生活很单调很无聊的时候,总要有一种东西让你对生活有点希望,那就是写诗喽。”她说,正如邻居们冬日打麻将一样,自己写诗也成了一种习惯,一天不写,心里就痒。
余秀华很高产,有时候一个下午就可以写五六首诗。在搁笔良久的小说《泥人》中,她把写诗称作“一个人的私密旅行”。只不过她的旅行用一根手指完成——因为脑瘫,她只会用左手食指打字,打字的时间远远超过构思。她的电脑是2009年钟祥的网友们捐赠的,因年久失修,屏幕会随着余秀华敲字而闪动。
1998年,余秀华写下了她的第一首诗《印痕》,诗中不无悲观地称自己“在泥水里匍匐前进”。当时,她结婚已有3年,有了儿子,但“从来与爱情无缘”。时至今日,她仍坚持16年前的看法。
无怪乎在她的博客上,有网友称,读余诗,常常让人有“悲从中来,不可断绝”之感。她的残疾、她不幸的婚姻、她无法摆脱的封闭农庄,和她的诗歌对比,悲情仿佛是注定的。然而余秀华对此却不以为然:“悲伤是我人生的主旋律,悲伤的时候更容易写诗,但我不是一个悲情诗人,我高兴时也写诗。”
“对我来说写诗是一种很小我的事情,写自己的经历自己的感觉,有时候只是自己一刹那的感觉。”写诗,对于余秀华来说,是一种个人体验和感悟式的写作,她不关心诗坛,也从不去想诗歌能给她带来什么。
《诗刊》发表余秀华的诗后,给她寄来了1000多元稿费,这让她非常高兴,毕竟,“我每个月的低保救助金才60元钱。”她说。
村庄、宿命以及无望的抗争
在横店村,余秀华没有读者。
“字都认识,但不知道她写的啥,你说,她写得行不行啊?”在村口的小卖部,一位村民说,当地媒体报道后,大家才知道余秀华写诗。小卖部是余秀华经常来的地方,看人下棋,一看就是一个下午。
在余秀华的诗中,横店村是一个常见的意象,爱恨交织,充满矛盾。“我生在这里,长在这里,以后还要死在这里,它给了我一个归属。但是这个地方又不是那么好,偏僻穷困,我爱它,又想摆脱它。”
余秀华曾尝试着逃离。2012年7月,她随同乡一起去温州打工,在异乡,她第一次感觉自己有了故乡,并写了一首诗《在异乡失眠》。
但是不到一个月,新奇劲儿还没过,她就被父亲余文海叫了回来。“他不放心我,而且我手慢,挣不了钱。”那次打工,余秀华不仅没拿到工资,还白贴了两趟路费。来回40个小时硬座,302元钱。
在邻居们的眼中,余秀华有她的幸福:“有父母养着、不用做农活、整天上网。”对这种残酷的“幸福”,余秀华甘苦自知。
余秀华的诗里,宿命的色彩浓郁。她顺从于生活本身的困顿,却又不甘心只是“临摹生命的图案”,因而竭力“在命运的漏洞里获取形体单薄的快乐”。
“这样的命运谁甘心呢!在这样的一个地方,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你想飞,但飞不起来!”余秀华咬牙切齿地说。诗歌,是她穿透平庸生活的唯一的希冀。
“她的诗,放在中国女诗人的诗歌中,就像把杀人犯放在一群大家闺秀里一样醒目——别人都穿戴整齐、涂着脂粉、喷着香水,白纸黑字,闻不出一点汗味,唯独她烟熏火燎、泥沙俱下,字与字之间,还有明显的血污。”在编后记里,刘年如此评价余秀华的诗作。
“有明显的血污”,余秀华喜欢这个评价。“我写实,写我自己的生活经历,我是脑瘫,也是一个撒泼骂街的农妇,相比诗人身份,我更能接受这个身份。”她说。
亲情、爱情以及长久的等待
61岁的余文海,看起来像是刚过五十。
“其实我知道,父亲到90岁也不会有白发/他有残疾的女儿,要高考的孙子/他有白头发/也不敢生出来啊”。一年前,在诗歌《一包麦子》里,余秀华这样写他的父亲。
更多时候,在诗中,父亲不止是承苦受难的形象,还要承担余秀华的抱怨与痛诉。在引起争议的诗歌《手(致父亲)》中,余秀华声泪俱下:“来生,不会再做你的女儿/哪怕做一条/余氏看家狗。”诗中,余秀华对父亲的情感真挚而热烈,同时又充满矛盾,爱得深沉、怨得无奈。
“有人说是表达我对父亲的不满、仇恨,也有人说是表达我对父亲的爱,我自己更倾向于是爱。”因为这首诗,余秀华的读者分成了截然对立的两派。
余家有8亩田地,1亩堰塘,田里劳作全靠余文海、周金香夫妇。对于父母的辛苦,余秀华只有苦笑,“这不是对等的,应该由我来照顾他们,给他们幸福,而不总是被照顾,被给予。”
除了亲情,爱情也是余秀华诗中常见的题材,这或许因为她的爱情还未盛开便已凋零。
1995年,19岁的余秀华刚刚辍学就被安排结婚了,她无法预料,多年以后,自己会经常想起结婚时的场景,悔恨交加、泪流满面。
“他性格火暴,心胸狭窄,斤斤计较,两个人在一起就是互相猜忌、打闹,跟他结婚是我人生的最大败笔。”在采访中,对于余秀华坦言“家丑”,记者一度愣神——余秀华的直言直行、敢说敢为,或许可以解释她在诗歌中为何能够如此直白地表露情欲。
她一直渴望爱情,但从未如愿。她只能等待,等待有朝一日,春暖花开;等待梦中“没有眼鼻”的男人,为她吐出“满是玫瑰的春天”。
然而,“我都快40岁了,人老珠黄,也就不奢望爱情了,现在我等着抱孙子。”余秀华说,儿子已经18岁了,在武汉读大一。
等待未完,除了爱情,还有诗歌被人认可,还有走出这封闭的村庄,还有回报父母。余秀华说,聊以自慰的是,目前已经有湖南出版社和长江文艺出版社跟她联系,希望可以为她出版诗集。
编辑/梁 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