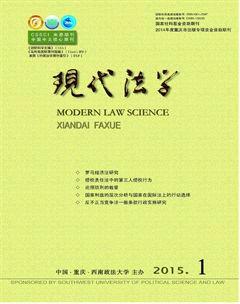挫折与修正:风险预防之下环境规制改革的进路选择
摘要:风险预防作为基础性原则正在主宰着法律体系的变革路向和精神维度,引导着环境规制从危险规制向风险规制转变。在环境规制实践中,风险预防存在纲领规定模式、规范裁量模式和制度规范模式三种适用类型。环境规制的格局正围绕着它们不断地调整、改进,但也在规制立法和规制实施层面呈现出阶段性挫折的一面。这种挫折的根源在于当前的环境风险规制采取了一种封闭式的技术规范进路。对此,应借助商谈式程序进路对其进行修正和补充,确立以“规制立法+规制决策+规制商谈”为主轴的环境风险规制新范式。在风险预防之下,这种双重复合进路对我国的环境规制改革实践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关键词:风险预防;环境规制;技术规范进路;商谈式程序进路
中图分类号:DF468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5.01.09
过去几十年间,风险预防原则毫无争议地在中国环境法的学理讨论中确立了它的灵魂地位,并被视为环境法体系发展的基础和引领环境规制改革的风向标。更有论者认为,环境法因该原则而“有别于传统秩序法”,“成为独立之法领域” [1]。在国内相关的讨论中,对此原则的反思性解读并不多见。在笔者的阅读范围内,比较深入讨论这个问题的中文文献有:胡斌.试论国际环境法中的风险预防原则[J].环境保护,2002,(6):17-20;陈海嵩.风险预防原则理论与实践反思[J].北方法学,2010,(3):11-18.但这并不意味着已成共识的风险预防不存在知识论方面的缺陷,也不代表我们在应用该原则时具备方法论的自觉。相反,在其生成伊始,相关的诘难与辩护在知识界从未止息。关于主要的反对观点,请参见:Giandomenico Majone.What Price Safety?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and Its Policy Implications[J].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2002,40(1):89-109;Frank Cross. Paradoxical Perils of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J]. Washington and Lee Law Review,1996,53(3):851-930;凯斯·桑斯坦.恐惧的规则——超越预防原则[M].王爱民,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在此,笔者并不试图在学理方面重述这个共识性的原则,而是尝试对“风险预防如何影响环境规制”这个问题作一框架式分析,整理风险预防在适用中所遭遇的难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改进之思路。
一、风险预防之下环境规制的改革诉求从环境法的发展史来看,传统的环境规制是以禁止、命令、许可等传统行政干预措施为手段的“危险(损害)排除”范式这里的“危险排除”范式是以目的为标准定位的,从手段来看,这种规制范式就是我们常说的“命令-控制”范式,它已被证明无法给我们提供有效且经济的环境保护。(参见:Richard Stewart. United State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 Failing Paradigm[J].Journal of Law and Commerce,1996,(15):585-596.),它的合理性依据是污染者负责原则。这种规制范式在传统自由主义法治理念下无疑是“依法行政”的具体表现,具有充分的正当性。其后,当环境风险随着科技进化和“知识的不确定性”全面干扰社会生活之时,国家的角色随之从自由秩序之“夜警”和公共福利之“提供者”转变为加载了“风险规制”功能的复合体[2]。但遗憾的是,环境法律系统的改进并没有与国家规制任务的变迁保持同步。在传统法律秩序下,行政分支对环境风险规制缺乏明确的操作经验,立法系统更无法为风险之源和风险之后果的规制提供规范上的可靠预期,而通过个案判决分配责任来应对环境风险的司法进路也被证明收效甚微[3]。总之,传统法无法为环境风险预防提供丰富且精确的措施,在此背景下,风险规制无疑成了当下环境公共政策演变和法律结构转型的主导逻辑,也自然成了证成行政国家合法性的着力点[4]。事实上,知识界和政府一直都在为建构风险规制的知识和制度体系而持续努力,为了规制环境风险,他们将风险预防从一种“国家承诺”式的政治原则提升为法律系统的一般原则,并将它视为一种“教义上的工具”,借此把环境保护这个政治目标在不损害法制稳固性的同时引入了法律体系[5]。在此基础上,环境法——甚至整个法律系统——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即从对环境损害的救济转向对环境风险的规制和预防。
现代法学杜辉:挫折与修正:风险预防之下环境规制改革的进路选择从这种变革的路向出发不难判断,风险社会无疑要求委身于其下的法治变革将风险预防和风险规制视为公共生活的基本价值加以倡导,并以此为标准裁剪制度、拟定政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社会、世界的外在变化直接对环境法的内在体系提出的历史性任务。与这种法治变革路向相对应的是:一方面,风险预防在近几十年来获得了广泛的国际支持[6],在国际环境法领域迅速占据了核心地位[7];另一方面,该原则也迅速成为诸多国家或地区环境规制政策的来源和变革驱动力,指导着政府“决策于未知之中”风险预防引领的国内风险规制发展与变革不仅体现在环境保护领域,还体现在食品药品安全、生物技术发展、职业安全和健康、有毒物质、核能利用等领域。在这些领域中,“风险”和“不确定性”是规制决策无法避开的关键词。(参见:David Freestone,Ellen Hey.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G]//David Freestone,Ellen Hey.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and International Law: The Challenge of Implementation.The Hague:Kluwer Law International,1996:3-18; Marjolein B.A.van Asselt and Ellen Vos.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and the Uncertainty Paradox[J].Journal of Risk Research,2006,9(4): 313-336.),甚至演变为政府环境规制系统之合法性的评价和理解框架[8]。比如,欧盟委员会早在2002年就通过《关于预防原则的委员会声明》将风险预防原则正式纳入公共决策的考量表,欧盟法院也在诸多司法判决中援用此原则,甚至将其视为主导判决的决定性因素[9]。无独有偶,在美国的司法判例中,风险预防原则同样被坚定地援用。在著名的Ethyl Corp. vs.EPA案中,法院在审查《清洁空气法案》时第一次明确了支持“在环境影响尚未确定的情形下采取积极的预防措施”的司法立场。参见:Ethyl Corp.v.EPA,541 F.2d 1,24-25(D.C.Cir),cert.denied,426 U.S.941(1976).由此可见,在世界范围内,风险预防的制度建构和适用已经上升为不同权力分支的重要职能,“风险”、“风险预防”、“风险规制”等概念正在主宰着法律体系的变革路向和精神维度。endprint
二、逻辑转换下的先决问题:环境规制中风险预防的适用类型风险预防到底是如何影响甚至决定环境规制重心和范式转移的?在回答这个问题时,环境规制实践的系统性和复杂性要求我们对其作一个严谨的、学术上的逻辑转换,即“风险预防在环境规制中是如何适用的”。风险预防不同适用方式所主张的内容及其体现的制度能力将决定环境规制在制度中的内在逻辑和外在结构,亦是评价风险预防对环境规制改革的影响效果的前提,更是分析风险预防之下环境规制的现实困局和未来走向的切入点。在这种背景下,厘清风险预防的适用方式,无疑是理解环境规制发展与变革的先决问题。
(一)纲领规定模式:以“国家承诺”为形态的政治化适用
在政治哲学意义上,环境风险的不断增加和复杂化引发了国家的合法性危机,而保护基本权利、提供社会福利这两个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任务已不能给其提供有效的合法性补充,国家的任务面临新的扩张。在这个背景下,很多国家将风险预防作为一种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对人民的承诺”提出来,并把它纳入各党派和政府的纲领性文件之中,比如,德国政府1970年制定的近期纲领和1986年发布的《环境风险预防》等纲领性文件都强调了风险预防作为政治原则的重要性。在澳大利亚,风险预防也被引入到《生态可持续发展国家战略》和《政府间环境协议》这两个纲领性文件之中,作为行政决策者的工作原则[10]。在这种适用方式之下,风险预防的要旨是“尽可能地仔细评估,以避免对环境造成严重且不可逆的损害”,同时“对不同的备选方案的风险权衡后果进行评估”[10]254。
政治化的适用方式通过对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的渗透为国家设定了新的价值取向。具体而言,就是要求国家在风险社会之下因势而为,将环境风险规制视为其合法性的当然补充,在对传统社会发展模式、制度规范、社会伦理和文化心理结构彻底反思的基础上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引领这类批评与反思的思潮,他的理论为我们重新理解这个社会的核心机制(财富分配还是风险分配)提供了智识资源。(参见:贝克.风险社会[M].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15-57.),重新谋划社会发展蓝图,保障环境安全和公民的环境权利,实现代内公正和代际公正。
但需要注意的是,政治意义上的风险预防常常被当作国内和国际政治谈判的新筹码,出现在繁杂的软法性文件之中,因此,政府或政党实施风险预防纲领的行为还不能在法理上与现行法律秩序相抵触。在成为法律原则或制度之前,任何以风险预防为理由限制自由权、财产权或者宣布所实施的限制措施合法的行为都是非法的。风险预防的泛道德化、泛政治化及其类似的表达方式尚不能对环境规制产生直接的、决定性影响。
(二)规范裁量模式:以“国家义务”为形态的宪法化适用
一般认为,宪法产生于“前工业化”时代,因此它的落脚点是保障个人自由,对社会风险尚未作出系统性回应。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宪法客观上要对“如何应对风险”这个现代性问题提供妥当的解决方案。理论界和立宪者都在探寻一个面向社会风险的宪法,构建应对社会风险的国家责任和基本权利。从现有立法例来看,我国《宪法》第26条“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之规定可以被视为《宪法》对于环境风险的粗略规范。但它的内容尚不明确,没有对环境风险预防的国家目标和进路作出完备的宪法安排。相较而言,《德国基本法》第20A条所言之“国家为将来之世世代代,负有责任以立法,及根据法律与法之规定经由行政与司法,于合宪秩序范围内保障自然之生活环境”,则更为精当地展现了风险预防的宪法适用。该条在理论界被解释为德国的“立国精神”,它的性质是在民主国、社会国、法治国、联邦国之后,确认德国“环保国”的属性。(参见:黄锦堂.环境宪法[G]//苏永钦.部门宪法.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6:709-748.)一方面,它虽然没有赋予人民那种“向国家主张”的主观权利,但作为基本价值,它对基本权利条款之“客观法”属性的解释有指引功能。在德国的宪法理论中,基本权利具有“主观权利”与“客观法”的双重性质,在客观法的属性方面,基本权利被认为是德国基本法所确立的客观价值秩序,对国家权力产生直接约束力[11]。因此,在积极的层面看,本条的具体功能是通过立法委托(当然还有后续的行政拘束、司法引导)的方式推动国家尽一切可能去创造和维持有利于基本权利实现的条件。另一方面,从消极的维度来看,它导出了国家在环境风险领域的保护义务,暗示国家负有保护国民的生命、健康、自由以及财产等方面的基本权利以及宪法所承诺的制度免受环境风险侵害的义务[12]。
综上,这种宪法化适用方式实质上是将风险预防视为相关环境立法的基础性裁量规范,目的是敦促立法者提供符合公众期待的良法。在这个功能之下,公民得以要求国家经由立法要求污染者提供防护措施、对排污许可设定条件与程序规范、为环境规制的决策主体和程序设定合法性标准、为政府环境风险规制的宽严松紧设定风险评估体系等。在规范裁量模式的意义上,风险预防对拟订环境法律和政策、塑造环境规制的方案具有导向意义,是判定环境法律关系、创制环境风险规制措施的准据。
与政治化适用类似,风险预防的宪法适用亦非坦途。一方面,关于风险预防宪法制度的范畴和实现方式仍未明确,它的内在机制和合法性缺乏有效的表现形式,造成了相关宪法实践的非规范性[13]。另一方面,它也会引起基本权利冲突和规则混乱。以我国宪法规范为例,从法教义学的视角出发,“人权条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与“环境条款”(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结合能够推衍出“公民环境权”。当立法者为了保障公民环境权而依据风险预防原则制定法律和规制措施时,不可避免地会侵犯公民其他的基本权利(尤其是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形成环境权对抗、限制经济自由权的困局。但是对于如何化解基本权利冲突,理论界和实务界尚不能提供有效的方法。此外,风险预防原则内涵的“模糊性”(vagueness)决定了它无法作为相关规制决策的直接基础[14],因为规制者无法在拟议和实施规制的过程中确定“何种程度的预防才是适当的”。加上环境风险的类型和规制机构具有多样性比如在中国,具有环境保护行政职能的机关就非常多。,它们对规制规则和措施的需求不尽相同。这两个因素给规制决策者任意解释风险预防原则提供了契机,规制者建构的规制体系无疑将被烙上“实用性、渐进性和可颠覆性”的印迹[15],从而缺少统一性。endprint
(三)制度规范模式:以“责任义务”、“证明责任”和“技术强制”为形态的具体化适用
明确国家的政治责任和宪法义务仅仅是风险预防适用的初级阶段。当上述两种适用方法遭遇无法克服的难题时,政府试图通过建立健全具有强制性、约束性的制度规范的方式,使风险预防转换为一种法律上的责任义务或许可授权条件。从世界范围内的立法例来看,这种具体化适用进路也得到了重视。比如,德国的《有害影响预防法》、《联邦自然保护法》、《循环经济和垃圾处理法》、《环境影响评价法》等重要法律先后确立了相关制度。在美国,尽管它常常在国际领域中质疑风险预防原则,但该原则却构成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第一波环境立法的基础,《清洁空气法案》、《水污染防治法》等规制性法律都在一定程度上将风险预防原则予以具体化适用。(参见:Daniel Bodansky.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in US Environmental Law[G]//Timothy ORiordan, James Cameron.Interpreting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London:Earthscan Publications Ltd.,1994:204.)我们姑且将其称为“制度规范模式”。
1.围绕“责任义务”建构的管理性规制措施
这些规制措施主要包括环境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环境标准等。环境规划是风险预防具体化适用的第一步,它代表国家的环境规制策略已从消极的“污染管制”转向了积极的“环境管理”[16]。环境影响评价则要求政府机构和事业开发者在拟定政策或开发计划时事先评估其对环境的可能影响,以此来预防环境损害的发生。环境标准(包括排放标准和品质标准)则通过科学技术要求的法律化为排污者设定了一个“明显可预见危险的最低限度”[16]426,给排污者设定了可预测的行为边界,并且通过行政处罚、刑事责任等方式来保证标准得以遵守。
这三者之于环境风险规制的意义在于:(1)它们是国家借助相关科学技术专家利用科学方法分析或预测的数据、结果,来把握环境风险的程度、社会的承受边界和管制目标的有效制度。透过对可能污染的数量、性质、环境条件等方面要素的综合分析,使原本抽象的环境风险的概念经由数据具体化为可供义务人遵循与主管机关执行的具体行为义务。(2)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环境风险的范围在法律上的确定,是平衡环境利益与技术、经济等对抗性利益的有效方法。(3)它们各自界定出政府规制介入的时点。
2.围绕证据建构的方法性规制措施
这种规制措施的常规形式是转移证明责任、降低证明标准和证据推定。
其一,在传统法律理论之中,规制者担负着某一行为和产品具有“危险性”进而需要采取适当规制措施的证明责任参见:APA,5 U.S.C.§556(d).,但在风险预防之下,一部分环境规制法律将证明责任转移给生产者及其支持者,要求他们对“相关行为或产品对于环境而言是安全的”承担证明责任。比如在美国,《有毒物质控制法》(TSCA)规定环保署在筛选新化学品时,应要求物质或混合物的生产商或加工商对有危害风险、暴露风险的化学品进行测试,以确定是否对健康或环境有不利影响。参见:TSCA,15 U.S.C.§§2604-2605.又如,《联邦杀虫剂、杀菌剂和杀鼠剂法》(FIFRA)并没有将证明新型杀虫剂有害的责任配置给环保署,而是要求生产者证明新型杀虫剂不会“给环境带来不合理的不利影响”。参见:FIFRA,§3(C)(5)(C),7 U.S.C.§136a(c)(5)(c).这种“规制者→被规制者”、“危险性→安全性”的主体和标准双重转换意味着,在风险预防影响之下,环境法律的规制假设变得更为严苛,即“除非能证明不应该实施规制,否则就应该实施规制”。当然需要注意的是,证明责任转移并不是建立在对风险严重性的简单考量之上,它毋宁要求立法者和规制者综合考量“风险是新型的还是旧有的”、“风险是否常见”、“风险是人为的还是自然的”、“风险是否显而易见”等相关要素。若非如此,在立法论上,不对风险作出类型和程度区分,一刀切地将证明责任转嫁给被规制者,将会混淆各种利益的位阶关系,从而引发权利或利益冲突。
其二,大部分的环境规制法律没有采用转移环境风险证明责任的规制方式,而是通过降低环境风险的证明标准来扩大规制的适用范围。尽管在现有的立法例中,不同的环境规制法采用不同的语言来描述规制行为的证据标准,但它们的旨趣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都不要求实施规制的证据具有科学上的确定性。因此,这种规制方式的通用表述应当是“缺乏充分确凿的证据,不应成为排除规制的理由”[17]。再以美国立法为例,《危险物质控制法》允许环保署在有相对合理的理由确信化学品存在或可能存在危及人体健康和环境品质的风险时就采取相应的规制措施。参见:TSCA, §6(a),15 U.S.C.§1605(a).与之类似的是,《清洁空气法案》也允许环保署在“有可能危及公共健康或福利的情形下”对汽油添加剂予以规制。参见:CAA§211(c)(1),42 U.S.C.§7545(c)(1).
其三,政府还在规制实践中发展出了新的证据适用方式,即基于证据的风险推定。在实践中,规制者常常以物质的类似程度来推定未知物质的危险程度,或者以某种物质对动物有害推定其对人类健康亦有风险。以动物实验类推于人类的证据推定方法肇始于食品安全领域的食品添加剂风波及其规制实践。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是“德莱尼条款”,依据该条款,如果某种食品添加剂在动物中引发了癌症,那么这种添加剂就属于致癌物质,是一种严重的健康风险。(参见: 21U.S.C.§348(C)(3)(A).)基于证据的风险推定也获得了法院的认可。在EDF v. EPA案中,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就支持环保署在某种物质的危险性尚不明确时适用“类比”的方法进行推定,以决定是否将其纳入规制范围。参见:EDF v. EPA(The “PCB Case”).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甚至声称,只要推定获得了大量著名科学知识的支持,规制机构就可以自由适用证据推定规则,因为过度保护总归优于保护不足。参见:Industrial Union Department v. American Petroleum Institute (The Benzene Case), 448 U.S. 607 (1980)endprint
3.围绕“最佳可得技术”建构的技术性规制措施
规制者还通常会对污染源提出“最佳可得技术”(best available technology)的规制要求,以此更直接地应付各种不确定性。所谓“最佳可得技术”是指那些“发展到一定规模的,对环境规制最有效,符合经济、技术可行性,能够被合理地获得并被允许适用到环境污染防治领域的先进技术”。更具体的论述,请参见:Best Available Techniques Guidance Notes [EB/OL].[2014-04-08].https://www.epa.ie/licensing/info/bat/.在这种规制措施之下,规制者和被规制者对于采取何种技术或者是否采用最佳可得技术都没有选择权,并且对于被规制者而言,如果他们无法证明“不存在可感知的危害风险”,就必须采取最佳可得技术将风险降至最低。
三、风险预防之下环境规制的挫折:从规制立法到规制实施的多重困境从世界范围内的规制实践来看,环境规制的格局正围绕着上述三种适用方法不断重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由于立法者、规制机构和公众对环境风险的本质、类型和规制序位存在巨大的认知差异,加上科学的确定性与风险的不确定性之间、规制规范的确定性与民意的不确定性之间的持续张力,环境风险规制在规制拟订和实施层面都显示出阶段性挫折的一面。
(一)立法者的风险意识滞后且易受外力影响,使环境风险规制议程具有很大的随意性
对于立法者而言,风险预防的题中之意是提前拟订法律以预防环境风险,但要求立法者对环境风险具有“先见之明”,难免过于苛刻。一般而言,立法者的风险意识与危机程度(风险转变为现实危害的概率及其影响)密切相关。概率越高(损害越高)越容易进入立法者的立法议程,反之,概率越低(损害越低)越容易被立法者弃置不顾。此外,立法者的风险意识还受媒体舆论、政治团体的运作能力、政治领导人的表态、民众的请愿等因素的影响,充满浓厚的利益衡量和选择性格[18]。例如,环境风险的相关知识或者涉及环境风险的案件、事实被媒体报道,会给立法者提供风险规制的立法动因;一个政治团体(或群体)环境风险意识的高低及其政治运作能力,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某一部环境风险规制决策能否获得通过;在我国这种政府主导国家立法的体制下,政治领导人的态度对环境风险立法的影响也是决定性的;民众的请愿(如我国近年来各类环境群体事件)也是环境风险规制立法中不可忽视的社会风险因素。立法者的风险意识滞后和各种影响因素决定了环境风险进入立法议程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一些危害极小的环境风险受到严格规制,而一些危害极大的环境风险却没有进入规制议程。
(二)立法者无法确定环境风险规制的目标与范围
环境风险规制立法受到公众和专家两种相互冲突的风险认知方式的影响。面对未知的环境风险,立法者不具备关于风险的完整知识,因此也就无法借助既有的规制经验来拟订风险规制规则,它需要求助于公众对风险规制的诉求和专家对风险的科学评价。然而,公众和专家对环境风险的本质、严重程度、评价方法的认知完全不同。公众对这些问题的认知往往基于(恐慌、与害怕相关的)经验或直觉,专家则更多地通过科学的分析方法进行判断。不同的认知路径决定了公众和专家在环境风险规制目标的厘清、范围的划定和方法的选择等方面会存在重大差异。在这种情势下,公众借助价值判断(合法性标准)来影响立法者,以使环境风险规制立法符合公众的心理期待;专家则借助科学的知识(科学性标准)来影响立法者,以使环境风险规制立法符合理性。在合法性考量和科学性考量之间,立法者很难充分平衡两者的关系,致使立法者无法给出环境风险规制的“合宜目标和范围”[19]。
(三)立法者无力对环境风险领域作整体式、体系化考虑,致使环境风险规制体系混乱
立法者拟订环境风险规制政策时往往采取“一事一案”的立法思路,缺少对环境风险领域的整体式、体系化考虑。其一,立法者将环境风险规制职能赋予不同的主体,造成环境风险规制决策的分散化,增加了不同规制决策之间冲突的可能性。比如,我国实行“统一监督管理与分级、分部门管理相结合”的环境规制体制,不同规制机构依据不同的标准行使职权,环境风险规制的实施很难统一。其二,立法者提供的环境风险规制决策有时缺乏可行性,有时又过于严苛。比如美国《清洁空气法案》要求环保署在规制有害物质排放时可以依照“安全边界”标准要求企业“零排放”,而环保署则认为这种立法要求极为不合理,既违背了风险预防的初衷,也过分限制了产业的发展,因此在规制实践中拒绝适用[20]。其三,囿于组织结构、程序条件和能力的限制,立法者无法持续地收集和分析信息以便给环境规制机构设定详尽的规制议程。其四,立法者无法把握风险预防的“内在不一致性”(inherently incoherent)[21]而使环境风险规制决策陷入瘫痪。风险预防原则本身在逻辑上有“内在不一致性”的瑕疵,一种风险规制措施可能引发“替代风险”[22]或者提高另一种风险的发生概率,进而使规制陷入“风险vs.风险”的混乱之中。 关于风险预防引发的副作用及相关解释,请参见:John Graham,Jonathan Wiener. Risk vs. Risk:Tradeoffs in Protecting Health and the Environment[M].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 Goklany.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Environment Risk Assessment[M].Washington, DC:Cato Institute,2001.比如,对核风险的过度规制将加重大规模使用化石燃料带来的空气污染问题。
(四)环境风险规制中存在大量规制失灵现象
主要表现为:(1)过度规制与规制不足并存,这是环境风险规制的显著特点。一方面,规制机构对相关事业者的干预超出了应有的程度,限制了事业者的自主经营权;另一方面,严苛的规制规则一旦被实施,就“不得不顺理成章地规制到一个不合理的地步”[19]120,因此被规制机构束之高阁。规制规则的悬置造成了事实上的规制不足,比如,“最佳可得技术”措施忽视了不同企业之间和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严格实施会使大量企业面临倒闭,因此环保署干脆对很多物质不加规制。(2)规制成本与效益失衡。布雷耶曾指出,规制者为了清除“最后10%”的环境风险,常常付出与之不相称的高昂成本[23]。在政府的风险规制资源有限和配置能力不足的背景下,“零风险”的规制策略并不具有可行性。(3)规制措施不协调。一方面是不同环境风险规制机构对环境风险的认知不同,因此在评估方法和应对策略的选择上各有差异;另一方面则是同一机构在不同环境风险的规制策略之间缺少协调性。(4)规制议程混乱。规制实施中同样存在议程随机性的问题,环境风险规制议程在很多时候并不是根据风险的严重程度与规制的可行性确定的,而是受到公众的恐惧、政治、历史或偶然因素驱使[23]25-29。(5)规制中的裁量权失控。行政自由裁量权渗透于风险规制进程的各个环节。在行政立法过程中,规制机关需要根据立法给定的风险预防目标来确定实现的路径和手段,它对风险预防的理解、对立法机关的指令以及风险规制的手段、技术和路径的选择,都涉及自由裁量。在规制实施过程中,规制机关要对立法尚不明确或者留待选择的问题进行事实、价值和法律方面的判断、取舍与执行。但由于条件和能力的限制,规制机关常常无法获得可以对未来事态的发展作出确定性预测的事实和可比照的类似经验[24]。尽管不确定性不能成为阻碍风险预防的理由,规制机关自由裁量权的盲目扩张确实也给规制权力的合法性带来了冲击。尤其是在证明行为和环境风险之间因果关系的证据尚未明确之前,如果采取强硬的风险规制,不但成本高昂关于环境风险规制成本过于高昂的讨论,请参见:凯斯·桑斯坦.权利革命之后:重塑规制国[M].钟瑞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92-93.,而且由于规制者对产生风险的“特殊因素”、“关系”、“模式”和“参数”缺乏科学的认知理解[25],很多规制决策难免滑入主观随意的“不确定性”深渊一般来看,不确定性分为“多变性引起的不确定性”(variability uncertainty)和“知识有限引起的不确定性”(epistemic uncertainty)。前者与多变甚至随机的系统行为相关,后者与人的认知能力和理性极限相关。(参见:W. E. Walker,P. Harremoes,J. Rotmans,J. P. van der Sluijs,M. B. A. van Asselt,P. Jansen and M. P. Krayer von Kraus.Defining Uncertainty: A Conceptual Basis for Uncertainty Management in ModelBased DecisionSupport[J]. Integrated Assessment,2003, 4(1):5-17.)这两者共存于风险规制之中,并且知识和不确定性之间并不是连通器式的相互关系,即知识的增进并不意味着不确定性的减少,相反,在风险规制中,知识的增进可能会进一步加剧规制决策的不稳定性。,进而遭遇合法性与合理性质疑,最终软化比例原则对规制活动的约束。endprint
(五)错误的规制实施引发利益失衡
环境风险规制法律关系中的利益相关者包括规制机关、被规制之事业者、风险波及者。被规制者和风险波及者的力量对比关系与它们的组织化程度密切相关,呈现出不同的博弈样态。由于受到规制俘获机制的影响,规制机构在执行宽泛的规制指令时“不公正地偏向有组织的利益,尤其是那些受管制的或受保护的商业企业利益以及其他有组织集团的利益,而损害分散的、相对而言未经组织的利益”[8]24-25。规制机构之所以如此选择,是因为规制机构、被规制者和风险波及者存在严重的利益分化。在这个三角关系中,规制机构代表“制度利益”[26]和公共利益,被规制者代表产业利益和企业利益,风险波及者则代表生存利益。被规制者的组织能力和政治影响力使其在利益博弈中处于强势地位,可以在公共利益和产业利益之间自由切换,将规制机构的利益目标从制度利益、公共利益置换为部门利益。
四、技术规范进路与商谈式程序进路之间:挫折之源及其修正作为风险预防最为核心的政府规制遭遇阶段性挫折,使得风险预防的相关要求及其制度推进,比如均衡性、非歧视性、一贯性、成本计算、新科学知识的再判断、举证责任等方面这是欧盟《关于风险预防原则的公报》中确立的采取风险预防措施的一般要求,现在已被公认为风险预防适用时的行动准则。,都遭到了全面的质疑。只有厘清当前环境风险规制的建构路径,以及全面反思规制的经验和教训,才能有效解释这种挫折的根源并找到补救的方案。
(一)技术规范进路:环境风险规制的挫折之源
笔者认为,政府将风险预防嵌入公共行政过程的方式是决定环境风险规制成败的关键,因此,环境风险规制的挫折之源在于政府采取的以立法规范为准则,以科学技术为核心,以单一行政规制为手段的封闭式规制模式,我们姑且称其为“技术规范进路”。
1.在风险认知与沟通方面,技术规范进路坚持科学与价值的二分
在环境风险规制实践中,科学与价值的二分必然导致专家认知模式和公众认知模式的对立。专家认知模式认为公众缺乏关于风险的必要知识,公众对风险的判断是一种价值判断和主观感受,价值具有多元性和相对性,主观感受与客观上科学存在之风险之间存在巨大差距。所以,公众对风险的认知在很多时候是错误的或非理性的[27],规制决策也会随之陷入错误或非理性。公众认知模式则质疑科学客观性的存在,认为纯粹以科学为依据的规制决策有合法性问题[28]。在民主国家中,普通人的直觉更具规范性,公众的观念应当作为环境风险规制的主要标准[29]。这两种认知模式都否定了风险理性之下风险知识的平等化特质,专家和公众很难在风险成因和规制选择方面达成最低限度的共识,导致政府的风险决策常常滑入权力恣意或民主无效率的两难之中。
2.技术规范进路重视规制立法,忽视规制过程
这种进路强调规制立法和政策系统的科学公正性和社会公正性,将规制机构定位为立法者的“传送带”[8]12,它的任务就是在法律框架内对各种信息进行梳理、取舍和应用。因此,规制机构的裁量权受到严格的限制:根据无法验证的证据进行规制,应被控制在最低限度内;风险规制的实施必须建立在严格解释立法、确定客观知识和获取公众偏好的基础之上。但是,“风险是因可能性的增加、扩大而引起的,很难通过规范来解决与风险相关的问题”,“风险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不可计测性很难通过法律和政府举措来缩减”[30],风险的边界也无法通过法律规范来确定,这在客观上要求环境风险规制必须对政治、经济、社会影响、当地特质等因素,以及国家发展状况、公众的选择等项目进行综合评估,在规制过程中达成规制共识。
3.技术规范进路在组织层面倚重科层制,轻视公众参与
在风险理性之下,风险知识的平等化是风险规制的基础,它对于公众参与环境风险规制尤为关键。由于在现实的规制实践中,科学知识优于公众知识、立法系统重于规制过程,以致现有的规制系统必须围绕科层政府来建构,这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公众参与的机会。稳定的科层制固然能够增强政府机构对国家规制立法的敏感性和重视程度,但潜伏着的异化危机时刻威胁着环境风险规制的实际成效。
4.技术规范进路不关注风险规制中的利益衡量
政府在环境风险规制之中必然要比较各种不同的利益,并选择优先保护的利益类型。但是,政府环境风险规制立法或政策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权利指向,规制实施也时紧时松,所以,权利的位阶在风险规制中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此时,当环境风险规制所涉及的自由权利(财产自由和合同自由)与环境权利的平衡与取舍无法依据权利位阶方法解决时,就只能救助于利益衡量的方法。利益衡量方法要求规制者将风险规制决策与基本法律价值、社会成员的意愿、经济秩序等要素的关联度予以整体考量,当以“后位利益”限制“前位利益”时,应赋予规制决策者较重的说理义务,反之,当以“前位利益”限制“后位利益”时,则承担较轻的说理义务。但在技术规范主义进路之下,规制者往往采取一刀切的利益决断,认为环境利益、健康利益构成了对财产利益、自由权利的当然限制。同时,该进路也忽略了利益位阶的变动性,即“前位利益”和“后位利益”所对应的利益类型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也就是说,并不是在所有的环境风险类型之中,环境利益、健康利益都绝对优先于财产利益和自由权利。
5.技术规范进路缺少合作规制的空间
环境风险规制的技术规范进路沿袭了自上而下的政府命令控制结构。在这个规制结构之中,规制机关在环境风险规制的议程设置、风险评估、风险沟通、风险管理等各个环节中都处于绝对支配者、领导者的地位;被规制者和风险波及者则处于服从规制机关命令和政策的地位;专家为规制决策提供合法性与合理性论证;一般公众则居于规制结构的边缘,被动接受规制者发布的决策、信息[31]。这种规制结构与现代社会治理对网络式的合作治理或合作规制的呼求并不匹配,自上而下的官僚化规制系统没有给公、私部门与社区、非营利组织的参与治理预留空间,限制了不同主体间的互动互信、资讯流通和资源互补,以致不同主体之间的高度对抗性、规制规则僵化、实施前后矛盾等问题日益涌现,给规制机关带来了沉重的负担[32]。endprint
(二)商谈式程序进路对技术规范进路的修正
以稳定性和可预测性为尺度的法律体系在面对风险规制命题时,它的权威性和可靠性都被大大削弱了,现有规制系统的失灵放大性地凸显了公众对依靠法治因应环境风险的信任危机,导致环境风险规制法治系统的形式化任务在尚未完成的情势下,就陷入了民主(民意)与科学(专家意志、政府意志)的持续拉锯之中。在这个时候,承前所述,单纯依靠法律条文、专家知识、行政措施的风险规制已经难以满足实践的需要,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围绕多元的主体、动态的相互关系建立起开放式的规制结构,以“规制立法+规制决策+规制商谈”为主轴确立新的环境风险规制范式。
围绕这个变革命题,相关学者提出了诸多有益的修正模式。比如,桑斯坦提出了“恐惧的规则”以及利用“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制约风险预防的思路[22]101-138。但从其属性来看,这种思路依然是一种技术性的修正进路,忽视了风险规制实践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对权利体系、权力制衡、法律控制进行了新的解读甚至改写。所以,修正现有的环境规制系统的工作必须建立在一种新的立宪主义逻辑之上,对此,英国学者费雪教授提出的“商谈—建构范式”是更有价值的尝试。在她的理论脉络中,规制立法并不是一套“严格”、“冷冰冰”的命令集合,“而是更接近一部宪法”,为规制机关行使裁量权提供了系统性的原则和广泛的考虑因素;规制机构也不仅是立法者的代言人,它们是有自由意志的“独立政治机构”。商谈过程则是多方主体合意交流和对抗交流的过程,与过度回应特定政治利益的传统政治过程相隔离[28]40-42,通过公共理性引导利益冲突,缓和科学与民主之间的紧张关系。通过商谈过程,风险和知识的不确定性转化为确定性的程序性机制,容纳风险评估中“事实和规范混合的复杂性”,保证规制者高效“行使实质性的、持续解决问题的裁量权”[28]39,最终提升了规制实施的灵活性。
借鉴费雪的思路,笔者认为,环境规制系统围绕风险概念的未来变革应侧重于以下几个主题:其一,融合科层组织和网络化组织在处理风险时的路径和绩效,发挥多部门规制方式、共同体规制方式以及命令控制规制方式的集合效应;其二,建立风险规制的系统和信息交流机制,更多地依赖风险信息披露而不是由政府单方规定“何为适当的风险水准”关于信息交流作为风险规制工具的功能优势,请参见:金自宁.作为风险规制工具的信息交流:以环境行政中TRI为例[J].中外法学,2010,(3):380-393.;其三,建构标准化的风险决策程序,借助一系列的风险决策程序,确保风险决策的可预见性,也使专家的科学判断和公众的价值判断得以交流;其四,风险认知的多元性和最低限度风险共识的统一;其五,构造风险共同体作为基本的规制单元,并以此重新审视法律、公共行政及其责任性等问题,充分考虑风险规制的非法律模型[33]。
笔者将这种修正方案称为“商谈式程序进路”,其与“技术规范进路”共同构成了环境风险规制的完整系统。围绕上述5个主题,商谈式程序进路的宗旨是要在主体多元、公开透明的话语空间中确立符合公共理性和科学,并且可以在同等条件下不断再现的共识,以及相应的可以统一适用的规则体系。它的功能优势在于,“通过‘怎样作出决定的程序共识来实现‘共同承认这样作出的决定的实体共识,并使之具有强制执行的力量”[34]。它对技术规范进路的补充使当前环境风险规制中的合作规制、不同知识的对话、规制过程的开放性、利益衡量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矫正。
表1:技术规范进路与商谈式程序进路之要素比较本表中的部分变量借鉴了费雪教授的研究成果,同时也是对其所分析变量的补充和完善。
技术规范进路商谈式程序进路框架规制规范(政策与法律)规制结构(政策法律、规制过程)对象客观的、可计算的风险复杂的社会政治和价值争议目标消除风险达成可容忍的风险判准行政效率沟通效率方法计算风险过滤风险角色专家知识与公众知识对立风险知识的平等化组织科层制网络化责任监督规制者在立法框架内行事对决策过程进行全过程实质性审查知识为规制提供依据的理性专业知识进入规制过程的所有知识交流自上而下的信息与命令输出商谈五、余论:对我国环境风险规制改革的启示回到我国的环境规制实践中,这是比简单谈论一般理论和经验哪个更为重要的命题。不可否认,无论是在制度建构层面,还是在规制实践方面,我国的环境风险规制与域外先进国家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但由于中外的环境法律制度体系存在某种程度的相近性,环境风险规制中的诸多难题也具有共通性,因此,域外国家在环境规制改革中遭遇的困境也会在我国以相似的形式呈现出来。这样一来,上述风险预防的适用类型以及在其之下的环境规制改革的双重思路,必然对我国的环境规制实践有很好的启示意义。
第一,在总体上,应坚持“技术规范进路”和“商谈式程序进路”并重。技术规范进路的重点在于完善规制立法和政策,以及为商谈确立切实可行的程序、标准和规则。商谈式程序进路的重点则是建立多元、动态的弹性结构,包括科层制内部的向下放权和外部的向社会放权。就前者而言,就是要疏通科层内部关于环境风险规制的商谈通道,将“法律制度协调统一”和“地方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内环境资源的状况因地制宜地行使环境行政权”相结合,防止环境立法在向下运行的过程中被悬置、异化[35]。在我国环境保护职能配置“条块分割”的格局下,这一策略显得尤为必要。就后者而言,是要打破独断的风险规制活动,强调公众的“在场”,以各种方式就环境风险的性质、可容忍程度、规制措施以及环境风险规制的绩效与规制机关进行对话和论辩,让公众理性、竞争性地表达其对上述问题的观点,从而不断在实践中保持风险规制的合法性、合理性。在我国环境公众参与严重不足的现实情境下,这一路径亦值得重视。
第二,应关注环境风险规制过程,尤其是规制过程中处理环境风险问题的不同主张,通过风险沟通达成风险认知多元性和最低限度共识的统一。基于我国的现实国情,我们处理环境风险问题主要有两种主张:一是以经济发展和权利优先为尺度的弱“规制论”,主张环境风险规制必须基于科学上的确定知识;二是以公众健康权益和环境权益优先为尺度的强“规制论”,主张环境风险规制应建立在公众价值判断和心理恐惧之上。这两种主张实质上代表了环境风险规制中的事实认定(科学议程)和政策选择(民主议程)的冲突和平衡问题。为此,需要通过设计风险沟通规则和程序予以化解:首先是借助专家知识来构建关于环境风险的科学模型(科学议程);其次是将之公告于公众,收集公众的反馈信息,以此建立环境风险的公众反应模型(民主议程初阶);再次是在科学模型与公众反应模型匹配的基础上拟议关于环境风险概率、程度范围、损害后果、成本效益等要素的风险沟通文件(民主议程进阶);最后是规制机构在最低限度共识的基础上进行规制策略选择。关于风险沟通模型与步骤的理论建构,参见:M. Granger Morgan,Baruch Fischhoff, Ann Bosrtom,Cynthia J. Atman.Risk Communication: A Mental Models Approach[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20-21.endprint
第三,从组织和程序两个方面强化风险决策之适度中立性,以防止利益集团俘获和规制机关滥权。在组织层面,可以建立独立性、客观性、透明度较强的风险评估委员会,将风险评估与风险决策适度分离。这种独立的风险评估委员会的优势在于,它能吸纳多元利益主体,将垂直分权和水平分权相结合,并提供利益享有者和权力享有者客观论辩的平台。在程序层面,可以设定标准化的风险决策程序,包括科学群体共同认可的评估程序和多学科(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分析方法。尤为关键的是,这个决策程序应具有阶段性和开放性,以便吸纳新的科学知识,全面考量与科学评估相关的政治、社会、经济、伦理价值等因素;并通过风险评估和风险决策的适度分离,使风险评估的结果和公众价值判断在决策程序中得以重新检视。通过这种程序机制,可以在风险规制过程中设定双重风险评估,有利于风险决策的客观化、中立化。当然,这种决策还应当具备公开性,某项环境风险规制决策背后的价值选择、各方意见、科学证据等,必须公之于众。
当然,毋庸置疑,中国环境规制改革的方向与思路必须与中国的法治建设保持同步。在这个前提下,中国环境规制改革的核心任务是探索如何将商谈式程序进路和技术规范进路嵌入法治进程,形成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互动。若非如此,在环境法治的形式化任务尚未完成的前提下,商谈式程序会给环境规制系统带来实质性难题,即民主的混乱无序、无效率和多元价值的胶着、冲突。ML
参考文献:
[1] 王毓正.论环境法于科技关联下之立法困境与管制手段变迁[J].成大法学,2006,(6):104.
[2] 汉斯·J·沃尔夫.行政法:第3卷[M].高家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中文版前言.
[3] Peter Menell.The Limitations of Legal Institutions for Addressing Environmental Risks[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991,5(3):94.
[4] Henry Richardson.Democratic Autonomy: Public Reasoning about the Ends of Policy[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2-8.
[5] 乌多·迪·法比欧.环境法中风险预防原则的条件与范围[G]//陈思宇,译.刘刚.风险规制:德国的理论与实践.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256.
[6] Arie Trouwborst.Evolution and Status of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in the International Law[M].The Hague: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02:23-36.
[7] Naomi Roht-Arriaza.Precation,Praticipation,and the “Greening”of International Trade Law[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Law & Litigation,1992,(7):57-60.
[8]理查德·斯图尔特.美国行政法的重构[M].沈岿,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3.
[9]Gary E. Marchant,Kenneth L. Mossman.Arbitratary and Capricious: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in the European Union Courts[M].Washington, DC: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2004:22-26,44-63.
[10]Ronnie Harding,Liz Fisher.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in Australia[G]//Timothy Riordan,James Cameron.Interpreting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London:Earthscan,1994:252-261.
[11] 张翔.基本权利的双重性质[J].法学研究,2005,(3):21.
[12]克里斯蒂安·斯塔克.基本权利之保护义务[J].李建良,译.政大法学评论,1997,(58):33-36.
[13] 韩大元.中国宪法学的学术使命与功能的演变——中国宪法学30年发展的反思[J].北方法学,2009,(2):16.
[14]Derek Turner,Lauren Hartzell.The Lack of Clarity in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J].Environmental Values,2004,13(4):453-458.
[15]Nicolas de Sadeleer.Environmental Principles: From Political Slogans to Legal Rules[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371.
[16]陈慈阳.环境法总论[M].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11:365.
[17]Richard Stewart.Environmental Regulatory Decision Making under Uncertainty[G]//Timothy Swans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Law and Economics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Issues in Institutional Design.Bingley: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2002:71.endprint
[18] 叶俊荣.环境政策与法律[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99-102,134.
[19] 凯斯·桑斯坦.权利革命之后:重塑规制国[M].钟瑞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84.
[20] Daniel Bodansky.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in US Environmental Law[G]//Timothy ORiordan,JamesCameron.Interpreting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London:Earthscan Publications Ltd.,1994:204.
[21]Julian Morris.Rethinhing Risk and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M].Oxford:ButterworthHeinemann,2000:1-21.
[22]凯斯·桑斯坦.恐惧的规则——超越预防原则[M].王爱民,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28.
[23]史蒂芬·布雷耶.打破恶性循环:政府如何有效规制风险[M].宋华琳,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11.
[24] 陈春生.行政法之学理与体系[M].台北:三民出版社,1996:183.
[25]Robert Raucher, Michelle Fery and Peter Cook.BenefitCost Analysis and Decisionmaking under Risk Uncertainty: Issues and Illustrations[G]//Eric Richard,Fred Hauchman.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Drinking Water Risk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IAHS Publ.,2000:144.
[26]梁上上.制度利益衡量的逻辑[J].中国法学,2012,(4):73-87.
[27] Dan M. Kahan,Pail Slovic,Donald Braman and John Gastil.Fear of Democracy: A Cultural Evaluation of Sunstein on Risk[J].Harvard Law Review,2006,(119):1074-1076.
[28]伊丽莎白·费雪.风险规制与行政宪政主义[M].沈岿,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21.
[29]戚建刚.风险交流对专家与公众认知的弥合[C]//沈岿.风险规制与行政法新发展.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201.
[30]季卫东.依法风险管理论[J].山东社会科学,2011,(1):7-9.
[31]戚建刚.我国食品安全风险规制模式之转型[J].法学研究,2011,(1):34-37.
[32]朱迪·弗里曼.合作治理与新行政法[M].毕洪海,陈冲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6-29.
[33]伊丽莎白·费舍尔.风险共同体之兴起及其对行政法的挑战[J].马原,译.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2,(4):142.
[34]季卫东.法治重构的新程序主义进路:怎样在价值冲突中实现共和[EB/OL].(2010-12-01)[2014-04-16]http://www.civillaw.com.cn/article/default.asp?id=51404.
[35]杜辉.论制度逻辑框架下环境治理模式之转换[J].法商研究,2013,(1):71.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