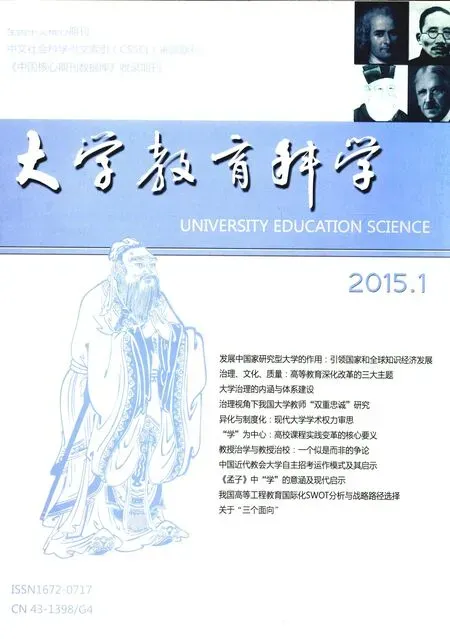教授治学与教授治校:一个似是而非的争论
□ 朱守信 杨 颉
教授治学与教授治校:一个似是而非的争论
□ 朱守信 杨 颉
教授治学与教授治校在中国作为备受争议的一对学术概念,既存在差异又相互联系。治学与治校的合法性来源不同,治学表示学术事务的治理权,是一种知识权力;而治校则指向学术组织的治理权,是一种组织权力,二者产生关联起源于学术活动的组织化。治学与治校并不存在严格的二分,学校事务以学术事务为核心,学术治理离不开学校治理的支持,教授治学与治校本身是一个连续体,而不是对立面。无论是教授治学还是治校,其核心都是对中国大学内部治理模式的探索,旨在重建以学术权力为核心的制度框架和组织结构。
教授治学;教授治校;治理;学术
教授治学与教授治校在我国学术领域一直是一个长期争论的话题,迄今为止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2010年颁发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这是教授治学概念第一次在国家官方教育文件中出现。这一提法鲜明地突出了教授治学,淡化了教授治校。有学者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教授治学’是个非常巧妙的概念,它一方面安抚了教授要求参与大学管理的意愿,另一方面又不破坏大学中的基本领导结构,保护了现有权力者的既得利益”[1]。官方对教授治学的肯定与学界对教授治校的呼吁产生了一种理念冲突和概念矛盾,进一步加剧了教授治学与教授治校的争论。对教授治学与教授治校关系的辨析,既要摆脱将两者完全对立的框架,又要避免将两者绝对等同的模式,更要超越治学与治校的话语之争,看到两者背后本质是对中国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的思索和探寻。
一、治学、治校与大学治理
历史上来说,教授治校起源于中世纪大学的学者自治,并一直作为西方大学的治理传统。而教授治学则更多作为一个本土化的概念出现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历程中,有着深刻的中国语境和现实背景。“我国大学教授治校制度的建立还是以政府为主导, 而不像西方大学教授那样,通过自己的斗争来争取”[2]。教授治校理念在中国最早见于民国初年颁布的《大学令》。1912年,时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主持并颁布了《大学令》,当时教授治校在制度上主要表现为评议会和教授会的设置。《大学令》规定评议会由校长、学长及各科教授代表组成,审议事项包括:(1)各学科之设置及废止;(2)讲座之种类;(3)大学内部规则;(4)审查大学院生成绩、及请授学位者之合格与否;(5)教育总长及大学校长咨询事件;(6)凡关于高等教育事项,评议会如有意见,得建议于教育总长。教授会由学科内教授组成,其审议事项包括:(1)学科课程;(2)学生试验事项;(3)审查大学院生属于该科之成绩;(4)审查提出论文、请授予学位者之合格与否;(5)教育总长、大学校长咨询事件[3]。该条令自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开始正式实施。
然而,教授治校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仅昙花
一现,1930年蒋梦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就迅速被教授治学所取代。蒋梦麟上任后,便抛弃蔡元培“教授治校”的理念,出台《国立北京大学组织大纲》,将学术事务和行政事务分开,并提出“校长治校、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的办学方针[4]。蒋梦麟主政北京大学时取消大学评议会,代之以校务会议,由校务会议和行政会议决定包括大学预算、院系设立废止以及大学内部各种规程等重大事务。《国立北京大学组织大纲》规定:校务会议“以校长、秘书长、课业长、图书馆长、各院院长、各学系主任及全体教授、副教授选出之代表若干人组成之,校长为主席”;行政会议“以校长、院长、秘书长、课业长组织之,校长为主席”;此外还规定“各学院院长、秘书长、课业长、图书馆长均由校长就教授中聘任之”[5]。这一系列规定将大学治理中的人事权与决策权集于校长一身,教授在学校事务中的治理地位日渐衰微,越来越限定于治学术而非治学校。蒋梦麟校长认为学术和行政是两类完全不同性质的事务,治学者和治校者需要具备不同的素质,大学治理中学术事务与行政事务应当截然分开,让学术的归学术、行政的归行政,从此开启了中国大学教授治学与治校对立之滥觞。
教授治学的合法性来于专业权威,即高深知识权力。学术事务中的权力主要来源于高深知识,高深知识不仅是构成学术组织的基本元素,也是治理学术的前提和基础。无论大学处于什么发展时期,“只要高等教育仍然是正规的组织,它就是控制高深知识和方法的社会机构。它的基本材料在很大程度上构成各民族中比较深奥的那部分文化的高深思想和有关技能”[6]。作为高深知识的掌握者,教授群体对于如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等学术事务的理解和把握更为深刻,最清楚高深知识的内容,因而最有发言权。与之不同的是,教授治校的合法性基础则来于利益相关者理论,教授群体作为学术组织内部重要的利益相关者,有权利、有必要对学术组织事务进行治理。治学是学术人员的自然权利和本职工作,也是学术组织的内在要求,因而较少产生分歧和争论。当前纷争的焦点主要围绕在教授要不要治校,以及治学与治校的关系上。
事实上,治学与治校从源头上并没有直接和必然联系,两者产生关联是起源于学术活动的组织化。治学表示对学术事务的治理权,是一种知识权力;而治校则指向对学术组织的治理权,是一种组织权力。大学本质上是一个集体性的教学与科研活动组织,也就是组织化的知识生产和传播场所。如果按照学术自由的原则,纯粹的学术活动应当归属学者个人管辖,不应纳入学术组织的管理范围。学术人员的个体活动之所以受到约束,是因为其使用了学术组织中资源,因此必须承担与之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因此,只有当学者必须在学术组织中进行研究,即治学必须在学术组织中实现时,研究学术才与治理学术相关联,治学才与学术组织治理(治校)产生联系。
在学术组织规模很小的时候,学术与行政完全一体化,学术人员同时充当行政人员,教授治学的同时负责治校。然而当组织规模扩大时,大学管理职能也日趋复杂,这使得大学必须借助行政管理机构才能保证其日常运行,专职的行政人员和行政官僚开始出现,大学治理主体逐步裂变分化。“高校的管理体制,就其本质而言,它体现为权力在管理的各阶层和高校内各个不同利益群体间的分配,以及它们相互间的权力作用关系。这种分配的模式和作用关系,即构成权力结构”[7]。这种权力结构的分化和异化使得教授治校从治学中剥离,治校权力逐渐成为大学治理中不同主体间相互博弈的筹码,而不再单独归属教授群体作为学术人员的专有权力。
可以看出,教授治学本质上是一种学术内行对学术事务进行管理的制度,其理论基础是学术自由与学术自治,强调的是学术人员的自我管理。教授治学指涉学术活动范畴,其目标是为了充分体现教授群体在学术事务管理方面的主体性,更多反映的是权力运行的范围、内容和对象。与之不同的是,治校问题起源于学术活动的组织化,属于学术活动的组织管理。教授治校权主要表现在学校权力的结构、规则的制定、资源的配置,以及各种学校事务的决策权,其更多反映的是权力结构的分配、设置和运行。从教授治学与治校的起源与合法性基础可以看出,两个概念指向不同的内涵与外延,存在概念分化的必要。因此治学与治校在参与方式、表达方式和决策方式上都应该有所不同,不能用治学的方式来治校,亦不能用治校的方式来治学。
二、治学与治校的内在关联
教授治学通常包含两层意义,一个是研究学术,一个是治理学术。当前学界有关教授治学的讨论主要更多集中于后一个用法,也就是将教授治学定位在治理学术上,主要是指“对学科、学术、学风和教学等学术事务进行管理与决策”[8]。治学与治校虽然存在较大区别,但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关系,学界产生争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把学术事务和学校事务置于对立面上。然而,在高等教育的具体实践活动中明确区分所谓的治学与治校并非易事,“学术管理和行政管理往往交织在一起,很难划分”[9]。治学和治校两个概念之间本身就存在很多交叉和重叠部分,过于强调两者的区别与对立,只能让我们忽略两者间的相关特质和相联属性。
学术组织的属性决定了学校的大部分事务是学术事务,学术活动必须在学术组织中完成,因此治理学术必然与治理学术组织产生关联。从学术组织活动的角度来看,学术性事务构成了学术组织事务的主体,学校的发展规划、人员晋升、资源分配等都是与学术密切相关的事务,这些事务基本上涵盖了学校的绝大部分事务。“人们对于以学术事务为对象和以学术事务为内容的管理称为‘学术管理’,学术管理既包括以行政权力为背景的管理活动,又包括以学术权力为背景的管理活动。也就是说在学术管理活动中,既有行政权力又有学术权力”[10]。从客体的角度来看,在实际的高校运行中,学术事务与行政事务经常统一于学校事务。主体意义上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虽有一定区别,但不是截然分开,两者统一于学校权力的内容下。以狭义方式划分学术事务必然导致高校管理上的学术与行政二分。正是考虑到这一点,伯顿·克拉克在分析西方大学的学术权力时才倾向采用客体的视角[11]。
学术事务和学校事务并不存在严格的二分,学校事务以学术事务为核心,学术事务离不开学校事务的支持。教授治学与治校本身是一个连续体,而不是对立面。“大学作为一种组织的存在,各项工作都是以学术活动为中心展开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学所有工作都是从属于学术活动,也需要服从学术活动,是以学术为核心的有机整体”[12]。治校的主要任务就是治学,学术事务是学校事务的最主要方面,大学的重大事务基本都是与学术相关,把学术事务的决策权交给教授,这本身就体现了教授治校。通常认为教授治学就是指教授有权从事学术活动,并对学术事务进行管理,与学校事务治理并无太大关联。然而在现实中,学术事务与学校事务息息相关,两者既不同又紧密相关,很难清晰划界绝对分离。以大学教师的人才引进为例,其不仅涉及到学术水平判断、人才梯队建设等学术考虑,又关系到学校人事编制、资源分配和后勤福利等全局问题,同时牵涉到学术和非学术两个领域,并不能单纯在学术范围内就得以解决。一些涉及院系发展和学科建设等问题,更要考虑学校整体规划、资源配置,更要从学校层面入手才能解决这些学术事务。
对于任何组织来说,资产权、人事权和财务权等都是该组织最重要的事务权力内容,大学也同样如此。以往认为学术人员仅仅需要赋予学术事务方面的治理权力,学校事务治理权力则可有可无。然而,“随着大学教师专业性的增强,在二战以来西方学术至上思潮的激发下,越来越多的大学日益改变过去的这种观点,认为教师不仅在诸如课程等专业实务上具有权威,而且在其他与教育相关的实务上同样拥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力”[13]。一些看似非学术的事务权力实际上对学术事务有着重大影响,与这些事务相关的决策权力是大学重要的权力范畴。因此可以说治学是治校的重要组成,学校事务是大集合,学术事务是相对的小集合。作为大集合,治校直接决定了治学能否有效实现,治校权的缺位导致治学权的缺失。正是由于学术群体在学校事务治理中的弱势、缺席和失语,才导致学术事务管理中行政权力大行其道,学术权力不断遭到挤压和被边缘化。“教授治学在许多方面被架空,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教授不具有参与学校重大事务管理的权力与机会,即教授治校这个前提缺失”[14]。大学的学校事务如果抛弃学术事务,大学将失去学术组织的根基;同样,学术事务如果离开学校事务,那么学术活动也将缺少组织保障而难以有序进行。
三、治学与治校之争的超越
教授治学与治校虽然在概念上可以做出明确区
分,但是二者在现实中却相互缠绕,难以绝对划分。治学和治校争论的一个焦点就在教授的权力应不应只限于学术事务,该不该涉及或包括学校事务。这种争论的原因在于先验地假设了学术事务与学校事务的对立,并不自觉地将其作为前提。“多年来,人们一直习惯于从行政与学术的二元分立来研究大学的权力结构。这反映人们大多依然将大学视为一个‘自我封闭系统’的思维定势,依旧尚未走出‘内部人控制’的窠臼”[15]。事实上,学与校本身无法分割,学术事务管理是学校的首要事务,治学是治校的核心,治校是治学的保障。两者的关系如同一个同心圆,治学是内圆,治校是外圆,圆心就是学术事业的发展。大学不是孤立的符号存在,对于教授治学与治校关系的理解应当从大学治理的现实入手,而不是从概念出发,抽象地探讨治学与治校只能加深冲突而无益于矛盾化解。
以往研究中对教授治校存在某些狭隘理解和片面认识,这是由于现实中教授治校是有条件的。教授治校不是无限参与和绝对掌控,因此实践中更应关注教授群体在什么范围内参与学校治理,以及参与到什么程度。教授参与治理学校更多体现为一种学术领导和决策,而不是具体事务的行政执行。当今大学日益成为一个目标多元的复杂组织,“传统意义上的教授治校指的是正教授完全掌管大学的机制,而现代意义上的教授治校则可理解为大学教师群体作为最核心的力量参与大学事务的决策和管理,发挥实质性的影响作用”[16]。从当代西方大学共同治理的实践来看,教授主要负责治学,并且有限度和有层次地参与治校。
无论是教授治学还是治校,其核心都是对大学内部治理模式的探究,即以教授为代表的学术人员在大学治理中的权利与义务边界。“大学治理结构是大学这个组织中各利益群体的相互关系,它通过权力的配置和运作机制来达到关系的平衡,以保障组织的有效运行并实现其根本目的”[17]。教授治学还是治校本质上是大学应当如何治理的问题,二者在目标上都是对学术自由的维护,保持大学的学术属性,进而更好地实现大学使命。“对于置身体制之外的传统知识分子而言,学术自由的诉求本身并无多大的实质意义。而大学中的人们之所以期冀这种特权并希望通过特定的制度安排来获得保障,恰恰是因为体制内部种种对‘自由’的威胁的存在”[18]。当前中国大学场域中,教授治理学术这一基本权利尚未得到很好保障,在治理学校上更是严重缺席。教授无论是治学还是治校都受制于行政力量,大学治理的结构、方式和路径仍没有遵循学术的发展逻辑,如何对不同群体在大学治理中的角色、作用和地位进行限定才是当务理论之急。
我们要看到,学术权力式微是当下教授治学和治校重议的共同背景。学术人员在大学治理中不断边缘化,行政人员成为学校的支配核心,学术权力空间受到挤压,因此更加需要突出和强调教授治学和治校的内在联系。“大学作为一种学术制度,一种学术机构,它必然有一些内在的东西,正是这些东西决定了大学之所以是大学,而不是其他什么机构。而中国大学之所以水平低下就是因为这些基本因素被遮蔽了,被排斥了”[19]。治学是学术自治理念的自然延伸,是学术规律的内在要求和题中之义;治校是学术组织的制度安排,是学术活动的必然选择和重要保障。无论是教授治校还是治学,都是一种手段理性,并非是目的理性。二者皆指向当前我国大学治理结构中的权力失衡,都旨在重建以学术权力为核心的制度框架和组织结构。必须认识到,教授治校和治学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大学实现其自身目的的手段。
教授是治学的主体,是治校的参与者,教授治学和治校都承认教授在大学治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治学和治校是统一的,统一于高校的本质和功能,推进教授治校是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由教授治学到教授治校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二者没有根本矛盾,并不互相排斥”[20]。当前争论在于假设了一个治学与治校的对立界面,从概念的角度出发辨析两者的区别,而不是从实践出发寻找两者的现实关联。这种争论更多是涉及个人的价值判断而非事实分析,因此争论本身既无法推进大学治理的进步,也无助于现实问题的解决。更多时候,教授治学和教授治校是对同一事物的两种选择和不同描述,如果仍然停留在治学与治校非此即彼的二分判断上,则不利于认识的深入和理解的突破。治学与治校争论从深层次上反映了我国高校管理体制改革中的理论挣扎与前行,我们需要超越两个概念表面的语义之争,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态度发现二者背
后的共同旨趣,才能探索出适合中国大学的内部治理结构和治理模式。
[1]王长乐.“教授治学”到底是什么意思[J].民主与科学,2011(4):17-20.
[2]张正峰.中国近代大学教授治校制度的特点分析[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8(6):74-78.
[3]王学珍,郭建荣.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93-94.
[4]孙善根.走出象牙塔——蒋梦麟传[M].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153.
[5]张国有.大学章程(第一卷)[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36-39.
[6][美]伯顿·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M].王承绪,等,译.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11.
[7]谢安邦,阎光才.高校的权力结构与权力结构的调整——对我国高校管理体制改革方向的探索[J].高等教育研究,1998(2):20-24.
[8]张君辉.中国大学教授委员会制度的本质论析[J].教育研究,2007(1):72-75.
[9]姚启和.高等教育管理学[M].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241.
[10]秦惠民.我国大学内部治理中的权力制衡与协调——对我国大学权力现象的解析[J].中国高教研究,2009(8):26-29.
[11][美]约翰·范德格拉夫.学术权力——七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比较[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85-207.
[12]杨克瑞.教授治学,也要治校——兼论现代大学制度建设[J].教育发展研究,2012(9):47-50.
[13]陈星平.现代大学共同治理中的教师参与[J].学术界,2011(5):148-153.
[14]赵蒙成.“教授治校”的实质与边界——与杨兴林教授再商榷[J].江苏高教,2013(2):1-5.
[15]王英杰.治理结构:现代大学制度的基石——评《董事、校长与教授:美国大学治理结构研究》[J].比较教育研究,2012(2):85-87.
[16]彭阳红.“教授治校”与“教授治学”之辨——论中国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变革的路径选择[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2(6):106-110.
[17]李建奇.我国大学治理结构变迁的路径选择[J].高等教育研究,2009(5):39-44.
[18]阎光才.精神的牧放与规训:学术活动的制度化与学术人的生态[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1:32.
[19]韩水法.大学与学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33.
[20]毕宪顺,赵凤娟,甘金球.教授委员会:学术权力主导的高校内部管理体制[J].教育研究,2011(9):45-50.
(责任编辑 黄建新)
Academic Governance by Professors and Administrative Governance by Professors: A Paradoxical Controversy
ZHU Shou-xin YANG Jie
Academic governance by professors and administrative governance by professors have been a couple of controversial concepts for a long time in China.There are similarities as well as disparities between the two concepts.Academic governance and administrative governance have different legitimate sources in that the former is the governance power on knowledge while the latter is the governance power on organization, which began to connect with each other since the systematization of academic activities.There is no absolute distinction between academic governance and administrative governance which, in essence, are continuums rather than opposites for the fact that both of them are indispensable to each other.Regardless of literal debate, both of the two concepts are the exploration of inner governance structure for China’s universities, aiming to rebuild an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an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that operates on the logic of academic power.
academic governance by professors; administrative governance by professors; governance; academic
G640
A
1672-0717(2015)01-0064-05
2014-11-20
朱守信(1988-),男,安徽金寨人,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原理与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杨颉(1972-),男,江苏南京人,上海交通大学规划发展处处长,高等教育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评估与管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