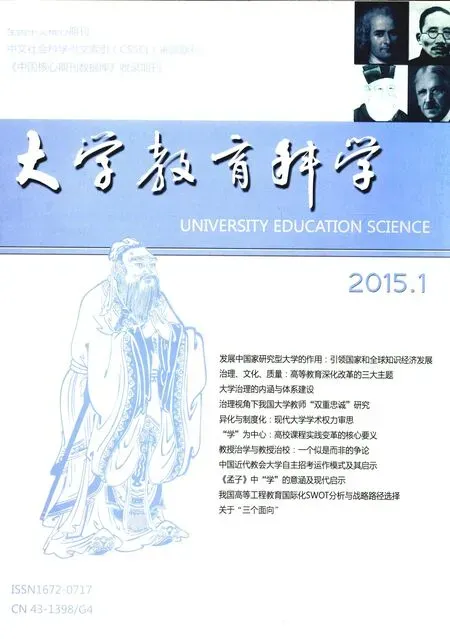异化与制度化:现代大学学术权力审思
□ 崔延强 吴叶林
异化与制度化:现代大学学术权力审思
□ 崔延强 吴叶林
学术权力来源于高深知识与学术自由,是大学组织的原生权力和基础权力。落实学术权力是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题中要义。当前我国高校学术权力偏离原始价值追求,存在诸多异化问题,主要表现为高深知识生产功利化、权力关系依附化、权力运行同盟化、学术利益本位化等。为消解学术权力异化困境,有必要从权力行为、权力组织、权力运行规则及权力监督四个方面展开制度化路径探讨,建立学术权力四位一体的运行规范体系。
现代大学;学术权力;异化;制度化
大学作为知识型社会组织存在了近800年,其基业长青的奥秘就在于大学具有独立的自治权,而这种自治权归根到底是来自于大学的高深知识及其真理追求。因此,学术权力是大学的核心权力。当前,我国高校学术权力运行存在诸多异化问题,有所偏离大学“何谓”与大学“何为”的原初精神,削弱了学术权力的合法性及其根基。究其原因,我们认为是学术权力规制不够。非制度化的学术权力一方面难以获得独立、主导地位,另一方面,权力运行过程也容易走向失范和异化。学术权力要得以有效运行与落实,制度化是前提。
一、大学学术权力的来源
厘清学术权力产生的根源是大学学术权力制度化设计的前提。中文“学术权力”概念由“academic power”翻译而来,从词源上考察power具有能动性的含义,内蕴着优势地位和强制能力。学界对英文“academic power”有两种理解向度,分别是“学术本身的权力”(power of academic)和“为了学术的权力”(power for academic)。前者建立在高深学问与专业知识基础之上,是“为了学术的权力”之合法性基础,体现了知识与权力的共生关系;后者是为了保证知识真理的正确与准确而产生的派生性学术权力,作为大学内部重要权力单元制衡其他权力类型,为学术及其事业发展提供空间和资源。
从高深知识向度(power of academic)来看,高深知识是学术权力合法性的根本来源,学术权力的形塑依托于大学的高深知识及其真理性。具体而言,高深知识之所以拥有权力,是因为知识表达了对于世界的作用,其权力地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在现实中的有效性:高深知识能够更好地促进行动者了解自然、控制自然和改造世界。这是高深知识与权力结合的立足点。正因如此,洪堡强调,“繁荣的大学及发达的科学正是国家的利益所在,所以国家应当为大学创造保障其繁荣所需的条件”[1]。高深知识的“有用性”及其对国家、社会需求的满足是学术权力被国家承认和赋予的根本,1849年《法兰克福宪法》在人类法制史上首次将“学术自由”作为人的基本权利纳入国家法律,确认了学术权力的正当性与合法性[2]。
从学术自由向度(power for academic)来看,大学不仅保存静态的高深知识,同时还是创新知识和发现真理的场域。学术自由是指在具有高深学问的高等教育机构中“教学并证明真理”的自由,在认识论哲学指引下,“为了保证知识的正确与准确,学
者的活动必须只服从真理的标准,而不受任何外在压力,如教会、国家或经济利益的影响”[3]。在学术探究实践中,如何确保人类对真理的追求过程具有理性、批判性,进而获得正确、准确的知识真理,这就需要对探索活动提供独立的场域,给予学术研究以自由权力。大学的这种诉求在其诞生之时就有印证,以巴黎大学为例,“12世纪,为了与教会的神权和世俗的王权抗衡,维护自身利益,巴黎大学的教师率先仿效中世纪城市手工业者采用自治管理方式与教会的本尼迪科特修道院制度,成立了以大学教师为主导的“学者行会”[4]。在与世俗王权及教会神权的争斗博弈中,夹缝中生存的大学学术权力逐渐获得正视和认可,并以大学宪章的形式予以确认和赋权,学术自治与教授治校滥觞于此。
二、现代大学学术权力异化表现
异化是指事物演进到一定阶段,分裂出自身的对立面,成为限制主体发展的异己力量。学术权力的异化即是权力的性质发生变异,把来自于高深知识与保障知识探究的权力演变为限制和阻碍知识探究和学问追求的力量。当前,高校学术权力异化现象主要表现在高深知识生产功利化、权力关系依附化、权力运作同盟化及学术利益本位化等方面。
(一)知识生产功利化
知识生产功利化削弱了学术权力根基,并最终影响高深知识向度的学术权力的合法性。高深知识以真、善、美为价值追求,逐利化的知识探究却是以利益为目标,两者价值取向存在明显偏差。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三个方面。其一,知识被规训,形成权力性知识。博格斯认为,“现代大学的悲哀在于知识生产为官僚程序所控制”,权力性知识是异化的知识,在权力介入下形成的知识系统,服务于权力和利益需求。权力性知识,“一是通过权力支配、控制和利用知识,使知识从属于权力,成为权力的工具;二是利用权力支配人力、物力及相关的知识资源与优先发展某些学科,从中获取权力者所需要的知识,使知识中渗透权力;三是利用权力弄虚作假或制造虚假知识,使知识远离真善美”[5]。其二,市场化的研究导向。学术研究市场化带来了学术研究的功利化。逐利动机驱动下的学问探究,其知识所承载的价值和作用形式发生了变化。与以往崇尚的自由研究不同,市场化的知识探究以面向需求和市场的实用主义价值来全面衡量和评价大学学术研究。其三,缘起于功利性的学术评价体制。现代学者被规训到专门化的体制之内,组织考核和职称晋升均与经济利益密切相关,学术GDP的多寡为学者所追求。正因如此,“大学盲目追求学术产出率和知识的外在价值,导致了诸如学术泡沫、学术腐败等现象泛滥”[6]。当大学学术倾向于以功利作为价值标准时,“大学必须警觉,如果大学失去守望社会的职能,不能给人类以终极关怀,那么就会异化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另类机构,从而被边缘化,进而失去独立存在的基本理性”[7]。
(二)权力关系依附化
当前,学术权力与行政约束张力失衡,相互侵入对方的权力领地。行政权超越了“外在保证”的职能范围,进入了学术活动内部;学术权也偏离了真理追求的价值取向,进入了行政权力范围。学术权与行政权的相互依附,使得具有行政身份的学者在学术资源的配置上更具有优势,其权力能力大于纯粹学问研究者,从而更易获得学术资源和学术成就。另一方面,在“学而优则仕”的理念下,学术成就突出的学者也更易获得一定的行政权和行政资源,学术系统中这种“马太效应”内在、深刻地影响了基层学者的学术利益和真理追求。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依附关系最为集中的反映是大学学术权力组织的科层化。据李海萍教授对我国约100所高校的抽样调查,大学学术委员会、学位评定委员会、教学委员会等三大学术机构成员与处级干部职务的相关系数分别达到0.786、0.910、0.738,与系主任干部职务的相关系数分别达到0.916、0.721、0.721[8]。学术权力组织逐渐演变为“由组织、权力和职责界定出来的被客体化了的产物”,按照学术研究人员所掌握的学术能力及专长,人为地将平面、自由的知识共同体变成一个等级森严的官僚组织。
上世纪由法国兴起的装饰艺术运动,极大的丰富了家具的奢华度,而这种设计从来都不是为大众服务的,展现了家具工匠的高超手工艺,直到现在这种家具仍在许多富人家里出现。日本提倡装饰极简主义与大师米斯·凡德罗的“少即是多”不谋而合,以现在风靡一时的无印良品为例。无印良品的家具设计简单,多以原木为主,其家纺方面也是很简单的素色棉质,桌子棱角、椅子扶手等进行过圆滑处理,极大提高了家具的舒适度,不仅满足了人们眼球的舒适度,更满足了使用时的舒适度,就此来看,无印良品的设计可以称为好的设计。
(三)权力运作同盟化
大学内部分布着不同的、基于学科差异的学术部落,现代大学继承了原型大学的学者行会同盟形式,并在范围上更加扩大。“通过各门学科穿越院校所形成的‘庞大而恒久的学术系统矩阵结构’,存在于各种跨校的乃至全国性的专业学术组
织中”[9]。学术权力运作同盟的纽带即是基于这种学科联系的关系网络,在以熟人社会与乡土情结为文化背景的中国高校,文化模式和心理特征表现为极强的“关系意识”。“关系”将学术部落内部及不同部落联系起来,“一方面,拥有相同或相似的学术观点、学术人脉、学术地位而结成的老友同盟,控制本学科的学术标准和学术资源,另一方面则是基于学术传承中的门派体系,也就是师徒关系网络,通过学术近亲繁殖而形成的学术联盟”[10]。由于高深知识具有专门性,以及学术生态系统的相对独立自治,学术权力同盟化在事实上容易偏离学术目标和旨趣,阻碍高深知识生产和创新。如在资源配置中,在有关学术评价、学术项目的申请及学术交流等学术活动中,以同盟的形式进行运作,为本位利益最大化提供组织支持。1970年,在美国国会举行的对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同行评议制度的听证会上,科兰等人认为学术项目申请上的“同行评议是一个基本上为极少数杰出的‘老友’(old boys )谋取利益的精英主导制度。负责国家资助项目的管理者往往依靠他们信赖的老朋友来对研究申请书进行评审,并让这些人再提请他们的朋友作为评审专家,它完全是一个“乱伦的‘密友体制’(an incestuous buddy system)”[11]。
(四)学术利益本位化
现代大学利益相关者数量庞大、已经超越了单一的师生共同体,大学场域中的权力形态以委托代理为路径,在重大决策上一般由民主代议机构实施。学术权力作为大学的根本权力同样以委托代理为路径,如学术委员会、教授委员会等。以学术委员会为例,学术委员会委员是代理人,接受了某一专业或学科的委托参与学术权力运行。委托代理背景下,信息隐藏与不对称是学术权力运行的主要风险。“委托人不能观测到代理人的行为,只能观测到相关变量,这些变量由代理人的行动和其他外生的随机因素共同决定。”其后果主要表现为学术利益本位化,本位利益最大化等,这里本位利益既可以是个体利益,也包括部门利益,专业、学科团体利益,突出地表现在学术资源的配置上。现代大学对资源的需求和依赖尤为突出,大学每一项功能的实现都需要资源的跟进与保障,作为学术权力的拥有者其本身即是学术研究的主体之一,也是资源的需求者。因此,在学术权力制度不健全的背景下容易出现利益本位化和本位利益最大化的可能,正如亚当·斯密认为的“自私自利是人们从事活动的驱动力,每个人都比他人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于是,从个人利益出发,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三、现代大学学术权力制度化路径
解决学术权力异化问题,根本办法在于规制,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学术权力的制度化就是通过对学术权力制度要素的固化、规制,形成大学人的“普遍化的理解和假定”[12]。具体而言,大学学术权力制度化可以从行为、组织结构、规则及监督等四个维度展开。
(一)学术权力行为制度化
1.合理定位学术权力功能。学术权力功能的界定和制度化有益于规范学术权力在大学内部治理实践中的行为,防止学术权力功能放大和泛化。笔者认为,现代大学学术权力在高校内部的行使应集中于对有关学术事项的评价、咨议和指导,参与学术性事务的决策及对与学术发展密切相关的部分校政事务的决策参与。首先,学术权力具有学术质量评价功能。学术权力的主体是以学术为志业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是高深知识的生产者和传播者,是专业领域内部的权威,对高深知识及其质量标准能够更好地把握,通过同行专家对研究成果的评鉴、甄别和筛选,从而保证学术研究的质量和水平。其次,学术权力具有学术规范导向功能。学术规范是学术研究的规则和范式。当前学术失范问题较为严重,学术不端、学术腐败等问题突出。学术权力要深入学术研究实践,通过对学术研究过程的监督以及学术研究成果的鉴别,发现学术问题,维护学术研究的规范性。第三,学术权力具有决策咨询功能。学术有关事务的开展不能离开学术权力的参与,如,在学科建设、专业设置、职称评定、人才引进上,学术权力的参与具有必要性,能够有效体现
教授治学。“行政事务乃至学术事务的执行则交由高度发达的校内科层机构体系负责,以发挥其在办事效率方面的优势”[13]。
2.规范学术权与行政权关系。当前我国高校仍然缺乏合理的、科学的内部权力配置模式和规范,行政权与学术权均存在相互依附的现象。对此,我们需要进一步从微观层面审视大学事务中行政权与学术权的边界问题,以制度为依托规范权力关系。从行政权来看,鉴于大学组织的独特属性,在关涉学术事务上,行政权需要有所保留,从而给予学术独立的空间和自由。行政只能“适度”参与学术事务,在学术活动的组织、协调及监督等管理领域上,通过计划和政策手段宏观和间接地参与学术权力的运行过程,避免越位到具体的专业知识决策领域和资源的内部配置上。从学术权来看,学术权力是基于知识的生产、传播、储存、应用而产生的权力能力,其权力范围应与权力功能一致。学术权力的范围主要表现在学术质量的评价、学术规范引导和有关学术发展的大学事务参与上。在发挥学者专业优势的同时,学术权力也要避免干预管理和执行,在涉及到具体事务时,要理清管理与评价环节,在学术管理上由行政权主导,而在学术评价上由学术权力主导。以学术资源为例,资源配置不仅是学术专业问题,而且也是行政管理问题。在资源供给的可能性、配置的合理性及其决策方案的有效性上就属于行政范畴,因为这些事项的完成仅靠学术权力是做不到的,行政力量的参与具有必要性。
(二)学术权力组织结构制度化
学术权力组织架构的制度化主要着力于两个方面:其一,根据学术研究的规律和特点,正确定位基层学术组织权力;其次,在学术权力落实过程中,优化权力组织的成员构成。
1.建立底层主导的宏观架构。大学组织的结构特点决定了大部分学者集中在组织机构的“底层”,即在基层学术组织中从事教学、科研活动,从而形成大学组织蓬勃发展、不断创新的动力源泉。根据学术自由理念,越是接近知识探索场域越应该赋予学术权力,在学术权力组织的宏观架构设计上,权力重心需要下移,增强基层学术组织的学术话语权。大学基层学术组织主要有学系、研究所和研究中心,承担着一线的教学科研任务,权力下移就是赋予学系、研究所和研究中心明确的学术权力。学院本身非学术组织范畴,无学术权力,学院是为了解决学科高度分化带来的学术部落隔离,以及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创新而形成的组织。学院的管理权能范围可以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学生管理;二是在全院和院校之间协调教学、科研等学术活动;三是与系共同负责教师管理[14]。因此,基于底层主导的理念,大学学术组织体系设计中可以“系”、“研究所”、“研究中心”等为学术权力实体,在学院组织内设置独立运行的学术权力机构,其权力运行不受学院行政的影响,与此同时将管理事务交给院一级。这样在行政上校院两级共同为基层学术组织服务,减少了院级行政对系等基层学术权力的干预,有利于充分发挥基层学术权力自我控制、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作用。
2.建立合理的成员遴选制度。学术权力组织成员接受利益相关者群体的委托,参与有关学校发展的重要学术事项,身份的重要性决定了其成员的遴选受多重制度条件的限制。首先,要考查成员的学术水平条件。学术权力组织成员的遴选应坚守学术的标准,深入考察其学术声誉、学术成果和学术道德,包括学者在外部学术组织公共空间中的影响力及其经验,举贤不避“长”,不能因为具有行政身份而忽视其学术成就,凡符合学术标准的学者都具备进入学术权力组织的可能性。其二,要考虑学科条件。学科的限制是指学术权力组织成员的遴选要考虑不同学科的实际情况,既要照顾到优势学科,同时也要兼顾新建学科以及基础学科等,科学安排不同学科的席位比例。第三,要平衡双肩挑与纯粹学问研究者比例。在坚守学术标准的前提下,要尽量减少行政力量的参与,严格恪守两个三分之一,即“担任学校及相关职能部门行政领导职务的委员,不得超过委员总人数的1/3;不担任党政领导职务及院系负责人的专任教授,不得少于委员总人数的1/3”。
(三)学术权力运行规则制度化
规则制度化意味着我们需要制订明确的规程体系确保学术权力运行具有独立性与规范性,消解学术权力运行过程中的异化问题。概而言之,规则制度化包括学术权力组织章程制订、运行机制和工作机制建设三个方面。
1.制订和完善学术权力组织章程。学术权力组织章程是大学学术权力运行的指导性规范,集中规定了组织成员的权利与义务、人员构成、会议制度、运行机制等。不同层次、类别的学术权力组织均应该配套自身的章程规范,从而规约权力运行。基层和专项学术权力组织在权力运行时除应遵循自身的章程外,同时还要接受校学术委员会章程的规范和指导。加强章程建设一方面要完善制度的内容,如明确决策形式、决策程序,明晰不同层次类别学术权力组织的关系等;另一方面要提升执行效力,加强权力运行的监督,保证学术权力有效、规范运行。
2.加强学术权力运行机制建设。学术权力运行机制包含两个层面,其一,宏观上大学内部学术权力与其他权力之间权力配置及运行的制度总和;其二,微观上大学学术权力组织内部权力配置及运行的制度化。因此,从宏观来看,学术权力运行机制的设计最为主要的是处理好学术权与行政权的关系,建立行政权与学术权的协调机制。从微观来看,即是要建立和健全以学术委员会为主要形式的学术权力组织的运作机制。具体而言,就是要完善以议事制度和票决制度为核心的运行机制,发挥学术权力组织的审议、咨询、评议等职能。
3.加强学术权力运行工作机制建设。学术权力的工作机制不同于具体职能部门,目前我国高校学术权力组织仍然是非实体性机构。由于学科差异以及成员的分散,学术委员会的工作开展较为困难,因此,需要在工作机制的安排上积极创新。其一,建立实体化的学术权力组织机构,承载大学内部日常学术权力事务;创新秘书工作制度,以此为纽带沟通大学内部不同级别和类型的学术权力组织,使秘书工作常态化、组织化、制度化。其二,加强学术权力组织成员履职监督,强化权力主体履职考核,从而提高学术权力运行效率,维护学者群体的利益。
(四)学术权力运行监督制度化
在高校建立起相对完善的学术权力制度基础上,运行监督仍然具有必要性,通过监督能够有效发现制度设计存在的深层问题,防止权力寻租与腐败。
1.加强内部监督。内部监督是学术权力运行规范与否的根本保证,现代大学学术权力的内部监督要从两个方面开展。其一,实行程序公开,规避委托代理信息隐藏风险。在参与学术事项的评价与决策时,学术权力组织要公开其程序,允许非学术权力组织成员(如学生、教师等)参与听证。以程序公开求实效,增强学术权力组织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其二,实行申诉和复议,加强学术权力运行内部仲裁。学术权力运行存在客观的异化问题,在权力运行过程中要打通路径,为学术权力弱势群体维权开辟通道。根据大学章程及学术委员会章程对学术权力及其功能边界的规定,对越界行为由学校学术委员会仲裁并给予相应的惩戒。
2.加强外部监督。良好的学术权力运行需要三方联动,除基于知识分子良知的学术道德自律和有效的校内学术权力制度设计外,一定程度的外部他律是必要的。首先,加强国家权力的监督。国家是大学办学的委托人,是当然的权力运行监督者,国家通过建立权力监督机制来规范学术权力运行,如制订有关学术权力运行的法律法规,建立专门的学术权力运行管理机构等。其次,加强高校内部行政权、政治权以及民主权对学术权力的制衡和监督,这是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核心要义。第三,加强社会权力的监督。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外部认证与评估体系尚不健全,学术权力运行的第三方社会评价基本欠缺,学术权力运行难以社会问责。因此,此类评估监督机制亟待建立,通过社会评价加强高校学术权力运行质量外部诊断。
[1]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97.
[2]周丽华.德国大学与国家的关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62.
[3][美]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79.
[4]王秀丽.从教授治校走向共同治理[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2(1):28-31.
[5]张之沧.从知识权力到权力知识[J].学术研究,2005(12):14-20.
[6]赵保全,罗承选.论大学权力的知识特质和伦理意蕴[J].理论导刊,2012(9):53-57.
[7][英]英利.高等教育的质量与权力[M].罗慧芳,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73.
[8]李海萍.高校学术权力运行现状的实证研究[J].教育研究,2011(10):49-53.
[9]冯向东.大学学术权力的实践逻辑[J].高等教育研究,
2010(4):28-34.
[10]黄永忠.高校学术权力的异化与规制[J].现代教育科学,2013(1):22-24.
[11]Stephen cole,Leonard Rubin and Jonathan R.cole.Peer Review and Support of Science[J].Scientific American,1997(10).
[12][美]沃尔特·W.鲍威尔,等.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M].姚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6.
[13]陈金圣.大学学术权力的概念厘定与定位分析[J].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11(9):133-136.
[14]柏昌利.试论大学学术组织结构的调整[J].中国电子教育,2004(4):27-31.
(责任编辑 陈剑光)
An Examination and Thinking of Alienation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Modern University Academic Power
CUI Yan-qiang WU Ye-lin
Academic power comes from the advanced knowledge and academic freedom, and it is the primary rights and basic power of university organization.Implementation of academic power is the essence of modern university system construction.Currently, academic power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deviates from the original value pursuit.It has some alienation problems, mainly manifested as utilitarian during advanced knowledge production, dependence of power relations, alliance of power operation, and selfishness of academic interests.To digest alienation of academic power, we should establish operation standard system of academic power from four aspects of power behavior, power organization, power operation regulation and power supervision.
modern university; academic power; alienation; institutionalization
G640
A
1672-0717(2015)01-0030-06
2014-06-16
中央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校级重大培育项目“现代大学制度构建研究”(XDSKZ009)。
崔延强(1963-),男,山东青岛人,西南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