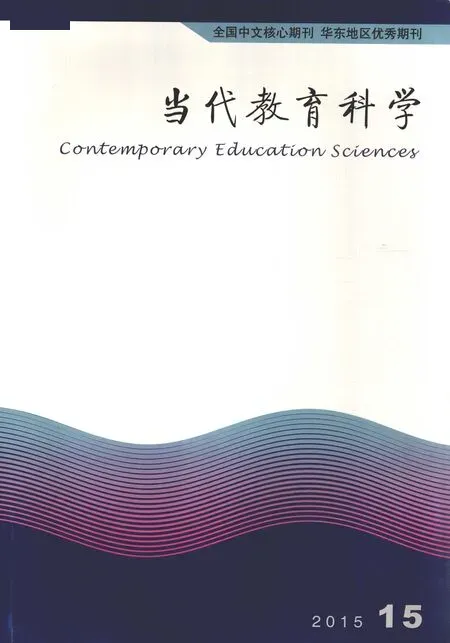从两极到融合:教师知识观的局限与突破
● 马蕾迪 范 蔚
知识观指导着课程改革,又是课程改革的主要内容。由于对现代科学知识客观性的膜拜产生了客观主义知识观,而随着后现代主义对现代知识客观性的解构,建构主义知识观强调知识的意义性、建构性,与客观主义知识观相对。受此影响,教师知识观主要表现为客观主义知识观和建构主义知识观。从文献分析和教学实践来看,教师知识观主要囿于知识本位的学科中心,或过于强调自主建构的学生中心,致使教学低效、不利于学生的发展。[1][2]因此,对教师知识观的审视,有助于教师突破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走向融会共生,是教师知识观的应然追求。
一、客观主义知识观:教师对工具理性的外在膜拜
客观主义知识观以知识取向为核心内容,认为知识是人类认识的结晶,是认识主体对客观世界的正确反映。因此,知识披上了客观性、普适性及中立性的科学外衣。其中,客观性是其主要特征。知识的客观性视知识为认识主体对客观世界的镜式反映,它超越了任何社会条件、具体的问题情境及价值观念,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具有普遍的应用价值和学习价值。受客观主义知识观的支配,教师的知识观对课程教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教师的教学理念和教学行为两个方面。
(一)视知识为教学的中心
从教育史的发展来看,知识一直是教育的核心问题。自夸美纽斯在《大教学论》中提出把一切知识教给一切人的百科全书式的教育;裴斯泰洛齐基于人发展的客观规律提出教育心理学化、教学的直观性原则,到赫尔巴特提出明了、联合、系统及方法的教学形式阶段理论,都试图从心理学的角度提高学习知识的效率;斯宾塞提出科学知识最有价值,这些教育主张都以知识为中心进行言说,其假定学生是无知的、狭隘的,知识是认识一切的基础,只有通过知识的学习,才能走出自身的无知和偏狭,最终通过学习知识促进人的发展。
将知识确立为教学的中心,从根本上倒置了知识与学生的关系,知识作为认识对象凌驾于认识主体——学生之上。在教学中,学生被视为空空的容器,教师的责任在于将知识储存在学生这个容器中。于是,知识成了连接教师与学生的中介,教学活动成为为知识而知识的传输活动。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人,其本身应具有的主体性、积极性长期被忽视,被知识遮蔽沦为教学中的客体。因此,教师与学生异化为讲授知识与接受知识的单向度的人,教育成为弗莱雷(Paulo Freire)笔下痛陈的存储行为,学生是保管人,教师是储户,教学成为知识的灌输。[3]
(二)忠实取向的课程实施
教师的知识观对其课程观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持客观主义知识观的教师将课程理解为学科或教学内容。课程被认为是确定的、静态的文本,是经过课程专家筛选后具有的权威性知识,甚至是不容置疑的合法性知识,这种课程观形成教师忠实取向的课程实施,致使教师的课程教学呈技术化特征。
基于对课程知识合法性和权威性的认定,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时忠实地执行课程标准、教师用书上的教学建议,甚至按部就班的将教师用书上的教学设计作为自己教学的模板,教学过程成为原原本本的诠释教师用书中教学设计的过程。教学的任务在于将确定的、真理性的知识教给学生,学生要么毫无怀疑意识地吸收教师传授的知识;要么终于有超出教师预设提出问题的,然而为了不打乱教学计划,教师往往忽视学生的问题,精确地按照教学设计的步骤走下去,使教学演化为导入新课——教授新课——课堂练习和布置作业的工艺学模式。教师对知识合法性的崇拜以及按图索骥的教学造成的直接后果是扼杀了学生的批判精神和创造性思维,正如有学者所言:“对知识无批判地记忆、理解、掌握和简单应用不就是在传递着某种文化的、价值的或西方的‘偏见’吗?所有的教学原则、教学方法、教学评价手段不都是在要学生放弃或干脆剥夺学生的‘批判意识’吗?缺乏了知识的批判意识和能力,所有的知识在学生头脑中不就成了‘无活力的知识’了吗,不就仅仅具有炫耀的价值而没有真正的思想价值了吗?”[4]
客观主义的教师知识观将课程知识视为实体,学生和课程知识都是作为独立的实体存在,学生通过教师的讲授去认识那些与客观世界相符应的、特选出来的人类文化知识。这样的知识观使课程知识成为系统的供应体系,使人类长河中悠久的历史文化知识、科学知识及被认为具有文化价值的不变的共同要素得以一代代传承,成为学生掌握基本知识与培养学生读、写、算基本技能的主要元素。然而,正是这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使知识成为外在于学生的符号,成为不容置疑的真理;教学成为教师中心、教材中心和课堂中心“见物不见人”的技术化路线;随着知识的转型和现代哲学对认识论的超越,教师开始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知识的个体性和意义性方面。
二、建构主义知识观:教师对价值理性的内在信仰
建构主义知识观以价值取向为核心内容,他们反对将知识作为确定性和客观性的认识结果,认为知识是在问题情境中,个体自我建构的过程而不是结果,强调知识的情境性、文化性和意义性。基于知识论的发展和知识的更新,新课程下教师对知识的价值认识由获得知识转向寻求意义。其集中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视儿童为教学的中心
儿童成为教学的中心受教育哲学的影响较大。如存在主义从人的存在为出发点,认为人是“自我意识”的存在,批判性地指出现实生活中人被异化为一种客观存在,萨特(Jean Paul Sartre)提出“存在先于本质”是存在主义的主要命题,认为通过客观的手段所得到的任何知识都是假设性的,真正的知识是通过人的直觉而得到的。[5]建构主义相对于客观主义知识观提出知识不是客观的,不是对客观实在的准确表征,它只是一种解释、一种说明,它是通过个体的自我建构获得的;知识社会学的代表人物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提出就认识的全部发展史而言,人们都是先对认识对象产生爱或者恨,之后才通过知性来对它们进行认识、分析和判断的。[6]可见,人在知识面前并非被动的。
建构主义的知识观凸显了人在知识面前的主动性,从斯宾塞对“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的诘问到批判教育家阿普尔(Michael W.Apple)提出“谁的知识最有价值”,人在课程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得到彰显。随着我国新课程的推进,“以学生为中心”、“尊重学生的主体性”、“一切为了学生的发展”是知识观转变最好的注脚。教学不再是为了知识而知识的认识活动,而是着眼于学生的兴趣,自学能力,态度、情感、价值观的培养。然而,正是居于这一知识观的转变,有学者指出在课程改革中反对知识本位的说法反映了一股轻视知识的教育思潮。轻视知识的教育思潮在理论上的失误主要源于不理会社会现实,轻视知识教育,无条件地追求学生个人发展,而这又是由于未能全面把握个人发展的机制和历史道路。[7]因存在着“轻视知识”的危险,儿童中心的教学在理论和实践中也遭到质疑。
(二)创生取向的课程实施
从英语词源学分析课程的内涵,“curriculum”原意为跑道,指静态的教学内容的系统组织;而当代许多课程学者从“curriculum”的词源“currere”的原意跑的过程出发,把课程的涵义表征为学生与教师在教育过程中的活生生的经验或体验。[8]如杜威(John Dewey)批判传统教育只注重以教材为主,传授间接经验,而忽视学生的直接经验,由于课程与学生生活经验相脱离,课程只是一些外在于学生的无意义的符号。因此,他提出注重学生与特定环境的交互作用。后现代主义对课程的解构有过之而无不及之势。美国著名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多尔 (William E.Doll)提出“4R”课程观,即课程应该具有丰富性、回归性、关联性、严密性,他反对将课程作为一种线性的、封闭的、预先设定好的工艺学模式,指出课程应该是开放的系统,是学生与教师、文本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生成的。
动态生成的课程观使教师认识到教学不是忠实地执行预先设定好的课程方案,而是教师与学生在具体的情境中共同创造教育经验的过程。特别是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为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体现教师作为课程开发者的角色,教学成了学生和教师共同的创造活动,形成创生取向的课程实施。创生取向的课程实施在实践中的表现有两种情况。一方面,教师依据自己的知识经验和学生的经验,创造出真正赋予课程意义性的课程资源,但是这样的情况在实践中非常少见;另一方面,教师在对课程方案的创造中完全偏离了原课程的主旨,造成教学中一些伪生成和乱生成的现象。如一位教师在讲解董存瑞舍身炸碉堡这段历史时,设计了这样两个问题∶“假如董存瑞拉开的炸药包没有炸,那会是什么原因,该怎么办?”“你能不能为董存瑞设计出一个更好的炸碉堡的方案?”应该说,这两个问题对于拓展学生的思维的确能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这位老师显然忘记了向学生讲授这段历史的主旨是为了什么。假如学生通过热烈讨论,真的找出了一种两全的炸碉堡方案,那么,这位教师究竟是应该为学生的 “聪明创意”而赞赏有加呢,还是为董存瑞的“思维反应迟钝”而喟然长叹呢?[9]这样的教学设计在于教师片面追求知识对于学生的价值性,致使教学设计与原本的课程主旨完全背道而驰,非旦没有做到创造性的课程实施,反而将教学带入了伪生成的泥沼中。
建构主义的教师知识观凸显学生的此在,将学生由认识主体提升为存在主体,课程知识不是学习的目的,而是通过对它的学习丰富学习者的意义。因此,在课程实践话语中,一直凌驾于学生之上的课程知识不再高高在上,学生成为了课程教学中的主人,创生取向的课程实施也体现了师生在课程中的主体地位。然而,不是所有的课程知识都能还原为学生的直接经验,也不是所有的课程知识都有必要让学生亲自去体验;学生对课程知识意义的追求需要以一定的知识为基础,同样地,教师对课程方案的创造需要建立在遵循课程主旨的基础上,过分凸显课程知识的价值容易滑入虚妄的价值论,造成教学中乱生成的现象。因此,在新课程背景下,走出二元对立的知识观是教师知识观的应然追求。
三、融会共生:教师知识观的应然追求
教师的知识观从认识关系到意义关系,都先在的把学生看做此岸,知识是彼岸,中间隔着湍急的河流,为了跨越这条河流,客观主义知识观从认识论的角度去连接学生与知识,建构主义知识观从知识论的取向关照个体。然而,这两种知识观都放大了自身的优越性,其缺陷也暴露无遗,辩证地看,教师知识观的转向是建立在反思与批判、借鉴与重构的基础上,矫枉过正的态度容易陷入杜威所批判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因此,教师应该正确地看待知识的性质及价值,树立普适性与境域性融合的课程知识观,以及知识性与意义性融合的教育目的观。
(一)知识的性质:普适性与境域性融合的课程知识观
长期以来,客观性、普适性的知识观支配着教师的教学实践,因此遮蔽了知识的境域性。文化再生产理论的代表人物布迪厄(Bourdieu,P.)认为学校通过传递某种文化才在社会阶级关系再生产中占据重要地位,通过“文化专断”与“符号暴力”来传递统治阶级的文化,贬抑或削弱其他阶级的文化,通过“霸权课程”进行“文化资本”的分配,从而保证统治阶级文化资本的合法化与再生产。[10]伯恩斯坦(Basil Bernstein)基于语言社会学理论,认为人们的日常语言是一种文化代码,其表征着两种阶级文化,一种是代表中上层社会阶级文化的精制代码(elaborateel codes),一种是代表下层社会阶级文化的受制代码(restricted codes)。学校课程知识是精选的具有普遍性及关联性的知识体系,因而是一种精制代码;而学生的文化主要受家庭文化的影响,来自中上层社会家庭中的学生能很好的适应学校课程知识,反之来自下层社会阶级的学生表现出不适应,导致学业成就低下。
六十年代以来,随着多元文化教育理论的发展,围绕下层社会阶级学生学业成就低下的讨论持续升温,形成两种有代表性的认识:文化剥夺观和文化差异观。持文化剥夺观的人认为,下层社会阶级的学生学业成就低下是因为他们在贫穷文化中被社会边缘化,他们的贫穷文化或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低下导致了学生文化认知上的不足,所以学校教育的目的是帮助他们体验其他文化的经验以弥补其文化认知上的不足。而持文化差异观的人认为,下层社会阶级的学生学业成就低下是因为这些学生自身的文化背景、生活经验和学校所教授的知识彼此隔绝、甚至背离,课程知识与这些学生的文化属于一种“异质性文化”,文化差异观揭示出课程知识背后的阶级、信仰、民族、地域、政治等多方面的文化差异性。然而,教师的知识观主要受文化剥夺论者的影响,将课程知识奉为客观的真理、教学中以忠实的教授课程文本中的知识为主,因而忽略了学生本身具有的特殊的文化背景和原有的知识经验。
普适性与境域性融合的课程知识观既将课程知识看做具有客观性的,代表着人类共同的文化要素;又关注知识背后所包含的情境性和文化性。因此,课程知识就指称着两个基本事实:首先是将课程知识看作教育性经验的知识,是学习者的认识对象,这彰显了课程知识形式的客观性,[11]使课程知识在形式上固定下来,因此,课程标准、教材、教学辅导用书等成为课程知识的载体。其次,将课程知识看作为教育性经验的知识,是人类已经获得的认识成果;[12]这言说着课程知识的文化性和主观性。教师的课程知识观表现在课程实施中,一方面,要求教师既整体把握课程标准、教材中教师用书的内容,但又不能完全照搬课程专家为教师编制的教学设计,因为课程设计者预设的课程是课程知识存在的客观形式,是以对学生和社会普遍性研究和一般特征的把握为基础的,因而预设的课程不可能规定具体情境下的课程实施,它的规范也只能是一般意义上的客观要求。[13]另一方面,要求教师在课程实施中,考虑具体的学校、学生的已有经验和多元文化背景。从而在既有课程计划的基础上,结合具体文化情境创生新的教育经验。
(二)知识的价值:知识性与意义性融合的教育目的观
追根溯源,客观主义知识观主要是受工具理性的支配。自牛顿时代开始,学者们就习惯于将世界看做是一台运作良好的机器。至少在理论上他们相信,在某种程度上,世界是受一定的基本法则约束和控制的。通过对世界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其中的顺序性和确定性。[14]从此客观性、确定性言说着知识,但这里的知识更多的指向科学知识,人文知识因其不确定性而被排斥在知识的大门外,培根“知识就是力量”的名言无疑也指向科学知识为人类带来的技术进步与物质繁荣。人人追捧知识,学生接受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获得知识,学校教育的目的是为未来生活做准备。
二十世纪以来,从胡塞尔开始的现象学运动试图抵御客观性、封闭性的工具理性对人精神领域的侵蚀,海德格尔“我们如何生存”的反思将人类带入意义关照的世界,人与知识不再是指向客观规律的认识关系,而是一种有关人自身存在意义的本源性追问;知识从工具理性的樊篱中解脱出来,走向了价值理性。一时间以学生为中心、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知识观的解构,提倡不以任何外在功利价值为诉求,只关心人的内在价值成为新的教育目的观。
客观主义知识观与建构主义知识观恰如一枚硬币的两个相互联系的面。基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教师需要具有知识性与意义性共存的教育目的观,因为没有知识的系统性、脱离实际,以及缺乏一定的价值观念的课程是不可想象的;[15]雅斯贝尔斯早就警醒人们:应该反思使教育的文化功能和对灵魂的铸造功能融合起来。[16]一方面要求教师不能只注重教授确证了的事实性、教条性知识,把教学内容作为一种既定的结论灌输给学生。如自然科学中涉及到的公式、概念、原理,不是只显示最后的结果,而需要在教学过程中加入这些概念产生的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过程才最终形成,从而培养学生的怀疑精神、批判精神和探究精神;另一方面要求教师要关注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可能存在的意义,通过对知识的学习敞亮学生自身存在的意义,关照学生个体精神自由的成长。如,教师应该舍弃语文课上对文本标准答案式的学习,改变历史课对历史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意义等题纲式的教授,而应彰显人文社会科学与学生精神相遇的意义性。正如赵汀阳所言:“科学知识是关于事实的知识,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是关于人的知识,是有关学生幸福的知识。 ”[17]
总之,从我国的教育实际来看,教师持二元对立的知识观无助于培养具有健全人格发展的学生。只有既注重知识的普适性和境域性,又树立知识性与意义性一体的教育目的观,才能让学生在掌握并记住大量的人类文化知识、开阔视野的同时走向对公共精神、文化知识的承继;也只有通过对公共知识的获得,学生才能返回自身,寻求理解,实现对自我灵魂的教育。
[1]夏永庚,童强.教师知识观中的问题及其重建[J].全球教育展望,2006,(4).
[2]潘新民,张薇薇.必须走出后现代知识观——试论科学知识教育的作用与价值[J].教育学报,2006,(4).
[3]保罗.弗莱雷,顾建新等译.被压迫者教育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25.
[4]石中英.知识转型与教育改革[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169.
[5]黄济.教育哲学[M].山西: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241.
[6][德]马克斯.舍勒著.艾彦译.知识社会学[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15.
[7]王策三.认真对待“轻视知识”的教育思潮——再评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提法的讨论[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4,(3).
[8]]张华.课程与教学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66.
[9]郑英.课堂:请走出“伪生成”的泥沼[J].中国教育学刊,2008,(3).
[10]吴康宁.教育社会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35.
[11][12]靳玉乐,董小平.课程知识的客观表征与主观建构——兼论课程与教学的内在整合[J].教育研究,2009,(11).
[13]郭元祥.教师的课程意识及其生成[J].教育研究,2001,(6).
[14]艾伦.C.奥恩斯坦等,柯森主译.课程:基础.原理和问题[M].江苏:江苏教育出版社,2012,226.
[15]麦克.杨著,谢维和等译.未来的课程[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230.
[16]雅斯贝尔斯著,邹进译.什么是教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1.
[17]赵汀阳.知识、命运和幸福.哲学动态[J].20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