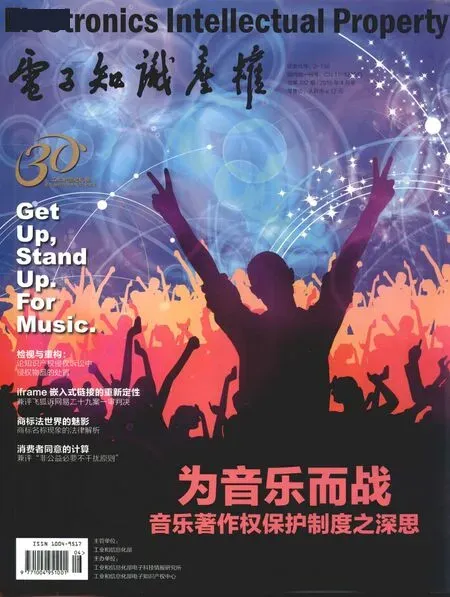不可忽视的“编曲权”和“编曲者权”
文 / 袁博 /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今年世界知识产权日的主题是“Get up, stand up. For music”,虽然对于主题目前尚无权威官方翻译,但是今年的主题无疑聚焦于音乐领域。凑巧的是,2014 年与2015 年之交,在国内音乐版权领域,版权交易与版权纠纷也以前所未有的密集姿态见诸于媒体。一方面,各大互联网音乐平台纷纷加强了与音乐制作公司的合作,大力购买版权资源;另一方面,以QQ 音乐、网易云音乐、搜狗音乐为代表的音乐版权“三国杀”也将版权竞争推向了白热化。不难想象,在新的一年,音乐作品的保护,将成为版权领域的新热点。
在音乐作品表演中,人们经常能看到作词、作曲和表演者的署名,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角色,经常被人们忽视——这就是“编曲”。对于“编曲”,在著作权法中并无相关界定,在业界,人们一度热议的问题之一就是,编曲者的“编曲权”受著作权法保护吗?
一、“编曲”的含义
首先,什么是编曲?编曲,对应英文为“arrange”(意为安排、排列、整理),是指以既有旋律为基础,利用各种方法形成复杂的多声部主调音乐的表达的过程,编曲工作是调配一首歌的精神、风格、特点及决定乐器搭配的种类。“编曲学”是20 世纪以来在欧美音乐研究中从配器法等作曲理论中逐渐分离出来的一门交缘性新学科,它与传统作曲技术理论之配器既存在一定的区别,也具有紧密的联系。是对音乐如何表现、以何种方式表达的创作,属作曲(compose)中的重要创作环节,最终音乐的表现形式基本决定于编曲过程。现代编曲技术是将作曲与音乐制作相结合的现代化音乐创作技术。随着音乐数字化,“编曲”逐渐衍生出了编曲软件、音源插件、效果器、合成器、频段、控制器、自动化等等作曲中原本不存在的概念,将这些音乐制作概念融入到作曲中,给作曲者提供了更多的实现音乐想法的可能性,使“编曲”具有了其独特的含义。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编曲和作曲的关系,更像是包装和被包装的关系,俗话说“人靠衣裳佛靠金装”,不同的编曲,会使同样的一首旋律具备不同的表达意境和艺术效果。例如,《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这首旋律在音乐史上有“如果没听过,你相当于少活了四分之一”的评价,在网上搜索一下,就会发现,这段脍炙人口的旋律有钢琴版、小提琴版、交响乐版、八音盒版、民乐版等不下数十个版本,显然,同样一首歌,不同的编曲,就会有完全不同的艺术效果。
二、没有得到司法承认的编曲权
商业娱乐流行歌曲中,作曲者和编曲者往往不是同一个人,因为很多歌曲创作者只有对旋律的灵感和体悟,却并没有相关的编曲技术。而编曲者则拥有相关的知识和技术,对于怎样体现旋律有着更多的技巧。在现代工业社会中,仅包含词曲的初级音乐作品是无法被消费的,很多情况下,需要编曲来给音乐作品包装定位,打造出丰富立体、风格多变的音乐“产品”。从专业方面来说,编曲不但要从乐器、音色搭配的角度对乐曲进行编配,而且要用电脑及软硬件实现音响效果的制作,是一项兼具艺术性和技术性的工作。
但是,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编曲者的智力成果在著作权法上的地位并未得到承认。例如,在“李丽霞诉李刚、陈红、蔡国庆侵犯邻接权、录音制作合同纠纷案”一审中,法院对编曲作出了这样的解读,“本案所涉的歌曲编曲并无具体的编曲曲谱,它的劳动表现为配置乐器、与伴奏等人员交流、加诸电脑编程等,编曲劳动需借助于演奏、演唱并最终由录音及后期制作固定下来。不可否认,经过编配、演奏、演唱、录音等诸项劳动所形成的活的音乐与原乐谱形式的音乐作品并不完全相同,构成了一种演绎。但是离开了乐器的演奏(或者电脑编程)及其他因素的配合,编曲的劳动无法独立表达,因此一般并不存在一个独立的编曲权。……由于本案诉争伴奏带的编曲曲谱只是对原曲进行了乐器配置、声部分工、组合,并没有改变乐曲作品的基本旋律。该编曲过程仅是一种劳务性质的工作,编曲目的是为了将乐曲作品转化为录音制品,故其劳务成果之一即编曲曲谱并不具有著作权法意义上的独创性,不能成为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
国外学界将“编曲”看成是一种对音乐作品的“再创作”或“改编”,具有足够独创性的编曲成果非常符合著作权法上演绎作品的概念。
三、编曲者的权利保护路径
笔者认为,严格考察编曲的性质,应当得出以下结论:对于具有独创性表达效果的编曲作品,应当承认其为原有音乐作品的演绎作品;或者至少应当给予编曲者邻接权即“编曲者权”,以保障其合法权益。如果说作曲的劳动是画出了一幅完整的人物素描,编曲的劳动就是对画面各部分进行上色、明暗表达等后期修饰,使作品的艺术表达更为饱满、丰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外学界也将“编曲”看成是一种对音乐作品的“再创作”(“The reworking of a musical composition”)或者“改编”。显然,编曲的这种含义使得具有足够独创性的编曲成果非常符合著作权法上演绎作品的概念。
(一)保护路径一:将具有独创性的编曲作品纳入演绎作品
演绎作品又称派生作品,是指在保持原有作品基本表达的基础上,增加符合独创性要求的新表达而形成的作品。构成演绎作品需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必须利用了已有作品的表达。如果没有利用已有作品的表达,或者只是利用了已有作品的思想,则不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演绎;第二个条件是包含有演绎者的创作。在利用他人表达的基础上,演绎者进行了再创作,演绎的结果和已有作品相比具有独创性,符合作品的要求。如果仅仅利用了已有作品的表达,但是没有演绎者的创作,没有形成新的作品,也不构成演绎作品【1】。由于借鉴了已有作品的表达,演绎作品对独创性的要求通常要高于已有作品。在这一问题上,美国法院通过Gracen案1. 参见Gracen v. Bradford Exchange 698 F.2d 300.和Snyder 案2. 参见L. Batlin & Son, Inc. v. Snyder 536 F.2d 486(2d Cir.)(en banc),cert. denied,429 U.S. 857(1976).分别确立了实质性区别标准和可区别性变化标准,明确了演绎作品必须要有区别于原有作品的实质变化,才能受到版权的保护。因此,对于一些技巧高妙,明显实现了较大效果区别的编曲劳动所产生的智力成果,笔者认为,可以作为原有音乐作品的演绎作品进行保护。
演绎作品的两个构成条件决定了它的双重属性:一方面,演绎作品在表达方面与已有作品具有一脉相承的共同性和依附性,由于与已有作品具有相似的表达形式和共同的作品元素,使得演绎作品较之新作品而言具有与已有作品紧密的联系和显著的依赖;另一方面,由于演绎作品具有再创作的性质,在已有作品的基础上加入了新的独创内容,使得其区别于对已有作品的抄袭。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演绎作品的特点就在于它既保留了已有作品的基本表达,又包含了演绎者的独创性劳动成果【2】。
由于演绎作品的双重属性,决定了其权利行使也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演绎作品的著作权人享有著作权法第10 条规定的全部著作权人身权和财产权;另一方面,由于演绎作品具有与原始作品“求同存异”的特殊属性,使得演绎作品的著作权与原始作品的著作权存在重合的部分,因而在行使时也必然受到原始作品著作权的制约和影响。我国《著作权法》第12 条规定,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原始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其著作权由改编、翻译、注释、整理人享有,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这条规定暗含了这样一条规则:演绎作品著作权的行使,实际上是由演绎作品和原始作品著作权人共同控制的,而且,在这个共同控制的关系中,原始作品的著作权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例如,某人经过原作品作者同意将音乐作品重新编曲并获得较为突出的艺术效果,则对编曲作品享有著作权,但是如果未取得原著作权人的同意,就不得再进行商业化利用或许可他人使用,因为编曲中含有原来音乐作品中的独创表达元素(旋律、节拍),而这些受到原作品著作权人的专有控制。之所以不承认演绎作品的独立地位,主要在于演绎权的行使实质为对原始作品的变化性使用,因此演绎权应受到原始作品著作权的控制。由于演绎作品与原始作品具有共同的表达元素,尽管演绎作品本身并不完全能替代原始作品,但演绎作品的权利行使如果不受限制,就很可能在客观效果上挤压原始作品的市场份额从而威胁原始作品著作权人对其作品独创性表达元素的专有。 例如,有人将《天龙八部》的小说改编成同名漫画,而一些电影制片人就会联系漫画作者要求授权改编成电影,此时,制片人除了获得漫画作者许可外,还必须要获得小说作者金庸的许可,因为如果无视金庸的权利,就会使得《天龙八部》小说改编成电影的权利直接被漫画架空,而《天龙八部》漫画所体现的原著中的独创的故事情节,本应是金庸才能享有的专有权利。
“编曲者权”应纳入邻接权范围,包含的权利内容至少应为:向公众表明编曲者身份的权利,许可他人按照编曲表演并获得报酬的权利。
(二)保护路径二:将编曲者权纳入邻接权
对于编曲者权益的保护,除了演绎权的承认,也有其他的选择。有一种观点认为,在“演绎”和“表演”之间,编曲更像是对音乐作品的“纸面表演”,即通过组织乐器和落实各声部实现对同一首音乐作品的不同表演效果。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也存在合理性。如果赞同这种观点,相应地,就需要给编曲者在法律上配置相应的“邻接权”。邻接权是指著作权之外的民事主体(主要是作品传播者)对作品之外又与作品密切相关的客体所享有的权利。邻接权的设立,在于传播者和作者一样对作品作出了贡献,付出了智力劳动,只是发生的环节在作品传播过程而不是作品创作过程。传播者虽然没对作品的产生付出劳动,但对于作品的传播投入了值得法律保护的新的劳动【3】。邻接权与著作权的区别主要表现在:第一,客体不同。著作权的客体是作品,而邻接权的客体是在传播作品过程中产生的创造性成果,如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等。第二,内容不同。著作权的权利内容包括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并且范围都较为广泛,而邻接权除表演者权外并不享有人身权利,即使在财产权利方面也较著作权要小很多。第三,保护期限不同。著作权的保护期限一般为作者终身加上死后五十年,而邻接权的保护期限则为自传播成果完成之日起五十年。
在我国,著作权法中包括表演者权、录音录像制作者权、广播组织权和出版者权。区分著作权与邻接权的关键是考察其客体独创性的高度。著作权的客体是指符合独创性要求的作品,而邻接权的客体则是未达到独创性要求不能构成作品的特定智力成果。邻接权产生的原因是保护那些独创性程度不高,但又与作品有一定联系的劳动成果。
对于音乐作品的表演活动而言,一个技巧高超的编曲者对于作品的艺术效果的展示和组织总是蕴含了再创作的成分,可能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例如,对于同一首旋律,不同的人按照不同的乐器编排和乐队配合,其效果和艺术感染力是不可能相同的。杰出的编曲者能够准确地理解音乐作品中所包含的作曲者所要表达的情感,调动自己的艺术激情,通过不同的乐器组织和表演者的安排来充分表达音乐作品的艺术价值,这其中必然包含了编曲者对于音乐作品与众不同的理解和判断【4】。尽管编曲只是“再现原作者在作品中已经设想好了的东西”,“只是把作品中作者的精神、作者的感受、作者的声音、作者的思想带给了我们”,但是,编曲活动中闪烁的智慧之光,是难以否认的。
随着我国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司法实践中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涉及文化产品的新型案件,从“故宫博物院诉北京天禄阁图文制作有限公司案”,再到“中华书局诉北京国学时代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案”,种种事实表明古文点校、古画临摹等类似的文化作品,难以构成版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但在权利类型上又不合乎现行法律关于邻接权的范围,在此背景下,邻接权的客体范围亟待扩充。 同样地,受限于“表演者权”的既有定义(演员、演出单位或者其他表演文学、艺术作品的人),编曲者难以归入“表演者权”,在目前著作权法修订之际,应当将“编曲者权”纳入邻接权范围,笔者认为应当至少包含下列权利内容:表明编曲者身份的权利,即向公众表明编曲者姓名或名称;许可他人按照编曲表演,并获得报酬的权利。
(三)两种保护路径利弊分析
1、独创性角度:“编曲权”较“编曲者权”要求更高
前文提到,由于借鉴了已有作品的表达,演绎作品对独创性的要求通常要高于已有作品。而事实上,音乐作品本身的独创性要求并不低。虽然看起来,组成音乐的各种元素有无限排列组合的可能,似乎音乐创作的天地无限广阔,然而事实上音乐作品特别是优秀作品的创作自由度却并非如此令人满意。这是因为,人的乐感和对特定旋律、节奏的偏好是特定的。考察一下那些脍炙人口的经典流行乐曲,不难发现听众喜好的都是包含特定和声的音乐。这就导致了两种现象:第一,音乐创作上有意识地趋同。例如,在西方创作中,通常有两个八度音域并持续三分钟,连续七音高在流行音乐中也很常见;第二,音乐上无意识地趋同。这种情形是指创作者因为潜意识的记忆而将他人有独创性的旋律、节奏当成自己的灵感而加入到作品中。正因如此,音乐作品的独创性和侵权判定相当困难【5】。音乐作品的独创性尚且如此,建立在音乐作品之上的演绎作品的独创性还要更高,这事实上就导致了大量的编曲由于独创性不够,事实上并不具备成为演绎作品的资格,而相较于对独创性要求偏低的邻接权(编曲者权)而言,将编曲权纳入音乐作品的演绎权利显然对编曲人是不利的。
此外,相对于音乐作品而言,音乐编曲在创作方面更多地呈现出一种模式化和类型化的趋势,导致对音乐的编曲更多的是对固定单元的串联而非对单个元素的创作,这就导致编曲中必然会出现大量音乐人熟知的片段或常见技法,而这些本身可能都不构成作品。这是因为,作品是由众多作品要素构成的,从创作作品的过程来看,有一些作品元素是很多作者在创作中常常用到的,在不同的作品类型中,体现思想的作品要素各不相同,例如,在美术作品、音乐作品、书法作品和舞蹈作品创作中表现为惯用技法和常见素材;在文学作品、戏剧作品和电影作品的创作中表现为剧情框架和惯用场景;在软件作品的创作中表现为设计思想、算法和通用处理方式等。因此,在排除出这些公共元素后,编曲内容的独创性元素就仅仅表现为对各种音乐表达元素的连接和组合,而这必然会使得大量的编曲被排除出保护范围。从这一角度而言,“编曲权”逊于“编曲者权”。
2、立法角度:“编曲权”优于“编曲者权”
从目前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来看,将“编曲权”解释为一种作品演绎权只需要法律解释,而要将“编曲者权”纳入邻接权却需要立法上的变动和若干新条款的修订。从维护立法体系结构稳定性的角度,通过法律解释和案例确认“编曲权”无疑能够节省大量的立法成本并最大程度保持立法的稳定和统一。
结语
近日,有新闻报道称韩磊在“《我是歌手》2015 巅峰会”中演唱的两首歌曲《雁南飞+呼伦贝尔大草原》借用了北京卫视综艺节目《音乐大师课》的编曲版权,涉嫌侵权,或将面临巨额赔偿。节目制作方宣传总监李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韩磊所演唱的两首歌编曲版权属于《音乐大师课》制作方,他是否侵权正在调查。而韩磊经纪人否认侵权,“这事儿跟侵权没关系。他唱那两首歌什么问题都不会有。因为两首都是老歌,歌曲的版权在作曲家手里。只有作曲家说你侵权才算数,什么时候听说编曲拥有版权了?编曲说了不算数。”
事实上,韩磊的“编曲门”事件只是不断浮出水面的涉及编曲权利的很多纠纷中较有影响力的一例。而这一事件中不同主体的反应和回应,也说明了在音乐领域,对于编曲权利的性质和地位,存在极大的认识上的模糊。如何确权,如何维权,取决于我们的立法选择或者司法解释,无论选择哪种模式(“编曲者权”或者“编曲权”),相应的维权模式都亟待架构,显然,随着音乐编曲人权利意识的觉醒,在看得到的将来,类似的纠纷将会不断涌现。
【1】陈锦川. 演绎作品著作权的司法保护【J】. 人民司法·应用, 2009(19).
【2】王迁. 著作权法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142.
【3】赵海燕. 田玉忠. 著作权法热点难点问题研究——兼论著作权法的修订【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4:178.
【4】王迁. 知识产权法教程【M】. 北京:中国人民法学出版社, 2009:197.
【5】崔立红. 音乐作品抄袭的版权侵权认定标准及其抗辩【J】. 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 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