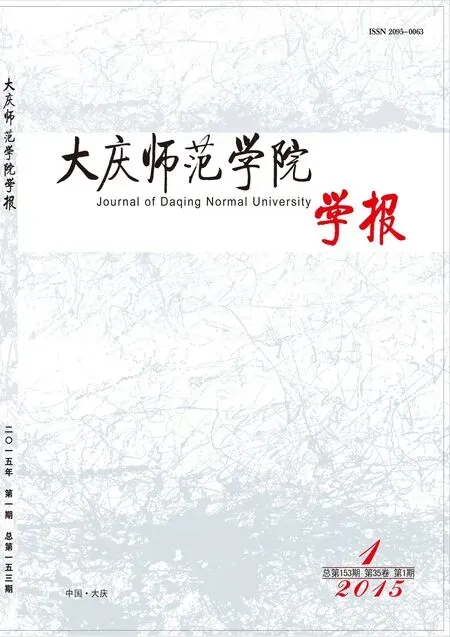泰山北齐造像碑记与敦煌“白衣佛”问题新证
作者简介:周晓冀(1971-),男,江苏宜兴人,博士研究生,泰山学院助理研究员,从事历史地理、佛教艺术史研究。
DOI 10.13356/j.cnki.jdnu.2095-0063.2015.01.028
在佛教艺术研究领域,弥勒与白色的关系问题,历来为学术界所关注。而学界提出所谓敦煌“白衣佛”,就其身份的认定、与禅法的关系等,也是意见纷纭,分歧较大。泰山北齐乾明元年(公元560年)佛教造像碑座,因其明确提及“白衣大像主”,故而成为释读“白衣佛”身份的新证据。
一、泰山北齐造像碑的发现与著录
北齐造像碑座今存泰安岱庙历代碑亭,长59.5公分,宽59.5公分,高20.5公分,是一尊佛教造像碑的底座。该碑于清代晚期发现于济南市长清区的泰山余脉,距五峰山东魏莲花洞石窟造像不远处。
民国《长清县志》载:“北齐徐明牟造像碑”,在“大齐乾明元年,莲花洞下石窝庄南阁墙壁上”。 [1]1966年该碑座移入泰安岱庙。碑文为造像题记和造像主题名,其中即有“白衣大像主”之名。县志录文多有谬误,而且文字缺失较多,唯“白衣大像主”清晰可辨。2009年笔者亲访岱庙,记录碑文如下:“齐乾明元年岁在庚□八月辛已朔□五日,比丘尼慧承、比丘尼静游、□□聂义美、率镇诸邑同建洪业,□敬造弥勒像一区。上为皇帝陛下、群臣宰守、诸师父母、含生之类。愿使电传冥昏,三空现证,法界共修,等成正觉。邑义主比丘尼识究、邑义主比丘尼僧炎、白衣大像主张苟生兄弟等、邑义樊兴、像主梁伏香、□□□□、由像主徐明牟、像主徐六周、像主苾苌受……(余有字痕,损毁严重而不能辨)”。
碑文提示,由比丘尼领导的民间社邑组织“敬造弥勒像一区”,并列众邑义及像主,其中唯一明确提到的造像主为“白衣大像主张苟生兄弟”。从上下文逻辑联系看,白衣大像就是指弥勒像。李清泉曾根据该题记,认为莲花洞石窟主尊即为弥勒, [2]这种观点在证据上还不够充分。因为该造像记在民国《长清县志》中提到,洞“左近有魏武定五年造像题名,又有齐乾明元年造像题名”。可见该题记并未在洞中,其后再次发现,是在五峰山下八百米处石窝庄南阁外北壁上。据此该碑不能确定就是莲花洞造像题记。
二、敦煌“白衣佛”研究综述
“白衣佛”一词最早由敦煌学者提出,是指在敦煌壁画中的五铺北朝佛像。即北魏时期的第254、263、431、435窟和西魏时期的第288窟西壁壁画中的说法图。这五铺佛像袈裟、身体皆呈白色,结跏趺坐,为说法相。“白衣佛”的名称显然是根据佛像的颜色特征,而敦煌壁画相关文献上并没有这种称呼。定名是确定佛格和分析佛像来源的重要步骤。1980年,贺世哲先生在《敦煌莫高窟北朝石窟与禅观》一文中认为,“白衣佛”典出《观佛三昧海经》,与“众窟中纯诸白佛、白妙菩萨”有关 [3]。后来贺先生又在专著《敦煌图像研究——十六国北朝卷》中明确提出,这五铺北朝“白衣佛”说法图乃是表现“佛影故事”。即《观佛三昧海经》中所云:“若欲知佛坐者,当观佛影。观佛影者,先观佛像。作丈六想,结加趺坐。敷草为座。请像令坐,见坐了了。复当作想,作一石窟。高一丈八尺,深二十四步,清白石想。” [4]因此“白衣佛”其实就是释迦涌身入壁后,留给众僧禅观的对象——白色佛影,实际上就是释迦牟尼的法身。
围绕着敦煌这五铺“白衣佛”像,学术界有许多争论。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
1.弥勒瑞像
王惠民根据《魏书》《隋书》《旧唐书》以及《唐大诏令集》中白衣弥勒教匪事,以及敦煌文献关于“弥勒白佛瑞像”的记载,认为“白衣佛”为弥勒瑞像,带有民间宗教色彩。 [5]而且根据《佛说法灭尽经》中有关末法时期,“沙门袈裟自然变白”等语,认为弥勒瑞像穿白衣具有末法象征意义。王惠民《白衣佛小考》提到《魏书·裴良传》载教匪“服素衣,持白伞白幡”。《隋书·炀帝纪》载“有盗数十人,皆素冠练衣,焚香持花,自称弥勒”。《旧唐书·太宗纪》载“禁白衣长发会”。《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三《禁断妖讹等敕》文载“比有白衣长发,假托弥勒下生”等。
2.千佛一佛
贺世哲在《敦煌图像研究——十六国北朝卷》中提到,陈慧宏认为“白衣佛”出自《法苑珠林》,其《法服篇》记载,释迦初成佛道时,穿上迦叶佛遗传下来的白色袈裟,大地为之震动。并且说“白衣佛”是“贤劫千佛中佛法付嘱的象征”,不是特定专指哪一个佛。
3.涅槃释迦
赖鹏举在《丝路佛教的图像与禅法》中认为,“白衣佛”与涅磐关系密切,而白色在中国自《周礼》以来即为丧服颜色之定制。“白衣佛”就是涅磐窟的主尊,象征已经入灭的释迦牟尼。 [6]
4.释迦佛影
滨田瑞美认为,“白衣佛”图就是《观佛三昧海经》卷四《观四威仪品》中所述“那乾诃罗的佛影”。“白衣佛”具有现在贤劫佛的性格,也可以说是映现在龙窟石壁内继续说法的释迦,是佛灭度后诸弟子观想的对象。 [7]这一观点与贺世哲先生不谋而合。
另外,约翰·亨廷顿(John Huntington)在其《犍陀罗弥勒造像的图像志与图像学》中认为,敦煌“白衣佛”来源于犍陀罗,具名为卢舍那佛。 [5]谢生保先生引用丁福宝编《佛学大辞典》中的“白氈释迦像”认为,“莫高窟最早的白衣佛说法像”与“经像初来之画像”有关,即画在白布上的释迦。
以上对“白衣佛”的观点,仅是针对敦煌这五铺说法图像。多数学者认为“白衣佛”是敦煌石窟特有的佛教艺术形式。如滨田瑞美在《关于敦煌莫高窟的白衣佛》一文中云:“此图像,除了莫高窟以外,其他地方还未发现。”王惠民则称:“佛经中并无白衣佛一名,我们据诸佛均着通肩袈裟而拟名,所以,更准确地说应是‘白袈裟佛’,敦煌以外的佛教文献、佛教造像中均无踪迹可寻。”在敦煌石窟中与白色相联系的佛教造像并不鲜见,而且都与弥勒有关。如:
敦煌遗书S.2113号壁画榜题底稿的记载:“南天竺国弥勒白佛瑞像记。其像坐,白。”
五代第72窟西壁龛顶西披北起第三幅有一立佛为说法相,榜题云:“南天竺国弥勒白佛瑞像纪。”
中唐开成四年(公元839年)建成的第231窟西壁龛顶东披南起第六幅图,为一身倚坐佛像,身着白色通肩袈裟,说法手印,榜题:“天竺白银弥勒瑞像。”
以上二窟,笔者未见实图,不清楚佛衣颜色,但据滨田瑞美文,目前尚未发现北朝以后的“白衣佛”图。
三、文献和文物中的佛像与白色的关系
其实跳开敦煌图像志,在其它地方还有更多的佛像与白色有关的事例。如《大唐西域记》中有犍陀罗国白石佛像的记载,《敦煌图像研究——十六国北朝卷》中第135页图标中,列出白玉像、白玉菩萨像等5例。其他的石佛像,就颜色而论,也应为白色居多。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东魏兴和二年(公元540 年)白石思惟佛像、唐天宝五年(公元746年)邸延果造白石佛像,均出土于河北曲阳。
白石佛像艺术在北朝时期是一个颇具地方风格的雕刻流派,艺术史研究称为定州系造像。定州系白石佛像始刻于北魏晚期,盛行于北齐和隋代。
以往的研究集中在两个关键点上,即白色与佛教的关系问题和白色佛像的佛格问题,这两个方面是解决敦煌北朝五铺“白衣佛”说法图含义的钥匙。
关于佛像身体颜色,首先可以排除对白石佛像的讨论。因为这类造像的白色质地主要是受汉白玉材质的影响,与造像度量无关,而且多数造像完成之后,还要绘彩涂金。至于白玉和白银像,则是出于尊崇的目的,采用贵重材质制作佛像,就像利用黄金、象牙等一样,所以也不予考虑。开成四年(公元839年)第231窟的壁画中的“白衣佛”像,应该就是当时天竺佛像做工考究、用料昂贵的真实写照。但是敦煌遗书S.2113号壁画榜题底稿及五代第72窟西壁榜题提到的“南天竺国弥勒白佛瑞像”又如何解释呢?
“白佛”,特别突出佛像的颜色是白色,为什么不是银色、不是金色或者其他颜色?白色在佛教中确有特别的含义。
白色作为化佛所展现的颜色之一,具有光洁耀目,超脱凡俗的视觉效果。“欲等漏垢所不染污,故名白色。” [8]
在《佛说观佛三昧海经》中多处提到白色化佛:“黄色化佛身黄金色。白色化佛身白银色。青色化佛身金精色。赤色化佛身车磲色。” [9]
佛穿白色袈裟也应有特殊含义。因为佛教规定一般僧衣应避开青、黄、赤、白、灰诸正色。而袈裟梵文kasaya,即为非正色,意用杂色染之。“于三色中白色为正” [10],所以现实中袈裟绝不可以为白色。“尔时世尊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时六群比丘着白色衣行,时诸居士见皆共讥嫌。” [11]676“时六群比丘,以大色染衣为僧受作功德衣。诸比丘白佛。佛言:不应以大色染衣作功德衣。彼用锦作,佛言不应用锦。彼用白色,佛言不应用白色。” [11]878
其实佛教对白色衣并不全都排斥,在《大乘入楞伽经》卷六中有这样的偈语:“修行者观察,皆住于无相。习气不离心,亦不与心俱。虽为习所缠,心相无差别。心如白色衣,意识习为垢。垢习之所污,令心不显现。我说如虚空,非有亦非无。” [12]
白衣在此象征内心的纯正,未受到行为的沾染,所谓“赤子之心”,率直、纯真、生命力旺盛,是最能接近佛性的。
汉、魏时僧人袈裟为赤色衣,后来又有黑衣(缁衣)、青衣、褐色衣和紫衣,紫色袈裟在唐代曾被作为朝廷对高僧的奖赐。反映在佛教艺术形象上也是如此,如与“白衣佛”同在的北魏254窟,南壁降魔图中释迦身着绛色袈裟,北壁难陀出家因缘图中释迦身着豹点纹袈裟。释迦牟尼提出:“若比丘得新衣应三种坏色。坏色者,染作青、黑、木兰也。” [11]676可见白色袈裟在佛教图像中出现,的确十分特殊,一定会有某种含义。
上文所云《佛说法灭尽经》中有“沙门袈裟自然变白”,实际是指所谓“坏色”袈裟于法灭时随之褪色,同文有“首楞严经、般舟三昧,先化灭去。十二部经寻后复灭,尽不复现,不见文字。” [13]可以看出佛经文字渐渐隐去给僧众带来的恐慌心理。该经描述的是释迦“涅槃后法欲灭时”的情形,故而不大可能是敦煌窟内的释迦身着白色袈裟现说法相。
其实白衣与宗教的关系在历史上曾有过确切固定的联系。最为明显的例子是,唐代曾经盛行一时的摩尼教崇尚“白衣”信仰,法国学者哈密顿也曾指出两者的关系。 [14]文献上首次明确记载摩尼教传入中原的时间是延载元年,而从史料线索上看可早至4世纪,唐人所著《灵鬼志》上有一段关于太元十二年白衣道士的记载。 [15]如同佛教一样,据信唐代的摩尼教也是从西域传来,而摩尼教自3世纪创立以来早已在西域地区广为流传。 [16]摩尼教在开元禁断之前长期与佛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假借佛教的仪轨和典籍,依附佛的名号进行传播。如20世纪初,在敦煌莫高窟发现的汉文摩尼教残经《摩尼光佛教法仪略》,其中署名拂多诞奉诏集贤院译。敦煌是西域宗教文化向内陆传播的桥头堡,在此首先接受并流行白衣摩尼信仰,并影响佛教造像艺术的可能性很大。尽管还没有在莫高窟发现摩尼教造像艺术的确凿证据,但是20世纪初期,国内外考察就已发现吐鲁番地区存在30几个摩尼教石窟,在胜金口、吐峪沟以及柏孜克里克或有数座摩尼寺庙。其中不少洞窟与佛教关系密切,甚至有的可以认定为佛教的“影窟”,而所谓“阴阳人图”与佛教的白骨观图像难以分辨,或许在艺术上两者的交融已经十分深入。 [17]这种白衣摩尼信仰能否在敦煌莫高窟造像上有所体现,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造像形式的创新改变不了佛教造像的本质,在莫高窟影响最大的还是佛教。即使摩尼教曾试图在佛教造像上多少体现一些自己的信仰,但是其比附依托佛教传播的性质不会改变。
四、结论
根据上文对佛教文献和考古调查的分析,敦煌北朝“白衣佛”最有可能还是弥勒。理由如下:
1.从敦煌有关文献看,该处唐代以后曾流行过天竺白佛弥勒瑞像,或许在北朝此类白佛瑞像就已成为画像范本。
2.王惠民所搜集到的资料显示,北朝以来民间弥勒教徒多着白衣,并成为特定的宗教符号,形成白衣弥勒信仰。唐代文献中多处记有“禁白衣长发会”事。史有白衣天子说法。“白衣天子”者,即“西方之天子”。《淮南子·时则训》言:“天子衣白衣,乘白骆,服白玉,建白旗。”905年,处敦煌的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张承奉建立“西汉金山国”,自封“白衣天子”。隋炀帝也“恒服白衣”,自比白衣天子。
3.按“五行”观念所指,西方属金,金为白色,佛从西来,身为金色。《魏书》释老志就记载:“孝明帝夜梦金人,项有日光,飞行殿庭,乃访群臣,傅毅始以佛对。” [18]实际造像画图时佛的金身多以白色代表。
4.从敦煌“白衣佛”所处窟的内容看,以弥勒解释也有可行之处。现存绘有“白衣佛”的北朝五窟皆是中心柱窟,窟内三壁绘画,其中西壁,即与窟门正对一面是该窟主尊所处位置,面积最大,地位显而易见最为重要。
最后,回头再看篇首提到的泰山北齐造像碑铭文,毫无疑问,白衣大像即是弥勒,而时代也与敦煌“白衣佛”相仿。
综合以上证据,笔者认为,敦煌北魏时期第254、263、431、435窟和西魏时期第288窟西壁壁画中“白衣佛”形象就是弥勒,是反映北朝禅观的弥勒说法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