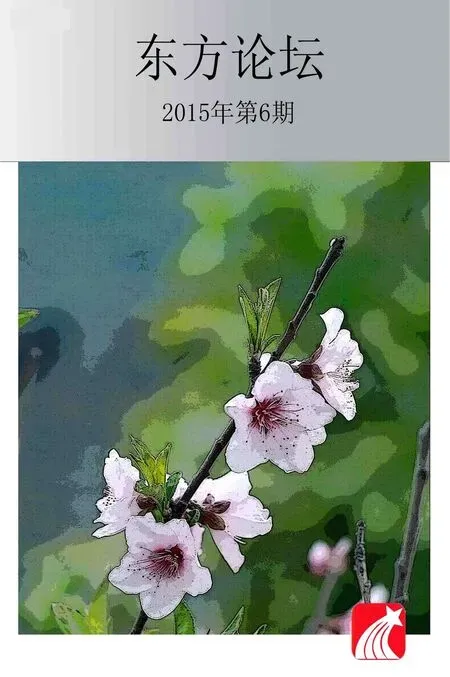中国现代文学作家表谱文献
徐 鹏 绪(青岛大学 文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中国现代文学作家表谱文献
徐鹏绪
(青岛大学 文学院,山东青岛266071)
摘 要:表、谱、传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作家生平研究中,被普遍采用,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文献的重要类型。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对于表这一历史体裁的采用,主要是年经事纬体的年表,用以编写作家个人的生平活动年表,著译系年和整个现代文学史大事年表等。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中的年谱与年表之间并无严格的区别。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作家;文献学;年表;年谱
作家生平史料,是知人论世深入研究和理解文学作品必不可少的辅助材料,因而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文献的重要内容。其文献存在的形式,除了作家的日记、书信外,主要有年表、年谱、传记和回忆录。回忆录是作家传记的史料,也是制作年表、年谱的依据。
表、谱、传都是记录历史的方式,是我国古代史书的体裁之一。
刘知己在《史通·表历》中指出:“盖谱之建名,起于周代,表之所作,因谱象形。故桓君山有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邪上,并效周谱。’”可知谱之名称创于周代。表是依据谱的形式又加以改造而制作。《史记》三代世表纵横成行,都是仿照周谱的。章学诚在《文史通议·和州志舆地图序》中也有相同的意见,并认为司马迁作《史记》列表不列图,致使后世史书相承,不收图而图亡,表却因之而兴。
关于表的作用,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曾有阐释:“《史记》作十表,仿于周之谱牒,与纪传相为出入。凡列侯、将、相、三公、九卿功名表著者,既立为传,此外大臣无功过者,传之不胜传,而又不容尽没,则于表载之。”就是说,表作为一种史书体裁,可以简而明的形式,将那些虽无功过,却有职位,够不上入传资格,而又不能完全埋没的大臣列表概述,以与列传相呼应。目前,史学界有专家将表的作用归纳为三点:整齐年差、通纪传之穷、会观诸要。“通纪传之穷”,也就是弥补列传只能收重要人物,而不能尽收有重要官职,但无大功大过大臣之缺陷。“整齐年差”“会观诸要”分别强调“线”和“面”,认为表可以以时间为线索,系统全面地反映历史发展的过程和概貌。可见,表、谱、传在古代史书中,是分别承担着不同的记述对象和任务,而相互间又成互补态势的史学体裁。
表、谱、传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作家生平研究中,被普遍采用,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文献的重要类型。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主要论述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的年表、年谱文献,其传记文献在它文中专门论述。
一、年表
中国古代史书中的表分为世表、年表和月表三种,以时间为纲,综合记录同时发生的各种事情。在《史记》各种史裁中,年表和本纪是按时序记述人和事,有提纲挈领的作用。书则以事类为纲,记录同类性质的重要史实。世家列传以人为纲,详记重要事件及其发展过程。在本纪和年表中概括提到过的事情,在世家列传中也有较详细的叙述,两者互相照应,共同形成了《史记》一书的合理构架。
《史记》十表的形式,可分为:世经国纬体,年(或月)经国纬体,国经年纬体,年经事纬体。十表中只有《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是以年为经以事为纬的体式。
表的作法,以简要为贵。阮芝生《司马迁之史学方法与历史思想》论述《史记》十表的特点时指出:“本纪体贵简要,表体亦贵简要,且比本纪更简。”“若以本纪为全书的大纲,则表实为大纲的大纲。”这个“简”当然不是指记人记事数量上的“少”,而是指记述某人某事时要做到简明扼要,记述文字应尽量简短。
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对于表这一历史体裁的采用,主要是年经事纬体的年表,用以编写作家个人的生平活动年表,著译系年和整个现代文学史大事年表等。简明扼要而又系统全面地反映作家的生平活动、著译情况,勾勒现代文学的发展线索和概貌。
年表的种类,可以不同的标准和从不同的角度来划分。按制表者的身份,可分为作家自著年表和研究者所编制的他著年表。按表所记述的对象来分,可分为单个作家的年表和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大事年表。按表所存在的方式分,可分为作为一书的附录而存在的年表和单行本的年表。
中国现代作家,几乎每人都有自制的著译系年和生平活动年表。但大都是简略的和不完整的,只记主要著作和重要活动,时间限于制表的当时。而文学研究者一般是在某一作家去世后,才编制其生平活动年表和著译系年,自然较作家个人的自著要完整。自著年表由作家本人手定,虽然也间有因记忆之误,或因作者故意隐瞒、显扬某些事实而造成的失真,但总的方面,史实是可靠的,因而会给读者以亲切、可信之感。而且从作者的叙述中,读者可以更真切地窥见作家的心态,他对自己作品和行事的认识和态度,有利于研究者对作家、作品进行知人论世的深入研究。
作家自制年表大多附于个人的文集或选集之中,言简意明,篇幅短小。附在《三闲集》之后的《鲁迅译著书目》[1](P177),实际上是作者的自制著译年表。该书目收作者1921年至1931年的著译书目,依年份排列,每种书目后用括弧注出有关著作(或译作)、文体、著作年份、篇数、印行所等情况。著译之外,又有“所校勘者”,“所纂辑者”,“所编辑者”,“所选定校字者”,“所校订校字者”,“所校定者”,“所印行者”。表末还有一大段回顾自己著译历程的文字,颇多体会与感慨,是对十多年来著译活动的总结,读来让人倍感亲切,这是在他制年表中所没有的。而且在表中列出了译著以外,作者所校勘、纂辑、编辑、选定、校定、校字、印行的书籍,这也是为作者以外的人所难以搜求齐备的。
《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16卷本末卷《附集》中,附有全集编委会所制《鲁迅著译年表》,以系年方式,列出鲁迅一生中的著译情况。为求完整,年表从鲁迅1881年出生开始写起,有著述之前的年份,简述生平活动。在有著述之后的年份,除记述著译情况外,亦兼记其它重要活动,与年谱近似。本年表是在编辑、注释《鲁迅全集》基础上编制,材料翔实可靠,考订精严。唯名为著译年表,却于著译之外,杂述其他活动,有乖体例。
197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近代文学组编写的《鲁迅手册》中,有《鲁迅年表》《鲁迅笔名表》和《鲁迅著译系年》。
《鲁迅年表》逐年列出包括鲁迅著译活动在内的生平活动。其编写体例,于每年之后,先标明鲁迅岁数,再叙本事,最后是本年发生的国内外大事和文化动态,作为年表的背景材料。
《鲁迅笔名表》,按年份列出鲁迅曾用过的笔名,说明每一笔名为写某文或译某书时所用,并解释笔名之含意,可借此窥见作者当时的情怀,是研究作者生平、思想和作品的重要资料。对于搜辑作者佚文也是重要的考证线索和依据。
以上各表,以纯文字形式写成。为了使内容更加显豁醒目,该手册的《鲁迅著译系年》是采取表格形式。其栏目依次为:篇名、署名、著译日期、发表日期、发表报刊、收入书籍、备注等。内容详备、眉目清晰,颇便观览翻检,是标准的“明细表”,与史书之表更为近似,在中国现代文学年表中可备一格。在此表之前,有吉林省四平师专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组编制于1972年11月的《鲁迅年表》,收入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馆研究室编的《鲁迅思想研究资料》(内部资料)一书中,是一个兼记鲁迅生平活动和著译情况的综合性年表。也是以表格形式制成,栏目分:纪年、事略及著译、文化动态、国内外大事等。
20世纪80年代初,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发起,全国有关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等分别承担编选《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甲乙丙种,其乙种为《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比较全面地搜集和整理了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有代表性的不同思想倾向、不同风格流派的作家作品资料。本丛书为全国文学学科重点规划项目之一,列入规划的,几乎囊括了现代文学史上全部有成就的作家。由于各作家的研究资料分别由全国各大出版社出版,在经济大潮裹挟下,许多已经编就的研究资料,因经济原因而未能出版。据徐廼翔先生说,他所收藏和见到的,已经出版的有90家左右。按照该丛书的编辑体例,每一位作家的研究资料中,均附有该作家的《生平活动大事记》和《著译年表》。“大事记”简要纪录作家的生平活动,包括著作活动,实际上是作家的简谱,所以有的作家资料的编者,干脆称之为年谱,如《郭沫若研究资料》介绍郭沫若生平著作活动,用的就是卢正言编《郭沫若年谱简编》;《林纾研究资料》用的是张俊才编《林纾年谱简编》,这将在以下年谱部分介绍。“著译年表”亦称“著译系年”,实际上是一种系年书目。其编录体例为,年份之下录入是年的著译篇目,著译时间与地点,发表时间,期刊与卷号,署名,初收文集名及版别。该丛书有统一编写体例,但具体做法有差别,有的著译年表不单独标出年份,而直接按写作发表时序列出篇名,因各篇之下已有写作和发表的年月日,如《刘大白研究资料》。有的还对作品有关情况加注予以介绍、说明,如《郭沫若研究资料》中,由上海图书馆所编的《郭沫若著译系年》,于1912年下录入《舟中偶成 三首》(五律),标明1912年3月8日作,然后加注注明:“《舟中偶成》之第2首初见于1924年3月18日所作之《十字架》中题名《休作异邦游》。后收入1959年11月北京作家出版社第1版《潮汐集·汐集》,写作时间误署1913年5月作于成都”。 又,《和王大登城之作 原韵二首》(五律)下注云:“王大即王维新,号伯恒,系郭沫若在乐山高等小学堂之同学”。
对每位作家,“年表”不仅收录其初次发表和出版的著译,也收录建国后重新编辑出版的旧作,其时间下限录至“年表”编成之前。如《王鲁彦著译系年》便收录了1951年7月北京开明书店出版的《鲁彦选集》,一直收录到《王鲁彦著译系年》编成之前,1982年7月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鲁彦散文选集》。
除作为书之附录的简明年表外,尚有自成一书以单行的“系年”。王观泉编《鲁迅美术系年》[2]和秦川编《鲁迅出版系年》[3]可为代表。
《鲁迅美术系年》以年系事,将鲁迅从1927年至1936年九年间的美术活动逐年予以详列,对1927年以前即从童年到定居上海之前的美术活动,由编者撰写《鲁迅先生早期美术活动》一文加以综述,作为系年的附录附于书后,帮助读者了解鲁迅美术活动的全貌。本系年乃是鲁迅美术活动的史料长编,在编写上有严格的体例。既为系年,全书严格按时间顺序,依据《鲁迅日记》记载将鲁迅美术活动的资料逐日编入;日记中无记载的,则根据《鲁迅全集》 《鲁迅书信集》及其它资料编入;非一日一时完成的事项,则综合编入。编入的资料包括美术论文,有关美术的言论、书简、藏书,以及同时代人对鲁迅美术活动的回忆,和有助于了解鲁迅美术活动的重大事件。编录的原则是,凡美术专著,只录篇名;而对非美术专著中有关美术的言论和书信中涉及美术的部分,则视情况或全部抄录,或摘录,或由编者略述大意。录入的内容依次为:一、美术活动;二、创作指导思想;三、美术运动情况;四、美术史料。引文注明原文初载刊物和初次编入的单行本,不见于鲁迅著作单行本或全集的有关美术的佚文则录全文;由编者鉴定的佚文录入时加以说明。该系年还将见于《鲁迅日记》和《书帐》的鲁迅购买画册的目录和有关情况全部录入,提供了了解鲁迅研究中外美术的资料。本系年编入了丰富的资料,理清了1927—1936年鲁迅从事美术活动的全部情况,特别是对他发起组织进步木刻运动的过程进行了详细的纪录。鲁迅有关美术的理论主张,鲁迅的美术活动以及与此有关的人、事、美术作品等,均得以充分而清晰的展现,为撰写现代中国美术史提供了经过整理的史料。
王观泉先生是精于史料考证治学严谨的学者,本系年于1973年5月完成初稿,至1977年经过两次修订成书,不算写作初稿及以前的研究,就经历了4年的时间。编者不仅锐意穷搜,获得了丰富的经过深入考证的可靠史料,而且对全书的构架包括一些细节,都进行了周详的考虑和安排,编写体例细密周严,堪称此类文献的典范之作。
秦川编《鲁迅出版系年》,逐年编入了上起1906年鲁迅筹办《新生》杂志,下至1936年逝世,前后30年间编辑出版活动的情况,是鲁迅编辑出版活动及有关言论的史料长编,研究鲁迅与出版问题的重要依据。
本系年以鲁迅的日记和书信所载编辑出版活动的资料为主,按年月日顺序编入。日记、书信未载者,则依据鲁迅自己的著作和其它第一手资料,包括已公开发表或收集的佚文顺次编入;对成年累月完成的事项在适当处予以综合说明。编入资料包括有关编辑出版的活动、言论、书简、论文、同时代人的有关回忆、整理出版中国古代典籍的资料等。本系年以丰富翔实的可靠资料,较全面地勾勒出鲁迅三十年从事编辑出版活动的概貌,对研究现代出版事业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关于整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大事年表,未见有专书出版。吉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由郑方泽编的《中国近代文学史事编年》一书,其编写思路、方法和体例,可资参考借鉴。此书以系年方式逐年编入中国近代文学史事,并适当辑录与文学发展有关之文化、政治、历史等大事。编排体例为按年系事,或由事系人。各年所编之史事按以下次序排列:①与文学有关的国内大事;②文艺思想斗争、文艺理论建树、文艺流派社团的活动,以及其他有关史事;③作家行止;④活动于本年前后,生卒年不详的作家;⑤逝世的作家;⑥创刊的报刊,主要是文艺报刊及兼载文艺的综合性报刊;⑦当年刊行的主要论著;⑧当年刊行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⑨电影记事。全书共辑录作家374人;作品包括诗词、散文、小说、戏曲、弹词、电影、论著等,共约400种左右;文艺报刊,包括兼载文艺的报刊105种。所列作家,在本编年内逝世者,在卒年介绍;卒年在五四运动以后的跨代作家,在参与文学活动的最初年代介绍;生卒年不详者,据史实在其活动的年代中介绍。书末还附有《作家索引》《作品及论著索引》《文艺报刊(包括兼载文艺的报刊)索引》。
在众多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中,附有《年表》的,有山东师范大学冯光廉、朱德发、查国华、姚健、韩之友、蒋心焕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程》[4],显示了编著者重视史实的修史倾向。注重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建设,是该校现代文学学科的历史传统。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曾编写过《中国现代作家研究丛书》计15种近300万字的资料。在当时,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史料搜集与整理,实在是一个创举。在此后的各个历史阶段中,该校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一直把史料建设视为学科建设的基础。这部《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程》的作者,在编写中有着明确的学术追求:“力求从原始史料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反映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本来面目”(教程《说明》)。在书后附《中国现代文学年表》,是编著者重视史料,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表现。该年表以系年方式,按年月日顺序录入了从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第2卷第6号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文学改良主张起,至1949年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止,前后32年间中国新文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史实。举凡文艺思潮与文学思想的论争;重要社团流派的成立、形成与解体;文艺报刊(包括刊载文学作品的综合性报刊)的创办与终刊;重要作家的行止及重要作品、论著的发表与出版;会议的召开与宣言的发布等等,无不在这个年表中得到反映。该年表内容翔实,史实可靠,体例周严,表述精当,与正文相互发明,相得益彰。
附有《年表》的还有后出的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5]。此书修订时适逢学术界对“新理论”“新方法”热进行反思之时,此前出版的现代文学史著大都受当时思潮影响,注重理论与方法的创新,而忽略史实,“以论代史”的倾向严重。《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则是一本有意纠正这种偏颇的书。该书修订本的《后记》宣称,他们撰写此书的“目的与任务是为现代文学史的教学提供基本的事实与发展线索,更进一步的理论总结与概括则留给本教材的使用者在教学与研究过程中继续完成。”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修订本删去了初版本的长篇“绪论”,不对现代文学发展的特点和经验教训作历史总结。甚至在各章标题上删去了概括性、判断性的内容。作者把这种做法称之为“低调处理”,认为这样的处理,“是稳妥的与必要的”。加强对现代文学基本史实的叙述和发展线索的勾勒,是此书一个鲜明的特点。用这种实事求是的做法,以纠正当时流行的把理论方法强调到压倒史实地位的错误风气,在这个《后记》中被表述得十分明确。在文学史著中附《年表》的做法,正是作者尊重史实学术思想的体现。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的《年表》在编写构想和体例上,与上述《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程》不同。它不是一个附于全书之后的总表,而是分附于各章之后的“本章”年表。这种分编的方法,并非把一个总年表分成几段,而是各章年表均形成一个自我完足的独立体系。各章年表间相互补充、呼应,但并不一定互相衔接。全书29章后所附的29个年表,大体可分为作家个人年表和综合性年表两类。凡列有专章的作家,该章的年表实际上就成为这一作家个人的大事年表,如鲁迅、郭沫若、茅盾等。内容包括作家的生、卒及重要经历,著译编辑活动和作品发表出版的情况等事项,按年月日顺序编排。综述性篇章则为综合性年表,如各个十年的《文学思潮与运动》以及《小说》《新诗》《散文》《戏剧》等章的年表,则综合叙述各阶段相关作家的文化活动和著译编辑、作品发表出版情况等,依年月日顺序录入。第29章《台湾文学》年表,综述台湾现代文学大事。这样,全书的年表就由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沈从文、曹禺、赵树理、艾青等九位作家的年表和新文学三个十年的《文学思潮与运动》《小说》《通俗小说》《新诗》《散文》《戏剧》的分文体年表,以及《台湾文学》地区性文学年表所构成。这些年表,合起来从不同方面用史实反映了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概貌和发展线索,而各年表又可自成体系,完成了对某一作家,某种文体,某一地区,以及现代文学思潮与运动基本情况与历程的勾勒。本书作者把重点放在对作家文学成就的论述,以及各文体代表性作品的分析、自身演变历史线索的梳理。应该说,上述各种年表的编制,对于这些任务的完成与实现,是起了重要的辅助作用的。
还有一种关于文学社团流派的年表,《文学研究会资料》和《创造社资料》均附有该社团的大事记。《文学研究会大事记》前有《引言》概述文学研究会的基本情况。大事记以年系事,记述了文学研究会从1921年1月4日成立,至1932年“一·二八事变”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印刷厂等处被炸,《小说月报》第23卷第1号(新年号)毁于战火,文学研究会无形消散为止的大事。《创造社大事记》前面亦有一段概述性的文字,正文按年月日列出该社从1921年正式成立起,至1930年停止活动十年间的大事。这两个社团的大事记,在编写体例上是一致的,都是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来介绍社团的重要活动。从社团的成立到停止活动,社团文学主张的提出,机关报刊的创刊、改刊、停刊,出版部的创办与出版活动,丛书的编辑,社团成员的创作活动及行止等等,凡社团一切可记的事件均依时序列出。虽未列表,但这种按年月日编排以简洁的文字记述的大事记,仍可使读者一目了然。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的研究,这类年表式的大事记,是极有帮助的。
此外,还有一种现代文学作家《家族世系表》,也是《表》这种文献类型的形式之一。周启祥、谢励武的《鲁迅家族世系表》[6],是根据周作人著《鲁迅的故家》《鲁迅的青年时代》等书编制的。两位编者认为,他们所使用的这些材料的真实性与可靠性,“是无可怀疑的”[6]。
《鲁迅家族世系表》是以史书标准的表谱形式编绘的。鲁迅家族始祖周逸斋,是在16世纪初期(明代中叶)由湖南道州(今道县)移居到浙江绍兴定居的第一代。世系表绘录了从周逸斋开始,到周寅宾,到致房、智房与兴房,从周苓年、周介孚、周伯宜到鲁迅,共14世近400年的家族承传关系。世系表中的不少人物,对少年鲁迅产生过影响。其中一些人被鲁迅写进《朝花夕拾》,或以艺术形象进入鲁迅创作里。因此,这个家族世系表成为深入了解鲁迅少年时代和鲁迅作品人物创作原型的重要文献。
二、年谱
年谱也是一种传记形式,是依时序逐年排列人物事迹的文献类型。年谱所记述的人物称为谱主。
梁启超指出:“年谱这种著述,比较起得很迟。最古的年谱,当推宋元丰七年吕大防做的《韩文年谱》《杜诗年谱》。”此后,“南宋学者做年谱的就渐渐加多了,到明、清两代简直‘附庸蔚为大国’,在史学界占重要位置。”[7](P210)
梁启超所说《韩文年谱》《杜诗年谱》即吕大防编于1084年的《韩吏部文公集年谱》《杜少陵年谱》。吕氏在韩谱后记中讲自己编写年谱的动机道:“予伤韩文、杜诗之多误,既雠正之,又各为年谱,以次第其出处之岁月,而略见其为文之时,则其歌时伤世、幽忧窃叹之意粲然可观。又得以考其辞力,少而锐,壮而健,老而严,非妙于文章不足以至此。”编著年谱,以年系事系文,一可以参考时代背景,结合时势以深入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体会其情感情绪;二可以从诗文编年中,梳理出作家作品艺术形式和创作风格的流变过程、发展脉络。章学诚在《文史通议·韩柳二先生年谱书后》中也说,年谱这种传记形式,可以“考次前人撰著,因而谱其生平时事与其人之出处进退,而知其所以为言,是亦论世知人之学”。也是从作家作品与时势的关系着眼,肯定年谱可以帮助学人对作家作品进行知人论世式的深入研究的意义。对这一点,梁启超讲得更为明了:“做年谱的动机,是读者觉得那些文、诗感触时事的地方太多,作者和社会的背景关系很切。不知时事,不明背景,冒昧去读诗文,是领会不到作者的精神的。为自己用功起见,所以做年谱来弥补这种遗憾。”[7](P210)鲁迅也对年谱发表过类似意见,他认为:“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现在新作的古人年谱的流行,即证明着已经有许多人省悟了此中的消息。”[8](P3)宋代以来,一是随着文学文献整理事业的发展,学者们需要对作品进行更准确的编年;二是为了更全面深入地了解作品,了解作家的思想演变和创作历程。于是,作家传记研究受到学者的重视。但他们不满足于一般性叙述作家生平的传记,而要求对作家行事,特别是作家的创作活动作更为精细确切的纪述,这样,年谱这种特殊的传记形式就应运而生并兴盛起来。
年谱要考订谱主的家世、师承、交游、仕宦经历等生平事迹,对于作家,除对其生平活动进行考订排比外,还要将其作品逐一考证分系于各年之下,并且还要叙述当时重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件,将谱主的生平和著作活动置于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以便“知人论世”,对谱主个人的行为、思想和作品做出合理的解释和实事求是的评价,并从这种考订、梳理、排比中,显现作家思想和创作发展的脉络轨迹。年谱除了为作家作品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帮助外,它本身还有保存人物传记和相关史料的作用,对人物传记和历史写作都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最初由宋代人编著的年谱,大都比较简略,多为别集的附录。发展到后来,其内容越来越繁细丰富,篇幅越来越大,遂从别集中独立出来,成为专门著作,其形式也日益多样化。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把年谱分为若干种。从年谱内容上划分,除单记一人的年谱外,还有记相关数人的“合谱”,记某人某一时期或某一方面活动的“专谱”,汇集一人多种年谱加以考订的“年谱会笺”,考订谱主作品写作年代的“诗文系年”(已在前文的《表》类叙及)。从年谱制作形式上划分,可分为纯文字叙述的“文谱”和以表格形式绘制的“表谱”等。从编谱者的身份划分,可分为:(一) 自撰年谱。此类年谱出现得很晚,梁启超认为清代康熙时的孙奇逢是最早自撰年谱者,但此谱甚为简略,后由其弟子补注完成。稍后黄宗羲也自做年谱,可惜已散佚不传。[7](P211)此外,冯辰据李恕谷自记《日谱》删繁存要而成的《李恕谷年谱》前四卷,梁氏以为亦可归入自撰年谱一类。(二) 他撰年谱。又可分为同时人和异时人所撰年谱。同时人所撰年谱指由与谱主关系密切的人,也就是友人及弟子门人为其父兄师友所撰年谱。此类年谱因时近地切,见闻最真,尤其那些对谱主能深知其学,自身又有学识的人撰写的年谱,其价值几与自撰年谱有同等价值。梁氏推崇《王阳明年谱》,因为那是由王阳明的许多得意门生共同搜辑资料,后由钱德洪编著而成。异时人所做年谱,是此种文献之大宗。编著者因景仰先哲,想彻底了解谱主的身份学问,在谱主逝后为之修谱。此种年谱因后出,撰者与谱主没有感情上的纠葛,容易客观;许多事情,往往需经时间淘洗,异时人反而可以考辨清楚,所以自有其价值。如从著述方式来看,可分为创作的或改作的。创作的是指前无所承,首先为谱主所修之谱;改作的是指在前谱基础上加以增订删改而成的新谱。一般要比原有的更为详尽充实可靠。
从修谱的具体方法上划分,则可分为平叙的或考订的。历来对谱主事迹没有异议和争辩的,自然勿需考订,修谱时直书其事,是为平叙的年谱;需要考订的,如:①谱主事迹记载太少,需从各处钩稽。王国维《太史公系年考略》,因太史公事迹在《史记》《汉书》中均无系统详细记载,王氏便将自己从其他典籍中零散钩稽出的史料详加考证,且逐条记出考订经过,说明入谱的理由。②旧有记载有误,需通过考证订讹正误。③旧有的记载故意对谱主加以贬斥诬蔑的,也应通过考证加以订正。如蔡上翔作《王荆公年谱》,将《王荆公文集》和北宋各书关于谱主的资料进行广泛的搜辑和严密的考订,纠正了《宋史》对王安石的诬蔑不实之辞。
从年谱的存在印行方式上划分,可区分为附录的或独立的。二者的不同在于详略。附录于书后的年谱,注重谱主的主要事迹,少引谱主的著作,比较简略。读者欲详知谱主的见解主张等有关著述情况,可细读本集。此类年谱附于本集以后,可给读本集的人以方便。独立单行的年谱,把谱主文集或全集的重要见解和主张与谱主重要事迹摘要编年,使人不读本集即可知谱主的身世、事业、学术、创作的大概。总之,附录的年谱须简切,单行的年谱须宏博。
中国现代文学文献中的年谱,本文此前所列述的作家的著译年表和系年,实际上也可归入年谱之中,表与谱之间并无严格的区别。附录在文集全集之后的简约的年表,既记作者的生平活动,也录其创作、著述、翻译等事项,与附录之年谱本无不同。简明的依年月日顺序编成的著译附表,纯由书目构成,自然可以称之为表,但它无疑又是目录的一种。单行的详细的著译系年,既录入作者的著译目录,又叙述与著译相关的活动。系年虽标明年月日,但所列内容远较目录为复杂,所以,虽可作为目录使用,但不能以单纯的书目视之。而且亦不如“表”之一目了然,与“表”亦颇不相类。故应将其列为“谱”之一种。如王观泉《鲁迅美术系年》、秦川的《鲁迅出版系年》等。李允经、马蹄疾编著的集中反映鲁迅美术活动之一的木刻活动系年,径称为《鲁迅木刻活动年谱》。本书为叙述方便,按习惯,将依年月日顺序编的简明书目和大事年表,特别是编者明确标明为“表”者,均在“年表”部分评述。而将依时序综合录入谱主行事(不论其繁简)者均在“年谱”中评述。
中国现代文学领域,鲁迅的年谱出现较早。鲁迅逝世后,由周作人、许寿裳、许广平合著的《鲁迅年谱》,是鲁迅年谱的开山之作。撰写者均为著名作家和学者,又是对谱主知之甚深的亲友。年谱的第一段(自1881年至1909年)由周作人执笔;第二段(1909年至1925年)由许寿裳执笔;第三段(1926年至1936年)由许广平执笔。最后由许寿裳总其成。在分工上,每人负责撰写自己最熟悉的段落。而且周作人、许寿裳又各有自己的日记作依据。所以,年谱史实的可靠性是毋庸置疑的。该年谱是为编印《鲁迅先生纪念集》而作,不是一个单行独立的年谱,内容简略,是现有年谱中最精简的一种。篇幅虽小,但因出自名家之手,而且作者们又有明确的文体意识和严格的编写体例,写作态度极为认真,因而此年谱具有不可替代的权威性和典范意义。
《鲁迅先生年谱》前有“凡例”五则,除第五条声明本谱材料的来源,“有奉询于先生母太夫人者,亦有得于夫人许广平及令弟作人建人者”外,均是就年谱材料的取舍、详略的说明。第一条为总则,申明因谱主自民国元年五月到达北京开始,即无间断地写日记,“凡天之变化如阴、睛、风、雨,人事之交际如友朋过从,信札往来,书籍购入,均详载无遗,他日付印,足供参考。故年谱之编,力求简短”。第二、三、四条分别说明于著译、古籍整理、编校活动“仅记大略”而不详述的原因,是对第一条的进一步申说。说明作者在动笔编写年谱之前,对入谱史料的取舍详略问题即有周密的思考。
从编写立场看,作者们力求客观,避免因执笔者与谱主关系密切而褒贬失当。据许广平回忆《〈鲁迅年谱〉的经过》,编定过程中,许寿裳因年谱前期叙述太略,曾向鲁迅母亲询问有关鲁迅幼年的生活情况,获得一些材料,增入年谱后请周作人审阅,周作人看后即复信许寿裳,声明自己不再署名:“鄙意此谱还以由兄单独出名为宜,已擅将凡例涂改矣。盖弟所写者本只百分之二三,只算供给材料,不必列名,且赞扬涂饰之辞,系世俗通套,弟意以家族立场,措辞殊若不称,如改为外人口气,则不可笑也。”所谓“赞扬涂饰之辞”,显然是指增添的有关先生幼小时的事情,此乃许寿裳得之于太夫人的确实史料,但周作人为避免因“家族立场”而堕入“赞扬涂饰”的俗套,乃放弃署名权。对于许广平与鲁迅的关系这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周作人在民国前六年(1906年)下明确记出:“六月回家与山阴朱女士结婚。”许寿裳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对此做如下处理:“关于弟个人婚事,裳拟依照事实,直书为‘以爱情相结合……’并于民七特标‘爱情之意见’一条,以示豫兄前此所感之痛苦,言隐而显,想荷谅解。”而许广平个人则干脆在民国16年10月下直书为“与许广平同居”。由此可见,年谱编写者追求客观公正的立场。
编者的写作态度也是极为严肃认真的。正如许广平在回忆文章中所指出的,年谱是“经过不少的波折,安排,增删和订正,并不是一挥而就,随随便便算了的。”这从许广平公布的围绕着年谱编写的一些往来信件中便可体会到。这些信件主要是三位作者就年谱的编写交换意见。年谱初稿写成后,则是对年谱内容的反复商榷修改。有些修改,如关于“19年10月与内山合开版画展,内山下应否增完造?”民国16年“3月主持北新书屋,供给未名、北新文艺……”,“未名”下应添一“社”字,“北新”下应添“书屋”,等等。乍看起来可改可不改,似乎并不重要,但作者们连此等小事亦不轻易处置,可见其一丝不苟的精神。
年谱的具体编写,在体例上充分体现了编者追求简约严明的写作精神。在年份的标示上,以民国纪年。民国成立前标民国前××年,又同时注明旧历西历年份,然后注明先生×岁。年份之下,即记本事,包括生平活动、人事交往与著译编述概况等。如:
前十年二十八年壬寅二十二岁
一九〇二年
二月,由江南督练公所派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
课余喜读哲学与文艺之书,尤注意于人性及国民性问题。
民国成立之后,除民国元年之外,均不带“民国”二字,径直标明×年,后边只注明西历×年,而不再有旧历年份。如:
七年 一九一八年三十八岁
自四月开始创作以后,源源不绝,其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以鲁迅为笔名,载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掊击家族制度与礼教之弊害,实为文学革命思想革命之急先锋。
是年仍搜罗研究拓本。
本事中,除《狂人日记》这样重要的作品对内容有简要介绍和进行总体评价外,一般只介绍书名篇名和发表报刊年号。
《鲁迅先生年谱》虽是一个简谱,但编者的写作立场客观公允,态度严肃认真,对史料的别择极为严苛,又有清醒的文体意识和周密的编写体例,文字简约严明,凡此,均足以垂范后世。
此后,又有多种《鲁迅年谱》相继问世。个人编著的有日本猪俣庄八的《鲁迅日本留学时代年谱》,是作者在1956年12月所写的“以日本留学时代为中心的”《鲁迅传觉书》的附录。有李芒的译文刊载于《鲁迅研究资料》(2),文物出版社1977年11月内部发行,译文稍有删节。该年谱有两个突出的特点:第一,它是一个阶段性年谱,只记谱主留学日本时期的活动;二是它的表格形式,近似于年表,眉目清晰,内容又不过于简略。
其撰写体例,全部内容分为5项,分别在表内列为5个栏目:年份(以西历表出,括弧内注明与之对应的中国和日本纪年)年龄、鲁迅事迹、中国文化界动向、外国文学、历史背景。中国文化界动向内容含:①一般动向;②学校、书店、文化团体;③报纸杂志;④小说、戏剧;⑤诗歌、评论;⑥国语运动史;⑦文化界人士的动向、生死。外国文学包括日本、俄国和其他国家的重要文学动态。历史背景含中国、日本和其他国家的重要历史事件。五项中以鲁迅事迹为主干,叙谱主的生平活动和著译编述活动,内容稍详。其末三项为历史文化背景,以与鲁迅的活动相比照。此种作法,对后出之年谱的编写,有较大影响。
完整的年谱则有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2年出版的曹聚仁《鲁迅年谱》。在中国大陆,迟至新时期后,才陆续出版了王观泉《鲁迅年谱》[9],鲍昌、邱文治《鲁迅年谱》[10],蒙树宏《鲁迅年谱稿》[11]。集体编著的有复旦大学、上海师大、上海师院合编的《鲁迅年谱》[12],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年谱》[13]。
王观泉《鲁迅年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 年3月第1版。该谱于1976年编成,正式出版前曾以黑龙江省文化局创作评论办公室名义内部印行。在编写体例上,本年谱分事略、自述、大事记、文化动态、著译等五部分。“自述”部分中有编者的叙述、考证或注释。谱主的全部著译目录均编入年谱,并注明写作日期、署名、初次刊登报刊、收入何集。生前著译之单行本,均在出版的当年著译栏内简述版本沿革。生前未出版的著作、书信、日记等,亦在1936年内简述版本沿革。编者还进行了阶段性划分,分为1881—1916年;1917—1926年;1927—1936年三部分,将鲁迅的一生的发展分为早期、前期和后期。每一部分前有一概述,简述该时期鲁迅思想发展状况。
该年谱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有谱主的“自述”。编者将散见于各处的鲁迅自述其生平的文字整理入谱,以与年谱中的事略相印证,便于读者详细而确切地了解鲁迅的生平事迹,而且更增强了年谱的可信度与亲切感。
鲍昌、邱文治《鲁迅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6月—1980年9月第1版。这是个人编撰的《鲁迅年谱》中篇幅最大的一种,全书74.1万字。初稿曾在《天津师院学报》连载。
在编写体例上,该年谱采取逐年、逐月、逐日的记载方式,为使读者对鲁迅思想和生平事业有一个更清晰、完整的印象,编者将谱主的一生分为若干时期,并对每一时期进行简约的说明,与上述王观泉《鲁迅年谱》将鲁迅一生划分为早期、前期、后期不同,该谱划分更细,上卷分为:①童年与少年时期(1881—1897年);②南京求学时期(1898—1901年);③日本留学时期(1902—1909年);④从辛亥革命前后到五四运动(1909—1919年);⑤从五四运动到五卅运动前夕(1919—1924年);⑥从五卅运动前夕到北伐战争的高潮(1925—1926年);⑦从北伐战争的高潮到“四·一二”政变(1926—1927年);⑧伟大的思想飞跃时期(1927—1929年)。下卷为:⑨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1930—1936年)。
本谱于每条本事之下均注明史料的出处,其史料的来源依次为:(1)鲁迅在其日记、书信、作品中关于自己的记述;(2)与鲁迅活动有关的文件;(3)具有直接见证意义和一定史料价值的回忆录、回忆文章;(4)根据调查研究而写的能够补充前人回忆之不足的文章,或能提供较详细背景的文章。每类资料另起一行排空两格。对第四类资料和在史实上具有参考价值的鲁迅作品,增加“参见”二字。首次引用的资料,均详细标明作者及出处,再次引用则只标题目和页码。选用未发表的回忆文章和访谈记录时,均标明“未刊”字样。凡未刊资料仅作为已发表过的资料的旁证,故不单独引用。
与鲁迅活动关系密切的重要的国内外大事于本事中叙述。为帮助读者理解鲁迅的生平和著作,本谱适当选取有关政治、文艺方面的国内外大事作为背景材料,以楷体字排于本事之后。1917年以前的,记于每年之后;1917年以后的,则记于每月之后。
本谱对鲁迅大多数作品均加简略的题解。
作为一部规模较大的年谱,其编写体例安排得细密周详,特别是于每条本事之下,均详注材料的来源出处,对于帮助读者进一步学习和研究鲁迅,都是极为便利的。
复旦大学、上海师大、上海师院合著《鲁迅年谱》 安徽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全书分上、下册,计57.1万字。
本谱综合运用了鲁迅日记、书信、著作和其他物证所提供的史料,参证了书籍、报刊、回忆录、访问记等,对谱主的生平思想、著述翻译、家庭交游,并结合时代背景,系年编谱。叙列一般按年月日,尽可能落实到月和日。无月可据的事迹,考订到季,无日可据的考订到旬。早年资料难得,故只能按年系谱。与鲁迅本事有直接关系的时代背景材料,编入正谱,否则,均附录于月末年终。对延续数月或数年的事件,则选择一处或两处集中叙述,力避分散繁冗。
鲁迅全部著译均入谱,各篇皆单独列目,并视其重要程度分别撰写时代背景、内容提要和写作经过。译作和部分作品及鲁迅自拟的图书广告等,则仅存目。凡有确实年月可考的作品,均按著译日期列目;著译日期无法考订的则按发表时间列目。
年谱所引资料,随文注明出处,首次引用标出作者、书名或篇名、刊行时间、出版社或报刊名称,以后只列作者和书名篇名。
与上述诸谱不同,本谱直接按年叙事,不再划分时期和阶段,省却了每一阶段前的概述性文字。对本事,亦不逐项分列,叙述比较集中,编写者注重材料的归纳综合,将引用的史料与编者的述评文字,有机地揉合在一起,行文简洁流畅,读来毫无阻隔。
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年谱》(四卷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至1984年出版,4卷,计130万字。
该年谱较上述诸年谱晚出,自然会汲取各谱编著的经验与教训。年谱的撰写者之一陈漱渝先生有《评三种新编〈鲁迅年谱〉》[14]一文,客观公允实事求是地总结了王观泉本,鲍昌、邱文治本,上海合著本年谱编写的成败得失。在本年谱修订本后,陈漱渝又撰写了《鲁迅年谱》(四卷本)重印后记,对鲁博本年谱编写中的一些问题作了深入的分析说明。从这两篇文章看,至少作为该谱撰写骨干之一的陈漱渝先生,对已公开出版的年谱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对其中的甘苦和经验教训有深切的体会和清醒的认识,对年谱这一历史体裁有着明确的文体意识。这些都不可能不反映在鲁博本《鲁迅年谱》之中。
鲁博本《鲁迅年谱》的主编系已故著名鲁迅研究家李何林先生,其主要撰稿人也都是鲁研界的知名学者。他们拥有得天独厚的研究条件,有明确的文体意识,又借鉴了此前各年谱编写的成功经验,这是修好年谱的基本条件。实际上,该年谱也确实是现有年谱中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体例最严整的一种,堪称鲁迅年谱,也是现代作家年谱的集大成之作。
该年谱之谱文由“时代背景”“本事”“注释”三部分构成,并插入了图片数百帧,可谓图文并茂。书末还附有《鲁迅著译书名篇目索引》《本书注释索引》(含《人物类首字检索表》《书刊类首字检索表》《社团机构类首字检索表》)、《鲁迅笔名表》《鲁迅教学生活一览表》等。《编写说明》12则,除关于年谱编写目的、写作分工情况的交待外,都是对编写体例的说明。
“时代背景”,为了说明鲁迅是在什么情况下或何种历史环境中从事革命工作和创作的,以及他的思想发展变化与客观环境的联系。所选均为与鲁迅直接间接有关的中外大事,置于鲁迅“本事”之前。1881年到1918年的均列于每年之前;1919年以后的,均列于每月之前;与鲁迅生平著作有关的较小背景,则编入“本事”。
“本事”,包括鲁迅生平事迹和全部著作及译文,包括小说、诗歌、戏剧、论文、杂文、散文、散文诗、序跋、前记、后记、启事、广告、案语、辑录校勘的古籍等,一律入谱。书信、日记有选择的入谱;入谱的著作和事件,均按年月日排序;仅知年月,不知日期者入于本月末;无月可据者,考订到季;无法考订到季者,则入于本年末。写作时间不可考者,按发表时间入谱。写作时间见于作品和日记,如不相符者,根据考订后的时间入谱。对入谱的鲁迅著作,一般每篇均写有题解(包括文章写作的背景或针对性、思想内容提要、编者简评以及其它材料)。
“注释”大体可分4种类型:①注明引文出处,提供资料线索。除时代背景和见于鲁迅日记者外,本谱引文和所据资料,均注明出处,为需要进一步了解、学习和研究者,提供资料的来源和线索;②介绍与评价与鲁迅有关的人物、书刊、社团、事件等;③对有分歧有争议的问题的考证,在注释中加按语予以说明;④订正鲁迅本人的误证与疏漏。如鲁迅注错了写作日期的著作或译作,本谱根据发表的原刊、鲁迅书信等有充分说服力的材料,在注释中予以订证。
“图片”,本谱中插入的数百帧图片,不仅起到活跃版面的装饰作用,而且生动形象地展示了许多与谱文密切相关、彼此呼应的珍贵文物,是对谱文内容的补充说明,使本谱显示了与众谱不同的图文并茂的特色。
鲁博本《鲁迅年谱》兼众谱之长而又有较大的超越。作为一种历史体裁的年谱,其生命的支柱,乃是史料的完备与可靠。恰恰在这一点上,本年谱的编者们不仅拥有博物馆本身所藏的丰富资料,而且他们自觉地在史料的广事搜集上“下了相当的功夫,即不仅认真阅读了鲁迅本人的著译、日记、书信等第一手文字资料,还参证了鲁迅保存的聘书、剪报、来函、契约等有关文物,此外,又查阅了大量当时的报刊和鲁迅同时代人的日记、回忆录等”[15]。他们集众人之力,以本馆及全国各地的收藏为依据,锐意穷搜,竭泽而渔,又精心考证,遂使年谱资料的丰富性与可靠性,达到难以超越的地步,使该年谱成为学习和研究鲁迅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
就文献类型而言,鲁博本《鲁迅年谱》的出现,是中国现代文学作家年谱这一文体成熟的标志。在编写体例方面,作者们从充分展现谱主生平事业,使年谱充分发挥其文体优势,为读者提供进一步学习研究鲁迅的门径等目的出发,深入思考,反复研究,进行了细密周详的设计安排,虽不能说已臻尽善尽美,但也足以成为这方面的典范之作了。
除《鲁迅年谱》之外,其他现代作家年谱的编纂出版情况尚无法精确统计。其中作为著作附录的年谱,仅收入上述《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乙种)“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中的就有百余种(列入编写计划的作家170多位)。按照该丛书的编辑体例,每位作家的研究资料中,于《传略》之后均有该作家的生平和文学活动大事记,如《茅盾研究资料》中有《茅盾的生平和文学活动大事记》。有的称为《××生平文学活动年表》,如《王鲁彦研究资料》中的“大事记”便称为《王鲁彦生平和文学活动年表》。有的称为年谱,如《郭沫若研究资料》中的《郭沫若年谱简编》。这些现代作家的年谱简编,都是由对该作家有全面深入研究的专家学者,在编选了“作家研究资料”之后编纂的,故其史料丰富可靠,叙述准确精当。这样,可以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的作家,都已经有了自己的年谱。
单行本的现代作家年谱,目前出版的已经很多。观其体式,与《鲁迅年谱》的编法,极为相近。其中规模较大的有龚济民 方仁念所编《郭沫若年谱》。该谱分上下册,总计约90万字,于1982年5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其责任编辑李福田先生亦是鲍昌 邱文治《鲁迅年谱》的责编。两部年谱,在编辑体例上大体相近。在出版的当时,该年谱大概也是由个人编纂的郭沫若年谱中篇幅最大的。两位编者历时三年,精心结撰,在作家年谱的编写上有心得,有创建。现将其《例言》照录如下,以见其编辑体例。
例言
一、郭沫若是继鲁迅之后,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是全国人民,特别是科学文化教育工作者和广大知识分子学习的榜样。为了给学习和研究郭沫若生平、思想、著译和战斗业绩的同志提供方便,我们尝试着编写了这部年谱。
二、本谱以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对郭沫若所作的评价为指导思想,力求真实、准确、系统地反映这位杰出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一生在文学、艺术、哲学、历史学、古文字学以及政治活动等各方面所作的努力和所取得的主要成就。考虑到郭沫若一生的实际情况,对他的文学艺术活动力求记述得更全面、更系统,以公同好。
三、本谱力图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强调从实际出发,审慎地引用资料,只作忠实的历史纪录,概不评述。对于一些目前尚有争议的问题,经考证、辨析后,就择定的一种选材,其余则不作介绍。
四、本谱正文叙述谱主本事,后面用异体字附录国内外大事、文化界动态以及有关人物往来情况。如背景材料与本事关系密不可分,则结合本事写入正文。本事一般按年月日次序编列,无日可考者系月,无月可考者系季,无季可考者系年。本事日期和书刊卷(期)数均用汉字标记,括号内注释中的有关数字,以及背景材料中的有关数字,则一律用阿拉伯字标记,以示区别。对谱主著译活动所注出处,如系当年当月,则年月从略。著译揭载的报刊,解放前的均标明地点和日期,解放后的一般只写期(卷)数,个别易混淆的则加注地点。
五、本谱将至今能见到的郭沫若著译全部列目。著作部分,择其要者撰写内容提要、写作经过和发表后的影响,较重要者则略述主要内容,一般文章则仅存目;译作部分,择取从中能窥见译者思想变迁的篇目作简要介绍,一般也仅存目。叙列按著译日期编排,著译日期无法考订者,则按发表日期编排。
六、本谱记事尽可能简括、明了。对延续较长时间的同一事件,有时采取相对集中的叙述法;对改题、改写或改译而重新发表的文章,则置于原先著译或发表时所列条目内一并叙述;对遍及国内外给单位或个人的题字,酌择其要者入谱。著译结集出版只列初版,再版一般从略;收入的集子以《文集》为主,如前后所收的集子名称相同,则不再提初收的集子。
七、本谱所引郭沫若著译,主要系根据《沫若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简称《文集》)、《沫若译诗集》(上海建文书店一九四七年版,简称《译诗集》)、《沫若书信集》(上海泰东书局一九三三年版,简称《书信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上海联合书店一九三0年版)、《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上海大东书局一九三一年版)、《金文丛考》(日本东京文求堂书店一九三二年版)、《新华颂》(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百花齐放》(人民日报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长春集》(人民日报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潮汐集》(作家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东风集》 (作家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蜀道奇》(重庆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邕漓行》(广西僮族自治区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五年版)、《沫若诗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七年版,简称《诗词选》)、《东风第一枝》(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郭沫若少年诗稿》(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简称《少年诗稿》)等。引用未收集的文章,一般以原刊报章杂志或书籍为准。
八、本谱所引资料均注明出处。首次引用时,详细标明作者、篇名(或书名)、发表时间及刊物名称(或出版单位名称),重复引用时,只列作者和篇名(或书名)。
《例言》涉及新文学作家年谱编写中的诸多问题,以及处理这些问题的原则、方法,具有普遍意义。全文照录,以资参考。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自撰自订较为完整的年谱者不多。周作人自订《知堂年谱大要》(载香港《南北极》第56期,1975年1月)算是一个特例。该年谱写于1964年7月15日,记载谱主从1885 年1月16日出生至1949年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生平事迹。在民国三十八年己丑(1949年)下,作者仅以数行文字概述建国后至撰写该谱之前的活动:
旧历除夕出狱,即往上海,寄住尤君处。八月归北京。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改用公元。
解放以后唯在家译书,别无所事,故私人行动无所可记。至所译书则大抵可分为古希腊文及日本的古典文学两部,大旨已详著译目录中。
周作人喜为和平冲淡之文,其年谱写作亦平实简要,不露声色,仿佛在记述着他人的事情。试看他写自己附逆前后的文字:
二十八年己卯
元旦狙击不死(因子弹为骨扣所阻)。沈扬在座重伤,前车夫一死一伤,犯人终未弋获。当系日人所为。八月任伪北京大学文学院长。
三十年辛巳一月
任伪华北政务会督办,四月往东京,出席东亚文化协议会文学部会,旋即回京。
三十三年一月
督办辞职。
三十四年十二月
为国民党逮捕入狱,居于炮局胡同。
三十五年丙戌五月
移居于南京老虎桥监狱,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其中唯“元旦狙击不死”一则,似在为附逆辩解,但也是事实的客观记述。此外,对这一于他至关重要的经历,既无忏悔,也无辩白。
《知堂年谱大要》附有周作人写于1964年7 月3日的《解放后译著书目》和一份《补遗》。
周作人在抗日战争时期变节附逆,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文化史和思想史上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巨大存在。对于这一复杂的历史人物,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从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对他的研究陷于停顿状态。直到80年代,才重新复苏并取得较大进展。这一阶段,在周作人研究,特别是在史料搜集和文献整理方面做出重要贡献的,是南开大学张菊香、张铁荣先生。他们在完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乙种)》《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中的《周作人研究资料》编写的基础上,编写了《周作人年谱》(1985年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该年谱资料丰富翔实,体例严整,它的编辑出版,打破了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禁区。事隔十几年后,为了吸收新的研究成果,利用学术界发掘的新史料,他们对旧作进行修订,增补了20余万字,于2000年4月在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新版《周作人年谱》。
年谱对周作人生平事迹及其著作翻译、校订的古籍、校阅的译文,一律记载。所写挽联、按语、书信、日记有选择的加以记载。对周作人著作,包括译文的序跋、附记、书信中,能说明其政治见解、思想状况、文艺主张、创作观念者,多作了概要的介绍。对于谱主所经历的重要事件,亦征引史料进行详细的说明。年谱所引用的文字资料,皆注明出处。书前有张中行先生作《序》,对年谱的编写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作者很好地解决了搜集资料、选择取舍、编写体例等方面的困难,让人不仅能从中“看到周作人的清晰影像”,“还能看到不少其时文化界高层人士的活动情况”。
参考文献 :
[1]鲁迅.三闲集·鲁迅译著书目[A].鲁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版社,1981.
[2]王观泉编.鲁迅美术系年[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79.
[3]秦川编.鲁迅出版系年[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
[4]冯光廉,朱德发等.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程[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
[5]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6]周启祥,谢励武.鲁迅家族世系表[J].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研究资料, 1982,(10).
[7]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8]鲁迅.且介亭杂文·序言[A].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版社,1981.
[9]王观泉.鲁迅年谱[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
[10]鲍昌,邱文治.鲁迅年谱[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1980.
[11]蒙树宏.鲁迅年谱稿[M].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1987.
[12]复旦大学,上海师大,上海师院合编.鲁迅年谱[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79.
[13]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年谱[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984.
[14]陈漱渝.《评三种新编〈鲁迅年谱〉》[A].鲁迅史实新探(修订本)[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15]陈漱渝.《鲁迅年谱》(四卷本)再版后记[J].鲁迅研究月刊,2000,(9).
责任编辑:冯济平
Writers' Chronicle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XU Peng-xu
(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Qingdao 266071, China )
Abstract:Tables, chronicles and biographies are generally used in studying the live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writers, and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genre in this fi eld. The chronological table is mainly adopted for listing the writers' activities, publications, translations and literary events. In summary, there is no strict difference between tables and chronicles in studies of document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Key words: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writer; philology; chronological table; chronicle
作者简介:徐鹏绪(1945- ),男,山东胶南人,青岛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批准号:02BZW046)部分成果。
收稿日期:2015-03-22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15)06-003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