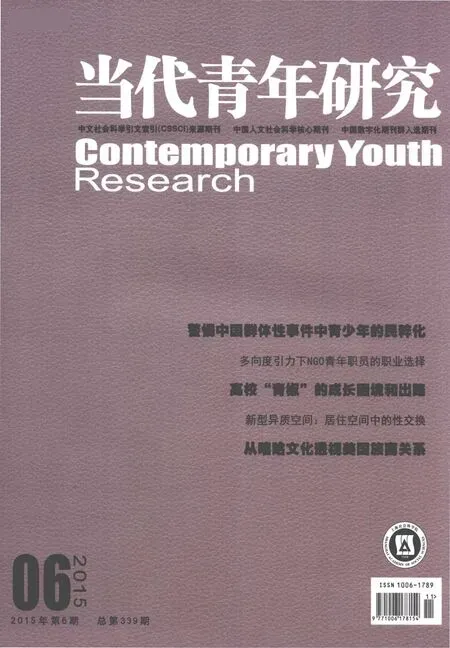警惕中国群体性事件中青少年的民粹化
谭 毅
(四川省团校共青团理论研究中心)
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而转型期群体性事件增多,其社会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群体性事件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了社会压力,是社会矛盾的解毒剂;另一方面,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给社会治理和公共管理带来了挑战。当前,国内的民粹主义思潮开始抬头,已有学者呼吁警惕下层民粹化[1]。正确认识群体性事件体现出来的民粹化因素对我国依法实施社会管理,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同时,遏制民粹化特别是青少年的民粹化也是我国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必然要求。
一、群体性事件与民粹主义天然亲近
群体性事件是指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由一定人数参加(一般是5 人以上)、通过没有法定依据的行为(如集体上访、阻塞交通、围堵党政机关、静坐请愿、集体散步、聚众闹事等)对社会秩序和政府管制产生一定影响的事件。[2]民粹主义是一种将“人民”视为铁板一块的统一体[3],主张平民至上而仇视精英、主张直接民主而拒斥代议制的一种社会思潮、一种政治运动或一种政治策略。[4]民粹主义是一种寄生性的思潮,基本上它可以和任何意识形态结合,作为一种外表“涂层”粉饰其他意识形态。与此相应的是,民粹因素也广泛存在于各类事件之中。例如,2012 年,哈尔滨一名青年因自认就医时被刁难而持刀砍死一名哈尔滨医科大学研究生。腾讯网对此事进行了调查,有65%的投票网友对此表示“高兴”,这一结果较选择“愤怒”、“难过”、“同情”大幅领先。[5]当然,民粹也存在于群体性事件之中,甚至可以说群体性事件与民粹主义天然亲近。民粹主义崇尚一种直接民主的原教旨主义,直接将让渡给政权的权利回收并兑现使用,这与群体性事件中不顾后果而要求诉求马上实现并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情形相通。在2008 年家乐福事件①本文所有事件的资料分别来源于新华网、网易网、中新网、凤凰网、《瞭望》、《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新京报》、《凤凰周刊》、《北京青年报》等主流媒体的报道,经反复对比甄别得出事件相关情况,以下不再重复说明。中,民众不推举代表与家乐福方面谈判,直接打砸商场,就是一个群体性事件与民粹主义相伴的例子。从理论上说来,当代中国的群体性事件与民粹主义天然亲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相似的社会背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贫富差距、群体无意识、政府公信力不足、少数精英得理不饶人、媒体缺乏责任感的舆论误导等。社会学家赵鼎新认识到从社会变迁到群体性事件发生之间一些机制的重要性,特别是目前中国缺乏制度化社会矛盾的能力。[6]概括起来讲,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主要在于社会转型这一大的社会背景,以及由此引发的这一时期利益格局的重组,社会公正缺失,官员腐败,社会控制机制弱化等方面的问题。[7]而“产生民粹主义的直接原因通常是社会的不公正,政治的腐败,政府的无能,特别是公民对政府的失望”。[8]由此可见,群体性事件与民粹主义产生的社会背景及原因是高度相似甚至是相同的,而这些原因也成为两者在一定时期内杂糅共存的养料来源。
相似的阶层基础。现实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往往也在利益表达上处于弱势。群体性事件在本质上是弱势社会群体在体制内表达渠道不畅和表达效果欠佳的情况下,通过体制外的方式来表达利益和实现诉求的群体行为。也就是说,群体性事件是一种“弱者的武器”。[9]而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巨大的利益调整,导致贫富差距过大、制度性腐败、基本公共服务不完善等问题,从而使得我国社会阶层出现高度分化,形成了上层与底层的割裂或对立。社会底层上升通道较为狭窄,甚至形成加速的阶层固化趋势。[10]民粹主义始终秉持底层人民或草根的立场。底层社会的失望是制造民粹情绪的催化剂。[11]由此可见,群体性事件和民粹主义都具有高度重合的社会基层基础,那就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
相似的简单逻辑。无论是以为“法不责众”的群体性事件还是以为“多数普通人民掌握着真理”的民粹主义,其背后的逻辑都是简单而相同的: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众怒难犯,人多势众者拥有真理。这种人的数量决定真理归宿的论调是一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反智主义逻辑。
相似的非程序主义。群体性事件是一种不经过现行体制设定的合法程序而解决自身利益困局的抗争方式,它通过体制外方式的聚集来对整个体制及其象征或代表施压。民粹主义的一大特征就是要求实行直接民主,靠民众直接决策乃至直接实行惩罚,绕过现行体制和制度所规定的合法程序。这种抽空中间程序直接由普通人民与政权代表面对面博弈的非程序主义是群体性事件与民粹主义本质趋同的表现。
相似的非理性狂暴。这一点与两者的非程序主义密切相关,程序被虚悬搁置的地方,理性往往也就自然隐退。在群体中,即使头脑最冷静的个人也会失去自我。勒庞以他天生的敏锐感分析到:“孤立的他可能是个有教养的个人,但在群体中他却变成了野蛮人——一个行为受本能支配的动物。他表现得身不由己。残暴而狂热……”[12]群情激愤本就是非理性的体现,许多群体性事件,特别是其中“无直接利益相关”的社会泄愤事件,都伴有非法的打砸抢烧等非理性行为。其中,许多与事件毫无关系的参与者表现出惊人的从众行为,并在群体性事件中失掉了日常习得的社会规范,成为群氓中无差别的一员。与此类似,民粹主义往往狂暴无常,以人数的多寡作为是非对错之标准,以所谓人民之众取胜,形成多数暴政的非理性。
相似的组织性不足。如果说群体维权事件还是具备一定组织性的话,那么社会泄愤事件则很缺乏甚至可以说没有组织性。社会泄愤事件的绝大多数参与者是路见不平或借题发挥,表达对社会不公的不满,以发泄为主,[13]背后并无所谓领导或操纵。很多民粹主义的行为或情绪没有组织性,如果说一些为精英所操纵的民粹主义运动在初期还具有一定组织性的话,那么其后期往往会因为失控而变得混乱。而在网络时代,网络民粹主义就更多地呈现出自发形成的集体喧嚣,没有明确的组织性。
群体性事件与民粹主义天然亲近,两者具有相似的社会背景、阶层基础、简单逻辑、非程序主义、非理性狂暴、组织性不足。这些相似性正是中国群体性事件中民粹因素涌动的逻辑基础和学理根基。
二、中国群体性事件的民粹化特征
作为群体性事件与民粹因素天然亲近的现实例证,中国群体性事件中民粹因素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或散落在某几个群体性事件中,或是多数群体性事件中共有的现象,均体现了民粹主义的某些做派和特征。
第一,要求正义立马兑现。群体性事件的非程序性本身就使其具有一蹴而就实现诉求的民粹性质。在许多群体性事件的现场,我们也发现了很多拒绝走程序,要求正义立即兑现的证据。如在2005 年,陕西西安一群围观人员殴打已被抓住的小偷,警察到场后打算将其带回审问,围观人员以为警察此举是要包庇小偷,不让警察带走小偷。与此类似,2013 年,广西南宁因交通事故引发群体性滋事事件,现场民警准备将肇事一方陈某带离调查并扣押无号牌车辆时,遭到现场滋事人员阻挠,部分人员甚至情绪失控,漫骂民警并围打陈某。这正是民粹主义以空泛的平等、公正等概念为号召,缺乏程序意识,枉顾程序正义,甚至拒绝等待、企图不经审批而动用群体暴力来快速兑现正义的体现。
第二,要求诉求直达天听。在许多群体性事件中,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要求直接与高层或主要领导见面以求解利益困境,主要领导不出面则誓不罢休。例如,2008 年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是在当时的主要领导亲自出面之后事情方告解决。2010 年,辽宁省庄河市上演千人政府门前下跪求见市长的一幕,市长拒绝现身而后被免。而事实上,在不少群体性事件中,不是不存在解决问题的制度化渠道,而是因为一些原因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不去走正规的渠道,形成了一种先哲老子所谓“大道甚夷,而人好径”的奇特现象。这种“抄近道”、“走捷径”的心理是民粹主义要求直接民主的一个现实变种。这种“有现成路不走却要生僻新路”的现象值得引起重视。
第三,极端仇视精英。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以穷人和弱者等于是精英对立面的角色自居,仇官仇富,反讽知识分子,极具民粹色彩。在2004 年的重庆万州事件中,打人者胡权宗谎称自己是公务员,出了事可花钱摆平。此举引发围观群众公愤,最终导致打砸政府财产的激烈举动。在同年的哈尔滨宝马车撞人事件中大量人群围观,宝马横行则被符号化为权力和金钱横行,整个事件也被认为是为富不仁的体现。肇事者则被谣传为副省长的儿媳,与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有关系(均被证明不实),这些都是仇官的民粹主义表现。在2012 年什邡事件中,出现了“打倒李成金,收了刘沧龙”的标语,前者为官,后者为富,这一标语是群体性事件中仇官仇富的民粹主义成分的鲜明体现。
第四,攻击体制象征物。群体性事件本来就是一种体制外的抗争和表达行为,其中出现的反体制行为与体现了民粹主义对现行体制不合作甚至敌对不谋而合,行为指向一般是市县级党政的办公场所、领导和处理群体性事件的警察。2012 年“启东反对王子纸业排污事件”中,民众扒光市委书记的上衣,强行给市长套上抵制王子造纸的宣传衣。警察经常出现在群体性事件处理的第一线,但是群体性事件让警察形象“很受伤”,在很大程度上,警察成了民众情绪的发泄口。[14]在2009 年的湖北石首事件中,围观群众中的少数人借机煽动群众袭击维持秩序的公安民警和前来灭火的消防战士。
第五,自恃道德高尚。民粹主义认为广大普通人民的道德淳朴和高尚,而少数精英则是道德败坏和腐化堕落的伦理渣滓。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自恃道德高尚的一个表现是喜欢寻找甚至编造精英们道德赤字的证据,以此对精英展开大肆的道德攻讦,企图以精英的道德丑态搞臭他们。上文述及的启东事件中,谣传从市长办公室搜出了避孕套就是企图用道德工具搞臭精英的民粹行为。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自恃道德高尚的另一个表现是制造一种自身道德高尚却在现实社会中受到不道德欺凌的弱者舆论,激起社会的道德义愤。2006 年浙江瑞安女教师戴海静跳楼身亡,有人怀疑这“几乎完美的女人”是被其夫家谋害而死。
第六,非理性的打砸抢烧。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有时陷入群体狂热之中,崇尚民粹主义那种底层、直接裁决的正义性,对于不满的对象疾恶如仇,追求古代江湖豪客那种“手刃强敌”的快感,这种情形成为民粹所谓人民直接统治的局部翻版。在以云南孟连事件,2009 年湖北石首事件,2012 年江苏启东事件等著名事件为代表的诸多群体性事件中无一例外都出现了非理性的非法打砸抢烧行为。
随着群体性事件的发展,我们对群体性事件的认识更加全面客观,应对更加及时有效。然而,群体性事件还在不断地出现,甚至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其体现的民粹因素需要警惕。
三、青少年是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参与主体
青少年的年龄阶段特征与社会背景结合导致其成为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参与者。青年群体因其对信息掌握能力比较强,权利意识较强,成为群体性事件的一大参与主体。[15]
在现实生活中,青少年是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参与者。而在媒体关注更多的台湾“太阳花运动”和香港“占中”等群体性事件中,青年更是走向街头,包围权力机构、阻塞交通,成为街头政治、民粹政治的主力军。青年工人集体维权抗争也是青年参与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形式。根据相关研究,青年产业工人社会抗争的主体多是“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而其抗争也已经从日常反抗发展到有组织的群体抗争,形式已经包含有群体怠工、罢工和游行等群体抗争行为[16],并已经形成了几种集体抗争的模式[17]。
青少年是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主力军。30 岁以下年龄段的网民长期占据我国网民总量的半数以上,18岁以下网民的数量在稳步发展,其在青少年网民在总量中的比重从最初的2%左右发展到目前的超过网民总量的20%,比重增加了10 余倍。[18]由此,有研究者得出结论称,30 岁以下青年群体是我国网络传播的主要参与者。在青年网民的行为结构方面,调查显示,10—29 岁的年轻人相对于其他群体更乐于在互联网上分享,尤其是10—19 岁的人群,有65.9%的网民表示比较愿意或非常愿意在网上分享[19]。与其他群体相比,青少年群体的网络舆论表达意愿更强烈,尤其是 10—19 岁网民网上发言积极性最高,占比50.2%;其次是20—29 岁的网民群体,占比46.6%[20]。青年网民的行为结构表明其更易于参与网络群体性事件。
四、警惕群体性事件中青少年的民粹化
当前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多,其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如地域扩大、情绪宣泄增多、暴力性更强、隐蔽性加强。民粹主义在群体性事件中有愈发壮大的趋势,群体性事件在青少年化现象,要在青少年中顺利推行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就必须警惕群体性事件中青少年的民粹化。
(一)警惕群体性事件中青少年学生的民粹化
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实现社会化对于国家政权延续和社会和谐稳定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然而,我国部分青少年却在群体性事件中沾染上了民粹主义习气,应当引起重视。一方面是学生群体性事件较多,其中体现出许多民粹化行为。2004 年,西部某大学后勤集团员工酒驾撞伤一名学生后试图逃逸被学生截下,聚集的学生将肇事车砸烂;2006 年6 月下旬,郑州大学升达经贸管理学院的数千名学生不满学历证书上“二级学院”的字样,要求得到一张校方招生时承诺的大学本部文凭,发起游行示威并伴有打砸行为。2010 年,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学院倒闭,1600 多名学生因为无法取得文凭而维权;同年,九江学院学生集体拒绝搬出将留给361 度公司培训员工住宿的宿舍楼;2011 年,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定向培养项目涉嫌招生虚假宣传,导致数百名非计划内招生学生为索文凭而集体上访;2013 年,南京工业大学上万名学生集体抗议学校断电没空调,学生们边喊口号边从楼上往下扔酒瓶、暖瓶等物品;2013 年9 月,河南省商丘市柘城县二高学生打砸学校,抗议学校封校制度以及校内食堂、超市出售高价食品。上千名学生从学校东大门开始,依次将食堂、超市、教室、西门、寝室设施砸毁,并围殴了学校一名主任。2013 年11 月,河北廊坊东方职业技术学院的数百名学生因不满校园管理及食堂高菜价而聚集抗议。在这些事件中,学生多数时候起于维权,终于打砸,表现出许多民粹主义特征。另一方面是部分非校园群体性事件中有学生的身影。在2012 年发生的四川什邡反对钼铜项目事件中,什邡和广汉等地有相当数量的中学生走上街头反对钼铜项目上马,部分学生在事件中受伤。
以上仅是笔者所知的部分青少年学生深度卷入的群体性事件,其他未知未被报道出来的类似事件未可计数。在这些事件中,青少年以聚众闹事、集体上访甚至打砸等方式成了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力量,其起因大多与整个社会转型大环境和学生的权益受损有关,但其中表现出来的挟人众以闹事、拒绝程序而直接要求校领导出面以达权益诉求、游走在违纪违法边缘的群体泄愤等民粹化因素对于青少年政治社会正常化进程的负面影响值得引起高度警惕。
(二)警惕群体性事件中青年知识分子的民粹化
知识分子是文明的重要传承者,也是创新的智力来源,其思想状况和政治立场关系着国家兴旺发达、政权和社会的稳定性。青年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中思想最为活跃的子群体,对于社会目前和未来的思想动向具有难以忽略的影响力。然而,作为知识、思想与激情的掌握者,我国的部分青年知识分子却出现了民粹化的倾向,这在群体性事件中也有所体现。
知识分子这一身份决定了青年知识分子的民粹化。“知识分子具有民粹主义的倾向,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世界性现象。”[21]美国政治学家马丁·李普塞特认为:“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倾向于拥护民粹主义,因为他们既同现有的权力等级体系缺乏联系,又对之不满,他们唯一的力量源泉在于人民。同时,他们的民粹主义也派生于他们对更发达国家所持的一种矛盾心理……对民粹主义的崇拜产生了一种信念,即‘相信普通民众的创造力和巨大的道德价值’”。[22]例如,在2012 年的9 ·18 反日游行中,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韩德强对一位老人大打出手,引起舆论哗然。于建嵘教授的研究也证实了,在湘南农村的农民维权行动、厦门抵制PX 项目的环保运动、上海市民抗议磁悬浮的散步行动中,知识分子与民众(包括底层)并非对抗关系,而是有着合作的可能与实践。[23]
随着我国对外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青年知识分子接触各类思潮的途径更多,超前思维、独立思考的能力更强,更容易离经叛道,在群体性事件中滑向民粹主义的渊薮之中。如北京某高校的青年教师利用高校讲台煽动进行群体暴恐行动,某知名的知识分子搞对“什邡事件”的现场调查,某名人在什邡事件之后写了题为《什邡的释放》之博文等。此外,中国高校部分文科青年知识分子、因失业等原因身处社会底层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因为经济状况不佳,在反日游行等群体性事件中走向民粹,也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三)警惕群体性事件青年叙事话语的民粹化
国家主流价值和主流舆论建构是实现国家政治整合的必然要求。然而,目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叙事话语却体现出一些民粹化的特征,这对于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官方话语的传播和主流舆论的构建十分不利,是我国进行有效的政治传播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群体性事件叙事话语的民粹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官方对群体性事件定性用语的民粹化,动辄称群体性事件“有组织、有预谋”,称事件的参与者为“不明真相的群众”,认为其受到“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或“黑恶势力”之煽动。这些用语将群体性事件视为暴动,将参与者视为民粹意义上的暴民。二是网络加剧了群体性事件参与者叙事话语的民粹化。如果说现实社会中群体性事件有大量民粹因素,那么以“众声喧哗”进行利益表达和群体抗争的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的民粹主义更甚。其中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有谣言、人肉搜索、语言暴力等。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是,专家、教授被称为“砖家”、“叫兽”。有的群体性事件甚至从现实蔓延到网络,形成了网上网下交互影响,民粹主义在其中大行其道。
官方和群体性事件参与者双方叙事话语的民粹化,导致了官方与民间两个“舆论场”的话语割裂和立场对垒。有传播学研究就指出,“官方与民间、体制内与体制外的舆论场从议题设置到表达方式都存在明显差距,尤其是在群体性事件的传播中,存在各说各话、沟通不畅、情绪对立的现象,突出表现为网络民意对官方话语的不信任、不理解、不认同”。[24]这种现象是我国舆论引导亟待解决的问题。
青年是社会流行语最频繁的创造者、使用者和传播者,青年亚文化也是非主流民粹话语的温床。青年对于群体性事件中这些叙事话语的民粹化功不可没,甚至大多数时候是创造、运用这些话语的急先锋,而群体性事件则是青年运用这些民粹话语最为集中、最频繁的场合。从长远来讲,这对于构建公民与政权、亚文化与主流文化、多元思想与主流价值观等之间的相互对话十分不利。
[1]孙立平. 警惕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EB/OL].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ggzhc/article_2011071739755.htm,2013-10-11.
[2]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课题组. 我国转型期群体性突发事件的主要特点、原因及政府对策研究[J]. 中国行政管理,2002(5):6-10.于建嵘. 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类型及其基本特征[J].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9(6):110-115.
[3]保罗•塔格特. 民粹主义[M]. 袁明旭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125.
[4] 俞可平. 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J]. 战略与管理,1997(1):83-89.
[5] 李良荣、徐晓东. 互联网与民粹主义流行——新传播革命系列研究之三[J]. 现代传播,2012(5):26-30.
[6] 赵鼎新.中国冲突性政治的民粹化倾向[J]. 文化纵横,2010(4):32-37.
[7] 吴佩芬、王国明. 近几年学术界关于群体性事件的研究综述[J].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9(5):40-46.
[8] 俞可平. 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J]. 战略与管理,1997(1):89-94.
[9] 张振华. “弱者的武器”:群体性事件的政治解读[J]. 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2(4):41-45.
[10] 中国新闻网. 中国社会阶层固化趋势加速 纵向流动通道渐狭窄[EB/OL].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1/06-27/3138497.shtml,2013-12-17.
[11] 陈尧. 网络民粹主义的躁动:从虚拟聚集到社会运动[J]. 学术月刊,2011(6):26-32.
[12]古斯塔夫•勒庞.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49.
[13] 于建嵘. 中国的社会泄愤事件与管治困境[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1):5-11.
[14]搜狐网. 群体性事件让警察形象“很受伤”[EB/OL]. http://news.sohu.com/s2012/dianji-949/,2013-12-18.
[15] 张明军、陈朋. 2011 年中国社会典型群体性事件分析报告[J]. 中国社会公共安全研究报告,2012(1):12-16.
[16] 刘程. “世界工厂”与青年产业工人的利益抗争[J]. 当代青年研究,2013(4):30-35.
[17] 汪建华、孟泉. 新生代农民工的集体抗争模式——从生产政治到生活政治[J]. 开放时代,2013.(1):165-177.
[19][20]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第35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502/P020150203548852631921.pdf,2015-05-14.
[18] 唐斌、赵国洪. 我国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主体特征及其影响分析[J]. 情报杂志,2012(5):47-52.
[21] 顾昕. 五四激进思潮中的民粹主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J]. 当代中国研究,1999(2):22-27.
[22] S. M. Lipset. The First New Nation[M]. Garden City:Anchor Books,1967:77-78.
[23] 唐小兵. 底层与知识分子的民粹主义[J]. 南风窗,2008(3):86-89.
[24] 岳璐、蒋超. 反思群体性事件中的网络民意[EB/OL]. http://qnjz.dzwww.com/lfjc/201301/t20130109_7894332.htm,2013-01-09/2013-1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