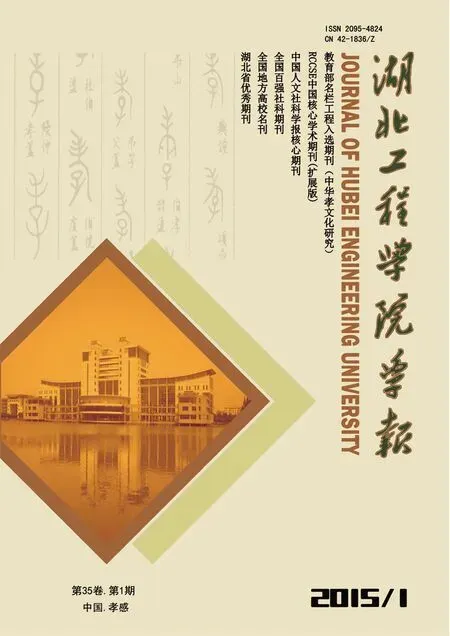法孝之变
——略论秦汉之际的政治伦理范式及其转换
王传林
(北京师范大学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北京 100875 )
主持人语:
法孝之变
——略论秦汉之际的政治伦理范式及其转换
王传林
(北京师范大学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北京 100875 )
纵观历史,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政治哲学与伦理范式。如果说短暂的秦朝(秦始皇统一六国至秦亡)是以法家的“法”为其政治哲学与伦理范式的,那么西汉初期则可以用“孝”来概括其政治哲学与伦理范式。秦亡汉兴,政权更迭,秦与汉在政治哲学与伦理范式方面不仅悄然发生了转换,而且形成了各自不同的伦理范式与价值向度。在西汉初期的历史进程中,“孝”的强化与“法”的弱化可谓是相逆而行;时至汉武帝时期,法孝之间又有新变化,呈现出同行并进、互为表里的特征。值得一提的是,董仲舒以“父为子纲”的论调对“孝”进行进一步的理论化与机制化,不仅拓展了“孝”的伦理意涵,而且增强了“孝”的绝对性与权威性。
秦汉之际;法;孝;政治伦理;伦理范式
通常大多数学者将秦朝与西汉更迭之际概称为秦汉之际,但是从政治哲学与伦理范式的更迭过程来看,秦汉之际的时间跨度则可以延展至西汉中期即汉武帝时期,即自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87年,前后跨度约130多年。从秦始皇统一六国至秦灭亡(公元前221年~前202年),由于时间相对较短,不少学者对秦时的伦理思想多语焉不详,即便论及秦汉,多是以汉为主,偶涉秦代,或者一笔带秦,直言两汉。细究之,其实秦朝的政治伦理思想不仅极具鲜明的时代特色,而且与西汉时期的政治伦理思想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对比与反差。秦时尚法,严刑于民;始皇“焚书”,且又“坑儒”;西汉伊始,刘邦虽曾戏儒简学,但很快他便意识到了儒学之政治统治的重要性,于是便有了叔孙通制朝仪与陆贾作《新语》。较之,法家之于秦与儒家之于汉,二者在政治伦理思想上有很大区别,而且各自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伦理范式。
循历史之迹,探伦理之变。通过梳理秦朝的政治伦理思想及基本范式并与西汉时期的政治伦理思想及基本范式进行深度比较,本文旨在探寻秦汉时期的政治伦理思想及伦理范式的根本差异及其演变进路。
一、法孝之辨
从法家之于秦与儒家之于汉的维度看,崇尚法家思想的秦朝在政治伦理思想上可以用一个“法”字来概括其基本范式及伦理特性,而崇尚儒家思想的西汉王朝在政治伦理思想上则可以用一个“孝”字来概括其基本范式及伦理特性。从文字学与语义学的角度看,质文代变,字义有衍,本文凡涉“法”与“孝”二字自然亦不例外。下面,首先厘清“法”与“孝”之义,其次略辨“法”与“孝”之别。
1.法、孝略考。何谓法?凡考,“法”之古字为“灋”,“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1]从广义上看,“法”与“范”、“式”属于同义互训,例如《说文解字·竹部》云:“笵:法也”,《说文解字·工部》云:“式:法也”。当然,从特性上看,“法”有强制性、规定性与恒常性等,例如《释名·释典艺》云:“法,逼也。人莫不欲从其志,逼正,使有所限也”[2]215;《尔雅·释诂》云:“法,则,刑,范……常也,柯,宪,刑,范……法也”[3]21-22。从先秦与汉代的文献记载看,“法”与“刑”密切相关,例如《周易·蒙卦》云:“‘利用刑人’,以正法也”[4];《尚书·吕刑》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5]927。复如《管子·心术》云:“杀戮禁诛谓之法”[6];《吕氏春秋·察今》云:“故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度则悖”[7]。又如《盐铁论·诏圣》云:“法者,刑罚也。所以禁强暴也”[8];《大戴礼记·礼察》云:“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9]等。
何谓孝?凡考,“孝”作为传统伦理哲学的一个重要理论范式早在西周时期就已形成。大致来说,孝之义有四:一曰尊祖敬宗;二曰慎终追远;三曰孝养父母;四曰传宗接代。从语义学的角度看,“孝”之义多体现在子女与父母之间的亲情伦理中。据《说文解字·老部》云:“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10];《尔雅·释训》云:“善父母为孝”[3]200;《释名·释言语》云:“孝,好也。爱好父母,如所说好也”[2]110。 又,《诗》云:“工祝致告,徂赉孝孙;苾芬孝祀,神嗜饮食”[11]753,“孝子不匮,永锡尔类”[11]890;《书》云:“以孝烝烝,乂不格奸”[12],“孝养厥父母”[5]677;《管子·形势解》云:“孝者,子妇之高行也”[13]1166等。从儒家伦理哲学看,“孝”作为体现血缘亲情的伦理范式是被极为推崇的,先秦儒家经典中不仅有《论语》多次论及“孝”而且有《孝经》专门论“孝”。
2.法、孝之别。无论在儒家的视野中还是在法家的视野中,“法”与“孝”的内涵与外延都有着明显的区别。具言之,儒家推崇“孝”,却并不否认“法”;相反,法家则过度地倚重“法”,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否定“孝”。细绎之,法、孝之别大致如下:
(1)孝始尊亲,孝发于情。在早期农耕社会中,“孝”观念是基于尊老、尚齿与祖先崇拜的原始而朴素的情感升华而成的,并逐渐成为一种基于血亲关系的伦理规范。面对变动不居的生存状态与自身难以抗拒的自然力量,先民们一方面通过祭祀上苍祈求洪福,另一方面又将求助的目光转向祖先那里,试图通过祭祀打通与祖先的对话通路,在向上苍与祖先表达崇敬与感恩的同时祈求获得他们的庇佑与襄助,进而借助他们的超凡力量去化解内心的恐惧与外在的灾祸。时至春秋,在先秦儒家那里,“孝”观念被进一步理论化、具体化,甚至被置于“为仁之本”的位置。例如孔子曾云:“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14]56;又如孟子云:“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14]307。由是观之,无论是在孔子那里还是在孟子那里,衡量一个人是否有“孝”, 不仅仅看其事奉父母是否能够做到“能养”、“有食”,更重要的是看其能否做到“能敬”与“尊亲”。其实,孔子对“孝”的定义亦有不同的层面,他在回答孟懿子、孟武伯、子游、子夏等人问“孝”时,所答略有区别。例如孟懿子问孝,孔子说:“无违”;孟武伯问孝,孔子说:“父母唯其疾之忧”[14]55。又,子夏问孝,孔子说:“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14]56此外,孔子还从父子之伦的角度论述“孝”,他说:“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14]51概之,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早期先民们所赋予“孝”的朴素情感以及对上苍与祖先的盲从逐渐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孝”观念在家庭伦理关系中的定向化、伦理化与情感化,其中,我们亦可以窥见人们对“孝”观念认识过程的转变——由对上帝、祖先的崇拜与盲信转向对父母的孝养与侍奉。也就是说,在“孝”观念的演进中,呈现出由远到近、由虚到实、由“追远”到“敬亲”的转向与落实。进一步讲,无论是“敬天”还是“追远”,无论是“追孝”还是“尊亲”,“孝”都需要落实到“情”的层面上,尤其是血缘亲情伦理关系中,孝始于事亲,孝发于情,孝显于行。当然,这里的“情”,是人之天性的自然呈现,而非后汉时的“举孝廉、父别居”之“伪情”。
(2)法内无亲,法内无情。从历史之维看,言“法”,必言韩非。战国晚期,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沿着其师荀子的“性恶论”走向了极端,由于韩非十分强调人性之恶,否定人性之善、人伦之孝以及亲情伦理的合法性,导致其伦理哲学过度地倚重于“法”。在韩非看来,“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15]477;“孝子爱亲,百数之一也。今以为身处危而人尚可战,是以百族之子于上皆若孝子之爱亲也,是行人之诬也”[15]367。他甚至质疑“修孝”,他说:“修孝寡欲如曾、史,曾、史不战攻,则国何利焉?”[15]439他认为:“不为人主之孝,而慕匹夫之孝,不顾社稷之利,而听主母之令,女子用国,刑余用事者,可亡也。”[15]118凡此可见,韩非对儒家所宣扬的“孝亲”与“父子之情”的否定与批判。也就是说,在韩非眼中,“天下皆以孝悌忠顺之道为是也,而莫知察孝悌忠顺之道而审行之,是以天下乱”[15]505。进而,他提出:“上法而不上贤”[15]506。此外,韩非也承认“法通乎人情,关乎治理”[15]520,但是他过度放大“法”的作用,则导致了“法”对“人伦之情”的淹没。他甚至认为:“法重者得人情,禁轻者失事实”[15]519,“法败而政乱”[15]374,并且极力鼓吹“法不阿贵”[15]41、“以法为本”[15]135、“以法为教”[15]482、“法立而诛必”[15]239等。由上可见,在法与亲情伦理之间,韩非是否定儒家主张的亲情伦理的,因此他极力主张以法为本、以法为教。尽管韩非的伦理思想走向了与儒家不同的另一个向度,但其却适应了时代与政治的需求。正因如此,在秦始皇的推崇下,韩非的政治哲学不仅登上了秦朝的政治舞台而且成为那时政治哲学的基本底色。
综上,通过考察“法”与“孝”之本义与衍义,我们发现先秦儒家与法家对“法”与“孝”的理解与定义不尽相同,他们的理论前提与理论旨趣亦有区别。在某种程度上,“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15]406,是“公义”,对“我”有“他律”的强制力;“孝,德之本也”[16]2,是“私义”或“私情”,对“我”有“自律”的约束力。相对而言,“法”出于官方,“孝”出于个人;于“公义”而言,不应有“私义”或“私情”;于“私义”或“私情”而言,也不可放大为“公义”。也就是说,道德之所以为道德是出于真情的自然流露,而非邀誉于人。概之,“法”淹没人性、人情与人伦,“孝”彰显人性、人情与人伦。因此,我们认为:儒家的“孝”与法家的“法”在理论旨归与价值向度上存在一定的悖反。
二、法孝之变
法家的重法思想之所以能被秦朝所接受,概因其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满足了秦朝急于统一六国的功利性政治目的。然而,严刑峻法与暴力政治却没能帮助秦始皇实现“江山万世”的梦想,时至秦二世,反秦的起义便爆发了。从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起义至公元前202年刘邦建汉,秦王朝与汉王朝在政权上完成了彻底性的更迭,随之,新旧王朝的政治哲学与伦理思想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向。汉初,出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与更好地建立新时代的需要,上至皇帝,下至学者,他们对秦朝的成败得失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反思与总结。从作品产生年代上看,前有陆贾与刘邦的“十二论”,后有贾谊的“过秦论”等。凡此,我们不难从政治伦理层面寻见秦时与汉初的相异之处。
1.秦时尚法。秦朝自孝公任用商鞅起,法家政治哲学开始走上政治神坛,时至秦始皇行韩非之学,任李斯为相,法家政治哲学在实际政治中的应用可谓达到了极致。在此,我们且以韩非为例并结合秦史对其政治伦理范式及特性略作剖析。概而言之,大抵有如下两个层面:
(1)尚法轻儒。与儒家崇孝轻法有根本不同的是,在韩非看来,“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15]476,“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15]477,“博习辩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则国何得焉”[15]439。韩非又云:“故治民者,刑胜,治之首也”[15]516,“严刑则民亲法。……亲法则奸无所萌”[15]516,“故治民无常,唯治为法”[15]517,“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15]34等。上引可见,韩非对儒家及其所推崇的“孝”伦理思想是十分不认同的,他不仅从政治与功利层面否定了“孝”的伦理价值与社会作用,甚至提出了极端的建议——“禁儒抑墨”。当然,从秦统一六国的事功来看,我们并不否认韩非的伦理哲学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秦朝国祚短暂的症结与严刑峻法的弊端。这一点,诚如司马迁在《史记》中所云:“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17]2236;又,司马迁借商君之口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弊一至此哉”[17]2236-2237。此外,据《史记》记载:“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17]2156;李斯“阿顺苟合,严威酷刑”[17]2563。由上可见,法家之法使人噤若寒蝉,即便是曾贵为立法者,有时也难免其害;法家用刑之深,不仅扭曲了人性而且淹没了人情,更疏离了正常的人伦关系与社会交往。从另一个角度看,秦时的法家与儒家大有水火不容之势,这一点并非仅仅体现在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中,其实韩非的政治哲学早已暴露无遗,韩非曾说:“天下皆以孝悌忠顺之道为是也,而莫知察孝悌忠顺之道而审行之,是以天下乱。皆以尧、舜之道为是而法之,是以有弑君,有曲于父。尧、舜、汤、武,或反君臣之义,乱后世之教者也。……故曰:‘上法而不上贤。’”[15]505-506韩非甚至认为:“故人臣毋称尧、舜之贤,毋誉汤、武之伐,毋言烈士之高,尽力守法,专心于事主者为忠臣。”[15]507-508凡此,不难看出韩非对儒家仁义孝悌等伦理思想的否定,他甚至批评儒家的仁义孝悌等伦理思想不但不能起到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反而引起弑君弑父的暴行。
(2)仁义不施。我们在某种程度上认为,秦朝国祚短暂的关键症结在于:“仁义不施”。纵观秦史,自秦孝公任商鞅实行变法以来,秦国“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18]1。时至秦始皇时期,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应时陈论,“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17]2155。秦始皇虽因李斯构陷韩非而未能用其人,但是却在政治层面广泛吸收了韩非的思想,加之以主张法家思想的李斯为相,因此法家政治哲学在秦始皇时期迎来了历史性的机遇,不仅成为秦始皇巩固政权的利器,而且成了秦始皇攻伐六国统一中原的工具。客观地讲,法家政治哲学对处于战时状态中的秦国而言,有助其迅速实现政治层面的从无序到有序之变,有助其迅速实现经济层面的从穷困到富裕之变,有助其迅速实现战争层面的从无力到勇猛之变。时至汉初,在总结秦亡的教训中,陆贾与贾谊对秦朝的严刑峻法之弊、急功近利之弊与仁义不施之弊进行了深刻的批判。陆贾在向刘邦进呈的“十二论”中,大谈“仁义”的重要性,他说:“圣人怀仁仗义……危而不倾,佚而不乱者,仁义之所治也。……守国者以仁坚固,佐君者以义不倾,君以仁治,臣以义平。”[19]25-30同时,陆贾明确指出“万世不乱,仁义所治也”[19]34。可以说,陆贾的“新语”为刘邦接受儒家仁义孝悌提供了理论依据。稍后,贾谊则从历史的维度批判分析说:“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18]3由此观之,无论是陆贾的“新语”还是贾谊的“过秦论”,他们在省思秦亡之痛的同时,为儒家的孝悌仁义之道打开了通往政治的大门。史载,汉高祖与汉文帝对陆贾与贾谊及其学说颇为欣赏。
2.汉初重孝。在家国同构的政治间架下,“孝”的理论边界与内力被逐渐放大,进而由家庭领域推展至政治领域。诚然,随着“孝”伦理观念进入到政治,原本冰冷而血腥的政治似乎多了几丝人情与温暖。这其间固然是因为政治的需要,但也映射出伦理亲情之于实际政治的一抹亮色。
(1)“孝”在政治。西汉前期,“孝”在政治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谥号多“孝” 。据《史记》本纪记载,西汉前期的诸位皇帝多以“孝”为尊,例如孝惠帝、孝文帝、孝景帝、孝武帝等。这一现象侧面反映出汉初诸位皇帝对“孝”伦理思想的认同与推崇,同时也折射出“孝”作为一种基于家庭亲情关系的伦理范式之于政治的重要性。尽管西汉初年官方在政治层面大力推崇黄老之学,但是在家庭生活与社会伦常中,儒家伦理哲学依然有其存在的价值与发展的空间,尤其是儒家推崇的“孝”伦理思想不仅成为维系家庭伦理关系的枢纽,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维系政治伦常的关键。诚然,“孝”在政治的重要表现还反映在西汉开国皇帝刘邦本人对“孝”伦理观念的认同与推崇。例如刘邦当上皇帝后,将其父封为太上皇。史载,高祖六年五月颁《尊太上皇诏》曰:“人之至亲,莫亲于父子,故父有天下传归于子,子有天下尊归于父,此人道之极也。”[20]62由是观之,此诏不仅体现了刘邦内心流出的基于血亲关系的至亲之情,而且也确立了汉家“以孝治天下”的政治伦理理念。又如,孝惠帝毁“复道”之事,更是反映出即使身为皇帝也必须遵守“孝道”,不敢贸然有违。据《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记载:“孝惠帝为东朝长乐宫,及闲往,数跸烦人,乃作复道,方筑武库南。叔孙生奏事,因请闲曰:‘陛下何自筑复道高寝,衣冠月出游高庙?高庙,汉太祖,奈何令后世子孙乘宗庙道上行哉?’孝惠帝大惧,曰:‘急坏之。’叔孙生曰:‘人主无过举。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坏此,则示有过举。愿陛下原庙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广多宗庙,大孝之本也。’上乃诏有司立原庙。原庙起,以复道故。”[17]2725-2726上引可见,儒家“孝”伦理思想在西汉政治中的规约性与影响力。
(2)“孝”在民间。上行下效,君为民师。因此,当基于血亲关系的“孝”被统治者放大后,无论是出于血缘亲情与人之本性,还是出于效法人君与迎合政治,老百姓对“孝”伦理思想均表现出高度的认同与推崇。这一点,从发生在汉文帝时期的“淳于缇萦代父刑罪”一事中可知一二。史载,“齐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诏狱逮徙系长安。太仓公无男,有女五人。太仓公将行会逮,骂其女曰:‘生子不生男,有缓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缇萦自伤泣,乃随其父至长安,上书曰:‘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复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也。妾愿没入为官婢,赎父刑罪,使得自新。’”[17]2795由此观之,淳于缇萦的“求赎父刑”其实就是儒家“孝”思想在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具体体现,当“孝”与“法”之间出现张力与冲突时,“孝”被凸显,而“法”则有所退让。也就是说,淳于缇萦的行为有其合情性与合理性,甚至还得到了以汉文帝为首的统治者的认可与表彰。换言之,一介女流之所以敢于以孝亲之举对抗国家的法律,并不仅仅是因为她的勇敢,更多的或许是她看到了“法无外乎人情也”,或者说她的行为恰好找到“孝”、“法”之间的平衡点。其实,汉文帝本人也曾以孝闻名,对此袁盎赞曰:“陛下居代时,太后尝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汤药非陛下口所尝弗进。夫曾参以布衣犹难之,今陛下亲以王者修之,过曾参孝远矣。”[17]2739据说,汉文帝为母尝药尽孝之事一时传为美谈,“当时天下咸祢颂帝之仁孝”。纵观历史,先秦时期也有子女孝养父母的典型事例,暂不说“曾子不忍食羊枣”[14]374,且说“北宫之女”之事就颇为典型。史载:“北宫之女婴儿子无恙耶?徹其环瑱,至老不嫁,以养父母,是皆率民而出于孝情者也,胡为至今不朝也?”[21]由此可见,无论是先秦的北宫之女还是西汉的淳于缇萦,他们的行为不仅反映出儒家“孝”思想广泛的民间基础,而且也反映儒家伦理思想对当时政治的影响力。
综上所论,我们发现,秦与汉各自有着不同的政治伦理思想与伦理范式,政权更迭,质文代变,他们的政治哲学与伦理范式悄然完成了转换。也就是说,新兴的汉政权在政治领域以黄老思想取代了法家的政治哲学,在社会与人伦领域引入了儒家的孝悌仁义,从而完成了由“法”至“孝”的伦理范式的转换。
三、孝法并行
在儒家的“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的伦理理念与美好蓝图的指引下,西汉初期的诸位皇帝多是以“孝治天下”而自居。如前所述,无论是刘邦颁《尊太上皇诏》,还是其他诸位皇帝的谥号加“孝”,足见他们对儒家“孝”伦理思想的认同与推崇;凡此,无疑也为儒家伦理哲学在汉代政治中的异军突起打下了良好的政治基础。虽然尚不能断言汉武帝之前官方所立经学博士确然包括《孝经》,但是通过汉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经博士”[20]726之事,可知儒家伦理哲学至此已经系统地为汉代官方所认可并得到大力推行。尽管如此,汉武帝依然没有放弃“法”与“刑”,只是他的手段更为机巧,以至于出现“阳儒阴法”、“阳德阴刑”的现象。从“孝”在西汉政治中的体现来看,“孝法并行”概由此始。
1.孝的强化。诚然,当我们说“孝的强化”时,并不局限于某个帝王的某个时期,而是从汉兴至中期这个大时段着眼的。因此,“孝的强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一个由亲情伦理向政治伦理转进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对政治伦常起到了规范作用,而且还影响了西汉前期政治哲学的走向及伦理范式的构建。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略加缕叙:
(1)“孝”在“诏令”中的体现。尽管西汉初期迫于经济与政治的压力,中央政府在政治层面实行黄老政策,但是儒家政治哲学尤其是伦理道德在实际社会生活中仍然有着较强适应性与生命力。这种现象反映在政治层面的标准之一就是汉初诸位皇帝在诏令中的尊老与重孝。例如汉文帝元年三月颁《养老诏》云:“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饱。今岁首,不时使人存问长老,又无布帛酒肉之赐,将何以佐天下子孙孝养其亲?今闻吏禀当受鬻者,或以陈粟,岂称养老之意哉!具为令。”[20]113又如:“孝文皇帝前六年,汉遗匈奴书曰:‘…… 愿寝兵休士卒养马,除前事,复故约,以安边民,使少者得成其长,老者安其处,世世平乐。’”[17]2897再如:“孝文帝后二年,使使遗匈奴书曰:‘…… 圣人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长,各保其首领而终其天年。’”[17]2902由是观之,西汉时期的尊老思想可谓是自上而下地得到了重视,同时在外交理念中也有所体现。与此同时,儒家的孝悌思想在西汉也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尤其是得到汉文帝等人的推崇。例如,汉文帝十二年颁《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诏》云:“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师也。廉吏,民之表也。…… 其遣谒者劳赐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问民所不便安,而以户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20]124复如,晁错在对策中云:“今陛下配天象地,覆露万民,绝秦之迹,除其乱法;躬亲本事,废去淫末;除苛解娆,宽大爱人;肉刑不用,罪人亡帑;非谤不治,铸钱者除;通关去塞,不孽诸侯;宾礼长老,爱恤少孤;罪人有期,后宫出嫁;尊赐孝悌,农民不租……”[20]2296又如,汉武帝元狩六年,“六月乙卯,诏遣博士六人分巡天下,存孤寡,恤废病,赈穷乏,劝孝悌”[22]。再如,汉宣帝地节三年颁《举孝弟等诏》云:“……《传》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其令郡国举孝弟、有行义闻于乡里者各一人。”[20]250凡引可见,西汉中央政府对儒家“孝悌”伦理思想的认同与推崇。
(2)“孝”在“三纲”中的体现。在农耕文化与宗法社会中,“孝”作为基本的伦理范畴无论是维系家庭伦常关系还是维系社会伦常关系都是十分重要的。同时,“孝”作为道德评价的标准之一,还体现出儒家伦理思想中的一种人文关怀与终极关怀。诚如,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14]50;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14]286;孔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16]36等。也就是说,“孝”作为个体本能地追求永恒的一种必然方式是极为重要的。这种思想在以宗族血亲为基础的农耕社会里,不仅成为一种必然而有效的手段,而且也日渐成为一种终极性的伦理理念。因此,“孝治”伦理思想成为西汉乃至以后历朝治理天下的主要政治理念,“民德归厚”亦随之成为一种政治希冀和伦理理想的合理诉求与价值旨归。这一点,对董仲舒拓展“孝”之伦理思想有很大的影响。在《春秋繁露》中,董仲舒将天与天子之间的关系虚拟为一种“孝”的伦理关系,他说:“故号为天子者,宜视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23]286在家国同构的政治间架下,“孝”被放大成政治领域中的“忠”,虽然忠与孝在字面及含义上有所不同但其内涵实质则是相通的,都是强调下对上的绝对服从。换言之,在某种层面上,“孝”不仅仅是一种家庭伦理思想的集中体现,而且也是维系君主专制社会良性运行的必要手段和道德价值导向。其实,以“孝”治家与以“孝”治国在精神实质与价值向度上是相同的,因为“孝”的伦理精神实际上统驭着“三纲”中的“二纲”,即“君为臣纲”与“父为子纲”。诚如《孝经·圣治》云:“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义也。父母生之,续莫大焉。君亲临之,厚莫重焉。”[16]43由此观之,我们发现董仲舒的“三纲”思想与先秦儒学的内在精神是一脉相承的。与前儒不同的是,董仲舒为“三纲”思想找到了形上依据,并试图将此番论证转化成稳定的伦常制度与教化机制。对此,我们认为董仲舒对三纲五常的理论化与系统化是有所助益的。当然,他将三纲五常与阴阳五行相比附,有意或无意地掺杂了神秘主义,这一点则是不妥的。
(3)“孝”在“决狱”中的体现。有关“孝”思想在“决狱”中的体现,我们可以通过董仲舒坚持的“春秋决狱”之例窥测一二。董仲舒认为在断案量刑时,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涉案的动机和所造成的结果应该二者兼顾,他说:“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23]92同时,董仲舒主张断案时,应该充分考虑伦理亲情,也就是说,要在伦理亲情的基础上进行“决狱”。在董子看来,“春秋决狱”就是彰显一种人伦关怀,这一点,有例为证:
凡例一:“时有疑狱,曰:甲无子,拾道旁弃儿乙,养之以为子。及乙长,有罪杀人,以状语甲,甲藏匿乙。甲当何论?仲舒断曰:‘甲无子,振活养子,虽非所生,谁与易之?《诗》云:“螟蛉有子,蜾蠃负之。”《春秋》之义,父为子隐。甲宜匿乙,而不当坐。’”[24]可见,在儒家那里,亲情伦理在很大程度上是具有至上性的。例如凡例一所言:“《春秋》之义,父为子隐。甲宜匿乙,而不当坐。”细绎之,董子此论继承了孔子主张的“父子相隐”(见《论语·子路》)之要义,而且敢于大胆运用到现实社会中,此举使得儒家推崇的“孝”思想在现实社会中得到认可。
凡例二: 甲、乙与丙,争言相斗。丙以佩刀刺乙,甲即以杖击丙,误伤乙。甲当何论?或曰:“殴父也,当枭首。”论曰:“臣愚以为,父子至亲也,闻其斗莫不有怵惕之心,扶伏而救之,非所以欲诟父也。《春秋》之义,许止父病进药于其父而卒,君子固心赦而不诛。甲非律所谓‘殴父’,不当坐。”[25]凡此可见,当事人无心伤父,其动机是善的,并不违儒家所提倡的父子有义、有情之道德伦理。可见,在董子那里,对于行为善恶的判断,不论从法律上还是从道德上,都是根据行为人的动机是什么来考虑的。
上述表明,“父子相隐”的崇孝轻法的伦理主张在西汉时期对社会、政治诸领域的渗透颇深,甚至连皇帝对“父子相隐”的伦理理念也极为认同。例如,《汉书·宣帝纪》云:“父子之情,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无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20]251由此观之,在西汉时期,“父子相隐”不仅被认为是合乎人情的表现,而且法律也是不予追究的。
2.法的弱化。西汉前期,由于黄老无为思想与儒家仁义孝悌思想在政治领域的应用与扩散,秦时遗留下的“恶法”开始逐渐被废除,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法”呈现出被弱化的特征。严刑酷法的紧张逐渐被无为的自由与孝悌的温情所舒缓,其中最突的表现可以从诏令废刑与设立政教两方面来概括。
(1)诏令废刑。史载,汉高祖元年十月颁《谕诸县乡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馀悉除去秦法。诸吏人皆案堵如故。”[17]362汉高祖六年十二月颁《赦天下》曰:“天下既安,豪桀有功者封侯,新立,未能尽图其功。身居军九年,或未习法令,或以其故犯法,大者死刑,吾甚怜之。其赦天下。”[20]59汉高祖七年颁《疑狱诏》曰:“狱之疑者,吏或不敢决,有罪者久而不论,无罪者久系不决。自今以来,县道官狱疑者,各谳所属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当报之。所不能决者,皆移廷尉,廷尉亦当报之。廷尉所不能决,谨具为奏,傅所当比律令以闻。”[20]1106尽管“刘项原来不读书”,且曾“戏儒简学”,凡此亦足见其对儒家仁义、宽厚思想的接受与应用。
时至文帝,淳于缇萦因代父受刑而书奏汉文帝,文帝怜悲其意,于汉文帝十三年颁《除肉刑诏》云:“盖闻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与!吾甚自愧。故夫训道不纯而愚民陷焉。《诗》曰:‘恺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轻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为令。”[20]1098此外,汉文帝二年五月颁发的《除诽谤法诏》废除了诽谤罪,汉文帝二年颁发的《诏议犯法者收坐》废除了连坐罪,汉文帝十三年夏颁发的《除秘祝诏》废除了因灾异而刑于百姓的做法。
时至景帝,汉景帝元年颁《减笞诏》云:“加笞与重罪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20]1100汉景帝中六年又颁《减笞诏》曰:“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毕,朕甚怜之。其减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20]1100汉景帝中三年颁《颂系老幼等诏》曰:“高年老长,人所尊敬也;鳏寡不属逮者,人所哀怜也。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岁以下,及孕者未乳,师、朱儒当鞠系者,颂系之。”[20]1106汉景帝元年冬十月颁《文帝庙乐舞》曰:“孝文皇帝临天下,通关梁,不异远方;除诽谤,去肉刑,赏赐长老,收恤孤独,以遂群生;减耆欲,不受献,罪人不帑,不诛亡罪,不私其利也;除宫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也。”[20]137凡引可见,西汉文帝、景帝之仁厚及其政治哲学中的儒家政治伦理之底色,后世传言的“文景之治”虽是美誉,但似乎也不乏其实。
时至武帝,汉武帝元封四年三月颁《赦汾阴等诏》曰:“朕躬祭后土地祇,见光集于灵坛,一夜三烛。幸中都宫,殿上见光。其赦汾阴、夏阳、中都死罪以下,赐三县及杨氏皆无出今年租赋。”[20]195汉武帝元朔元年三月颁《赦天下诏》曰:“朕闻天地不变,不成施化;阴阳不变,物不畅茂。《易》曰‘通其变,使民不倦’。《诗》云‘九变复贯,知言之选’。朕嘉唐虞而乐殷周,据旧以鉴新。其赦天下,与民更始。诸逋贷及辞讼在孝景后三年以前,皆勿听治。’”[20]169此外,汉宣帝地节三年十二月颁《置廷平诏》,汉宣帝地节四年五月颁《子首匿父母等罪勿坐诏》,汉宣帝与汉元帝多次颁《赦天下诏》,汉成帝河平年间颁《减死刑诏》,汉哀帝建平元年正月颁《诏举孝弟》等诏令亦反映出西汉中央政府对“法”、“刑”与“罚”的弱化。
(2)设立政教。西汉伊始,萧何根据李斯所制秦律、具律、盗律、贼律等编成“九章之律”,加之叔孙通制订的“傍章十八篇”,张汤制订的“越宫律二十七篇”和赵禹制订的“朝律六篇”,时至汉武,帝国的法网罗织基本完成。然而与秦朝严刑峻法不同的是,汉帝国的中央政府并没有放弃道德说教,汉武帝不仅在组织机构上设置了专职礼官,“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20]172,而且其本人也时常告诫下属,“公卿大夫,所使总方略,壹统类,广教化,美风俗也”[20]166,并由此建立了一个宣德教化的官吏系统。尽管汉武帝在政治宣传上重视道德教化,缘饰儒术以粉太平,然而他在实际政治运作中却是极为强调刑罚的。例如张汤等酷吏曾以残酷威慑于市井。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认为,自汉武帝伊始,汉朝中央政府在政治伦理上采取的是:孝法同举,德刑并用。究而言之,刑罚与教化到底应该是怎样的关系?对此,董仲舒提出:“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23]94。在董仲舒看来,教化要比刑罚来得更为有效,刑罚只能使人畏惧并不能使人心悦诚服,而且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个人对社会伦理的认同和对社会秩序的遵守,更不可能使人们居有礼义、行有伦常。在某种程度上,汉武帝推行的“政教”思想正是源于董仲舒及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他们试图以儒家的亲情伦理弥补法律制度的不足,试图以儒家的道德理性统率法律理性,以“情”与“理”去舒缓“刑”与“罚”的残酷与血腥。然而由于诸种原因与局限,汉武帝时期的政治伦理理念并非完全出自儒家,以至于出现“阳儒阴法”的怪异现象。
总的来看,在西汉初期,“孝”的强化与“法”的弱化可谓是相逆而行;时至汉武帝时期,法孝之间有新变化,开始呈现出同行并进、互为表里的特征。汉初,基于血浓于水的至亲之情的“孝”伦理思想在家国同构间架下逐渐由家庭向政治扩散——“以孝治天下”,这种扩散与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彰显了“孝”伦理思想的生命力与普适性。当然,这种根植于人伦亲情的伦常规则被官方政治化、制度化后,它所释放的力量不仅仅是使“人”合乎情理地接受“规训”,同时也伴随着政治制度与道德规范的强制力以及人言可畏的社会舆论压力,诸种力量迫使“人”接受“教化”,以致其在“教化”中发生“异化”——“成为被承认的东西、成为特定存在”。[26]如前所述,这一点在董仲舒建构的“三纲”之“君为臣纲”与“父为子纲”以及“五常”中表现得尤为强烈。概之,孝文化演进至汉代呈现出多维向度与鲜明特征,“首先是孝道理论的纲常化与理论的神秘化;其次则是孝道的政治化、实践化;最后,是孝道义务与实践的片面化、绝对化”。[27]
四、小结
秦亡汉兴,政权更迭。秦与汉在政治哲学与伦理理念方面不仅悄然发生了转换,而且形成了各自不同的伦理范式与价值向度。诚然,从历史的维度看,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政治哲学与伦理范式。如果说短暂的秦朝(秦始皇统一六国至秦亡)是以法家的“法”为其政治哲学与伦理范式的,那么西汉王朝则可以用“孝”来概括其政治哲学与伦理范式。在西汉初期的历史进程中,“孝”的强化与“法”的弱化可谓是相逆而行,时至汉武帝时期,法孝之间又有新变化,开始呈现出同行并进、互为表里的特征。
需要补充的是,尽管我们承认“孝”伦理思想在西汉前期比较突出,但是却不想掩饰那时依然存在重刑与滥刑的事实。史载,“诸与衡山王谋反者皆族”[17]3097,“族灭瞯氏”[17]3133等。凡此从侧面说明,所谓的“文景之治”也许只是后人眼中的政治神话,文治武功与侈靡浮华只是属于少数的统治者,所谓的政治福祉对于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只是随声附和的谈资,这种缺乏道德维系与物质支撑的欢愉似乎注定只能是昙花一现。尽管历史给我们留下足够的想像空间,但是似乎也不应该仅仅依靠有限的史料与残存的宫阙去过度地夸大那时的政治文明与道德水平。
[1]许慎.说文解字:下[M].北京:中华书局,2013:787.
[2]毕沅,王先谦.释名疏证补[M].北京:中华书局,2008.
[3]邢昺.尔雅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4]高亨.周易大传今注[M].济南:齐鲁书社,1979:101.
[5]王先谦.尚书孔传参正:下[M].北京:中华书局,2011:927.
[6]黎翔凤.管子校注:中[M].北京:中华书局,2004:759.
[7]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下[M].北京:中华书局,2009:392.
[8]王利器.盐铁论校注:下[M].北京:中华书局,1992:595.
[9]高明.大戴礼记今注今译[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53.
[10]许慎.说文解字:上[M].北京:中华书局,2013:672.
[11]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下[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2]王先谦.尚书孔传参正:上[M].北京:中华书局,2011.
[13]黎翔凤.管子校注:下[M].北京:中华书局,2004.
[1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5]梁启雄.韩子浅解[M].北京:中华书局,1960.
[16]汪受宽.孝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17]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8]阎振益.新书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0.
[19]王利器.新语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0]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1]刘向.战国策: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418.
[22]荀悦,袁宏.两汉纪:上[M].北京:中华书局,2002:221.
[23]苏舆.春秋繁露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2.
[24]杜佑.通典: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8:1911.
[25]李昉.太平御览:第三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0:2868.
[26]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M].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49.
[27]肖群忠.孝与中国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58.
The Change between Law and Filial Piety:On the Political and Ethical Paradigm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Wang Chuanlin
(SchoolofPhilosophyandSociology,BeijingNormalUniversity,Beijing100875,China)
Throughout the history, each era has its own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paradigm. If the short Qin Dynasty is the “law” of legalism as the paradigm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ethics,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can be summed up as the paradigm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ethics in terms of “filial piety”. As Qin Dynasty was gone, Han Dynasty came into being, and regime changed. The Qin Dynasty and Han Dynasty were also quietly transformed from “law” into “filial piety” in the paradigm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ethics, thus forming the different ethical paradigm and value dimensions. In the early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filial piety” was reinforced and “law” weakened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In the Han-wu emperor period, a new change took place between “filial piety” and “law” and revealed the hand-in-hand characteristics and formed an integral part. It is worth mentioning that Dong Zhongshu, by “father to son outline”, argued for “filial piety” for further theoretical and mechanism defense, not only to expand the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s but also enhance the absoluteness and authority of “filial piety”.
Qin and Han dynasties; law; filial piety; political ethics; the ethical paradigm
2014-09-21
王传林(1978- ),男,安徽阜阳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B232.1
A
2095-4824(2015)01-0005-09
本栏目入选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名栏建设工程之后,发文数量明显增多了,可能会令人有庞杂之感,实际上这些文章还是围绕孝道文化及其时代价值与养老尊老的关系等主题而展开的。孝道是中华传统美德与优秀文化传统,其产生于周初,大兴于汉代,因此,本期有专文讨论秦汉之际的法孝关系、尊老文化。马一浮是新儒家中特别重视孝道与《孝经》的代表人物,对其崇孝思想进行新的维度的解读,是有重要学术意义的。孝廉文化在历史上的确是一种文化和察举官员的制度,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上来探讨孝廉文化的功能也是有价值的。对传统文化不仅要进行历史与学理的研究,对其时代价值进行揭示,以利于孝道文化在当代实现创新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无疑都是极为重要的。《新世纪孝道实践推广活动述论》一文较为全面地总结了新世纪以来孝道实践推广活动的背景、内容与特点,可资借鉴。还有另文探讨孝道与尊老文化的时代价值,更有文章探讨了孝德教育与大学生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这些都是对孝道研究广度的一种新探索。
(主持人肖群忠,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