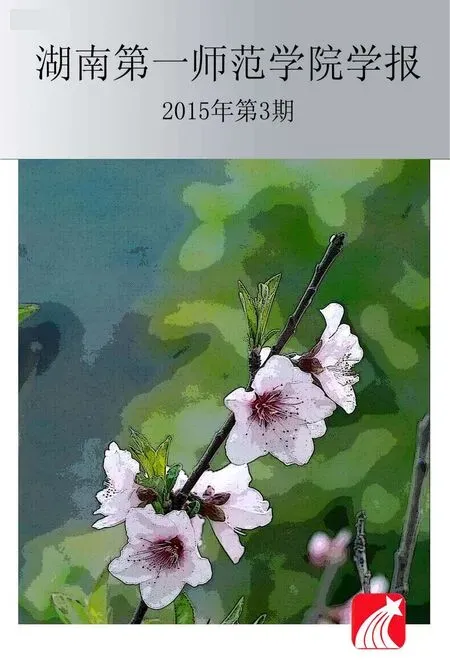青年毛泽东生命观初探
张 俨,陈名扬
(1.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长沙 410205;2.宁波大学 人文与传媒学院 浙江 宁波 315211)
生命观是一个人从自我的价值预设出发,依据现实体验和间接理论作出的对于生命的基本伦理态度和基本社会追求。生命观是人生观的一部分,其包含于主体对现实存在的一切评价,并在这种现实评价之中寻找、改变并完善着自我与他者的真实联系。毛泽东现存早期作品中有着大量关于生命及相关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他在青年时期颇富特色的生命观,青年毛泽东的生命观在未来漫长的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亦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一、生命是什么:生命是自然规律,但精神是不死的
1917年下半年杨昌济老师在湖南第一师范给毛泽东上修身课时采用了泡尔生的伦理学著作作为教材。毛泽东在这本著作上写满了上万字的批语,即著名的《<伦理学原理>批注》。他提到“人类者,自然物之一也,受自然法则之支配,有生必有死,即自然物有成必有毁之法则。凡自然法则,有必然性……且吾人之死,未死也,解散而已。凡自然物不灭,吾人固不灭也。”[1]194此时青年毛泽东还处于精神、物质皆不灭的二元论思想阶段。他认为生命体在产生之前肉体和精神是分散的,生命体在人间之时便是肉体和精神的合一,生命体结束后精神就脱离肉体而自存。所以他推导出来的结论是生命体的消逝并不意味着绝对的消逝,只是回到了生命体本真状态。庄子云:“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2]青年毛泽东沿袭了庄子的“聚散学说”。此学说认为聚散是生命的常态,每一个人都会发生相同的境遇,但并不意味着通向人的精神的灭亡。在精神不灭亡的前提下“细胞生命的自然状态,总是向前继续,至一定年龄而后老死”[1]430、“老人安然寿终,在一种自然状态之中,其事当必如此”[1]196等自然生命规律便无所畏惧了。青年毛泽东一方面强调人的生命的必然规律,一方面强调精神与物质永恒,就为自我的存在意义埋下了前提性假设,即不用担心自己的存在是短暂的与无意义的,在永恒的时空里我们都将获得终极价值。
针对有人终日忧虑死之痛苦,毛泽东言“吾人未有死之经验,如何知其有痛苦?”[1]196他用直接经验来排除此时的痛苦可能,将此在的生命意义扩为无限大。他还借用登海舟搏涛浪的壮阔气象来比拟生死更替之波澜:“大风卷海,波澜纵横,登舟者引以为壮,况生死之大波澜何独不知引以为壮乎!”[1]198联想起毛泽东老师徐特立当年断指血书恨国家耻辱一事,一个人只要将一生放置于与社会、宇宙同演化之高度,就会超脱原本带有凄凉悲切情愫的生命问题,因为生命主体已经将生死之变视为对宇宙规律和人生真谛的终极拥有,自然豪情万丈一往无前。
二、生死安足论:与其自杀而死,宁可奋斗而亡
1915年5月湖南第一师范召开了对易永畦同学的追悼大会。毛泽东和易永畦是同班同学,感情至深,他在《悼友人易永畦》这一挽联中写道:“胡虏多反复,千里度龙山,腥秽待湔,独令我来何济世;生死安足论,百年会有役〈没〉,奇花初茁,特因君去尚非时。”[1]6他对好友易永畦的去世感到无比痛心,并在是年次月《致湘生信》中抄录有他写给易君的挽词,其中有“鸣鸡一声唱,汗漫东皋上;冉冉望君来,握手珠眶涨。关山蹇骥足,飞飚拂灵帐;我怀郁如焚,放歌倚列嶂”[1]8句,直接表达了其“悲叹有余哀”之情切。挽联中“生死安足论”出自文天祥《正气歌》,其中有“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3]句,即指人的正道精魂将和天地永存,死生一事又有何惧。青年毛泽东生命观与此契同。他认为精神是不灭的,所以易君只是从人间离开并未真正远离我们,但只有在做出一番“平天下”的丰功伟绩之后才具有更高意义。在挽词中他即道出了最深伤痛的原因:“列嶂青且蒨,愿言试长剑;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1]8因为易君匆匆远逝并未有机会与他一道奋斗,用“长剑”将岛夷日本和北山俄国驱逐出我们的国土。此亦表明了青年毛泽东深沉的民族主义情怀和对儒家传统中最终“平天下”之宏伟愿景的积极践行。
1917年4月青年毛泽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其第一篇理论著作《体育之研究》,代表其生命观的理论自觉。他在文中详细叙述了体育运动的意义、作用和方法,强调体育为国民教育中第一要旨,先于德育和智育。文中说“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1]67,并说“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其载知识也如车,其寓道德也如舍”[1]67。他认为体育才是真正的“命中致远”之事,说“夫命中致远,外部之事,结果之事也;体力充实,内部之事,原因之事也。体不坚实,则见兵而畏之,何有于命中,何有于致远?坚实在于锻炼,锻炼在于自觉”[1]65。号召国民自觉锻炼身体。他认为体育锻炼对个体和国家拥有共同利益,对自己“内断于心,百体从令,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1]69,自己管理着自己的“祸福”,对国家一旦国民“身体平均发达”便能重振自庄子、仲尼以来之中华“武风”,方能与日本及西洋文明诸国做最后竞斗。青年毛泽东认为对于人的生命要积极地促成其发挥最大的意义,这个意义蕴藏在社会的共同进化之中。意志被青年毛泽东赋予了极大的意义,他在此文中强调“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1]72。虽然“生死安足论”,但需通过“强筋骨”达到“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特别是“强意志”。没有极强之主体意志,无事可成。
1919年,对新娘赵五贞自杀事件,长沙各界展开了讨论。青年毛泽东此时作为《大公报》记者,也连续发文十篇,从《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到《婚姻上的迷信问题》对封建婚姻制度展开了至为猛烈之批判。其中《非自杀》一文专门探讨到生命问题。他首先表明自己排斥自杀的观点,然后从四个方面论证自杀百害而无益。从伦理学来看,多数伦理家主张人是以“生”为目的的,“个人及全人类的生存发达”的基础是个人体魄和精神的完整;从心理学来看,人类最大多数的心理是欢迎生排斥死的;从生理学来看,自杀是反抗细胞生命不断继续的自然状态;从生物学来看,“普通都是以生为乐,体合环境,百折求生”[1]430。毛泽东进而剖析了赵女士自杀之原因,认为她“乃是想要求生”,而“社会尽行夺去某一个人的希望,而给与以完全失望”[1]431,得出“吾人是以求生为目的”,“与自杀而死,宁奋斗被杀而亡”[1]433的结论。青年毛泽东是不畏惧死的,但号召人们要充满斗争意志的生,在“先造新社会”前提下的有人格的生才是青年毛泽东对自我生命意义的至高追求。
三、生命的终极价值:以天下万世为身,奋斗以造新社会
青年毛泽东对生命本体的“聚散论”认识,主要是突出死亡不可怕,而将我们的注意力从死转向生。认识死,是为了更好地生,这也正是儒家伦理所奉行的不二真理。毛泽东从小受到儒家“内圣外王”之教育,拥有崇高的道德和社会使命。他在《讲堂录》中记有“毒蛇蛰手,壮士断腕,非不爱腕,非去腕不足以全一身也。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世为身,而以一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家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1]590天下是一个整体,虽然个人牺牲但世界是因为我的壮举而永存的。他一方面改造传统伦理而提出“精神的个人主义”,一方面将利他作为利己不可取代的部分,把利他归结为利自己的精神发展,而不是个人对物质占有欲的简单满足。他说“一切生活动作所以成全个人,一切之道德所以成全个人,表同情于他人,为他人谋幸福,非以为人,乃以为己。吾有此种爱人之心,即需完成之,如不完成即时于具足生活有缺,即时未达正鹄”[1]203。毛泽东将“爱人之心”化为一种亟需完成的行动,倘若没有如此爱人的自觉行动,那么就不能拥有“具足”生活,则生命有亏。他又说“济人之急、成人之美与夫履危蹈险舍身救人以拯人,亦并不在义务以上,盖吾欲如此,方足以安吾之心。设见人之危难而不救,虽亦可以委为无罪,而吾心究果以此见难不救为当然乎?不以为当然,则是吾有救人之义务也。”[1]236毛泽东将为他人谋利作为自我的根本使命,倘若不如此,便不能“安吾之心”,此乃儒家“内圣”之道。儒家将人生的终极价值划为“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首先在自己的内心拥有纯洁无暇的动机,然后以此自动的内心发出自动利他的行动,而为万世之圣。这与阳明学一致。而当时的社会氛围大抵封建主义、犬儒主义,更多以麻木不仁、见死不救为主流。青年毛泽东拥有并提倡的舍己为万民的凌云壮志,也为其后来思想转入马克思主义为全人类利益而奋斗做好了伦理思想的前提准备。
在解决了关于死的焦虑的问题后青年毛泽东面对所有人提出了如何完美的生的方法,其中主要就是增强意志、依靠奋斗与一切不合理、不正义决战,以在社会变革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真实幸福。他在《“社会万恶”与赵女士》文中提到赵女士为何不能逃亡而选择自杀的原因,他认为是“男女极端的隔绝”,是“社会上不容有女子位置”,并反问即使她选择逃亡那么“他逃亡向何处去?”[1]426在最后一篇评论《非自杀》中提出要“有人格的得生,须自己先造新社会”[1]433,即为我们指明了社会改造的必要性。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如果不进行最为坚决地奋斗,社会的问题得不到解决,自我问题也最终得不到解决,个体的幸福则无从谈起。针对不具备“内圣外王”之心的多数民众,青年毛泽东认为宜将“意志”与“奋斗”提到相当的高度,宜突出个体生命价值与国家及宇宙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事实。意志不坚强,没有奋斗力,没有主动地去参与创造不朽的人类事业,那么个体注定是悲剧的。相反,倘若用强大的意志与不懈的奋斗来造就谋子孙万世之利的人类事业,则自会流芳百世永恒不灭。他提到“吾人且非建功业以遗后世,此功业自有足以利后世之性质存在其中,况吾之不灭也,吾本有此不灭之性质具于吾之身中而已之耳。”一方面个体精神是不灭的,一方面我们所进行着的改造世界之事业内在就已经包含了“利后世之性质”,不用突出其“建功业”而已经是功业了。当时社会政治动荡不安,老百姓生活难以为继,多数国人被迫麻木不仁,青年毛泽东于此时提出须注重“意志”与“奋斗”,提倡民众将自己的生命与国家、人类之前途联结起来,具有改天换地之意义。
青年毛泽东肯定矛盾、礼赞矛盾,认为人是在进行正反对抗之后才达到目的,才能真正达到社会之改造与实现生命之终极价值。他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说“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1]180-181一切事物都在对抗之中显示自己的伟大力量。泡尔生在《伦理学原理》中提出,人的最大才干的发展须经历人生最大的事变,而不只是享受眼前的安稳。毛泽东认为这是“振聋发聩”[1]258之言。他认为每个人均会遭遇各种不幸,却正好锻炼自己的意志和奋斗力,那种无障碍的满足,无反抗的成功,难以充分展示人的主体潜能和本质力量,因而会减弱幸福的体验感,甚至感受不到幸福。毛泽东在1917年日记中提出“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4]39,即著名的“三奋斗”。此被后人误解并作攻讦之诟。事实上“奋斗”与“斗”不同,“奋斗”特指一个人在具备“内圣”之心的同时进行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斗争,指的是与一切不合理、不正义的现实发生决战,是改天换地的创造性劳动。青年毛泽东的生命观是立足于个人幸福的获得,同时又是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单纯的物质主义。他认为个人的幸福不仅仅是感性欲望的满足,更重要的是精神的高度发扬,生命的终极价值是在改造全社会的奋斗过程之中不断“澄明”的。
青年毛泽东在完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的生命观虽还处于唯心论阶段,其中有着不少的争议,但其对于生命本体的认识以及其拥有的积极奋斗的意志和行动力确是永远值得当代青年人学习的。一方面,毛泽东从小接受中华传统的儒学伦理体系教育,其“内圣外王”思想促使其不断进行自我的道德实践;另一方面,毛泽东之所以为毛泽东更在于他从小敢于利用各种矛盾进行不断奋斗,用自己强大的意志力战胜生命中遇到的诸多困难。青年毛泽东认为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因为眼前的束缚或压力而轻视自己的生命,可怕的是我们在人间之时并未为他人为社会为世界使尽全力进行整体改造。成长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进行不断地自我否定,还可能会发生数次认识论断裂,但我们的目的在乎生命价值之终极实现,在乎与他者互动前提下自我的完美体验,在乎不断地抵抗,在乎自我无比的韧性,在乎永远的乐观精神,在乎将生命意志、历史意识和宇宙精神融为一体[5],如此才能达到至善。“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4]37,青年毛泽东的生命观将永远激励我们当代青年,为进行虽简易却热烈的生活与实现人生的最高理想而奋斗。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
[2]胡仲平.庄子[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217.
[3]黄兰波.文天祥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199.
[4]麓山子.毛泽东诗词全集赏读[M].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7.
[5]刘自觉.毛泽东生命美学初探[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4):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