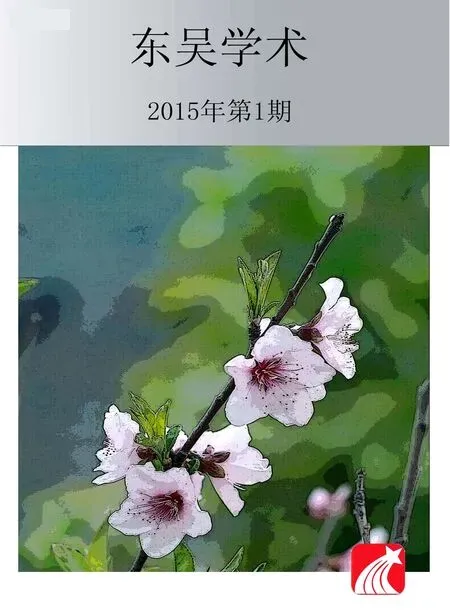文学对现世的道义
——林建法主编《二○一四中国最佳中篇小说》①序
胡传吉
中国文学
文学对现世的道义
——林建法主编《二○一四中国最佳中篇小说》①序
胡传吉
林建法选编的《二○一四中国最佳中篇小说》,收入红柯的《故乡》、唐颖的《当我们耳语时》、李浩的《丁西,和他的死亡》、李月峰《无处悲伤》、孙频的《同体》、方方的《惟妙惟肖的爱情》、尤凤伟的《鸭舌帽》。制度现实与人文传统,决定了中国当代作家不仅要关注普遍意义上的人的困境,更要关注具体制度下的人的遭遇。无论是何种主义及潮流在中国现当代盛行,作家们骨子里都有现实主义在。这七个中篇小说,有共同的气质。他们都很清楚现世中人的痛楚在哪里,尽管叙事手法有异,修辞办法有别,但关注现实为苦难发声的趣味是基本一致的,他们不绝而同地,以或明朗或变形的方式记录了具体制度下的人的困境。
二○一四;中篇小说;文学的道义
林建法选编的《二○一四中国最佳中篇小说》,收入红柯的《故乡》、唐颖的《当我们耳语时》、李浩的《丁西,和他的死亡》、李月峰《无处悲伤》、孙频的《同体》、方方的《惟妙惟肖的爱情》、尤凤伟的《鸭舌帽》。编选前,林建法嘱我写序,虽忐忑不安,但心领厚意,于是奋笔一试。不敢称序,但作阅读感受,与读写诸君共勉。
体制使然,中国当代作家有多重的背负。除了立足于文学艺术的本体,作家还要背负对现世的道义。文学并不必然背负现世的道义,但体制在客观上为之添附了这种必然性。通俗一点地来讲,体制内的作家,享有“俸禄”。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追溯,“俸禄”属于家国财富再分配的环节,“俸禄”最终必然对家国背负道义。无论何种时代,个体总会与社会发生关联。由血缘及等级而生的社会关联,显而易见。个体透过俸禄、赋税等因素与社会发生的关联,未必一目了然。俸禄、赋税等,是催生良知与责任的理性力量。良知非生而有之,正如人性之向善,总要经过教化。性善论与性恶论在设置人性前提时,明显对立,但两者在教化问题上殊途同归,性善论者并不因对性本善的执著而放弃教化,性恶论者在教化问题上刑礼兼施,两者在教化问题上绝不含糊。良知的生发,不仅需要道德力量的启蒙,也需要理性力量的推动。由于传统和现实的因素,中国的文学被赋予比文学更大的内容,文学也因此分担且分享了政治的权力。体制内的作家,更像是旧式士大夫的现代象征。他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官,但有级别之差,这是不争的事实。或者说,他们至少是处在一定的工资及奖励体系内,用学术话语来讲,就是大部分作家仍然“活”在文学制度里。尽管制度不具体追查作家的上下班时间,不严格限制作家的公私生活,但后面那个人身依附关系并没有消除,自一九四九年之后规范完善起来的文学制度,在今天并没有失效。文学制度设立的初衷,当然是明确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但无可否认,制度也对文学寄予了承担社会责任的希望,无论作家们是否愿意提及这一制度现实,制度现实都对写作提出了潜在要求。体制外的作家当然也不少,特立独行如王小波、薛忆沩者亦可数。但王小波即使远在江湖,薛忆沩即使身在异邦,他们的作品,无时无刻都有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印迹。说到底,文人这一群体,多多少少还是有来自于士大夫传统的入世情怀。
而由于现代社会的分工,古典意义上的官僚系统变得更细化。古典社会,尤其是贵族社会崩溃之后,士农工商之首的士,能凭诗赋经义进身官阶,参与治国平天下,诗赋等文学乃至经学并不是独立于官僚体系之外的,诗赋策论与仕途经济乃兼美之事。到了现代社会,尤其是当代中国,由于文学制度的介入,文学成为一个可以分门别类的部门。诗文仍然可以安身立命,但并不能凭此进身以治国平天下,“士”与“大夫”的身份分离,但传统下的现实对“士”的期待并没有消逝。之所以说当代作家有如士大夫的现代象征,就是因为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延续旧式士大夫以诗文立身之道。同时,传统社会早已为文字赋予神圣意味。由中国古文字的来源可知,集体的无意识实际上也对文字寄予厚望,传统并不认为文字只是实用之物。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仓颉作书等传说,无一例外地与圣人有关,与经世致用有关。与其说古文字发明本来如此,倒不如说古文字的起源被后人神圣化使命化。反过来,也可以说明,中国古文字的发明及应用本身,即藏有治世理想。文字在某种程度上分享乃至承担了古典社会治国之道,它的实施主体当然是读书人,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苏秦张仪等人能凭三寸不烂之舌以鼓动天下,这也是为什么孟子敢于夸口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士能以庶民身份进级为低等贵族,与文字大有关联。宋时文官当道,清入关后,八旗子弟被圈在北京,不用多长时间便武事尽废,满清皇室不得不大量起用前朝遗臣又尤其是文臣治国,这些,都是史证。士大夫之所以能凭诗赋策论立身进阶,体制内外的作家之所以能凭文字作品安身立命,与这个更深远的文字传统有关。
制度现实与人文传统,决定了中国当代作家不仅要关注普遍意义上的人的困境,更要关注具体制度下的人的遭遇。“多重的背负”,有的来自文学本体,有的来自制度现实与人文传统。这也就能理解,为什么中国当代作家会背负托尔斯泰、博尔赫斯、马尔克斯、卡夫卡、索尔仁尼琴、曼德尔施塔等写作风格不同的作家的影响焦虑。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对写作提出的潜在要求中,必然包含着对现世苦难指认并表态的要求。这很难说是文学的幸还是不幸。对现世来讲,文学承担了道义,对三生以外的世界而言,是否是幸事,又是另外的话题。但至少可以看到,无论是何种主义及潮流在中国现当代盛行,作家们骨子里都有现实主义在。写作者禀赋各异、趣味不一,其实很难归类。凑巧的是,这七个中篇小说,有共同的气质。他们都很清楚现世中人的痛楚在哪里,尽管叙事手法有异,修辞办法有别,但指痛打痛的趣味是基本一致的,他们不绝而同地,以或明朗或变形的方式记录了具体制度下的人的遭遇与苦难。
红柯的《故乡》,戳穿了现世温情款款的面子,方式直截了当。小说提出的问题就是家在哪里、如何回家。渴望回家的潜台词是无家可归无乡可回,你可以说这是一个普遍的存在真相,也可以说是中国无节制城镇化的无穷后患。当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乡土可以让人回家时,这回家的欲望就落在人的身上,简而言之,就是把思乡之情放到母亲身上,见到母亲,也就回到了家。小说语速急促,节省标点符号,不给喘气的机会,红柯有意制造一种急不待可的情绪,以配合归心似箭的小说主题,颇有心思。“一个在异乡混得不如意的人是没有故乡的,即使回到故乡也只能看见自己的亲娘”,小说中的周健,设想各种办法回家,譬如把自己想象成邮包,假想自己魂归故里,总之是各种不切实际,认定故乡就是娘。小说还借回乡主题回溯了更大的主题,即维拉特土尔扈特蒙古族的东归史,对比叙事的意味在于寻找传统与现代的连接点:古典社会的游牧生活与现代社会的居无定所,是否有共同的故乡。红柯以情感及自然来解释回到故乡。既然回家在事实上已不可能实现,那么,就让回家在情感尤其是家庭情感中得到实现。蒙古草原同时暗示,大自然对人心有足够的控制能量。《故事》主题明朗,叙事有豪迈气。可惜小说回避了反向的问题,即,假如在异乡混得如意,假如游牧不被农耕同化,那么,故乡的故事该如何书写。
唐颖的《当我们耳语时》,读来有惊艳之感。作者善于小题大做,小世界可喻大世界,小历史里有大历史。题目也有隐喻之效,在高音喇叭肆行的时候,耳语是禁忌,但恰好又是最“相信”的时代,到了可以耳语的时代,人们知道了真相,但又找不到母亲,找不到可以相信之物。小历史是三个人年少时的感情纠葛,建平、金默(男)、慢雨三人之间,看上去似乎是金默爱慢雨,但实际上是金默与建平在信件里相爱——所有给金默的回信都是建平代慢雨写的,但中间的那层纸从没有当面被捅破。多年以后,建平与金默在芝加哥机场转机时偶然遇到,建平开始回想彼此的年少时光,慢雨的电话加入进来,共同回忆“我们”的历史,弄清楚究竟谁在爱谁是带动故事发展的关键叙述视角,但这不是作者的重点,重点是弄清楚为什么人们爱上了虚假的高尚,明知道他假、夸张、有目的地乐于助人,但建平和慢雨还是爱他,显然,爱他就是爱五十、六十、七十年代。建平和金默最终逃离了历史,但留下了伤痛,作者以建平的腿伤、金默的脑病揭示了逃遁者的永久伤痛。最妙的是,没出国的慢雨,最清楚个人及历史的来龙去脉,尽管她的词典里有许多禁忌,但她洞悉一切。《当我们耳语时》以叙事带动观念,内含悲伤的情感,最大的悲剧暗示是,“我们”都失去了母亲。留在国内的慢雨“失去”了母亲,她的娘家人都移民海外。出国的建平和金默,虽日夜想念母亲,却再也见不着母亲。唐颖的叙事与观念,都相当有分量。
《丁西,和他的死亡》,题目中的逗号,显示出李浩的有意犹疑,丁西是生是死,李浩不想给出准确答案。模糊处理是最好的办法,生不如死,生死互置互换,以死为照妖镜,收尽人间妖魔鬼怪。文学的修辞帮助作者回避现实中的种种禁忌,以避免文学跟既定秩序发生正面冲突。如果直写现实,那就会冒犯,如果是写死后的世界,那就是想象。“某个九月的凌晨,四十三岁的丁西打着鼾进入了死亡”,丁西由此进入冥间。经查,丁西原来还有两年零三个月的命,因冥间工作人员的失误,丁西提前被索命。丁西于是求告冥间的各种主管部门,但无一部门能解决其生死问题,不能让他重生,也不能让他投胎,丁西死也死得不踏实,最后还是靠亲戚关系才获得投胎的希望。小说固然立足于对现实的嘲讽,但如果往深层考究,不写现实,只写假想的世界,让怒火包裹绝望,也写出了活着的悲哀与死后的失落。人活一世,大部分时间在与各式机构打交道,且必须学会在被拒绝甚至是羞辱中生存,现代官僚体系的日趋严密,加重了人的窒息感。这未必是单单某一个国家的现实,它可能是现代社会被商业及电脑捆绑之后的一个缩影。求告无门的寓意也不仅仅是制度层面,它有精神层面的讽喻,这样一来,制度便不再是罪恶的唯一制造者。《丁西,和他的死亡》明显有卡夫卡《城堡》之风。
李月峰的《无处悲伤》书写了一种很普遍的情况:没有父母可依靠,没有亲戚朋友可依靠,更没有上帝可依靠,生计及精神依托全失之际,人应该怎么办。为了改变无依无靠的状况,有的人眼中只有钱,有的人成全他人。小说中的李长欢,离过婚,通过办家政公司站起来了,曾有过妈,妈离开后,尸骨未寒,离家多年的大哥就回来争母亲留下来的房子,李长欢放弃了继承权,把房子留给兄长,自己在一无所有之后,重新开始。李长欢谁也不靠,就靠自己。现实中有无数被社会“遗弃”的个体,你过你的,他过他的,各人过各人的,这里的“靠自己”,其实是被生活逼迫后的“靠自己”,跟自立意义上的靠自己有着显然的区别,靠自己的后面,其实是失去他人的生活,这种痛楚,确实是“无处悲伤”。小说并不以故事取胜,但非常耐读,字里行间,皆可看出小说作家对生活有深入细致的观察及体验,这在一个务虚的写作时代,实为难得。譬如作者对老年人的描述,就十分到位,李长欢眼中的妈,“我妈要是跟谁强辩,没有谁比得了她。她老了嘛,人老了你除了要跟她讲理,还要磨叽。但我知道跟她讲理没什么用处,我就跟她磨叽”,“磨叽”两字出来,比较普遍的“老人病”就一览无余了。女儿与妈妈的斗嘴,女儿对妈妈的口头敷衍,等等,都写得贴近生活,读之不由莞尔。写作之务虚有乐趣,务实也有力量。
孙频的《同体》,叙事用力。故事把生活素材改写成一个圈套,冯一灯在打工的地方快活不下去的时候,掉进了一个陷阱。这个高中没读完的女孩子,想尽办法拒绝卖身,但最终还是难逃悲剧。冯一灯被抢劫被轮奸被解救,都是温有亮设计的结果。温有亮在冯一灯不知情的情况下,获取冯一灯的完全信任。温有亮欲擒故纵的手法,甚至让冯一灯死心踏地爱上了他。前奏完成之后,温有亮逼迫冯一灯色诱官员敲诈官员,齐齐赚大钱。小说的结局是温有亮逍遥法外,冯一灯下落不明,或自焚或逃走,语焉不详。小说写得最好的地方是冯一灯父亲的遭遇,父亲变成了一个罪人。她父亲是山村小学的最后一个老师,在最后一个学生(女学生)要离开这个学校的时候,强奸了这个女学生,父亲用粗暴、可耻、违法的方式表达了他对生活的绝望、对失去女儿的恐惧。女儿因父亲的罪,忏悔自己的罪。父亲被判了八年,关在监狱里,女儿去看他,“他说他不见任何人”,“父亲不见她是因为他觉得他无颜面去面对她,就像她这么多年里不回水暖村不见父亲,只是因为她觉得她无颜面去见他”。故事圈套一般,但父女的罪恶对照书写得很好。那些被诱惑的罪人都毁灭了,但那个罪源还在——罪源到底是启蒙忏悔之源还是诱发罪恶之源,小说写得很暧昧,暧昧得高明。
方方一直有写实的情结,也有对现实的高度敏感,为时代把脉的能力强大。她的小说,有拍案而起的霸气,也有嘻笑怒骂的洒脱,有任性的地方,也有庄重的时刻。随“新写实主义”潮流而现的《风景》等作品,捕捉到了后革命时代庸常生活的颓废。透过《惟妙惟肖的爱情》,方方看到了交易时代知识分子的落魄。惟妙与惟肖是禾呈和老婆所生的双胞胎,一家四口大致可分为两派,禾呈和儿子惟妙是读书永乐派,基本持读书有用论,禾呈老婆和惟肖是读书臭屁派,基本持读书无用论。禾呈和惟妙是历史学系的教授,惟肖学历不高,原是大学里的司机,后来跟着表姐赚钱,一举发达,房子、车子等,应有皆有了。于是读书有用论者与读书臭屁论者在家里的地位发生了颠倒,有钱者取代知识者成为大声者。但有趣的是,惟妙与惟肖都离了婚,知识与金钱都守不住一个完整的家。看上去知识分子的值已贬无可贬,但有钱人赚够了钱之后,还是要去大学加冕,或讲课或任荣誉博士或当兼职博导。是金钱无法彻底催毁知识的尊严还是金钱早已操纵知识的灵魂?虽然方方没有明说结论,但小说对现实有悲观的看法。
尤凤伟喜欢为小人物的故事赋上离奇色彩,《鸭舌帽》也不例外。姚高潮的不如意生活主要来自私生活,当然,工作也不见得能让他舒心。姚高潮的老婆跟学校一男老师在一起了,于是姚高潮想跟那男老师的老婆见上一面,商量解决办法——什么办法都想到了,就是没想到要离婚,人生在世,能拥有的太少,那么,能抓住一点就是一点,即使抓住的那一点点东西是虚无,也要死命抓住。也许姚高潮的心里还有更龌龊的想法没说出来,譬如跟对方的老婆睡上一觉,那么双方就算扯平了,等等。老婆避而不见,也不接电话,姚高潮在找老婆的过程中,目睹了离乡别井之人互相搭伙的生活,所谓搭伙,也就是许多人秘而不宣的临时夫妻生活,姚高潮也在这方面尝到了甜头,这些甜头没有让生活更甜美,反而让人更快地奔向虚无。这些不能光明正大的生活角落里,充满了不合法的、非道德的尴尬人生。
如前文所言,作家们很清楚现世的痛楚与尴尬在哪里。这些痛楚与尴尬,有的可以明说,有的必须借助修辞来说。看到就是承担,在中国,文学很难摆脱对现世的道义。
二○一四年十一月十日
胡传吉,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著有《中国小说的情与罪》、《自由主义文学理想的终结(一九四五年八月-一九四九年十月)》。在《红楼梦学刊》、《东吴学术》等刊发表论文四十余篇。
① 林建法主编:《2014中国最佳中篇小说》,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