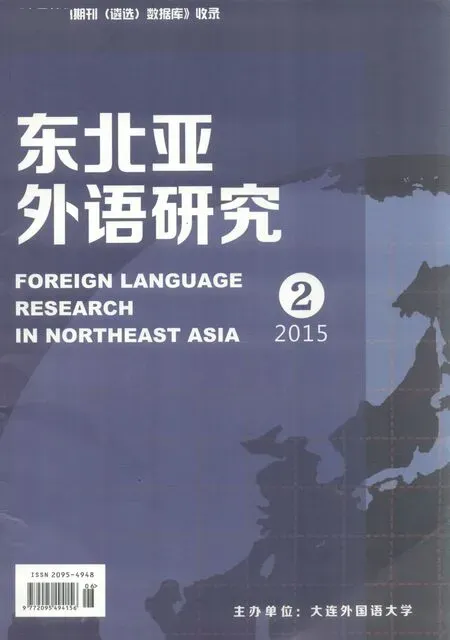漂洋过海的无产阶级文学备忘录
——从诗歌杂志《燕人街》的发刊到野川隆的登场
西田 胜
(法政大学,日本 东京 102-8160)
漂洋过海的无产阶级文学备忘录
——从诗歌杂志《燕人街》的发刊到野川隆的登场
西田 胜1
(法政大学,日本 东京 102-8160)
本文将传播到“满洲”的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作家向“满洲”的报纸和杂志投稿;第二种类型是受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影响在“满洲”展开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第三种类型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作家以及受其影响的青年来到“满洲”从事创作。本文对其分别作简要论述,揭示了无产阶级文学在“满洲”展开的复杂性。
日本;无产阶级文学;“满洲”;传播
一、“漂洋过海”的三种类型
所谓“漂洋过海的无产阶级文学”,在本文中主要指传播到“满洲”的以下三种类型的日本无产阶级文学。
第一种类型是语言上的“漂洋过海”。事实上,许多无产阶级文学作家和评论家都向“满洲”发行的报纸和杂志投稿。仅以“日中战争”之前而言,其代表人物有青野季吉、江口涣、秋田雨雀、新居格、窪川(佐多)稻子、松田解子、细田源吉、岛木健作等。之所以限定在“日中战争”之前,是因为在那之后,这些作家便以转向作家的身份开始创作。
“飘洋过海”在此还包括传入或“搬运”入“满洲”的无产阶级文学的图书和杂志。究竟有些什么样的无产阶级文学作品和杂志传入,其阅读情况如何,可以说目前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还处于几乎无人问津的状态。
第二种类型是“漂洋过海”后落地生根,发展成为独自的运动。1930年1月创刊于大连的无产阶级诗歌杂志《燕人街》便是其中的例子。但由于“满洲事变”爆发到“满洲国”建立期间的戒严令,处于萌芽期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很快便夭折了。
第三种类型是无产阶级文学作家,以及受无产阶级文学影响的青年的“漂洋过海”。前者基本上是所谓的“转向作家”,代表人物有山田清三郎、上野市三郎(岛田和夫)、木崎龙(仲贤礼)、平八郎(清水平八郎)、野川隆、横山敏男(池田寿夫)、叶山嘉树等。至于后者,代表人物有牛岛春子、北尾阳三、加纳三郎、塙政盈等,大内隆雄(山口慎一)和古川贤一郎大概也可归于这一类。
“满洲国”政府于1941年9月,将“满洲文艺家协会”、“满洲美术家协会”、“满洲乐团协会”、“满洲剧团协会”、“满洲摄影家协会”、“满洲书法家协会”、“满洲工艺家协会”合并组织为“满洲艺文联盟”。该联盟显然是模仿10年前由无产阶级文化各个团体合并而成的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简称KOPF)①而组织的。在近代日本历史上,像KOPF这样的文化活动联合团体史无前例。组成KOPF的诸团体如下:新兴医师联盟、新兴教育研究所、日本战斗的无神论者同盟、日本无产阶级电影同盟、日本无产阶级世界语同盟、日本无产阶级戏剧同盟、日本无产阶级音乐家同盟、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日本无产阶级摄影同盟、日本无产阶级美术家同盟、无产者计划生育同盟、无产阶级科学研究所(日本プロレタリア文化聯盟,1931:88)。
以下本文将就这三种类型,分别举例作简要论述。
二、“漂洋过海”的语言
“漂洋过海”的语言是第一种类型。青野季吉于1935年常在《满洲日日新闻》发表文章,同年12月15、16两日连载题为《文学之叛逆性》的文章。该文论及“言论统制”的现状,认为近代文学本质上是“叛逆的”,“没有不叛逆的文学”;以及应当跨越“本国特有的私小说以及其他众多文学种类”的封闭性,回归近代文学“优良传统”。最后总结说:
近代文学的优良传统就是在其叛逆性上。为了真正继承和发扬其传统,仅仅让不顺从的叛逆灵魂发出呻吟、原地挣扎是不够的,还要必须有明确的社会方向性和内容。
(青野季吉,1935)
再举两个例子。其一是作家江口涣,他同样在《满洲日日新闻》上于1936年1月22日、23日两天连载短评《期待讽刺文学》。他认为,当文学受到“时下政治的压制”而思想不能“正当”表达的时候,最懦弱的人便会屈从压力放弃思想;“虽懦弱却出于良知不愿丢失自我的人”便陷于虚无主义;意志坚强且“理智”的人则避开同“政治压制”的正面冲突,转向“讽刺文学”。然后他介绍了壶井繁治等无产阶级文学作家组织的“山顶社”。江口涣认为,日本自夏目漱石的《我是猫》诞生以来30年间鲜见出色的讽刺文学作品,“现在也到了应该出现反映新社会的讽刺文学了”,并期待它的出现②。
其二,作家松田解子(1936)也在《满州新闻》的前身《大新京日报》上,于1936年1月16日发表短评《文艺三十六年文坛动向》。她指出,1936年“政府”通过文艺恳谈会“有组织地插手”文学界。对此,一方面“资产阶级文学”不得不表示“要下新功夫,立誓诚实”,另一方面无产阶级文学也表示“即使失去组织,也要挣扎着存活下去”。她在做了这样的概括之后,认为在将要到来的1936年诸多课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如行动主义运动将去向何方,纯小说论和偶然论能带来什么,以及无产阶级文学“创作方法上的问题——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是否是○○现实主义的问题”③等。她尤其要求“所有一丝不苟的进步作家、无产阶级作家”能够“切实地解决这些面临的问题”。
然而,以1937年7月爆发的“日中战争”为分界,无产阶级文学作者向报纸杂志的投稿,除连载作品之外,其他顿时销声匿迹。自此以后,虽偶尔可见无产阶级文学作者的投稿,但如上所述,已然是以转向作家的身份发声。
例如松田解子,她在战争爆发半年后,在《大新京日报》1938年1月11日号中发表短评《妇女评论·战争与儿童漫画》,其中提到一首刊登在少年漫画杂志上的题为《后方母亲》的歌:“为钱卖命,支那愚兵,糊涂上阵,无力起誓,父母之国,不胜不还。”这首蔑视中国人的歌是用日本的军歌填词而成④。松田以这首歌和日本军对中国实施轰炸为例子,反问前者难道不是与素日宣传的“作为真诚的教训,支那不应该被侮辱”这一观点自相矛盾的吗?而关于后者则指出,可能那就是明天的自己,不应该用“空袭”的战果来“煽动孩子”(松田解子,1938)。
这样的批判的确是尖锐的,但这是对侵华战争肯定基础之上的批判。虽屈从亦抵抗——松田也成了转向作家中的一员。
三、被扼杀于萌芽期的“满洲无产阶级文学运动”
这是第二种类型。1930年1月,无产阶级诗歌杂志《燕人街》在大连创刊,虽然名为诗歌杂志,但《燕人街》刊登的作品并不限于诗歌,也发表很多评论,后期逐渐开始刊登小说。同人们自己也将这个蜡纸刻板油印版杂志定位为“满洲”最初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阵地。
在这本诗歌杂志之前,久吕澄狂介等人还创办过同人杂志《红街》、篠垣铁夫(中村秀男)等人创办过《赭土文学》。同一时期还有大内隆雄等人的移民文学社的文学活动。但除《浅利胜集》以外,该社发行的宣传材料和杂志全部散失,具体内容至今仍然是迷。
《燕人街》是菊版开本每期31页的月刊杂志,1931年4月停刊,历时1年零4个月,总共发行了14期。同人最初有上述久吕澄狂介、以及高桥顺四郎、落合郁郎等13人,之后古川贤一郎和篠垣铁夫加入,土龙之介也逐渐在该刊发文。
杂志名“燕人”原指从中国山东省到“满洲”外出做工的季节工人,而从日本漂洋过海的作家也可以说是一种“燕人”,杂志因此得名⑤。
该杂志上的评论文章对于了解当时大连文学状况很有价值。高桥(1930:7)在《无产阶级诗歌的单纯性》一文中,将“无产阶级诗歌”的特征总结为“现实性”、“斗争性”、“反个人主义性”和“单纯性”四点,主张用简单明了的语言将艰深的思想传播给“大众”,进一步清算“超现实主义诗歌的费解、未来派的复杂、达达主义的杂乱”等问题。该文至今未丧失其意义。冬木绅一(或许是古川贤一郎)的《模仿诗》(1930)也对《亚》的追随者展开了尖锐的批判。大概是因为遵循以上主张创作,诗歌产生了优秀的作品。
《燕人街》停刊一事原因尚不明了,但大概是迫于当局的言论压制。比如,2卷2号(1931年2月)登载赤田靖(1931:15)的文字“他从军队中寄来的明信片上盖有‘射击奖’大印章”,这绝非容易刊登的内容,因为是以呼吁士兵内讧的言辞结尾的。
军令要求我们枪口瞄准的目标
甚至包括那个将十八钱军饷全数寄给故乡母亲的他
枪口不要仅是朝着前方
(赤田靖,1931:15)
因此,“满洲事变”一爆发,大连刚诞生的“满洲无产阶级文学”便被扼杀。
值得注意的是,1931年12月“满洲事变”刚一平息,土、高桥和落合的诗集《三人集》(东勇编)便由“奉天”的“胡同编纂所”出版发行,而不是在大连出版。《胡同》是诗歌杂志的名称,土是该杂志的同人,高桥负责“后记”,加藤郁哉和古川贤一郎撰写“跋”⑥。
四、远渡“满洲国”的转向作家以及各种有志于文学的人
远渡“满洲国”的转向作家的创作态度,同上述松田解子的情况相同,即“虽屈从亦抵抗”。并且,这种“抵抗”的强弱因人和时期而异。
山田清三郎最初在政府报纸《满洲新闻》担任学艺科长兼论说委员,不久出任“满洲文艺家协会”委员长。虽成为支持“满洲国”文化政策的主要文人,但内心深处仍然感到愧疚,并对遭受残酷殖民统治的中国作家和农民抱有些许同情。这在他1942年和1944年编辑的两本《满洲国各民族创作选集》中有所体现。
另一个极端例子是野川隆。他通过农业合作运动接近贫困的中国农民,并因此被政府逮捕,投入监狱,最终病死在狱中。野川隆歌颂中国农民的长诗《屯里的圣母》和《老头儿》可谓是集革命文学和文学革命于一体的现代诗的绝唱⑦。
山田似乎将野川的这种生存方式当作自己“满洲生活的情感支撑”。他不仅因野川被拘捕一事受到沉重打击,甚至在战后回忆说“如果他们还活着,会如何为今日的到来而感到高兴”(山田清三郎,1957:219)。
以下再看看两个受无产阶级文学影响“漂洋过海”的青年的例子。
第一位是批评家加纳三郎。转向文学作家木崎龙在《建设文学》中提出,只有通过努力实现“满洲国”的“王道乐土”才有可能冲破日本近代文学的死胡同,“满洲文学”是其条件之一⑧。对此,加纳撰写《幻想文学》,批评木崎龙的文章的观点是“幻想文学理论”、“法西斯主义文学理论”,主张以写实的手法描写“满洲国”的现实⑨。他也由此以文艺批评家的身份崭露头角。
加纳不仅发表文艺时评,也执笔社会时评,曾在《东亚思想的诸条件》一文中论述真正的“日中合作”实现的条件,其中包括对近代中国“半殖民性”“封建性”“资本主义的矛盾”的综合理解⑩。该文是真正直面中国历史的论文,至今读来仍发人深省。
然而,加纳由于法官工作兼写作劳累过度,最终身患重度结核,于1942年5月返回日本,三年后英年早逝,终年41岁⑪。
另一位作家是北尾阳三。1939年4月,北尾以中篇小说《铺子》入选《满洲日日新闻》的悬赏征文活动,在文坛初露头角。之后他笔下的内容便以描写飘洋过海到“满洲”的日本人为主要对象,也涉及市井中的中国人和俄罗斯人。北尾的作品中包含着对日本帝国统治殖民地的批判。且据笔者所知,他在“大东亚战争”爆发之后从未发表过支持战争的言论。
这种情况非常少见。即使是曾经对“满洲”农民的生活充满同情并在作品中歌颂过他们的古川贤一郎,也在“大东亚战争”期间发表了数首所谓的“歼灭英美诗”。
人神共难容
邪恶残虐的英美!
魔鬼野畜的英美!
扬言要杀光
地球上我们的英美
你们听好了!
我们要将你们逼迫到
地狱的角落
我们要变身复仇的阿修罗王
来吧——英美呆货
来吧——英美混蛋
(古川賢一郎,1943)
这是古川《来战斗》中的一节。该诗刊登在1943年6月16日的《满洲新闻》上。
北尾在1945年秋天,日本战败投降后,帮助受八路军邀请的大冢有章,将他自己工作过的“满映”改造成为中国人管理的“东北电影公司”⑫。
注释:
① 当时,担任“满洲文艺家协会”委员长的山田清三郎(1957:62),在回忆录《转向记风暴的时代》中说道:“文艺家协会自6月以来,以‘志愿’的方式协助政府的询问,并进行设立协会的准备。我在此并未忘记运用无产阶级运动的经验。例如在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领域,将各个独立的团体联合成为满洲文艺联盟组织。该提议是以我在纳普时代学习到的经验为根据的。”
② 请参阅江口涣于1936年1月22日—23日在《满洲日日新闻》上发表的连载短评“期待讽刺文学”。(江口渙.1936.諷刺文学待望[N].満洲日日新聞,1936-1-22-23.)
③ 如果所避讳的词是两个字,很可能是“革命”。当时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声音中有“反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的主张。
④ 显然,这是在诙谐地模仿军歌《陆军军歌》(大和田建树作词、深泽登代吉作曲)的第一节:“替天行道,忠勇无双,欢歌相送,父母之国,不胜不还,我心誓勇”。
⑤ 详情请参阅以下文献:西田勝.2006.プロレタリア詩誌『燕人街』の登場及び『燕人街』総目次[J].植民地文化研究,(5):121-127.
⑥ 详情请参阅笔者于2006年—2010年连载于『植民地文化研究』上的“詩誌『燕人街』抄”系列论文(共计五篇)。
⑦ 详情请参阅以下文献:西田勝.2007.中国農民に殉じた詩人野川隆.近代日本の戦争と文学[M].東京:法政大学出版局.
⑧ 详情请参阅木崎龙于1937年9月21日—23日于《满洲日日新闻》上发表的连载作品“建设文学”。(木崎龍.1937.建設の文学[N].満洲日日新聞,1937-9-21-23.)
⑨ 详情请参阅加纳三郎于1937年10月21日—23日于《满洲日日新闻》上发表的连载作品“幻想文学”。(加納三郎.1937.幻想の文学[N].満洲日日新聞,1937-10-21-23.)
⑩ 详情请参阅加纳三郎于1939年4月发表在《新天地》上的“东亚思想的诸条件”一文。
⑪ 详情请参阅以下文献:西田勝.2009.『満洲国』における芸術的抵抗の一例——加納三郎の場合(一)[J].植民地文化研究,(9):91-102;西田勝.2010.『満洲国』における芸術的抵抗の一例——加納三郎の場合(二)[J].植民地文化研究,(10):114-131.
⑫ 详情请参阅以下文献:西田勝.2014.『満洲国』における芸術的抵抗の一例——北尾陽三の場合[J].植民地文化研究,(13):96-106.
[1] 青野季吉.1935.文学の叛逆性[N].満洲日日新聞,1935-12-16.
[2] 赤田靖.1931.軍隊にゐる彼から来たハガキには『射撃賞』と大き判があつた[J].燕人街,(2):15.
[3] 高橋順四郎.1930.プロレタリア詩の単純性について[J].燕人街,(9):4-7.
[4] 日本プロレタリア文化聯盟.1931.日本プロレタリア文化聯盟規約草案[J].プロレタリア文化,(創刊号):88-89.
[5] 冬木紳一.1930.模倣詩[J].燕人街,(3):34-35.
[6] 古川賢一郎.1943.来り戦へ![N].満洲新聞,1943-6-16.
[7] 松田解子.1936.文芸 三十六年の文壇の動き[N].大新京日報,1936-1-16.
[8] 松田解子.1938.婦人評論 戦争と子供の漫画[N].大新京日報,1938-1-11.
[9] 山田清三郎.1957.転向記 嵐の時代[M].東京:三一書房.
A Memoire of Proletarian Literature across the Sea——From the Publication of Yanren Street Magazine to Nogawa Takashi’s Coming on Stage
The Japanese proletarian literature in Manchuria, in current research, falls into three categories: the first category is marked by contributions to Manchurian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by Japanese proletarian writers; the second type is characterized by proletarian literature campaigns in Manchuria under the inf l uence of their Japanese proletarian literature counterparts. The last one features literature creation activities in Manchuria by Japanese proletarian writers and the young influenced by them. Each individual category has been briefly discussed so as to disclose the complexity and sophistic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proletarian literature in Manchuria.
Japanese; proletarian literature; Manchuria; transmission
I106
A
2095-4948(2015)02-0023-04
西田胜,男,日本法政大学教授,殖民地文化学会会长,研究方向为近代日本文学和“满洲国”文化。本文原稿为日文,由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日文系2014级硕士研究生罗霄怡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