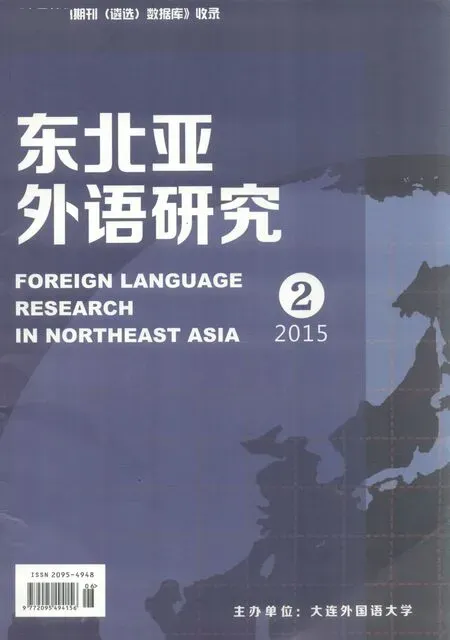叶山嘉树,被“搬运”到中国的无产阶级作家
吕元明
(东北师范大学 外国问题研究所,吉林 长春 130024)
叶山嘉树,被“搬运”到中国的无产阶级作家
吕元明
(东北师范大学 外国问题研究所,吉林 长春 130024)
本文全面梳理了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叶山嘉树的作品在中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翻译和接受情况;既肯定了他的作品对同时代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的积极影响,也指出他堕落为天皇主义者后遭到中国读者的抛弃。1970年代以后中国开始重新评价叶山嘉树,但如何辩证地把握其文学依然是未解的课题。
无产阶级作家;搬运;精神粮食;天皇臣民1
作为日本著名的无产阶级作家,叶山嘉树(1894—1945)的名字对上个世纪的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 他在中国的知名度并不比在日本国内低。他的作品表现日本劳苦大众的生活和精神世界,描写日本资本家和工人阶级的激烈冲突,其大众化的语言和富于同情心的创作态度深深地打动了当时及以后的中国读者的心。长期以来,对叶山嘉树的作品,中国读者不仅是当做文学艺术来欣赏,更是作为革命的精神食粮来吸收的。对他作品的翻译介绍,左翼翻译家冯宪章将其比作是“搬运”,“搬运”来为中国人民所用。本文主要关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叶山嘉树的作品被“搬运”到中国来的状况,同时也留意“搬运”潮过后的翻译介绍以及两者之间的差异。
一
在叶山嘉树开始创作后不久,他的作品就被介绍到中国来,迅即引起中国读者的关注。对他的翻译和介绍首先见于各种杂志。1928年,杂志《乐群》第1卷第1期刊登了他的短篇小说《士敏土罎里的一封信》(与后文中的《士敏土桶里的一封信》《洋灰筒里的一封信》为同一作品,因译者不同致作品名出现差异),译者为张资平。张资平是当时中国最活跃的作家之一,发表了不少左翼倾向的作品。但“七七事变”后,他开始与日本合作,最终为中国人民所弃。同年,《大众文艺》第1卷第3期刊登了君乔翻译的《卖淫妇》,《北新》第3卷第6期刊登了张我军翻译的《樱花季节》。进入1929年后,《现代小说》第4卷第6期刊登了沈端先翻译的《别离》;《乐群》第2卷第1期刊载了陈勺水翻译的《佃户的狗和地主的狗》。鲁迅、周作人等人创办的《语丝》第5卷第28期刊载了《洋灰筒里的一封信》,译者为张我军。1930年,另一著名的杂志《新文艺》第2卷第2期刊登了《一个残酷的故事》,译者为郭建英;《新文艺》第1卷第5期刊登了《随笔三篇——挨蛰的男人、散步、代价码的贵夫人》,译者为崔万秋。著名的革命杂志《拓荒者》第1期刊登了《没有劳动者的船》,译者为冯宪章。关于这些译者的情况,后面将分别介绍。得力于他们的翻译,叶山嘉树逐渐成为为中国熟知的日本无产阶级作家,他的小说一经发表就受到读者的欢迎。
1933年,中国出版了叶山嘉树的第一个译本,题名为《叶山嘉树集》,由上海现代书局出版,译者为冯宪章。书内收有《没有劳动者的船》《卖淫妇》《印度船》《坑夫的儿子》《士敏土桶里的一封信》《湾街的女人》《苦斗》等小说。冯宪章在该书《写在译稿的前面》里称叶山嘉树“曾经是日本文坛中有力的一个”作家。还透露他东渡日本后,起初想翻译叶山嘉树的小说,为此和“日本其他作家们交谈过”(叶山嘉树,1933:2)。我们不知道这里的“日本其他作家们”都是谁,也不知道他是否和叶山嘉树见过面,但可以感受到译者对叶山嘉树的关注。当时是“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高涨期,冯宪章特地说明他为什么要翻译叶山嘉树的作品。他把翻译的作品比作粮食,说:“这个集子便是我搬运来的一个面包。翻译是较次于创作的一个工具,我素来这样想。但是,当民众需要着米饭,而我手里只有巧克力糖的时候,从别的地方搬运面包来,也是一桩紧要的事业。就是面包不十分适合食惯米饭的口味,至少也能够充饥。所以,最近,除自己学习种田耕耘之外,也还做搬运工人。”(叶山嘉树,1933:1)
冯宪章在这里是将中国革命的问题,比作大众的吃饭问题。当时的南京政府对出版实行严格的控制,左翼文学的作品很难问世。翻译叶山嘉树的作品,也含迂回战术的成份,无疑是为了中国的大众。对此他不便直说,便将思想借鉴比作吃大米、面包,将翻译称之为“搬运”,也含有尽量忠于原文的意思。同时,冯宪章对叶山嘉树在日本无产阶级运动中迷恋合法斗争的倾向也提出了批评,批评他“脱离了实际生活”,但他认为“叶山嘉树从前的小说,也不会象他现在的倾向,与我们完全没有作用”(叶山嘉树,1933:3)。他在最后交代翻译的选本时说:“这一个集子,从以前许多著作中选出交改造社出版的《没有劳动者的船》的全译。这是很好的面包,因为在制造这些面包的时候,他没有喝酒。我敢担保,这依然可以充饥!”(叶山嘉树,1933:4)冯宪章留学日本的时间很短,在有限的时间里,比较过几种版本后,最终决定以新出版的改造社版作品为翻译的底本。可见他从事翻译工作的认真态度。改造社的《没有劳动者的船》出版于1929年。叶山嘉树的酒瘾看来是早就出了名的,在这里冯宪章拿他开玩笑罢了。不知叶山嘉树看到这样的调侃作何感想,是不是有想戒酒的冲动呢?
冯宪章生于1908年,广东人,诗人。1931年不幸英年早逝,享年23岁。翻译叶山嘉树的作品是他为数不多的译业之一。1925年,17岁的他加入共青团。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共青团和共产党是作为一个组织两个团体来开展活动的。建党四年,冯宪章便参加了党领导的革命活动。1926年,冯宪章主编共青团广东梅县县委机关刊物《少年旗帜》。大革命失败后,他参加了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于1929年去上海,进入艺术大学学习。这所大学有党的组织和大量的进步学生,在校期间,冯宪章参加了作家蒋光慈等人组织的太阳社,开始专心从事文学创作。学校后来被国民党政府解散。同年,他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值蒋介石政权镇压和屠杀中国共产党人最疯狂的时候。不久他东渡日本留学,在东京组织太阳社东京支部。1929年,日本的特高警察发现他的革命活动,将其驱逐出境。1930年,冯宪章参加了左翼联盟。后被捕,受到非人折磨,于第二年死于狱中。冯宪章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如彗星般划过天空,炙烈,灿烂,天才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就熄灭了。在国共残酷斗争的年代,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冯宪章的诗作有《战歌》《凭吊》《匪徒的呐喊》等,以及他唯一的诗集《梦后》。冯宪章从创作之初就涉足革命文学,是无产阶级作家。其作品为中国的劳苦大众发声,为他们的苦难与不幸鸣不平,为中国革命的兴起摇旗呐喊。他的激情以及为民请命的态度与叶山嘉树有不少相似之处,大概这就是他“搬运”叶山嘉树的缘由之一。只是作为同行,冯宪章比叶山嘉树更坚定,更不屈。他的炙热的感情,生动的语言,乐观的态度,对信仰的忠诚都在翻译中有所体现。冯宪章不是专门的翻译家,对日本文学也没有很深的造诣,他的翻译也可看作是一个革命的诗人以革命的名义对异国的同行的致敬。其翻译作品除《叶山嘉树选集》外,还有译自日本的《新兴艺术论》。在他去世后的1933年,上海现代书店又重印了《叶山嘉树选集》,显然含有悼念之意。
二
叶山嘉树文学的另一搬运者是张我军。1939年7月,上海北新书店出版叶山嘉树的小说集《卖淫妇》。内收《卖淫妇》《别离》《灰桶里的一封信》《没有劳动者的船》《山崩》《跟踪》《樱花季节》《疏浚船》《天的怒声》《火夫的脸水手的脚》《扑鳬》等作品,共计十一篇。另卷收录有叶山嘉树小传。全书的篇幅比冯宪章的译本要多一些。如果说冯宪章是以作家身份翻译,那张我军则是以日本文学翻译家的身份翻译的。因此,虽说是同一篇小说,但译者不同,在修辞、风格上也会出现差异。可以说这就是文字语言表现的魅力所在。同时,不一样的叶山嘉树反而使我们能更多维地品味他的文学。
张我军,原名张清荣,1902年出生于中国台北。少年时代当过鞋店学徒。从幼时起学习欲望就很强烈。为了继续深造,1923年进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升学补习班,学习十分努力。在京期间,受“五四运动”思想的影响,人生观发生了很大变化。旋即回到台北,任《台湾民报》中文编辑。这期间,发表了充满“五四”新思想的文章,向台湾地区的旧思想、旧文化发起猛烈批判。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地区宣传“五四”新思想、输入新思潮,台湾地区新文学也因之蓬勃发展起来。1925年,他又回到北京,就读于中国大学国文系。1926年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学习,期间和朋友创办《少年台湾》杂志。1929年毕业后,在母校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大学任日语教师。在此期间张我军致力于日本文学理论与思想评论的翻译,他的作品引起了读者的关注。他先后译有有岛武郎的《生活与文学》(北新书店,1929年)、秋浅次郎的《烦闷与文学》(北新书店,1929年)、千叶龟雄的《现代世界文学大纲》(神州国光社,1930年)、宫岛新三郎的《现代日本文学评论》(开明书店,1930年)、夏目漱石的《文学论》(神州国光社,1931年)。叶山嘉树小说集《卖淫妇》也是在这一时期出版的。
之前,张我军翻译的书多为文学理论书籍,他也因此出名。翻译叶山嘉树的小说算是一个例外,这标志着他的文学翻译开始了新的尝试。他在谈起叶山嘉树的翻译时说:
今年春回,偶然在北平的日本书肆,看到一本小册子《没有劳动者的船》,因为我正在注意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看到了这个题目,马上从书架上抽出来翻看了,在目录上看出了《洋灰桶里的一封信》时,我的心一时跳起来了。一如见了没有见过面的恋人。过几天我又得到了改造社出版的《新选叶山嘉树集》,就在这个集子里,我完全认识了叶山嘉树,我在这里满足了有生以来第一次的欣赏欲。老实说,原来的文学作品,能像叶山氏这样使我感到欣赏的快意的,还没有遇见过。
(叶山嘉树,1930:1)
张我军的反应是如此强烈,凸显了叶山嘉树作品的魅力不仅仅在其革命性,也在于其艺术性。在那个革命和叛逆的年代里,他的心动无疑是真实的。对叶山嘉树的创作赞美有加,说明他对二、三十年代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有较深入的了解,对其成果也有很高的评价。张我军很快就把他的“恋人”打扮(翻译)出来了。书前的小传,是他给叶山嘉树写信,请他自己写来作为译书之序的。叶山很快答应了他的要求,寄来了他的自传。这就是张我军译书中的“叶山嘉树小传”。这个小传和信件的原文现在下落不明。这也许是叶山嘉树第一次和中国作家通信,所以态度很积极。张我军翻译过山川均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解剖》,他在序言里说:“打倒帝国主义这个口号,在我国已普及至小学生和洋车夫,都会背了。然而再问一问:那么你所要打倒的帝国主义是什么?于是连大学生和知识阶级很多要哑口无言了。不过帝国主义的确是我们的催命鬼,的确是必须打倒的大虫”(张我军,2012:369)。张我军有爱国之心,故他早期译作和《语丝》结缘,然而他既没有冯宪章那样的革命热情,更不是冯宪章那样的革命家。背景的差异是否会投影到译者的译笔上呢?笔者认为把两人甚至更多的译者的译文排列起来比较应该能够加深对叶山嘉树的理解。
“七七事变”后,张我军没有像很多爱国人士那样奔赴大后方,而是留在了北京。须知他在1935年就出任北平社会局秘书,已经是官场中人物。这一经历可能影响了他的选择。张我军的选择使他滑向他曾反对过的日本帝国主义一边。1942年、1943年,他两度参加日本文学报国会主办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为争做与会代表,落水者们在当时闹得一塌糊涂。1943年,叶山嘉树也参加了这个大会,从已知的资料来看,两人在会上并没有见面。当时,叶山嘉树是作为普通作者参加的,而张我军则是正式的与会代表,两人的地位已有很大的变化。叶山嘉树只参加一天大会,就回长野去了,看来对大会没有什么兴趣。当年曾经通信往来的译者和作者只能失之交臂了。总而言之,张我军在中日战争的紧急关头做出错误的选择,从此走上歧途,堕入深渊。在这一点上他远不如生活在北京的许多台湾地区人,他们以各种方式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一直坚持到了胜利的那一天。
三
上世纪二十年代后期至三十年代前期,是中国翻译介绍叶山嘉树的第一个高潮期。参与翻译的译者或介绍者,几乎都是革命者或曾经的革命者及抗日爱国的志士。其中不少人,如夏衍、张资平、陈勺水、崔万秋、胡秋原等,还是中共文化方面的领导人或各界知名的抗战人士。他们在面对日本近代文学时,都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叶山嘉树。这个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当时中国革命文学流行的状况。
1929年1月乐群书店出版张资平的翻译集《范某的犯罪》,除了江口涣、藤森成吉的小说外,还收入叶山嘉树的《士敏土坛里的一封信》。这篇作品后来又被收录在1933年由现代书店出版的《资平译品集》里。译者张资平为广东人,是当时的流行小说家,名声很大,人生道路却很曲折。虽然翻译家的头衔不及他小说家的名声响亮,但在中国现代文学翻译史上,他仍占有重要的一席。他的译作还有翻译佐藤红绿的长篇小说《人兽之间》等。他的作品在伪满洲国也有一定的影响力。1943年,“新京”(今长春)大东书局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一代女优》,他在上海出版的日本文学译书,在伪满的书店也时时可以见到。
1929年1月,上海晓山书店出版林伯修的翻译集《俘虏》,内收入叶山嘉树的小说《卖淫妇》,另外还收有金子洋文、鹿地亘、藤森成吉、西泽隆二等人的小说。林伯修是共产党员,后来不幸牺牲。他认为叶山嘉树的小说可以作为“教材”。1929年6月,乐群书店出版陈勺水翻译编辑的《日本新写实派代表杰作集》,其中收有叶山嘉树的小说《狗船“迦茵”》和《佃户的狗和地主的狗》,还收有平林泰子、黑岛传治、立野信之、桥本英吉、太田千鹤夫等人的小说和青柳信雄的戏剧,这些作家都是日本左翼文学的代表作家。书前附有译者序。陈勺水以翻译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的著作闻名于世。翻译叶山嘉树和日本左翼作家的作品构成他革命活动的一部分。
同年,上海大江书铺出版沈端先翻译的小说集《初春的风》,内收入中野重治、平林泰子、林房雄的小说,金子洋文的戏剧、叶山嘉树的小说《印度的鞋子》也在其中。“沈端先”为夏衍发表翻译作品时使用的笔名。夏衍原名沈乃熙,杭州人。1920年公费留学日本。在日本留学期间参加日本的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文学运动,1929年被通缉,遂回国。他和田汉、欧阳予倩等组建左翼剧联,也是中国早期电影的创立者之一。作为评论家、剧作家、翻译家、左联成员活跃在文坛上。他的翻译是和文学创作同步开始的,并且多产,在翻译界享有很高的声誉。解放后曾任新中国最初的文化部副部长。
1933年,北平星云堂书店出版张一岩的《日本新兴文学选译》。这是在中国北方出版的为数不多的日本左翼文学的结集,内收有前田河广一郎、片冈铁兵、岸田国土、叶山嘉树的小说,叶山嘉树的小说是《苦斗》。本书值得注意的是它有一个总序,由译者张一岩执笔,篇幅较长,为译者文学研究的成果。另收有作者的传记。在五位作者中,叶山嘉树的传记很长,这是应张一岩的要求,由叶山嘉树自己撰写的。不知道这个传记和应张我军之约写的那个有什么区别,只是在分量上前者比后者多出很多,这可能是因为两位译者对作者的要求不同造成的。五位作家分别收有年谱,可见张一岩在编译上很花了一番功夫。
总序从日本近代文学史的角度来评论日本左翼文学。译者写道:“从大正末期到昭和间的过程,是多方面的、复杂的、深刻的,是日本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互及各部分的变异,动摇,各式各样的倾向,令人炫目地展开了。这种现象常反映于时代的尖锐化之文艺上,簇拥出了有特点异彩倾向的诸作家。他们与已成为文坛的坚壁相对立,显示着勇敢的存在,一年年潜入大众的心核,终于在社会方面和文坛上都取得了辉煌的地位。现在所收集的五作家,就是代表这种倾向的最尖端,他们都是飒爽的,新锐的”。在谈到叶山嘉树时,称他和前田河广一郎、片冈铁兵是“站在普罗文艺阵的第一线上,不断作前卫的创作家”。“叶山氏因其代表作《在海上生活的人们》,不但确定了他个人的价值,而且是第一期的日本普罗文学者永远的纪念碑,他是彻头彻尾的普罗利塔亚罗曼斯特,他是把握着从特殊的经历得来的特殊题材,加以普罗利塔亚的热情,成了如歌咏的创作的劳动的诗人”(张一岩,1933:1-2)。也许这是叶山嘉树的译者中给他予以最高的评价。在二三十年代,中国已经有人在讨论、评价叶山嘉树对中国的影响了。
胡秋原是中国二、三十年代重要的评论家。1929年留学日本。他在《语丝》第5卷第34期发表题为《日本无产文学之过去与现在》的论文,涉及面很广,对叶山嘉树有如下评价:无产文学战线“声势甚振,耳目一新”,“创作方面林房雄、叶山嘉树、黑岛传治等以新鲜之笔登于文坛”。胡秋原称叶山嘉树的笔触是“新鲜”的,指出《卖淫妇》《水门汀桶之信》《生于海上的人们》“最博好评”(胡秋原,1929:354-358)。他将叶山嘉树和小林多喜二、德永直相比较时,认为叶山嘉树的“文战”倾向是很大的不足。在这个问题上胡秋原站在小林多喜二一边,这和中国大多数人的观点是一致的。评论家们大多认为叶山嘉树的作品不错,就是政治立场有问题。叶山嘉树的政治立场的确为他日后带来灾难。1932年,华蔕(崔万秋)在《北斗》第2卷第1期发表评论激烈批评日本文战派,指出:“文战干部青野季吉、前田河广一郎、叶山嘉树、金子洋文却没有一点善化的倾向,而且更加紧了他们的行动。”(华蔕,1932:90)显然,这是从政治运动上批评叶山嘉树而不是在艺术上。华蔕一向语言尖锐,这篇文章也不例外。
四
从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前期,日本帝国主义对外加紧扩张侵略,对内强化法西斯统治。小林多喜二被特高警察活活打死,让日本国民及亚洲人民看到了日本国家政权的残酷嘴脸。对此,包括鲁迅、郁达夫等人在内的中国文化界人士极为愤怒,发表了言辞激烈的抗议书。叶山嘉树到小林多喜二家慰问其家属,看到了受到严刑拷打遍体鳞伤的遗体,受到极大的震动。他在1933年2月23日的日记里写道:“听说告别仪式今天下午一点开始,我要去看他那已经变形的脸跟他道个别。太可怜了。虽然在政治上意见不同,但他是我喜欢的男子汉”(葉山嘉樹,1971:107)。
此时的叶山嘉树在政治上受到监视,加上生活状况日益恶化,不得不离开城市,到山里的铁路和水坝工地过活。叶山嘉树离开社会活动,其作品也丧失了原有的风格。“七七事变”爆发后,中日进入全面战争,叶山嘉树也开始在思想上转向,逐渐沦为一个天皇主义者。从此,他不再成为中国人“搬运”的对象。在中国,对叶山嘉树的翻译与研究由高潮跌到谷底。夏衍等人奔向抗日战争大后方,为争取抗战胜利写了大量的作品。留在敌占区的日本文学翻译家、研究家附敌、资敌的人很少,他们自然对叶山嘉树失去兴趣。在敌占区和沦陷区,除军事进攻之外,日本也在宣扬提倡日本文化。尽管如此,翻译介绍日本文化的书籍的出版比起战前萧条多了。
偶尔也有人出版翻译日本文学的新书,如当年在文坛上很有名气的章克标。1943年上海太平书店出版由他翻译、编辑的《现代日本小说选集》。该书出版计划似乎比较大,1943年出版第一集,翌年出版第二集,计划好像还要继续出下去,但由于日本战败投降而中止。章克标出书显然有日本的背景,太平书店是日本资助的书店,随着日本的投降而关张。在章克标译本的第一集里,收有叶山嘉树的一篇作品《往海洋去》。原作发表于1942年,是叶山在日本发动“大东亚战争”后表决心的作品,传达的是他要为国尽忠的思想。积极支援战争的态度使中国的读者对他愈发失望。叶山嘉树的声望在中国读者中间开始受到质疑。这个结果可能是译者始所未料的。
在伪满洲国,叶山嘉树文学的命运也同样不济。伪满洲的中国人不再视其为必读,而日伪当局也在有意压制他。在伪满,他的作品一篇都没有被翻译出版过,书店里他的作品,多是在关内的上海或北平出版后辗转运来的。
叶山嘉树的作品在中国再次受到关注是在一个新的时代——新中国成立之后。新中国时期,随着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中国的读者与研究者再次把目光投向了叶山文学。不过,这次和二、三十年代热情“搬运”的情况已大为不同。那时中国处在革命斗争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紧张时期,叶山嘉树的作品起到了动员和鼓舞中国人民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历史条件已与过去不同。虽然很长一段时期革命文学仍然是文坛的主流,但对叶山嘉树的接受发生了变化,他的作品与其说是作为精神粮食,更多的是作为了解日本的社会和文学的文本被提供给读者的。由于时代的变迁引起的接受的错位,新中国时期对叶山嘉树的介绍和阅读终未形成红火的局面。不过,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在经历了热情“搬运”后,接受趋向理性,叶山文学回归原位意味着深化阅读的开始。
1979年,在中国开放改革的大潮中,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叶山的《生活在海上的人们》,这是在新中国出版的叶山嘉树唯一的单行本,译者为徐汲平。从译文质量上看,徐的译本比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译本有极大的提高。另外,在一些作品集中也可见到他的小说的身影。如1981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日本短篇小说选》中收有《卖淫妇》,为刘新华所译。1994年北京华夏出版社出版的《中外文学名著速读全书·外国卷3》节录了《卖淫妇》。建国以来,对叶山嘉树的研究尚无专著问世。不过,较之二、三十年代有了不少的进展,有较多的文学史著述言及了叶山嘉树的文学活动,预示着系统研究的开始。1987年由吉林出版社出版的笔者著《日本文学史》将“叶山嘉树·黑岛传治的创作”列为单独一节,笔者指出“叶山嘉树是无产阶级文艺运动最早成熟的作家之一”,谈到他的晚年说:“因不堪忍受农村生活,作为‘满洲开拓移民’,1943、1945年被迁至中国东北黑龙江落户。日本失败后,回国途中,病死在南行的列车上。”(吕元明,1987:274-275)陈德文(1991:189)也在其著《日本现代文学史》中的《无产阶级文学》一章里谈到叶山嘉树时说明:“战时曾到中国东北,战后在撤离途中病死于由哈尔滨开往长春的火车上”。影响了一代中国人的无产阶级作家战时搭着“国策”的战车来到伪满,最后作为天皇的臣民消逝在曾经拥有众多读者的中国大地,这是多么可叹而又可悲的一幕。
1984年《日语学习与研究》第5期发表了李芒的《论叶山嘉树》,这是当时为数不多的研究论文(后收入《投石集》)之一。李芒从世界革命文学、日本革命文学的宏观角度评论了叶山嘉树在文学上的贡献。他指出:“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工人文学’如宫岛资夫(1886—1951)的《矿工》(1916)等,其主人公是尚未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的个别分子,靠一己的力量,单枪匹马,盲目反抗;那么叶山嘉树所描写的这些生活在海上的人们,则是二十年代觉醒的工人阶级。他们以新兴阶级的崭新形象,首先登上日本文坛;这些在日本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尽管主人公的表现还不完全具备自为阶级的特征,但是这部作品毕竟促发了后来无产阶级文学——《蟹工船》的诞生。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活在海上的人们》可说是奠定了无产阶级文学的基础,为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发展开辟了蹊径。”(李芒,1984:51-52)在中国编著的日本文学辞书中也可以见到叶山嘉树的名字,如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吕元明主编《日本文学辞典》,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张岩峰等人编著的《简明日本文学辞典》,都将叶山嘉树列为重点辞条。
[1] 葉山嘉樹.1971.葉山嘉樹日記[M].東京:筑摩書店.
[2] 陈德文.1991.日本现代文学史[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3] 华蔕(崔万秋).1932.一九三一年的日本文坛[J].北斗,(1):88-95.
[4] 胡秋原.1929.日本无产文学之过去与现在[J].语丝,(34):337-369.
[5] 李芒.1984.论叶山嘉树[J].日语学习与研究,(5):51-53.
[6] 吕元明.1987.日本文学史[M].长春:吉林出版社.
[7] 叶山嘉树.1930.张我军译.卖淫妇 [M].上海:北新书店.
[8] 叶山嘉树.1933.冯宪章译.叶山嘉树集[M].上海:现代书局.
[9] 张我军.2012.张我军全集[M].北京:台海出版社.
[10] 张一岩.1933.日本新兴文学选译[M].北平:星云堂书店.
Hayama Yosiki: a Proletarian Writer Who Has Been Carried to China
This paper is a brief research on the works of Hayama Yosiki who as a Japanese Proletarian writer has been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Chinese literature. The thesis thoroughly introduces the translation and acceptance of his works in China in 1920s and 1930s. It conf i rms his works’ positive inf l uence on Chinese left wing literary movement, whereas points out the fate of being abandoned by Chinese readers because of his later degradation of being a dutiful subject to the Emperor of Japan. Since 1970s, Chinese literary intellectuals have been re-evaluating Hayama Yosiki’s literary status, but it remains unresolved on how to def i ne his literature critically.
Proletarian writer; carry; intellectual food; subject of the Emperor of Japan
I106
A
2095-4948(2015)02-0017-06
吕元明,男,东北师范大学外国问题研究所教授,研究方向为日本文学。作者于2015年1月因病去世,本文为遗稿。本刊发表此文以此纪念。本文在整理发表过程中得到了日本崇城大学单援朝教授和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日文系2014级硕士研究生罗宵怡的大力协助,特此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