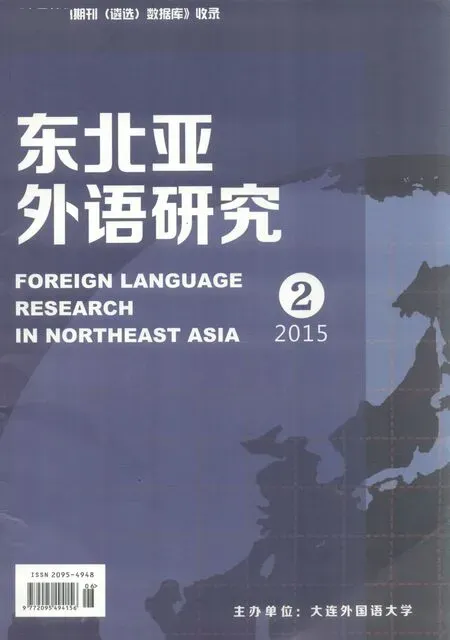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译介
王志松
(北京师范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北京 100875)
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译介
王志松
(北京师范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北京 100875)
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20世纪前半期被大量译介到中国。一直以来,相关研究主要是在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框架中展开的。但这样的研究不仅排斥了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之前和之后的相关理论,也忽视了其与现代派文学的关系,存在很大局限性。因此,本文没有沿用一般文学史上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一词,而使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概念,力图从更广的角度进行把握。本文分三个阶段宏观梳理了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译介情况,并在此基础上从历史社会文化语境的角度揭示了其影响的广泛性和多样性。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日本;革命文学;现代派;法西斯主义批判1
有关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译介状况,迄今大多是个案研究①,缺少整体上的宏观把握。在宏观梳理上最值得关注的是,日本学者芦田肇的著作《中国左翼文艺理论的翻译・引用文献目录: 1928-1933》②该著作翔实辑录了1928年至1933年期间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在中国的翻译以及引用情况,其中大部分与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关。该著尽管出版于1978年,但目前仍然是考察中国接受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最重要的基础资料。该著将资料辑录范围选取在1928年至1933年之间,大概因为此时段正值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和中国左翼文学运动蓬勃展开时期,可以说是抓住了问题的重点。然而不得不指出的是,该著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由于该著聚焦于1928年至1933年间,因此对这一时段之前和之后的状况缺少把握。其次,该著除鲁迅的译著外,主要集中于上海的近三十种杂志的搜录,因此缺少单行本译著的辑录。第三,尤其是忽略了上海以外地区的译介情况。这样实际上直接导致了对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理解的偏差,即主要将其放在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文脉上理解。但这样的理解存在很大局限性。因为这不仅排斥了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之前和之后的相关理论,也忽视了其他领域中的相关理论。因此,本文没有沿用一般文学史上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一词,而使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概念,力图从更广的角度来进行把握。当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概念,并不排斥“无产阶级文艺理论”,而是将它包含其中。要搜罗如此广泛的资料绝非易事,也不是本文在有限篇幅内所能完成的课题。本文将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分为萌芽期(1921-1927)、发展期(1928-1936)和余波期(1937-1945)三个阶段,尽量关注杂志译文与单行本译著、以及上海以外地区的译介情况,作一个总体性的勾勒和评述。
一、萌芽期:民众艺术论与新俄文学的介绍
社会主义思想自19世纪末开始传入中国。1899年梁启超在《自由书》的《中国之社会主义》中,最早提到社会主义和麦喀士(马克思)(梁启超,1989:101)。1903年,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先驱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被翻译到中国。这是第一部译成汉语的系统介绍科学社会主义的著作。此后该著被再三翻译出版,成为许多中国留日学生和早期革命民主主义者受社会主义思想启蒙教育的重要著作(蒋逸人 戴梦桃,1983:22-26)。
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展开,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从1918年进入一个新阶段。在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作理论准备的过程中,日本的相关著作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期间被翻译介绍的著作有大杉荣的《劳动运动的精神》(《北京大学学生周刊》1920年9期,列悲译)、《社会的理想论》(《民国日报·觉悟》1920年1期,罗豁译)、河上肇《马克思之经济论》(《法政学报(北京)》1920年4期,罗琢章译)、山川均《从科学的社会主义到行动的社会主义》(《新青年》1921年4期,李达译)等。如山川均的《从科学的社会主义到行动的社会主义》依据列宁的建党思想阐述了建党理论。山川均(1921:1-4)认为,与达尔文发现生物进化一样,马克思阐明了人类社会的进化过程。“这个社会进化底原则,马克思学徒叫他作‘唯物史观’”。“这唯物史观进化在实际上转动着的枢纽”是阶级斗争。马克思经济学说阐明了资本制度必然崩溃的历程。但资本主义不甘毁灭,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须要由无产阶级来承担推动历史的重任。而对这样的历史重任,在开始阶段只有少数无产阶级才能认识到。他由此论证了建党的必要性。该文译者李达是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之一,出席了第一届建党大会。山川均(1921:4)在附记中专门指出:“这篇文章是日本社会主义者山川均先生特意为本杂志作的,他把行动的社会主义介绍给我们,这实在是一篇最切要的最有效的文字,读者都自然能够知道,用不着我来絮说。”由于该文正好发表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前夕,不难看出该文既对共产党的成立是一个“最切要的最有效的”理论支持,也对一般社会是一个“最切要的最有效的”理论宣传。
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社会主义思想一道也传入中国。目前所能见到最早的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翻译著作是1921发表于《小说月报》上的平林初之辅的《民众艺术底理论与实际》。该文开首便指出:“民众艺术的问题不是纯粹艺术学的问题,乃是今日的艺术的问题。我们不能离开了时代文化来论民众艺术。”(平林初之辅,1921:9)关于“民众艺术”与无产阶级文艺的关系,在日本文坛曾展开争论。1916年,本间久雄(1972:13-21)在《民众艺术的意义及价值》中认为民众艺术是对一般平民乃至工人阶级的教化。大杉荣(1972:26-38)在《为了新世界的新艺术》中则主张民众艺术应该是“民众为了民众创造并为民众所拥有的艺术”。大杉在此所说的民众是指工人阶级。1919年,小川未明、滕井真澄等创办杂志《黑烟》,加藤一夫、福田正夫等创办杂志《劳动文学》,长谷川如是闲等创办杂志《我们》,将“工人文学”的创作推向繁荣。“民众艺术争论”和“工人文学”虽然已经涉及到文学的阶级性问题,但还缺乏足够的阶级自觉意识。1921年,小牧近江和金子洋文等创办同人杂志《播种人》第一次明确竖起“无产阶级文学”的大旗。平林初之辅与《播种人》有交往,致力于无产阶级文艺的理论化工作。《民众艺术底理论与实际》一文显然是在上述争论和无产阶级文学发展新动向的背景下,将“民众艺术问题”切换到“无产阶级艺术问题”进行论述的。关于为什么要提倡无产阶级文学的问题,平林初之辅(1921:13)回答说:“有产阶级是今日的支配阶级,支配阶级维持其位置的战略乃是坚强的守势,乃是维持今日之秩序。有维持今日之目的的,在他们都是宣传。”因此他提出:
对于有产阶级底总动员,非用无产阶级底总动员来对抗不可,(中略)对于资产阶级底科学艺术非用无产阶级底科学艺术来对抗不可。
(平林初之辅,1921:11)
这是中国最早明确提倡无产阶级文学的译文。由于1920年代初,日本也正处于由“民众艺术”转向“无产阶级艺术”的阶段,无论理论还是创作上都处于摸索时期,因此这一时期翻译介绍更多的其实是日本学者关于俄国文学的研究文章。1921年发表于《小说月报》上的升曙梦《近代俄罗斯文学底主潮》介绍了从18世纪到20世纪初俄罗斯文学的演变发展。在第20节“马克斯主义与戈里奇”中指出,在19世纪末俄国文学虽然停滞了,“但这停滞的时代一过,所谓现代文学底黎明期的九十年代又便开始了。自戈里奇等提倡了马克斯主义,社会便生出一道的光明,渐次活动起来。”(升曙梦,1921:18)1922年,片上伸来中国在北京大学作演讲“北欧文学的原理”,后被翻译成中文发表于《晨报》(副刊)(1922年9月25日-27日)。该文虽然主要谈北欧文学,但特别提到俄罗斯文学最新动向:“向来人们对于布尔塞维克主义的主张,以为是一种危险思想,是一种不能实行的空想。然而,他们虽是破坏的——现在且不论其失败或被非难的地方,但新的光明的生活便要从破坏与失败的中间产出来了。”(片上伸,1922)这两篇文章虽然论述的对象不同,但都以无产阶级文学的兴起作为文学史演变发展的新方向来议论的。
从艺术的角度对无产阶级文学的主题和特征尝试探究的文章当推升曙梦的《无产阶级诗人和农民诗人》。该文认为,“无产阶级诗人底诗第一是都市诗。在各诗人里,都能看出要从土地底支配,从田园底家长的宗教的支配离脱的自由解放的气氛。”并比较了田园诗人和都市诗人的区别,田园诗人喜好的题目是耕地或耕夫,都市诗人喜好的题目是工厂、机械、警笛、大众和集团。无产阶级的诗在“集团的火”里燃烧着(升曙梦,1926:846-852)。该文从主题和手法等方面探讨了无产阶级诗歌的都市性质。
第一阶段对译介新俄文学特别用功的是冯雪峰,相继出版升曙梦的《新俄文艺的曙光期》(北新书局,1926年)、《新俄的无产阶级文学》(北新书局,1927年)、《新俄的演剧运动与跳舞》(北新书局,1927年)。
二、发展期:革命文学与现代派艺术
第二阶段是从1928年至1936年。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于1928年杂志《文化批判》和《太阳月刊》同时创刊拉开序幕,之后历经1930年“左翼联盟”成立,至1936年“左翼联盟”解散而落下帷幕。
《文化批判》是创造社系统的杂志,其实《创造月刊》从1926年已经开始向无产阶级文学转变。郭沫若于1926年发表在《创造月刊》上的《革命与文学》一文,被李初梨(1928:150)看作 “是在中国文坛上首先倡导革命文学的第一声。”郭沫若(1926:1-11)在该文中论述了文学与革命之间的关系,认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革命文学,当下的革命文学就是无产阶级文学。郭沫若之所以写就这篇论文不是一时兴起,早在1924年就曾翻译过河上肇的《社会革命与社会政策》(《学艺》1924年6期),已经开始关注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值得一提的是,郭沫若的《革命与文学》写于广州,当时正值国共联合进行北伐时期,是革命运动的高潮时期。革命运动的高潮之际,许多文人投身实际的革命运动,因此并没有出现革命文学。当共产党的革命与国民党的革命出现分歧,并于1927年遭到失败后共产党的革命阵地出现两个大转移:其一是转移到农村进行武装斗争;其二是转移到城市进行文化斗争。因此,1928年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勃然兴起绝非偶然。
从新文化发展的角度看,无产阶级文学的兴起也有其内在逻辑。李初梨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中系统地梳理了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革命运动的历程。他认为,中国十年前的文化运动,实为当时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之争,他们的口号是塞先生和德先生。塞德二先生,是资本主义意识的代表,所掀起的文学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但“欧战告终,帝国主义列强的魔手又复伸到东方的中国。中国资本主义的发达因之又停滞起来。国内的布尔乔亚对外既不能与帝国主义列强竞争,对内又不能与封建势力对抗;在这样困难的状态当中,他们为自存起见,遂不得已向封建势力投降——妥协;而他们的革命能力,从此消失。”(李初梨,1928:164)因此,在他看来现在能担当起革命重任的是无产阶级。接着他就在文中对十年前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周作人等展开了排炮般的轰击。
后期创造社对鲁迅等作家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现在看来确有偏激之处。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由此形成的革命文学争论却起到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效果。争论各方为了加深认识无产阶级文学的性质、发展方向和创作方法,大量翻译介绍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其翻译介绍的特色主要有以下三点:
首先,以问题为向导进行翻译。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兴起之初,急需了解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性质和创作方法,因此在1928年和1929年间较为集中地翻译介绍了这方面的论著,如藏原惟人《到新现实主义》(《太阳》1928年7期,林伯修译)、田口宪一《日本艺术运动底指导理论的发展》(《我们月刊》1928年3期,林伯修译)、青野季吉《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开展》(《乐群》1929年9期,陈勺水译)、藏原惟人《普罗列塔利亚底内容与形式》(《海风周报》1929年10、11期,林伯修译)、升曙梦《现代俄国文学思潮》(北新书局,1929年,陈叔达译)、片上伸《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大江书铺,1929年,鲁迅译)等。尤其是藏原惟人的相关论文被翻译介绍后影响广泛,即刻被运用到解决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创作和大众化问题上(王志松,2007:111-134)。另外,陈勺水翻译的青野季吉《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开展》也值得关注。 该文概述了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理论发展的过程,其中包含对“目的意识论”的反省:
从实事看来,那时期的理论的努力仍然带着很重的机械性的偏向。举例说,在组织上,把无产的文学团体误认为先锋的组织,在文学理论上,竟由一部分人倡导着所谓“进军喇叭主义”,等等事情,就是显著的例子。这种偏向的责任,一部分固然由于提倡人的提倡方法,太过于简洁,然而一部分也未尝不由于那时的人们把文学并文学的运动不看成文学和文学运动,倒盲目地把当时在政治理论界最有势力的以谓务(应为“福”——引者注)本主义的机械的并合式的理论,贸然应用到文学并文学运动上面去。
(青野季吉,1929:11)
在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发展过程中,青野季吉提倡的“目的意识论”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青野在1926年发表的《自然生长和目的意识》中提出,无产者的创作如果仅仅停留在满足个人的表达欲望的程度上,还不能称其为无产阶级文学。只有当作者自觉地认识到无产阶级斗争的目的时,其作品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艺术。即是说,在社会主义思想的引导下,为了阶级利益而进行创作时,才会产生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因此,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是对自然发生的无产阶级文学注入“目的意识”的运动,并由此让全体无产者参加阶级斗争的运动(青野季吉,1967:77-78)③。这篇文章在日本不仅引起激烈争论,还引发了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一系列分裂。青野季吉的“目的意识论”和“福本主义”传入中国,成为后期创造社攻击鲁迅等作家的主要理论根据。因此,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翻译介绍“目的意识论”提倡者本人的自我反省,显然对于纠正后期创造社的偏激行为有重要的意义。1930年“左翼联盟”的成立,既有共产党组织的努力,应该说也与这样的理论准备分不开。
又如,从1931年底文坛爆发关于“第三种人”的争论,论战双方所据理论均有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理论。为了廓清其中的问题,一些译者也有意识地翻译介绍了相关论著,如藏原惟人《关于艺术作品底评价问题》(《北国月刊》1932年2期,王集丛译)④、川口浩《文学的党派性》(《文艺月报》1933年创刊号,张英白译)、藏原惟人《新艺术的内容与形式》(《四高中校刊》1933年7期,王贞谔译)等。其中,藏原惟人《关于艺术作品底评价问题》这篇文章其实此前已经被翻译过两次,但这次重新翻译发表时译者王集丛特地说明:“前两年日本的文坛发生了一个新的论战,这论战直到现在尚未完全结束。(中略)在这次日本的文艺论战中所争论的问题,与目前中国文坛上的一切理论纠纷都很有关系。因此,我很想把这次日本文艺理论论战的各方面的理论用中文翻译出来,以供中国一般文艺爱好者之参考。”(藏原惟人,1932:1)
其次,超越阶级文学的范畴对现代派文学和现代文化产生广泛影响,翻译介绍了许多都市社会与当代文化的论著,如片上伸《都市生活与现代文学》(《北新》1928年20期,侍桁译)、平林初之辅《文学及艺术之技术的革命》(大江书铺,1929年,陈望道译)、岩崎昶《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萌芽(新地)》1930年3期,鲁迅译)、板垣鹰穗《机械美》(《当代文艺》1931年3期,陈望道译)、岩崎昶《电影与资本主义》(《明星(上海)》1933年2期,伊文译)、《电影艺术学之史的展望》(《微音月刊》1933年1期,曼青译)等。
需要指出的是,最早关于欧美现代派艺术的系统介绍并不是来自于现代主义流派的著作,而是藏原惟人的《向新艺术形式的探求去:关于无产的艺术的目前的问题》。藏原(1929:1-35)在该文中指出:“个个时代,个个阶级,在他们发达的各阶段上,都发见了,创造了他们各自的‘美’。(中略)近代的,有了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发见出来,并替我们留下来的美,就是大都会和机器的美。”以此为前提,藏原在该文中分析了资本主义背景下各种现代派的形成和特点,认为不少现代派的艺术手法表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尤其对未来派的“诗语”特征作了精当的三点概括:节奏快,充满力量,富于感性。他分析说,未来主义文学派的诗人为了加快语言的节奏,破坏文章的规则,删除所有无用的词语,如形容词、副词、标点符号,喜欢罗列名词和使用原形动词。为了突显力量,他们不停留于单个形象的描写上,而是同时捕捉各种形象揉在一起。为了表现人体感觉,喜欢使用拟声词、各种音乐和数学的符号。藏原断言,如果有人认为无产阶级艺术可以在陈旧缓慢的节奏、非力学的形式中发展,那他就大错而特错了。因为近代无产者在工厂和各种无产者组织机构中劳动,他们当然具有力学的、敏捷的、正确的、合理的、合目的的感觉和心理。这种敏捷、力学、正确、合理性和合目的性的表现形式理所应当放入艺术的形式之中。该文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对当时的现代派文学和都市文学产生了影响⑤。
再次,翻译介绍的地域广阔。左翼联盟的总部在上海,文学活动和翻译活动展开最活跃的也是上海,因此芦田肇的《中国左翼文艺理论的翻译・引用文献目录: 1928-1933》将收录范围限定在上海的期刊杂志不无道理。但左翼联盟除上海总盟以外,还先后建立北平左联(又称北方左联)、东京分盟、天津支部,以及保定小组、广州小组、南京小组、武汉小组等地区组织,因此也不可忽视这些地区的文学活动。其中,北平左联和东京分盟的活动也相当活跃。北平左联创办机关刊物《文学杂志》、《文艺月报》等,东京分盟办有《东流》、《新诗歌》、《杂文》(后改名《质文》)等。在这些刊物上可以查找到以下翻译著作:川口浩《文学批评上的几个问题》(《文艺月报》1932年2期,里正译)、秋田雨雀《接受文学遗产的两个方向》(《杂文》1935年2号)、永田广志《文学与哲学·世界观》(《杂文》1936年5、6号合刊,晓雨译)、熊泽复六《高尔基创作中的浪漫主义》(《东流》1936年2期,梁蕙译)、熊泽复六《高尔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东流》1936年2期,梁蕙译)、小林多喜二《墙头小说与“短”的短篇小说》(《东流》1936年2期,叶文律译)等。
从时间上看,北平左联的《文艺月刊》发表译著的时间主要集中在1932年,而同一时期在上海的期刊上发表无产阶级文学的翻译论著很少。其主要原因大概是1931年左联在上海受到国民党政府的镇压后暂时无法发表,北平左联的相关杂志则承担起了相应的宣传功能。东京分盟的《东流》和《杂文》上发表的文章主要集中在1935年至1936年,而这一时段国内几乎没有发表。究其原因,大概由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在1934年相关组织已经解体,国内无法捕捉到新的信息,而身处日本的东京分盟则能够把握其中的一些新动向。由此看来,如果不对上海以外地区的情况进行调查,难以全面把握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接受的全貌。
三、余波期:对法西斯主义的剖析与批判
随着1936年左翼联盟解散和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译介急剧减少。第三阶段的主要译著如下:户坂润《作为认识论的文艺学》(《时事类编》1937年7期,楚客译)、《日本思想界及思想家》(《时事类编》1937年11期,宋斐如译)、鹿地亘《文学的感想》(《战地》1938年5-6期,魏猛克译)、《关于“艺术和宣传”的问题》(《抗战文艺》 1938年6期,适夷译)、《何谓东亚协同体》(《国民公论(汉口)》 1939年1期,朱洁夫译)、《日本法西斯蒂长期建设论的批判》(《建设研究》1939年4期,夏孟辉译)、《日本反侵略作家鹿地亘及其作品》(新国民书店,1938年,衣冰编)、森山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论》(希望书店,1940年,林焕平译)等。
上述译著除森启山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论》外,其余全是户坂润和鹿地亘的著作。究其原因,与这两位作者独特的理论路数和特殊的处境有关。先看户坂润。户坂润曾师从西田几多郎研读哲学,并受欧洲存在主义和现象学的影响,尔后转向马克思主义研究。因此,他对文艺理论的思考从一开始就和单纯地受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影响的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主流不同。这种角度的不同,使得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独具特色,也使得他在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失败后仍然能够继续从事文艺批评,成为“暗谷”时期抵抗法西斯主义文艺的极少数知识分子之一。1945年,他遭受日本法西斯当局迫害死于狱中。
被翻译介绍到中国的户坂润的这两篇文章选自他的论文集《日本意识形态论》。该论文集对1930年代流行于日本的主要思潮——日本主义、法西斯主义和自由主义展开辛辣的批判。当时,许多日本知识分子批判法西斯主义,但并不批判日本主义和宗教主义,更是热烈拥护自由主义。户坂的批判则紧紧抓住日本自由主义的特殊性展开论述。他说,自由主义本来是经济和政治上的范畴,但日本的自由主义却剥离了这两个范畴。在此,自由主义通过宗教意识为媒介,转变为一种“宗教主义”。而当它与日本的绝对君主制相结合时便产生日本主义,最终蜕变为“法西斯主义”(戸坂潤,1966:228-229)。
在从自由主义蜕变为法西斯主义的过程中“文学主义”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1933年,无产阶级文学运动遭到当局镇压而退潮,同年10月武田麟太郎和林房雄从个人主义、艺术主义的立场出发,邀请小林秀雄、川端康成等人,共同创办了《文学界》(第二次)。随后,横光利一、阿部知二、岛木健次、村山知义等也先后加入了这一行列。他们针对此前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出现的政治化倾向,提出了要拥护纯正的文学权利。从当时的文学创作看,一度被无产阶级文学否定的私小说随着“转向文学”的产生又复苏了,在审美取向上表现为回归传统美学。另一方面,在思想界和社会科学研究方面也出现回归传统价值观的倾向。这些动向被称为“文艺复兴”。但户坂(1966:362)认为,这些现象非但不是“文艺复兴”,反而是正在危险地滑向法西斯主义。因为西洋的“文艺复兴”的核心是恢复人的理性精神,但日本“现在的‘文艺复兴’与之完全不同,复兴的只有宗教、神学和形而上学等”,而以对抗西洋文明为名,要打倒的权威却是科学精神。因此户坂并不认同“文艺复兴”的提法,而讥之为“文学主义”。在被译成中文的《日本思想界及思想家》这篇文章中可谓集中了户坂润的最主要的观点。户坂在该文中批判说:
文学主义本来是相当于文学的自由主义的一种。原来日本的近代文学依其对封建道德的观念上的批判任务而一般以自由主义为本流。(略)丰岛与志雄、广津和郎、菊池宽是最有意识的自由主义者。不安文学的一派人,乃至比较积极的发动主义的一派人,也都属于自由主义者。并且这个自由主义的意义本身就是文学的,必定是决定地和政治行动上的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是必然发展到民主主义的追求)分离的自由主义。即令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在这里也不过是完全的超政治的文学概念的自由主义。——但是这种文学的自由主义意料之外的,有与法西斯主义相通之道。所谓能动精神有此危险性是今日差不多一切人所警戒的地方。不安文学等也都经过良心及人间性到达道德的宗教。一切意义上的宗教现在的作用,自客观上说来实际已经不是自由主义了。
(户坂润,1937:83-84)
户坂对1930年代中期日本出现的“文艺复兴”现象的认识可谓切中要害,超越时代至今仍然是最犀利尖锐的批判。
另一位作者鹿地亘的境况比较特殊。鹿地亘因从事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于1930年代初在日本被捕入狱,出狱后来到中国上海。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开始后,离开上海,经由香港来到武汉,后又到重庆,一直在中国从事反战活动。因此,他对日本法西斯政府的批判更为直截了当。在文艺评论上值得关注的是《文学的感想》一文。他在该文中分析了1930年代日本文坛上流行的“不安的文学”。鹿地亘(1938a:130)认为,日本不安的文学虽然受到欧洲不安文学的影响,但两者的立足点不同。欧洲的不安文学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主要是对过去的价值观崩溃而产生的迷茫,但同时也包含了“伴着摸索新的立脚点的绝望底斗争。”而“在日本却是相反的。在从来革命文学运动退却的知识阶级之间,是因为防卫现代的世界观的困难而产生了不安。因此,就没有摸索新的立脚点的必要。也没有绝望底斗争的必要。想逃出不安是只要放弃立脚点,中止斗争就成了。”也就是说,“不安的文学”在日本仅仅是遭到政府镇压后的一种退却,脱离人民龟缩进自我的小圈子。鹿地亘对日本主义的批判角度与户坂润不同。户坂润是从哲学层面进行的剖析,而鹿地亘则是从与脱离人民的角度进行分析的。该文对日本政府的御用文人——“笔部队”也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在日本军阀占领地带,便有称为宣抚班者活动着,这是负担了制造汉奸的任务的政治底教育部队。”这可能是日本作家最早对笔部队的批判。鹿地亘发现,笔部队中最有成绩的是“左翼转向者”。因此鹿地亘(1938b:163)认为,“军事法西斯蒂政府,充分参考着这种经验计划着把全国数万的‘转向者’送上大陆。”
但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是否就彻底崩溃了呢?鹿地亘(1938b:164)说,自己曾失望过,也咒骂过日本文学界,但通过中野重治他发现了新的希望。鹿地亘知道中野重治的“转向”,但令鹿地震撼的是,中野并不回避这一问题,而是承认了自己对劳苦大众的背叛。中野认为,自己重生的前提必须是对背叛行为的深刻反省。鹿地亘从中野的这种态度上敏锐地意识到,后续的斗争或无产阶级文学的重建只能建立在中野这种对“转向”的反思之上,因此在他的暗影里的额上,发现了“有一种严肃的光辉出现。”当然限于当时的条件,鹿地并没有明确指出这种可能性到底是什么。虽然关于“转向”问题在思想上的意义在战后才真正展开深入的思索⑥,但在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失败的时期,能够指出无产阶级文学发展新的可能性也实属难得。
尽管第三阶段的翻译作品数量大幅度减少,但从相关译文能够了解到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暗谷时期的新动向。这些著作不仅依然保持了批判锋芒,并且其中不少观点已经孕育了战后文化思想发展的新萌芽。
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20世纪前半期被大量译介到中国,不仅促进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发展,对中国的现代派文学乃至一般现代艺术也产生广泛影响,构成中国现代文化的重要篇章。但迄今的相关研究主要考察与上海左翼联盟的关系,因此难以全面把握这种影响跨越地区、跨越文学流派和艺术种类的广泛性以及多样性。许多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译著不仅在当时推动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发挥积极作用,也有不少关于现代性的思考和批判至今依然是有效的思想资源。本文分三个阶段宏观梳理了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译介情况,从历史社会文化语境的角度揭示这种影响的广泛性和多样性。限于篇幅许多问题都是点到为止,今后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考察。
注释:
① 主要有以下论著:斋藤敏康.1983.福本主义对李初梨的影响——创造社“革命文学”理论的发展[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3):339-360;艾晓明.1988.后期创造社与日本福本主义[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3):138-161;黎活仁.1990.福本主义对鲁迅的影响[J].鲁迅研究月刊,(7):12-21;张福贵.1991.青野季吉的“目的意识”论与李初梨的“革命文学”观[J].吉林大学学报,(2):76-81;熊文莉.2004.藏原惟人理论的翻译和革命文学[A].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文学研究室编.日本文学翻译论文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王成.2010.“直译”的“文艺大众化”——左联“文艺大众化”讨论的日本语境[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4):27-40;王志松.2012.20世纪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徐秀慧.2013.左翼文本的文化翻译与现代性——鲁迅与瞿秋白的左翼文学理论翻译初探[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5):118-122;陳朝輝.2004.魯迅と上田進——魯迅の日本プロレタリア文學受容に關する一考察[J].東方学,(107):137-152;陳朝輝. 2005.中国における片上伸受容史試論:プロレタリア文学の様式と内容を探求する人々[J].東京大学中国語中国文学研究室紀要,(8):92-117;陳朝輝. 2009.魯迅と藏原惟人[J].東方学,(117):118-138;陳朝輝. 2009.魯迅が見た日本プロレタリア文学[J].国文學:解釈と教材の研究,(1):17-29;長堀祐造.2011.魯迅とトロツキー:中国における「文学と革命」[M].東京:平凡社。
② 芦田肇『中国左翼文芸理論における翻訳・引用文献目録: 1928-1933』(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附属東洋学文献センター,1978年)。此外值得关注的还有刘柏青《三十年代左翼文艺所受日本无产阶级文艺思潮的影响》和徐秀慧《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旅行(1925-1937)——以日本、中国大陆与台湾“文艺大众化”的论述为例》,主要关注的是左联对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接受。(芦田肇.1978.中国左翼文芸理論における翻訳・引用文献目録: 1928-1933[M].東京: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附属東洋学文献センター;刘柏青.1981.三十年代左翼文艺所受日本无产阶级文艺思潮的影响[J].文学评论,(6):102-109;徐秀慧.2013.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旅行(1925-1937)——以日本、中国大陆与台湾“文艺大众化”的论述为例[J].现代中文学刊,(2):34-46.)
③ 青野季吉的「自然成長と目的意識」最初发表于『文芸戦線』(1926年9月),本文参考『現代日本文学全集55』第77-78页。
④ 该文原标题是「マルクス主義文芸理論の旗の下に―芸術作品の評価について―」,最初发表于『近代生活』(1929年8月),本文参考『蔵原惟人評論集』第一卷第300-311页。(蔵原惟人.1966.蔵原惟人評論集第一巻[M].東京:新日本出版社.)
⑤ 关于接受无产阶级文学与现代派文学的交汇影响问题,参看邝可怡《两种先锋性理念的并置与矛盾——论《新文艺》杂志的文艺倾向》和王志松《刘呐鸥与“新兴文学”——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接受为中心》。(邝可怡.2012.两种先锋性理念的并置与矛盾——论《新文艺》杂志的文艺倾向[J].现代中文学刊,(1):41-56;王志松.2013.刘呐鸥与“新兴文学”——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接受为中心[J].山东社会科学,(10):82-88.)
⑥ 参阅王志松《“转向”与本土化——日本文化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王志松.2005.“转向”与本土化——日本文化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J].日语学习与研究,(3):64-69.)
参考文献:
[1] 青野季吉.1967.現代日本文学全集55[M].東京:筑摩書房.
[2] 戸坂潤.1966.戸坂潤全集第2巻[M].東京:勁草書房.
[3] 大杉栄.1972.新しき世界の為の新しき芸術[A].遠藤祐等編.近代文学評論大系5[C].東京:角川書店.
[4] 本間久雄.1972.民衆芸術の意義及び価値[A].遠藤祐等編.近代文学評論大系5[C].東京:角川書店.
[5] 郭沫若.1926.革命与文学[J].创造月刊,(3):1-11.
[6] 户坂润.1937.宋斐如译.日本思想界及思想家[J].时事类编,(11):77-86.
[7] 蒋逸人 戴梦桃.1983.《社会主义神髓》的中译问题及其它[J].浙江学刊,(1):22-26.
[8] 梁启超.1989.饮冰室合集6 自由书[M].北京:中华书局.
[9] 李初梨.1928.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A].霁楼编.期革命文学论集[C].上海:生路社.
[10] 鹿地亘.1938a.魏猛克译.文学的感想(一)[J].战地,(5):129-131.
[11] 鹿地亘.1938b.魏猛克译.文学的感想(二)[J].战地,(6):163-167.
[12] 片上伸演讲 川岛笔记.1922.北欧文学的原理[N].晨报(副刊),1922-9-27.
[13] 平林初之辅.1921.海晶译.民众艺术底理论与实际[J].小说月报,(11):8-13.
[14] 青野季吉.1929.陈勺水译.论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开展[J] .乐群,(9):1-22.
[15] 山川均. 1921.李达译.从科学的社会主义到行动的社会主义[J] .新青年,(1):1-4.
[16] 升曙梦.1921.陈望道译.近代俄罗斯文学底主潮[J].小说月报,(12卷号外):1-20.
[17] 升曙梦.1926.画室译.无产阶级诗人和农民诗人[J].莽原,(21):846-852.
[18] 王志松.2007.“藏原理论”与中国左翼文学[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3):111-134.
[19] 藏原惟人.1929.陈勺水译.向新艺术形式的探求去:关于无产艺术的目前的问题[J].乐群,(12):1-35.
[20] 藏原惟人.1932.王集丛译.关于艺术作品底评价问题[J].北国月刊,(2):1-8.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Japan’s Marxism Literary Theory in China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Japan's Marxism literary theory was intensively introduced to China. By now, related studies have been focu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Proletarian Literature Movements. But such researches have many limitations. Not only have they excluded the related literary theories appearing before and after Proletarian Literature Movements, but also they have neglec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letarian Literature Movements and Modernism. For this sake, instead of using the phrase “Proletarian literature theory”which is frequently referred to in literary history, here the concept of“Marxism literary theory” is chosen so that much more aspects can be explored from this subject. This article combs the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situation of Japan's Marxism literary theory in China in three phases, and reveals the universality and variety of its inf l uence in the context of socio-history and culture.
Marxism literary theory; Japan; revolutionary literary; modernism; criticism of Fascism
I106
A
2095-4948(2015)02-0010-07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日本近代文论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研究”(12JJD750008)的阶段性成果。
王志松,男,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日本文学和中日比较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