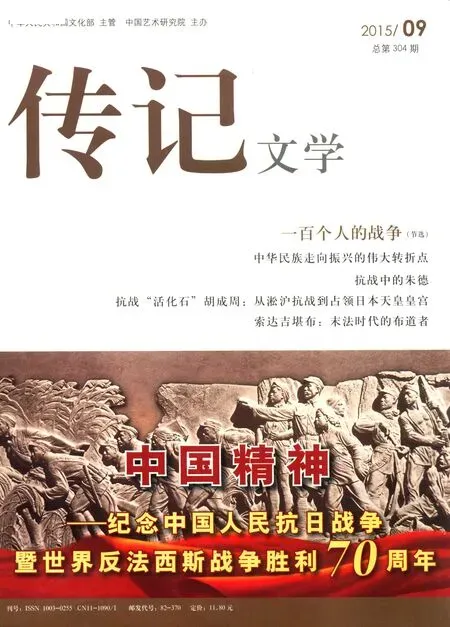炼 形
文 陈玉圃
炼 形
文 陈玉圃

大仙 陈玉圃 作
诗需炼字,字则珠玑;画需炼形,形则传神。中国画对于形的认识历来有独特的看法。苏轼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齐白石也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贵在似与不似之间。” 这里的“似”与“不似”皆是相对于客观物象而言。绘画本来就是形的艺术,其实,“似”与“不似”皆形也,只是有具象与抽象的差别罢了。而齐白石说之“似与不似之间”的形,即是画家所炼之形。
中国画这种以“似与不似之间”为形之品评标准的独特艺术观点,大略是来自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来自佛学的影响。《金刚经》认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相就是形象,说其虚妄是因为形器世间,也就是物质世界的一切,无时不在变化中。所谓“四大皆空,五蕴非有”,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一分钟也不曾暂停,就像是梦幻泡影般把握不定,而世人不知其幻,往往穷毕生精力去追逐、迷恋、竞争,实在是愚迷之极。所以佛陀慈悲为怀,指导众生抛弃其虚幻,而回归那个真实不虚、如如不动的本体。这就是中国画所以不重视“形似”的理论根据,因为“形似”只是事物的表相而已。但是,既然这实有的物质世界(也就是有、形似)并不可信,那么彻底否定它(也就是绝对空,即不似)对不对呢?也不对,那是因为世间万物在一定时空条件下,视之有色,闻之有声,触之有物,又的确明明白白地存在着,所以无论有,还是空,都不是绝对正确。那么正确在哪里呢?其实正确也并不离乎空和有。所谓“道不可离,可离非道”。那么惟有不离空、有,亦不执着空、有,从容中道,才是接近正确的途径。从绘画而言,这和齐氏“似与不似之间”的审美观点不是若合符节吗?只是这个“似与不似之间”,既不是形似,也不是不形似。且不可误解为一半形似,或一半不形似,而是似与不似之形的融会与升华,是画家真性情,即精神气质与山川真景物的巧妙结合和再创造,是真形的熔铸和提炼,即所谓之炼形也。
形有万状百态,画有美丑妍媸,然而妍媸美丑皆属表相,不可凭借,画虽以真善美为标准,然毕竟以真字贯穿始终。故中国画尚质朴,忌浮华,尚内美,忌粉饰,多有寓美于丑、怀真于朴的造型格致,就像黑头钟馗、虬髯张飞的形象分外讨人喜欢一样。即便是貌若天仙的西子、王嫱,如果涂上了一脸厚粉,也会大煞风景。还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为好。画如此理,所以,中国画之炼形的标准,颇有宁拙勿巧、宁丑勿美之倾向。是以有青藤、八大、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诸大家出,一个个蓬头垢面,如散僧入圣,胸藏风云者也。但此所谓拙者非拙,是大巧若拙,此所谓丑者非丑,是真美寓于丑也,是皆可为炼形者参照。“且山水之大,广土千里,结云万重,罗峰列嶂,以一管窥之,即飞仙恐不能周旋也。”所以必当“测山川之形势,度地土之广远”,约略众形,取其概要,然后“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也”。所以形愈简,而神愈全。形简如筛糠见米,去伪存真;神全则遗貌忘形,灵光独回。不去伪难以显真,不简形何以全神?所以简形就是全神,全神全赖炼形也。于是,万仞之山,寥寥数笔可取其形势;百尺之泉,仅留寸白线可状其仿佛。长松挂壁,笔出斜势传神;游人隐现,约略数点即成。至于亭谢、楼台、桥梁、舟车,皆不可以谨毛失皮,皆当以概括、约略之法炼其形。清画家恽南田这样说:“画以简为尚,简之入微,则洗尽尘滓,独存孤迥,烟鬟雾鬓,敛容而退矣!”可见,炼形之功,又不惟全神也,尤其可以避免俗气,创造高雅之境界。我们翻看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尤其是八大山人的《山水册页》,其中之形可谓简之又简,而画家真性则油然逸出画外,此即炼形之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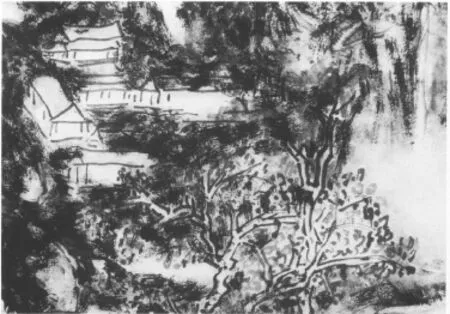
黄宾虹作品局部黄氏画真可谓“简之入微,洗尽尘滓,而独存孤回”者也,格调高雅,脱尽凡俗。观其所作房舍、树木,造型简练,几乎等于符号。其笔如画砂,便捷明白,而书意盈然,此即画家修养与心态所炼之形。黄氏虽经乱世,而毕竟与八大山人不同,故其画虽日高逸,却不失温润冲和之气。

明·八大山人《山水花果》之一八大山人忍亡国破家之痛,隐遁山林,以笔墨宣泄胸中不平,顾其画虚寂凄清,逸出尘外。其用笔旷达野逸,其造型约略简圆,其墨润冷隽苍凉,是皆因其情绪心态所炼之形也。所谓“画如其人”,诚不我欺。
由于画家的情绪、气质、世界观、文化素养、审美品位,以及地域、风土人情、师承等因素的差异,画家对于“形”艺术语言的锤炼格致亦有所不同,或严谨、或洒脱、或高逸、或朴拙、或苍秀、或萧索,于是有董巨之蕴藉,荆关之雄奇,八大之冷峻,倪迂之飘逸;于是有刘李马夏、王黄倪吴、石涛、石溪……于是有变幻新奇、丰富多彩的中国山水画艺术形式,其炼形之功,不亦伟哉!

山静居图 陈玉圃 作
有一点需要说明的,那就是切不可把“炼形”误认为是“变形”。“炼形”和“变形”虽一字之差,却是意旨殊别。当代风行的变形说,是为变形而变形,是主张装饰趣味的工艺手段之一。多有做作扭曲、以丑怪为美者。其实丑和美是一对完全不同的概念。甚至有人以“丑即美,美即丑”的诡辩来混淆其界限。我们所说,张飞、钟馗之黑丑,仅是表面现象,而其正直、善良、勇敢、仁爱的品德和真率的性格,则组成了他们内美的特质。世人所喜爱的是其内美,是内在的真与善,并非黑头、虬髯的表相。只是出于对其真与善的顶礼膜拜,以至可以爱屋及乌罢了,更何况黑头、虬髯并非真丑也,而是一种雄放大气的美质。且黑头虬髯的内层,却又显露出笔墨韵律的形式美感,故不可以以丑视之也。如果仅仅是为了追求丑怪,甚至以丑怪为美的话,那不是糊涂,就一定是误会了。如八大山人的山水画,因其特殊的社会经历,而厌倦了尘世之喧嚣和扰攘,故其逃世的心态在他画作中表现出寂寥,甚至萧索的境界。其实寂寥萧索乃是一种美的格致,可以使人发世外之思,是逸士高人心态的真实表露。至于有人故作混乱浊败之笔,作乌烟瘴气之境,渲染出世界末日般的气氛,也许,这也是一种说教,但却失去了绘画艺术“尚美”的特质,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艺术以真善美为依归,真善是其内质,形美乃真善之表露。所以中国画所谓炼形,是以画家之真与善所炼之形也。因其重其内质(即真与善)而忘乎形之妍媸可也,即所谓“得意志形”。因其忘,故能随内美之驱使,即使变现妍媸美丑而皆不失其自然之趣也,与故意做作、以丑为美者当不可相提并论。
责任编辑/斯 日
——评朱良志先生《八大山人研究》(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