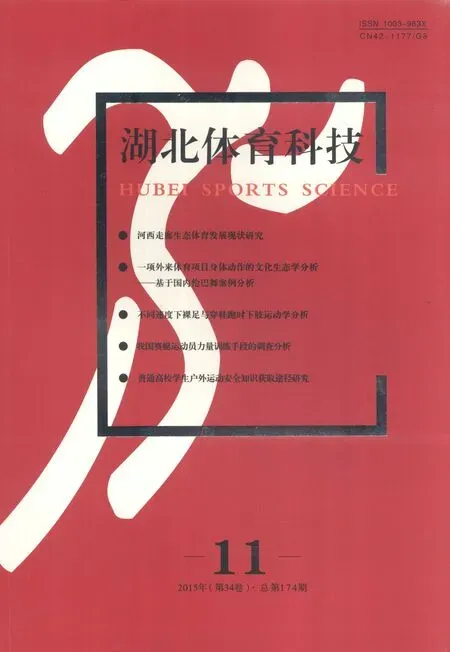土家族跳丧舞的体育文化学意义
覃兴耀
“跳撒叶尔嗬”是广泛流传于湖北清江流域的丧葬仪式舞蹈,或称“打丧鼓”、“丧鼓歌”,现有资料表明“跳撒叶尔嗬”已有大约3000多年的历史,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土家先民巴人的丧舞和军歌军舞。土家族分布区特殊的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土家族特有的生死观、价值观和道德观造就这种独特的仪式文化。“跳撒叶尔嗬”建构在图腾崇拜与祖先崇拜之间的文化心理的行为上,以其古朴的气息传达独特的生命价值观和原始群体意识。民族的民风民俗以及表达情感的方式,一般来说是风格迥异,浓郁鲜明,亦大体符合喜则乐、悲则哀的通常景象。但土家族在大喜大悲的时刻,做出了超乎想象的情感表达方,一是以悲托喜的“哭嫁”,一是以喜寄哀的“跳丧”。
跳丧与体育似乎是毫不沾边的,跳丧仅仅是一种较为特别的情感表达方式,一种仪式文化,一种生命哲学观。但事实上,做一点简单的比较就可以清楚地发现二者在内核上有许多交融的地方。《体育概论》在论及体育产生的多源性时认为“体育产生于人类社会生活的2种需要:……,另一种是人类生理、心理活动的需要”[1],而跳丧也正是土家族人在亡人面前对生理和心理活动的表达,是一种对生命意识的仪式化表达。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会用身体活动来渲染他们的酒神狄俄尼索斯的狂欢文化;跳丧——“绕尸歌舞”,同样是以身体活动在亡人面前倾述一种欢娱。在发生学意义上,它们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因此土家族跳丧舞的体育根基是存在的。随着人们对它的认识和开发,它成为民族民间体育项目的潜力是存在的。
1 基础——身体活动
跳撒叶尔嗬是否具有体育文化学的意义,首先应当明确它是否满足体育文化的要求。体育文化是社会整体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由表层运动形式,包括身体运动形式及所使用的场地、器材等物质形态;中层体育体制,包括体育的社会组织、教学训练、管理等;深层体育观念,包括身体观、运动观、价值观、方法观等要素构成。严格说来,跳丧舞不具备完整意义上的体育文化要求,它在简单的身体运动形式上是满足的,在组织、训练、管理层面是不满足的,在深层的体育观念上也只是简单满足,但这并不能完全否定它具备和成为一种大众健身娱乐项目的发展潜力。
尽管当前对体育概念的定义还未统一,但其核心是确定的,即身体运动。跳撒叶尔嗬的身体运动形式是具体的,即是以“歌、乐”辅之,在丧葬上的“跳”和“舞”。在谷深林密的土家村落,一旦有哪家有老人过世,不分死者性别、不分声望高低、不分职位尊卑,乡邻们都要怀着虔诚的心情赶去为死者 “跳丧”(跳撒叶尔嗬)。在死者棺前空地上,或2人一组、或多人同跳;一人站在棺侧击鼓并领唱,或多人配合击鼓打锣并领唱。跳舞者在前面合着鼓点、锣声,边唱边舞。舞者其头、手、肩、腰、脚一齐动作,全身有规律的颤抖,双肩上下耸动扭挫,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如痴如醉,忘乎所以。随着鼓点、锣声的节拍和唱腔曲牌的变化,舞者也随之变换舞步,和着古老粗犷的唱词。唱词基本上不涉及令人伤感的事,多为颂先民的斩草创业、开辟家园事迹;或述山乡的渔猎农耕生活;或赞死者生平的高尚人品;或扬美丽爱情故事;或诵本族历史和“图腾”崇拜的叙事诗,整个现场气氛欢悦、格调明快,少有悲伤之情,真正个热热闹闹陪亡人,欢欢喜喜办丧事。
“跳撒叶尔嗬的舞姿以 ‘曲’、‘颤’、‘靠’、‘转’ 而独具一格,除了‘跑场子’和‘四大步’等基本套路之外,多为模仿走兽、飞禽、鱼虫、灵怪、人物的动态”[2]。据说一共有六十多个套路,其中很多的套路和动作,与我国传统武术中的动作相似,但更多的是对劳作生活的观察、模仿和高度概括,同时使其娱乐化。如“牛擦氧”,二人背靠背,双手叉腰,左右相对擦晃,腰胯以下作慢幅度颤动,稳健明快。“凤凰展翅”,二人背对背,上下扇动,恰似凤凰展翅,其动作含蓄,隐喻力强。“燕儿衔泥”,在地上放一手帕或一枝香烟或一樽酒,一人叉开双腿站立,随着鼓点的急骤而动,慢慢下腰,最后以嘴近地衔物,双手后伸作燕儿翅膀扇动状,反复数次。除此之外,其余如“猛虎下山”、“白鹤展翅”、“鹞子翻身”、“犀牛望月”、“蜻蜓点水”等,这些动作形象逼真,矫健敏捷,要做到准确到位,对跳舞者的身体条件要求甚高。在“跳撒叶尔嗬舞”中,且歌且舞,舞姿浑朴、淳厚、古雅。“整套舞蹈都保留着溜边、含胸、曲膝的特点,这也是由于在鄂西湘西溪峒中长期背负托重、攀岩爬山的生活习惯所演化而来的,所以具有有别于其他民族舞蹈的明显特点”[3]。
目前,关于跳撒叶尔嗬对身体机能的影响的实证研究成果尚不丰富,蒋在爽在《土家族巴山舞练习对老年女性BMI及血脂的影响》一文中作了初步的研究,认为长期参加巴山舞(由跳丧舞改编而来)练习,“可使老年女性体重减轻,体脂减少,血压降低,改善心血管系统和呼吸系统的功能”[4]。除了在此方面研究的弱势外,跳撒叶尔嗬在两方面是确定的,一是跳撒叶尔嗬是以身体活动为基础的一种舞蹈形式,二是以歌舞送丧,无论是对亡人的家属,还是对舞者本人,在身心方面都是一种愉悦,因此它具有体育文化学意义的表层形式。
2 主线——文化传承
仅有符合表层的形式,一种在丧葬仪式上的舞蹈还是难登大雅之堂,是不可能具有体育文化学意义的。对此,关于体育文化的大众理解就不得不拿出来剖析一下了。一提到体育文化,始终是绕不过奥林匹克文化的,事实上关于奥林匹克文化,根据现代奥林匹克的创始人顾拜旦的认识,它是不同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奥林匹克竞技文化的。在我国金牌至上的体育价值观引导下,国人理解的体育文化多为以奥林匹克(或类似的竞技比赛)为舞台的竞技文化观。这种文化观是一种强者、强势和强权文化,感召、同化、融合和统摄了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体育文化,剥夺了其他国家和民族体育文化的主势地位,使其沦为“亚体育文化”或“准体育文化”[5]。而事实上,奥林匹克文化是体育文化中的一部分,更是一种教育文化,对身体、生命、个体社会化、价值观、世界观教育的文化。跳撒叶尔嗬也正是以身体活动为载体,以“乐、歌”辅之的展示和传承生命文化观,群体文化观,具有强大的社会功能和效益。
2.1 独特的生死伦理观
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死亡这一自然现象仍是人类没有能支配的永恒主体,而死亡是其中最肯定的事件。面对死亡,恐惧如影随形的伴随着人类的心路历程。正如古希腊哲学家爱比克泰德说:“可怕的事件不是死亡,而是对死亡的恐惧。[6]”面对这一窘境,处于深山密林,过着与世隔绝的土家族人吸收了庄子及其道家的生命哲学观,以颠倒的逻辑思维,对死亡和死亡的恐惧进行了另类的诠释。
面对个体生命的终极选择死亡,“土家人却能以坦然、乐观的心态对待死亡,以放纵激情的方式化解死亡带给人们的哀伤”[7]。在土家人看来,老人去世不是悲事,老人的正常死亡应当看作是走“顺头路”,有生亦有死,正如植物的荣枯一样。对个体而言,个体的解体虽是一种最高的痛苦,然而这种痛苦却是解除衰老的躯体在生理苦难上的根源,是个体的一种超脱,是生命向另一存在形式的转换,获得了与世界本体融合的最高的欢乐;对死者的亲属而言,丧失亲人的哀痛比起老人苦难的超脱是不足为重的;对氏族群体而言,老人的去世对氏族的生存利益是有益的,为氏族的生存繁衍减轻了负担,节省了资源,留下了空间。因此土家人欢欢喜喜办丧事,热热闹闹陪亡人,哀而不伤,尽情歌舞。土家人对生死的超脱认识,对老人有着超脱苦难的关心体贴,对氏族利益的根本自觉维护,丧事习俗“撒叶尔嗬”才强烈而独特的体现出一种热爱生命,渴望幸福平安,积极进取的执着乐观精神,充分反映了土家人生命意识的极度张扬[8]。
土家族在清初的改土归流完成后受到汉文化、佛教文化的强烈冲击;近代受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侵蚀;建国后又受到历次政治运动的影响,但跳撒叶尔嗬这种反映人类永恒的死亡现象;表达土家人对生命流动的真切认识,对生命律动的张扬,对死亡的洒脱;具有“准宗教”功能的信仰与理性结合的艺术形式,辅以高山峡谷的屏保,经受住了各种文化的冲击、侵蚀和同化,反而逐步为世人认同和称赞。
2.2 强烈的群体意识观
恶劣的生存环境、低下的生产力使土家人认识到群体的力量是群体生命延续的强力保障,氏族的兴盛发展依赖于氏族成员的团结协作,“群体的生命力可战胜脱离于群体的个体死亡的恐惧。[9]”这种原始的群体意识在土家人之间积淀、散播,土家人借助丧葬的特殊时空场所,将这种原始群体生命意识极度宣扬出来,对亡者是一种慰籍,对生者是一种警示。土家人云“人死众人哀,不请自然来”,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土家人对群体和个体之间关系的认识,个体是群体的构成单位,当一个个体消亡后,群体的力量就相应的削弱,故而人死众人哀;二是土家人群体意识的流露,每个以土家人都自觉的认识到死者是群体的一分子,自己也是群体的一分子,对群体的认同感和使命感,使得大家不请自然来。“半夜听到丧鼓响,脚板心就发痒,不管南方和北方,你是南方我要去,你是北方我要行,跳一夜丧鼓送人情”,土家村落有老人过世,除了亲戚朋友必到之外,同村同寨的无亲无故之人,甚至是与死者生前有嫌隙的人也会自觉到场,跳一夜丧舞化解以往的嫌隙。在这里,群体内部间的矛盾,以丧舞为表达形式,最终为群体意识所消解。“打不起豆腐送不起礼,打一夜丧鼓送人情”,跳丧并不以钱财为重,更重要的是传递一份浓浓的感情,表现一份分担变故的关心体贴,传达一种同舟共济的信念。而这种意识的传递,又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精神纽带,有效地加强了联系,沟通了情感,增进了团结。土家老人走了“顺头路”,年轻人继承重任,民族的生命得以一代一代传承延续[10]。
2.3 诙谐的狂欢仪式(土家人的诙谐:跳“撒叶尔嗬”)
狂欢精神指群众性的文化活动中表现出的突破一般社会规范的非理性精神,表现为纵欲的、粗放的、显示人的自然本性的行为方式[11]。西方的狂欢精神是酒神狄俄尼索斯的真正面目,是“个体化原理崩溃之时从人的最内在的基础,即天性中升起的充满狂幸福的狂喜”[12],它具有破坏性、娱乐性、戏谑性、民间性、自发性等多样性质,展示感性美,打破既定秩序、藐视权威、解构理性。我国的主流狂欢文化,在强力的封建社会体制下,笼罩着浓厚的理性帷幕。如我国的元宵节,它由汉明帝在宫廷寺院“燃灯表佛”演变而来,具有强烈的官方性和规范性。其余的主流狂欢文化形态大抵也如此,或具有封建宗教伦理性、或具有宗教规范性、或是宗教程序仪式性。
土家跳撒叶尔嗬的狂欢文化却是介于二者之间,即是理性认识和感性表达的结合。对生命观的独特认识,才有了土家人在丧堂上的狂歌热舞,这是一种理性的认识,却用了颠倒逻辑思维的表达形式。对封建皇权给与的压抑,封建伦理纲常等观念强加的束缚,土家人用自己精神的自由权、表达的诙谐和戏谑权,统统将其瓦解。在丧葬仪式中,借助人死为大的特殊权利,土家人消解了象征最高权力的皇权。跳撒叶尔嗬唱词中直白无疑的唱道“皇帝佬儿是我的放牛的”,显然,这里借贬低皇帝的方式消解了他的权威,官方秩序中永恒的、不可变动的、绝对的规则瞬间被摧毁[13]。“二字下来二条龙,二位将军显神通,差他神仙去破岭,杀死皇帝国丈人”。在这首唱词中,神权和皇权则都被颠覆了。
“丧堂打鼓有个窍,不打风流不热闹”,关于在丧堂上出现的许多火辣且直白的情爱唱词,生动且赤裸的性爱模拟动作,有人认为是一种文化糟粕,有人从生存繁衍的角度肯定它。考虑到土家人独特生死观,回归到这种文化现象形成的原初态,我们更为确切的肯定它的贞节性。土家族改土归流之前,男女耕作出入同行,无拘无束,道途相遇以歌舞为媒,这完全反映了土家人原始的自由和平等,但随着封建礼教统治力的加强,这些行为又被贴上了有伤风化的标签,受到压制和打击。为了对抗这种精神和行为上的压迫,土家人的诙谐创造力发挥了它的能量,在丧堂上大唱情歌,狂跳热舞。
3 动力——继承与创新
虽然具有身体运动和表现、传承独特的生命观、群体意识观,同时具有狂欢性、仪式性的体育文化学上的基本表现形态,但它是丧葬文化,还不是一种体育文化。由于它满足了体育文化学上的一些特定条件,因此它又具有了开发成民间体育项目的潜质。
2004年7月,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县委、县政府决定申报跳撒叶尔嗬为国家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但怎样在尊重千百年来形成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冲破人们的忌讳思维,扬长避短,大胆地把它从死人棺材那里解放出来,将‘死’变‘活’,改变这种死了人才能跳舞的状况,使之成为适应现代生活和人民群众的需要,扩大接受对象[14],是将跳撒叶尔嗬开发成民间体育项目的关键。
为此,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文化馆馆长——舞蹈艺术家覃发池为主的舞蹈工作者,在对民间跳丧进行多次深入的收集、整理、改革、创新之后,赋予了它新的力度和时代的旋律,成功地把这种民间舞蹈改编成了“巴山舞”[14]。新改编的“巴山舞”保留了留了原始“跳丧舞”鲜明的节奏和有特色的鼓点,增加了弦乐伴奏,选用人民群众所熟悉的与舞蹈情绪相吻合的山歌、民歌、小调为基础,加以发展继承与创新是“跳丧舞”变为民间体育项目的不竭动力,在其原始素材上,淡化其浓厚的祭祀成分,保留其身体动作律的粗犷、乐点的跳荡性、歌词的古朴,保留其场面的狂欢性、参与的集体性,利用其舞蹈语汇,改编成易学易练的,自娱性强的集体舞和个人舞[15]。以覃发池为主的舞蹈工作者经过不懈的努力,开发出了 “半边月”、“靠身子”、“喜鹊登枝”、“双龙摆尾”、“百凤朝阳”、“风摆柳”、“巴山摇”等系列舞蹈。
这些脱胎于跳撒叶尔嗬的巴山舞一经问世,便受到了关注,逐渐为世人熟悉,称颂和学习。1979年巴山舞在长阳乐园乡首届“七一文化节”登台表演之后,便迅速成为长阳人民喜爱的舞蹈,并在长阳周边地区产生了巨大影响。1985年,湖北电影制片厂摄制了电影《锦绣长阳》,巴山舞走上了银幕。1991年,巴山舞作为表演项目参加了在广西南宁举办的全国第四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1995年6月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东方之子》栏目播出了对覃发池的专访。1997年,巴山舞演出团体应邀赴香港演出,“美国之音”资深记者周幼康跟踪向全世界报道,中国著名舞蹈家覃作光称其为 “东方迪斯科”,欢乐的“毕兹卡”引起了港人的浓厚兴趣。2000年,长阳巴山舞荣获第十界全国“群星奖”广场舞蹈金奖。2001年4月,在大三峡夷陵广场举行的“国际龙舟拉力赛”闭幕式上,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明、副局长张发强与土家儿女一道欢畅的跳起了巴山舞。张发强同时指出巴山舞是一种很好的广场集体舞,音乐节奏明快,简单易学,男女老少都适合,是一种很好的健身方式。同年,“中国长阳巴山舞获得国家注册商标,被国家体育总局确定为“全国十大健身舞”之一。2005年,巴山舞健身项目在国家体育总局举办的全国民族民间全民健身项目的评选活动中,荣获一等奖。
经过20多年的创新发展,巴山舞不断在省内及全国文艺表演中获奖,巴山舞日益大众化,学跳巴山舞的群众也越来越多,其现已成为长阳县、宜昌市全民健身的热门项目[16]。同时,巴山舞在朝更大的目标迈进,湖北省体育局加大推广力度,力争使巴山舞成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表演项目。
现在,巴山舞在土家民间传统的“跳撒叶尔嗬”的基础上,创新发展成由八套乐曲和舞蹈组成的一个系列舞蹈。至此,通过去祭祀性、去迷信成分,升华其身体运动形式、高扬其文化精髓,跳撒叶尔嗬完全脱胎换骨,成为了真正的具有体育文化学意义上的一种民族民间健身运动项目。
4 推广——当地农村体育的出路
全民健身,建设新农村等方针政策的提出,为我国农村体育的发展带来了机遇。我国农村的现实情况却是生产力低下,经济水平不高,居住较分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给需要付出大量时间和金钱的现代健身项目在农村的推广设置了几乎是不可逾越的屏障。而从跳丧舞到巴山舞的成功,却为农村体育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可供参考的模式。
巴山舞带着古朴的身体动作形式,独特的文化理念,豪迈的时代气息,已经在农家院舍、校园工厂、广场社区和节日盛会中扎根。湖北宜昌市成立了巴山舞推广小组,组织了多期巴山舞培训工作,一大批来之全省各县、市的学员拿到了培训资格证,这标志着巴山舞从宜昌走向全省目标的初步实现。组织推广工作的有序顺利开展,使巴山舞在体育文化学上的中层形态得到了体现。中层文化形态是体育体制,包括体育的社会组织、教学训练、管理等。巴山舞在这些方面的形态逐步显现,如长阳县的中小学已经用巴山舞代替了广播体操,获得了预期的效果。在中小学推广巴山舞的构思已经逐步在宜昌市全市范围逐步实施,全市各大中小学及幼儿园都在结合学的资源开展巴山舞练习,受到了师生的欢迎。社会其他单位部门也在积极组织推广该项运动,如宜昌市妇联曾经举办过的“跳起巴山迎三八”活动,茂名学院离退休教师办起了巴山舞学习班,各乡镇定期举办巴山舞比赛等。
巴山舞脱胎于当地的民俗舞蹈,具有群众基础和文化认同感,同时它打破了跳丧舞的时空结构,赋予其时代因子,使之成为能够迅速为当地广大群众接受的健身舞。巴山舞的成功为我国边远地区农村健身项目的开展提供了一种可供借鉴的模式,它以当地的民俗舞蹈为基础,吸收了传统文化的精髓,在再创造过程中,它立足农村的现实情况,基本避免了农村体育开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经济的发展水平,受制于现代健身项目所必需的场地、器材等基础设施的要求,改变了跳丧舞只能在特殊的丧葬时间和地域进行的限制。总的说来,它是来源于群众,以满足新时代群众需要而创新,再回馈给群众。这也是各地区民间健身项目获得持续健康发展的有益的思路,是丰富我国民间体育文化的一条出路。
5 结语
从跳撒叶尔嗬到巴山舞,从丧堂时空到闲暇健身、到节日狂欢,从生活生产劳动模拟到具有健身、艺术性质的舞蹈,从祭祀到大众化,跳丧舞走出了一条如同它自身一样神秘但不乏精彩的路。至此,跳丧舞在体育文化学意义上的形态已经完全展露,完成了它从蛹到蝶的生命质的转变。同时,它的成功还为我国农村地区开展推广民间健身项目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样板。
[1] 体育概论教材编写组.体育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
[2] 董 璐.巴风土韵——土家文化源流解析[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3] 《土家族百年实录》编委会.土家族百年实录[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
[4] 蒋在爽.土家族巴山舞练习对老年女性BMI及血脂的影响[J].中国运动医学杂志,2003(6).
[5] 卢元镇.中国体育文化忧思录[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6.
[6] 段德智.死亡的哲学[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1996.
[7] 宋仕平.鄂西土家族跳丧习俗的文化意蕴[J].青海社会科学,2005(3).
[8] 曹 毅.土家族民间文化散论[M].北京:中央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9] 余 霞.土家人的诙谐:跳“撒尔嗬”——对土家族丧仪之狂欢性的解读[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社科版),2001(4).
[10]裴 亮.鄂西土家族“跳丧舞”的文化解读[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5).
[11] 赵世瑜.中国传统庙会中的狂欢精神[J].中国社会科学,1996(1).
[12] 尼 采,周国平.悲剧的诞生[M].北京:三联书店,1986.
[13]余 霞.土家人的诙谐:跳“撒尔嗬”——对土家族丧仪之狂欢性的解读[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社科版),2001(4).
[14]张 颖.对长阳土家族“巴山舞”深层开发的思考[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6).
[15]长阳县概况编写组.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概况[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9.
[16]陈绍艳.对湖北省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巴山舞的研究[J].湖北体育科技,20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