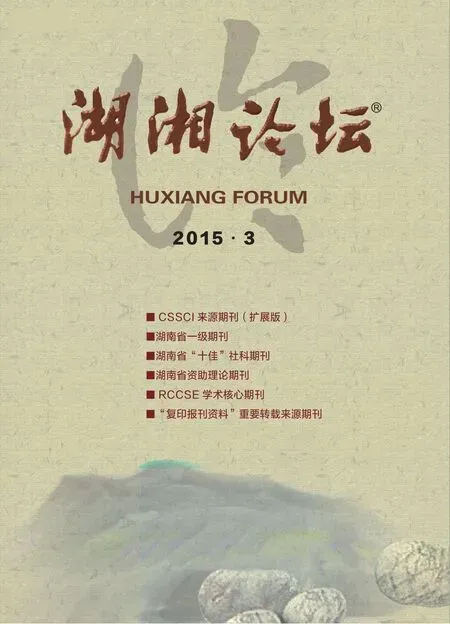论中国苏区社会关系的变革*
谢开贤
(湖南医药学院,湖南 怀化 418000)
近代中国社会关系尤其是宗族关系严重地制约着广大工农群众革命的积极性。不打破旧式社会关系,工农群众就无法摆脱家族影响,走出家门,投入革命洪流之中,继而中国共产党、苏维埃政府以及工农红军也就得不到广大民众的支持。为消除旧式社会关系的消极影响,推进革命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来到苏区后,领导苏区人民采取一系列措施,实现了苏区社会关系的根本变革,使苏区变成了“一个自由的光明新天地”。[1]p329
一、民众之间由宗族关系转向阶级关系
以家庭为本位,由家庭而家族,由家族而宗族,宗族有宗法,尊卑有序,等级森严,这是中国旧社会的重要特征。在这样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处在一定的家族或宗族之中,各种社会关系都宗族化了。土地革命之前,苏维埃所处区域莫不如此。正如毛泽东所感慨的:“无论哪一县,封建的家族组织十分普遍,多是一姓一个村子,或一姓几个村子,……家族主义不能战胜。”[2]p69家族拥有很多公田。公田年年收租。收租所得除祭祖用费外,大多数年份会有剩余,便把剩余积蓄起来。积蓄的方式不是用稻谷等实物积蓄,而是每年把多余的谷子卖给贫民,再把钱存起来。积存若干年后,聚得一笔大款。再用这笔款去购买田地。如此以来,这一家族的公田就日益增多。
以公田经济为基础,家族发挥着多种功能。其一,维护本族利益。家族的首要功能即是维护本族的利益与声望,为其成员提供最大限度的保护。其二,协调宗族矛盾。为和谐乡村宗族之间关系,族长的职责之一即是协调本族与他族的矛盾。其三,组织祭祀活动。家族时常利用族产举办一些祭祀活动,如瑞金“春夏宴集,大享族人,庖丁专司各族祭飨及各族子弟毕业宴会者,竟多至二干余人”[3]p62-63。通过这些活动,族众的认同感提升,宗族的凝聚力增强。其四,组织慈善活动。宗族常利用族产周济族众,不仅养赡“族之鳏寡孤独”,而且会用少量的收获来接济本族的穷人,以公堂祠堂的公款鼓励和资助本族子弟读书等。因此农民的家族观念特别浓厚,对于本族豪绅地主富农表示妥协。这样,民众之间甚至是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关系都蒙上了一层温情的宗亲面纱。他们往往以血缘宗亲关系作为立身行事的依据。以致各地的游击队、赤卫队,都各自保守一隅,不愿打自家的地主,而是时常过界打土豪,即甲地到乙地去捉土豪,乙地到甲地去打土豪等,并不时为此引起两地的纠纷。“如中鹄,白沙与纯化东固之纠纷……”[4]p339。
宗族虽具有协调矛盾、培养子弟和赡养老人等积极作用,但根深蒂固的宗族观念常使农民只重血亲,不分敌我,甚至保护本族豪绅地主,严重阻碍了土地革命的进行。因此,要取得革命的胜利,作为前提必须剔除民众的宗族观念,改造宗族组织,使其为苏维埃革命服务。应此要求,党与苏维埃政府领导苏区人民从经济、政治和思想意识等方面入手对宗族进行了多维消解与改造。
经济上,没收宗族赖以存在的公田。1930年颁布的《苏维埃土地法》明确规定:“须立刻没收……豪绅、地主、祠堂、庙宇、会社、富农之田地、山林、池塘、房屋,归苏维埃政府公有”[5]p366。之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又规定:“一切祠堂庙宇及其他公共土地,苏维埃政府必须力求无条件地交给农民”[5]p371。公田的没收,瓦解了宗族存在的经济基础,消除了宗族对族众的经济吸引力。
政治上,剥夺宗族首领参政议政的权利。宗族首领即为一族之长,一般由在族内拥有较大影响力的豪绅地主担任,他们理所当然应该成为政治上的打击对象。1930年初的《闽西工农兵代表会(苏维埃)代表选举条例》规定:城乡绅董族长地保等以及他们的家属一律没有选举和被选举之权。政治上的打击,使族长威信扫地,丧失了原有的影响力。
思想意识上,用阶级观念取代宗族意识。1930年中国共产党指出,随着历史的发展,氏族或家族已经阶级化,家族关系掩盖了“本族大人物”对家族一般成员的剥削。氏族或家族土地的收入均归“本族大人物”所占有。引导群众认识到乡村中充任族长的地主豪绅,他们堂而皇之地借家族公事名义聚集田产与收取地租,同时趁机将地租的绝大部分收入自己的囊中,实质上把家族公田变成了他们的私有财产,他们仍是家族一般成员的阶级敌人,表面上的宗亲关系掩盖不了其实质上的阶级剥削和压迫。基于此,苏区“提高群众对于豪绅、地主、富农的阶级仇恨”[6]p176,发动本地本族的贫苦工农,去冲击、打倒本地本族的地主豪绅,做到“打土豪劣绅不分亲疏一律革命”[7]p716。号召即使是“我们的朋友、亲戚,甚至父、子、兄、弟如果反革命,就应杀死他”[8]p156。这样,在革命的冲击下,苏区工农群众打破了与地主豪绅和平共处的现象,极大地削弱了宗族观念,阶级观念开始取而代之,人们更多的从阶级角度而不是从宗族角度思考、解决问题,原有的宗族关系日趋淡化,阶级关系逐渐成为苏区社会关系的主流。
二、党政军群之间形成新型合作关系
在国民党统治下,党政军群关系是一种剥削与被剥削、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正如杨克敏在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中所说,国民党军队“见了曾经割据了的区域内的民众,不分皂白,极残酷的见了就捉,捉了就杀,见东西就抢,见房子就烧,……反之反军所到之处,粮饷需索,悉取穷苦的工农,拉夫掳掠在所不免”[4]p16。而加入国民党需交钱一元,不加入者则视为共匪,同时逼迫人们缴纳各种捐税,人们稍有怠慢,国民党则露出狰狞的面貌,白区民众不管是贫苦工农,还是小资产者对此都深感痛苦,这是国民党反动派不可狡辩的事实。毛泽东也指出,当苏维埃所辖区域原来处在国民党统治时,工人简直是雇主的劳动机器,他们工作时间长,待遇微薄,劳动条件差,而且他们的地位与权益没有任何法律保障。而农民的状况则更惨。其结果是地主与富农掌控着大量的土地,而绝大多数贫农没有土地,他们处于求生不得和求死不能的悲惨境遇。
当共产党来到苏区后,旧有的国民党统治下的党政军群关系一扫而光,而新型的平等、合作、和谐的关系逐渐形成。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苏区党群之间。中国共产党将“改良群众生活”视为当时两大任务之一,因而特别关心群众疾苦,殚精竭虑地帮助群众解决“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2]p136-137,正因如此,在苏区群众看来,中国共产党是他们根本利益的争取者和守护者,因而真诚地拥护与欢迎共产党。当时,很多工农群众自发地到处找共产党,主动地张贴诸如“拥护中国共产党”、“推翻反动的国民党政权”之类的标语,这种做法一时成了苏区群众的家常之举。在对敌斗争中,即使有人不幸牺牲了,群众也不会怨恨共产党,在党与苏维埃政府的帮助下,他们收埋好被打死的家属,重新建好被白匪烧掉的房子。他们只会从心底里更加支持与拥护共产党和红军,同时更加憎恶国民党反动派。
其二,苏区政群之间。苏维埃政府与群众之间形成了一种水乳交融的关系。经济上,当全中国卷入经济浩劫,数万万民众陷入饥寒交迫的困难之中时,苏维埃政府仍在“为了革命战争,为了民众利益,认真的进行经济建设”[1]P328,政治上,苏维埃政权赋予一切被剥削、被压迫的劳苦民众以选举与被选举之权,苏区女子也获得了与男子同等的选举权利,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文化上,苏维埃政府实行革命的文化教育制度,剥夺了地主豪绅阶级在文化教育方面的特权,赋予了工农群众充分的文化教育权利,砸碎了反动统治阶级强加在工农群众身上的精神枷锁,创造了属于工农群众的苏维埃文化。不仅如此,为了进一步巩固工农民主政权,苏维埃还发动工农群众积极监督政府工作人员,使每个革命群众能够随时检举苏维埃工作人员的缺点与错误。在苏维埃政府中如果发现有贪污腐化与官僚主义份子,一般群众可以立即检举他们,苏维埃政府则须立即惩办,让他们绝无藏身之所。
第三,苏区军民之间。红军将士经常无偿地帮助群众。譬如保护与指导群众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帮农民兴修水利、插秧打禾等,不仅不要工钱,甚至连农民的饭也不吃。红军将士人人都坚守“上门板,捆谷草,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买卖要公平,说话要和气,窝屎要毛坑,不抄白军士兵的腰包”[4]P401等八项注意。而广大群众也是全身心地帮助与拥护红军,“群众对扩大红军,非常热烈的拥护与参加,各地举行以送红军去前方,优待红军家属(农民替红军士兵官伕家属作田……)三五一伴,几十名一伴,时常到苏维埃政府来请求到前方去的,到处都有。”[4]P351在很多地方,工农群众潮水一般地涌进红军中去。比如江西省长冈乡,十六岁至四十五岁的男子共四百零七人,其中当红军做工作的有三百二十人,留在家中的八十七人,即干革命工作的占总数的百分之八十。[1]P304这样,通过亲密无间的相互支持与帮助,军民之间结成了一种生死与共的鱼水关系。
三、男女之间由压迫依附转向平等独立
在旧社会,中国一直是男尊女卑,女性被压制,沦为男性的附属物。土地革命之前,苏区也是如此。在家庭中,女性除要受“政权”、“神权”、“族权”三大绳索束缚外,还受到“夫权”的压迫。正如民谣所说“马有笼头猪有圈,婆娘有个男子汉”[9]p223。相比之下,女子所受的劳苦比男子所受的更多、更厉害,“除助男人出去耕田外,他回家要做饭,及家里其他一切事情”[10]p12。但作为封建男子经济的附属品,女子没有政治地位与人身自由,她们可以说是男子的农奴。比如在赣西南地区,男人做事回来或要购点好菜或买点酒喝,“女子是没有吃的,并且……统统没有资格上桌吃饭的,其余穿衣方面,什么一切都比较男人要苦点。”[10]p12
而使女性最为痛苦的是当时的包办、买卖婚姻和童养媳制度。这一婚姻制度,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不人道、最无人性的制度。在此制度下,妇女象商品一样任人买卖,当时农村妇女有百分之八十的被卖去当童养媳或婢女。而被卖去的妇女,在新家中地位极低,只能拼命做事和生育子女。但假如生多了女孩,还会遭到夫家额外的歧视和虐待。同时,翁姑与丈夫等认为是花钱买来的媳妇,为其家所有,可以对她们随意打骂和欺凌。由此可见,在土地革命之前,女性毫无自主自由可言,男女之间的关系总体上是一种压迫歧视和依附顺从的关系。
男女之间的这种旧式关系极大地限制了女子革命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要调动广大妇女的革命积极性,就必须革除旧式男女关系,打破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束缚,满足妇女的政治经济文化诉求。在党的领导下,苏维埃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实现和保护了苏区妇女的根本权益,使苏区男女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革。
经济方面,苏区立法保障妇女平等参与土地分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规定:“被没收的土地,经过苏维埃由贫农与中农实行分配。……雇农、苦力、劳动农民,均不分男女,同样有分配土地的权限。”[5]p370这为苏区妇女获取与男子同样的一块份地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障,而土地的获得继而为妇女的平等独立奠定了物质基础。
政治方面,苏区妇女获得了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经济上的独立带来了政治上的觉醒。苏区妇女在政治方面有了更多的诉求。她们的诉求得到了苏维埃政府的充分尊重和保护。1931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境内的一切工农和其他劳动群众、红军及其家属,不分性别,在苏维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只要年龄在十六岁以上都享有选举和被选举之权,“有权选派代表掌握政权的管理”[5]p6。这为妇女在政治上不再依附于男子提供了根本保障。
文化方面,苏区妇女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教育权利。一方面,妇女有权受教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是苏维埃政权的目的之一,同时实行各种办法,为妇女摆脱家务的束缚、切实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创造条件,使她们能够真正融入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另一方面,在法律的保障下,苏区妇女开始主持教育,享受了作为教育主体的权利。在苏区,很大一批妇女从受教育者转为教育者,从教育的客体转为教育的主体,担任着一批小学与夜校的管理角色,为促进妇女独立自主做出了贡献。
婚姻方面,妇女由被包办转向自主,由依附转为平等独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令规定:“男女婚姻,以自由为原则,废除一切封建的包办强迫和买卖的婚姻制度,禁止童养媳”,“男女结婚,须双方同意”,同时“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即行离婚”[5]p232等。这些法令确立了妇女在婚姻中的自由权利,为避免妇女在婚姻中沦为男子的附属物提供了法律保障。
通过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一系列的努力,苏区妇女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她们在经济、政治、文化及婚姻上,都与男子一样。妇女分得了属于自己的一块份地,享有了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开始在苏维埃政府中做事。她们第一次走进学校大门,参加夜学、扫盲班、识字班,取得受教育权;她们也第一次有了婚姻自主权,能够自由地“找爱人”,自由地离婚。这样,苏区“消灭了一切男女不平等的痕迹。”[11]p376女子“再不做奴隶,也不是‘货物’,更不是‘玩意儿’,她们已经是独立自由的人了。”[11]p376她们与男子之间原有的压迫依附关系开始消解,逐步确立起一种新型的平等独立关系。
总之,中国共产党来到苏区后,领导苏区人民打土豪、分田地、搞选举、办教育、废陋习、立新规,根本变革了苏区社会关系,使苏区民众从旧式社会关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空前激发了他们的革命热情,极大地促进了革命发展。
[1]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Z].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
[2]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万振凡.弹性结构与传统乡村社会变迁--以1927-1937年江西农村革命与改良冲击为例[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8.
[4]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Z].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
[5]厦门大学法律系,福建省档案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法律文件选编[Z].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
[6]湖南省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贵州省档案馆,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党史办公室.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汇集[Z].(内部资料,无出版社),1984.
[7]湖南省财政厅.湘鄂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摘编[Z].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
[8]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近代中国的乡村社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9]成都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川陕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史[M].成都市: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
[10]江西省妇女联合会,江西省档案馆.江西苏区妇女运动史料选编[Z].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11]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7-1937)[Z].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